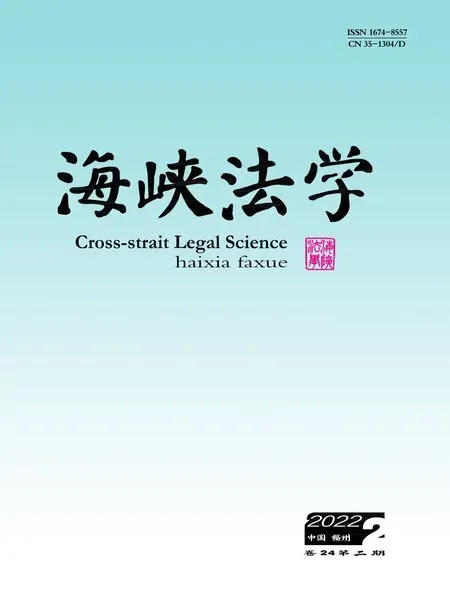国际商事仲裁实体法适用的理论误区与归正
王一栋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当事双方通常在合同中约定了仲裁事项,却未具体选择解决实体争议所适用的法律,这种情形并不少见。目前主要存在以下四种解决方式:(1)由当事人协议选择特定准据法;(2)强制适用CISG;(3)由仲裁庭自主选择实体法。(4)其他用以弥补漏洞的习惯性做法。①孙法柏、宋春霞:《论CISG项下习惯做法的内涵及其认定》,载《海峡法学》2015年第1期,第45~54页。需要注意的是,这四种解决方式原则上具有程序的互斥性,当事人不得重复选择,选择了某一种解决方式意味着排除了其他方式。因此,本文将这种只能在多项并行的实体法律规则中间择一作为解决实体争议准据法的行为,称之为“排除规则”。同时,由于双方约定了仲裁事项,仲裁条款生效时自始排除了法院的管辖权,并赋予相关仲裁庭以管辖权。从法律程序上,只有第(1)种解决方式赋予了当事方协商选择的权利,若当事方未选择或无法协商确定准据法时,根据仲裁程序,由仲裁庭“代替”当事方选择解决实体争议所适用的准据法。
一、CISG的“硬法”属性并不等同于“若符合,即适用”
在国际商事仲裁中,当事人的合意是仲裁程序的源头和基础。因此,当事人自始且当然有权选择仲裁事项本身所适用的法律,无论实体法还是程序法。这不仅是仲裁程序区别于诉讼程序“便利原则”的不同之处,亦是当事人基于仲裁协议的契约属性而享有的契约自由原则的体现。②肖永平主编:《中国仲裁法教程》,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1页。当事人一旦选定准据法,仲裁庭就应当适用,且同时排除其他法律规则的适用,这其中当然包含《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以下简称为CISG)。然而,与诸如《国际商事合同通则》《欧洲合同法原则》等国际商事合同领域的示范性“软法”不同,CISG自1980年生效始就并非将模糊性、妥协性和可替代性作为立法宗旨,①刘瑛:《论排除适用条款与CISG的适用》,载《政法论丛》2019年第4期,第69页。其第1条第1款开宗明义地规定:“本公约适用于营业地在不同国家的当事人之间所订立的货物销售合同:(a)如果这些国家都是缔约国;或者(b)如果根据国际私法规则导致适用某一缔约国法律。”更为关键的是,成立CISG的基础性条约——1980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6条和第27条规定,条约对各缔约国均有约束力,各缔约国不得以履行国内法为由拒绝履行公约规定。与此相对应的是,适用CISG的例外规定②此处仅指满足CISG所规定之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形式要件而不适用CISG的情形,不包括不符合CISG调整范围的合同类型,例如CISG第2-5条。仅出现在CISG第6条③CISG第6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协商不适用公约或协商减损公约的规定或法律效力。。从体系上看,符合CISG第1条第1款的合同均应强制性适用CISG,即使第6条存在当事人通过协商排除CISG的适用,也是在合同符合CISG第1条第1款的形式要件后借由当事人的合意加以修正,本质上依然无法改变CISG“国际硬法”的本质。④刘瑛:《论排除适用条款与CISG的适用》,载《政法论丛》2019年第4期,第69页。既然属于国际硬法,当事人的协商选择权与公约的强制适用规则相冲突时,何者具有更高的优先性,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为此,本文特意考察了与CISG同为国际买卖合同通用公约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1.2条对通则的适用情形作出了规定。其中“当事人协商适用”被置于所有适用情形的第1款,而包含“当事人未选择准据法”在内的“其他适用情形”则置于第2款中,从立法体例上优先保护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立法宗旨十分明显。而在CISG中,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法律优先级显然不同。首先,CISG允许当事人排除适用CISG,但这一排除规则本身就置于CISG之下,从立法逻辑上应当认定为CISG的排除规则属于CISG适用规则的例外。换言之,若没有第6条的规定或当事人未加排除,各国仲裁庭均应自动适用CISG。其次,从法条编排顺序上,由于第1-5条均规定了“非基于当事人选择的”适用与不适用CISG的不同情形,因此,仲裁庭应当首先考察涉案合同是否属于CISG第1-5条的排除适用情形,最后考察的才是第6条当事人合意。实践案例也明确支持了这种适用顺序。⑤Appellate Court(OLG)Oldenburg,Germany,December 20,2007,availableat http://cisgw3.law.pace.edu/cases/071220gl.html.,下载日期:2021年5月16日。这种鲜明的法律程序与包括《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在内的“软法”具有显著区别。因而,若某部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符合CISG第1条的构成要件,则应当适用CISG的实体规则,除非当事人“明确而具体地”⑥Hanwha Corporation v.Cedar Petrochemicals,Inc.,U.S.District Court,Southern District of New York,United States,January 11,2011,http://cisgw3.law.pace.edU/cases/110118ul.html,http://www.unilex.info/case.cfm?pid=l&do=case&id=1583&step=Abstract.,下载日期:2021年5月16日。另参见(2013)穗中法民四终字第91号。排除CISG的适用。但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所提到的关于CISG强制适用规则,仅包含法院管辖的情形,即国际强行法的“硬法”属性体现在规制同样具有强制性的国家司法主权体系中,而对于奉行当事人意思自治高于一般强行法的商事仲裁领域,CISG所谓的“硬法”属性就没有显著的法律意义,其仅在当事人未合意排除且符合其适用条件时才得以“强制适用”。⑦韩健:《CISG在中国国际商事仲裁中的适用》,载《武大国际法评论》2008年第2期,第274~276页。
事实上,这种由当事人约定排斥CISG的适用并非仅包含“明确而具体”的唯一路径。包括《维也纳公约》外交会议主席在内的多国代表均对“默示约定”的方式达成共识,①Martin F.Koehler,Guo Yujun.TheAcceptanceof the Unified SalesLaw(CISG)in Different Legal Systems[J].Pace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2008,20.这种“默示约定”并非是非原则性的,它应当得到程序上的认可,与“明确而具体”的排除约定具有相同的法律地位。默示约定甚至可以发生在终审判决前的任何一个阶段。②Ingeborg Schwenzer and Christopher Kee,Global SalesLaw—Theoryand Practice.ALLSchwenzer and Lisa Spagnolo.TowanlsUniformity:The2nd Annual MAA Schlechtriem CISG Conference[C].The Hague:Eleven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2011.另参见Stefan Vogenauer.Oxford Civil Justice Survey-Civil Justice Systems in Europe:Implications for Choice of Forum and Choice of Contract Law[EB/OL].http://denning.law.ox.ac.uk/iecl/pdfs/Oxford%20Civil%20Justice%20Survey%20-%20Summary%20of%20Results,%20Final.pdf,下载日期:2017年5月16日。一般来说,符合商事惯例和当事人既有交易习惯的默示行为是被准许的,但仅仅因当事人之间未作相反意思表示就推断当事人对排除CISG达成共识,是值得推敲的。③JorgePlazaOviedov.Sociedad AgricolaSector Limitada,SupremeCourtof Chile,September22,2008,availableathttp://cisgw3Jaw.pace,edu/cases/080922ch.html.从法理上分析,这种“默示排除”应近似于“消极选择”,即当事人对其他准据法的选择从而排除CISG的适用。从CISG第1条第1款(b)项“依据国际私法规则导致适用某一缔约国法律”可以合理推断出,若当事人之选择依据国际私法规则转向了某一非缔约国法律,或者转向了某一缔约国的特定实体法,则均可排除CISG的适用。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等国判例均采此观点。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在加入CISG时对第1条第1款(b)项提出了保留,因此依据国际私法规则导致适用中国法律或其他缔约国法律时,CISG并非当然适用。由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允许各国对具体内容提出保留,中国对此项提出的保留构成了CISG内容适用的先决条件,CISG第1条关于适用CISG的原则性规定应基于中国保留的前提予以适用。④有学者认为,非本国法对于本国法院和当事人而言,属于介于法律和事实之间的一种状态。参见董金鑫:《国际私法视野下外国法的性质和证明──处于法律和事实之间》,载《海峡法学》2011年第4期,第89~96页。这种法律适用的顺序同样属于强制性规范,且位阶高于CISG条文内容的规定顺序。对于国际商事仲裁而言,该法律适用先后顺序亦当然适用,即由中国籍当事人与非中国籍(无论是否是CISG缔约国)当事人签订的仲裁协议,首先应当排除CISG的当然适用,除非双方当事人合意选择CISG,才能有效破除中国对CISG第1条第1款(b)项保留所带来的程序限制。
若CISG被当事人排除适用,实体法的选择问题依然可由当事人协商确定。在国际买卖合同中,国际普遍立法例中均承认双方当事人可以选择原被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合同履行地和合同签订地等多个连接点所在地国的法律作为准据法。由于仲裁更加强调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在国际商事仲裁中,当事人甚至可以约定与合同相关的其他连接点所在地国法律,甚至是与合同无关的第三国法律。
综上所述,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通过合意以排除适用CISG的法律要件应当为:(1)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明确而具体地”排除CISG的适用。这是仲裁当事人意思自治对抗强制法律适用的体现,但明确具体排除CISG并不要求当事人同时指明希望适用的法律。(2)当事人虽未明确具体约定排除适用但也未同意适用CISG的情形下,通过商事惯例及双方在先的交易习惯可以合理推断出当事人默示排除CISG的适用;或者当事人已经明确选择了特定国家的某部具体实体法。(3)当事人虽未明确选择准据法,但根据国际私法的冲突法规则指向了中国法律;或者根据国际私法的冲突法规则将适用CISG其他缔约国的法律。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当事人在此情形下均同意适用⑤但若准据法的确定系当事人事先约定(情形A),而非先经冲突法规范指向特定法律再由当事人对此加以同意(情形B),则不在此限。此处所指的“同意适用”,是指情形B。CISG或仲裁庭裁决适用CISG,也会因对抗我国国家司法主权而归于无效。
二、当事人未排除CISG的适用时,CISG和“最密切联系地”法律的适用不得互相取代
若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当事人未排除适用CISG,CISG是否当然适用?这个问题在CISG本身并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符合CISG第1条规定的国际私法主体,在原则上应当受到CISG的约束;即便为证明系争事项不适用CISG,该证明结论亦应当基于CISG框架内部得出。由此,无论是当事人还是仲裁庭,在决定仲裁事项实体法的权限上都受到了约束。从某种程度上讲,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在生效时,就基本可以确定CISG能否作为准据法得以适用。然而,现代国际私法理论所确定的“最密切联系地原则”对CISG的适用依然存在理论和实践的分歧,也出现了不少法律从业者对二者的混淆和通用。
在国际私法理论发展的早期,各国法律之间互不相同的情形导致当事人适用法律产生了极大的不确定性。为了降低国际私法的不确定性,德国著名法学家萨维尼在19世纪末提出了应当根据法律关系本身的特征以取代机械的“人法”和“物法”来确定法律的适用。①马德才:《论萨维尼的“法律关系本座说”在国际私法发展史上的影响》,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第40~44页。萨维尼所提出的这种基于“法律关系本座”的学说经过演变和发展所形成的“最密切联系地原则”已经为绝大多数立法所采纳,例如1979年《奥地利联邦国际私法法规》第1条②1979年《奥地利联邦国际私法法规》是最早确立最密切联系原则的主权国家成文法。第1条规定:“(一)与外国相连结的事实,在私法上,应依与事实有最强联系的法律裁判。(二)本法规所包括的适用法律的具体规则,均应认为均体现了这一原则。”、1987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第15条③1987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第15条第1款:“根据所有情况,如果案件与本法指定的法律联系并不密切,而与另一法律的联系明显地更为密切时,则可以作为例外,不适用本法所指定的法律。……”、美国《冲突法重述》第188节④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第188节第1款规定:“如果当事人没有选择有效适用的法律,那么……交由与此交易和当事人有最重要关系的州的法律决定。”等。我国1999年《合同法》第126条⑤我国《合同法》第126条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甚至是已经废止的1985年《涉外经济合同法》第5条⑥我国已废止的《涉外经济合同法》第5条规定:“……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均规定了“最密切联系地原则”。而这一准据法原则同样适用于国际商事仲裁。国际商事仲裁庭一般均许可当事人通过“最密切联系地原则”选择案件之准据法。无论是对最密切联系地的理论源头还是各国立法的横向比较进行研究,都不难发现,最密切联系地原则的适用具备如下特征:(1)适用于国际自然人、法人之间的商事活动;(2)适用于当事人事先未约定或约定不明的情形;(3)允许当事人在诉讼和仲裁程序中自由约定。从形式上,采用最密切联系地原则选择准据法和适用CISG具有相似性,但就此认定二者可以互相替代从而混淆法律适用的顺位,是存在理论误区的。
国际商事仲裁独有的私权性和契约性虽然是区别于司法管辖公权性和强制性的典型特征,⑦韩健:《CISG在中国国际商事仲裁中的适用》,载《武大国际法评论》2008年第2期,第278页。但并不意味着国际商事仲裁的准据法也可任由当事人协商确定而不受法律尤其是强行法的干涉。母国均为CISG缔约国的甲乙(其中甲为中国籍)签订了一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若甲乙就履行合同产生争端后提交仲裁,仲裁庭在协商无果后根据仲裁地法律认为适用合同签订地M国(同为CISG缔约国)法律作为解决争端的实体法规则。①如当事人未选择实体法时,在诉讼情形下,法院通常依照法院地的冲突规范选择准据法。而在仲裁情形下,仲裁庭选择法律的方法错综复杂,但依照冲突规范选择准据法是最常用的方法,仲裁庭适用冲突规范有相当大的自由度。由于仲裁庭根据案件自行作出适用法律的裁决属于冲突法规范的范畴,因此根据CISG第1条第1款(b)项的指引,本案仅能适用CISG而非M国法律作为准据法。同时,中国对(b)项提出了保留,本案又存在中国籍当事人,因而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0条和第21条,CISG又不得作为本案的准据法。由于商事仲裁的契约性决定了仲裁庭适用法律的合法基础来自当事人的合意,在当事人未作相反或特定意思表示之前,仲裁庭只得另行确定准据法,且需保证(1)新的准据法所指向的法律不得再度触及上述情形;(2)仲裁地所在国许可仲裁庭不适用“仲裁地法”;以及(3)尽可能降低仲裁的承认与执行地国因仲裁庭未依据仲裁地法作出的裁决而不予承认和执行的法律风险。②宋锡祥、田聪:《“一带一路”视野下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载《海峡法学》2019年第2期,第26~36页。由此不难看出,过分、单一强调保护仲裁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极易造成法律适用和仲裁后续程序的阻碍,徒增仲裁成本,无谓拖长仲裁程序。最佳的处理方式应当是由仲裁庭督促当事人通过明示或默示的方式选择或排除实体法律的适用,既保障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又避开了CISG关于“冲突法规范指引”所带来的两难困境。如果当事人始终无法达成一致,又未对CISG的适用予以排除,则应当由仲裁庭裁决适用CISG作为准据法,即使此项裁决有违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换言之,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应当在悬而未决的情形中视为一种让步和放弃,而CISG的“强行法”特性在此时应当得到充分保障。
因此,“最密切联系地原则”所赋予的国际商事仲裁当事人自主选择实体问题准据法的权利是一种相对“软性”的权利,它事实上受到了诸多因素的限制。除“仲裁地法”理论③即国际商事仲裁当事人可自由选择仲裁实体和程序的准据法,但大多数国家立法中规定该“自由选择”一般不得脱离本国的强行法规定,同时还要承担任意选择所带来的仲裁承认与执行的风险。这是国家主权论所决定的。参见邓瑞平等主编:《国际商事仲裁法学》,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167~168页。对当事人这种自由选择权的限制以外,包括CISG在内的具有“硬法”性质的国际商事法律规范依旧对仲裁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施加了法律选择的限制。这些法律选择上的限制决定了CISG的适用既不属于与案件“最密切联系”的法律,也决定了仲裁当事人对法律的选择与CISG的自动适用规则存在程序的排斥,不得互相取代,除非当事人事先明确选择适用CISG。
三、当事人确定实体法,并不等同于仲裁庭必须接受
伴随现代国际商事仲裁理论的发展,仲裁庭可以分别对仲裁程序和实体问题适用不同法律的做法,几乎已经不存在争议。对于仲裁实体法的选择问题,各国大多置于国际私法的冲突法规则下予以规定,或直接许可仲裁员在当事人未作明确约定时有权决定仲裁实体法的适用。众所周知,仲裁实体法的选择将会直接影响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判定,对仲裁结果有直接的影响。然而,这种影响有时会是本质的,会造成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规避。当这种规避达到了超出当事人对仲裁结果的合理期待或有违公共秩序时,当事人没有义务必须接受这种安排,甚至可以向当地法院提起对仲裁裁决的合法性审查。
在Westacre Investments Inc.v.Jugoimport—SPDRholding案④Westacre Investment Inc.v Jugoimport-Spdrholding Co.Ltd and others,[2000]Q.B,288.(以下简称为案例一)中,塞尔维亚公司Jugoimport—SPDR(以下简称为SPDR公司)同巴拿马的Westacre公司签订了一份准据法为瑞士法的合同。基于此项合同所达成的协议,Westacr公司将作为顾问为SPDR公司在科威特境内的武器销售给予协助,后者负有支付前者协助款项的义务。合同包含了一条仲裁条款,约定所有产生于合同履行的争议提交国际商会(以下简称为ICC)并依据《ICC仲裁规则》解决。合同签订后,SPDR公司虽然同科威特国防部就出售武器达成了协议,却拒绝向为其提供协助的Westacre公司偿付合同项下的报酬,后者遂提起仲裁。在仲裁程序中,SPDR辩称合同因包含有贿赂科威特政府官员的非法内容因而无效。然而,仲裁庭在审理过程中认为“利用影响接近政府官员”不符合瑞士法中关于行贿的任何行为,因此驳回了SPDR公司的抗辩事由,并作出了有利于Westacre的裁决。本案的仲裁庭适用了当事人协议选择的实体法,但是显然瑞士法没有对SPDR认为的贿赂行为作出明确界定,加之《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此规定也较为模糊,致使影响合同效力的条款含义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显然超出了被告的合理期待范畴。本案与Omniumde Traitementet de ValorisationSA(OTV)v.Hilmarton Ltd一案①ICCcase No.5622(Hilmarton-1988&1992).另参见A.Timothy Martin,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nd Corruption:An Evolving Standard,Transnational Dispute Management,VoI.1 issue2,May 2004.(以下简称为案例二)几乎如出一辙,而后者可能更具说明力。②OTV公司与Hilmarton公司签订了关于建造排水系统设计的公共项目开发合同,并由OTV支付Hilmarton公司价款。合同中约定由ICC仲裁并适用瑞士实体法。后双方发生争议诉诸ICC,仲裁庭在审理中发现,Hilmarton为获取该公共项目建造权而主动接触阿尔及利亚政府官员的行为在瑞士法上并不构成合同无效条款,该独任仲裁员转而考察合同履行地法即阿尔及利亚法律,发现阿尔及利亚法禁止任何在贸易中利用个人影响的行为,并据此认定阿尔及利亚法律应当作为本案适用的实体法,从而作出Hilmarton公司败诉的判决。然而,Hilmarton公司向日内瓦当地法院起诉,该法院经审查后认定该判决不符合当事人所选定的实体法规范,即瑞士法,因此判决撤销原仲裁裁决。1990年,ICC对该案作出第二次裁决,在事实不变的情形下,新的独任仲裁员裁定适用瑞士法,判决Hilmarton公司胜诉。
很显然,在案例二中,仲裁庭对实体法的适用规则经历了一次考验。适用当事人选定的瑞士法,某些行为就不被认定为是贿赂,因而不会影响合同③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涉及贿赂的合同具有可仲裁性是有立法和实践基础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曾经受理过一个贸易合同纠纷,经查明,当事人违背中国《海关法》,以贸易为名行走私之实,仲裁庭以认定合同无效、双方的利益不受法律保护结案。本案虽不涉及贿赂,但同样是源于一个非法合同,仲裁庭没有因为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涉嫌犯罪就否认其可仲裁性,而是行使了对该案的管辖权并最终作出了裁决。本文认为,我国当事人订立的国际商事仲裁条款同样应该适用于涉及贿赂的仲裁案件。参见郭玉军、裴洋:《论国际商事仲裁中涉及贿赂的合同的仲裁》,载《法学评论》2005年第2期,第15~25页。的效力——哪怕这些行为从公认的法理角度缺乏正当性和合法性。如果这种判例加以推广,很容易引导当事人通过订立仲裁条款从而规避各国不利的法律规定,既不利于各国司法主权的维护,也容易催生道德风险。事实上,这与国际商事仲裁制度过分强调当事人意思保护而缺乏关注仲裁制度基本原则有直接关联。众所周知,契约应当严守,但同时,契约的履行又不得有违公共秩序。这种带有哲学辩证性的规定赋予了合同法以制度对称的美感,从而使得“权利不得滥用”逐渐演变成了民商事活动最基本的原则之一。然而,从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历史来看,一部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史基本是对抗国家司法主权和国际强行法规范的“斗争史”,因而国际商事仲裁制度不断演化发展直至今日,保护当事人意思自治不受制于他人,尤其是国家司法主权的原则已经超越了其他仲裁法原则(如果有的话),并已经逐渐在人们心中常态化和法制化。这种略显偏激的司法替代制度已经逐渐对很多传统司法制度提出挑战,并逐渐开始显现问题。而无视“最密切联系地”的司法主权和公共政策就是其中之一。尽管包括贿赂和腐败在内的国际性犯罪已经由各项国际公约所规制,但这些国际公约往往为吸纳更多国家加入而在条约中规定了更多的模糊性条款。这些模糊性条款往往会授权成员国在基于条约意旨的基础之上在其国内法中自行规定,这同时也是国际法对各国司法主权的尊重。案例一和案例二所反映的不同国家立法差异正式基于此。
然而,没有任何法理能说明,法律模糊的规定等同于放任或默许特定行为的发生,这种法律的模糊性同样体现在一些国家对某些“非法”商业活动的宽容与谦抑性处理,例如瑞士法对商业贿赂的态度。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商业活动的合法性与否将直接决定着商业合同条款的效力,进而直接影响合同双方权利义务的内容。不可否认的是,各国对不同商业行为的法律性质均有不同的规定,某种行为在A国违反了商业秩序,但在B国可以成为由来已久的商事惯例;而在B国不予承认的合同条款,在A国却可以得到法院的认可。因此,出于减少法律冲突和降低仲裁承认与执行难度的考量,同时包括最基本的公平与正义理念,应当对各国不同的法律制度、商业秩序和公共政策予以平等的尊重。这就要求仲裁庭在适用某项实体法时——无论是仲裁庭自主决定还是依当事人协议所确定适用——都应当进行最低限度的法律条款比较与审查。尤其是当仲裁庭自主决定适用某项法律时,如果依据“最密切联系地”以确定准据法,该项准据法的适用不得与其他“最密切联系地”法律相违背。需要说明的是,这并非要求仲裁员是一名精通多国法律和语言的天才人选,但他(她)必须具有最基本的法律与道德评价标准——当出现某种不符合朴素的、普遍的价值观的法律条文时,①国际公共政策维护的不应是个别独特的、非国际性的制度,而应是人类社会普遍认可、并作为整体接受的一些根本性的制度。参见何其生:《国际商事仲裁司法审查中的公共政策》,载《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7期,第143~163页、第207~208页。应当意识到并阅览所有可能适用的法律,并从中选取对各个法律母国商业秩序和公共政策影响最少的那一部法律作为准据法。基于这一结论,案例二的ICC首次裁决结果更应当值得尊重。
因此,并非所有当事人协商选定的准据法,仲裁庭都要无条件接受。依据仲裁实体法所作出的裁决应当至少无损于以下国家的公共政策和法律要求:(1)当事人母国;(2)最密切联系地所在国;(3)仲裁裁决的审查②张宪初:《外国商事仲裁裁决司法审查中“公共政策”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载韩健主编:《涉外仲裁司法审查》,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77页。、承认与执行国。本文认为,应当将这一结论上升至国际商事仲裁乃至国际仲裁的基本原则角度加以深入研究。事实上,这一问题不仅存在于仲裁实体法的适用,也适用于仲裁程序法的选择。在1970年James Miller v.Withworth Street Estates Ltd.仲裁案③James Miller&Partners Ltd.V.Withworth Street Estates(Manchester)Ltd.,(1970)A.C.P.584.中,尽管当事双方一致协商适用苏格兰法作为仲裁程序法,但由于苏格兰法中没有“案件陈述”(case stated)的规定,英格兰当事方遂提请法院确认撤销该仲裁程序并改用英格兰程序法。据此不难看出,在仲裁程序法的适用过程,也存在不同程序法之间的冲突,尤其是体现最基本的程序价值冲突。
四、结论
国际商事仲裁法在程序法的适用规则上相对成熟,但在事关当事人具体权利义务的实体法的适用规则上依然相对模糊。尤其是在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中,CISG的存在加剧了这一问题的不确定性。国际实践许可当事人协商确定准据法,但事实上,大多数当事人选择实体法依然是基于对某部法律的了解程度。这种选择方式在理论和实践上会产生较多的误区,亟待从理论上加以探讨并归正。同时,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和国际贸易水平上升到新的高度,构建更加合理的仲裁准据法制度也更有利于保障我国当事人的合法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