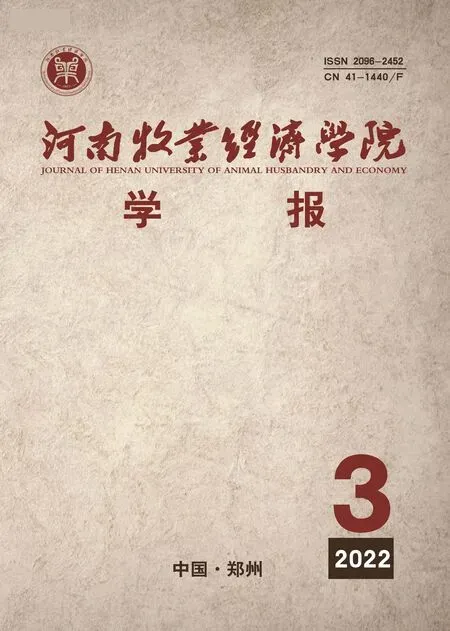从“桃花源情节”看元末明初士人心态
——以《剪灯新话》为例
高 攀
〔沈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
“桃花源情节”狭义上是指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人物设定、结构及环境都大体相同的小说情节:先是主人公在优美的环境中发现一个特别的村落,居住在里面的村民衣着古朴非本朝人,因避乱而隐居,再与之交谈,最后主人公一路做标记离开,想再次拜访但不复可寻。《剪灯新话》中的《天台访隐录》就是非常典型的一篇,内容及语言基本与《桃花源记》相同。广义上的“桃花源情节”大体是指参照陶渊明《桃花源记》的基本模式,对人物、环境、结局等要素进行一些改动,但主要架构没有改变。遵循相似的结构:现实中的主人公因为各种原因来到一个超现实的地点,在里面遇到了异人,主人公与之交流相处,最后回到现实,同时这一不寻常的经历带给主人公意外之喜。以广义的标准来看,《剪灯新话》中有六篇包含这样“桃花源情节”的小说,分别是《水宫庆会录》《三山福地志》《天台访隐录》《申阳洞记》《龙堂灵会录》和《鉴湖夜泛记》。
一、《剪灯新话》的“桃花源情节”概述
《剪灯新话》中的六篇带有“桃花源情节”的小说,可以分别从以下三个角度划分:进入桃花源的方式、主人公身份及结局设定。
1.进入“桃花源”的方式
以进入“桃花源”的不同方式来看,可以分为不小心误入和受到邀请进入两种。《三山福地志》《天台访隐路》和《申阳洞记》属于第一种,主人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偶然发现并进入了“桃花源”。《三山福地志》中元自实想跳井自杀,结果突然发现“其水忽然开辟,两岸皆石壁如削,中有狭径,仅通行履”[1],顺着小径走到尽头,来到了“三山福地”。《天台访隐录》中徐逸在采药途中,突然在水中发现一个巨瓢,顺着水流“不里余,至一弄口,以巨石为门,入数十步,则豁然宽敞”,来到了一个隐居的村落。《申阳洞记》中李生在古庙过夜的时候,打伤邪魅,白日之时顺着血迹发现一个洞穴,在环顾之时失足而坠,“寻路而行……更前百步,豁然开朗”,来到了申阳之洞。这三篇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在不经意的情况下,来到了异地。而《水宫庆会录》和《龙堂灵会录》属于第二种,主人公受到邀请来到“桃花源”。《水宫庆会录》中余善文在白日闲坐之时,两个广利王的使者忽然出现,替广利王邀请他到南海水宫做客。《龙堂灵会录》中闻子述在游览龙王庙时,突然遇到“鱼头鬼身者”,称“龙王奉邀”,便跟着使者来到了龙王水府。《鉴湖夜泛记》则是介于前两种情况之间,主人公成令言在泛舟之时,船突然自己航行,来到了仙境,其实是仙娥邀请他来的,但成令言本人不知情。
2.主人公身份
以主人公身份的不同来看,可分为粗人、武人和文人三种。《三山福地志》属于第一种,主人公元自实“生而质钝,不通诗书”,家里较为富裕,曾借同乡二百两,因“乡党相处之厚,不问其文券”,可见元自实的性格十分善良敦厚。他虽然是一个粗人,但却有着“宁人负我,毋我负人”的高尚品格,这也是他在跳井自杀后没有死,反而来到了三山福地的原因。《申阳洞记》属于第二种,主人公李德逢是武人,“善骑射,驰骋弓马,以胆勇称”,他凭靠自己的武力和智谋,进入申阳洞,杀死了邪魅。其余四篇《水宫庆会录》《天台访隐录》《龙堂灵会录》和《鉴湖夜泛记》都属于第三种,里面的主人公都是读书人。《水宫庆会录》中余善文是一介儒生,因龙王听说他“负不世之才,蕴济时之略”,邀请他到水宫畅谈诗词。《天台访隐录》中徐逸粗通书史,与隐士陶上舍评论古今历史。《龙堂灵会录》中闻子述“以歌诗鸣于吴下”,在游览龙王庙时,被龙王邀请到水府与伍子胥、范蠡、张翰和陆龟蒙各赋诗词以为乐。《鉴湖夜泛记》中成令言是一名“处士”,是有德才但隐居不愿做官的读书人,被仙娥邀请到仙界。
3.结局设定
以结局设定的不同来看,可分为保平安、得富贵和脱世俗三种情况。其中《三山福地录》属于第一种,元自实在“三山福地”中遇到一个道士,得知“不出三年,世运变革,大祸将至”,道士指引他到“福宁”去躲避灾祸。三年后果然战乱四起,而元自实因听从道士的指引而得以平安。《水宫庆会录》《申阳洞记》和《龙堂灵会录》属于第二种,在结尾,主人公都得到了一大笔财富。《水宫庆会录》中余善文最后“携所得于波斯宝肆鬻焉,获财亿万计,遂为富族”。《申阳洞记》中李德逢因为救了大户人家的女儿,而“一娶三女,富贵赫然”。《龙堂灵会录》中龙王“以红珀盘捧照乘之珠,碧瑶箱盛开水之角”馈赠给闻子述。《水宫庆会录》和《鉴湖夜泛记》的结局属于第三种,主人公在最后都脱离了世俗。《水宫庆会录》中余善文从水宫回来之后,“弃家修道,游遍名山,不知所踪”。《鉴湖夜泛记》中成令言“轻舟短棹,长游不返”二十年后,被人遇到时“颜貌红泽,双瞳湛然”“御风而去,其疾如飞”,已然成仙。《天台访隐录》是较为特别的一篇,与《桃花源记》几乎一模一样,最后结局是徐逸回家后想再拜访陶上舍,但是无果而归。主人公在“桃花源”一游之后,看似什么也没得到,但其实这一独特经历,还有和隐士陶上舍的对谈,都对徐逸大有裨益,使他对于世情有了更加清晰的认知,也向往着归隐的生活。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将《天台访隐录》的结局归为第三类,即脱世俗。
二、《剪灯新话》中“桃花源情节”反映出的元末明初士人心态
《剪灯新话》算上附录共有二十二篇文言小说,其中包含“桃花源情节”的有六篇之多,超过了四分之一,透过这些文字,能窥探到元末明初这一特殊时期士人的心态,主要有以下三种:对现实的躲避和反战意识、乱世之中“仕”与“隐”的矛盾心理和对现实失落的追寻。
1.对现实的躲避和反战意识
首先,从陶渊明创作《桃花源记》开始,“桃花源”这一意象经历了无数后人的丰富加工,已然成为现实人们理想的居住地,象征着没有斗争、安宁平静的世外生活。瞿佑在《剪灯新话》中多次使用“桃花源”这一情节母题,鲜明地表达了当时士人对安稳和平的隐逸生活的向往。
其次,“这部作品集是瞿佑在‘士人与战乱’的总标题下进行的系列创作”[2]58,在这六篇小说中,主人公所处的现实生活都十分黑暗和动乱,元自实深受战乱和人心不古的荼毒,以至于想要自杀。李德逢所处之地邪魅盛行,掳掠女子。瞿佑在小说中,从不同侧面勾画了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为了躲避这种现实,作者给笔下的主人公安排了“桃花源”一般的理想环境。通过构建虚幻的小说世界,瞿佑将人们对战争的厌恶与对世外乐土的向往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将这种愿景寄托在不可能存在的“桃花源”,则更衬托了现实世界的黑暗程度,以及人们无能为力的艰难处境。
再次,从进入异地的不同方式来看,瞿佑不仅创作了与《桃花源记》的主人公误入“桃花源”这一原有情节相同的小说,也进行了改编创作,令主人公收到邀请再进入异地。这个“邀请”就是连接主人公与“桃花源”的桥梁,“桃花源”本身就是虚构的,“邀请”则更加不可能,瞿佑将士人走投无路,只能寄希望于虚假的梦幻这一思想心态展露无遗。
2.乱世之中“仕”与“隐”的矛盾心理
在《剪灯新话》中瞿佑大量描写了乱世中士人面对战争时的无奈,揭示出士人对入仕与归隐二者的艰难抉择,在作品中加入“桃花源”情节,把视线聚焦在这一矛盾心理并将其放大深化。
从小说主人公的身份来看,进入“桃花源”的大多是读书人,他们学识深厚,身负不世之才,因为社会的动乱与政治的黑暗,无法进入官场施展抱负。“桃花源”是一个归隐的理想场所,但士人们所希冀的隐居生活其实并没有脱离世俗。如《水宫庆会录》的余善文因为“蕴济时之略”在龙宫中受到尊重与优待,龙王和三神对他的作品赞不绝口。离开龙宫后,余善文却不求功名,弃家修道,归隐于山川。从余善文在求仕与隐居二者之间的徘徊中,可以看出当时士人的复杂心态,想要出仕实现自己的志向,但无法对抗腐朽而庞大的社会阻力;想找到一个安宁的世外之地,归隐田园,又放不下自己的理想抱负。
除此之外,“桃花源”的隐逸之人,也不是完全不问世事。在《桃花源记》中,人们只知有汉而不知魏晋,但《天台访隐录》的陶上舍却与徐逸讨论南宋末年的历史旧事,将文天祥等爱国志士与贾似道等奸佞小人对比讲述。过着隐逸避世、悠闲自在生活的陶上舍,却有着“可怜行酒两青衣,万恨千愁谁得知”的慨叹。瞿佑其实是借隐士陶上舍之口,表达自己及当时广大士人的拳拳爱国之心与愤愤不平之意。“桃花源”般的美好生活固然是乱世中士人们理想的生活状态,但选择归隐也无法消去内心的惆怅与无奈。无论是入仕还是避世,都不能抹平战乱带来的创伤,这种宿命般的痛苦使广大士人在“仕”与“隐”之间难以抉择。
3.对现实失落的追寻
弗洛伊德在《作家与与白日梦》一文中将文学作品看做作家创造的与现实世界有区别但又很真实的幻想世界,“幻想的动力是尚未满足的愿望,每一个幻想都是一个愿望的满足,都是对令人不满的现实的补偿”[3],《剪灯新话》叙写了当时动乱的社会与士人的无奈,这也是作者瞿佑心态的写照,他通过设置笔下人物的经历与命运,满足了自己的现实欲望。
在这六篇小说中,不论主人公是以何种方式进入“桃花源”,都是从一个“穷困”的现实,到达一个畅达的环境。士人余善文和闻子述在现实生活中因战乱不得志,却在龙宫水府得以施展才华;李德逢在现实生活中被乡党贱弃,但在申阳洞中却杀邪魅、救三女,最后娶三女富贵赫然;元自实穷困潦倒难以养家糊口,想要自杀,却在三山福地中保住了自己的生命,还躲避了三年后的战乱且“家遂稍康”;不求闻达素爱山水的成令言,在仙境中游历一番之后,最终脱俗成仙。这些主人公的经历不尽相同,但在某种程度上却又出人意料的一致,那就是他们现实生活中想要却无法得到的东西,在“桃花源”中都轻而易举地拥有了。
瞿佑把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愿景,交给笔下的人物,让他们在异地中得到自己期望已久的东西。他们渴望建功立业、太平盛世,但动荡不安的社会,令他们无法实现自己的价值。于是只能寄托在虚假的异地世界,通过小说人物的价值得到彰显以及富贵平安的结局,来补偿自己在现实社会中的缺失。
三、《剪灯新话》中所体现的元末明初士人心态的成因
《剪灯新话》的创作体式受到了我国传统史学及宋元小说“实录其事”的影响,在22篇小说中,除了《令狐生冥梦录》一篇之外,其余每一篇都表明纪年。小说所表现的社会生活主要是元大德间到明洪武七年,而尤以元末明初为主。这一时期,恰是政权更迭前后社会剧烈大动荡的年代。
正如杜贵晨在《剪灯三话》中所说,“《新话》特殊的思想面貌在于较多渗入了作家个人的主体意识,从对文人生活处境的关怀和历史命运的反思中,表现了乱世风云中和高压政治下一代知识分子郁怒惊悸的心情,从而构成全书又一重要主题。”[4]瞿佑(1347—1433)一生历经元顺帝、明太祖、建文帝、明成祖、明仁宗和明宣宗六朝,他亲身体验了元朝末期的社会大动荡和明初的政治斗争。他作品中反映出的士人心态,与元末“乱世风云”和明初“高压政治”的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
元末时期,人情淡薄,道德沦丧,社会动荡不安,蒙古统治集团黑暗腐败,官吏残忍,官逼民反,爆发了红巾军起义。丧乱之际,黎民百姓流离失所,多遭杀戮,陈大康在《明代小说史》中称《剪灯新话》“相当集中地、且真实而细腻地表现了士人阶层在战乱期间的经历遭遇、价值取向、心态情绪乃至他们的情感生活,而在那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士人对于动荡社会的许多方面的感受,其实也与广大百姓十分相近”。[2]52确实如此,在战争面前,士人与百姓并无不同,他们也经历着同样的遭遇。瞿佑“生值兵火,流于四明、姑苏”[5],出生的时候正值元末农民大起义前夕,从小就过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备尝战乱的辛酸和痛苦。但好学的瞿佑并没有因为战争而放弃读书求仕,他一边躲避战乱,一边拜访当地名流,得到当时不少文人的赞赏,包括文坛领袖杨维桢。瞿佑在战乱中失去了自己的亲人和爱人,又与大量乱世文人相互交往,谈论时政,表白心迹,特殊的经历使他深刻地意识到社会动乱带给人们的伤害。
明朝的建立结束了烽火连天的时代,带来了和平与稳定,备受战乱摧残的百姓得以安居乐业。而广大士人期待的却不仅仅是安宁,还有清明政治。他们渴望建立功业施展抱负,以为明朝的统一能给自己带来机会,但却大失所望。
元代统治阶层虽然“在硬环境上采取野蛮的民族歧视政策,但在意识形态上却是很宽容的”[6],总体来说,元代的文化环境是宽松自由、开放多元的。元末时期的东南地区、沿海地区经济尤其繁华,达官贵人对于文士的礼遇,使文人的生活环境相对宽松,虽然不能在政治上施展自己的抱负,但悠游山水,生活也较为安逸。明朝的建立意味着一种文化转型,明初统治者重农抑商打压东南富室,对元末士人自由散漫的风气十分不满。
明初由乱入治后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文化高压政策,其中最惨绝人寰的就是“文字狱”,譬如洪武七年(1374)高启一案,《明史》记载“帝见启所作上梁文,因发怒,腰斩于市”[7],朱元璋仅因为高启用“虎踞龙盘”四字比喻张士诚,便断定高启有谋逆之心,足可见当时士人在这种残忍的文化状态下严峻而艰难的生存状态。而瞿佑本人极有可能就是“文字狱”的受害者。
瞿佑在《乐府遗音》中自述,“自罹罪谪独处困厄中,与妻即睽隔逾十寒暑矣”,又在《归田诗话》中写到“胡子昂亦以诗祸继至”,可以合理地推测他获罪的原因很有可能是文字之祸。“诏狱”一事,对瞿佑影响极大,他年少时壮志凌云,才高八斗,受到杨维桢等文坛前辈的提携,但他一生却只做过长史一类的小官,还因为诗祸在狱中苦耗多年,等到自由之时,已经是耄耋老人了。无奈之下,他将自身的仕途经历,以及心中的郁郁不平之气,融入到小说创作中。在《水宫庆会录》中安排余善文在龙宫作“上梁文”受到龙王优待,与现实中高启的悲惨经历对比来看,瞿佑的这一设定毋庸置疑是对时政的讽刺。
元末明初特殊的社会及政治背景,令广大士人产生迷茫、失落、愤懑又恐惧的心态。而瞿佑个人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促使他将士人们的遭遇和渴望付诸笔端,融入在“桃花源情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