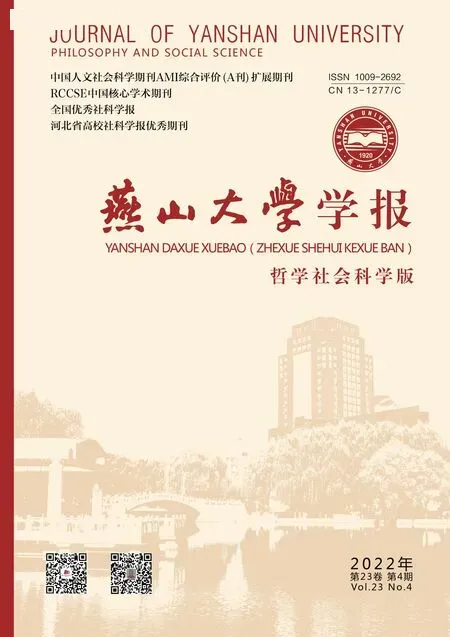从存在到价值
——宋明理学的逻辑开展
宋志明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100872)
关于宋明理学,有的学者不主张分派;有的学者提出两派说,主张划分为气学和理学两派;有的学者提出三派说,主张划分为气学、理学和心学三派;有的学者提出四派说,主张划分为气学、理学、性学、心学四派。笔者没有新的分法,只对张岱年先生提出的三派说表示认同。不过,张先生只是列出三派,并未论及三派之间的逻辑。笔者认为,三派并不是并列的关系,而是逻辑上的递进关系,由浅入深,后来居上,层层展开,构成一个完整的发展系统。三派先后出登场亮相,体现出宋明理学逐渐展开的内在逻辑。本文拟综合论述宋明理学三派逐步展开的逻辑进程,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趋向:三教归一
在成吉思汗执政时期,曾任中书令的耶律楚才虽然身为契丹人,却通晓中华学问。他向成吉思汗进言,阐明儒、释、道三教的区别:以儒治国,以道治身,以佛治心。儒家在政治哲学方面占优势,道家或道教在医学和养生学方面占优势,佛教在信仰领域中占优势。不过,耶律楚才的概括只适用于传统儒家,未必适用于已为新儒家的宋明理学。他毕竟是少数民族士大夫,对宋明理学还不够了解,不知道宋明理学家已兼治国、治身、治心于一身,化三教为一。
在宋明理学产生以前,儒家之所以能在政治领域占优势,乃也是长期以来历史选择的结果。按照司马谈的概括,先秦学术分为六家。六家之中,阴阳家神秘色彩太浓,不在哲学之列;墨家庶民色彩太浓,也不会得到统治者的赏识;名家爱走极端,难以实施。即便儒家,也只是一家之言,当时在政治上并不占优势。先秦诸侯虽对儒者恭敬有加,却不打算采纳他们的学理。首先被采用的政治哲学却是法家。秦始皇依据法家理论,用拳头说话,扫平六国,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大帝国。想不到偌大的秦帝国竟然二世而亡,不啻宣布法家被淘汰出局了。汉代秦立,汉初皇帝把目光投向儒家,对儒家采取扶植政策。刘邦是第一个以太牢之礼祭祀孔子的皇帝。汉初儒家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派,但无论哪一派,在政治都不占优势。继法家之后,政治上占据优势的学说竟是道家。汉初的道家已经被政治化了,称为黄老之学。“黄”是“黄帝”的简称;“老”是“老子”的简称。黄老之学的宗旨是“无为而治”,颇适用于汉初的情况,对于医疗战争创伤、与民休息有指导意义。可是,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其局限性也暴露出来了。一些地方豪强以“无为而治”为口实,要求朝廷不要干预地方,而自己却乘机为所欲为。地方豪强经常举兵造反,朝廷为平叛疲于奔命,“无为而治”政策再也贯彻不下去了。这意味着,道家也被淘汰出局了。在先秦六家中,只剩下儒家成为皇帝唯一的选择。汉武帝刘彻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坚定地实行“以儒治国”的国策,遂使儒家从一家之言上升到官方政治哲学的高度。不过,汉武帝眼中的“儒”,并不是那种只会从事道德说教的醇儒,而是深谙两手策略的大儒。孔子作为儒家开山鼻祖,当然提倡王道,但并不排除霸道。他在评述两种治国之道时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尽管他断言王道比霸道高明,但不否认设置霸道的必要性。荀子沿着孔子的思路,明确提出王霸并用的两手政策,主张“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荀子·大略》)。董仲舒继承荀子学脉,进一步把法家智慧融入儒家学说之中,形成“阳儒阴法”的思想,建议皇帝“发庆赏以立其德”,“发刑罚以立其威”。一方面实行王道,运用软的一手,使人主动地为善;一方面实行霸道,运用硬的一手,使人被动地不为恶。自汉武帝之后,儒家所设计的两手政策为历代皇帝采纳。汉宣帝明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其实,“以儒治国”也不是汉家的专利,哪个朝代不是如此?即便少数民族掌握全国政权,同样“以儒治国”。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是这样,满族人建立的清朝也不例外。由于“以儒治国”,大多数朝代延续百年以上。元朝虽然没有延续达到百年,也长达九十多年。佛教传入中国后,一度在信仰上占优势,但从未改变“以儒治国”的局面。宋明理学产生以后,儒家的政治优势一仍贯旧。宋明理学家虽然在治国理论方面没有什么创建,毕竟维系着儒家的政治优势。
宋明理学产生以前,儒家在医学和养生学方面不占优势,优势在道家或道教一边。中医处方大概都是道家或道教发明的,“以道治身”所言不虚。在孔子的“七十二贤人”中,没有哪一位懂得医学;也没听说哪位经学家以医学见长。到宋代情况有了变化,儒家开始向医学领域进军。一些受理学影响、屡试不第的儒生,悬壶济世,从事医生行当。他们把儒者情怀融入医学,被人们称为儒医。儒医的出现改变了儒家在医学领域的颓势。宋明理学家大都注重养生文化。理学宗主周敦颐“绿满窗前草不除”,有人问他为什么,他答复说:“观天地生物气象。”程颢喜欢养鱼,“欲观万物自得意。”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把万物视为朋友。宋明理学家已经成功地把儒家观念同养生文化融合在一起,倡导人与自然和睦相处,完全可以取代道家或道教,发挥“以儒治身”的作用。
在宋明理学产生之前,儒家在信仰领域不占优势,优势在佛教一边。东汉末年,经学衰微,玄学崛起。玄学家试图对儒家伦理作出本体论证明,但没有获得成功。囿于“一个世界”的观念,玄学家往往从道家那里找到“体”;可是,道家的“体”如何能证明儒家的“用”呢?他们失败了。不意玄学家开创的本体论思维方式却成了佛教在中国流行的突破口。佛教秉持“两个世界”的观念,认此岸为虚假,不值得留恋;彼岸是真实的,才是本体之所在。终极价值目标不在此岸,而在彼岸。这是一种出世主义导向。然而,在底蕴深厚的语境里,中国没有被佛教化,反倒使佛教中国化了。具体地说,“两个世界”的观念,逐渐向“一个世界”的观念靠拢。在中国华严宗那里,“两个世界”的边际变得模糊起来:此岸离不开彼岸,反之亦然。作为“理法界”的彼岸,同作为“事法界”的此岸密切相关,圆融无碍。在禅宗眼里,佛不在彼岸,就在心中。“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只不过一念之差而已。他们已经在佛教内部做足了功课,接近突破的边缘。
真正打破“两个世界”观念的正是宋明理学家。他们重新恢复“一个世界”的权威,认定此岸世界的真实性,断然否定彼岸世界的存在。从“一个世界”的观念出发,终极价值目标自然不能定位在彼岸,只能定位在此岸;终极价值目标不再是成佛或成仙,而是成为圣人。人在此生、此世,完全可以靠自身力量自我完善,不需要什么佛或仙来点拨。宋明理学讲的新儒学,既可以治国,也可以治身,还抢走了佛教在信仰领域中的风头。宋明理学迅速地把佛教挤到后排,使之无法再现往日的辉煌,再也没有走出过知名高僧。能给皇帝讲学的人,大都是理学家,而不有僧侣。
二、气学:一个世界
宋明理学同佛道二教的分歧在于:世界到底是一个,还是两个?作为此岸的世界到底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宋明理学认为,世界只有一个并且是真实的;佛道二教反是。宋明理学必须在本体论层面同佛道二教展开对话,从而使儒家入世主义在信仰领域得以彰显;必须彻底否定彼岸世界,对此岸世界的真实性作出本体论证明。率先出场的理论形态,便是张载创立的气学。他的主要论点是“太虚即气,则无‘无’”(《正蒙·太和》)。意思是说,我们只有一个真实的世界,没有此岸彼岸之分。
太虚原本是道家或道教的观念。《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老子》第十六章)这是太虚观念的发端。道家演变成道教以后,“太虚”作为核心观念便流行起来。许多道观就叫作太虚观。例如,在河南周口市,就有一座太虚观。张载从道家或道教那里借来太虚观念,对其作了新的解释,用以指谓世界总体。
张载接受玄学的教训,不再从道家那里寻找本体,就在儒家留下的资源中寻找本体。他找到的本体就是气。荀子曾将世界区分为四个层次:“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荀子·王制》)在荀子那里,气还只是一个质料范畴;而到张载这里,却上升为本体论范畴。张载认为,支撑起太虚的唯一本体就是气。气有本然和实然两种状态。本然的气无形不可见,弥漫于太虚之中;实然的气有形可见,乃是万物构成的质料。万物皆由气变化而来:气凝聚起来,构成万物;万物发散开来,复归本然状态。实然之气与本然之气原本是统一的,只是状态不同而已。气凝成万物,抑或万物复归于气,都没有离开气这个本体。气凝成万物,犹如水结成冰一样;万物复归气,犹如冰化为水一样。水和冰没有本质的差异,只不过形态不同而已。“本体”二字就是张载发明的。他说:“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正蒙·太和》)我们可以说中国没有西方式的本体论,但不能说中国没有本体论。总之,在张载看来,宇宙万物之所以是真实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气。
张载指出,由气生成托起的世间万物,永远处在运动变化过程中;而变化的动力就来自气本身。他断言:“动非自外”,“一物两体,气也。”(《正蒙·参两》)气有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如虚实、动静、聚散、浮沉、升降、健顺、阴阳、刚柔等等。两个方面相互感应,构成万物的演化过程,这叫作:“一故神(自注:两在故不测),两故化(自注:推行于一),此天地之所以参也。”(《正蒙·参两》)一中有两,两中有一,二者不可分离。“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正蒙·太和》)气既是万物之所以构成的质料因,也是万物之所以变化的动力因。
基于气本体论,张载断然否定佛道二教的宗教世界观。佛教认为世界有两个:一个是虚假的此岸世界;一个是真实可靠的彼岸世界。本体不在此岸,而在彼岸,他们称其为“真如”。道教也认为世界有两个:一个是人所在的世界,没有本体可言;一个是神仙所在的世界,那才是本体之所在。他们把本体叫做虚无。张载认为,所谓彼岸世界根本不存在,其实是对不可见的气产生的一种误解。气是唯一、真实的本体。“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正蒙·乾称》)气既有不可见的本然状态,也有作为客形的实然状态,但绝没有“有无”之分。在任何情况下,所谓“无”,本质上就是“有”,皆由气担保其真实性。在儒家的观念中,根本没有“无”这个字。儒家“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无之故’”(《正蒙·太和》)。北宋年间流行起来的婚礼,第一项竟叫作“拜天地”。这种习俗大概同张载的气本体论有关系。从这种仪式透露出信息是:我们只有一个世界,并且是真实的世界,应当在这唯一的世界中寻求精神慰藉;任何关于彼岸世界的虚构,都是站不住脚的。
基于气本体论,张载断然否定佛道二教的出世主义价值观,回归儒家入世主义价值观。张载认为,对于人来说,终极价值目标不是成佛,不是成仙,而是成为圣人。圣人的责任在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集·横渠语录》)。张载用“天地”二字标示宇宙总体,“立心”乃是确立气本体论观念;“立命”就是为民众立规矩,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往圣”乃是指孔、孟、荀确立的儒家学脉;“开太平”表示人们向往的理想境界,体现出以天下为己任的儒者情怀。
从入世主义价值观出发,张载试图实现气本体论同儒家伦理的衔接,尤其是同孝道的衔接。在他引以为戒的《西铭》中,有这样一段话:“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已成也。”他主张以一颗感恩的心对待自己的境遇,无论富贵,还是贫贱,都应无怨无悔地生存于天地之间,视天地为父母,尽到自己的责任。如果学会这样做,便会收获一份心灵的宁静,收获一份人与社会的和谐。张载作为中国哲学家,不像西方哲学家那样,只关切存在问题,而是把天人紧紧联系在一起。“天人合一”一词就是他发明的。他说:“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横渠易说·系辞下》)他认为,为人之道就是以天为楷模,不断地“变化气质”,克服自身的缺陷,以天道为归宿,“善反之天地之性存焉。”(《正蒙·诚明》)。在张载那里,“天”象征无形的存在,“地”象征有形的存在。在他看来,有形的存在不过是气化的糟粕而已,无形的存在才是精华之所在。人作为万物中之一物,也属于“糟粕”,因此,自我改造很必要。他的价值观有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为多数理学家所接受,并且进一步演化出“存天理,灭人欲”的诉求。
受佛道二教的影响,张载既谈人生观,也谈人死观。众所周知,传统儒家讳谈死亡问题。有弟子向孔子请教死后的情形,孔子的答复是:“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张载继承了儒家传统,也突破了儒家传统,不再回避关于死的话题。他的态度是:“生,吾顺事;死,吾宁也。”(《西铭》)但凡是人,总是要死的。这是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谁也不例外。面对死亡,我们不必恐惧,不存幻想,仍旧保持着平静、无愧、坦然、安详的心态就足够了。一个“顺”字,融入道家“想得开”的智慧;一个“宁”字,融入佛教“放得下”的智慧。不过,张载的生死观仍旧以儒家“拿得起”的智慧为基调。
张载在主观上想以气学同儒家伦理接榫,在客观上却遇到接不拢的困难。气作为本体,不含有价值意味,乃是中立的。从气中既不能引申善,也不能引申不出恶。就这样,张载以气证善的意图落空了。大多数理学家没有沿着张载的思路讲下去。气学可以对世界的真实性作出雄辩的证明,却不能为儒家伦理提供担保。
三、理学:发现核心
程朱理学认可的本体论核心范畴是天理,而不是气。程朱理学同张载气学对着讲,没有接着讲。但是,没有张载气学在先,也就不会有程朱理学在后,二者之间的逻辑联系还是明确的。理和气不同。理既可以担保世界的真实性,也可以担保价值的真实性。气只有存在意涵,没有价值意涵;理既有存在意涵,也有价值意涵。由于这个缘故,大多数宋明理学家都选择理作为核心范畴,而没有选择气。理的价值意涵就是“应该如此”,人一旦对天理有了本体论体验,就可以理所当然、理直气壮、心安理得地安排价值生活。用理对儒家伦理做本体论证明,显然比中性的气更有说服力。继气学之后,程朱理学作为第二个理论形态,影响力迅速超过气学。狭义的理学是指程朱理学,广义的理学是指整个宋明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思潮。
天理本体论的发明者是程颢、程颐兄弟。他们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确是自家体贴出来。”(《二程外书》卷十二)张载虽说是他们的表叔,可是他们并不认同张载的气本体论,尤其不认同“凝聚成万物、万物发散为气”的说法。他们觉得此说同佛教轮回说相似。二程认为,只有天理才可称为本体,气没有资格称为本体。他们说:“天理云者,这一个道理,更有甚穷处?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穷居不损。这上头更怎说得存亡加减?是他元无少欠,百理具备。”(《二程遗书》卷二上)天理逻辑地在先,不生不灭,永恒存在,不受人世间变故的干扰。天理才是本体,一切事物都是变体。世界的多样性来自理的统一性,一切事物都是天理的分有,二程叫作“理一分疏”。至于如何分疏,朱熹解释得很形象。他引用佛教中“月印万川”说法:天上有一个月亮,地上的湖泊却呈现出成千上万个月亮。每个湖泊呈现的月亮,不是天上月亮的部分,而是月亮的整体。这就叫作“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或者“万个是一个,一个是万个”(《朱子语类》卷九十四)。在他看来,“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朱子语类》卷一)天理是万物的成就者、总根源、总前提、最终依据,“天下之物,皆实理之所为,故必得是理,然后有是物。”(《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第二十四章》)
至于气,则被朱熹界定为质料,置于从属于理的地位。气扮演着理“挂搭处”的角色,“无是气则理亦无挂搭处”(《朱子语类》卷一)。气并不能与理等量齐观,前者属“形而下”,后者属“形而上”。他说:“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八)气帮助理获得现实性品格,“如人跨马相似”。骑手骑在马身上,堪称为骑手;否则就是普通人。在这个意义上,理气不分先后,二者皆不可或缺,有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天理把世间万物结为一个整体。天理是真实的,万物同样是真实的。朱熹指出,充分肯定万物的真实性乃是天理本体论与佛教本体论的根本区别。如果把世间比作一个水桶的话,佛教所认定的世界,好像什么也没装的空桶;而天理本体论所认定的世界,好像装满水的水桶。看上去,似乎是空的;用手摸一下,就会感受到天理的实有。世界的统一性和真实性皆由天理来担保。
程朱认为,天理既可以说在诸事之上,也可以说在诸事之中。人与万物中的区别在于,人肩负着自觉体现天理的责任。在程朱那里,“理”有“规律”“规范”二义。就其存在意义上说,理有“规律”的意思。任何事物必须遵守自身的规律。二程说:“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则,一物须有一理。”(《二程遗书》卷十八)倘若违背了客观规律,必然遭到失败。就其价值意义上说,理有“规范”的意思。理乃是人必须遵守的当然之责,程朱显然更重视后者。二程强调:“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二程遗书》卷五)朱熹也说:“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朱文公文集·甲寅行宫便殿奏札一》“三纲五常终变不得。”(《朱子语类》卷二十四)二程把儒家伦理同天理内在地统一起来,把“礼”上升到“理”的高度。二程说:“视听言动,非理不为,即是礼。礼即是理也。”(《二程遗书》卷十五)他们认为,恪守儒家伦理并不是被动地表示服膺,而是一种主动的本体论体验。传统儒家偏重于伦理,很少论及本体论。子贡感慨地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程朱理学弥补了传统儒家的这一缺陷。他们用儒家式的“体”(理),论证儒家式的“用”(规则),达到“体用一元、显微无间”的境界。他们终于完成了对于儒家伦理的本体论证明,理论深度超过了气学。
基于天理本体论,程朱对人提出过分的理想化诉求,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二程说:“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二程遗书》卷二十四)他们甚至主张“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朱熹抱着同样的看法,他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朱子语类》卷十三)这样,便使程朱理学成为一种严酷的道德说教。
对于程朱理学来说,困难的问题是理究竟在哪里呢?理在天上呢,还是在内心世界?如果说理在天上,那么,“自在之物”何以能转成“为我之物”呢?对此问题的进一步探讨,导引出心学一系的出现。
四、心学:彰显价值
陆王心学和程朱理学的接点是“理”。陆王心学认同“理”的观念,接受“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法,至于“理”究竟在何处,看法同程朱理学有分歧。陆王坚定的认为,“理”不在天上,就在人的心中。心与理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理固然包含有价值意涵,毕竟不能排除存在意涵;而心则是纯粹的价值范畴,是价值判断的主体。陆王牢牢抓住一个“心”字,回避存在本体论问题,只谈价值意义上的本体论。他们吸收气学和理学的理论思维成果,也汲取气学和理学的经验教训,最终实现三教归一的意向,从而成为宋明理学中最后一个理论形态。在宋明理学思潮中,气学不算正统学脉,因为理学没有接着气学讲。陆王心学却是接着程朱理学讲的,同属于宋明理学思潮中的正统学脉。
心学的始创者是陆九渊。他丝毫不疑世界的真实性,但世界之真,同存在之真无关,乃是价值之真。价值世界永远是属于人的世界,人与价值同在。他不否认理的核心地位,但是把理的权威性紧紧同人心联系在一起。他说:“上下四方曰宇,古往今来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万世之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东南西北海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陆九渊集》卷二十二)在鹅湖之会上,陆九渊批评朱熹过于支离,缺乏整体性观念。他要把这一环节补上,“先立乎其大”。这个“大”,就是孟子说过的本心。本心不是每个人的肉头心,而是成为圣人的总依据。本心与天理等值:“盖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陆九渊集》卷一)他由此得出结论:“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陆九渊集》卷十一)于是,他便把理学发展为心学。心学和理学相比,理学关切存在,心学更看重价值;理学关切天理对于人的超越性,心学更看重天理对于人的内在性。陆氏心学已经实现理论重心的转移,成为理学合乎逻辑的发展。
南宋陆九渊开心学之发端,明代王阳明则集心学之大成。王阳明接过“心即理”的说法,发展成为“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的系统理论。他只谈价值世界如何树立的问题,而对客观世界则存而不论。在《传习录·下》中,记载了一段他同友人的谈话:
“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有何相关?
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在一般中国哲学史教科书中,编纂者根据这段材料,通常把王阳明说成“主观唯心论者”,其实是一种误解。王阳明在这里讲的是价值本体论,不是存在本体论。他并没有否认花的客观存在。当人们未看花时,“同归于寂”。“寂”是“没有意义”的意思,并不意味着花不存在。所以,给王阳明戴上“主观唯心论”的帽子并不合适。王阳明在同弟子对话中也指出,天之高、地之厚、鬼神之灵,其实都是人做出的价值判断;倘若离开了人,一切都无从谈起。价值世界是人的精神创造,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盖天地万物与人原为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的一点灵明。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木石,与人原只一体。”(《传习录》下)王阳明十分看重价值判断中的主体性原则,并不认同贝克莱式的“存在就是被感知”。王阳明讲的是价值本体论,贝克莱讲的是存在本体论,二者不可以相提并论。王阳明不否认,在认识论上,应当走从物到人的路线;而在价值论上,必须走从人到物的路线。价值是指客体对于主体的有用性,倘若离开了人,遑言价值?我们只能在价值的意义上领会心学的趣旨。
王阳明的价值本体论叫做“致良知”。“良”有“值得”的意思,与“不良”刚好相反,设定儒者应当追求的、合乎理想的终极价值目标。他接过孟子所说的良知,当成价值本体论观念,用来取代陆九渊所说的本心,把儒家的人学讲透了。陆九渊的本心论还有脱胎于天理论的痕迹,“致良知”则是地地道道的价值本体论。既然价值判断是人做出的,那么,终极价值目标就应该由人来设定,而不需要由佛或仙来设定。本着良知说,王阳明直指做人的远大目标,即成为儒家一向倡导的圣人。他对圣人重新加以界定,强调做圣人的关键,就在于一个“德”字,同社会地位的高低无关,同才能的大小无关。按照王阳明的说法,“满街都是圣人”。做圣人如同淘金子,讲究的是成色,而不是分量。做圣人也没有名额限制,小人物照样可以成为大圣人。他不再倡言尧舜禹之类的“圣王”,更看重小人物出身的“圣人”。他已突破儒家的政治哲学,讲出儒家的人生哲学。在王阳明这里,儒家三教归一的宏愿,终于变成现实:儒学可以治国,自不待言;也可以治身,养成“仁者与万物同体”的坦荡胸怀;还可以治心,树立做圣人的远大目标。王阳明所讲的儒学,已从官方儒学演变成草根儒学。
由于在学理上陆王心学以佛道二教为对手,故而其末流过分关切价值而忽视了实践,过分关切穷理尽性而忽视了经世致用。至于如何纠正这一倾向,已不在宋明理学的范围里了。
综上所述,气学也好,理学也好,心学也好,都是宋明理学发展长河中不可或缺的逻辑环节。按照自身的逻辑轨迹,气学、理学、心学递次出场。张载以气学开篇,论证一个世界的真实性;程朱理学将存在与价值合而论之,发现理为核心;陆王心学落脚于价值本体,最终完成儒家三教归一的大业。宋明理学家从存在本体论讲起,最后以价值本体论为归宿。换言之,气学开其端,理学为中坚,心学断其后。中国之所以没有沦为宗教国家,宋明理学居功至伟。他们重塑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成功地用儒家入世主义取代佛道二教的出世主义。在中国古代社会后期,宋明理学始终占主导地位,没有哪一家可以取而代之。在宋明理学中,学者互相批评,互相讨论,互相辩难,都是十分正常的学术现象,不必大惊小怪、小题大做。假如都是“一脉相承”,人云亦云,后人只重复前人说过的话,难道还有发展可言吗?过去那种把气学同理学截然对立起来的观点,那种把理学同心学截然对立起来的观点,实在值得商榷。
——《宋明理学人格美育论》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