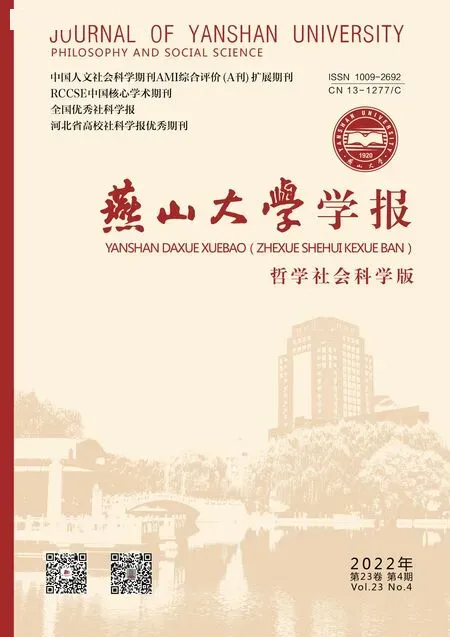湛门与王门之间的“良知良能之辩”
程 潮
(广州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在欧阳德文集中有一封写给湛若水的信,指责他是学术界以“舍良能而言良知”批评其师王阳明的始作俑者。湛若水回信指出自己先前对此说并不知情,后来才得知汪得之说过、张文海与何廷仁辩论过,故对欧阳德的指责极为不满。不过,现存古文献的相关记载非常零碎分散,无法直接获得王门与湛门之间的辩论详情,需要一番精细的考证功夫。本文以时间链为线索,以证据链为依据,将散落在古文献中的相关资料作一番汇总与梳理,以图揭示湛门与王门之间“良知良能之辩”的来龙去脉及其历史影响。
一、 王阳明生前的“良知良能之辩”
首开王门与湛门之间“良知良能之辩”的主角,湛若水弟子张文海曾在其《增城县志》中介绍了他与何廷仁辩论前学术界对王学的态度:“阳明之学,大要只‘致良知’,又为‘知行合一’之说,学者多疑之。”[1]12-13而他这里所讲的对阳明之学有“疑”的“学者”到底有谁?我们不妨先去追溯一番,因为他与廷仁的论战正是接着这些“学者”所“疑”的话题而展开的。
我们知道,“知”与“能”是儒家思想的重要范畴。孔子既重“知”,提倡“博学”“多识”;又重“能”,但他重修德之“能”,以行“仁、知、勇”等“君子之道”,提出“患其不能”。却轻谋生之“能”,视“艺”为“鄙事”,主张“君子不器”。[2]97,178,156,110,57不过,孔子虽承认“生而知之”,但更重视后天的“知”(“学”)和“能”的价值。孟子则从性善论出发,提出先天的“良知良能”说,并将“学问”局限于“求其放心”[2]334。他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2]353这是将“良知良能”视为人人生而具有的善的本能,“少知爱亲,长知敬兄”乃是人的“良知良能”的外化,而将爱亲敬长的“良知良能”施于天下,则能建立一个仁爱的世界。故在孟子那里,“良知良能”与“知行”功夫密切相关。
汉儒赵岐在《孟子注》中释“良”为“甚”,视“知”犹“能”,则“良能”似乎可包含“良知”。他称“良能良知”为“性”中所“自能”“自知”,而非后天的“学”和“虑”所得。[3]233这是从心理(本能)上而不是从“道德”(性善)上来理解“良知良能”的。
到宋代,“良知良能”变成了学者们议论的热门话题。张载将“良知”与“良能”分说。“良知”仅指人类之“天德良知”,又称“诚明所知”“德性所知”[4]20,24;“良能”则有自然的“天之良能”“二气之良能”[4]17,9,有人类的“物感之良能”“天德良能”[4]20,17。但他认为,世人之心止于“闻见之狭”,……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4]24;“圣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立心求之,则不可得而知之”[4]17。若如此,则“天德良知”和“天德良能”都只能为圣人所独有,这就将常人堵在“成圣”的殿堂之外。不过,张载把议论的重心放在“良能”上,还以“天人本无二”为立论基础,提出“天良能本吾良能,顾为有我所丧尔”[4]22。程颐喜将“良知”与“良能”并说,提出“夜气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扩而充之,……可以至于圣人”[5]321,则肯定了良知良能对后天道德修养的价值。他又提出“万物皆有良能”说,认为禽鸟全靠“良能”做事(如做窠)而“不待学”,而人只有初生时吃乳“不是学”,其他“皆是学”,“学”则“智多”,“智多”则“害”之。[5]256这似乎视后天的“学”对先天的“良能”有破坏性。朱熹谓张载的“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之语“尤精”[6]26,称程颐的“夜气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之语“最分明”[7]2809,又引程颐的“良知良能……出于天,不系于人”之说为证,释“良”为“本然之善”[2]353。这都表明他的“良知良能”观深受张载和程颐的影响。他还将孟子的“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这句话释为“才,犹材质,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则有是才,性既善则才亦善”[2]328,说明他肯定“才”“能”的价值。程朱学派将“良能”视为万物皆有的属性,而将“良知”视为仅人类才有的属性,则意味着人类的先天本能自然是“良能先于良知”。
朱熹已注意到“良知”与“致知”的关系。他在《吕氏大学解》中称:“吕氏曰:‘致知格物,修身之本也。知者,良知也……’。”[7]3791意即吕氏将“致知”之“知”释为“良知”。但他未明说“吕氏”到底指谁,后世有“吕希哲说”“吕大临说”和“吕本中说”三种说法。黄佐(字才伯,号泰泉)先是持“吕希哲说”,在《泰泉集·复林见素》(1524)中提出“惟宋吕希哲氏独以致知为致良知”[8]234,在《泰泉集·与何燕泉书》(1527)中提出“吕希哲解《大学》曰:‘致知,致良知也’”[8]251;后转持“吕本中说”,在1530—1549年间[9]518的讲稿中提出“吕氏本中解‘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曰:‘致知格物,修身之本也;知者,良知也……’”[9]645,这应是他后期的定论。朱彝尊则称“吕氏《大学解》”为“吕氏大临《大学解》”[10]813。相比较而言,“吕本中说”更为可信。[11]5不过,吕本中没有将“致知”与“良知”合成一个“致良知”范畴,这一事项是由王阳明完成的。
程朱学派基本上是将“良知良能”与“知行”分开论述的,他们在“知行”观上强调“知本行重”“知先行后”。程颐说:“须以知为本,知之深则行之必至”,“不致知,怎生行得?勉强行者,安能持久?”[5]164,187朱熹虽承认“知轻行重”,但又指出“万事皆在穷理后,经不正,理不明,看如何地持守,也只是空”[12]134,137。他还主张“大凡义理积得多后,贯通了,自然见效。不是今日理会得一件,便要做一件用”[12]142。意即零碎的知识会失之片面,只有通过积累而获得系统性知识,才能更有效地指导实践。不过,过分地强调“知先行后”,则会造成“行”迟迟不至,也使“知”流于空疏。故明代王阳明在正德七年(1512)“与徐爱论学”[13]673时,批评程朱学派“将知行分做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而他提出“知行合一”以作“对病的药”[14]5-6。正德九年,他在南雍与薛侃论学[13]752时提出“后儒不明圣学,不知就自己心地良知良能上体认扩充”[14]39。正德十五年(1520)秋,他提出“致良知”说[13]1286,但“良能”概念开始淡出。嘉靖三年,他在《答陆原静书》(即《答陆澄书》)[15]47中再提“良能”,提出“知行本体,即是良知良能”[14]85,将“良知良能”与“知行”打通。嘉靖四年,他在《答顾东桥璘书》中提出“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但惟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致”[13]1705,将“良知良能”与“致良知”打通,不过仅将“良知”作为“致”的对象。此后,他的文章中再也不提“良能”。而他寡言“良能”或“能”,与他对区分圣凡标准的认知有关。他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也。孔子之圣,则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是明伦之学,孩提之童亦无不能;而及其至也,虽圣人有所不能尽也。”[14]308意即孔子虽圣,也曰“事父未能”;孩童虽小,亦有“爱亲”之“知能”。言外之意在于:圣凡之分在“明人伦”而不在“良能”。他还说:“为圣者,在纯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后世不知作圣之本是纯乎天理,却专去知识才能上求圣人,以为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我须是将圣人许多知识才能逐一理会始得。故不务去天理上着工夫,徒弊精竭力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拟,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14]34-35这里阳明更关注“才力”(良能)的异化而沦为“作圣”的障碍。因他生前大谈“良知”,寡言“良能”,故引发黄佐和孙扬等宗程朱者与他展开了“良知良能之辩”。
黄佐嘉靖二年(1523)任岷府南渭王册封副使时取道杭州,与王阳明在绍兴展开辩论。阳明主张“知行合一”,“行了乃是知”,黄佐主张“知先行后”,“使知不在先,恐行或有不善”;阳明只论“良知”,黄佐主张“圣人于达道达德,皆责己未能当,言明德则良能可兼”。[9]646他还以孔子自谦“未能一焉”和“我无能焉”说明孔子对“能”的重视,并提出“仁义之理必先知而后能”[8]235。嘉靖七年六月,王阳明托广东提学副使祝品(字公叙)回广州时带信招黄佐来南宁敷文书院论学,并说自己已“附纳”他的观点,还手书“欲求明峻德,惟在致良知”对联于敷文书院。嘉靖七年十月,阳明离开广州北行后又给黄佐去信,提出“明德只是良知,所谓灯是火耳”。[9]646因此,在阳明与黄佐的书信往来和当面辩论中,讨论的核心议题是“良知良能”问题。阳明去世后,黄佐便直白指出“惟王阳明祖述吕希哲氏,专言致良知”[8]237,说明他先前明为批判吕希哲,实则针对王阳明的“致良知”说。
东阳孙扬(号石台)在嘉靖戊子阳月作的《<质疑稿>序》中说:“前年先妣遐弃,去岁(1537)居垩室中,哀痛无所措身,因复取阅之,而旧疑有戚戚焉者,既而以乞《墓铭》走越,偶过(阳明)先生之门,妄举所疑之大者,笔之为书以质问焉。”[16]8-9而他登门向阳明质疑的是“知行合一之旨”[16]1。他又在《质疑稿》中提出“良知、良能是两个名目,须分得明,阳明则混为一目”[17]4。
当然,张文海在《增城县志》中所说的对阳明之学有“疑”的“学者”还应包括其师湛若水。黄宗羲曾指出:“王、湛两家,各立宗旨。……先生与阳明分主教事,阳明宗旨致良知,先生宗旨随处体认天理。学者遂以良知之学,各立门户。”[18]875-876王门与湛门的宗旨不同,则双方的争论也在所难免,但主要反映在对“格物致知”说的理解上,如若水所说:“两承手教格物之论,足谂至爱。然仆终有疑者,疑而不辨之则不可,欲辨之亦不可。”[19]252但他还是选择了“辨”。阳明训“格物”为“正念头”,“致知”为“致良知”,并坚称“致知之说,鄙见恐不可易”[14]220。若水则训“格物”为“体认天理……兼知行、合内外言之”,释“致知”为“知”此“实体”“天理”“至善”“物”,且视之为“吾之良知良能”,因人为“气习”所蔽,故须“学、问、思、辨、笃行”以“警发其良知良能”。[19]253这说明,若水在与阳明的辩论中总是将“良知”“良能”并提,只是他们二人并没有将“良知良能”作为辩论的焦点。
二、 张文海与何廷仁的“良知良能之辩”
张文海(?—1549),字原道,号龟峰,广东增城人。约嘉靖二年(1523)为“弟子员”;七年“举乡荐”[20]3;八年二月京试下第,住仪真,与何廷仁展开“良知良能之辩”[21]13;十三年在南京闻湛若水“二业合一之训”,退修于增城“龟峰之麓”;二十五年会试下第,就选于天官;二十九年任华容县令,阅月而卒[22]335。若水称他为“张生文海”[23]379,张星称他为“甘泉公高第弟子”[20]3,说明文海确实为若水弟子。不过在文海仅存的著作《嘉靖增城县志》中,并未说明他是在何时何地从师若水的,这就必须从二人活动时空的重合处去寻找。若水于正德十年(1515)至十六年底在家乡并在西樵讲学,嘉靖元年(1522)正月至八年六月在南京任职并于七年在新泉精舍讲学,八年(1529)七月至十二年七月在北京任职,十二年(1533)八月至十五年夏在南京任职并在新泉精舍与弟子问辩,十五年(1536)归增城。文海自称“儿时已闻湛母之贤”,又称“湛则余所亲睹”[21]15-17,说明他很早就认识若水。若水在正德年间回增城时,自文海到南京会试到若水北京任职前,都有可能向文海面授过。故若水说:“吾邑龟峰张子原道文海,久从予游,既举于乡,不肯专门举业,于书无所不窥,往往发为著论。”[22]335这似乎说,文海在中举前就已师从于他,而他对文海中举后的学问与人品也非常赞赏。
何廷仁(1483—1551),初名秦,字性之,号善山,江西赣州雩都(今于都县)人。嘉靖元年(1522)举于乡[24]23,二十年授新会知县,二十五年迁南京工部主事[25]62。他少时崇拜陈献章(号白沙),为诸生时,听到同邑黄宏纲(一说弘纲,字正之)在南赣闻“阳明之旨”后,相信阳明就是“今之白沙”[26]320,于是赶到南康拜其为师。因他与黄宏纲及钱德洪(字洪甫)、王畿(字汝中)对王学的“解悟”最为突出,故同门中有“浙有钱王,江有何黄”[27]535之称。那么廷仁是如何与文海遇上的呢?耿定向载道:嘉靖己丑(1529),罗洪先在外舅岳父带来明肃宗赐他“进士及第第一人”消息的当日,“犹袖米偕何(廷仁)、黄(宏纲)二君,联榻萧寺中商学焉”[28]30。罗与何、黄同为阳明江西籍弟子,应为会试而住在南京某佛寺同一房间。而文海该年也在京城参加会试,故能与廷仁在京城相遇。明朝会试一般在农历二月份进行,而王阳明在嘉靖七年(1528)十一月二十九日病逝于江西大庚县,次年二月四日丧至浙江越城。何廷仁可能在会试期间还不知道其师已去世,也才会有与文海辩论的雅兴。
文海与廷仁的首次辩论是在京城会试结束后开始的,按照他自己的描述:“余嘉靖己丑岁(1529)下第,回至仪真,偶阳明之门人何廷仁,与辩论数日,别去。”[1]13辩论的地点究竟在何处呢?或指文海从京城回仪真时偶遇廷仁,或指文海途经京城某地偶遇廷仁,但这无关论辩事实的发生。廷仁先向文海示以“致良知之说”,抛出话题。文海回应说:“孟子言良知,便继曰良能,今委良能,而专以良知为训,恐渉偏堕。”[1]13
经过首轮当面辩论后,文海对自己的观点有所反省,并向廷仁表示自己对“致良知”说初未领会,后经三四涵泳,乃悟其立言之“深意”在担心人们“舍行以为知,徒事支离”,故言“知则行已具,知而不行,未为真知”,实欲令人“将知行合作一事”,以对治后学“务口耳而废实践”之病。但他还是觉得“致良知”说亦只是“矫枉之说”,恐后来者概其“宗旨”时主张太过,未免会“以知为行,以行为知”,反生扞格。故他主张“将知行调停说去,更觉工夫明整浑全”。[1]13这实际上回到其师湛若水的“知行并进”说上。
这场辩论结束后,文海又向廷仁“出拙草求正,因觇尊意”,也就是将自己的观点写成文稿,呈给廷仁,以求其批评指正。但廷仁却每每不以为然,只以为“学须有大头脑,头脑既得,旁节自当疏畅,不必泛滥”[1]13。按照王阳明的说法:“学问大头脑”乃是“致良知”[14]88。尽管文海将廷仁的观点视为一种担心他“知浮于行”的善意批评,但他仍然坚守自己的观点,并于嘉靖十一年(1532)离开仪真时,在“舟次”中给廷仁写了一封信,提出了自己的“格致”观。[1]13廷仁在辩论中将向外格物穷理视为“泛滥之学”,这与王阳明的“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14]52之说相一致。文海在信中辩称:“宇宙如是其博,万物如是其繁,精精粗粗,巨巨细细,莫非吾心道义,苟于宇宙万物,有一理未究,便是吾心体用犹有缺也。故以吾心放之宇宙万物不为外,以宇宙万物约之吾心不为内,体用一原,内外无间也。是以用心穷理,未必即为泛滥之学;而专心事内以遗外者,其学乃偏枯也。”[1]13-14这又与湛若水在《答杨少默》(1521)中所说的“程子所谓‘体用一原,显微无间’,格物是也,更无内外”[19]252相一致,也反映了湛门的“格致”观与程朱理学的继承关系。
三、 欧阳德的责难与湛若水的反驳
欧阳德(1496—1554),号南野,江西泰和人。弱冠(1516)举乡试,从学王阳明于赣州虔台[18]357;嘉靖二年(1523)进士,会试时“直发师旨”[29]5286;六年为翰林编修,十一年升南京国子司业[30]6,十二年合王门同志“会于南畿”,并与何廷仁、黄弘纲等“嗣讲东南”[14]1518;十四年迁南京尚宝司卿,十七年升太仆寺少卿[31]17;十九年任南京鸿胪寺卿[32]2;二十六年升太常寺卿,掌国子祭酒事[32]5;三十一年任礼部尚书[33]5。
继张文海之后,仍不少学者批评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忽视“良能”的价值。安阳崔铣于嘉靖癸巳年(1533)指出:“孟子曰良知良能。知能,心之用也;爱敬,性之实也;本诸天,故曰良。今取以证其异,删良能而不挈,非霸儒与?”[34]2其后,湛若水在嘉靖丙申闰十二月(即1537年1月,见饶宗颐的《薛中离年谱》[35]516。《泉翁大全集》误标为“戊戌三月望”,即1538年农历3月15日)所作的《明故征仕郎右给事中东泓薛君墓志铭》(又称《薛黄门墓志铭》)中表达出与王门师徒相异的“良知良能”观。
若水在《薛黄门墓志铭》中虽承认薛东泓(名宗铠,字子修)“学王阳明公良知之学,推阳明之意”,但却又从“良知”和“良能”两个方面对东泓的“好德”“孝敬”“恻隐”“羞恶”“恭敬”和“是非”六个方面进行积极评价。[36]946-948此说一出,就遭王门学子的质疑。有人向他发问道:“东泓子之良知,则何以荐良能矣?”意即东泓只信“良知”,若水却以“良能”赞之,是否违其所愿。欧阳德则提出“致即良能”[36]948之说,以在若水和质疑者之间打圆场,意即“致”的功夫就是“良能”的体现,无须在“良知”之外另立“良能”。欧阳德先前又承阳明的“良知之外更无知,致知之外更无学;外良知以求知者,邪妄之知矣;外致知以为学者,异端之学矣”[37]15-16之说,提出“良知无外,而有外之学,非真致其良知者也”[37]28。他先前受其师“良知即是独知时,此知之外更无知”[14]939说的影响,提出“独知也者,良知也;慎之者,致知也”[37]38。若水在《薛黄门墓志铭》中一并回应说:“良知所同也,致所独也,是故学焉而后良知致矣。”[36]948这就是说,若水与欧阳德的不同之处在于:欧释“良知”为“独知”,而他释“良知”为“同(知)”,“致”为“独(致)”;欧将“学”排斥在“致良知”之外,而他将“学”作为“致良知”的重要手段。他最后总结说:“曷曰良知?天知地知。曷曰良能?天地成能。曷以致之?学之、问之、思之、辩之、笃之、行之。”[36]948这是将“良能”与“良知”对举,并指出了“致良知”的具体途径。
欧阳德长期在京城任职,应对学界批评其师“只言良知,不言良能”的言论早有所闻。他在嘉靖乙未至丁酉年间作的《答李古原》中说:“心之良知之谓知,心之良能之谓行,良知、良能一也。故行也者,知之真切运用;而知也者,行之明觉精察,本合一者也。”[38]12这是将知行关系等同于良知良能关系,以“知行合一”来说明“良知良能合一”。
若水在《薛黄门墓志铭》中对欧阳德的“致即良能”说的回应,又使他很不自在。而令欧阳德大为光火的是,若水弟子张文海所撰《增城县志》含有攻击其师的“致良知”和“知行合一”说的内容。文海于1537年应增城县令文章(字成之,号念斋)之邀而担任该《志》的“纂修之责”[39]2,约在1538年前后(即若水知晓前)完稿。他能迅速完稿,一因有明代正统年间李玉撰的增城旧《志》作参考[39]1;二因选材以所熟悉者(“所亲睹”[21]17)、资料丰富者(“前令不书,后特书”[40]1)、重要者(“体制重大”[40]8)为详。该《志》完稿后被送到京城让太学生帮校稿,书稿校完后请若水裁定,若水裁定后请太常寺少卿张星过目,一群太学生又带若水之命请张星作《序》。[20]1由于该《志》在京城的校对、裁定、作序和联络工作有这么多人参与,则《志》中质疑王学之论以及文海与廷仁之辩的信息也就为京城中越来越多的太学生和官员所知晓,这也难免会传到在京城任职的欧阳德那里。故他护师心切,随即(约1538年初)给若水去信(即《答甘泉先生》)说:“近日士夫论致良知之学,往往补良能一语,以为良知犹有未尽。某窃疑之,乃不知本先生云尔也。”[38]32“补良能”既可指若水在《薛黄门墓志铭》中“补”薛东泓之“良能”,也可指文海在与廷仁的论战中“补”王阳明之“良能”。他对前者还能容受,但对后者则无法容忍,以为是对其师的大不敬,故而将对文海的不满迁怒于其师若水。他辩解说:“《大学》只言致知,不言致能;孟子亦只言知爱知敬,而不言能。鄙意能知爱知敬即是能,致此知即是成能,即此是学,而问、思、辨者,问、思、辨此学而已,勿忘勿助者,勿忘勿助于此学而已。”[38]32这里所提“爱敬”“成能”“学问思辨”等术语都在若水的《薛黄门墓志铭》中出现过,而“勿忘勿助”更是若水的口头禅。
若水收到《答甘泉先生》后非常生气,随即于嘉靖戊戌(1538)三月十一日在《复欧南野说良知良能》信中说:“舍良能而言良知,吾初不之知,乃一见汪宪副得之言之于徽州,再见张举人文海辩之于赣州何廷仁,张之言又先于汪者数年,而皆本孟子先良能后良知以为说也。吾初为之愕然,执事以为本于区区者,误矣。……执事因愤人之说,而咎于区区,不亦过乎!恐执事者之不见察,故不得不复贡其说,惟执事其详之。”[19]307他将汪得之和张文海的观点统统归结为本孟子的“先良能后良知”以为说,而将自己的观点概括为“以良能继于良知之后,见知行未尝相离”,以示既有别于汪得之和张文海的观点,也有别于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和欧阳德的“致即良能”说。若水在信中提到的汪得之和张文海二人,是在何时以“舍良能而言良知”批评王学的呢?
先看汪得之。《新泉问辩续录》第三卷所载若水答学生刘代“十条”之问的第三条说:“前谒文公阙里,见汪得之宪副偶说出一句,云:‘今日只说良知,如何不说良能?’予为之愕然。”[41]26这与他给欧阳德的信中说法完全一致。不过,洪垣认为,《新泉问辩续录》为若水“由北而官南都,以至十四年终”的问辩记录。[42]1若此说法成立,则若水应在嘉靖十二至十四年间去过婺源的文公阙里,但现存的文献中并未发现相关记录,只有嘉靖十六年去过的记录。如《游梅岩题名》:“嘉靖丁酉(1537)二月十日,甘泉湛子将赴上都,取道谒婺源朱文公阙里。”[19]137《谒朱文公先生庙庭文》:“丁酉二月十有二日,后学湛氏若水将达上都,取道婺源以渡大江,敬诣宋文公朱先生阙里而拜焉。”[43]732他又在《福山书堂讲章》中写道:“今婺源同志诸君共立福山书院为讲习之地,时余谒文公阙里而过焉。”[44]277意即他在谒文公阙里后,就到婺源的福山书院讲学。福山书院又称福山书堂,为若水在婺源的学子诸生与乡义士所建,也是弟子方纯仁、方瓘等人的讲学之地。[23]384,215《新泉问辩续录》第四卷中载有方瓘问若水的一段话:“昨蒙针灸,亦不敢不自收敛,以深藏自晦,反躬责己,与诸同志互相砥砺于福山也。”[45]2-3而方瓘“闻湛元明讲学南都,往从之……;及湛北上,瓘不惮险阻,徒出远从之;归以所学策勉同志”[46]14。也就是说,方瓘离开北京后就回到了家乡婺源(福山书院)讲学,则不可能第二次在南京新泉精舍从学。“昨蒙针灸”自然是指若水在福山书院讲学期间对方瓘的批评。由此推之,《新泉问辩续录》第三和第四卷中涉及“谒文公阙里”和“福山”问辩的段落应为若水嘉靖丁酉年在婺源发生的事,可能是孙然对《新泉问辩续录》进行“补刻”[41]1时加进来的。
再看张文海。既然若水获得文海与廷仁的“良知良能”之辩晚于获得汪得之的“只说良知,不说良能”之言,则他获得文海与廷仁之辩的信息应在1537年农历二月十二日之后。而若水从婺源回南京之后,与居家的文海天各一方,自然不易获此信息。而张星说:“(《增城县志》)既成帙,寓书于太宰甘泉湛公,请裁定焉。”[20]1则若水应是审阅老家寄来的《嘉靖增城县志》书稿后得知文海与廷仁的“良知良能之辩”之事的。
欧阳德收到若水的回信后,似觉对若水责备太过,闹得王门与湛门之间有隔阂,故他随即复信(即《奉甘泉先生》)说:“然则师友之间,固不可以同声相和为贵,非分彼我也。……朋辈不得因异同生彼我,不得因彼我起异同,然后此道可明。”[47]10这明显表达了王门与湛门之间“以和为贵”的和解愿望,强调不同派别、不同观点之间应相互尊重、相互包容。他与若水之间经过了这段不快的互责后,也开始重视起“良能”和“学”来。在他1546—1551年间所作之文中,《答项瓯东》提出“孟子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不虑而知者其良知,皆以学属能,以问辨思索属知,盖良知本能爱亲敬兄、忠君信友,汨于私意,始有所不能,必学焉而后能”[48]25;《答冯州守》针对胡森(号九峰)嘉靖十九年作的《良知解》中“阳明言良知而不言良能,此知行合一之说,言良知而良能在其中矣”之说法,而提出“举良知则良能固在其中……;举良能则良知亦在其中”[49]41。
欧阳德去世后,若水作《奠欧南野文》说:“维公初第,予会京邸。人曰王门,入室弟子。视我前辈,阳明是以。载讲南都,数会拟议。人语良知,良能亦语。以訾未尽,乃在公矣。匪予则然,孟氏大指。良知良能,爱敬仁义。空知则禅,师门自毁。吾与阳明,斯文共起。有如兄弟,异姓同气。天理良知,良能天理。相用则同,二之则异。”[43]841这里若水叙述了与欧阳德及其师王阳明的交往过程,特别提到二人在“良知良能之辩”上的分歧及由相互责难到重归于好的变化过程。
不管怎么说,欧阳德与若水围绕“良知良能”问题所发生的争辩,再次暴露出王阳明“致良知”说所存在的逻辑矛盾,特别是被王畿等弟子引向只求“任心”,不重“功夫”的空疏禅化境地,故除欧阳德外,在王门其他弟子和后学中也出现了纠偏之论。季本(字明德)晚年提出“良知、良能本一体也。先师尝曰:‘知良能是良知,能良知是良能,此知行合一之本旨也’”,将“良能”与“良知”并列;但又说“所知者即是行,所行者即是知”[50]73,则又重犯王阳明知行相混的错误。
而“尝受学于阳明先生”[51]57的陈大纶(号豹谷)任韶州知府时,在若水的引导下而肯定“良能”之价值,并使他认识到,实现“善政之道”是一个由“良知”到“良能”到“知能合一”到“达之天下”的递进过程。故若水赠诗说:“良知何似良能实?实即良能是所知。使君报政真何政,天下知能可达之。”而“赠诗之指”在于“假良知”以“发端”,希望大纶行“知能之政”以达于天下,利泽苍生。[52]581
四、 余论
湛若水与王门弟子欧阳德之间所展开的言辞激烈的论战将明代的“良知良能之辩”推向了高潮,它使王门弟子从严守师说到承认“良能”在“致良知”中的价值,提出“知能合一”“良知良能一体”,但仍以“知”(“良知”)统“能”(“良能”),“良能”始终包裹在“良知”之中,使人看不到“良能”的存在,所以质疑的声音一直不断。有六合县令向泰州学派耿定向(号天台)问道:“阳明先生但言良知,不言良能,得无遗漏否?”[53]3而欧阳德弟子薛应旗(号方山)因王学的弊端转成程朱信徒,并诘难说:“至王伯安,独言致良知而不及良能者,以为知可以兼能也。学者多矮人观场,尊信而不敢致诘,恐非当仁不让之义也。”[54]11他觉得王学言“致良知”而不及“良能”是不对的,理当受到批评。
至明末清初,对王学不言“良能”的质疑又达小高潮。一是认为忽视“良能”则不利于“知”与“行”。王夫之就张载的“天良能本吾良能”的话题指出:“孟子言良知良能,而张子重言良能……。故知虽良而能不逮,犹之乎弗知。近世王氏之学舍能而孤言知,宜其疾入于异端也。”[55]101意即只有“良能”才能使人“尽伦成物”,取得成效;没有“能”(“良能”)则“良知”就不能转化为真正的“知”。故在这个意义上,他批评王学“舍能言知”是禅学“异端”之论。魏象枢说:“良知,知也,良能,行也。王阳明只讲良知,是教人有始无终,有内无外。”[56]354。意即无“良能”,则无法“行”。二是认为忽视“良能”则有违经义。劳史认为,王学抛却“良能”,与孟子兼言良知良能的“本意不合”[57]16;胡煦以“天才”释“良能”,认为“阳明言良知而不言良能,未尽孟子之旨”[58]5。魏象枢认为,“致良知”不讲“良能”,是“言知不言行”,虽说“致”字就是“力行”,亦非《大学》“致知之意”[59]50。
王门与湛门之间的“良知良能之辩”之所以了而未了,在于他们对“良知良能”与“知能”的关系、“知”与“行”的关系以及“良知良能”与“知行”的关系的理解都存在着理论与实践上的缺陷。第一,先天的“良知良能”与现实的“知能”的关系。王门与湛门都基于孟子的“良知良能”观来立论,只是王门向内存守,湛门内外兼修。而清初熊赐履在顾宪成的“不能而学亦良能,不知而虑亦良知”之说的基础上提出“学而能亦良能,虑而知亦良知”之说,主张“不学、不虑”者“究不足恃”,“学、虑”者“终不可废”。[60]198这就是说,人不能躺平在先天的“良知良能”上,而更应培养后天的“知能”,只有通过后天的“学”“虑”工夫才能巩固“良知良能”,成就“知能”。第二,“知”与“行”的关系。王阳明通过“以知释行”和“以行释知”来解读“知行合一”,造成王学末流“以知代行”和“以行代知”之病。湛若水基本继承程朱学派的“知先行后”和“知行并进”说。“知”和“行”分属主观和客观范畴,二者在理论上是不能含义相混,在实践上是不能相互替代的。“知”和“行”也不能简单地以“先后”论,“行而生知”“行以证知”体现“行先知后”,“知以导行”则体现“知先行后”。第三,“良知良能”与“知行”的关系。王门时将“良知”(知)与“良能”(能)分别对应于“知”与“行”。实则“知”(“良知”)本身就是一种“能”(“良能”),故郝敬提出“良知便是良能”[61]42,陆陇其释“才”(“能”)字兼指“良能”和“良知”[62]17。而“能”既可助“知”,也可助“行”;“知”既可助“能”,又可化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