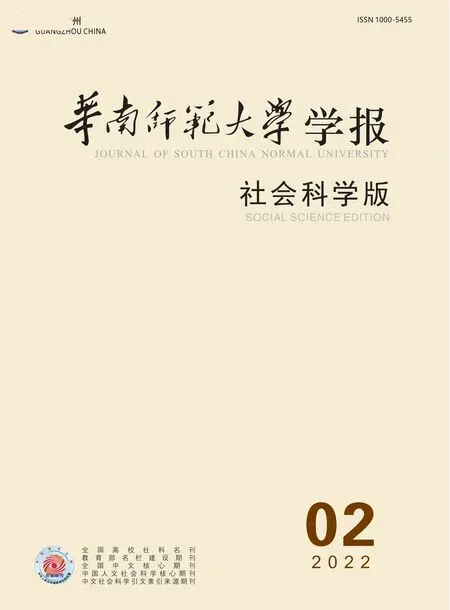“知行不一”:张之洞的骈文理论与骈文创作
吕双伟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长沙 410081)
张之洞(1837—1909)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并称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事功卓著。其实,他还是著名的学者、文人,学问与诗文成就突出。他五岁入家塾,师从何养源,读书详询字义,必索解乃止;九岁读完四书五经;十岁学作诗和古文辞,泛览经、史、子部典籍;十一岁即席作《半山亭记》,歌颂父亲张锳的为官政绩;十二岁时,诗文集《天香阁十二龄课草》刊刻。以上可见其为学基础的扎实与为文的早慧。
对于张之洞的诗歌,汪国垣、徐世昌、胡先骕等都加以高度评价,多认为其可与王闿运、陈三立在晚清鼎足而立,有的甚至认为其是晚清翘楚:“之洞忠忱蹇蹇,勋业巍然,原不必以诗为重,而诗实空前绝后,足为晚清之冠。”(1)张之洞著,庞坚点校:《张之洞诗文集》“附录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第615页。可见其诗歌地位之高。同时,张之洞的奏议、骈文、古文成就也较高,“文章典赡,为一代宗工”(2)袁祖光:《绿天香雪簃诗话》,载《张之洞诗文集》“附录三”,第544页。。陈衍评曰:“张广雅相国在近代达官中最为博洽,四部罔不谈,而尤熟《资治通鉴》;诗、文、骈、散罔不作。余尝以为奏议第一,诗次之,骈体文次之。生平文字务博大昌明,不为奥衍僻涩以号称高古,而用事尤以雅切见长。”(3)陈衍:《广雅堂骈体文笺注序》,载《张之洞诗文集》“附录三”,第524页。博洽学识正是博大昌明文风的形成原因之一,加上用事雅切,最能概括其骈文的典型特征。钱基博以当行本色之身份论骈文,也云“晚清骈文,以南皮张之洞孝达为大家,刊有《广雅堂骈文》”(4)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 骈文通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125页。。已有研究集中在他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和诗歌等方面,但对其散文、骈文很少关注,迄今尚无专门的骈文研究论著。本文拟从其骈文理论与创作的不一致出发,对其骈文思想加以全面探究。
一、重视清代骈文及推崇晋宋体
在晚清兼具达官、学人与文人三种身份的士人中,张之洞对骈文的关注,堪比其前辈曾国藩(5)关于曾国藩对骈文的重视及其影响,参见吕双伟:《曾国藩与晚清湖湘骈文批评的崛起》,《文学评论》2017年第6期。,他的骈文创作成就则超越了曾国藩。光绪元年(1875)和二年(1876),张之洞署名编撰的《輶轩语》和《书目答问》(缪荃孙实编)相继刊行。书中观点,无疑经过张之洞的审视并同意。两书都表达了对骈文的重视。清代,乾嘉汉学兴盛,骈文也迎来发展高峰,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密关系。张之洞则指出清代汉学家,包括小学家、骈文家都精通选学:“国朝汉学、小学、骈文家皆深《选》学。”(6)张之洞撰,范希曾补正:《书目答问补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265页。《文选》所录诗文,风格典雅,多讲究典故与遣词造句的精练等,因而底蕴深厚,得到清代汉学家和骈文家的青睐。在《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总目》“骈体文家”条目中,他认为:“国朝工此体者甚多,兹约举体格高而尤著者,胡天游、邵、汪、洪为最。”(7)同上书,第270页。将胡天游、邵齐焘、汪中和洪亮吉四人视为清代骈文体格最高者,开启了清末民初将此四人视为清代骈文成就代表的先河。在这个总目中,他接着列举了毛奇龄、胡浚、王太岳、刘星炜、朱珪、孔广森、杨芳灿、曾燠、孙星衍、阮元、凌廷堪、彭兆荪、吴鼒、刘嗣绾、董祐诚、谭莹等20位骈文家,但没有选录陈维崧、吴绮、章藻功等清初骈文三大家及吴鼒《八家四六文钞》中所选的袁枚、吴锡麒,这与咸同以来文章领域流行相对风格淡雅、骈散交融的思潮有关。陈维崧和袁枚等人的骈文,骈俪精致,隶事丰富,风格有时不免轻佻,“体格”多评价不高。
张之洞在学术著述和日常交往活动中,也常涉及骈文。1892年,周锡恩(1852—1900)的骈体文和写本诗刊行,张之洞评曰:“其诗宏雅雄骏,岸然升乾嘉诸作者之堂。其述事览古之篇,词采奇伟而事理秩然可寻;刻画山水草木之作,百态毕尽而俊气不为之遏抑。若夫才调锋发而天性笃厚,哀乐纯至,足以感人,是则以前作者所难兼,尤其可贵者也。”(8)张之洞:《传鲁堂诗集序》,载《张之洞诗文集》,第213页。推崇宏大、典雅又雄俊的诗歌风格。又曰:“至其骈文沉博绝丽,而事理之清明,性情之过人,一与诗同。”(9)同上书,第214页。指出其骈文“沉博绝丽”,即学问与辞章兼备的特征;而事理之清晰明了和性情之真,则与诗歌一样。由此类推,张之洞认为古今人文章,大率辞不没理者,必有干事之才;文不掩性者,为友缓急可恃,可见其将文章与事功、人品视为三位一体,具有同一性。在其署名总纂的《顺天府志》中,艺文部分著录了《万善花室骈文》六卷、《续集》一卷,并题曰:“履篯之学,自天文、地理、氏族、金石、六书、九章之法、耆阇梵夹之书,无不旁通博涉,贯串洞达。其骈文雄深浑厚,典丽磅礴,髙者渊源两汉,次亦纂组六朝。自嘉道以来,以骈文鸣者,《栘华馆》外,鲜能抗手。”(10)周家楣总裁,张之洞、缪荃孙总纂:《(光绪)顺天府志》卷一百二十六,清光绪十二年刻、十五年重印本。也强调学问渊博对骈文雄厚风格的影响及方履篯突出的骈文成就。在日常生活的雅集活动中,他也特意对交往诸人是否擅长于经学、诗歌或骈文加以说明。如《致潘伯寅》中提到某次龙树寺雅集没有赴约的人,其中加注“骈文”的有“会稽李莼客慈铭(经、诗、骈文)”,“黄岩王子常咏霓(经、诗、骈文)”,“南海谭叔裕宗浚(骈文)”,“秀水赵桐孙铭(骈文)”。(11)张之洞:《张文襄公古文、书札、骈文、诗集》之《书札一》,民国十七年刻《张文襄公全集》本。在《致谭叔裕》的书信中,他对谭宗浚的骈文欣赏不已:“一再谈宴,温充过人,浅学粗材,不觉倾倒。顷奉到骈文两册,即亟炳烛展读数首,闳丽之观,方驾芥子(王太岳);宕逸之气,足药穀人(吴锡麒)。近世当家,已足高参一坐。明日早起,从容卒业,瞠目挢舌,抑可知也。惜会办严,未获款洽,相见殊晚,蕴结而已。”(12)同上。书信措辞难免夸饰,但认为谭宗浚的骈文兼备“闳丽”和“宕逸”,可与乾嘉骈文名家王太岳和吴锡麒抗行,为本色当行之家,所言不虚。接着指出谭宗浚骈文的家学渊源:“执事家学渊源,文章淹雅,海内曾有几人?”确实,谭莹、谭宗浚父子文章风格都渊博典雅,堪称晚清骈文家的重要代表。在《书目答问》卷四“集部总目”中,张之洞专门单列“国朝人骈体文家集”,著录清代陈维崧、吴绮、陆繁弨、章藻功、胡天游、邵齐焘、胡浚、袁枚、孔广森、汪中、朱珪、孙星衍、洪亮吉、杨芳灿、吴锡麒、刘嗣绾、彭兆荪、姚燮、曾燠、吴鼒、董基诚、董祐诚22人的骈文集和诗词集。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单列骈文家文集且收录如此多的代表性骈文家诗文集,这应该是第一次。这不仅是清代骈文集单列且大量刊行的结果,还可见张之洞等编撰者对骈文家的留意与重视。
在清初李绂将骈文分为六朝体、唐体和宋体的基础上,《书目答问》指出:“诸家流别不一,有汉魏体、有晋宋体、有齐梁至初唐体。然亦间有出入,不复分列。至中晚唐体、北宋体,各有独至之处,特诸家无宗尚之者。彭元瑞《恩余堂经进稿》用宋法,今人《示朴斋骈文》用唐法。”(13)《书目答问补正》,第270页。将清代骈文分属于汉魏体、晋宋体、齐梁至初唐体、中晚唐体、北宋体五类,认为后两种清代名家多不宗尚,又指出彭元瑞和钱振伦的骈文宗尚。应该说,这些评论都是符合事实的,可见张之洞等对骈文史的娴熟。他还指出清朝(其实应该是晚清以来)最推崇的骈文体貌,强调博学对骈文的重要影响:“国朝讲骈文者,名家如林。虽无标目宗派,大要最高者,多学晋宋体。此派较齐梁派、唐派、宋派为胜,为其朴雅遒逸耳。取明王志坚《四六法海》、国朝李兆洛《骈体文钞》、曾燠选《骈体正宗》读之,可知骈文指归。总之,文、学两字,从古相因,欲期文工,先求学博。空疏浅陋,呕心钻纸,无益也。”(14)张之洞撰,程方平编校:《劝学篇》附《輶轩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第134页。晋宋体骈文的流行,确实是道咸以来清代文坛上比较突出的现象。此派骈文,其实是骈散不分之文;其形式浑融,风格朴雅遒逸,比齐梁派、唐派和宋派的四六骈体更加清新自然,更加符合文章写作“学博”而后“文工”的状态,因此得到晚清以来较多文士的推崇。这种推崇,正是骈散交融、骈散不分的文章流行现象在当时的反映。偏于典型的四六骈体或纯粹单句的散体,都遭到时人的批评。如张之洞的《輶轩语》叙述“古文骈体文”曰:
试场策论用散文,今通谓之古文。对策间有用骈文者,但不常有,惟词馆应奉文字用之耳。然骈散两体,不能离析,今为并说之。周秦以至六朝,文章无骈散之别。中唐迄今,分为两体,各为专家之长,然其实一也。义例繁多,殊难备举,试言其略。古文之要曰‘实’,骈文之要曰‘雅’。实由于有事,雅由于有理。散文多虚字,故尤患事不足;骈文多词华,故尤患理不足。各免偏枯,斯为尽美。(15)《劝学篇》附《輶轩语》,第134页。
既按照惯例将古文与骈体文对举叙述,同时又强调骈散两体不能截然分开。周秦到六朝,文章骈散不分,只有一种形态;中唐到清代,经过唐宋古文运动的有意区分,才人为区分为两体,但本质上都是文章形态,写法相通;其主要区别在于古文重视实在内容,骈文重视雅致形式;要以充实的内容和丰富的道理来克服古文与骈文的不足,避免各自的偏枯,努力达到完美的境界。一般认为,齐梁体和初唐体骈文的精致形式,特别是较多使用四六隔对的形式,促使了唐代律赋的形成。《輶轩语》论述赋,特别是律赋时,反对通篇使用四字句或每段四六隔对之联太多:
“忌通篇四字句”:古人间有。施之律赋,短促伤气。宋广平《梅花赋》,乃宋人伪作耳。前人已辨之。舒元舆《牡丹赋》中,六字句仍不少。(16)同上书,第129页。
“忌每段四六联太多”:多则重膇滞塞。若以唐法论之,每韵中四六隔对,止宜用一联。今难如此深论,但不必过多耳。近代名家赋中,一段往往有三四联四六者,实皆非法。读书嗜古,洞悉文章流别者,自能知之。(17)同上书,第129-130页。
赋多用四字句或四六隔对,正是齐梁骈赋和唐代律赋的一般特征。张之洞从文风朴雅遒劲的角度出发,主张少用此类句式,确实为精到之论。
在清末新政中,张之洞主张改革科举制度,建立学堂,开设中学和西学课程;同时主张单独创办存古学堂,学习经史辞章,其中包括骈文。如1907年他在《创立存古学堂折》中提出,学堂课程设置无论经学史学,皆须兼习词章一门;而词章之中,或散文,或骈文,或古诗、古赋,皆可兼习者。可见,即使到了清末新学兴起、学堂竞开的时候,张之洞依旧重视经史和辞章之学,强调散文、骈文、古诗、古赋在文化传承中的重要意义。
二、体国经野、润色鸿业的代言体骈文
张之洞科举顺利,仕途通达。咸丰二年(1852),16岁中顺天乡试第一名,解元;同治二年(1863),27岁时中进士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担任过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等要职,官至体仁阁大学士。这种经历不仅对其政治态度、学术思想有重要影响,同时也决定了其诗文特别是骈文创作的主要内容。他的骈文与其功业仕途及儒家思想、时代思潮等紧密相关,堪称其为官经历中的政事记录表。高凌霨曰:“无何玉楼之文,竟归天上;茂陵之稿,半佚人间。许君同莘乃裒辑公在京、在晋、在粤、在楚诸骈体之作,付之剞劂。扶风弟子,缉剩锦于天孙;山阳故人,拾零玑于琼圃,拨劫后之残灰,留吉光于片羽。虽嘉祐万言,《会昌一品》,不是过也。”(18)高凌霨:《广雅堂骈体文笺注序》,载《张之洞诗文集》“附录二”,第523页。可见其骈文散佚过半,现存的都是在北京、山西、广东、湖北为官时所写,成就堪比王安石的奏章《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及李德裕的《太尉卫公会昌一品集》。张仁青曰:“香涛淹贯经史,综核流略,在清季达官中最为博洽,所作骈体,步趋两宋,务博大昌明,不为奥衍僻涩,以号称高古,而树义精深,取材渊茂,直如杜诗韩笔,无一字无来历,宋四六之会光,遂又再度返照矣。”(19)张仁青:《中国骈文发展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第480页。在清末民初学人评价的基础上,张仁青指出张之洞骈文取法宋四六,博大昌明,义精学富,堪为的论。而宋四六的主体是制诰、表奏等庙堂之作,多为骈文中的“大手笔”,张之洞也非常善于撰写此类骈体。
体国经野,润色鸿业,反映当时重大的历史事件,正是张之洞骈文在晚清甚至清代的突出特征,也是其特殊意义。《广雅堂骈体文》共两卷,其中卷一只有五篇文章,都是代朝廷或达官而写的“大手笔”,属于诏诰、表奏类庙堂骈文。前两篇是代朝廷写给袁保恒的,即《恭撰谕祭刑部左侍郎袁保恒文》《恭撰谕赐刑部左侍郎袁保恒文》;第三篇是代朝廷写给蒙古族保恒的,即《恭撰谕赐署乌鲁木齐都统、哈密办事大臣保恒碑文》;第四、第五篇则与太平天国、捻军起义紧密相关,即代恭亲王奕所写的《恭进剿平粤匪方略表》《恭进剿平捻匪方略表》。对已有重大历史事件或重要人物的功绩加以文学归纳与形象书写,是骈文的历史使命与天然属性。这里以《恭进剿平粤匪方略表》为例,探讨此类骈文的特征。
康熙年间平定三藩之乱,修《平定三逆方略》。《钦定大清会典》卷三记载:“每次军功告蒇及遇有政事之大者,奉旨纂辑成书,纪其始末,或曰方略,或曰纪略。”后遂成为国家修书定制,各朝沿袭而行,目的是“光大烈业,垂示后昆”。同治七年(1868)十一月,在礼部一再奏请的背景下,同治帝同意编纂平定粤、捻方略,以“毖后惩前,益深兢惕”。次年二月开馆纂书,总裁由清廷任命的五名高级官员组成,以恭亲王奕为首,总纂则由宗人府府丞朱学勤等担任。历经三年,《剿平粤匪方略》告成。该书大量收录了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形成的谕旨、奏章,内容包括双方交战情形及清军的作战部署、军队调拨、粮饷筹备、官员配置和奖惩抚恤等史实,卷帙浩繁,规模庞大,是研究太平天国运动史利用率较高的档案资料汇编。《剿平捻匪方略》则是对咸丰、同治间清廷镇压捻军起义的档案文献汇编。帝后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英明形象,在两本方略中得到充分体现。两文夹叙夹议,铺张扬厉,复述刚刚过去不久的历史事件,实录与粉饰共存,才情与学识交辉,充分发挥了骈文润色鸿业、体国经野的特征。此时张之洞在翰林院教习庶吉士。庞坚认为这两篇文章:“铺张扬厉,藻采纷呈,褒美得宜,极受慈禧太后赏识,这为他之后的仕途亨通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20)《张之洞诗文集》“前言”,第4页。
文章开篇结合天文、地理、河岳的光明气象和祥瑞等夸赞当朝皇帝和太后的圣明:“钦惟我皇上虹璧当阳,龙图启运。灵台测景,值汉日之再中;柳谷占星,识尧天之无外。两宫垂训,孝治洽而钩钤明;六幕同文,威祾张而玉衡正。以圣继圣,秉大武于三曾;鞠人谋人,扬天声于七德。商威有截,轸驰桂海之文;姬箓无疆,策探岱宗之字。善继观成之志,有此武功;实惟懿德之光,受兹介福。睹瑶光七宿,为河海清宴之休征;考金版六韬,见旋转乾坤之经纬。”(21)《张之洞诗文集》,第264页。句式基本由隔句对而不是单句对组成,但有少量单对交错使用,故形式富赡工整而文气依旧流畅;遣词古雅,多用典故,风格雍容典雅。这种遣词、隶事和句式特征贯穿全篇。宋人洪迈说:“四六骈俪,于文章家为至浅,然上自朝廷命令诏册,下而缙绅之间笺书祝疏,无所不用。则属辞比事,固宜精策精切,使人读之激卬,讽味不厌,乃为得体。”(22)洪迈:《容斋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第505页。所谓“至浅”,说明在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打击下,四六骈文地位的卑微。而在骈散求对等地位的清代,此类代言体表文的开头,自然多用精工的骈体。文章接着对太平军发起时间、战争的残酷和毁灭性破坏等作了概述,然后转而对咸丰帝知人善任、用兵得宜,清军勇往直前、连战告捷的情形加以铺叙:
文宗显皇帝拯万方之厄,申九伐之经,欧刀行失律之诛,斋斧选折冲之将。懿亲藩卫,河间孝恭之贤;异姓名王,沙陀赤心之勇。廉颇、李牧,出自禁中;闳夭、泰颠,拔于材武。得狄青于西班,而任以专阃;收徐勣于归义,而用作干城。虞允文起自书生,岳家军出于义勇。知之而善任,用之而不疑。乃斡璇机,阐金策,以为欲倾孽窟,先据上游;欲折凶锋,先清三辅。河魁应将,井钺森芒;太乙陈军,雷硠郁怒。羊头鹤膝,尚方兰锜之兵;朔簳燕弧,六郡良家之子。鼓洪炉而烁毳,蒙汜以浇萤。鼓殷天,锋旗卷雾。老罴当道,先扼胜于天津;狂象走林,遂合围于连镇。赤龙吐电,挟炮石以飞鸣;铁骑凌霜,踏河冰而平渡。中黄士劲,筈矢三镰;太白旗高,冲輣百丈。长缨系贼,吉林诈马之健儿;飞火注枪,蒙古打生之蕃部。布周阹而刬地,晕月成规;拔渠答而逾濠,阵云如墨。剖巢入穴,桎贰负以归朝;饮刃伏椹,血温禺而衅社。高唐州一鼓而下,枭鸣牙中;冯官屯三版难支,蛙沈灶底。临戎鼓盖,人识高敖曹之容;破阵笳铙,军奏《兰陵王》之曲。投弓穷羿,果知射日之难;被发狂夫,始悔渡河之误。(23)同①书,第266页。
将主要由文臣武将,如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等人奠定的战绩归为咸丰帝的知人善任、用人不疑;又对清军与太平军交战的激烈场面,连用多种工整的隔对铺陈而出,形成了虎啸风生、排山倒海的气势。当然,文章也写了清军失利后善于吸取教训,精心谋划、稳打稳扎、步步为营的谋略和战绩,同样句式工整,大量使用隔句对偶。如果说前面的篇幅主要在写战争原因和战斗过程,接下来张之洞就专门歌颂咸丰帝的广纳贤才、殚精竭虑和英明仁慈等:
当是时,文宗显皇帝方以十科选士,五听求言。周宣侧身,汉文拊髀。神经《金匮》,授自九天;澄鉴银华,烛乎万里。发踪导窾,晨披白阜之图;昃食求衣,夜听赤囊之报。辍裘攽赐,千营衔挟纩之温;画箸伐谋,诸将决埋根之计。为民请命之语,恻怆于丹纶;胁从罔治之条,谆详于申命。七旬弗格,知顽恶之将歼;百六已过,卜贞元之必复。觇燕巢于齐幕,待槖牧野之弓;闻鹤语于尧年,遽铸荆湖之鼎。应门顾命,不忘未济之艰难;毕郢升祠,即兆大勋之底定。(24)《张之洞诗文集》,第267页。
在夸饰和铺陈中,刻画了咸丰皇帝“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光辉形象。接着,文章对同治帝继承父命、平定天平天国的功绩加以颂美。最后曲终奏雅,论述《剿平粤匪方略》的编订缘由,表达居安思危、金瓯永固之意,有曰:
前光垂宪,继序绍闻。用能苍縡孚精,珠钤制胜,下湔墋黩,上答光灵。文母冠十乱之勋,汤孙建四方之极。钧台誓众,瞻禹迹之重光;鄗邑升坛,告炎符之上瑞。北征《六月》,南征《采芑》,焕景命以重熙;内治《天保》,外治《采薇》,播休声为大恺。臣等依光丹地,载笔兰台,实均庆于普天,敢竭诚于测海。系年系月,知整军经武之有方;丕显丕承,著保大定功之有本。守难于创,绎魏征敷对之言;安不忘危,鉴宣圣系辞之训。订长编四百廿卷,宝笈常辉;祝鸿祚亿万斯年,金瓯永巩。东南尉而西北候,定皇舆一统之经;天地辟而日月光,上帝世六符之颂。(25)同上书,第270页。
全文遣词古雅,造句工整,结构细密,叙事清晰,气势流畅。作为润色鸿业之篇,难免溢美之词和偷天换日之术,将主要是文臣武将的功劳记在两朝皇帝和慈禧太后头上,但不得不说该文善于复述和润色史料,并用典雅生动的文学之笔表现出来,堪称骈文佳作。《恭进剿平捻匪方略表》的手法和结构、骈俪与隶事,都与本篇相似,同样具有富赡工整的特征。两文都是骈文名篇:“两表成,各两千余言,历叙发捻始末、兵势利钝、庙堂及诸大将方略如指诸掌,枢府惊叹,竟不能改易一字。”(26)张之洞:《抱冰堂弟子记》,载《张之洞诗文集》“附录四”,第663页。原书存放在馆阁之内,无法阅读,张之洞却能写出令上级不能“改易一字”、惊叹不已的文章,可见其才华之富、学问之深及见识之广。龚显曾认为张之洞经济、文章独冠一时,“胸罗经史百氏,学兼汉、宋诸儒,上而典册高文,下至一诗一赋,每有述制,同人咸敛手咋舌,咤为难逮。盖根柢既宏深,构思时尤冥搜苦索,博综繁稽,不苟落笔,故卓然为当代著作才”。这些文辞博雅的庙堂高文就是其“著作才”的主要代表。高凌霨评曰:“上窥班、马,下睨骆、卢。长卿凌云之赋,麟凤腾其光辉;子昇仙露之词,珠玉增其声价。”(27)高凌霨:《广雅堂骈体文笺注序》,载《张之洞诗文集》“附录二”,第523页。指出其骈文成就超越“初唐四杰”,媲美班固、司马迁,兼备司马相如、温子昇的辞藻和声律之美。这类“大手笔”骈文,以清军与太平军或捻军战斗的史料为依据,进行细节加工或修饰夸张,讲究行文的结构逻辑和叙述章法,从而摆脱了公牍表文的模式化,具有很强的独创性。这与他为文反对剿袭、浅俗,主张学古积学有关:“作为文章,以剿袭为逸,以储材为劳,读近人浅俗之文则喜,古集费神思则厌,甘仰屋以课虚,不肯学古而乞灵。虽日日为词章,无益也。用心之状,古书虽奥,必求其通,不能通者,考之群书,勿病其繁,问之同学,不以为耻。文章纵苦涩,勿因人纵蹈摹古之讥,勿染时俗之习。如此而不效,未之有也。”(28)张之洞:《创建尊经书院记》,载《张之洞诗文集》,第230页。
此外,《恭撰谕祭刑部左侍郎袁保恒文》《恭撰谕赐刑部左侍郎袁保恒碑文》《恭撰谕赐署乌鲁木齐都统、哈密办事大臣保恒碑文》分别为祭文、赐文、碑文,都是张之洞代朝廷所写。袁保恒(1826—1878)是晚清名臣,为袁世凯叔父,在平定捻军上战功卓著。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刑部左侍郎。1877年,回家奔丧,遇到河南特大旱灾,参与赈灾。积劳成疾,次年溘然长逝,谥“文诚”。他少随父袁甲三治军,谙练武事,曾先后佐李鸿章、左宗棠军幕多年,建立大功。祭文开始引经据典,比兴点题:“朕惟《周礼》重行人之选,赒彼凶荒;《雅》诗称从事之贤,伤其尽瘁。况际此需材之会,忽夺兹任事之臣。”然后顺势引入祭祀对象,对其道德、功业特别是军功加以铺叙:
赡智肫仁,瑰材闳器。羽仪华国,绮龄登瀛海之班;弓冶承家,雅志殄淮之丑。惟有文必有武,何敌不摧;资事父以事君,有功不伐。锡霸都之勇爵,超坊局之华资。一持分校之衡,屡负从军之羽。调和诸将,扫河朔之风尘;馈饷三秦,龛西陲之组练。度支入佐,薄算缗言利之为;刑宪分司,无钳网深文之习。(29)《张之洞诗文集》,第260页。
平定捻军,袁保恒随父袁甲三作战,功不可没。徐世昌《晚晴簃诗话》:“文诚弱冠入词林,从先德端敏公军中,夜佐草檄,朝履行阵,身经百战,名动九宸。历参合肥、湘阴军事,管西征馈餫。及以少司农内召,立朝謇谔,屡陈大计,恪守端敏家风。光绪初,晋豫久旱岁饥,文诚奉诏旋豫督振,以劳瘁卒。诗不多作,俊伟中见悱恻,信名臣之吐属也。”(30)徐世昌著,傅卜棠编校:《晚晴簃诗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1089页。最后,叙述河南遭遇干旱,袁保恒持节还乡积极参加赈灾,任劳任怨,以至积劳成疾,赍志而没。结尾尤其情感悲痛,气韵沉雄:“幸哉两河之更生,已矣九京之不作。以尔官亚九列,而立朝未满五年;以尔气雄万夫,而赋命不登中寿。未殚厥用,深恻于怀。于戏!罄方社之牺牲,竟丁耗斁;听泽中之鸿雁,永念劬劳。茂此饰终,庶歆昭奠。”(31)同①书,第260-262页。《恭撰谕赐刑部左侍郎袁保恒碑文》开头同样是铺垫,但不是用典,而是直接引出光绪帝的褒奖之语;然后再引入袁保恒,铺叙其家世、才能、志向和文才武略等,解释谥号“文诚”的来由,与祭文堪称“同题异构”,各有特色。《恭撰谕赐署乌鲁木齐都统、哈密办事大臣保恒碑文》则是为蒙古族保恒所写的碑文,褒扬保恒在西北边关作出的巨大贡献。同样是文辞博雅,骈俪工整。如写保恒保卫边疆、英勇善战的事迹:“簪袅勋门,珠钤将种。衍四卫拉特之贵族,气奋风云;读七大黄册之祕书,胸罗象纬。出为牙将,领银枪效节之都;继帅偏师,居黄河远上之地。属重臣经营西事,为国家荐举边才。一岁超迁,三边提控。甘泉烽火,惟资当道之王罴;滹水坚冰,不渡临流之铜马。”(32)同①书,第262页。声律抑扬顿挫,气势如虹。这些“大手笔”骈文,内容堂皇正大,虽为代言之作,但内容贴近现实,情感丰富,波澜起伏,感人至深。
三、表彰忠烈、宣扬教化的哀祭类骈文
除了这些反映当时重大事件的骈文外,张之洞还有较多宣扬仁义礼智、忠孝节义的骈文。无论在北京、山西还是在广东、湖北为官,他都致力于建书院、修祠庙,培养人才,表彰乡贤。与众不同的是,这些宣扬教化类的骈文,主要由哀祭类组成。《广雅堂骈体文》卷二的16篇中,含祭文9篇,内容都属于化民成俗,宣扬忠义;寿序4篇,启、颂、碑各1篇也多是如此。与晚清其他骈文别集多序跋、书启、赠序、辞赋相比,张之洞的骈文集包含的文体类别不多,但这些文章体现了这位官僚、文人和学者希望经世致用、振衰起敝的政治抱负。骈文,成为张之洞政治理想、学术思想和教育设想的重要载体。
张之洞以儒学为安身立命的根本,视之为立身、行道和为政的指导思想和精神支柱。在晚清西学东渐和救亡图存的背景下儒学遭遇了危机,变得不切实用而备受质疑,但他仍旧坚持不懈,坚守初心。他在各地为官时,都非常关心地方教育与民俗民风,热衷文教,重视各地先贤。为各地先贤建立祠庙,倡导纯正学风和优良民风。畿辅先哲祠、三君祠、七公祠、二公祠、濂溪祠、楚学祠、十贤祠等的建立,就是明证。通过祭文来表彰先贤事迹,宣扬忠节观念,如《祭畿辅先哲文》《祭汉虞仲翔唐韩文公宋苏文忠公文》《祭晋陶桓公唐宋文贞公明韩襄毅公王文成公国朝李恭毅公阮文达公林文忠公文》《祭关中节公天培张忠武公国梁文》《祭岳忠武王文》《祭吴文节公文》《祭罗忠节公文》等。这些骈文“小之足见其熔经铸史之才,大之足见其纬地经天之略,可作文学观,而不可仅作文学观也”(33)胡大崇:《书广雅堂骈体文笺注后》,载《张之洞诗文集》“附录二”,第528页。。祭文抒情应该讲求恭敬且悲哀,如果辞华而靡实,情郁而不宣,文品就不高。张之洞能在遣词造句、对偶押韵方面都打破常规,自成一格,词句求典雅,对偶讲工整,押韵不强求。
他早年所作《祭畿辅先哲文》就是为顺天、直隶的先哲祠而作。这些先哲包括历代圣贤、忠义、孝友、名臣、循吏、儒林、文苑、独行、隐逸等九类。文章开头用四七隔对点出乡邦与社祭的意义:“入国知教,圣人观王道于乡;以德为馨,古者祭先生于社。”(34)《张之洞诗文集》,第319页。随后切入到畿辅人杰地灵,各类先哲各有所长,均有功于名教,理应得到祭祀。全文说理清晰,文气流畅。此外,张之洞非常重视流寓广东或广东本籍的先贤,在骈体祭文中大力表彰。光绪十三年(1887),张之洞将广州城南的小蓬仙馆改为七公祠,以祭祀对广东发展“德业最著”的陶侃、宋璟、韩雍、王守仁、李湖、阮元和林则徐七位名臣,他认为这七位名臣“虽治术不同,要其功德沾被粤民,措施动关大计”。同样是重视地方文化,但这里更加注重事功,可见其表彰当与激励广东人民奋发有为、抵御外辱有关。他在广州修建三君祠,纪念东吴、唐、宋时代的虞翻、韩愈、苏轼,他们都曾寓粤。虞翻讲学不倦,门徒众多;韩愈政教兼施,化民成俗;苏轼济人化俗,惠州学子从风向学。他们都因忠直被贬,又都以文学教化岭表,文章气节,异代同符,因此合祠祭祀,并作《祭汉虞仲翔唐韩文公宋苏文忠公文》以颂之。文章开头总论三君立德、立功、立言,兼三不朽;历汉唐宋,为百世师。接着对三人的主要事迹,特别是经学、文学成就与忠君爱国的行为加以高度概括,说明建三君祠的目的是激扬忠谠之气,开启人文之光。张之洞还将七位对广东发展贡献很大的名臣放在一起,合写《祭晋陶桓公唐宋文贞公明韩襄毅公王文成公国朝李恭毅公阮文达公林文忠公文》。广东从汉代成为交州刺史治所,到清朝成为海疆重地,历代名贤著绩,不可胜数。“惟七公应北斗之星辰,作南天之柱石,运甓励澄清之志,教陶除回禄之灾。断大藤而靖诸徭,平三浰而收八寨。国朝名宦,不乏去思;南昌尚书,尤称弭盗。开名山之讲舍,筑列屿之敌台。经解大盛于皇清,舆图远搜于海国。虽仁经义纬,一时之治术不同;而外攘内安,千载之心源悉合。有功德于民则祀,微斯人吾谁与归?”(35)《张之洞诗文集》,第317页。高度评价七位大吏的主要功绩,表明自己的向往之心。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张之洞的祭文注重对太平天国运动、鸦片战争等重大事件的书写。罗泽南和吴文镕死于湖北战场,张之洞担任湖广总督的时间较长,任期内大兴教化,建忠贤祠等。《祭罗忠节公文》是为理学家兼儒将罗泽南而作,全文言简意赅但力重千钧,曰:
惟公学宗濂洛,功著湖湘,率义旅以同仇,挫凶锋而莫抗。迈南宋张彦闻之壮烈,教授提兵;媲前明王新建之遗风,军中讲学。英雄洒泪,甘遂志而结缨;部曲传心,终集勋而奏凯。怆怀战地,肇建崇祠,溯伟绩以难忘,洁明粢而祗荐。呜呼!按渭原之营垒,犹叹奇才;数鲁国之门徒,咸怀忠义。仰邀灵爽,庶冀来歆。尚飨!(36)同上书,第318页。
单对与隔对交融,隶事精妙,情深义重,气势恢宏,将罗泽南的为学与为人、治军与报国等饱含深情地表达出来,抒发了自己的敬仰之情。《祭吴文节公文》为吴文镕而作。有曰:“相兹魁阜,宜冠灵祠。攒白云黄鹤之遗墟,忆铁雨金风之英烈。呜呼!曾为门生,胡为故吏,拔人杰以佐中兴;陶殉城守,唐殉水师,结同心而完大节。永瞻正气,祇荐维馨。”(37)同上。同样读来令人觉得忠愤气填膺,大义凛然。1888年,张之洞建关天培(1781—1841)、张国梁(1823—1860)二公祠于珠海,作《祭关中节公天培、张忠武公国梁文》:
惟二公关、张华胄,褒鄂英姿,勇略奋于风云,忠诚耿乎日月。溯自岛夷萌蘖,赭寇狓猖,一则当番舶内犯之初,首遏长鲸于炎海;一则际中原糜烂之会,独摧封豕于金陵。王濬乃水中之龙,敖曹实地上之虎。篇成《筹海》,志清欧亚诸洲;军比撼山,力保苏、杭半壁。天颜有喜,亲承召对于五番;宸翰亲挥,诏进图形于两本。徒以魏绛狃和戎之议,卫青挠飞将之权。啮指痛而空壁无援,量沙饥而长城遂坏。此则英雄未捷,为今古所同悲;功烈不刊,推中兴之首出者矣。兹者双忠并祀,五岭同高,餍馨香百代之人心,厉水陆三军之士气。虎门截海,难平伍庙之云涛;羚峡撑天,争附征南之旧部。于戏!天上双腾之剑气,豹死而皮常留;波心一颗之珠光,海枯而石不烂。(38)同上书,第315页。
关天培是江苏人,在广东担任水师提督时,英勇抗击英军侵略,壮烈牺牲。张国梁是广东人,在江苏围剿太平军,被李秀成所杀。从维护清朝的角度出发,张之洞对这两位英雄的勇敢和忠诚、气节和功业作了简要论述,摆脱了传统哀祭文押韵的格式,以散行之气,运俳偶之文,读来令人心潮澎湃,无限向往。全文堪称“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苗民在论述明代四六启的礼文属性时,认为:“四六启文体形式层面彰显礼仪的特性正使得其在表述这种‘大抵其德不可称而必欲称之,其事不足述而必欲述之’的内容时,有‘舍此体其谁’的效果。”(39)苗民:《应俗的“礼文”:明代四六启的“礼文”属性及其价值探讨》,《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1期。而张之洞的骈体祭文,对象都是有“德”可称,有“事”足述,故能避免格套,情文并茂。
时人认为最能代表张之洞文章成就的奏议,就文体属性而言,多属骈文。但因其成就突出,加上属于上行文,体裁独特,故单独列出。在义和团运动中,张之洞和刘坤一等倡议东南互保,没有向列强宣战,为清廷保存了东南疆土,稳定了财税收入等。事后(1901年)得到朝廷嘉奖,张之洞赏加太子太保,上《谢赏加太子少保衔摺》。该文也是一篇典型骈文。何圣生《檐醉杂记》评此段文字曰:“文襄于各体文字皆极矜炼,此尤其经意之作。典雅深厚,在宋人《播芳文萃》中端推上乘矣。”(40)《张之洞诗文集》“附录三”,第539页。就是以宋人四六成就来映衬的。
相对于宋代四六偏于诏诰、表启,主要发挥庙堂应用功能,作者多是高级官员来说,清代骈文文体范围扩大,序跋、论辩、杂记等都大量运用,从而使得清代骈文具有浓郁的抒情性,更多是由怀才不遇、沉沦下僚的文士来写,如陈维崧、吴绮、胡天游、邵齐焘、汪中、洪亮吉等。因此,整体来说,清代骈文中的庙堂内容所占比例很低。而张之洞的现存骈文,记载晚清大臣袁保恒、保恒、冯子材、李鸿章等的重要事迹,概述当时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熔铸经史,茹古涵今,结构宏伟,气象峥嵘,堪称清代乃至中国骈文史上的“大手笔”。庞坚认为“凭这二十几篇骈文,张之洞足可确立其清代骈文名家的地位”(41)《张之洞诗文集》“前言”,第33页。,当为的论。
综上所论,可知张之洞在骈文上主要学习宋四六诏诰、奏之文,故被一般学人视为清代骈文中“宋体”的代表。但是,张之洞又将盛唐“燕许大手笔”的博大内容、雍容风格与宋四六的句式特点融会贯通,形成超越宋体的特征。“文襄生平于书无所不窥,故其发为文字,昭明宏伟,陶铸事物,驱使卷轴,无斧斫襞绩之痕,猝不易省其所自出。”(42)王彭:《广雅堂骈体文笺注序》,载《张之洞诗文集》“附录二”,第527页。这里的“文字”,主要当指铺张扬厉又讲究隶事无痕的骈文。明白晓畅又宏大雄伟,正是其主要特征。宋四六体骈文,清人多评价不高。孙梅说“盖南宋文体,习为长联,崇尚侈博,而意趣都尽,浪填事实以为著题,而神韵浸失,所由以不工为工,而四六至此,为不可复振也”(43)孙梅著,李金松校点:《四六丛话》,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第663页。。俞樾在《春在堂笔录》中也批评宋人骈文中的长联对冗长拖沓,贪用成句,又以议论行文,从而导致文体卑陋。对于宋人剪裁成语,钱基博指出“六代初唐,语虽襞积,未有生吞活剥之弊,至宋而此风始盛,运用成语,檃栝入文;然有馀于清劲,不足于茂懿”(44)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 骈文通义》,第112页。。张之洞的骈文基本摆脱了宋四六的长联对、大量运用前人成语等特征,堪称自成一家。
四、背离原因及张之洞对晚清骈文的影响
张之洞的骈文融汇了盛唐典雅富赡的“燕许体”和宋四六对偶工整、隶事精妙的特征,与他在《书目答问》《輶轩语》等书中推崇晋宋体的倾向明显不同。这种理论和创作的不一致,一方面是他署名的专书中,有的只是名义上的撰写者,其观点与他本人的实践态度并不一致;另一方面,个人的通达经历和宏大视野,决定了他创作骈文难以学习晋宋体的清丽形式和主要书写个体情感的内容。动荡的时代和多难的政局,需要位居高位的他撰写庙堂高文及表彰忠义、宣扬教化的骈文。
张之洞虽然撰写并由门人编定了《广雅堂骈体文》,但他对于骈文盛行的六朝之道与文,都是批判和不满的。这在其《哀六朝》诗中表现最为突出:“古人愿逢舜与尧,今人攘臂学六朝。白昼埋头趋鬼窟,书体诡险文纤佻。上驷未解昭明《选》,变本妄托安吴包(世臣)。始自江湖及场屋,两汉唐宋皆迁祧。神州陆沉六朝始,疆域碎裂羌戎骄。鸠摩神圣天师贵,末运所感儒风浇。玉台陋语纨袴斗,造象别字石工雕。亡国哀思乱乖怒,真人既出归烟销。”(45)《张之洞诗文集》,第78页。对时人学六朝诡异书法、纤佻诗文的倾向加以批评。这不仅是因为六朝文品、书艺不佳,更因六朝是乱世,戎狄骄纵,佛道盛行,儒学衰微,亡国之音流行,雅正之风衰微——这是他深恶痛绝的。1909年,张之洞去世,好友陈宝琛撰墓志铭,认为他:“为学兼师汉宋,去短取长,恶说经袭《公羊》、文字模六朝,谓为权诡乱俗。”(46)《张之洞诗文集》“附录一”,第506页。说他厌恶《公羊学》,因为公羊学者往往托古改制,诡异乱俗;说他厌恶六朝文字,则当指他鄙视六朝的华而不实的文章。李详也云:“张南皮之洞《抱冰堂弟子记》,实自撰也。云最恶六朝文字,谓南北朝乃兵戈分裂,道丧文敝之世。凡文章本无根柢,词华而号称六朝骈体者,必黜之。吾友上元周左麾钺,于壬寅(1902)客南皮幕府,言南皮极不以胡稚威等骈文为然,谓‘以艰深文其浅陋’。今观此言,益信。”(47)李详:《愧生丛录》卷四,载《张之洞诗文集》“附录一”,第539页。六朝南北分裂,僭越不断,确实是“道衰词华”之世。张之洞厌恶六朝骈体,不认同胡天游的骈文,正是对六朝政治、士风不满,从而延伸到六朝骈文的结果。徐世昌、王树枏等编纂《大清畿辅先哲传》,也说张之洞“最恶六朝文字,谓纤仄拗涩,强凑无根柢,道丧文敝,莫甚于此”(48)徐世昌等:《大清畿辅先哲传·张之洞传》,载《张之洞诗文集》“附录一”,第501页。。在这种文章思想的主导下,张之洞自然难以学习“晋宋体”骈文并努力践行。
毋庸讳言,在特定的场合和语境中,张之洞还反对使用骈文。光绪二十三年(1897),他上疏变法,提出改革科举内容与文体文风:“一曰正名。正其名曰《四书》义、《五经》义,以示复古。二曰定题。《四书》义书《四书》原文,《五经》义书《五经》原文,不得删改增减,亦不得用其意而改其词。三曰正体。以朴实说理,明白晓畅为贵,不得涂泽浮艳,作骈俪体;亦不得钩章棘句,作怪涩体。四曰徵实。准其引徵史事,博考群书,凡时文所禁忌者悉与蠲除。五曰辟邪。若周、秦诸子之谬论,释、老二氏之妄谈,异域之方言,报馆之琐语,凡一切离经叛道之言,严加屏黜,则八股之格式虽变,而衡文之宗旨仍与真正之圣训相符。”(49)同上书,第492页。反对科考使用“骈俪体”和“怪涩体”,与后来新文化运动中胡适、陈独秀的文学改良革命论中的观点相近。不过,张之洞是希望通过改革制艺文体与文风以复兴古学,消除离经叛道之言,维护儒家道统,目的显然与胡适、陈独秀不同。
张之洞对晚清骈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主要是通过其创办的书院来实现的。他非常重视人才培养,认为谋国立基,以人才为先,辅之以器械与地利,这样才能救亡图存,与时俱进。他认为天下物情事势,不外政治和学问两途,其表在政,其里在学。 在致用思潮的影响下,他通过创办书院来培养人才。1869年在武昌创立经心书院,1873年在成都创建尊经书院,1882年在太原创立令德书院。教育内容主要为经史与辞章,骈文为其辞章中的重要内容。无论是在湖北经心书院还是在四川尊经书院,他都效法阮元在诂经精舍和学海堂所为,重视经史和辞章之学:“选高材生百人肄业其中,延聘名儒分科讲授,手订条教,略如诂经精舍、学海堂例。”(50)胡钧:《张文襄公年谱》,载《张之洞诗文集》“附录五”,第698页。可见肯定的说,张之洞因为身份和学养、仕宦经历等与阮元的相似性,其为官为学与为文,都深受阮元的重要影响。阮元在书院教育中对骈文的重视,当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
张之洞为学通达,善于革新;为文重视诗赋、古文、骈文各体,不名一体。他对守旧而不知变、喜新而不知本的现象都加以批评,反对学术上的门户之见。“学术有门径,学人无党援。汉学,学也;宋学,亦学也;经济、词章以下,皆学也;不必嗜甘而忌辛也。大要读书宗汉学,制行宗宋学。汉学岂无所失,然宗之则空疏蔑古之弊除矣;宋学岂无所病,然宗之则可以寡过矣。”(51)张之洞:《创建尊经书院记》,载《张之洞诗文集》,第231页。各不偏废,不抱一而自足,是此而非比。对汉宋之弊,心知之而不攻之或争之。在成都尊经书院中,张之洞认为经史根柢深厚而不工词章者少,故从“既惩其情,又惜其力”出发,“月至二课”“课止四题”,即经解一、史论一、杂文与赋为一、诗一;其中赋与杂文不并出,杂文或骈或散惟宜。(52)《张之洞诗文集》,第234页。规定杂文与赋为月课四题之一,杂文中使用骈体、散体都可。这对晚清四川地区骈文的发展,无疑起到了促进作用。1887年,张之洞担任两广总督。为了培养精于洋务又熟悉经史辞章的人才,他创办广雅书院。首任学长为梁鼎芬,后任有朱一新、廖廷相、邓蓉境、谭莹、丁仁长等。课程分为经学、史学、理学、文学四门,学生可自由选择;同时要求兼习诗赋、古文或骈文等文章之学。学长中有著名骈文家朱一新和谭莹等,课程中的文学包括赋、骈文之学的兼习,给两广地区的读书人提供了良好的创作氛围,无疑促进了当地骈文的发展。
张之洞思想融通,不固执己见,作茧自缚,而是著书立说宣扬其思想;又能兼容并包,与晚清著名骈文家为友,邀请他们到书院讲学,这客观上也促进了晚清骈文的发展。早年他在京城倡导龙树寺雅集,汇聚了当时大批著名文士,如王闿运、李慈铭、赵铭、谭宗浚、王咏霓、张预等著名骈文家都参加或受邀参加其主持的雅集。1867年,他担任浙江乡试副考官,袁昶、许景澄、陶模、孙诒让、谭献等都考中举人,其中谭献是晚清著名的骈文家。谭献晚年还应张之洞之约,主讲经心书院:“庚寅辛卯,座主南皮张尚书督两湖,招之至江夏,聘主都会经心书院讲席,遂为院长两年矣。书院为公视学日所创立,一以文达公西湖诂经精舍为规模,以吾乙丑后,尝为精舍监院,习旧闻,非必学行足式高才诸生也。”(53)谭献:《复堂谕子书》,载罗仲鼎、俞浣萍点校:《谭献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第684页。谭献在这里度过了一生中最为快乐的两年时光,可见张之洞对他的照顾。屠寄(1856—1921)两次入张之洞幕府,担任广雅书院、两湖书院教习。他不仅有自己的骈文集,还编选了《国朝常州骈体文录》。晚清知名骈文家易顺鼎也是张之洞的门人。张之洞有《谢易实甫饷庐山茶蔌》《谢易实甫再惠庐山三峡泉》《腊月十六日邀汪进士、陈考功、易兵备、杨舍人至两湖书院讲堂看雪月,余以畏寒头疼先归》等诗。朱铭盘(1852—1893)是张之洞的学生,有《桂之华轩遗集》,其中文章全为骈文。通过担任浙江乡试副考官、湖北学政、四川学政、两广总督等重要职务,创办书院和各类学堂等,张之洞培养了一批学术、经济与辞章人才,包括骈文人才。这对晚清政治、经济、文化、科举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背景下,新学、旧学之争异常激烈。面对新旧碰撞及新学的流行,旧学的衰微,张之洞非常忧虑。光绪三十三年(1907),他上《创立存古学堂折》,提出专门开辟存古学堂,教育学生学习经学、史学和辞章之学,以保存国粹,传承文化,维护人伦价值观念等。他从爱乡爱国、心善敬祖、阐明道德、维持世教等方面论证存古学堂主要开设国文课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强调经学、史学和辞章之学的重要:
数门之中,经学为一门,应于群经中认占一部,《说文》《尔雅》学、音韵学亦附此门内。史学为一门,应于《廿四史》及《通鉴》《通考》中认占一部,本朝掌故即附此门内。词章为一门,金石学、书法学亦附此门内。以上或经或史,无论认习何门,皆须兼习词章一门。而词章之中,但专习一种,即为合格。或散文,或骈文,或古诗、古赋。皆可兼习者,听博览为一门。(54)张之洞:《张文襄公奏议》卷六十八,民国刻《张文襄公全集》本。
辞章不仅与经学、史学课程三足鼎立,且专习经学的学生,也应该兼习辞章。辞章当中,骈文也赫然在列。可见,骈文与古文、古诗、古赋一样,都是传承文化、维持世教的重要载体,不可自我决绝。
总之,张之洞的诗文成就高,影响大,徐世昌等编的《大清畿辅先哲传》就说他“以文章道德主盟坛坫者数十年。五洲之士,皆仰之为中华山斗”(55)《张之洞诗文集》“附录一”,第503页。。但相当程度上,这被他的政治、教育等事功遮蔽了,如《清史稿》《清史列传》的本传,都没有涉及其文学成就。事实上,其骈文典雅高华,影响甚大,故在民初被郭中广和陈崇祖加以笺注,广为流行。在民初新学流行、旧学贬抑的背景下,笺注具有继承风雅、振兴古学的意义。1925年,高凌霨为《广雅堂骈体文笺注》作序曰:“沧海流横,敷天日蚀,艺林之珠丛全碎,诗人之玉屑都沉。敝帚谁珍?《汉简》奚益?览作述于兹编,辄有感于斯文。”(56)《张之洞诗文集》“附录二”,第523-524页。同年,朱士焕跋曰:“今文襄鸿文震耀,风格既驾两太史而上之,而献侯用力之勤,亦不让程、黎。值此旧学孤鸣之秋,得此编刊行于世,可以使览者知当时学术之昌,文献之盛,岂仅衍师门之薪火已哉!”(57)朱士焕:《广雅堂骈体文笺注跋》,载《张之洞诗文集》“附录二”,第529页。不仅认为张之洞的骈文风格凌驾陈维崧、袁枚,还肯定陈崇祖用力之勤,不减程师恭和黎光地对陈、袁骈文的笺注;同时,特意指出在旧学衰微的时代,笺注张之洞骈文集的学术价值和文献意义——繁荣学术、传承师学和赓续传统。这也是今天我们研究张之洞骈文的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