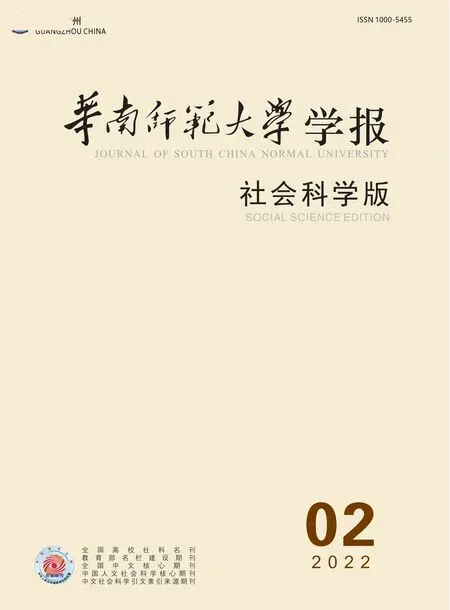从“小谢”到“三谢”:古近之辨与谢惠连的诗史地位
吴晋邦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陈郡谢氏是六朝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族,先后涌现谢混、谢瞻、谢灵运、谢惠连、谢庄、谢朓等诗人,对后世影响巨大。诸人中,“大谢”谢灵运作为元嘉诗人的代表,在文学史上一直占有较高地位,与之相对的“小谢”则经历了从谢惠连到谢朓的变化过程。谢惠连享寿不永,作品散佚较多,学界关注相对较少,相关研究集中于“谢惠连体”与《雪赋》等著名作品。(1)如Stephen Owen. “Hsieh Hui-lien’s Snow Fu:A Structural Stud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94, No.1(Jan.- Mar.,1974); 曹道衡:《从〈雪赋〉〈月赋〉看南朝文风之流变》,《文学遗产》1985年第2期;刘传芳:《谢惠连考论》,硕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文学院,2008;孙玉珠:《谢惠连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文学院,2010,等。另参见王运熙:《乐府诗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学史料丛考》,中华书局,2003,等。就“小谢”指称这一问题而言,笔者管见所及,仅有对李白诗中“小谢”指称的讨论。“小谢”最初何以称谢惠连,又为何移置至谢朓名下?宋代以来,谢惠连与谢灵运、谢朓并称“三谢”,这种称谓的背后体现出怎样的诗学思想?本文从谢惠连代称的变迁这一角度出发,考察其文学地位的升沉历程与其中所关涉的诗学命题。
一、推崇惠连:《诗品》中的“小谢”
“小谢”之称,始见于钟嵘《诗品》对谢惠连的品评“小谢才思富捷”(2)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第372页。。考之年辈、成就,与之相对的“大谢”自属谢灵运无疑。与后世谢朓声名大噪、谢惠连湮没无闻的状况不同,钟嵘在《诗品》中对谢惠连大加赞赏,对谢朓却颇有微言。
试观《诗品》对二人的评语:
小谢才思富捷,恨其兰玉夙凋,故长辔未骋。《秋怀》《捣衣》之作,虽复灵运锐思,亦何以加焉。又工为绮丽歌谣,风人第一。(宋法曹参军谢惠连)(3)《诗品集注》(增订本),第372页。
其源出于谢混,微伤细密,颇在不伦。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足使叔源失步,明远变色。善自发诗端,而末篇多踬,此意锐而才弱也,至为后进士子之所嗟慕。朓极与余论诗,感激顿挫过其文。(齐吏部谢朓)(4)同上书,第392页。
谢灵运、谢惠连皆元嘉诗人,上距《诗品》成书八十余年;谢朓是钟嵘的同辈,在《诗品》成书时也已去世。(5)关于《诗品》的成书时间,参见《诗品集注》(增订本),前言第10页。谢灵运文声斐世,在世时便为公认的大家巨擘。《诗品》上品十二家中,从古诗至左思的十一家皆在汉晋之间,西晋以后的二百年内惟谢灵运一人获此殊评。钟嵘谓其“才高词盛,富艳难踪”,又谓“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曲新声,络绎奔发。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6)同①书,第34、201页。,其称道可见一斑。钟嵘将谢惠连与灵运并论,既是鉴于二者关系密切、酬和频繁,也是对惠连五言诗的称许。才思富捷、善于创作绮丽歌谣的评价,就谢惠连现存作品来看是较为公允的。谢惠连现存乐府十三首、五言诗二十一首,钟嵘标举的《秋怀》《捣衣》等篇什皆入《文选》而广为流传。谢惠连与谢灵运交游日久,诗风有一定相近之处,研究者已指出二者长于铺叙、工于锤炼字句等共性。(7)参见丁福林:《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刘传芳:《谢惠连考论》;孙玉珠:《谢惠连研究》。江淹、萧纲等人皆有摹拟谢惠连风格之作,时人论诗亦有“追步惠连”(8)王筠赞谢贞《春日闲居》诗可“追步惠连”,见姚思廉:《陈书》,中华书局,1972,第426页。之赞,足见谢惠连在六朝时期尚有一定的影响力。谢惠连虽年辈较晚,但享寿不永,与谢灵运同年去世。谢惠连才力不及乃兄,风貌差近。其能获得钟嵘的好评,与此有着很大关联。
钟嵘在激赏谢灵运、揄扬谢惠连之余,面对与自己同时的谢朓则褒贬兼具。在序言中,钟嵘便已针砭当时风气谓“次有轻薄之徒,笑曹刘为古拙,谓鲍照羲皇上人,谢朓今古独步”(9)同①书,第69页。,对风靡一时的谢朓颇不以为然。钟嵘认为谢朓源出仅属中品且“才力苦弱”的谢混。上溯源流是《诗品》重要的批评方式,以一位具有明显瑕累的诗人作为谢朓诗风之源,体现出钟嵘对谢朓的不取之意。至于论其诗多细密不伦、卒篇不佳、才弱而少顿挫,则是更为实际的批判。自然,钟嵘也欣赏谢朓诗中的奇秀之处,然褒不掩贬的倾向甚为明显。钟嵘创作《诗品》时,沈约、谢朓、王融等所代表的永明诗人已然兴起,诗歌处于从古体向近体转变的发轫时期。在这一转折阶段,钟嵘的文学审美仍重古体,对影响巨大的“永明新体”态度并不积极。这种在当时并非主流的消极态度直接影响了《诗品》对谢朓的评价。沈约谓谢朓诗“二百年来无此诗也”,梁武帝“不读谢诗三日觉口臭”,加之《诗品》所记载的后进士子对谢朓诗的喜爱,足见当时谢朓诗歌已经获得了从上而下的广泛认可。(10)萧子显:《南齐书》,中华书局,1972,第826页;阳玠撰,黄大宏校笺:《八代谈薮校笺》,中华书局,2010,第232页。但在排斥用典、不重声病的钟嵘看来,谢朓所代表的这种新风潮对诗歌发展并无必要,反而造成古风的沦丧。钟嵘所秉持的较为保守的文学观,并不能完全反映时代风气。齐梁以还,“永明体”进一步得到发展并脱胎出近体诗的体式,谢朓亦广受赞誉,影响日盛。
鉴于谢灵运在诗史上的崇高地位,与“大谢”对称的“小谢”无疑是一种尊称。在钟嵘创作《诗品》时,这一名号被赋予谢惠连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当时距离晋宋之际未久,谢惠连的诗赋保存状况当胜后世,时人更加熟悉其人其诗。谢惠连与谢灵运既为从兄弟,酬和又多,与“大谢”并举自是理所当然,晋宋之间的谢氏家族亦无第二人能当此名。谢朓虽受时人追捧,然其“变多于复”的创作尚未获得所有人的接受,不喜“永明新体”的钟嵘自然不会将此名号赋予谢朓。齐梁以降,谢惠连作品散佚,影响渐微,已不能与谢灵运、谢朓相提并论。唐人推重谢朓而不重惠连,在钟嵘写作《诗品》的时代便早已埋下伏笔。
二、低首宣城:唐人对谢朓典范地位的确立
王士禛《论诗绝句》:“白纻青山魂魄在,一生低首谢宣城。”(11)王士禛著,李毓芙、牟通、李茂肃整理:《渔洋精华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第327页。虽专论李白,实可作为唐人推重谢朓的不刊之论。元兢《诗人秀句序》已以谢脁为“小谢”并将“小谢诗”作为典范加以阐释,盛唐后“小谢”彻底转称谢脁。盛唐后“小谢”彻底转称谢朓。谢惠连在唐代的影响力甚微,难以与谢朓相较。谢朓广受唐人推崇甚为明显,学界对此已有大量研究。初唐诗坛承续齐梁诗风,整个8世纪则是“律诗的世纪”(12)吴光兴提出八世纪为“律诗的世纪”,见氏著:《八世纪诗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谢朓作为最杰出的永明诗人,在这两种体系中无疑都是赫赫前辈。中唐以来,诗人对谢朓的接受更为多元,其诗中的吏隐、友谊、乡情、山水,成为唐诗的重要主题;其遣词造句的方式,也得到唐人长久的效法,终唐一代,流波深远。(13)参见蒋寅:《大历诗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第27-37页。
龙朔年间,元兢、刘祎之、范履冰等人对“小谢诗”已有较多讨论。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则是盛唐诗人指称“小谢”的典型。由于此前谢朓罕有“小谢”之称,故有学者认为此处的“小谢”乃指谢惠连而非谢朓。(14)主此“小谢”为谢惠连的其他论据包括李白《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有“群季俊秀,皆为惠连;吾人咏歌,独惭康乐”句;诗题中“谢朓楼”字样使人望文生义。详见赵善嘉:《“小谢”并非指谢朓》,《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4期。按,《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引康乐、惠连乃为切合从弟典故,与谢朓无涉;诗题虽有异文,诗作于宣州则无疑问。谢朓为宣州名贤,谢惠连则与宣州无涉。此数端恐皆难成立。考虑到此前的元兢、同时稍后的李嘉祐、皎然等诗人皆已称谢朓为“小谢”,此诗又作于谢朓曾出守的宣州,此处“小谢”指谢朓无疑。李白一生倾慕谢朓,“玄晖难再得,洒酒气填膺”,“解道澄江静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其尊崇之意溢于言表。蒋寅指出谢朓乃大历诗人的偶像。大历以还,“小谢”指称谢朓已然司空见惯:
萧条人吏散,小谢有新诗。(李嘉祐《和都官苗员外秋夜省直对雨简诸知己》)(15)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第2153页。
常爱谢公郡,幽期愿相从。(皎然《奉和崔中丞使君论李侍御登烂柯山宿石桥寺效小谢体》)(16)同上书,第9199页。
小谢才难比,诸荀道亦俱。(张祜《投宛陵裴尚书二十韵》)(17)陈尚君辑校:《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1992,第214页。
敬亭山下百顷竹,中有诗人小谢城。(杜牧《自宣州赴官入京路逢裴坦判官归宣州因题赠》)(18)《全唐诗》,第5948页。
前两例取吏隐之意,后两例关合宣州故事,皆指谢朓。中唐以来,唐人引谢朓诗句时亦往往呼之“小谢”:
小谢诗云:“虽无玄豹姿,终隐南山雾。”(李匡文《资暇集》)(19)李匡文:《资暇集》,中华书局,2012,第184页。
小谢轻埃日日飞,城边江上阻春晖。自注:小谢《咏雨诗》有“散漫似轻埃”句。(陆龟蒙《春雨即事寄袭美》)(20)同②书,第7177页。
白居易有《草词毕遇芍药初开因咏小谢红药当阶翻诗以为一句未尽其状偶成十六韵》诗,亦如是称呼。(21)同②书,第4943页。唐代传世文献中的“小谢”皆称谢朓,这一尊称已彻底确定。
与谢朓相比,谢惠连在唐代的接受状况较为冷清。唐人诗文中对谢惠连的称引集中于兄弟间的酬赠、咏雪时的用典,范围狭窄,并不能代表唐人对其有诗史上的定位与认同。如王维《赠从弟司库员外絿》“惠连素清赏,夙语尘外事”(22)同②书,第1237页。,司空曙《送魏季羔游长沙觐兄》“惠连仍有作,知得从兄酬”(23)同②书,第3333页。,又高适《苦雪》“惠连发清兴,袁安念高卧”(24)同②书,第2215页。,皆为此类。谢惠连的五言古诗在唐代仍有追慕者。任希古《和李公七夕》自注“谢惠连体”,全篇仿谢惠连《七月七日夜咏牛女诗》,篇章结构、联内句法多同,因袭明显。(25)同②书,第544页。李绅《泛五湖》亦自注“效谢惠连”,仿谢惠连的名篇《秋怀诗》。两诗皆十六韵,韵部相同,情思亦近。(26)同②书,第5464页。这些案例表明谢惠连在唐代并非全然湮没无闻,然谢惠连体五古在唐代的风行程度自然不能与谢朓相提并论。在这样的情况下,“小谢”转称谢朓便显得合情合理。
在“小谢”指称转移的同时,唐代出现了“二谢”并称的提法。杜甫《解闷十二首》(其六)自述其诗学思想,云“孰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唐语林》中所载的杜甫轶事,亦谓其自称“使昭明再生,吾当出刘、曹、二谢上”(27)王谠撰,周勋初校证:《唐语林校证》,中华书局,1987,第172页。。 “二谢”何指,宋人已多有歧议。北宋的邓忠臣(即伪洙注)谓指谢灵运、谢朓,《九家集注杜诗》同此说,黄鹤、赵次公则谓指谢灵运、谢惠连。杜甫集中对前辈诗人多有涉及,然鲜及惠连,诗中仅见的“报与惠连诗不惜”乃酬赠之典,并非文学评价。观杜甫诗中“谢朓每篇堪讽诵”,“绮丽玄晖拥”(28)杜甫著,谢思炜校注:《杜甫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第1121、2287、2424页。等称扬谢朓之语,此处的“二谢”仍指谢灵运、谢朓为是。中唐李翱、李观等称赞孟郊时亦谓其体兼“二谢”,考虑到唐人鲜少从文学层面述及谢惠连,“二谢”又是作者在推荐他人时不无夸张的比较对象,这一并称亦当如上解读。(29)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第5265页; 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第114页。
唐代是中国古典诗歌诗体完备的时代。从汉魏而来的古诗传统与从“永明体”生发而出的近体律诗,在唐代都已发展成熟;谢灵运、谢朓分别作为两个传统的重要诗人,皆为唐人敬服效法。在这一过程中,谢灵运的影响力较之近体未兴的时代已有一定下降。学者已指出,随着声律审美受到重视,谢灵运的文学史地位出现了明显的失落,在唐宋以后甚至到了“不为人识”(30)李晓红:《永明声律审美的继古与新变——兼及谢灵运文学史地位之失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的地步。谢灵运的地位尚有此陨落,与其风格相类而水准逊之的谢惠连自然更甚。唐代密迩六朝,对“小谢”的归属有着决定性作用。此后,虽有论者出于各种理由重新注意到谢惠连,然一般概念下“小谢”指称谢朓已成不可移易的事实。
三、标举“三谢”:宋元人对谢惠连文学价值的发掘
“小谢”指称谢朓在唐代以后已成定局,但宋代以来谢惠连的文学价值又重新得到发掘。虽然唐人十分推崇谢朓,但“二谢”的指称直至宋代尚并没有确定下来。上文已述及宋人对杜诗中“二谢”的不同解读。由于谢氏家族名人、轶事众多,宋元时期的“二谢”包含多种组合,拥谢惠连、谢朓者各有其人:
诗人首二谢。灵运在永嘉,因梦惠连,遂有“池塘生春草”之句。玄晖在宣城,因登三山,遂有“澄江静如练”之句。(葛立方《韵语阳秋》)(31)葛立方:《韵语阳秋》,载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2004,第483页。
(谢逸、谢薖)时称二谢。吕居仁云:无逸似康乐,幼槃似元晖,真足追配古人。(《两宋名贤小集》本《溪堂集》卷首)(32)陈思编,陈世隆补:《两宋名贤小集》卷三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二谢联诗而刻木。若耶溪有潭,潭有栎木。谢客时与弟惠连作诗联句刻于木上。(《舆地纪胜》新昌县条)(33)王象之:《舆地纪胜》,中华书局,1992,第533-534页。
昔谢康乐善为诗,每见从弟惠连辄得佳句,至今人称二谢。(程端学《跋夏氏诗文》)(34)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32册,凤凰出版社,1988,第178页。
诗自曹刘至二谢,日趋于工,然犹未以联属校巧拙。灵运自夸“池塘生春草”,而无偶句亦不计也。及沈约、谢朓竞为浮声切响,自言“灵均所未睹”,其后浸有声病之拘……极于唐人而古诗废矣。(叶适《习学记言》五七言律诗条)(35)叶适:《习学记言序目》,中华书局,1977,第705页。
吕本中、葛立方皆处南渡之时,以谢朓配灵运,主要考虑到二人的文学地位。以惠连配灵运者,则主要源于二人的兄弟交情。其他的“二谢”还包括谢灵运、谢瞻(因其同在戏马台赋诗),谢安、谢万(因其皆为将相),谢庄、谢惠连(因其有《雪赋》《月赋》)等。宋元之际,《小学绀珠》《敏求机要》等类书中的“二谢”条目多取谢安、谢万之说,这也表明“二谢”并非是大小谢的简单并称,此时尚未固定下来。所引叶适一条则表明,在南宋中期已经出现了将谢灵运、惠连视作古体代表,而对谢朓颇有不取之意的论调。这与唐人的评价已大相径庭。
这向我们透露出谢惠连重新得到重视的原因。北宋晚期唐庚从《文选》中辑录谢灵运、谢惠连、谢朓三人的作品为《三谢诗》,已有此倾向。唐庚认为,谢庄诗不见于《文选》,谢瞻、谢混之诗未工,唯有谢惠连诗可附骥于大小谢之后。唐人仅标举谢灵运、谢朓,唐庚此论自然是对谢惠连文学价值的肯定。唐庚亦强调了“三谢”之间的异同。其云“三谢诗,灵运为胜”,又云“诗至玄晖语益工,然萧散自得之趣亦复少减,渐有唐风矣。于此可以观世变也”。(36)魏庆之辑,王仲闻注解:《诗人玉屑》,中华书局,2007,第400-401页。在古体、近体皆已发展完备、分庭抗礼的时代,诗人回首“三谢”演变时仍以谢灵运为最佳,并认为谢朓在由古向近的转变中诚有所得,然亦有所失。谢惠连诗风近谢灵运,宋代以来称道惠连者多从这种古近之辨出发。就近体而言,谢惠连自然地位有限;而在尊崇古体者看来,谢惠连诗尚存古风,有其自身价值。
南渡之后,“三谢”逐渐成为常见的文学称谓。《苕溪渔隐丛话》转引《后山诗话》谓王安石“然学三谢,失于巧耳”(37)胡仔纂辑,廖德明校点:《苕溪渔隐丛话(前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第222页。。单行本《后山诗话》又作“二谢”,孰是孰非,已不易断,然此实“三谢”已为南宋前期时人接受之一证。与胡仔的年代相接续,淳熙进士赵师侠有词《菩萨蛮·用三谢诗故人心尚远故心人不见之句》。此句出谢朓《和王主簿季哲怨情诗》,赵师侠以“三谢”称之,足见“三谢”此时作为习称已有一定的影响力。这种并称还造成一些表述不确的情况。如刘克庄云“(谢安)诸孙如康乐,如惠连,如元晖,亦迭主风骚之盟”。谢灵运、谢朓在世时皆享盛名,称其主掌文坛问题不大。谢惠连与灵运同年去世,时年仅二十七岁,人微言轻,始终在从兄谢灵运的影响下,“迭主风骚之盟”的说法难称允洽。后村另有诗云“弟兄玉映更珠联,岂减元晖与惠连”,将本为从叔侄关系的谢惠连与谢朓认作从兄弟。在这样的并称中,谢惠连的地位与谢灵运、谢朓几于相当,谢灵运、谢朓的成就也外溢到了谢惠连身上。(38)刘克庄撰,辛更儒笺校:《刘克庄集笺校》,中华书局,2011,第801、3925页。成书于南宋的《历代名贤确论》亦于宋武帝条下辟“谢灵运惠连玄晖”条,亦见在“二谢”定论不一时,“三谢”概念已成为常见的诗学称谓。(39)佚名撰:《历代名贤确论》卷六十三,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晚宋至元代,“三谢”已常见于诗歌、诗话中:
诗到二南风化在,句流三谢语言工。(谌祜《评诗》)(40)刘埙:《隐居通议》,商务印书馆,1937,第81页。
五言短篇,如韦柳、三谢、嵇阮、建安七子。(方回《滕元秀诗集序》)(41)方回:《桐江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第21页。
安得三谢辞,远与陶阮并。(刘将孙《感遇》)(42)刘将孙:《刘将孙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第5页。
凡读《文选》诗分三节:东都以上主情,建安以下主意,三谢以下主辞。(陈绎曾《文筌·诗谱》)(43)陈绎曾:《文筌》,载王水照编《历代文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1321页。诗中此类表述更多,如洪咨夔“逸气盖三谢,英词参二班”,仇远“健笔凌三谢,高风继二疏”,黄玠“朝临二王书,暮吟三谢诗”,廼贤“五言往往凌三谢,八法翩翩逼二王”,陆恒“推诗夺锦欺三谢,侠气凌云比五陵”等。这与“三”是数字中少见的平声字、“三谢”适合用来对仗关系很大,不宜凿实而观,但也反映出三谢并称采用之广。
足见“三谢”不只是诗中的故实,时人确实将其视作诗史上的重要人物。“三谢”概念的风行与宋人对谢朓乃至近体诗风的反思有着密切关联。方回在《文选颜鲍谢诗评》中,对唐庚“玄晖渐有唐风”的观点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
“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佳之尤佳,然磔元气甚矣。阴铿、何逊、庾信、徐陵、王褒、张正见、梁简文、薛道衡诸人诗,皆务出此,而唐人诗无不袭此等语句。灵运、惠连在宋永初、元嘉间,犹未甚也。“宋六十岁至于齐而玄晖出焉”,唐子西之论有旨哉!(44)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1861-1862页。
“花丛乱数蝶,风帘入双燕”,灵运、惠连、颜延年、鲍明远在宋元嘉中,未有此等绮丽之作也。齐“永明体”自沈约立为声韵之说,诗渐以卑。而玄晖诗徇俗太甚,太工太巧。阴、何、徐、庾继作,遂成唐人律诗,而晚唐尤纤琐,盖本原于斯。(45)同上书,第1902页。
方回明确指出谢灵运、惠连与谢朓的区别。“磔元气甚矣”,即指谢朓诸作古风大失。方回认为“散义胜偶句,叙情胜述景,能如是者,建安可近矣”,注重偶句、述景的“三谢”总体上与建安诗风渐行渐远。(46)同上书,第1853页。但谢灵运、惠连兄弟毕竟还是古诗作手,谢朓绮丽工巧、讲求声律的风格则纯是近体风貌。在近体诗完全发展成熟后,诗论家又逐渐转回钟嵘的批评体系中。方回将“诗渐以卑”归咎于援声韵入诗的永明诸人,与钟嵘如出一辙,谢惠连地位的回升便也在情理之中。(47)地位回升并不意味着普遍的赞赏,谢惠连轻佻的作风、颓荡的诗情皆为方正君子所不喜。元人刘履便抨击其“智识浅狭”,见《风雅翼》卷七,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较之寂寂无闻的唐代,这也反映出谢惠连受到更多的关注。此时谢朓的典范地位已然确立,失去“小谢”名号的谢惠连只能成为“三谢”中的一员。对于存诗不多的谢惠连来说,这已经是其地位的一大提升。
宋元时期对谢惠连本身的品评并不多,然实为谢惠连被接受的重要时段。在唐人对其缺乏关注的情况下,宋人将谢惠连与声名籍甚的两位大诗人谢灵运、谢朓并称,发掘了他在诗史上的意义。谢惠连与谢朓分别处于存古与趋近的不同范式之中,这一观点为明清诗论家进一步承袭光大。
四、重寻惠连:明清诗论家对“小谢”的古近之辨
作为诗歌批评最为发达的时代,明清时期对谢惠连的关注超过此前。受复古风气影响,其文学地位虽不能与谢朓相埒,较之宋元则仍有进一步上升。不惟“三谢”并称习见不鲜,部分诗论家乃至将“小谢”之称还与惠连。郭绍虞指出《诗品》“晦于宋以前而显于明以后”,《诗品》在此时受到重视无疑也使得钟嵘评语的影响进一步扩大。(48)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商务印书馆,2012,第127页。
明初文宗宋濂在《答章秀才论诗书》中指出:“元嘉以还,三谢颜鲍为之首。”其认为沈约、王融、江淹、阴铿、徐陵、庾信等人都“方之元嘉则又有不逮”,直到初唐四杰才“务欲凌跨三谢”。(49)宋濂:《宋濂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第57-58页。“三谢”、颜鲍并举的说法源自方回,宋濂之后唐顺之、王祎等亦沿袭此论。在这样的评判体系中,齐梁至初唐的诸家作为颓靡婉丽的代表评价不高,其间最杰出的诗人谢朓则作为“三谢”的一员被含混地纳入元嘉诗人中,免于批判。在复古风潮中,“三谢”与建安、盛唐一起成为明人心目中的诗歌标杆:
自北地、信阳显弘正间,古体乐府非东京而下至三谢,近体非显庆而下至大历,俱亡论也。(王世贞《宋诗选序》)(50)王世贞:《弇州续稿》卷四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即有构,而亡近于建安、三谢、开元、大历,弗出也。(王世贞《青萝馆诗集序》)(51)王世贞:《弇州四部稿》,伟文图书出版社,1976,第3318-3319页。
“雨砌堕危芳,风轩纳飞絮”实近三谢,宋人一代所无。(胡应麟《诗薮》)(52)胡应麟:《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第210页。
无论是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还是王世贞、胡应麟等“后七子”“末五子”成员,都将“三谢”看作古体的晚期典范。近于“三谢”即可称眼空宋诗,实属过誉,亦可看出此时尊古抑近风气之盛。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三谢”的内部评价也出现了回归《诗品》的趋势。如王世贞所论,明代中期诗风“勉之(按即黄省曾)诸公四变而六朝”(53)同②书,第5923页。。虽统称“六朝”,黄省曾实拥晋宋而远齐梁,对六朝诗人的论断皆与《诗品》无甚差异。如其评谢惠连:“小谢才如涌泉,然流中宫商,奔应节数,是亦人间罕才也。《秋怀》《捣衣》之篇,亦何让于客儿。想其幽丰远论,必善感人,不然则康乐何于梦中瞻对,亦得‘池塘生春草’?即诵其珠玉,千载可见其风流矣。”对谢惠连作品评价甚高。黄省曾论谢朓则谓“感激顿挫”“足齐混照”,又引其诗句谓“虽陈思观览亦必赏为奇士”,用语全出《诗品》。黄省曾既熟稔《诗品》对谢朓才弱的评价,仍大赞谢惠连“才如涌泉”,复将“小谢”之名重与惠连,其微意似可推见。(54)黄省曾:《五岳山人集》卷二十七,明嘉靖刻本。唐顺之、徐中行等人亦以“小谢”指称惠连,皆源《诗品》。何良俊乃将“三谢”置于颜、鲍之上:“盖所谓芙蓉出水者,不但康乐为然,如惠连《秋怀》、玄晖‘澄江净如练’等句,皆有天然妙丽处。若颜光禄、鲍参军,雕刻组缋,纵得成道,亦只是罗汉果。”(55)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中华书局,1959,第214页。“元嘉三大家”并称数百年,惠连不列其中。但在晚明人看来,谢惠连甚至超过了颜延之、鲍照,如此推尊,实属罕有。
黄省曾等人对《诗品》近乎步趋式的仿效,距离扬惠连而抑谢朓只去一间。在这一基础上,王夫之《古诗评选》最终完成了这一转变。《古诗评选》以惠连为“小谢”,录诗十五首,接近其存诗总量的一半。王夫之对谢灵运的推崇近乎观止,流波亦及惠连。谢惠连多佻达之举,居父丧期间与小吏杜德灵关系过密,备受前人诟病。船山却谓“遥想此士风流,当知缑岭吹笙,月明人澹,而飘然欣赏,固不在洞庭张乐下也”,又称其“广远”,对其人品赞誉有加,此前可谓罕见。(56)王夫之著,李中华、李利民校点:《古诗评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第40页。关于谢惠连、谢朓二人的优劣,王夫之最直接的品评见于谢惠连《泛湖归出楼中望月》诗的评语:
平极净极。居恒对此,觉谢朓、王融喧薄之气逼人,必不使晋宋诗人与齐梁同称六代。(57)同上书,第210-211页。
此处王夫之重申了晋宋、齐梁之间诗风的重大转关。谢朓与王融皆永明新体的重要人物,船山只觉其“喧薄”,足见不取之意。王夫之并非不满于谢朓本身,而是不满于新体对古风的斫丧。正如其在谢朓《送江水曹还远馆》下所评:“晋宋之不能不变而唐,势也。宣城即不坠素业,而已堕风会中矣。”(58)同①书,第234页。所谓“素业”,即谢氏家族的文学传统。能够“不坠素业”,正是谢朓作为“三谢”的一员在明代风评胜过其他齐梁诗人之所在;然而谢朓毕竟是“永明新体”的典范诗人,这一风会是为王夫之等诗论家所不取的,是以,同样“不坠素业”又不染喧薄的谢惠连更为王夫之所赏识。虽船山殁世后其书不彰数百年,然仍可看出经历有明一代的复古思潮与古近之辨,谢惠连的地位已经远胜唐宋时期,甚至堪与谢朓分庭抗礼。清人对明代的复古思潮有所反拨,对谢惠连很少有这样的称扬,但也承认其为晋宋之际一大作手。清人拟谢惠连体、和谢惠连诗者众多,何焯《义门读书记》、方东树《昭昧詹言》、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等重要的诗歌批评著作都对其多加称赏。(59)如单隆周、邓显鹤、顾八代、李绂、莫友芝、王相等皆有拟体、和作;陈文述、茹纶常、王昶、王嘉曾、王鸣盛、谢元淮等皆称其小谢。如方东树谓谢惠连“一往清绮,又步步留迟,真味无穷,亦古今绝境也”,又谓其“奇伟高古,笔力开退之”,其论皆少为前人所发。(60)方东树著,汪绍楹校点:《昭昧詹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第157、186、423页。对于一位青年沦谢、作品留存不多的作家来说,能够得到这样的评价与认同颇为难得。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谢灵运一直保有上佳的文学史地位,虽有波折,未曾失坠。谢惠连一生与灵运关系密切,诗风亦如许学夷所论“与灵运绝相类”,是晋宋之际杰出的诗人,钟嵘誉之“小谢”,自有根柢。(61)许学夷著,杜维沫校点:《诗源辨体》,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第115页。然谢朓出而引领一代诗风之转变,近体与古体此后双峰并峙。谢朓为后人激赏自不待言,“小谢”之名转与谢朓亦合情合理。此后谢惠连文学地位的升沉,遂系于时代好尚。在近体诗迅速发展成熟的唐代,谢惠连几被遗忘;到了诸体诗歌俱已成熟,后人回顾诗史、多倡复古的时代,宋人又重新发掘谢惠连的文学价值。明代以后《诗品》受到重视,明清复古诗论中谢惠连的地位亦大有提升,乃至有以惠连置谢朓之上者。平心而论,张溥认为谢朓“虽渐启唐风,微逊康乐,要已高步诸谢矣”(62)张溥撰,殷孟伦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第196页。,是较为公允的评价。随着近体诗的勃兴,即便是谢灵运的地位亦有下降趋势,遑论惠连?谢惠连的成就难与谢灵运、谢朓相提并论,其升沉毁誉、跌宕起伏,遂与文学思想的发展流变紧密相关。不同时代的文学思想间差别甚著,就诗人接受状况而言,不惟王国维所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每一代亦能发掘其他时代较少重视的作家与文学。谢惠连一类小家诗史地位的变迁,正是文学思想演变的风信与见证。我们仍可以发问,倘若世与时殊,明清以来的“经典诗学”体系不再成为衡量诗人与作品的圭臬,我们是否会发掘出文学史上更多的“谢惠连”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