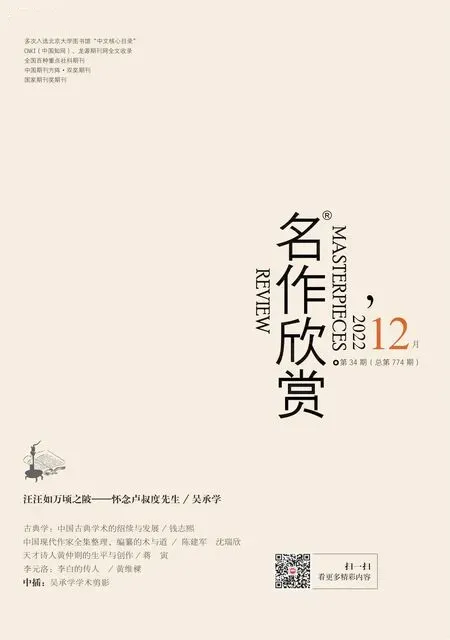“一个人的合唱”
——《呼麦文化研究》自序
北京|范子烨
合唱,不是齐唱:合唱有多个声部,齐唱只有一个声部;合唱能够产生和声,而齐唱却没有和声。呼麦艺术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它是“一个人的合唱”,一唱便是和声。柏拉图(Platon,前427—前347)说:“节奏与和声根植于灵魂深处。”当我初次听到呼麦之声和胡笳之音的时候,我感到自己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这种震撼是有生以来从未体验过的,它来自俄罗斯卡尔梅克共和国蒙古族歌唱家查干扎木(Okna Tsahan Zam)演唱的《萨满的声音:大草原之旅》(SHAMAN VOICES,A Journey in The Steppe),来自我国新疆阿勒泰喀纳斯湖畔的图瓦老人叶尔德西(1938-2006)用苏尔(胡笳)吹奏的《美丽的喀纳斯湖的波浪》。那神秘的宏大而静穆的音声,从皓齿丹唇之间,从悠悠笳管之内,时升时沉,时缓时急地飘出——仿佛是林壑的鸟鸣,温馨而温情;仿佛是煦日的风语,轻柔而轻盈;仿佛是高柳的蝉唱,悠远而悠扬;仿佛是巫峡的猿啼,悲怨而悲伤;仿佛是深山的虎啸,清雄而清壮;仿佛是沧海的龙吟,广袤而广远……种种杳渺、空灵、淳厚、深邃的音乐胜境,来自艺术家的灵魂深处。这人间的天籁、这天国的异响,无疑具有一种使人神共舞、使天地同悲的大自然的伟力!在极度的惊讶、惋愕、迷茫、困惑和愉悦中,我感觉自己确确实实和一个未知的声音世界遭遇了。
北方游牧民族的呼麦艺术无疑是我国古代音乐文化的积淀,它确实堪称为人类“原始音乐世界的活化石”。呼麦作为一种喉音艺术,在我国内蒙古、新疆和哈萨克斯坦(Kazakhstan)、蒙古国(Mongolia)均有流传,在俄罗斯境内的图瓦(Tuva)、塔塔尔(Tatal)、哈卡斯(Khakass)、巴什基尔(Bashkirs)、卡尔梅克(Kalmyk)、布里亚特(Briat)和雅库特(Yakut)等七个自治共和国以及戈尔洛—阿尔泰(Gorno-altaisk)的“蒙古文化圈”流传更为广泛,拥有多种发声与演唱类型,而以图瓦人的抒情型呼麦与蒙古人的粗狂型呼麦最为引人注目。呼麦是人类历史最悠久的声乐艺术形式之一,是人猿相揖别之际的产物,因此,研究呼麦艺术对探寻蒙古族源,构建蒙古史前史框架具有非常重要的音乐人类学意义。呼麦(蒙古语Хөөмий,古蒙古语kцgemi,西文khoomei)是浩林·潮尔(Holin-Chor)的俗称,所谓“潮尔(Chor)”,蒙古语意为和声;“浩林”,蒙古语本意为喉咙,由此引申为喉音之意。在古代汉语中,呼麦通常被称为“啸”。所以,啸史也就是呼麦史。这是我们研究呼麦艺术的基点。而呼麦的本质,实际就是喉音歌唱(Throat Singing)。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喉音艺术:歌唱者运用特殊的声音技巧,一人同时唱出两个声部,形成罕见的多声部形态。演唱者运用闭气技巧,使气息适当冲击声带,发出粗壮的气泡音,形成低声部。在此基础上,巧妙调节口腔共鸣,集中和强化泛音,唱出透明清亮、带有金属声的高音声部,获得美妙的声音效果。调节口腔共鸣的关键在于舌位的控制。歌唱者用舌头将口腔一分为二,随着前后的移动,制造出不同的共鸣腔。“呼麦”一词可以解释为“喉音歌唱”(Throat Singing),但因其在声音形态上的特性,很多学者又称为“泛音歌唱”(Overtone Singing)。“译名的不同体现出呼麦在生理器官与物理现象上的两种特征,代表了呼麦这一概念本身所包含的两个层次,即:如果从全球多样的文化传统当中来考察,则在‘喉音歌唱’层面,其与一切运用喉部特殊发声技巧的人声演唱相关;在‘泛音歌唱’层面,则与所有产生明确的泛音,形成双声的人声演唱相关。这两个层面既不能完全重叠,其概念也不能通用与互换。也就是说,所有的泛音演唱都是‘喉音歌唱’,而所有的喉音歌唱并非都是‘泛音歌唱’。”①二者不是并列的概念范畴,而是既互有交错,又彼此独立。”徐欣还指出,产生在16 世纪的一首法国诗歌可能是比较典型的呼麦记录:
我看到,在我看来
一个尊贵的强壮男子
用高低不一的声音
一个人同时演唱着。
其实,关于这种声乐艺术的西方记录,我们似乎也可以从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神曲·地狱篇》第六歌第三圈《饕餮者》的神话描写上见到一点影子:“塞比猡,一只凶猛的怪兽,有着三个喉咙,像狗一样地对着那些浸没在水里的幽魂狂吠。”②三个喉咙当然可以同时发出三个声音,这使我们联想到经常在佛典中出现的双首兽身的命命鸟。或许,这些人文动物在客观上彰显了人类对多声部发声技能的渴望和神化。
以往人们对呼麦艺术的关注,主要在于其“形成双声的人声演唱”的艺术特质以及此种艺术特质对西方声乐理论的彻底颠覆,但是,双声的产生首先是以一声部的单声持续音为基础的,这就如同飞机起飞前在跑道上滑行的状态,而在起飞之后,则进入二声部乃至更多声部的泛音世界;但是,飞机的飞行永远是以大地为根基为依托的,所以,在喉音歌唱或泛音歌唱中,一声部“嗡嗡”的持续音极为重要,没有它,就没有双声部乃至更多声部的泛音世界。事实上,自1967 年匈牙利音乐家拉乔斯·瓦戈亚斯(Lajos Vargyas)和法国人罗伯特·哈马扬(Roberte Hamayon)赴蒙古录制唱片以来,西方音乐学界对“泛音歌唱”已经逐渐摆脱了斯文赫定(1865—1952)式的陌生和困惑③,各种科学手段的运用、多种科学仪器的使用以及声学、医学、音乐学、人类学和艺术文化学的多学科交融、渗透,使呼麦艺术的研究更为科学化,更为理性化,相关的论著蝉联而出,异彩纷呈。尤其是在以文化寻根为主题的轰轰烈烈的新世纪运动(New Age Movement)中,陈光海教授主持拍摄的纪录片《泛音之歌》(The Song of Harmonics)以及在欧美电影界囊括所有奖项的美国纪录片《成吉思汗蓝调》(Genghis Blues),在喉音艺术的大众化普及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其出色的现代影视艺术中所具有的高学术与高文化含量使之成为永远令人感动的不朽经典。在我国音乐学界,莫尔吉胡先生关于蒙古潮尔音乐的田野调查和学术研究,杨玉成教授对现代呼麦流变的深入探讨,李革临医生对艺术嗓音的科学检测和研究,韩宝强教授、蔡振家博士对呼麦艺术的科学分析和研究,陈自明教授对泛音艺术的广泛探索,以及锺明德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中西方音乐思想、音乐理念和艺术实践的融汇④,都是对西方学术界的积极回应,代表了东方学者在这一领域的卓有成效的开拓。
对于这种特殊的声乐艺术的真实记录,在我国中古时代的文献中是屡见不鲜的,通常是以“啸”或与之搭配的多种语词形式(如“长啸”“清啸”“啸歌”等)出现。而呼麦艺术在我国内蒙古地区的迅猛发展,使得这一古老的歌唱艺术形式焕发了新的光彩,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但遗憾的是,关于喉音艺术在中国文化系统中的存在与发展,不仅西方人一无所知,即使中国学者也知之甚少,相关的研究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此种局面的产生有多方面的原因:就西方音乐学者而言,我国浩繁的古典文献以及古代汉语的艰难,给他们造成了难以逾越的阅读障碍;而就中国汉文化圈的音乐学者而言,多数人的研究兴趣不在于此,相关的艺术修炼极为欠缺,这使他们既疏离于喉音艺术的现代世界,更无缘于喉音艺术的古典世界——在一片风华国乐声中对我国古代辉煌灿烂的喉音艺术置若罔闻。
其实,古代的呼麦歌唱家准确地把握了呼麦的文化特质。譬如成公绥作为中古时代长啸艺术的专家,不仅对长啸有深刻的理论认识,而且在艺术实践方面也是行家里手。《晋书·成公绥传》说他“雅好音律,尝当暑承风而啸,泠然成曲,因为《啸赋》”。“良自然之至音,非丝竹之所拟。”“信自然之极丽,羌殊尤而绝世。”他对长啸的礼赞深刻地传达了他亲证自然的体验,而在无数次经历了同样的亲证之后,我也产生了同样真切的体认:“乃知长啸之奇妙,盖亦音声之至极。” 呼麦是最自由最浪漫最纯粹的声乐艺术,正如成公绥《啸赋》所言:“声不假器,用不借物,近取诸身,役心御气。动唇有曲,发口成音,触类感物,因歌随吟。”长啸超越了尘世的回声,回答了人们看不见也听不见的本质。长啸的国度是信仰的国度,在这个国度里,我们的种种疑惑和苦难都被消释在啸音的河流中,人类的纷繁吵嚷被忘掉了,言语交流的喋喋不休以及象形文字的芜杂烦琐也被彻底摒弃了。我们的心灵脱离了尘世,缓缓进入静穆的信仰之国,进入自己的精神乐园。在啸音中,没有专业人士与业余爱好者的区别,也没有创作者与倾听者乃至天才与凡人之间的对立。长啸拥有创造神话的魔法和巫术效应,通过声乐艺术对人类心灵进行改造,最终实现宇宙和谐、万物统一的目标。长啸的魅力就在于它是一种文化中的声音和一种声音中的文化,它代表了一种声音中的历史和一种历史中的声音,由此我们能够发现音乐是如何书写并表征历史的,也能够找到一条东方世界连接并维系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之密切关系的纽带,从而为伟大的华夏古国的多元文化共同体的形成提供有力的现代性阐释。聆听啸声,就是在聆听历史老人的述说,因为长啸作为人类的艺术音声,对人类的情感具有最广大的包容力和最集中的显现力,东方社会乃至东方各民族的情感赖此得以凝聚。长啸,这种似歌非歌、似唱非唱、似吟非吟的喉音艺术,在我国文化史上实际构成了另一种历史书写方式——其本质乃是声乐形态的诗史亦即精神史。
基于上述认识,我试图结合丰富的历史文献以及个人学习长啸艺术与喉音歌唱的心得体会,对我国中古时代的呼麦文化史钩沉索隐,阐幽发微,期能引起人们的关注。本书作为啸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主要目的在于从民族音乐学和草原文化学的角度对呼麦文化进行深度的阐释,揭示其特殊的草原文化精神,并彰显此种精神的人文价值。二十年的刻苦研读,暂时告一段落,但是,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本书的缺点和错误也在所难免,但开风气不为师,期待着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①徐欣:《泛音歌唱研究在西方》,《中央音乐学报》2010 年第2 期。
②但丁:《神曲·地狱篇》,朱维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 年版,第43 页。
③斯文赫定在《亚洲腹地旅行记》中写一位西藏“幽闭的和尚”在“大欢喜”中发出“牛鸣”之声,“有人同他们说话都听不见”,开明书店1948 年版,第489 页。
④锺明德:《OM:泛唱作为艺乘》,国立台北艺术大学2007 年版。
——为混声四声部合唱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