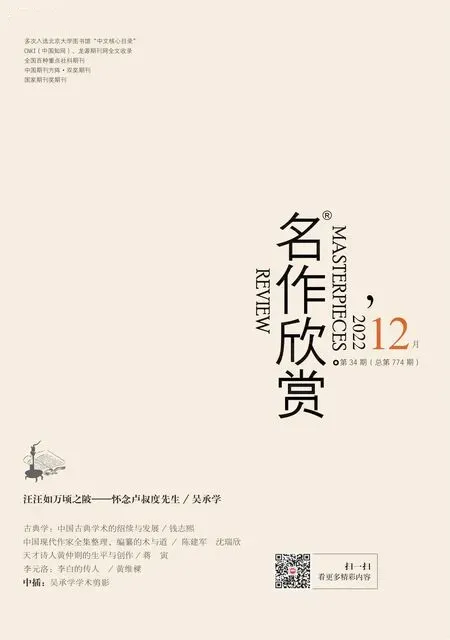我的同学吴承学
上海|曹旭
与承学同入王门
我和承学是两条远远的互不认识的光线,在复旦大学王运熙老师门下攻读文学批评史博士学位的时候,交叉在一起。
在我即将毕业的时候,承学进来了;在王老师那里,我们重叠了半年,王老师指导我们。承学有一位从西北师大来的赵晶晶同学,考前和我联系,问我考题的类型、考试的难度、王老师的要求,等等。那时,我和承学不认识。但听说王老师招了新生,就像父母又生了弟妹一样,一位男生,一位女生,我有了做哥哥和师兄的自豪。他们住在松花江路复旦大学博士生校舍,我去看望他们。
那天不巧,承学外出,只见到赵晶晶。赵晶晶向我谈了她对吴承学的印象,他的风貌、学习方法和学术品格,譬如冷静、睿智、好学、思辨,等等,而这些品质和特点,正是我所缺少的。还没有见面,第一次耳闻,在我的心里,就已经建立起对承学的钦佩之情。
认识以后,想象中的激动并没有发生,我讲什么话,哪怕不当心唐突了他,他永远只是谦虚地“笑笑”。由此我认定,在一群读书人里面,承学是最儒雅的一个,他待人、处事、说话特别有分寸,天生低调。
我们的性格很不一样,我自控能力差,承学的自控能力强,他能周而复始地做同样一件事,作息制度很有规律,看书、写作都会去图书馆,平时在办公室,节日也一样;不像我,有时随心所欲,乘兴而往,兴尽而返,经常在校园里一边走路,一边唱歌。
承学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高、很严格的人,在学生面前,不怒自威,学生都很害怕他。同一师门的彭玉平教授,人很幽默,善于言辞,非常有才气,有时很严厉,但学生们说,他们不怕彭老师;他们怕的是,好像从不严厉,说话也不高声的吴老师。
登黄山记
我前面说,承学未进复旦前我们不认识是一个错误。
有一张老照片显示,我和承学已经见过面了——那是一张集体合影,我们都在,一九八六年四月,安徽屯溪,全国《文心雕龙》第二次年会。
那次会议,王运熙、徐中玉、王元化、杨明照、周振甫、詹锳、林其锬、祖保泉、梅运生,很多老师都来了,他们都是研究《文心雕龙》的大家、专家、著名的学者;此外,还有很多研究生,如蒋述卓、曹顺庆、胡晓明、吴承学、汪涌豪、吴兆路,等等;虽然现在他们都成了各个大学的领军人物,成了教授、校长、党委书记、图书馆馆长,变得越来越重要,但那个时候,都还是学生。
会议既在黄山脚下的屯溪召开,开完会,主办方的想法是,组织专家学者,登黄山光明顶望天都峰,或者眺望云海,可以更好地体会刘勰说的天文、地文和人文,让研究《文心雕龙》得到江山之助。但作为学生,我们当时的任务,却不是研究《文心雕龙》,而是把老先生们扶上黄山。
搀扶老师们上山的时候,我们没有分工,但有目的。我和吴兆路是王运熙老师的学生,所以很自然地要跟着王老师;曹顺庆始终和我们在一起,因为他以后博士论文答辩,想请王运熙老师当答辩委员会主席,一路走,一路正好向王老师说他的论文;承学因为以后想考王老师的博士生,也要和王老师接触,有所交流。所以,王老师的手和胳膊有时轮不到我,我就搀扶詹锳先生上黄山。
当时,得知詹锳先生要在上海古籍出版三大册《文心雕龙义证》的时候,我们走到一处很陡峭的山崖前,便对詹锳先生说:“我们现在把您搀扶上黄山,到时候您的书出版了,要送我们一套的噢。”他说:“好的。好的。”我们继续往前走。
又走到了一个险要的路口,我们又停下来。他疑惑地想,怎么停下来了?我们说:“前面的路很陡很难走。一套书太少了。我们想要两套书,您同意不同意?”他想了一想说:“同意。同意。”
那时还没有索道,据说正在造;詹锳先生一定想,今天怎么会遇到一个敲诈勒索的家伙?快到半山寺的时候,会议组织者传达黄山有关领导的话说:“六十岁以上的老同志,恐怕吃不消,就不要再往上走了。”
詹锳先生听说,立刻决定放弃,不上山顶了。这就意味着,我们刚才签订的口头协议,不管是一套还是两套,都自动作废。
后来书出版了,詹先生还是送了我一套;曹顺庆的答辩也心想事成,王老师去了,因为有了事先的预习,答辩很顺利;而承学第二年就考取了王老师的博士研究生。这些是我们登黄山的故事。
学术会议之缘
十几年过去了,我们又一起参加四川大学庆祝杨明照先生诞辰的学术会议。会议结束去了九寨沟,傍晚的时候,几个朋友傍山而行。或许有高山反应,缺氧,我的表情有点落寞,承学就拿出他的手机,让我给爱人打一个电话。
他说:“你打,打时间长一点不要紧。”
我不好意思。那时很多人没有见过手机,甚至没有听说过手机。当时,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我为什么会记住这件事,并且现在要说?因为学生都说,吴老师是很会关心人的,我体会到了。说承学对自己要求高,低调,学生怕他,那不是他的全部,真正的承学很入世,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人。同时,他也温柔体贴,内心很热,很会帮助别人和照顾别人的情绪,有天真可爱的一面。
又是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在广州中山大学开的中华诗教会上见面,那次会议由张海鸥兄主持,诗人、诗会、诗一样的激情,凡是被海鸥的手碰过的东西就会自带流量,闪闪发光。
那次与承学谈得最多的是学术。
我们两人一起走的时候,我问他怎么写论文。他说他写论文主要学习陈寅恪和王运熙老师的路子,文史结合。王老师也经常对我们说,他继承的是陈寅恪先生的研究方法,但我一直怀疑这种说法,也怀疑承学的说法。因为在我看来,他们三者都不一样,无论是选题、方法还是逻辑过程和结论都不太一样。先不谈学养、分析方法、历史学和文学的本位,就望闻问切,陈寅恪的论文,一和他在西方学到的理性判断有关;二与他的家族有关,与他的祖父、父亲有关,他的门第,他的自豪感、使命感和失落感,让他时常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眼光,虽然敏锐,有时并不讲理。
但王老师是极讲理的,讲究以小见大,平易中见奇崛,用四两拨千斤;承学从题目开始,就具有新一代学人的眼光,写作过程与前辈也不一样,尤其是结构和结论,更加完整、更加严密。
我们互相谈到对方的学术。我很钦佩他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和《文学遗产》上发表了那么多高端的论文;他说他很钦佩我《诗品》系列研究的独断之学。
我们都在学术会议中老了。但三百年以后,假如有人要研究现在的学术,搜集各种会议指南很重要,哪些人出席了,哪些人没有来,可以做年谱,也可以考证。
我让学生抄写吴承学的论文
承学是写优秀论文的典范之一。我指导研究生,遇到写不出论文的学生,就拿出承学的论文,再发500 格稿纸给他们,请他们把承学的论文往500 格稿纸上抄。我一届一届的学生,都抄过承学的论文。除了承学的,也抄昌平等学兄的,效果很明显。开头怎么写,当中怎么写,结尾怎么写,各部分怎么关联起来,手熟了,他们都说:“原来论文就是这么写的。”是的,知道就好;你进步了,我的目的也达到了。
但是,他们抄的许多稿子都交给我,堆在我这里,堆积了很多。
我不要这些稿子,但扔了可惜。因此想到寄给承学看看,就寄了一部分。
我想承学收到稿子,一定很吃惊。他做过《中山大学学报》的主编,也许以为是有人投稿,一看怎么都是他自己的稿子,还寄给他,肯定想不通。
但我为什么要把这些稿子寄给他呢?因为我觉得,这些稿子的厚度、重量、重要性,以及对他学术的肯定,都远远超过了承学曾经获得的任何奖项和纸质的荣誉证书。
我比承学痴长九岁
我比承学痴长九岁,假如人生是乘车,痴长九岁,就是耽搁了九趟列车。
对于耽搁九趟列车的后果和严重性,我不想多说。我想说的是,我是过了三十周岁才有资格参加高考进入大学,成为1977 级大学生的。错了一纽扣,就会影响一辈子的纽扣,不过,我认了。
《古诗十九首》里的同学,有人飞黄腾达以后,“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我们同学里,很少有飞黄腾达的人,我也没有感受到“弃我如遗迹”的悲哀,但是,承学现在是长江学者,我们隔江相望。虽然我不会像织女那样惆怅,但对承学的祝福还是油然而生。
作为同学,我们像两条笔直的轨道,性格特点、做学问的方法,虽然心向往之,但始终不能向对方靠近。这使我每次面对承学,都像一个初恋的男生面对一个女生,想说什么,每次都说不清楚。
现在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