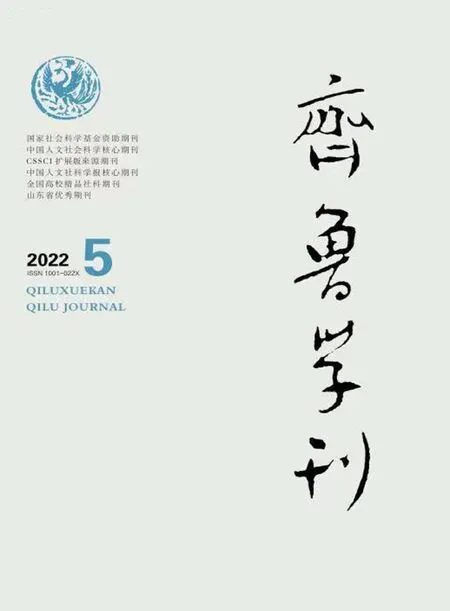《洪范》“彝伦”释义
惠翔宇
(成都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610059)
作为今本《尚书》中的重要篇章,《洪范》被奉为“统治大法”而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尚书》是“中国自有史以来的第一部信史”(1)金景芳、吕绍纲:《〈尚书·虞夏书〉新解》,沈阳: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页。,《洪范》则被学者誉为“中国古代文明的活的灵魂”(2)朱本源:《〈洪范〉——中国古代文明的活的灵魂》,《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第18-25页。,成为研究中国政治哲学思想史的一篇重要文献。“彝伦”一词即出自《尚书·洪范》篇首一节文字。传统观点认为,该节所记乃周武王与箕子于陈《洪范》之前的问答之辞。其文曰:
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陻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3)孙星衍撰,陈抗、盛冬铃点校:《尚书今古文注疏》卷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92-294页。
关于上述引文,以往研究乃聚焦其真伪性的问题——或视为史实,或谓其附会,或置之不问。而对篇首“彝伦”一词作专题考释,学界热情似嫌不高。有之,亦多为相关研究中的附带性论述,不易受人关注。目前所见,学者主要有三种解读观点,即“宇宙常理”说(4)刘起釪:《〈洪范〉成书时代考》,《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第155-170页。、“伦理规范”说(5)朱本源:《〈洪范〉——中国古代文明的活的灵魂》,第18-25页。和“社会秩序”说(6)晁福林:《说彝伦——殷周之际社会秩序的重构》,《历史研究》2009年第4期,第4-14页。。但综观《洪范》所叙及《尚书》宏旨,则前述三说似有未安。那么,何谓“彝伦”?作者为何用“彝伦”概说“九畴”精义?先贤提出这一概念的思想价值何在?这些问题的答案,均是我们探赜索隐、钩深致远、研究《洪范》的关键所在。
一、“彝伦”的典籍检讨与内涵考释
遍检史籍,“彝伦”一词最早见于今本《尚书·洪范》。那么,何谓“彝伦”?按《尚书·康诰》载周公训诰康叔曰:“汝陈时臬,事罚蔽殷彝,用其义刑义杀。”孙星衍疏引《释诂》云:“彝、法,常也。”(7)孙星衍撰,陈抗、盛冬铃点校:《尚书今古文注疏》卷十五,第366页。曾运乾曰:“蔽殷彝者,以殷常法当罪也。义,宜也。刑罪相报,谓之义刑义杀。”(8)曾运乾:《尚书正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74页。是“殷彝”即“殷法”“殷常法”。照此类推,“彝伦”当可解释为“常伦”,指正义伦理与价值秩序。反之,则为“非彝”。《尚书·酒诰》谓殷王纣“诞惟厥纵淫泆于非彝,用燕丧威仪”(9)孙星衍撰,陈抗、盛冬铃点校:《尚书今古文注疏》卷十六,第380页。可证。又,《国语·周语中》载单襄公之语云:
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赏善而罚淫,故凡我造国,无从非彝,无即慆淫,各守尔典,以承天休。”今陈侯不念胤续之常,弃其伉俪妃嫔,而帅其卿佐以淫于夏氏,不亦嬻姓矣乎?陈,我大姬之后也。弃衮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简彝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懋帅其德也,犹恐陨越。若废其教而弃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将何以守国?居大国之间,而无此四者,其能久乎?(10)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68-69页。
单襄公将“无从非彝”与“各守尔典”对称,又谓“不念胤续之常”“不亦简彝乎”,则“彝”可训为“典”“常”“法”。《尔雅·释诂》曰:“典、彝、法、则、刑、范、矩、庸、恒、律、戛、职、秩,常也”(11)《尔雅注疏》卷一《释诂第一》,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569页。,可证。《大戴礼记·四代》有云:“上服周室之典以顺事天子,修政勤礼以交诸侯。”王聘珍释之曰:“服,从也。典,法也,常也。政,犹制也。礼,谓邦交之礼。”(12)王聘珍撰,王文锦点校:《大戴礼记解诂》卷九《四代第六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65页。亦为明证。联系单襄公论陈必亡的语境,故而“彝伦”可解释为“常伦”(13)其实,即便从另一途径爬梳,结论亦然。按:《孟子·告子上》引《诗经·大雅·烝民》“民之秉彝”为“民之秉夷”,则“彝”与“夷”可通训。毛传云:“彝,常。”《逸周书·武穆解》云:“揆民之任,夷德之用。”孔晁曰:“夷,常也”,朱右曾从之(参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卷三《武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21-322页)。征诸典籍,徐锴《说文解字系传》于“殬”字下引《洪范》恰为“夷伦”(徐锴:《说文解字系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78页)。总之,将“彝伦”释为“常伦”,无疑也。“常法”“典常”,指周之礼乐(典制)与伦常,近同于人伦关系、政治秩序与价值系统的代名词。单襄公“废其教而弃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一说,即此之谓也。或许正是源于这一认识,司马迁在撰《史记·宋微子世家》时遂将同一史事记述为:
武王既克殷,访问箕子。武王曰:“於乎!维天阴定下民,相和其居,我不知其常伦所序。”箕子对曰:“在昔鲧陻鸿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从鸿范九等,常伦所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鸿范九等,常伦所序。”(14)《史记》卷三十八《宋微子世家第八》,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611页。
通过文献对比,是《宋微子世家》所言“常伦”实即《洪范》之“彝伦”。但在《史记·周本纪》一篇中,司马迁的叙史之辞则是:“武王已克殷,后二年,问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恶,以存亡国宜告。武王亦丑,故问以天道。”(15)《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第131页。太史公将“问以彝伦”径改为“问以天道”,又是以“天道”释“彝伦”之证。裴骃《史记集解》引郑玄曰:“帝,天也。天以鲧如是,乃震动其威怒,不与天道大法九类,言王所问所由败也。”(16)《史记》卷三十八《宋微子世家第八》,第1611页。与司马迁释义同。要而言之,在汉儒的知识体系之下,“彝伦”可解读为“天道”或“常伦”;而在其具体形态上,诸家并无异议,均指向“洪范九畴”(17)《洪范》内容分为九个部分,故名之曰“洪范九畴”。《尔雅·释诂》云:“洪,大也。”又云:“范,法也。”(《尔雅注疏》卷一《释诂第一》,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568、2569页)因此,汉儒也称其为“大法九类”(《宋世家·集解》引郑玄注)或“大法九章”。《汉书·五行志》于“初一曰五行”至“畏用六极”云:“凡此六十五字,皆《雒书》本文,所谓天乃锡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自班氏书以降,诸如李昉《太平御览》卷十六《时序部一·律历》,王应麟《玉海》卷九《律历·历法》,章如愚《群书考索》卷五十四《历数门·历类》,马骕《绎史·洪范五行传》等均沿用其说。。精赅之,其纲目为“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义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18)孙星衍撰,陈抗、盛冬铃点校:《尚书今古文注疏》卷十二,第294-296页。然而,汉儒何以用“天道”阐释“彝伦”?
按周初政治伦理思维,周人之有天下,系出于“天”;周室君主乃天之胤嗣,奕世载德,故受命于天帝而代商。这可从《诗经》《尚书》《逸周书》以及金文、简帛佚籍的记载中得到印证。如《尚书·康诰》曰:“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天命(19)按:“诞受天命”一句,孔颖达疏《尚书正义》作“诞受厥命”,参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03页。,越厥邦厥民,惟时叙。”(20)孙星衍撰,陈抗、盛冬铃点校:《尚书今古文注疏》卷十五,第359-360页。《毛公鼎》(5.2841)叙周初历史记忆:“丕显文武,皇天引厌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率怀不廷方,亡不闬于文武耿光。”(2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二卷),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33页。又《史墙盘》(16.10175)云:“上帝降懿德,大,匍有上下,受万邦。”(2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六卷),第133页。《逸周书·祭公解》亦载王曰:“呜呼!公,朕皇祖文王、烈祖武王,度下国,作陈周。维皇皇上帝度其心,寘之明德。付俾于四方,用应受天命,敷文在下。”(23)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927-928页。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换言之,“德”乃周革殷命获取统治合法性的根据。然而“上帝引逸”,统治者承受天命,即须肩负起道德使命,并接受上天的道德裁决。若其逸豫不“德”,则早失天命。此即《尚书·多士》所谓“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丧,罔非有辞于罚。”(24)孙星衍撰,陈抗、盛冬铃点校:《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二十,第427页。又,《尚书·召诰》载召公之训:“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国命,嗣若功。”(25)孙星衍撰,陈抗、盛冬铃点校:《尚书今古文注疏》卷十八,第398-399页。可见,“天命”(无形无声的至善标准)与“德”(人世可及的价值标准)的联动,不但是周人藉之获取天下权力“正统性”的根据,而且演变为周人的文化价值及意识形态,是两周社会政治权力转移的思想源泉(26)惠翔宇:《“上帝引逸”辨正——(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商榷一则》,《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第7-10页。。齐思和说:“此种天命思想乃周人思想最特异之点,亦殷、周思想根本不同之点也。”(27)齐思和:《西周时代之政治思想》,《中国史探研》,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70页。因此,对“彝伦”一词的解读,需要结合殷周时期的天命思想来理解,当非“彝伦就是政治体制、社会秩序”(28)晁福林:《说彝伦——殷周之际社会秩序的重构》,第13页。一言所能概括。联系“洪范九畤”的具体内容及前文考释,所谓“彝伦”,乃是殷周先哲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及其运动规律的高度提炼,是一个具有广泛涵义的哲学范畴。关于这一认识,顾炎武就曾一阵见血地指出:“‘彝伦’者,天地人之常道,如下所谓五行、五事、八政、五纪、皇极、三徳、稽疑、庶征、五福、六极,皆在其中,不止《孟子》之言人伦而已。”(29)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91页。可谓慧眼独识、一语中的。
实际上,“彝伦”概念的复杂性并未到此止步,因为传世典籍还存在另一种解读的可能性。《汉书·五行志》载周武王访箕子问“彝伦”之事云:
周既克殷,以箕子归,武王亲虚己而问焉。故经曰:“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王乃言曰:‘乌嘑,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逌叙。’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陻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弗畀洪范九畴,彝伦逌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逌叙。’”此武王问《雒书》于箕子,箕子对禹得《雒书》之意也。(30)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二十七上《五行志第七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315页。
将《五行志》与今本《尚书·洪范》对勘,可知班固除改“攸”为“逌”外,一仍《洪范》旧文。对“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逌叙”一语,颜师古注引应劭云:“阴,覆也。陟,升也。相,助也。协,和也。伦,理也。攸,所也。言天覆下民,王者当助天居,我不知居天常理所次序也。”(31)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二十七上《五行志第七上》,第1316页。可见应劭释“彝伦”与司马迁异曲同工,均释“彝伦”为天常、天理。这一解释与前引单襄公“各守尔典,以承天休”之说不谋而合。《孟子·滕文公上》云:“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赵岐注:“养者,养耆老。教者,教以礼乐。射者,三耦四矢以达物导气也。学则三代同名,皆谓之学,学乎人伦。人伦者,人事也,犹《洪范》曰‘彝伦攸叙’,谓常事所叙也。”(32)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43页。论述至此,“彝伦”又可解读为“人伦”和“人事”。若从这一视角来阐释,“彝伦”在概念上又与“伦理”一词有了可相通、可交融之处。
二、传世典籍中的“伦理”与“人伦”
何谓“伦理”?按《说文解字》人部:“伦,辈也。从人仑声,一曰道也。”段玉裁注曰:“军发百辆为辈,引申之,同类之次曰‘辈’。郑注《礼记·乐记》(33)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引作“郑注《曲礼·乐记》”,有误。今据《礼记正义》卷三十七《乐记第十九》改之,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528页。曰:‘伦,犹类也。’注《既夕》曰:‘比也。’注《中庸》曰:‘犹比也。’”(34)段玉裁:《说文解字段注》(影印本),成都:成都古籍书店,1981年,第394页。据此,“伦”可训为“辈”“道”“类”,引申为类次、位置、辈分、等列、秩序等义。《说文解字》王部:“理,治玉也,从王里声。”段玉裁注:
《战国策》郑人谓玉之未理者为“璞”,是“理”为剖析也。玉虽至坚,而治之得其理以成器不难,谓之“理”。凡天下一事一物,必推其情理至于无憾而后即安,是谓之天理,是谓之善治。此引申之义也。戴先生《孟子字义疏证》曰:“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在物之质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得其分也,则有条理而不紊,谓之条理。”郑注《乐记》曰:“理者,分也。”许叔重曰:“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古人之言天理,何谓也?曰:“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天理云者,言乎自然之分理也。自然之分理,以我之情絜人之情,而无不得其平是也。”(35)段玉裁:《说文解字段注》(影印本),第16页。
概而言之,循“理”之本义,可引申出剖析、善治、天理、文理、条理、情理、分理等涵义。应劭曰:“伦,理也。”(36)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二十七《五行志上》,1962年,第1316页。又段氏注:“《小雅》‘有伦有脊’,传曰:‘伦,道。脊,理也。’《论语》言‘中伦’,包注曰:‘伦,道也,理也。’按:粗言之曰‘道’,精言之曰‘理’,凡注家训‘伦’为‘理’者,皆与训‘道’者无二。”(37)段玉裁:《说文解字段注》(影印本),第394页。若以上疏证不误,则“伦”“理”“道”之义通,三者可互训。就目前考索而言,“伦”“理”二字合称使用,最早始于西汉学者贾谊。他在《新书·时变》中说:
商君违礼义,弃伦理,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秦人有子,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假父耰鉏杖篲,耳虑有德色矣;母取瓢椀箕箒,虑立讯语。抱哺其子,与公併踞。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睨。其慈子嗜利而轻简父母也,虑非有伦理也,亦不同禽兽仅焉耳。然犹并心而赴时者,曰功成而败义耳。蹷六国,兼天下,求得矣;然不知反廉耻之节、仁义之厚,信并兼之法,遂进取之业,凡十三岁而社稷为墟。不知守成之数,得之之术也。悲夫!(38)贾谊撰,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97-98页。
在《新书·辅佐》中,贾氏又曰:“祧师典春,以掌国之众庶,四民之序,以礼义伦理教训人民。”(39)贾谊撰,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第206页。可见,贾谊所谓之“伦理”乃指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等差秩序和道德观念,即“人道”(40)按:“人道”与“天道”对言,常见于传世典籍。如:《左传》文公十五年,鲁国季文子曰:“礼以顺天,天之道也。”[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614页]《左传·襄公九年》载:“晋侯问于士弱曰:‘吾闻之,宋灾于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对曰:‘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咮,以出内火。是故咮为鹑火,心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阅其祸败之釁,必始于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963-964页]《左传》昭公十八年,郑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1395页]又,《国语·周语下第三》载柯陵之会,单襄公论晋将有乱,“鲁侯曰:‘寡人惧不免于晋,今君曰‘将有乱’,敢问天道乎,抑人故也?’对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见晋君之容,而听三郤之语矣,殆必祸者也。’”(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第83页)鲁成公所言“人故”即“人道”,单襄公的答语可证。《国语·鲁语上第四》载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之言顺矣,僖又未有明焉。犯顺不祥,以逆训民亦不祥,易神之班亦不祥,不明而跻之亦不祥,犯鬼道二,犯人道二,能无殃乎?”(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第165-166页)《老子》第七十七章亦有“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的思想认识。可见至少在春秋时代,“天道”“人道”已是时人的常用语,殆无疑议。。王充《论衡·书虚》:“夫乱骨肉,犯亲戚,无上下之序者,禽兽之性,则乱不知伦理”(41)黄晖:《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90页。,可证。
然揆之典籍,先秦时期人们的话语体系中似乎并无“伦理”一词。它的语义表述为“类”“伦”“伦类”“伦列”,多数场则合称之为“人伦”。这些词语的基本涵义,先秦诸子多有阐释。譬如墨子曰:“义可厚,厚之;义可薄,薄之,谓伦列。德行、君上、老长、亲戚,此皆所厚也……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之中。己在所爱,爱加于己。伦列之爱己,爱人也。”(42)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卷十一《大取第四十四》,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405页。孟子云:“人之有道也,饱食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43)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卷十一,第386页。荀子亦云:“亲亲、故故、庸庸、劳劳,仁之杀也。贵贵、尊尊、贤贤、老老、长长,义之伦也。行之得其节,礼之序也。”(44)梁启雄:《荀子简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67页。《吕氏春秋》强调政治伦理与社会秩序,谓“先王所恶,无恶于不可知,不可知则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妻之际败矣。十际皆败,乱莫大焉。凡人伦以十际为安者也,释十际则与麋鹿虎狼无以异,多勇者则为制耳矣。不可知则知无安君、无乐亲矣,无荣兄、无亲友、无尊夫矣。”(45)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卷第二十二《壹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610页。庄子则一语道尽人性的实然与应然状态:“若夫万物之情,人伦之传,则不然。合则离,成则毁,廉则挫,尊则议,有为则亏,贤则谋,不肖则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乡乎!”(46)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卷七上《山木第二十》,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668页。
此外,出土文献亦不乏其证,例如《郭店楚简·教(原题“成之闻之”)》载:“天登大常,以理人伦,制为君臣之义,作为父子之亲,分为夫妇之辨。是故小人乱天常以逆大道,君子治人伦以顺天德。”(47)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58页。综而论之,汉人所言“伦理”实与先秦时期“人伦”一词类同,均指生活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的等差秩序及其制度与道德认同。
“伦理”与“人伦”的文献疏证如上,再看“彝伦”与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按《尚书·君奭》载周公语:“无能往来,兹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国人。”孙星衍疏引《释诂》云:“‘迪,道也。’‘彝,常也。’”(48)孙星衍撰,陈抗、盛冬铃点校:《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二十二,第453页。曾运乾《尚书正读》从之(49)曾运乾:《尚书正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43页。。《诗经·大雅·烝民》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毛传云:“烝,众。物,事。则,法。彝,常。懿,美也。”(50)王先谦撰,吴格点校:《诗三家义集疏》卷二十三《烝民》,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967页。《左传》定公四年,卫祝佗叙周初分封有“备物、典策,官司、彝器”,杜注云:“常用器”(51)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537页。。那么,“彝伦”可释为彝教、常教、常伦,即周人所宣扬的统治伦理与道德观念。《逸周书·祭公解》云:“我亦维有若文祖周公暨列祖召公,兹申予小子追学于文、武之蔑”(52)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第928页。,即此之谓也。
前文业已指出,伦、理、道三字可以互训,故“常伦”可径称之为“常理”“常道”。需要赘述的是,由于“彝伦”与“伦理”在概念上的相通和交织,故而在传世典籍中,先儒有时也用“伦理”一词概指宇宙万物的天然形态及运行规律。例如:《礼记·乐记》曰:“乐者,通于伦理者也”(53)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卷三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982页。,又曰:“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54)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卷三十七,第990页。;刘熙《释名·释水第四》:“小水波曰沦。沦,伦也,水文相次有伦理也”(55)刘熙撰,毕沅疏证,王先谦补:《释名疏证补》,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35页。;《释名·释采帛第十四》:“纶,伦也,作之有伦理也”(56)刘熙撰,毕沅疏证,王先谦补:《释名疏证补》,第153页。;《释名·释典艺第二十》:“论,伦也,有伦理也”(57)刘熙撰,毕沅疏证,王先谦补:《释名疏证补》,第217页。。若细究上述引文,可知汉儒所言“伦理”泛指宇宙万物的自然状态、结构、逻辑及秩序,而与今日所言之伦理(Ethic)概念不同。如果把这一层涵义与上文对“伦理”的疏证相关联,则“彝伦”与“伦理”或可对等使用。
根据以上考释,我们把“彝伦”解释为彝教、常教、常伦、常理、伦理、人伦、人事、秩序、规范、法则、典制等等,殆无疑议。或基于这一理解,晁福林先生以为:“彝伦表示社会之常理、秩序、规律、法则等。”(58)晁福林:《说彝伦——殷周之际社会秩序的重构》,第8页。又,朱本源先生说“所谓‘常伦所序’,就是指维持社会秩序(谐合其生)的行为规范”,认为殷遗箕子所陈《洪范》“九畴”是“把宗教经验理性化为伦理·政治文化”,从而“《洪范》也就成为殷周之际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和中国古代文明的活的灵魂”(59)朱本源:《〈洪范〉——中国古代文明的活的灵魂》,第18-25页。。两位先生虽就《洪范》阐发幽微而创见良多、发人深省,但在“彝伦”概念的解释上,似嫌少了一些意涵和韵味。
三、“彝伦”的两重维度与思想价值
语言文字是人类文明的结晶,经典赋予历史以永恒生命。要阐明“彝伦”精义,还须回归历史文献本身,探讨《尚书·洪范》篇的生成问题。《书序》曰:“武王胜殷,杀受,立武庚,以箕子归,作《洪范》。”(60)孙星衍撰,陈抗、盛冬铃点校:《尚书今古文注疏》卷卅,第595页。因而传统旧说均认为该篇作于周武王时期(或西周初年),已然成为古代儒士之通识。逮及20世纪初,疑古思潮渐盛,学术风气为之一变。众所周知,自刘节《洪范疏证》(61)刘节:《洪范疏证》,《东方杂志》1928年第25卷第2号,第61-76页。辩难以来,学术界对《洪范》的成书年代便聚讼不已,新说迭出而莫衷一是。仅就目前所见,主要有夏商说(62)张怀通:《由“以数为纪”看〈洪范〉的性质与年代》,《东南文化》2006年第3期,第51-57页。、西周说(63)李学勤:《周易溯源》,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20-28页。、春秋中叶说(64)杜勇:《〈洪范〉制作年代新探》,《人文杂志》1995年第3期,第75-79页、战国说(65)陈梦家:《尚书通论》(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2页。、汉初说(66)汪震:《〈尚书·洪范〉考》,《北平晨报》1931年1月20日。按:此条转引自徐文珊:《儒家和五行的关系》,《史学年报》1931年第3期,第62页。等五类观点,而以西周、战国两个时期的争论为其主流——前者存在西周初期(67)陈蒲清:《〈尚书·洪范〉作于周朝初年考》,《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1期,第90-96页。、中期(68)李军靖:《〈洪范〉著作时代考》,《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第79-83页。和晚期(69)李行之:《〈尚书·洪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求索》1985年第4期,第109-110页。之争,后者亦有战国初期(70)童书业:《五行说起源的探讨——评顾颉刚先生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参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五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660-669页。、中期(71)张西堂:《尚书引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90页。和末季(72)刘节:《洪范疏证》,第61-76页;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1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232-233页。之论。按《洪范》第六畴“三德”中有云:“平康正直,强弗友刚克,燮友柔克。沉潜刚克,高明柔克”,与《沈子它簋》“考克渊克”句例类同。于省吾先生据之认为,“《洪范》乃晚周人所作,绝非西周之文”(73)于省吾:《双剑誃尚书新证;双剑誃诗经新证;双剑誃易经新证》,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00-101页。。关于《沈子它簋》的断代,郭沫若列此器于昭王,容庚定该器于成王,陈梦家隶为康世(74)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15页。,唐兰将其归于穆王之世(75)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20-326页。,均与于氏之说相悖。此外,屈万里认为《洪范》成书于“战国初叶至中叶”(76)屈万里:《尚书集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第115-116页。,赵俪生又指出,《洪范》篇就其原型而论,乃是“夏商周三代传递下来的一件文化珍宝”(77)赵俪生:《〈洪范疏证〉驳议——为纪念顾颉刚先生诞辰100周年而作》,《齐鲁学刊》1993年第6期,第70-75页。。以上诸学说,丁四新先生已有系统爬梳和评论(78)丁四新:《近九十年〈尚书·洪范〉作者及著作时代考证与新证》,《中原文化研究》2013年第5期,第12-22页。,兹不赘述。但综观诸家所述,仍以刘起釪先生《〈洪范〉成书时代考》所论最为平实可信,即《洪范》原稿从商代流传至周代,经过西周至东周时期史官们层累地加工和润饰,“到春秋前期已基本写定成为今日所见的本子”(79)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218页。。至若《洪范》篇首的历史记载,皮锡瑞据《史记·周本纪》云:“武王和箕子于陈《鸿范》之前尝有问答之辞,惜不传耳。”(80)皮锡瑞撰,盛冬铃、陈抗点校:《今文尚书考证》,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41页。刘起釪先生则认为:
很可能《洪范》原篇并没有周武王访问一节,而只有所谓箕子讲的“九畴”全文,因而都称它为《商书》;后来唯心主义神学观的“五行说”出现后,才加上了一套宣扬五行的周武王访箕子及箕子托词上帝的神话,才成了今天所见的《洪范》。从篇首所说以土塞水就是搞乱五行次序,提出了类似后来所鼓吹的五行生克关系的说法与第一畴中五行的朴素意义不一样,就可以看出是后来勉强加上的痕迹。加上了就成了周武王访箕子的谈话记录,当然只能作为《周书》了,所以后来就编进了《周书》中。(81)刘起釪:《〈洪范〉成书时代考》,第159-160页。
然而,若能超越既有辩论,从新视角对待《洪范》篇首的古史叙述,其意义或将勃然有味。郭沫若在《周官质疑》中指出:“古人并无专门著述立说之事,有之,盖自春秋末年以来。其前之古书,乃岁月演进中所累积而成者也。”(82)郭沫若:《金文丛考》,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91页。既然如此,我们为何不转换思路?与其费力探讨周武王与箕子问答之辞的真伪问题,不如覃思周代史官(或殷周先哲)创造“彝伦”范畴而纂修序辞的思想价值。
事实上,通过对“彝伦攸叙”和“彝伦攸斁”的阐发,周代史官将上帝授命、鲧禹治水、洪范九畴、周武王、箕子等历史记忆关联起来,从而超越史传本身而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古史重述、社会建构与传统延续。或如扬·阿斯曼所言:“神话也是回忆形象:神话和历史之间的区别在这里显得有些模糊。对于文化记忆来说,重要的不是有据可查的历史,而只是被回忆的历史。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在文化记忆中,基于事实的历史被转化为回忆中的历史,从而变成了神话。神话是具有奠基意义的历史,这段历史被讲述,是因为可以以起源时期为依据对当下进行阐释……历史不是变得不真实了,恰恰相反,只有这样,历史才拥有了可持续的规范性和定型性力量。”(83)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6-47页。更深言之,周代史官以此“关联—聚合”方式把古史记忆变成其概念和判断的象征理想,并赋予它最为独特的历史面貌。因此,《洪范》篇首的古史叙事,不但赋予周革殷命以神圣性,而且演变为“殷周鼎革”的叙事典范。而该节所蕴先哲之玄训,又成长为传统延续的意识潜流。赵善湘《洪范统一》释“王访于箕子”曰:
王访于箕子,就见之也。武王可使箕子归周,不能使箕子朝王,道不可屈也。方念天下之民未安其居,彝伦不得其叙,道在箕子而可臣致之乎?武王访之,不为失尊。访而问之,遂陈《洪范》,箕子不为失节。武王所以圣,箕子所以仁也。(84)赵善湘:《洪范统一》,永瑢、纪昀等纂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五三,第5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49页。
综观全文所叙,要理解“彝伦”精义,当从两重维度进行把握,方能走近殷周时代。一则,“彝伦”为周代史官们探索宇宙本体的思想结晶,是对天道、人道及其运行规律的高度抽象,以阐释天人之际的哲学架构与政治伦理。从这一维度观察,“彝伦”类同于老子的“道”(85)关于老子“道”的系统阐述,可参詹剑峰:《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陈鼓应、白奚:《老子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2-139页。。二则,“彝伦”等同于先秦两汉话语体系中的“伦理”“人伦”和“人事”,主要指人与人之间的等差秩序、现实社会的典章制度及其价值系统。从这一视界理解,“彝伦”又略同于现代伦理学的三个维度“人际关系、政治秩序和个人品质”(86)邓安庆:《正义伦理与价值秩序:古典实践哲学的思路》,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7页。。
先儒解读之所以有“天道”和“人伦”两相之说,实皆断章取义、各求所需,割裂“彝伦”概念的完整性而造成——或偏重天命要义,或强调人间价值,或游离于“天道”与“人道”之间。当代学者之间的不同观点,同样导源于此。但在殷周先哲的话语体系中(至少在先秦典籍的语境中),说“彝伦”、辨“伦理”则兼及“天道”与“人伦”,不言自明。《礼记·乐记》云:“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87)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卷三十七,第984页。据戴东原考证,此“天理”指自然之分理,“自然之分理,以我之情絜人之情,而无不得其平是也”(88)戴震著,何文光整理:《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页。。又,林之奇在《尚书全解·皋陶谟》中写道:
人之生也,其人伦之典,天也,故其彝伦有自然之叙矣。人君勑之以为五典,使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五者各致其厚,盖所以助乎天之所叙也。谓人之生、交际之礼,天已定其差等,有自然之秩矣。人君自已为五礼,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示,以凶礼哀邦国之忧,以宾礼亲邦国,以军礼同邦国,以嘉礼亲万民,五者各得其常,所以助夫天之所秩也。勑有典自有礼,必在夫君臣共致其寅畏、恭谨、衷善之意,然后可以施化。故曰:“同寅协恭和衷哉”!(89)林之奇:《尚书全解》卷五《皋陶谟》,永瑢、纪昀等纂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四九,第5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02-103页。
按林氏所说,“人伦之典”是“天”,是“自然之叙”“自然之秩”。换言之,“人伦”实属“天道”“天理”的一部分,天道与人道浑然一体。当天、地、人处于有序的运转状态时,即“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90)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3页。,所谓“彝伦攸叙”矣(91)与本文对“彝伦攸叙”的解说不同,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说:“冀为帝都,既在所先,而地居北方,实于五行为水,水生木,木东方也,故次之以兖、青、徐;木生火,火南方也,故次之以扬、荆;火生土,土中央也,故次之以豫;土生金,金西方也,故终于梁、雍。所谓‘彝伦攸叙’者,此也。与鲧之汩陈五行,相去远矣。此说予得之魏几道。”(参洪迈撰,孔凡礼点校:《容斋随笔》卷一《禹治水》,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5页)按洪迈所言,可商者有二:其一,洪氏以“阴阳五行”释《禹贡》叙治水次序,与史不合。根据刘起釪先生的研究,《洪范》是最早把水、火、金、木、土列为五行的传世文献,但《甘誓》《洪范》所言“五行”指辰星、太白、荧惑、岁星、填星(镇星)等五行星,与金、木、水、火、土无关,而是以“五行”来代表五行星在天球面上的运行现象。《洪范》“五行”乃朴素唯物的五行的早期发展阶段,没有战国至西汉的“阴阳五行说”的术数味道[参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二册),第869-871页]。其二,洪氏所论“顺五行治水”与实际地理情势有悖。对此,黄镇成在《尚书通考》已驳其非:“今考《禹贡》所书,其次第固如此。然冀州京都,天下根本所在。禹施功先自内始,盖以重轻而论也。兖、青、徐平田虚壤,泛滥溃决之患视他州尤甚,拯溺捄饥莫先于此。扬、荆则江汉下流,次当疏凿以泄水势。豫虽有河、济、荥、洛之浸,而渐居上流。独梁、雍居西北,地髙,水患差少,用功宜后。此盖以缓急而论也。所谓顺五行而治之者,亦偶合耳。”[黄镇]成:《尚书通考》卷七,参(清)永瑢、纪昀等纂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五六,第6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47页]这一点已得到《遂公盨》的印证:“天命禹敷土,随山濬川,迺差地设征,降民监德,迺自作享民,成父母。生我王、作臣,厥贵唯德民,好明德,顾在天下。”(参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8页)。反之,则“彝伦攸斁”。总而言之,“彝伦”乃是殷周先哲人对物质世界的高度提炼,反映出我国先民探索社会形态演变的整体视界。《洪范》不但探究天人之际,而且垂训人间大法,更赋予思想与理论见诸行事的中国特色。这一点有别于西方,恰是理解中国思想文化的关键所在。
——《洪范大义与忠恕之道》简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