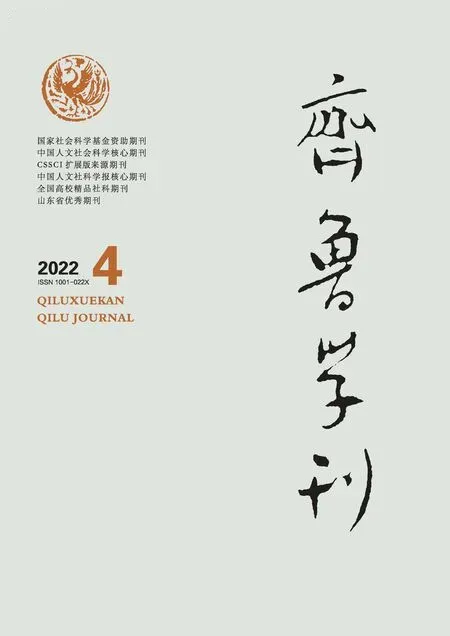理气为一与心性格物:罗钦顺诠释经典的两个向度
康宇
(黑龙江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被誉为“朱学后劲”“江右硕儒”的罗钦顺,生活于明代中期心学兴起的年代。作为程朱理学的坚定支持者,他批禅学、驳心学,但在思想上却不与程朱合,而是为明代气学开规模、定纲领。就学术理论而言,他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其学说关联着理学、心学和气学,着力于在“理”“气”“心”“性”等核心范畴间架构一个彼此照应、逻辑旨归同一的哲学体系,而结果又难以被三方学派完全认可。虽然如此,罗钦顺却成为理学发展由理本论向气本论过渡的关键人物,而且还影响了明代心学的前进路向。究其原因,他对传统理气关系的改造、对“理一分殊”命题的修正,顺应了时代思潮的发展,其与王阳明心性问题的争论,观点出入道学、心学、老学、禅学,独具匠心,深刻启发了后学对于心学理论的认知。
近年来,学界对于罗钦顺思想的探讨或专注于其理气关系的思考,或执着于其心性问题的思辨,而将理气、心性问题归一共述的研究较少。其缘由是,两种思想体系间可能存在矛盾之处。恰如黄宗羲言:“先生(罗钦顺)之论心性,颇与其论理气自相矛盾。夫在天为气者,在人为心;在天为理者,在人为性。理气如是,则心性亦如是,决无异也……岂理气是理气,心性是心性,二者分,天人遂不可相通乎?”(1)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四七,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107页。即罗氏在理气论中主张“气”是宇宙万物的根本,“理”是“气”运动变化的一定条理秩序,但在提出性体心用之说时似乎将理气关系颠倒了,又回到了理先于气、理能生气的传统思路之上。此“矛盾”之说,在当代学者的论述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同,有关罗氏在阐发其基于人生界之“性本论”的心性说与提供其立论根据的自然界之“气本论”的理气说中存在无法统一之内在矛盾的说法,已十分常见。但笔者认为,此“矛盾”如变换理解切入点,确实存在“消解”的可能。其钥匙即在考察罗氏对经典的诠释,其中已蕴含了统一理气与心性关系论题的线索。并且,细思罗氏解经释典理路,亦可对明中期理学发展形态给予更为明晰的呈现。
一、“天下之理莫不备于经书”
在明代心学“水月镜花”式理解文本流行的时代,脱离文字而“贵意象”的阐释理论颇为盛行。那种强调发挥诠释者主观性的“六经注我”范式成为解经方法的主流,人们相信任何文本的意义都是游移不定的,所谓“《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2)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95页。。文本的意义需要诠释者运用自己的意念与情感呈现给读者,要让经典由过去融入现在,让诠释成为一种主观的情绪理解。忽略文本原义,以诠释者自己的情知感悟为中心,无视诠释的有效性,不再刻意追寻作者原意,将经典作为一种表达自己情感的工具,成为这一时期经典诠释的最大特点。如此一来,经典文字本身的重要性下降了,诠释已俨然成为一种超越原作的再创造。
面对这样的情况,罗钦顺颇不以为然。他指出理学义理的发明,绝离不开儒家经传真义的理解:“凡古圣贤经传,其言累千万计,无非所以发明是理。博学而慎择之,审问而精思之,明诸心,体之身,积之厚而推之善,其仁至于不可胜用,然后为学之成。不此之求而徒事空言,以徼利达,则其志亦陋矣。”(3)罗钦顺:《韵州府重修庙学记》,《整庵存稿》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儒家经典上所记载的,都是圣人对义理的发明,只有立足于经典文字,潜心钻研,厚积薄发,方能获取理学真谛。于是乎,他说:“凡天下之理莫不备于经书,必其讲之素明,然后行之不缪。故终始典学,高宗之德所以无愆;好古敏求,孔子之圣所以为大。”(4)罗钦顺:《献纳愚忠疏》,《整庵存稿》卷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讲义理不可离经书,因为任何文本都有一个绝对正确的意义存在,而这也是作者的创作意图,或曰“理”正是经典想要揭示的东西。
虽说罗钦顺学宗朱子,但他的为学历程却十分曲折。据载,他早年志注于禅学,后来转向于研究儒家的典籍和濂、洛、关、闽之论著,才意识到“前所见者乃此心虚灵之妙,而非性之理也”(5)罗钦顺:《困知记》,阎韬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44页。。再持续专研而到深思熟虑的阶段后,自述:“积数十年,用心甚苦,年垂六十,始了然有见乎心性之真。而确乎有以自信。”(6)罗钦顺:《困知记》,第44页。进入思想成熟的第三阶段后,他不但不再接受禅学,且也不再依傍程朱理学,而是建构了修正朱学的思想体系。正是有着如此丰富的经历,才使得他对心学、禅学那种不求甚解、肆意发挥诠释者主观情感的解经方式产生内心的抗拒,并自觉地转向到着力于经典文本之“知识论”方向的解读。不过,罗钦顺的经典诠释并非汉儒式的训诂考证,就整体而言“扬宋抑汉”乃是其总的思路。
罗钦顺强调:“学莫先于明道也,道苟明焉,日新而不已,则积之而为和顺之德,发之而为炳蔚之文,措之而为正大光明之业,由体达用,沛然有余,盖学之有得于心者然也。然自孟子没而圣学不传,千数百年之间,道术四分五裂,上焉者类以佛老之似乱孔孟之真,正焉者记诵词章而已。”(7)罗钦顺:《月湖文集序》,《整庵存稿》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圣学之所以不传,原因是佛道二教思想的流行,动摇了儒学的社会正统地位。而理学的出现正是为了重建道统,尤其是濂、洛、关、闽之学的出现,将道的理解由体达用,并践行于百姓人伦日用,从而将儒家精义以“理”的形式表达出来,其所言“道”,精粗隐显,一以贯之,大小合宜,天下莫不能用,绝非汉唐诸儒可比。为学问者,最终目的是得孔孟之学,但亦不可离开程朱理学此一中间环节:“舍程朱之说而欲求至于孔孟,与希升堂而闭门者有以异乎?亦多见其惑矣。呜呼!世道之隆污鲜不由于学术,而吾人之所谓学,其不及者如彼,过之者又如此,有志之士可不明辨而熟讲之乎!”(8)罗钦顺:《万庵县重修儒学记》,《整庵存稿》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经典之所以重要,因为它承载着“明体”之学。学问只有“明体”才能“适用”,但“明体”不可以己说经,或是为了纠正记诵词章之弊而走向“脱略章句而注心玄妙”的心学方向。正确的做法是,强调客观的向外探求,把阐发道理与章句解读一定程度地结合起来,以形式化和知识化的理路,明确圣人赋予经典文本之上的微言大义与切实义理。“圣贤千言万语,无非发明此理。有志于学者,必须熟读精思,将一个身心入在圣贤言语中,翻来覆去体认穷究,方寻得道理出。从上诸儒先君子,皆是如此用工。其所得之浅深,则由其资禀有高下尔。自陆象山有‘六经皆我注脚’之言,流及近世,士之好高欲速者,将圣贤经书都作没紧要看了。以为道理但当求之于心,书可不必读,读亦不必记,亦不必苦苦求解。看来若非要作应举用,相将坐禅入定去,无复以读书为矣。一言而贻后学无穷之祸,象山其罪首哉!”(9)罗钦顺:《困知记》,第94页。
在诸多文本中,罗钦顺最重《易》与《大学》。他称《易》为理学“性与天道”之旨。“程子曰:‘圣人用意深处,全在《系辞》。’盖子贡所谓‘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者,《系辞》发明殆尽。学者苟能有所领会,则天下之理皆无所遗。凡古圣贤经书微言奥义,自然通贯为一,而确乎有以自信,视彼异端邪说,真若蹄涔之于沧海,碔砆之于美玉矣。然或韦编屡绝,而不能辨世间之学术,则亦何以多读为哉!”(10)罗钦顺:《困知记》,第33页。对于《大学》,他的定位是其不仅是“入德之门”,更是经学与理学联系的桥梁。尤其是其中的“格物说”,更是理学思想的核心组成。由此,罗钦顺对于《易》与《大学》两个文本的诠释也成为认识其理气论与心性论的“快捷”通道。
二、理气为一:一种解《易》的思路
对于“理”,罗钦顺的解读是:“理果何物也哉?盖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气本一也,而一动一静,一往一来,一阖一辟,一升一降,循环无已。积微而著,由著复微,为四时之温凉寒暑,为万物之生长收藏,为斯民之日用彝伦,为人事之成败得失。千条万绪,胶葛而卒不可乱,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谓理也。初非别有一物,依于气而立,附于气以行也。”(11)罗钦顺:《困知记》,第6页。“理”是宇宙本原“气”运行变化的条理形式,是内在的规则、规律和属性。“气”是物质性的:“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12)罗钦顺:《困知记》,第6页。它只有聚散而无生灭,所以宇宙得以长存。理与气的关系是:“理只是气之理,当于气之转折处观之。往而来,来而往,便是转折处也。”(13)罗钦顺:《困知记》,第89页。此结论初一看,似乎是罗氏在强调气为第一性,理为第二性。细味后会发现,实则不然。罗氏并非在说理是气的派生物,而是说理并不是先于气而制宰于气的“别为一物”,理气可为一。不过“为一”不是“合一”,其强调的是统一性。“往而不能不来,来而不能不往,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若有一物主宰乎其间而使之然者,此理之所以名也。‘易有太极’,此之谓也。若于转折处看得分明,自然头头皆合。”(14)罗钦顺:《困知记》,第89页。人们可以通过读《易》明知“太极”的道理,继而也就可清楚理气间到底是如何统一的。
南宋大儒朱熹是“理气二物”命题的提出者。罗钦顺虽继承朱子理学,但却不认同朱子的理气说。“所谓朱子小有未合者,盖其言有云:‘理与气决是二物。’又云:‘气强理弱。’又云:‘若无此气,则此理如何顿放?’似此类颇多。唯《答柯国材》一书有云:‘一阴一阳,往来不息,即是道之全体。’此语最为直截,深有合于程伯子之言,然不多见,不知竟以何者为定论也。”(15)罗钦顺:《困知记》,第7页。“理气二物”乃是朱子“未定于一”之处,可以进一步商榷。不过,罗氏也不赞成理就是气、气就是理之言,而认为理是虽非别于气的“二元”存在,但在形式上二者又非完全等同,准确地说是二者是一种“一物二体”的关系。如何认知这一点?我们同样须从罗氏对《易》的诠释中寻找答案。
罗钦顺解《易》,将之视为穷理尽性之书。“夫《易》之为书,所以教人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也。苟能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则学《易》之能事毕矣,而又何学焉。性命之理,他经固无不具,然未有专言之,如《易》之明且尽者。《易》苟未明,他经虽有所得,其于尽性至命,窃恐未《易》言也。”(16)罗钦顺:《困知记》,第97页。在对《易》的解读中,他最为关注的是对太极和两仪关系的解释。他说:“《易大传》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夫太极形而上者也,两仪四象八卦而下者也。圣人只是一直说下来,更不分别。可见理气之不容分矣……还有可为证者一条: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须着如此说:器亦道,道亦器是也。合此数说观之,切恐理气终难作二物看。”(17)罗钦顺:《困知记》,第196 -197页。因为太极作为无形之理同有形的两仪、四象、八卦不能分割,所以可以推论理与气亦不是二物。又因为道器不能分割,故太极之理同卦爻象不容分割,也可说明理气不容为二物。宇宙的形成源于气化的运动,而此运动是有规律的,这个规律便是理。“易有太极”,即事物的变易皆有其理,但理并非实体,主宰气的运动变化,只是阴阳变易自身固有的规律性罢了。
在论及《太极图》时,罗钦顺说:“至于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三语,愚则不能无疑。凡物必有两而后可以言合。太极与阴阳果二物乎?其为物也果二,则方其未合之先,各安在耶?朱子终身认理气为二物,其源盖出于此。”(18)罗钦顺:《困知记》,第37页。理与气的关系并非合一:“理须就气上认取,然认气为理便不是。此处间不容发,最为难言,要在人善观而默识之。”(19)罗钦顺:《困知记》,第42页。理与气严格来说不是等同的,气为实体,理是气的运动形式。如以哲学之思辨对之理解,那么理气关系可为:气运的大化流行是气,气之所以如此存在、运动是理。在此意义上说,气是实存,理亦为实存。因为“若有一物主宰乎其间而使之然者,此理之所以名也”(20)罗钦顺:《困知记》,第89页。,故理是形上,气是形下,理是气不得不“往而来”“来而往”的主宰,“而”就是转折处,但理不是外在的主宰物,而是气运内在的自然。
罗钦顺还言:“天地间非阴阳不化,非太极不神,然遂以太极为神,以阴阳为化则不可。夫化乃阴阳之所为,而阴阳非化也;神乃太极之所为,而太极非神也。‘为’之为言,所谓‘莫之为而为’者也。张子云:一故神,二故化。盖化言其运行者也,神言其存主者也。”(21)罗钦顺:《困知记》,第17页。此处说的太极,即是阴阳二气统一体和气运动变化的规律,正是因为“统一性”的存在,所以宇宙才有运动变化的存在,此即“神乃太极之所为”。但我们不可以太极为神,如同不能以阴阳二气为化一样。太极和神,阴阳和化,虽有区别,但不可遗弃一方,言神即包涵化,言化即包涵神,言太极即包涵阴阳,言阴阳即包涵太极。此复杂关系同样可推及理气,“理气为一”,它们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存在。
应该说,“理气为一”是罗钦顺对于程朱理本论最大的修正,其带来了“气本论”的论说。不过,他对于理作为事物的本质说,即程朱所言一物之所以然,是否先于本体事物而有的问题并没有进一步论说,而是接受了他们“理一分殊”的思想,认为:“人犹物也,我犹人也,其理容有二哉?然形质既具,则其分不能不殊;分殊故各私其身,理一故皆备于我。”(22)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四七,第1107页。不过,罗氏的创造性运用是利用“理一分殊”的思想,将《易》中的太极还原到物质世界里:“盖人物之生,受气之初,其理惟一;成形之后,其分则殊;其分则殊,莫非自然之理;其理之一,常在分殊之中,此所以为性命之妙也。”(23)罗钦顺:《困知记》,第9页。人与事物的理都是一气变化的理,其理是同一的,所以叫“理一”。但在成形之后每一个具体事物的规律或特性,其表现又是各不相同的,这就叫“分殊”。万物的根源是气,人与物禀赋之初都是相同的,因为此时气还没有变化,而按其“理”决定于气的前提,故曰“理一”;但当气化流行、生人生物后,气就呈现出千变万化的“聚散”,于是“理”自然也就会跟着变化,一物有一物之理,自然会表现出“成形之后,其分之殊”的样态。于是乎,可以说“理一”存在于具体的分殊之中。“所谓理一者,须就分殊见得来,方是真切。”(24)罗钦顺:《困知记》,第53页。
罗钦顺坚信,“理一分殊”是普遍而绝对的真理,亦可进一步确证“理气为一”命题的正确性。“仆从来认理气为一物,故欲以‘理一分殊’一言蔽之。执事谓:‘于理气二字,未见落著。’重烦开示,谓‘理一分殊,理与气皆有之。以理言,则太极,理一也;健顺五常,其分殊也。以气言,则浑元一气,理一也;五行万物,其分殊也。’”(25)罗钦顺:《困知记》,第196页。进而,罗钦顺将之视为解读《易》之经传的基本方法路径。但其与程朱所言之“理一分殊”具有差异性又是毫无疑问的,它绝非论证“理”为世界的本体,而重在强调理气之统一。由此,他解释《易》中之道、器关系时,主张“道器不二”。“明道先生尝历举《系辞》‘形而上下’数语,乃从而申之曰:‘阴阳亦形而下者,而曰道者,惟此语截得上下最分明。元来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识之也。’截字当为斩截之意。盖‘立天之道曰阴与阳’及‘一阴一阳之谓道’二语,各不过七八字耳,即此便可见形而上下浑然无间,何等斩截得分明。若将作分截看,则下句‘原来只此是道’更说不去,盖道器自不容分也。”(26)罗钦顺:《困知记》,第139页。甚至他还提出“太极”亦不是“主宰”:“或者因‘《易》有太极’一言,乃疑阴阳之变易,类有一物主宰乎其间者,是不然。夫《易》乃两仪、四象、八卦之总名,太极则众理之总名也。”(27)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四七,第1107页。“太极”只是“众理之总名”,本质上是“理”,按“理气为一”的思路对之诠释,则“太极”也就不是气外的“另一物”,而按理为气之理去理解,则“太极”也同样不是什么世界主宰了。
综观罗钦顺解《易》,“理气为一”是其总的诠释路向。他“理气为一”运用的重点,并非为判别理气何为第一性问题,而是着重讲二者的统一性关系。这是一种对理气关系认知的新视角,即由外在必然支配转向内在自然秩序的理解过程。其意图绝不在突出主体意识与客观实存的对立,而在于建构一种“理气合一”的宇宙观。认识到这一点,可以为后面“化解”罗氏理气论与心性论之间的“矛盾”奠定理解的前提。
三、心性格物:从对《大学》“格物”的诠释看
罗钦顺治学以心、性、理、气为宗,“心性理气诸说,凡《记》中大节目”(28)罗钦顺:《困知记》,第148页。。他将“心”视为人的“神明”,将性视为人的“生理”:“孔子教人莫非存心养性之事,然未尝明言之也;孟子则明言之矣。夫心者,人之神明,性者,人之生理。理之所在谓之心,心之所有谓之性,不可混为一也。”(29)罗钦顺:《困知记》,第1页。人的知觉作用“心”是可以变化的,随着感应的不同而不同,故人心可称为“情”;性则是人、物成形后的定理,是不能随着感应变化而变化的,故性可称为“理”。心、性之间关系密切不可分割,心性是一物的两个方面。
罗氏曾专门针对人心、道心问题修正了朱子的心性论。朱子言“人心道心”以心之知觉“理”或“欲”对二者进行区分,“道心”不是性体,也不具有“本体”的地位和高度,只是具有认知主体和实践主体的作用。对此,罗氏表达了不同看法。他将“道心”界定为未发之性,将人心界定为已发之情。由此,作为性体的“道心”上升至本体论高度,“道心”就是本体,不仅人有道心,物物皆有道心,工夫的重点,乃归向此性理本原,天命之性。然而,罗氏又说:“人心道心,只是一个心。道心以体言,人心以用言,体用原不相离,如何分得?性命,理也,非气无缘各正。太和,气也,非理安能保合?亦自不容分也。”(30)罗钦顺:《困知记》,第204 -205页。道心、人心在概念上有形上、形下之分,人心不是道心,心也不是性。但若从具体的天道创生言,道心(理)非悬虚之体,需有气之活动而成人与万物之性,而人心气之活动也必须以理为共主宰,才能长久而不已,所谓“保合太和”。所以理气不相离,由之推论心性:“盖心性至为难明,是以多误谓之两物又非两物,谓之一物又非一物。除却心即无性,除却性即无心,惟就一物中分割剖得两物出来,方可谓之知性。”(31)罗钦顺:《困知记》,第51页。
从罗氏对道心、人心,心性关系等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如同“理气为一”,心性间同样体用而别但不相离。理气若有分,则儒家生生不息之性理创造性难以证立;心性若有分,人之心则不能由“知觉”作用而彰显性理。可见,罗氏对心性关系的认知与理气关系一样,重在讲统一性而非对立性。而此一点在其对《大学》的诠释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明代心学领军人物王阳明阐释《大学》,认为其所言“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诸条目,说得是“工夫之详密,而要之只是一事”,“夫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皆所以修身,而格物者,其所以用力实可见之地”(32)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66页。。也就是说,“明明德”的工夫,重在格物。由此,他推论出心、性、理以及意、知、物等其实具是一物,曰本心或良知。“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则谓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则谓之心,以其主宰之发动而言则谓之意,以其发动之明觉而言则谓之知,以其明觉之感应而言则谓之物。”(33)王守仁:《王阳明全集》,第67页。在阳明看来,格物就是格心,也就是诚意的外在工夫。“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34)王守仁:《王阳明全集》,第39页。对此,罗钦顺提出了反对意见:“格物,莫若察之于身,其得之尤切。程子有是言矣。至其答门人之问,则又以为,求之情性固切于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盖方是时,禅学盛行,学者往往溺于明心见性之说,其于天地万物之理,不复置思。”(35)罗钦顺:《困知记》,第4页。《大学》之格物的真正意思是:“格物致知,学之始也……物格则无物,惟理之是见。”(36)罗钦顺:《困知记》,第13页。通过格物以致其知,认识事物之理。不仅如此,格物致知的目的更在于认识性命之理:“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然物格知至,则性命无不了然。”(37)罗钦顺:《困知记》,第18页。格物致知是过程,认识理是目的,最终是为了“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一语来自《易·说卦》,罗钦顺对之解释为:“人之有心,固然亦是一物,然专以格物为格此心则不可。说卦传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此理在人则谓之性,在天则谓之命。心也者,人之神明而理之存主处也。岂可谓心即理而以穷理为穷此心哉!”(38)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四七,第1108页。理在人便是性,心作为人的神明,在于认识和存住此理。所谓格物是在事物上穷理,不是格心。“故有志于学者,须就天地万物上讲求其理,若何谓之纯粹精,若何谓之各正。人固万物中之一物尔。须灼然见得此理之在天地者,与其在人心者无二……方可谓之物格知至,方可谓之知性知天。不然,只是揣摩臆度而已。”(39)罗钦顺:《困知记》,第160页从心性之辨出发,罗氏强调阳明把“格物”之“物”释为“意之用”,即物是心意的产物;而把“格”训为“正”,所谓格的不是正心内之物的说法与《大学》宗旨不合。“物者,意之用也。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也。此执事格物之训也。向蒙惠教,有云:‘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诚意者,诚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自有《大学》以来,无此议论……夫谓‘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凡其为物也三。谓‘正其物之心,诚其物之意,致其物之知’,其为物也一而已矣。就三物而论,以程子格物之训推之,犹可通也;以执事格物之训推之,不可通也。就一物而论,则所谓物者果何物耶?如必以为‘意之用’,虽极安排之巧,终无可通之日。”(40)罗钦顺:《困知记》,第147页。
细究罗钦顺以心性关系论格物、批阳明,其理论基点实为打通理、气、心、性之间的联系,理之所在谓之心,心之所有谓之性。“天命之谓性,自其受气之初言也。率性之谓道,自其成形之后言也。”(41)罗钦顺:《困知记》,第11页。性与气一致,是化气而出的,需要向外格物而认知。“天性正于受生之初,明觉发于既生之后。有体必有用,而用不可以体也。”(42)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四七,第1107页。“盖心之所以灵者,以有性焉,不谓性即灵也……天地间非太极不神,然遂以太极为神则不可,即此义也。夫宾主之分,乃其理之自然。是以虽欲一之,而语脉间自不能无对待之势,不可得而一也。”(43)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四七,第1107页。心与理相通,是形下的不同表现,同样经由向外格物而认知。如果像王阳明那样主张格心以“致良知”以求,则理气、心性间的统一性必会受到质疑:“既言‘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又言‘正惟致其良知,以精察此心之天理’。然则天理也,良知也,果一乎,果非一乎?察也,致也,果孰先乎,孰后乎?此愚之所不能无疑。”(44)罗钦顺:《困知记》,第148页。
显然,在心性问题上罗钦顺是“性即理”的坚持者,这也是黄宗羲说他“言理气不同于朱子,而言心性则于朱子同”的原因。不过,罗氏的观点与朱子相较还是有不少差异的:他始终以认识器官和认知能力来释“心”,认定心不是理,而朱子则有将“心”本体化的嫌疑;在人性论上,朱子主张天命与气质之性的二元论,而他却反对以天命释性,认为性即气,是一元人性论的立场。更为重要的是,经过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发现在罗钦顺的经典诠释思想中理与气、心与性实则不存在产生时间的先后关系,亦不存在彼此的派生关系。从他对《大学》中“格物”问题的言讲中,更可知其着重彰显的是人与万物虽皆以性(理)为本体,但却需人之“心”的体悟作用明了性理,所以格物就是性由心显,即人心而体认道心的过程。“就形而下者之粗,悟形而上者之妙,二之则不是也。”(45)罗钦顺:《困知记》,第203页。可以认为,罗氏开辟出理学理论发展的又一新方向。
四、总结与评价
以经典为依据,罗钦顺阐发出自己的哲学思想,其总的思路是批驳心学而扬弃理学。罗氏讲理气,在顺天理之自然的前提下,回归融合程朱、张载之学,以“理气为一”命题消解了传统的理本论,但又保存理气相即不离以及理存于气的见解,并由此论证了世界一本于气,理只是气化流行所呈出的属性。气是体,理则是此体所显现出的一种用,理、气虽不同,但这只是体、用之间的差异,两者本质上是同一的,即统一于气,理、气是一物。这样,理既不可能先于气、外于气而存在,理也不能成为气外的另一本体,自然理、气也就不可呈现出二元态势了。罗氏谈心性格物,强调从分殊处求其理一,从而导出即天地万物而求天理的结论。其重点在于心性不离不混,心是人的神明,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在理一分殊的前提下格物,必然导致向外三极(天、地、人)之理的穷至,格物最终要明心性之理,体认得精之又精,才得真切。在言及理气与心性关系时,罗氏说性作为阴阳之理,在受气之初便为“理一”;成形之后,因心的作用化为万殊。孔子论性,称“性相近”,子思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至宋代朱子提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分别。总之,“性命之妙,无出理一分殊四字,简而尽,约而无所不通,初不假于牵合安排,自确乎其不可易也”(46)罗钦顺:《困知记》,第9页。。
从上面的论述不难看出,罗钦顺在根底上讲还是一个理学“中坚”。他要扬理而非抑理,其气学的思辨终归还是为理学服务的。但其对心学和禅学的批判也是坚定的,除了前文所涉及的相对“隐含”的表述外,他在诠释经典时还曾直接提出批评。例如:“《虞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论语》曰:‘从心所欲不逾矩。’又曰:‘其心三月不违仁。’《孟子》曰:‘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此心性之辨也。二者初不相离,而实不容相混。精之又精,乃见其真。其或认心以为性,真所谓‘差毫厘而谬千里’者矣。”(47)罗钦顺:《困知记》,第1页。“佛氏有见于心,无见于性,象山亦然。其所谓至道,皆不出乎灵觉之妙,初不见其有少异也……盖以灵觉为至道,乃其病根。”(48)罗钦顺:《困知记》,第148 -149页。可见,罗氏深知自己的学术使命,他要竭力维护理学之道统。
现在让我们回到前文黄宗羲对于罗钦顺理气论与心性论存在矛盾的评判上。显然,其说法存在可质疑性。黄氏所言的立论依据是“在天为气者,在人为心;在天为理者,在人为性”,而此依据与罗氏的思想是不相符的。罗钦顺言性,不是传统的“理”,而是阴阳之理、人之生理,理与性均从属于气,以气为存在的根据。其所说的心,亦不是黄氏认知的心,而是对“阴阳不测之神”的反映,并从属于气。黄氏认为罗氏之矛盾生于其性体心用论混同了“理能生气”说,但真实的情况是罗钦顺以体用关系说心性,性为体并不是说性是整个宇宙的本体,性也不能主宰气,而产生于受气之初,从属于气。其所说的心与性均以气为存在的前提,其性也不是本体之理。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理气关系,还是心性关系,罗氏均未刻意区分第一性和第二性问题,而关注的焦点是其统一性的问题。所以不可武断地认为程朱“理能生气”的观点与罗氏的心性均从属于气的性体心用论之间存在什么必然的联系。换言之,罗钦顺的理气论与心性论并不矛盾,只是各有所指罢了。而这也正体现出罗氏哲学思想的时代价值,他开理学发展之新风尚,由此在宋明理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