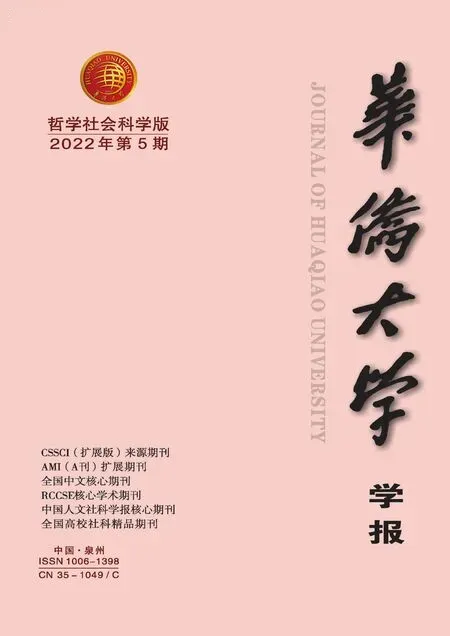当代欧美文献剧的三种艺术探索
○黎 林 戴小春
现代文献剧(documentary theater,也有译为“纪实戏剧”或“纪录剧”)发源于德国。1925年,德国戏剧导演埃尔文·皮斯卡托(Erwin Piscator)在执导《无论如何!》时,在剧中使用了大量政治文献,并启用了纪录电影镜头。菲尔沃德(Alan Douglas Filewod)认为是1926年布莱希特首次使用了“史诗般的文献戏剧”一词来评论皮斯卡托的剧场实验。(1)Alan Douglas Filewod, The Development and Performance of Documentary Theatre in English-speaking Canada, Ph.D.diss., University of Toronto,1985, p.3.1929年皮斯卡托在其著作《政治戏剧》里第8章使用“文献戏剧”一词作为标题,来描述自己开创的这种新的戏剧形式。但文献剧真正崛起为一种引人瞩目的戏剧类型是在20世纪60年代。由于德语剧作家彼得·魏斯(Peter Weiss)的大力倡导和实践,文献剧同荒诞派戏剧一起成为战后欧洲舞台的主要先锋力量,影响深远。法国戏剧理论家帕维斯(Patrice Pavis)在其编撰的《戏剧艺术辞典》中对文献剧作出如下极简的定义:“一种只使用文献和有真实来源的事件并根据编剧的社会政治观点加以选择和拼接的戏剧。”(2)[法]帕特里斯·帕维斯:《戏剧艺术辞典》,宫宝荣、傅秋敏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第376页。从以上定义不难看出,虽然文献剧源自真实素材,但并非绝对客观,材料仍然需要经由剧作家、创作人员的筛选、构思,以某种独特的形式呈现在舞台上。因此文献剧的创作和演出方式往往会呈现与传统剧场相背离之处。当代德国戏剧理论家雷曼(Hans-Thies Lehmann)将其视为剧场艺术的革新范例,列入他的《后戏剧剧场》中“新先锋派”一节加以讨论,认为60年代兴起的文献剧以法院场景“取代了对事件的戏剧化呈现”,“比传统戏剧剧场更进了一步”(3)[德]汉斯-蒂斯·雷曼:《后戏剧剧场》,李亦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57页。。国内对欧美文献剧的探讨较少,主要集中在对个别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本文重点总结欧美文献剧的总体艺术特征,为新时期国内戏剧的发展提供借鉴。作为欧美戏剧舞台上的革新剧派,文献剧从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历经美国的艾米丽·曼 (Emily Mann)、安娜·德维尔·史密斯(Anna Deavere Smith)、德国的克罗辛格(Hans-Werner Kroesinger)等人之手,在艺术手法和舞台表演上积极创新,不断焕发出自己独特的光彩。最主要的艺术探索:其一,艾米丽·曼代表的对独白组合的多声部对话和超文本对话性的凸显;其二,建立声音档案的安娜·德维尔·史密斯创导的单人文献剧的崛起;其三,德国新浪潮文献剧代表的多媒介的舞台呈现。
一 对话特质
以独白为主要形式构成文本内部和超文本对话,这种艺术手法和舞台表演特征在美国文献剧代表人物艾米丽·曼的作品中得到充分发展。艾米丽·曼的戏剧始终致力于推动社会各阶层、各群体就历史创伤、社会现状开展对话和讨论,为实现这一目的,她逐步丰富加深自己作品的对话性。借用巴赫金的对话性艺术理论和后戏剧剧场关于独白剧场的研究,可以更深入清晰地理解其文献剧的这一特征。对话性艺术理论是俄国著名文论家巴赫金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研究的基础上发现并提出的。在巴赫金看来,对话是这个世界存在的前提,人类生活的本质及人类的意识都具有对话性。“根据对话理论,作品能否形成对话性,不在于叙事性作品的艺术样式,而在于作者的思想意识与创作观念,在于时代生活、意识的表现形态。”(4)袁联波:《新时期中国探索戏剧的“对话性”艺术》,《戏剧文学》2003年第12期,第79页。戏剧虽然与小说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可以发现巴赫金所分析的对话性特征也会得到体现,这一点国内不少学者都提出过。例如,范一亭就认为:“通过动作和对话的表达方式,戏剧是一种具有‘对话性关系’的对话性艺术。”(5)范一亭:《试论巴赫金复调对话理论在戏剧领域的移植》,《戏剧》1998年第4期,第125页。袁联波也提出:“由于社会结构、价值体系、思想体系的复杂多元,作家思想意识、创作观念的矛盾性与不确定性,戏剧中其实也较为广泛地存在着对话性艺术。”(6)袁联波:《新时期中国探索戏剧的 “对话性”艺术》,《戏剧文学》2003年第12期,第79页。包含对话性艺术的作品中的肯定或补充、同意或反对、问与答的关系,一般在作品中不会有非此即彼的一元选择,它是多元性的、未完成态的。这种多元性的、未完成态的不同意识之间的对话关系为观众留下了大片审美空白,其艺术完整性是在更高层面完成的。文献剧因为强调对历史的多维叙事以及作品的社会介入功能,所以这种对话性特征也尤其显著。
依照对话主体与文本的关系,对话性形式可分两种:一种是文本内对话性关系,它包括文本内语言、思想意识、情节主题、结构关系等层面的各对话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对话性关系;另一种是超文本对话关系,即文本外部对话性关系,它包括作者与主人公的对话性关系、文本与观众的对话性关系等。以艾米丽·曼的《阿纽拉:一部自传》(AnnullaAllen:AutobiographyofaSurvivor)、《静止的生活》(StillLife)和《正义的实施》(ExecutionofJustice)为例,可以看出剧作家如何努力建构两条线上的对话关系并使之相辅相成。
文本内部对话性艺术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探讨。第一,他者话语进入剧作形成对话性。在《正义的实施》中,在对戏剧上演历史进行一个简单介绍后,艾米丽·曼又以编年史的形式罗列了一份“旧金山编年史”,记述了从1975年到1985年这十年间发生在旧金山重大的跟该案相关的历史事件。这份真实的“旧金山编年史”强化了戏剧的纪实性效果,增加了作品的真实可靠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份“旧金山编年史”就是一个文本,这个历史文本为剧本提供了对话的历史背景。通过这个历史文本,艾米丽·曼陈述了发生在旧金山历史上的这次谋杀案的社会背景和历史事实,同时通过历史文本与戏剧文本的对话,也为读者解读戏剧中剧作家与读者的对话埋下伏笔。
第二,以独白为主要形式构成文本内部对话。雷曼认为独白已成为后戏剧剧场的基础形式。陈恬也指出“以独白作为戏剧文本和舞台基本结构的 ‘独白剧场’ 成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美出现的新的戏剧类型”(7)陈恬:《独白剧场:理论与实践》,《文艺研究》2019年第6期,第93页。。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献剧受后戏剧剧场潮流的影响,也愈来愈倾向采纳独白作为文本和演出的中心构架,这在重述历史的文献剧中尤为明显,在探究当代热点事件的文献剧中也较普遍,不过在审判文献剧中则是独白和对白交织。文献剧之所以青睐独白形式,主要因为独白的对象是观众,更容易引发共鸣,增加戏剧事件的真实性,而且它“使观众从观看者(spectator)转变为见证者(witness),并最终在剧场建构起一种关系艺术(relational art)、一个临时性的共同体”(8)陈恬:《独白剧场:理论与实践》,《文艺研究》2019年第6期,第101页。,引发作品和观众的对话。
不同人物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视点之间的对立也构成了文本内部对话性。在文献戏剧中, 艾米丽·曼善于利用独白,把彼此冲突的观点并置,以此来突出截然不同的观点之间的对立与摩擦,形成一种奇妙的相互补充的关系。《静止的生活》只有三个人物:马克,他的妻子谢莉尔和他的情人纳丁,但他们却每每两两就同一问题、同一事件面向观众直接发表自己的看法,有时是马克和谢莉尔,有时是马克和纳丁,有时又是纳丁和谢莉尔,更有的时候三人同时就某一问题发表观点,比如他们都谈到了各自的创伤经历和体验。表面上看起来,三个人都在各说各的,但实际上形成了对话关系,从而使不同身份、性别和背景的人物的声音都得到倾听。在《正义的实施》中,对待同一事件的两种不同意识,针锋相对, 各有理由,作者也并没给予仲裁,点明谁是谁非,没有唯一的正确答案,让观众自己去思索,带有主观性色彩的双重视点构成了较为强烈的双声性对话关系。《正义的实施》第一幕开场中,艾米丽·曼选择了两个有代表性的人物,布姆修女(Sister Boom Boom)和一位警察,他们各自的独白实际上构成了对话,代表了两种敌对的观念。警察代表的是传统的美国人的观念,他们认为同性恋人群在公众场合表达爱意会有伤风化,并且对年轻一代会产生不良的影响。警察这样反问道“当我看到两个秃着头,胡须剃得很干净的男人,他们穿着紧身裤,肌肉健硕,身上到处挂着链条在路上接吻时,难道我还应该微笑着离开,装作这一切都很正常吗?”(9)EmilyMann, Testimonies: Four Plays, New York: Theater Communications Group,Inc., 1997, p.154.而布姆修女代表的则是同性恋这一社会边缘群体。她认为,美国社会蔓延着对弱势群体的暴力,作为同性恋黑人女性,所遭受到的暴力更为严重。暴力孕育着暴力的种子,只会产生更大的暴力,而唯一能打破这个恶性循环的是爱、理解和原谅。但是让她难过的是有些人一边叫嚣着我们要爱,理解和原谅,另一方面又对弱势群体实施暴力。警察和布姆修女的双重独白其实代表着的是美国社会保守势力和受排斥的边缘群体之间的对话。从他们的对话中,观众可以看到不同人群的诉求和期望。了解不同群体的诉求和期望其实是建立对话的基础,而这个对话其实也为剧作家与读者之间的对话奠定了基础。
艾米丽·曼剧本中的超文本对话关系主要体现在作者与主人公的关系及文本与观众的关系这两个方面。在她的剧本中,我们看不到剧作家对主人公全知全能的俯瞰,也看不到她对作品人物的臧否,而更多展示出剧作家与主人公之间平等的对话关系。在《静止的生活》中,虽然作家本人的声音从未出现,但我们通过马克等三人各自的独白可以看出,实际上作家始终在场,她的采访问题牵引着人物一步一步袒露心扉。而在《阿纽拉:一部自传》中,剧作家更是亲自作为人物之一现身剧中,扮演了双重身份。该剧是艾米丽·曼根据自己1977年的一部单人独白剧《阿纽拉·艾伦:一个幸存者的自传》改编而成,于1985年上演。从最初的作品的一个人物到改编版里加入作者本人的声音,不难看出艾米丽·曼在有意识地推动作者和人物间超文本对话关系。首先在作者按语中,艾米丽·曼提到这部作品主要由1974年阿纽拉在伦敦接受采访时的原话和十年后作者在美国对导演的所说的话构成。阿纽拉是一位74岁的犹太女性,经历了纳粹统治时期而侥幸生存,寓居于伦敦北区,而作者在作品中是一个30出头的年轻美国女性,犹太人,20多岁时通过做家族口述史项目来追溯现代犹太移民创伤史,在叙述自己当时的经历和当下的感受。阿纽拉的舞台时间是过去,年轻女性的时间则是现在,这看似远隔了时空的两人独白,通过作者有意识的选择排列,她们对各自家族在二战期间的创伤记忆讲述形成了跨越时空、互相呼应的对话。在1985年的演出中,时钟的滴答声始终伴随着年轻女性的声音,不断地提醒作者和观众:时间在流逝。一老一少的声音最终交织汇聚成一种共识:历史正在快速地消失,曾经的创伤被掩埋遗忘。整部作品以独白构成复调的方式,传达了保存历史的迫切感。
文献剧的介入现实特征决定了其对文本、演出与观众关系的重视,文献剧作家史密斯曾说,她的作品是对共同体的召唤,“鼓励更多的人加入对话”(10)Anna Deavere Smith,Twilight:Los Angeles,1992,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97, p.xxiv.。如何实现这方面的超文本对话是文献剧作家们重点考虑的一方面。首先独白的大量采用使观众更迅速融入见证者的角色,从而产生对话。除了通过以独白形式在舞台展现不同观点的交汇碰撞来引发观众参与讨论外,艾米丽·曼通常会通过富于寓意的标题和意味深长的结尾,通过各种声音和影像媒介来激发观众思考。“静止的生活”的英文表达有双重含义:静物画和静止的生活。这样语义模糊的剧名很容易使观众产生好奇,希望通过观看作品以确定具体含义。而剧终马克展示了他摄于越南战场的一幅作品,食物和手榴弹一起摆放在营地的桌上,像静物画一样,但腐朽的味道随着照片中的苍蝇清晰可闻。这样给人强烈视觉冲突的意象使观众清晰感觉到深受战争创伤困扰的人物生活中的寂静压抑,无处可逃,也最终确定了剧名的深刻含义。此外,《静止的生活》中在主人公马克的独白间运用了大量停顿,尤其是第三幕的后半段,当马克艰难地坦白自己对越南儿童的屠杀以及随后念自己在越战中牺牲的战友的名单时。这样的停顿一方面使观众感同身受,另一方面给他们留下思考的空间。“正义的实施”这样一个醒目的戏剧标题诉诸读者和观众的道德热情,引导他们参与到这场审判中。而剧末当“正义的实施”几个词出现在屏幕上时,法官木槌敲击的声音不绝于耳,警醒观众即使在走出剧院后仍然思考着作品提出的问题。《阿纽拉:一部自传》的结尾定格在作者和主人公的互道再见。一个总是跑着去做事,被时间追赶的老妇人在最后的时刻忽然停了下来,转身,很艰难地说:再见,然后退出舞台。她的不忍不舍、难说再见绝不仅仅只是针对作者,她落寞的声音、苍凉的背影更是对着观众的呼唤,恳求公众不要忘记她所代表的过往,那段黑暗伤痛却很快被时光淹没的历史。以这样余音绕梁的结尾,艾米丽·曼的作品化作桥梁,铺就了与观众的对话之路。
艾米丽·曼的文献剧呈现明显的对话特质,因为对她来说,文献剧忠实于对普通民众的采访和档案资料,它不能撒谎,在这样的剧场“你会同时听到许多不同的声音”(11)Attilio Favorini, “ The Documentary Plays of Emily Mann”.In Alison Forsyth,Chris Megson,ed.,Get Real: Documentary Theatre Past and Present,Basingstoke: Palgrave Mamillan, 2011, p.154.。文献剧构建的对话实际上不仅指说,还包括有人物间的听与听众的听,法沃里尼在评论艾米丽·曼时说她“让自己的人物发声,这也是一种倾听,一种对少数声音的识别”(12)Attilio Favorini, “ The Documentary Plays of Emily Mann”.In Alison Forsyth, Chris Megson, ed.,Get Real: Documentary Theatre Past and Present,Basingstoke: Palgrave Mamillan, 2011, p.165.。文献剧的对话性艺术特征实际上也反映了它搭建公共空间的政治目的以及寻求正义的伦理诉求。综观艾米丽·曼在上世纪80年代的作品,可以看出剧作家坚持不懈地运用各种手法构建文献剧的对话性,推动了该剧派在当时的蓬勃发展。学者们也越来越注意到文献剧的这种对话性特征的发展,如福塞斯(Alison Forsyth)和麦格森(Chris Megson)就指出,虽然文献剧一直是辩论和宣传的有力工具,但它的方式却在不断演化,不再只提供一种占主导的声音或者观点。努斯鲍姆认为文献剧有二元性,一方面声称提供事实,另一方面挑战了公众对事实的信念。因为它提供的往往是来自不同群体讲述的事实,让观众听到不曾听到过的,对事实的复杂性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对真相也有了更加审慎的判断。文献剧场的独声邀请观众参与对话,双声和多声表达不同甚至冲突矛盾的观点。这种对话性艺术特征“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捍卫了其参加公共论坛的权利”(13)Jacqueline O’Connor, Documentary, Documentary Trial Plays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Theater,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013, p.7.。
二 基于声音档案、身体的单人表演
除了艾米丽·曼,美国非裔女性文献剧作家和演员安娜·德维尔·史密斯也积极进行独白式的文献剧创作,而美国文献剧在20世纪90年代声誉日显,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她对舞台表演的锐意变革。《新闻周刊》曾称她为“当今美国剧坛最激动人心的人物”(14)张新颖:《“在媒体与政治间旅行”—评安娜·德维尔·史密斯的单人文献剧》,《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6年第5期,第34页。。史密斯最大的艺术贡献在于创造了建立在录音采访基础上的女性“单人文献剧”,即一人分饰多角的独角戏。作为屡屡被提及的文献剧典范,她的《镜中之火》(FiresintheMirror)和《暮色:洛杉矶,1992》(Twilight:LosAngeles,1992)由系列独白组合的章节构成,受到广泛关注,奠定了其作为当代美国文献剧代表作家的地位。除了在结构上完全摒弃对白,这两部作品最突出之处在于完全取材于真实生活场景中的真人真事,对采访录音进行了逐字逐句的还原,方言土语的原汁原味和受访者的语气完全保留。《镜中之火》取材于1991年夏季爆发于纽约布鲁克林区皇冠高地的一场种族骚乱。史密斯采访了包含受害者家庭在内的50多位相关人士,其中有皇冠高地的居民、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宗教领袖、帮派成员等,选取了其中26人的采访素材,呈现于剧中。1991年首演时,借助服装、发型和道具,她一人分饰这26个形神各异的角色。为了能完成一人饰演多个角色的挑战,她“把档案的作用扩展到编剧以外的表演过程中。她创造了声音与手势的档案”(15)[美]卡洛·马丁:《千年美国文献剧》,虞雯译,《戏剧艺术》2006年第5期,第56页。,注重不同年龄、性别、种族和阶级人物的声音、语调、手势,从而演绎出他们各自的身份。曾执导过史密斯作品的艾米丽·曼曾说,在创作她的文献剧时,史密斯“非常仔细,连哎、嗯这样的语气词都要记录下来”(16)Gary Fisher Dawson, Documentary Theat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 Historical Survey and Analysis of Its Content,Form and Stagecraft,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99, p.132.。这样的创新使她的作品在演出时“现场感和真实性非常鲜明”(17)周维培、韩曦:《当代美国戏剧60年:1950—2010》,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416页。,也因此她的作品被称为“实录剧”。《暮色》于1994年获最佳剧本托尼奖、普利策戏剧奖提名。作品直面了当时震惊全美的事件:洛杉矶暴乱。1991年3月,关于洛杉矶警察在逮捕超速驾驶的黑人罗德尼·金时暴力执法的录像被公之于众,涉事警察受到指控,但经过长达一年的审讯后,除一人外,涉事者全部被宣告无罪。该判决引发了大规模抗议集会,随后集会演变为暴力冲突。这场暴乱使洛杉矶经历了三天的烧杀抢掠。为了创作这部作品,史密斯采访了大约200人,最终保留在剧本中人物多达50人,受访者跨越了不同种族和阶级。实际演出时,史密斯通过更换舞台场景、服饰、特色道具,模仿不同人物的口音、语气、表情,单人扮演了其中的25人左右。值得注意的是,史密斯创作时一方面完全依赖采访录音,不放过一个停顿,确保了作品的真实性,另一方面要从众多的参访中挑出最有代表性的证人证言呈现于舞台,她是有自己的标准的,即不拘泥于自己的非裔身份,“通过努力反映广泛不同的人群来捕捉一个地方的个性”(18)Alison Forsyth, “Performing Trauma: Race Riots and Beyond in the Work of Anna Deavere Smith”,In Alison Forsyth,Chris Megson,ed.,Get Real: Documentary Theatre Past and Present, Hampshire: Palgrave Mamillan, 2011, p.145.。因此她最终在舞台上扮演的人物不仅有创伤受害者、还有施害者、旁观者,不仅有各种宗教派别人士、也包括从政客、知识分子到街头青年各个阶层的人士。可以说她在舞台上的呈现并不是随意的证言并置,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受其创作原则影响的。故而有评论家认为她的文献剧“有着自己的因果序列和对事件的阐释原理,这些粗看时只是简单的文献引用,但实际上我们发现是精心设计的,展现了史密斯作为富有创造力的文献核查者、组织者和表演者的技巧”(19)转引自Alison Forsyth, “Performing Trauma: Race Riots and Beyond in the Work of Anna Deavere Smith”.In Alison Forsyth, Chris Megson, ed.,Get Real: Documentary Theatre Past and Present, Hampshire: Palgrave Mamillan, 2011, p.143.。
史密斯之所以在舞台表演上着力创新,是因为她认为“公共表演有一种独特的能力,可以将我们聚合在一起,在批判性的内省和艺术享受中把我们带出种族意识”(20)张新颖:《“在媒体与政治间旅行”—评安娜·德维尔·史密斯的单人文献剧》,《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6年第5期,第38页。。当观众看到不同身份在一个人的身上自由转换时,会惊讶于身份的可流动性和变化性,开始反思自己被关于身份的固有思维束缚的状况,并“认识到种族、性别和阶级身份的社会构成是阻止他们看到彼此之间存在共性的重要因素”(21)张新颖:《“在媒体与政治间旅行”—评安娜·德维尔·史密斯的单人文献剧》,《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6年第5期,第38页。。在空间和性别研究中,身体“是多种社会关系的产物,铭刻着权力的烙印”(22)黎林:《隔离、边缘与重塑: 女性主义地理学视域下〈晚安,妈妈〉之主题再探》,《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131页。,与身份认同相关。史密斯对身体的充分利用使她得以实现身份的跨越。作为一名黑人女性,因为她自己的特殊身份,史密斯的表演包含了性别和种族的转变。她有意识地通过这种演员和人物在性别和种族身份的跨越让观众看到演员和被采访者间的差异,从而欣赏她试图接近他人的努力,欣赏她对自我之外的他性的渴望,正所谓“我们的肤色、我们的性别、我们的身高、我们的体重都只不过是外在的框架……我们应该成为‘我们’,应该从我走向‘我们’。”(23)Alison Forsyth, “Performing Trauma: Race Riots and Beyond in the Work of Anna Deavere Smith”,In Alison Forsyth, Chris Megson, ed.,Get Real: Documentary Theatre Past and Present, Hampshire: Palgrave Mamillan, 2011, p.144.这是一种致力于建立互相靠近的异质共同体的表演,福赛斯称之为“有意运用演员性别化、种族化的身体造成与被采访者的身体的割裂”(24)Alison Forsyth, “Performing Trauma: Race Riots and Beyond in the Work of Anna Deavere Smith”.In Alison Forsyth, Chris Megson, ed.,Get Real: Documentary Theatre Past and Present,Hampshire: Palgrave Mamillan, 2011, p.144.的表演策略,表演揭示的差异背后是试图沟通和协商的努力。她注意到了这种单人表演中利用个体身体的变换展示来实现创伤治愈的可能性,认为当互相分割对立的族裔、宗教群体肩并肩坐在剧场,观看发生在自己社区的种族冲突事件时,史密斯的表演使他们见证了文献剧场的治愈功能。凭其独特的创作和表演文献剧的方式,史密斯被誉为发明了“一种新的文献剧,既有现场戏剧的及时性,又有电影的流动感”(25)G.F.Dawson, Documentary Theat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 Historical Survey and Analysis of Its Content,Form and Stagecraft,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99,p.165.。从而,她开创的这种文献剧场成为对诟病文献剧缺乏审美效果的评论的一种有力回击。
三 多媒介的舞台呈现
文献剧在当代欧洲的革新和美国剧坛不尽相同。德国文献剧在20世纪90年代开启了第三次浪潮。在描绘这一时期的文献剧时,托马斯·艾尔默(Thomas Irmer)用了立方主义的透视法一词,认为可以用来说明德国文献剧代表人物克罗辛格的多视角的舞台呈现特征。(26)[英]托马斯·艾尔默:《寻找新现实——德国文献剧》,谢克纳、孙惠柱主编:《人类表演学:平行式发展》,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第87页。不同于德国20世纪60年代传统的文献剧,克罗辛格的文献剧“把不同视角的文本(如历史文献、文学文本、统计数据、亲历者的讲述等)拼贴在一起,使用各种媒体(如演员的现场表演、视频转播等),让它们交互补充、批注,甚至互相解构。”(27)李亦男:《德国当代文献剧创作概览》(上),《新剧本》2017年第3 期,第46 页。他的第一部文献剧是《问题和答案》(1996),源自电视直播的艾希曼审判。他把舞台分为三个房间,一个房间里是审讯现场,观众可以进去旁听;第二个房间里观众只能通过扬声器听到第一个房间里的声音;第三个房间采用屏幕同时播放第一个房间里的画面和当年的历史审判电影。观众被分为三组,每组进入房间的顺序并不一样。演出结束后,观众再聚到一起交流感受。观众进入采用不同媒体技术的不同的空间,感官和感受便会不同,此外进入不同空间的顺序不同也同样会产生不同的印象。当他们进行交流时会惊讶地注意到这些差异,从而打破原有的对历史事件的单一的固定看法。通过多空间、多媒介的舞台呈现,克罗辛格呼唤观众自己做理性分析、探索答案,正如他在访谈中所言:“我的作品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就同一历史事件创造尽可能多的视角”(28)[英]托马斯·艾尔默:《寻找新现实—德国文献剧》,谢克纳、孙惠柱主编:《人类表演学:平行式发展》,第93页。。在后来的作品中,克罗辛格越来越多地进行档案文献、文学文本、新闻报道等各种材料的拼贴,并运用广播、电视、电影片段、图片等多媒介来呈现以形成各种观点的并置和冲突。2015年克罗辛格和人合作完成了《国家剧院的绊脚石》,该剧取材于巴登州卡尔斯鲁厄市国家剧院的员工档案,重现了纳粹德国时期该剧院犹太员工被歧视排挤和解雇的过程。2017年克罗辛格带团来华演出了该剧。演出开始前,四名主演在剧场门口引领观众入场。演出中,部分观众被邀请和演员一起围坐在舞台中间一张巨大的桌子旁,桌子上堆满了文件、信件、公函和照片。大屏幕投影上播放着纳粹上台时期群众集会的影片和图片。演出后半部分是对亲历者的采访,此时观众返回观众席,国内学者高子文认为这种设计使观众“获得一种他者视角,因此可以更加冷静与理性”(29)高子文等:《<国家剧院的绊脚石>:让历史的记忆永远不要沉睡》,《广东艺术》2017年第4期,第34页。。在这部剧里,克罗辛格延续了他一贯的手法,利用空间安排和影像、声音等媒介来尽量客观地展现各方观点。当观众处在类似档案室或是研讨室又或是审判室的空间内时,他们有一种参与的责任感,去探寻这些材料、演员的口述里构建的历史,去对同类的行为做出自己的判断。在评价克罗辛格通过空间的安排、多媒介的使用等手法再现历史和现实的多维度的努力时,艾尔默说“他的作品改变了德国文献剧的潮流,由单向的、左倾的政治宣传转向多维、多媒体的呈现,为同一主题提供多重视角”(30)[英]托马斯·艾尔默:《寻找新现实——德国文献剧》,谢克纳、孙惠柱主编:《人类表演学:平行式发展》,第93页。。克罗辛格代表的文献剧场并不为观众提供唯一正确的真相,它们所做的事是要通过有选择地呈现一些事实来引导观众反思。正如李亦男指出:这类文献剧“通过材料碎片化、媒体多元化的手段来达到去中心化的目的。观众面对一片纷乱的文献,没有人做方向的指引,只能自己找寻迷宫的出口,自身的分析能力从而得到了锻炼。”(31)李亦男:《德国当代文献剧创作概览》(上),《新剧本》2017年第3 期,第47页。卡洛·马丁(Carol Martin)指出21世纪的真实剧场和后现代主义有共同之处,其中就“包括拒绝普遍性,认识到戏剧常用的虚构框架和搬演事实之间的矛盾,以及质疑事实和真相之间的关系。当真实剧场声称真相依赖于语境、是多维的、可被操控的,它的策略是后现代的”(32)Carol Martin , “Bodies of Evidence”.In Carol Martin, ed.,Dramaturgy of the Real on the World Stage,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3.。
从克罗辛格的文献剧创作可以看出,为了呈现多视角,他的文献剧舞台利用了不断发展的媒介技术,这说明文献剧的创新与技术进步密不可分,这一点从文献剧一词的正式使用开始就为研究者们关注。皮斯卡托在《政治戏剧》一书中讨论自己的文献戏剧时,就重点介绍了电影影像技术的舞台运用。随着科技的发展,他的追随者们也越来越多地使用各种多媒介形式:电影剪辑、幻灯片、录音等。20世纪90年代,道森(Gary Fisher Dawson)在其论述美国文献剧的专著里就谈到,文献剧需要“合适的空间和技术”(33)GaryFisher Dawson, Documentary Theat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 Historical Survey and Analysis of Its Content,Form and Stagecraft,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99, p.169.。就此而言,它产生于20世纪,更是21世纪的戏剧艺术,是属于未来的,并预测随着科技的进步,数字信息系统、虚拟现实技术等都会融入文献剧。当前学界仍然关注文献剧与科技的关系,并提出了更具体的分析,这类研究以马丁为代表。他认为文献剧场为了再现独特视角的事件、传达观点、信念,需要充分利用复制技术:“录像、电影、录音机、收音机、复印机和计算机”(34)Carol Martin , “Bodies of Evidence”.In Carol Martin, ed., Dramaturgy of the Real on the World Stage,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 2010,p.17.。这些技术手段有时可见,有时并未出现在舞台上。在他看来,当代文献剧场呈现科技、文本、身体三元结构,科技为实现舞台再现的主要因素。正如我们在克罗辛格的文献剧中看到的,剧场对不同媒介的对比使用是创作者有意引导观众注意到媒介对人们认知的影响,从而意识到文献剧的运作方式。所以马丁认为以克罗辛格的作品为代表的文献剧“通过复杂化和质疑档案材料的真实性,颠覆了普通的文献剧类型”(35)Carol Martin , “Bodies of Evidence”.In Carol Martin, ed., Dramaturgy of the Real on the World Stage,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22.,而这种颠覆很多时候借助了技术的力量。佩吉特(Derek Paget)在总结文献剧的艺术表现方式时,把科技技术的运用分为两类:视觉、听觉。其中,听觉就包括了在舞台上用设备播放事件亲历者的声音录音。克罗辛格的文献剧正是注重运用技术手段不仅从视觉上、而且从听觉上激发观众感受。可以看出,文献剧研究者普遍认同技术的发展给当代文献剧带来了新的活力。
文献剧是力图客观呈现事实的戏剧,传达了有良知的创作者直面历史和现实的犀利勇气,成为欧美剧坛的一种先锋势力。在艺术手法、舞台表演上力图创新,一方面以艾米丽·曼为代表的剧作家积极探索加强作品内外部对话性的途径,以安娜·德维尔·史密斯为代表的剧作家创立和推广以录音档案为基础的单人文献剧,利用演员身体突破身份界限,孜孜于舞台表演上的开拓。另一方面以克罗辛格为代表的文献剧则受现代技术发展的启示,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致力于利用空间、多媒介呈现多视角的舞台。当代欧美文献剧的成功得益于内容和形式的相得益彰,正是由于其在艺术表现手法以及表演上的不断变革,文献剧在治愈集体创伤、重塑社会凝聚力,以及促进社会的民主、公正、和谐方面才能有所突破,从而展现艺术的操演性,实践以艺术影响现实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