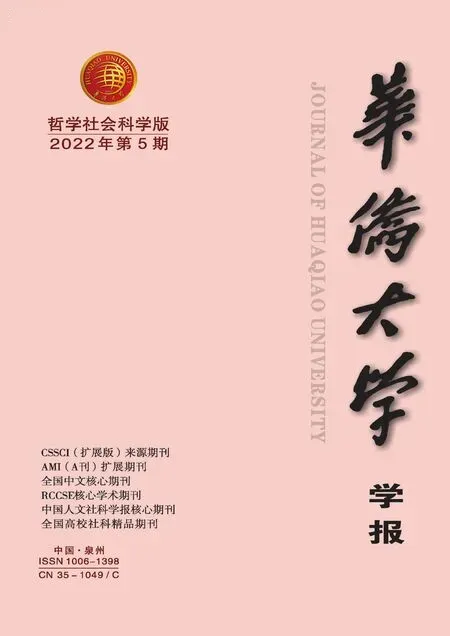论自然审美中的框架问题
○梁向真
对自然审美中框架问题的思考始于艺术审美,框架是艺术品作为独特审美对象的显著特征,对欣赏者的审美体验起着重要的作用。典型的绘画框架限制了欣赏者视觉注意力的范围,使艺术作品内容得以清晰显现。同样,戏剧、歌剧、舞蹈和其他各种表演也受到其表演环境的限制,文学作品的封面、音乐作品的表现时长、雕塑作品的物理维度都被视为一种框架。在自然审美方面,18世纪英国哲学家发展起来的“无利害性”概念,支持了一种“如画”的审美方式,这种审美方式在18世纪末成为一种自然审美的标杆。如画审美实践中给风景施加的框架,其功能和艺术品的边框有着本质的类似,即都设定了审美对象与其背景的边界。如画和与之伴随的形式主义审美是自然有框审美的典型,在19、20世纪相当长时间内主宰着大众的自然审美。
但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环境美学的兴起,以赫伯恩、卡尔松为代表的环境美学家对把有无框架作为区分自然与艺术的根本特征之一,他们认为作为审美对象的自然是无框的,给自然对象强加上一种类似艺术品的边框阻碍了自然欣赏的无限可能。卡尔松更是通过对形式主义审美的猛烈抨击否定了凸显事物形式属性的框架的功能。但是,在当代的自然审美理论中,以温和形式主义审美的提倡者赞格威尔(Zangwill)为代表的少数美学理论家依然支持对自然框架式的欣赏,并坚持认为框架概念不可避免地存在于自然审美的理论研究和审美实践中。
本文分析了框架概念在自然美深化语境中的扩展,梳理了有框自然审美和无框自然审美的争议点,结合框架概念的新内涵展开论证,拟解决以下两个具有递进关系的问题:(1)自然审美中是否存在框架?或自然审美是否需要设置框架?(2)如果存在框架,那么框架在自然审美欣赏中的作用和意义是什么?
一 艺术的框架与自然的框架
关于美学语境中的框架或边框(frame),通常是指审美对象所具有的、使之区别于其他对象从而有利于进行审美欣赏的边界,框架不仅指实质性的物理边界,还指各种广泛地将审美对象与其他事物区分开来的隐形边界。赫伯恩给框架下了一个宽泛的定义,即“它不仅涵盖了绘画的物理边界,还涵盖了不同艺术中所使用的各种装置,这些装置用来防止艺术对象被误认为是自然事物或没有审美趣味的人工制品”(1)Ronald, Hepburn, “Contemporary Aesthetics and the Neglect of Natural Beauty.” In The Aesthetics of Natural Environments.Edited by Allen Carlson and Arnold Berleant.Peterborough: Broadview Press, p.46.。因此,在这个广泛的意义上,艺术作品中的框架包括:剧院里舞台区与观众区的划分,音乐会上表演者的表现时长,文学作品页面排版中的版式和字距,比如在诗歌与题目、页码、评论性注释、脚注之间所留出的空间等。框架使艺术作品与其背景泾渭分明,为欣赏者的欣赏划分了一个明确的起始边界,既圈定了欣赏者注意力的范围,使其审美兴趣和审美评估都保持在框架之内,又使艺术品的内容及其整体性得到了清晰的凸显,艺术品凭借其框架具有了一种确定性和稳定性。一般来说,艺术品的框架具有以下特性:(1)框架具有边界性。框架的作用是设置边界,使审美对象与周边的背景分离;(2)框架具有固定性,是静态的、二维的;(3)框架具有封闭性,它是对审美对象完整性的确定。因此,框架是艺术,尤其是视觉艺术作品的显著特征。
早在古希腊的历史中我们就可以窥见框架概念的雏形。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到,美在体积与安排:“一个非常小的活东西不能美,因为我们的观察处于不可感知的时间内,以致模糊不清:一个非常大的活东西,例如一个一千里长的活东西,也不能美,因为不能一览而尽,看不出它的整一性。”(2)亚里士多德《诗学》,罗念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25、26页。塔塔尔凯维奇(Tatarkiewicz)把亚里士多德的论述与自然事物联系了起来,他认为:
他(亚里士多德)在自然中看到了美,因为那里的一切都有合适的比例和大小,而人,作为艺术的创造者,却很容易误入歧途。他提起人体的美,却从不说风景的美。这可能与希腊人的一种信念有关,即美源于比例与和谐,而这两者在风景中比在单个生物、雕像或建筑物中更难找到。这也是一种特殊鉴赏的表达,当浪漫主义者偏爱景观的布局时,古典时期的人则偏爱单个的事物,因为它们的限度(limit)更清楚地显示出它们的比例、尺度和统一。(3)Wladyslaw Tatarkiewicz,History of Aesthetics.Vols.1-3.The Hague: Mouton, 1970,1974.pp.152-153.转引自Ronald Moore, Natural Beauty, Peterborough: Broadview Press 2007, p.44.
把古希腊时期限度(limit)的概念与自然事物审美评价的条件联系起来,这可以被视为自然审美框架概念的萌芽。亚里士多德的单一性和限度的概念为现代美学理论中的框架概念提供了重要的铺垫,与限度联系着的框架成为审美体验的重要元素。
然而,框架问题并没有止于艺术审美,而是延伸到受艺术审美影响的自然美学中。18世纪之前的自然哲学美学研究鲜有成果,而进入18世纪之后,严肃的自然审美及其研究在世俗艺术和科学发展营造的背景中兴盛起来。现代美学的奠基者们在科学的新发展和日益增长的经验主义的倾向中,开始把自然看作审美体验的理想对象,并把“无利害性”作为这种体验的标志。18世纪的无利害性概念作为一种审美标准,把欲望、知识和种种联想从审美体验中排除出去。阿里森(Alison)在夏夫兹博里(Shaftesbury)对无利害性概念的系统阐述上做了进一步发展,提出了一种与审美对象契合的“心灵状态”,即一种空白和闲暇的心灵状态。只有在这种状态中,注意力才不会被导向任何个人的方面,才能体验到审美对象所产生的强烈印象。阿里森把无利害性概念发展到了极致,他要求审美主体成为一面纯净无暇的镜子,以便去接受审美对象没有被曲解的所有品质。无利害性概念发展的一个重要结果是,无利害成为审美感知中不可缺少的一种注意力模式,即审美主体专心致志于一个像艺术作品这样的客观对象,只感受它的色彩、形状和比例等,对它边框之外的其他内容和环境没有任何的关心。框架作为一种将审美对象与其背景分割开来的手段,契合了审美无利害对主体审美关照时心无旁骛的要求。在这个意义上,无利害性不仅把自然与阻碍它被欣赏的宗教联想和种种个人道德利害分离开来,也把这种对艺术品框架迎合的影响延伸到自然欣赏中,为一种自然的如画审美模式奠定了基础。同时欧洲风景画的流行也促进了对自然的如画审美方式。通过为自然风景加上一道框架,可以使欣赏者更好地专注于框架之内的景色,这更有利于保持一种空灵的心灵状态去体会自然美。在这种赋予自然的框架中,体现了一种无利害的专注与沉浸于审美对象的理念。
因此,追溯自然审美中的框架体现,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如画审美和形式主义。“如画”作为一种美学观念或者说审美理想,萌芽于17 世纪意大利和荷兰风景画的创作中,并在18世纪被英国艺术家移植到本国的风景描绘中。同时,经过英国美学家吉尔平(Gilpin)、普莱斯(Price)和奈特(Knight)各自的理论阐述,逐渐把如画演变为一种观看和描绘自然风景的鉴赏标准。不列颠人通过对欧洲风景画的研究,不仅掌握了如画美在画面上的构成规律,还由此培养出了一种欣赏自然风景的新方式:在英国的乡村风景中寻找如画美的元素和构图。观景道具“克劳德镜”(Claude glass)的发明无疑为游客在自然中追求审美卓越的理想提供了极大支持。克劳德镜是一种凸面的着色玻璃,观景的人手持镜子背对自然,身后的风景就反射在镜面上,克劳德镜就如同一个画框圈住了宜人的风景。镜子的凸面可以缩小总体景观、去除无关紧要的细节,因此,透过克劳德镜观看到的是经过处理的画面,镜中的画面相对于自然实景更加紧凑且均衡有序。克劳德镜既是风景的真实折射,又改进了风景,它把景物的真实感和对审美卓越的理想追求结合了起来。对体验者来说,看似普通的乡村风景被以一种理想化的方式呈现了出来。如画提升了纯形式的视觉景观,促进了自然风景审美的迅猛发展。这种自然审美的特点是仿照艺术绘画的手法和构图,给不均衡、无规律的自然风光加了一种人为的构图和框架,使之呈现出比例协调、元素均衡、形式统一的审美特点。如画促进了形式主义审美的发展,使自然事物的形状、颜色和线条等形式元素成为自然审美体验的核心。确实,如画和形式主义审美是自然有框审美的典型,在19和20世纪相当长时间内主宰着大众的自然审美方式。在如画审美中,给自然赋予的边框和艺术的边框有着本质的相似,即都是一种物理边界的清晰设定,以使审美对象与其背景产生明显的界限,形成最优的构图以将注意力保持在审美对象上,通过无利害的静观实现审美欣赏的最大化。
对自然美的兴趣和研究在经历了如画的巅峰发展之后,于19世纪进入了哲学美学研究的边缘领域。虽然如画和形式主义审美在自然美被哲学美学遗忘的19、20世纪继续延续着自然美欣赏的传统,但直至20世纪下半叶,自然美才重新回到美学的主流研究视野。1966年,赫伯恩(Ronald Hepurn)用一篇开拓性的文章重启了美学界对自然美的关注,同时明确地把“无框”(frameless)作为自然审美的主要特征。他在《当代美学与对自然美的忽视》一文中提到,自然对象与艺术对象相比,一个最显著性的区别就是自然对象是无框架的(4)Ronald Hepburn, “Contemporary Aesthetics and the Neglect of Natural Beauty.” In The Aesthetics of Natural Environments.Edited by Allen Carlson and Arnold Berleant.Peterborough: Broadview Press, p.46.。诚然,与自然相关的概念是无限的、广袤的、无边无际的,而与框架相关的表述通常有边界(bound)、限度(limit)和限制(limitation)、局限(confinement)等,因此框架所具有“限度、局限”的含义与自然的无限性看起来并不协调。赫伯恩明确地把自然的无框性作为自然与艺术的重要区别,这引发了当代大多数以自然环境为研究对象的环境美学家的共鸣,自然审美的无框性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当代环境美学研究者的共识。
但是,尽管反框架自然审美理论家对破坏与削弱自然欣赏的框架大加批判,还有一小部分框架概念的支持者依然坚持自然欣赏中框架或施加框架的合理性。20世纪初,布洛(Bullough)提出的审美“心理距离说”(Pshychical Distance)就暗含了一种框架的概念(5)Edward Bullough, “ ‘Pshchical Distance’as a Factor in Art and as an Aesthetic Principle,”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5, 1912, pp.87-98.。布洛认为审美中要保持一种“心理距离”,这是与艺术和自然环境都相关的基本原则,即在审美中,要脱离实际的、真实的自我,使审美对象摆脱人本身的需要和目的。欣赏者对审美对象保持一种恰当的心理态度,才能捕捉到令人愉悦和具有启示性的审美品质,而这种心境与正常的或本能的心境不同。观察者必须从体验中抽走他最初始的感觉,而将注意力放在现象的客观方面。这种操作在最初陷入实际焦虑的自我和最终体验到深刻审美特质的自我之间插入了“心理距离”。距离其实是一个程度的概念,依赖于审美主体和客体的诸多元素,而后者其实就是指框定了客体的种种元素,比如舞台、音乐起止前后的寂静、底座等。布洛把框架看作决定心理距离的一个重要参照物。
杰罗姆·斯托尼茨(Jerome Stolnitz) 认为自然欣赏是自框定(self-framed)的,这符合大部分的自然审美实践。他说:“虽然除了人类的感知外,自然界就其存在来说缺少一个框架,但当它被审美地理解时并非如此。那时,观看者自己给自然景观加上了一个框架。他选择在审美中要关注的事物,并为之设定界限。我们都时不时地这样做。”(6)Jerome Stolnitz, Aesthetics and the Philosophy of Art Criticism: A Critical Introduction.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0, p.48.准森(Drenthen)呼应了斯托尼茨的说法,他从两个角度看待自然的框架问题,“缺乏框架…一方面使自然事物变得更加不确定和不可预测。但另一方面,这也为感性的惊喜和开放的冒险感创造了空间,并促使自然环境的欣赏者提出自己的‘框架’”(7)Drenthen, M.and Keulartz, J.ed.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Crossing Divides and Breaking Ground.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14,p.3.。准森的陈述涵义十分丰富,既承认自然的无框性,又默认了无框自然审美中萌生“框架”的可能性。卡罗尔(Carroll)在回应自然欣赏的唤醒模式如何解决审美焦点的问题时说道:“一些自然景观有天然的框架,或者我更愿意称之为天然闭合:如洞穴、小树林、岩洞、林中空地、林荫道、山谷等。其他自然景观尽管缺少框架,但却具备对人类生物来说的天然显著特征——流动的水、明亮的光等都是自然本能地吸引我们注意力的特征。”(8)Carroll, “On Being Moved by Nature,” in Allen Carlson and Sheila Lintott (eds), Nature, Aesthetics, and Environmentalism: From Beauty to Du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p.415.卡罗尔把自然中一些相对封闭的景观看作是一种框架,这与其它自然特征的显著性,共同抓住了欣赏者的审美注意。
以上论述表明,框架问题在自然审美的理论研究和审美实践中是一个隐性但不可忽视的问题,并且触发了种种争论。随着自然美理论研究的深入,重新思考框架理论的内涵成为奠定自然审美基础的重要考量因素。与艺术美学里单纯的框架概念不同,自然美学中的框架有了更宽泛的概念和外延,框架以及施加框架的手段都发生了显著变化。自然的框架与艺术的框架,既有共同点又有显著差异。首先,不同于艺术品框架的显而易见和形式化,自然审美中的框架更多地带有心理学和认知维度的隐性色彩,更加接近美学意义上的框架概念,而非物理意义上的框架概念。其次,在自然欣赏中,框定欣赏对象的手段多种多样,有形式的,也有非形式的,既有人为施加的,也有自然形成的。再次,框架在自然审美中是变动不居的,根据欣赏者所处的环境条件发生变化。总之,框架的“限度、限制”维度与自然审美的无限潜能并非不可调和,对过去基于艺术欣赏的、狭隘的框架概念需要在自然美的语境中,结合自然审美的理论和实践进行重新的思考与审视。
二 有框的自然审美
如画作为一种自然审美范式,本质上是以艺术欣赏的方式来构建自然欣赏,如画附着给自然的边框是刻意的、人为的。但是在自然审美体验中,还有一种框架,是自然的、非人为施加的,甚至抽象的。在自然审美实践中,人们有意或无意地习惯用无数种方式来框定自然景物,以达到审美愉悦的目的,比如欣赏风景时,人们时而用手比起的取景框。从某种意义上说,许多自然事物或多或少都是自带框架的。一朵蒲公英、一个洞穴、或一座山都是一个被其物理边界所框定的自然事物,这些由其自然边界构成的自然事物或风景是令人愉悦的。从洞穴看出去的美丽景色,是由洞穴的墙壁框定的。极其微小的自然生物可能因为与其所处背景的比较关系而变得美丽。体型适中的麋鹿,其自身的物理尺寸和身材结构,就是一种值得欣赏的美。身处自然环境之中,鉴赏者都在体验中不断地、习惯性地组织部分和整体,毕竟鉴赏者所在的环境并不是一个无差异的广阔的体验全景。鉴赏者通常都是在行进的过程中构建或框定自身体验的。艺术品的边框只不过是一种更广泛的框定行为的典型。甚至自然事物的名称、范畴,都可以视为一个边界,帮助人们锁定要观察的审美对象,从而在其中可以体验到它作为该事物本身独一无二的美。一朵百合花被称之为百合,人们欣赏的就是它所展现出来的特有审美特质:洁白如玉的花朵,自由舒展的花瓣形状,亭亭玉立的花枝。在无边界的自然中,欣赏者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将自己的欣赏框定起来。在这些有框的自然审美中,自然事物的形式特征比如色彩、形状和线条等往往表现得十分突出。
因此,形式主义自然审美大抵与框架概念相伴相随。形式主义产生于对艺术审美的思考,在自然美学的领域有着它独特的影响力。20世纪早期,英国文艺评论家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把形式主义发展成一种对后印象派画家比如保罗·塞尚(Paul Cézanne)等作品的处理方式。贝尔认为,后印象派画家和传统艺术家不同,他们的主要目的不是呈现角色和事件、描述故事和表达观点,而是制造线条和色彩的特殊结合,特定的形式和形式之间的关系。在这些画家的作品中,所呈现的实际物体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绘画过程中所产生的单纯的形式。贝尔把后印象主义的成就不仅仅看作是艺术实践的转变,而更多的是对艺术本质和审美体验的根本发现。如果画中的形状和图案唤起了欣赏者对人物、事件、情感和想法的思考,则会阻碍对艺术的审美欣赏。贝尔认为这些想法与审美是“不相干”的。恰当的欣赏必须仅仅专注于纯粹的形式,为了能够进行这样的欣赏,贝尔说:“我们只需要有一种形式感和色彩感,以及关于三维空间的知识。”(9)Clive Bell, Art, New York: Frederick A.Stokes.1913, p.27.
尽管贝尔的主要兴趣在于对视觉艺术的欣赏,他也提到了自然形式审美的可能性。关于自然审美,贝尔说道:“谁又在生命中,不曾有一次会突然把风景看作了纯粹的形式?那时我们看到的不是田野和村舍,而是线条和颜色……显然我们从实在美中获得了通常只有艺术才能给予的激动,因为我们已经把这一切看成了线条和颜色纯粹形式的结合。”(10)Ibid., p.53.贝尔把自然审美与艺术审美的基本活动等同起来:即二者都是把审美对象看成纯粹的形式。但他同时也承认自然的审美欣赏要比艺术的审美欣赏更难也更稀有。鉴于绘画和自然风景作为审美对象在性质上的不同,这种“难”并不是指站在艺术馆里,把塞尚画中山边的房子看成纯粹线条、形状和颜色的组合很难,真正难的是欣赏者能够把真实的山看作是“线条、形状和颜色纯粹形式的结合”。因为真正的风景并不是一幅画,它不是尺寸合适而又整齐得呈现在框架内,且能一览无余的。相反,自然是广阔而包罗万象的。欣赏者很难看到各种各样的形状起止于何处,因此很难判断审美对象的准确边界。自然景物具有不确定性,比如山峰,其外观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甚至因为光线和大气状况的改变而分分钟呈现出不同。欣赏者位置的移动也会导致事物的显现发生变化,比如距离的拉近和角度的改变等。最后,风景不可能隔离在艺术馆平静和可控的环境内。大自然不断提醒人们它的风景不仅仅是线条、形状和颜色的组合,自然以吹到我们脸上的风、冲刷着我们的雨水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方式靠近我们。
鉴于以上情形中的问题和质疑,形式主义者的对策之一是观景台的应用。事实上,形式主义审美方式也是现代观景台实践的理论基础。观景台是一个特定的地点,比如公路上的岔道口。观景台的地点选择可以让观看者把周围的风景元素融合起来构成一张精美的“图画”。比如山口位置的观景台可以让各种山脉的形状看起来互相平衡,或者能让观看者看到各种形状赏心悦目的多样性。另外,观景台给观看者重现了艺术馆中的宁静氛围,避开大自然可能给观赏者带来分神的狂风骤雨,也省去了跋山涉水的艰苦旅程。欣赏者在这片刻的宁静中可以专注于眼前优美的线条、起伏的形状和悦目的颜色。从这种意义上看,观景台确实把自然变成了一幅巨大的立体画卷,为欣赏者而展开。形式主义和如画欣赏一样,都进一步地提升了纯形式的景观视觉,促进了形式特征在自然环境中的欣赏。
在形式主义自然审美中,有无框架对形式特征具有重要意义。无论是观景台、克劳德镜还是现代的相机取景框、照片和幻灯片,它们在自然审美中发挥了异曲同工的作用,即通过给自然风景施加上一种或大或小的边框,将欣赏者在自然欣赏的时候导向风景的形式特征,突出了形状、颜色和线条。自然环境中的形式元素通常只有在以某种组合或某种方式被框定为一个可品味、可欣赏的整体时才具有审美吸引力。形式自然美是自然事物各种特征之间的关系,或者其特征与审美群体中其他事物特征之间关系的结果,这些有联系的各种特征在某种程度上被框定或组合成一个整体才生成了美感。正是由于这些关系,而不是由于任何一个特征或一组特征的存在,一个事物才被认为形式上是美的。框架的存在舍去了不相关的形式元素,只把欣赏锁定在框架内具有强烈感官特征的形式元素上。例如,在冬日暖阳的照射下,湖面上荡漾着无数的涟漪,波光粼粼、生动迷人。在人们的审美意识中,涟漪和波谷呈现在太阳映射的湖面上才会如此吸引人,而框架之外的湖边的树木和飞鸟都不在人们的欣赏范围。这种框架蕴含了一种形式的统一,一种感觉元素的具体性。框架之于形式美就如同杜威“完整的经验”,保证了此刻体验本身的整体性或统一性之美,通过连续性、轮廓和圆满性来加以澄清和强化。自然欣赏中的框架有着和艺术品框架类似的作用,即保证了相对整体中体验的完整性。
桑塔亚纳(Santayana)说过:“自然景观是一个不确定的对象:它几乎总是包含着足够的更多样性,给眼睛极大的自由去选择、突出和组合它的元素,而且,在暗示和模糊的情感刺激中更为丰富。一处被欣赏的景观总要是构建的。然后我们可以感受到景观的美。这种美依赖于幻想、想象和客观化的情感。杂乱无绪的自然景观不能被除此之外的其他方式欣赏。”(11)George Santayana, The Sense of Beauty, New York: Scribner’s, 1936, p.101.这些经典的论述背后隐藏着一个微妙的事实:即如果欣赏者想要把变动不安的、无穷尽的感官领域转换成可感知的整体,那么就需要某种边界和阐释。在此,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从未谈及风景之美的亚里斯多德,暗示美的可能性取决于限制的概念。正如他所言,“限制”使人们能够把自然事物作为一个个整体看待。根据特定于它的适宜性准则,如果一个自然事物结构匀称,它可能是美的,否则就不是。根据这种理解,我们可以这样概括桑塔亚那的观点:即被视为美的自然事物,必须是被构建的,否则它可能是杂乱无章、毫无头绪从而无法掌控的。而要被构建,就注定它必须是有界限或框架的,这也同时显示出它是作为整体之中的部分的意义。温和形式主义的支持者赞格威尔对此的观点是:“与其说自然审美没有框架的,不如说它有着无限多的框架,自然在所有的框架中都具有审美属性。”(12)Zangwill Nick.X*—Formal Natural Beauty[J].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2015(1):1, p.220.这种形式的审美属性并不会随着框架的变动而产生波动。因为在赞格威尔看来,框架的变动也许会增强或减弱部分形式属性,但自然的实质性审美属性(substantive aesthetic property),即自然独立于人类的本质审美属性并不会因框架而产生变化。框架是人类在浩渺的自然中感知审美的手段,并不一定会损害自然的审美属性,或者至少可以说,自然审美中的框架揭示的是自然美学问题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 环境美学对有框自然审美的批判
20世纪中下叶,随着环境美学的兴起,自然美的研究进入到更深层更多样化的发展阶段。环境美学主张将自然审美置于环境的维度中进行研究,以卡尔松和柏林特为代表的环境美学家提倡自然环境的审美模式和参与模式,拒绝割裂自然事物与自然环境,反对景观式和静观式的自然审美。在这种背景下,仅关注事物形式特征的形式主义被环境美学理论家们诟病,而与形式特征相互强化的框架概念也受到了多方面的质疑。赫伯恩认为框架拆分了自然事物与其环境,成为分隔自然与自然体验者的屏障,浸入到自然之中欣赏者才是自然欣赏的局内人(insider),而通过边框去欣赏自然,则只能是自然欣赏的局外人(outsider)。赫伯恩的描述是:“我们身处自然,是自然的一部分;我们不是站在它的对面,就像站在一幅墙上的画的对面一样。”(13)Ronald Hepburn, “Contemporary Aesthetics and the Neglect of Natural Beauty.” In The Aesthetics of Natural Environments.Edited by Allen Carlson and Arnold Berleant.Peterborough: Broadview Press, p.45.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观点把框架看作一道墙,屏蔽了自然审美的动态性和参与性,隔开了本该融入到一起的整体。赫伯恩承认艺术品所使用的框架,其构图优势在艺术领域是有益的,但应用于自然中却扭曲了自然审美的本质属性。再者,框架的静态和二维,与自然本身就无法协调,无法框定动态变幻的自然。自然带来的是无限的视角和可能性:“没有‘框架’妨碍了自然审美对象的完全确定性和稳定性,那么它至少提供了回报……即不可预知的知觉惊喜。”(14)Ibid., p.47.这些惊喜的可能性赋予了自然体验一种开放和冒险的感觉,而任何对自然事物施加的框架都破坏了这种开放和冒险的感觉,扼杀了灵动神秘的自然审美体验。
赫伯恩对自然审美中框架的批评主要是建立在艺术作品与自然对象的区别上,卡尔松则从他的科学认知主义和自然环境模式的自然审美为出发点抨击有框的自然审美。首先从科学认知主义的立场看,卡尔松主张科学知识的介入会改变人们的审美体验,这使风景上受到挑战的自然区域也能因生态美得到恰当欣赏。而作为框架审美基础之一的无利害性思想,是拒绝与对象有关的知识进入审美感知的。在这种意义上,卡尔松用基于科学认知的审美模式驳斥了传统审美无利害的观念,也彻底打破了框架存在的意义。其次,从卡尔松的自然环境模式来看,他坚持在任何形式的框架内对自然形式特征的欣赏,都不是对自然如其所是地欣赏。的确,艺术作品中的某些品质依赖于框架的组织力,因为它们只有通过艺术家的设计才会产生,而设计是在框架包含了内容之后将它们呈现出来。例如,一幅画只有通过它的空间边界限制才能成为一幅作品。交响乐的形式被它的传统组织形式所限制,在其组织形式中构成了一个审美的整体。卡尔松把有无框架视为艺术和自然之间“一个明显但重要的”(15)Allen Carlson, Aesthetics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Appreciation of Nature, Art, and Architecture.London: Routledge, 2000, p.36.区别,因为这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当传统艺术作品被框起来时,框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形式品质。因为画框是静态的,审美对象是在画框内被欣赏的,所以形式品质成为作品的一个重要决定性因素,这解释了对艺术作品的欣赏和评价相对比较明确。但在自然环境中,框架是人为施加给动态自然的静态条件,自然环境只有在观赏者给它加上一个框架时,才会显得具有形式特征。但人们对环境审美品质的体验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自然环境欣赏因为需要与对象的互动因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所以自然环境是不具备形式特征的。人们进入自然,穿过自然,或围绕自然,这使框架的概念和它所伴随的形式品质都变得无关紧要。在卡尔松看来,静态框架的概念既不合适也不正确,它是不适用于自然美的恰当欣赏的。卡尔松把框架与需要高度参与性的自然环境欣赏对立起来,因为:“一个人不能既置身于他所欣赏的环境之中,又同时去框定环境;如果他通过身处其中来欣赏环境,那么他欣赏的就不是一个有框架的环境。”(16)Allen Carlson, Aesthetics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Appreciation of Nature, Art, and Architecture.London: Routledge, 2000, p.37.
卡尔松用一个典型例子来论述有框自然审美与无框自然审美的区别,以此来抨击自然审美中的框架。在加拿大阿尔贝塔省加普斯附近,有六间带有大窗户的小屋,从窗户俯视可以看到一个巨大的高山环绕的湖泊。对站在小屋外的人来说,自然环境看起来既说不上均衡也说不上不均衡,既不那么统一也不混乱。对一个坐在小屋里的人,他透过窗户往外看,窗户作为边框使风景均衡又统一。但对一个站在屋里透过窗往外看的人来说,这种风景被部分地破坏掉了,因为窗框遮住了山顶,破坏了景致的平衡。这个例子说明了自然环境与两种被框定的自然环境的区别。只有第一个人在真正的欣赏自然,后两者是在被框定的场景中被动地观看这或好或糟的构图而已。这个例子再次说明,自然环境只有在以某种方式对其施加一种框架,从而在形式上形成一种景色时,才具有形式特征。但在卡尔松看来,自然审美的恰当模式应该是以事物所属类别的科学知识为基础,是一种积极的、参与的、互动的审美体验,这与远距离地静观自然并对其施加框架显然是不相容的。卡尔松对框架的拒绝也否认了自然环境具有形式属性这一论断。卡尔松把框架视为形式主义歪曲自然审美的一种工具,通过框定手段把丰富动态、千变万化的自然还原为一个个孤立、远观的二维场景,只剩下线条、颜色和形状的组合。
总之,作为一个坚定的反形式主义和反框架主义者,卡尔松坚持把形式品质与框架同等对待,都视为对自然审美的贬低,因为要感受形式属性就必须在框架施加的范围内感知形式和谐或平衡的构图,但对自然环境的欣赏最重要的是不受框架的限制。其次,卡尔松认为将框架中的自然事物视为线条、平面、颜色、纹理等的组合,最终是否定了它们的自然性(naturalness),不是按照自然本来的样子进行如其所示的欣赏,而是把自然看作一种准艺术品从而贬低了对它的审美欣赏。卡尔松反对“风景崇拜”,框架把千变万化的、多维度的自然切割成一个个没有生命的、静止的风景,这是风景崇拜和如画的直接产物,和风景画、明信片和照片一样抹杀了自然无限的审美属性,失去了自然审美的全部意义。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卡尔松对框架和形式主义观点的反对,考虑的是自然环境的欣赏,抨击的是框架对自然环境作为一个整体的连续性、无限性的破坏和拆分。卡尔松重视的是在丰富的环境背景下观察自然事物可以产生的不同和惊喜的欣赏效果。但是,并非所有对自然事物美的欣赏都必须是基于自然环境中的欣赏,对自然事物的形式特征之美也不能全盘否定。比如对一颗天然紫水晶纯形式的欣赏,这种欣赏所关注的形式特征使我们联想到的是水晶作为自然物而非人工制品的属性,它依然具有卡尔松所说自然性。因此,如果因为某些自然事物脱离了它的环境,其作为自然事物的形式特征也与美脱离了关系,这显然有些过于绝对。
卡尔松对自然审美中框架的抨击主要源于他对审美无利害性和形式主义审美的反对,而推崇自然审美自由模式的费舍尔(Fisher)却用自然框架的任意性解构了有框的自然欣赏。在检验审美欣赏客观性原则的两个标准,即认同要求和对象指导要求时,费舍尔切入到对自然欣赏框架问题的讨论中。以自然声景的声音事件为研究对象,费舍尔对自然欣赏中框架的批判主要围绕三点。第一,为自然声音施加客观框架的不可信性。第二,不存在一种客观、正确的框定自然的方式。第三,自然声音欣赏的框定方式是任意的。关于第一点,费舍尔把自然中的声音与视觉艺术和音乐进行比较。自然声音因为没有自然边界和物质阻挡,也没有作曲家的规定指导,因此无法为之设置框架。正如费舍尔所言:“我们无从得知对于正在聆听的自然声音,如何规定一种框定方式比另一种更加正确。”(17)John Fisher, “What the Hills Are Alive With”.In The Aesthetics of Natural Environments.Edited by Allen Carlson and Arnold Berleant.Peterborough: Broadview Press, p.241.费舍尔批评了对自然声音施加框架的一种做法,即对自然声音进行录音。费舍尔指出这种录音虽然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但是更多的是它对自然声音欣赏的误导性。首先因为这种录音与实际听到的声景完全不同,录音本质上是给聆听者设计了一个场景,一组平衡,排除了很多其他声音而只关注于选定的声音,这就像风景照片的边框,以一种特定的、人为的方式构建了风景。录音体现更多的是录音师的个人偏好,而非欣赏者身临其境所聆听的真实声音。
另外,通过把自然声音事件与音乐作品进行类比,费舍尔再次质疑了对自然声音施以某种客观框架的可能性。第一,自然声音事件的独特性不同于音乐作品的再现性(repeatability)。演奏同一音乐片段的声音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之间的复制,音乐作品能够长久流传下来并且获得美学评价的原因就取决于作品的再现性。再现性是音乐作品最重要的核心概念之一。相比之下,自然中的整体声音事件大多是独特的。它并不是从某一声景之中抽离出来的声音对象,也不能达到音乐作品那种程度上的再现性。这种独特性不仅体现在受人类影响的声音事件中,比如飞机从头顶飞过的轰鸣以及遥远的火车汽笛声,而且由于天气和季节的多变性以及某些特殊事件的复杂性,对于纯粹“自然的”(natural)声音事件来说亦是如此。第二,在时间框架(temporal framing)的问题上,自然声音时间框架的不确定性不同于音乐作品的明确性。对音乐作品来说,作曲家为其确定了时间长度、结构关系和形式等要素,因此音乐具有明确的时间框架。但对聆听自然声音来说,时间长度和重复的旋律都无从确定,就如同无法判定十秒聒噪的风声和三十秒的突然寂静哪个是更适合美学鉴赏的长度一样,因此自然声音事件并不具有本质规定的时间框架。至此,费舍尔推进到他的第二个观点,即如何为声景中的声音事件作框不存在有意义的、约束性惯例,不存在某种唯一正确、客观的框定自然声音欣赏的方式。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费舍尔的观点:一方面费舍尔对自然声音欣赏约束性惯例的否定体现出他对施加声音欣赏框架的批判,同时另一方面费舍尔又用框架的任意性解构了自然声音审美中框架的可信性。费舍尔指出,与艺术相比,自然的框架相对缺乏。自然欣赏并未围绕着一个框架,而是有许多不同的、合法的方式来框定它。在艺术中是由艺术家或艺术范畴框定出审美对象,在自然欣赏中则由欣赏者自由地选择如何框定审美体验,而这种框定自然的方式基本上是任意的:“当然,我们可以选择框定的原则,但是我看不出它们是如何摆脱这种任意性的。”(18)John Fisher, “What the Hills Are Alive With”.In The Aesthetics of Natural Environments.Edited by Allen Carlson and Arnold Berleant.Peterborough: Broadview Press, p.241.费舍尔认为,欣赏者可以自由选择在自然中应该倾听的对象、时间以及方式。他用下面的例子阐明了框架的任意性:
假设你正坐在亚利桑那沙漠中一个城市的热水浴缸里,聆听着周围的声音。你是否只听见西莺歌唱和那穿过果树与棕榈树间的风,抑或是你(应该)也注意到热水浴缸喷口和它喷出的泡泡所发出的愉快的嘶嘶声?你是否会注意到或是忽略换气风机从阁楼旋转出热空气的声音,还有空中偶尔掠过的喷气式飞机的声音?置身于尼亚加拉瀑布,我是否会透过水的持续咆哮声而努力倾听森林中鸟儿的鸣叫呢?在托斯卡纳的乡村,我又是否会忽视蚊子的高声牢骚呢?我应该专注于明尼苏达湖面的潜鸟,还是应该尽力聆听更遥远地方的其他声音?这些声音中是否掺杂着松鼠的叽叽喳喳声和苍蝇的嗡嗡声呢?(19)Ibid., pp.240-241.
以上论述表明,对于自然环境,欣赏者选择的评价单位是任意的,对于环境的任何部分,都有近乎无限可能的框定方式,而这些不同的框架又会产生近乎无限的审美品质。这些无数的任意框架无疑相当于没有框架。费舍尔用框架的任意性解构了自然审美中框架的存在和意义,强调了自然审美拥有艺术欣赏所没有的无框的自由。这与赞格威尔“自然不是没有框架,而是有着无限多框架”的论断有交叉点,但又各自走向了不同的方向。费舍尔认为不同的框定方式会产生不同的审美品质,而赞格威尔认为框架的修正并不会改变自然的“实质审美属性”,前者用无数的框架数量消解了框架的可信度,而后者则强调各种框架的事实存在对感知自然审美属性的意义。
赫伯恩、卡尔松和费舍尔从各自不同的立场质疑了自然审美中的框架,其共同理论指向是框架破坏了对“自然是自然的”“自然是环境的”两个维度的审美体验,产生相对应的两种后果。首先是框架的运用增加了人为的因素,不是对自然作为自然本身进行如其所是的欣赏;其次是框架的存在削平了自然欣赏的立体和深度,将动态三维的自然环境降格为平面二维的风景画。
四 无框自然之有框审美的合理性论证
自然审美中的框架主义者和反框架主义对框架的存在赋予了各自所理解的内容,以此来阐释自己支持的美学理论。框架主义者坚持的是一种带有形式特征欣赏倾向的自然审美,或者一种审美判断中注意力聚焦的必然行为,如果不以某种方式去框定审美对象,那就失去了可以去理解的事物的范围。反框架主义者通常也是反形式主义者,从根本上他们反对的是一种自然欣赏的艺术模式,支持的是对自然参与的、全方面、无框的审美体验,所需要的就是打破所有的框架,来获得一种动态的、参与性的体验。浩瀚无垠的自然确实是无边框的,但是在这个没有框架的整体中,不能否定可以框定自然中的部分从而进行有框审美的审美行为。主流环境美学家对框架问题的彻底批判值得进一步分析。那么,框架在自然审美中究竟是否有其合理的存在,它在审美体验中充当怎样的角色?对这些问题的研究需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交叉思考:(1)对框架扩展内涵的理解;(2)对审美行为和审美判断的理解;(3)对自然整体性的理解。本文认同这样一种观点,即自然作为一种不受人类干预的存在是无框的,但无框自然中存在有框的自然审美,这种审美在很多层面上具有合理性。
首先,自然美语境中的框架是一个十分弹性的概念。它可以是形式的,也可以是非形式的,它的形成可能是自然的,也可以是人有意识或无意识而为的。我们可以过摩尔(Moore)的描述来感受自然欣赏中这种框架概念的弹性:
有一次,我在明尼阿波利斯一个刮着大风的下午出去散步,我发现了一个地方,它周围的建筑物和树木的特殊轮廓把风引入了一个有限的空间中,风在那里不停地旋转。它收集了各种各样的秋叶、小树枝和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把它们卷成一个巨大的、摆动的圈,离地两三英尺,时而上下摆动,时而下坠,但从不放松。闪闪发光的东西沿着环线蜿蜒前进,又绕回来,构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令人愉快的景象。我被它的奇异之美所震撼,于是赶紧跑回去召集一些朋友来分享我的体验。幸运的是,风并没有减弱,那些新奇的旋转的树叶也为他们提供了享受。我们都站在那里看了几分钟,羡慕地笑着,一句话也没说。(20)Ronald Moore, Natural Beauty, Peterborough: Broadview Press 2007, p.119.
摩尔和他的朋友在获得了充分审美体验的同时,并没有意识到他们会把这个可爱的大漩涡看作是在某个想象的框架内构建起来的景色、构图或自然风景,也不会特意关注到这个非形式框架的存在。但是很明显,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某个富有变化、但又或多或少恒定的空间里。在这个空间里,树叶快速而曲折的运动,它们翻滚的颜色如万花筒般地展示,随着不同物体的相互移动,出现了的新图案又立即被其他图案所遮蔽,以及所有这些事物的脉动和节奏等等,这些元素综合在一起形成了美。审美主体只有在把意识局部化到这个框架范围内,才能欣赏到这种自然现象的美。
鉴于上面的例子,需要把框架与限制(limitation)和限度(limit)的关系进行一个重新梳理(21)limitation,limit在英语里都有“限制”的意思。limitation做名词还可以指“局限”,而limit则还有限度、极限的意思。两个词作名词时的语义需要根据语境进行甄别。。一方面,在艺术品中,框架意味着边界和限制,但在自然中它更多地意味着一个注意力的范围或感知的限度。比如当欣赏者想观察的是一片云而不是整个天空,要观察这一棵树而不是另外一棵或者整片树林,是池塘的这部分水域而不是其他部分等,这都是欣赏者选择体验重点的做法,是想从审美角度审视那些吸引注意力的自然事物而已。此时的框架是一种没有限制的聚焦或专注(focus without confinement),是一种审美注意的体现。审美注意的特点是强烈的、专一的、高度集中的感知和思考。从审美心理学的角度看,审美注意作为审美心理过程的开端,是审美活动初始阶段的主要心理因素。审美注意激发了欣赏者对审美客体的期待情感,构成了审美主体的一种特殊的心理定势,即审美态度。这成为即将开始的审美感知觉的前奏。审美注意的基本特征是指向性、集中性与日常意识的中断(22)常存文:《试论审美注意的特征》,《内蒙古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第25-28页.。前两者是指心理活动对一定审美对象的指向和集中,是审美注意最基本的特征。指向性是指选择一定的对象作为心理活动的对象,并将注意力在一定时间内保持在审美对象上,此刻,与审美对象无关的日常活动和意识处于被抑制的状态中。审美注意的指向性与集中性不可分离。审美的指向性必然导向审美的集中性,又通过集中性表现出来。审美注意将主体的心理活动指向并集中于审美客体,使主体的心理在暂时的一段时间内高度集中到审美客体上。审美对象从欣赏者所意识到的广泛的事物中突现出来,并成为心理活动指向的中心。这种聚焦的行为可以有选择地将一些事物放在意识的前景(foreground)中,而把另一些事物放在意识的背景(background)中。在这种有意识的选择性关注行为中,欣赏者一直在非形式地框定和再框定感知的自然对象。如果把框架看作是有限的范围内注意力的集中,那么自然的每一种审美体验都是有框架的。进行审美判断必须利用一种或多种感官密切和持续地注意所观察的一个或多个事物、特征或这些特征的组合。这种需求已经有了框架的内涵。卡罗尔自然欣赏的唤醒模式需要的也是这种注意力的指向性,这是唤醒体验模式的关键因素。卡尔松也承认,这种聚焦框架一直都在发生:“我们将周围的环境体验成一种显眼的前景,使我们对环境的知识能够选择某些具有美学意义的焦点。”(23)Allen Carlson, “Appreciation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37,1978, p.273.无论是科学知识还是想象力引发的审美关注,这种注意力集中下的审美体验是对某个对象、某种品质或对象与品质结合的体验,这些体验此时完全可以与其他背景环境无关。
另一方面,框架与局限(limitation)和限度(limit)的关联体现了自然的整体欣赏与部分欣赏的关系问题。根据赫伯恩的观点,框架之所以不适用于自然,是因为框架中的自然是不完整的。但是再回头看卡尔松的例子,无论是站在小屋外欣赏自然的人,还是坐在屋内透过窗户欣赏风景的人,他所看到的都是巨大自然现象财富中被选中的部分。人类对这个世界的感官接触是有限的,理解或欣赏这个世界的方式也是有限的。这些限制不仅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人类感知世界可理解性的基本条件。一个人走在山间小道上,一边四周观望,一边听着风声,一边闻着高高的松针的清香,一边感受着脸颊上凛冽的寒风。当他继续徒步旅行时,他对所有这些自然审美品质的认识不断地被非形式地框起来,不断重新地选取和再框定,因为如果他的感官体验完全没有框架,那么这种体验将是混乱和不可理解的。从这种意义上说,自然作为一个无框的整体是难以被审美地欣赏的,这取决于我们的认知和感官局限(limitation)。每一种感官的范围都是有限的,无论在欣赏中动用的是视觉、听觉、嗅觉、触觉还是它们的综合,都有其局限性。这种局限,就像许多其他人类的本质局限一样,在人类的审美中自然而然地附着了一种框架。因此,人类只能坚持在自然的某些部分中寻找美和崇高,而不是在一个无限的、不可感知的巨大整体中探索。人类有限的注意力和理解能力,不可避免地限制了我们体验自然现象的能力。作为一个欣赏风云变化的天空或者火山喷发的观察者,选择一个地方驻足凝视这些自然场景,也是自然环境欣赏的恰当行为。即便正确的自然审美方式是积极的、参与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欣赏者必须不断地移动,才能被看作是以适当的方式进行自然审美。除非欣赏者有着上帝般的全能视角,能够把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同时为人类观察者的体验所用,否则就不可能以这种方式欣赏自然整体,更不可能欣赏整体的美。“审美整体论”适用于艺术品,适用于诗歌等文学作品,却未必适用于自然。自然之美无法等同于整体之美,当然,这并不是说在整个自然中没有一个个整体可以被欣赏,只是对自然的审美关注必须是有选择性的。
罗尔斯顿(Rolston)提出,人们认为满是蛆虫的麋鹿尸体具有消极的审美价值,这源于人们对它施加了框架从而将其从大背景中分离出来了。“一定不能在孤立的框架内去看待事物,而应在它所处的环境下去欣赏,并且该环境相应地也会成为我们必须欣赏的更大图景中的一个部分——更确切地说,这并非‘框架’,而是一场戏剧。”(24)Holmes Rolston III, Environmental Ethics: Duties to Values in the Natural World,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239.罗尔斯顿的言下之意是,观察一个自然景物或现象时,欣赏者应将其放在大背景下,无论是空间还是时间背景,然后才能明白它在生命周期这出戏剧里或者生态系统的维持中扮演着什么角色。简而言之,生态系统中的自然景观几乎无一例外在本质上都是美的。然而,齐藤百合子对此持有异议。她认为过于强调整个生态系统,会使得审美对象模糊不清。究竟审美对象是整个生态系统还是单独的个体?如果看似丑陋的部分“仅仅是播放中的电影里一个静止的镜头”“拼图中的一小块”、或者“不断进化的生态系统”这部戏剧中的一个角色,那么审美对象应该是整部电影、整个拼图或者整个生态系统,而不是事物的个体本身(25)Yuriko Saito, “The Aesthetic of Unscenic Nature” in Nature, Aesthetics, and Environmentalism: From Beauty to Duty, Edited by Allen Carlson and Sheila Lintot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p.242.。若是如此,即使我们赞同整体是美的,这也不代表其部分(比如蛆虫)同样具有美感。假设如罗尔斯顿所主张的那样,包含麋鹿尸体和蛆虫的特定生态系统“相应地成为了我们必须欣赏的更大图景中的一部分”,那么欣赏的最终对象也并非仅仅是环绕这些事物的当地环境,而是全球环境。如果我们应当把自然当成大图景来欣赏,那么也就导致了一个违反常理的结论:即人们在欣赏自然时,唯一合理的对象应该是整个宇宙的生态圈。但是从生态的基本原则来说,生态系统之中的人,无法从根本上对宇宙的生态系统拥有全部的认知。生态系统要求对一个最后整体的认识,而这一整体人类无法认知,特别是以西方科学的方式是无法认识的。科学致力于形成的学科“整体”对真正的整体来说仍然是“部分”。坚持生态整体论的贝特森说过:“没有哪一个观察者能够步出一个生态系统,然后高高在上地回头俯视它,以期成就某种对它的统一性的整体面貌。”(26)彼得·哈斯·琼斯:《理解生态美学:贝特森的挑战》.《国外生态美学读本》李庆本主编.长春:长春出版社,2010年,第217—218页。
在欣赏者调动所有的感官探索自然环境时,自然会有一种审美体验。但既然自然审美中部分和整体的关系十分复杂,并不像反框架主义者设想的那样容易表达,因此,不能据此认为这种体验应该抹煞或贬低作为其组成部分的自然元素的体验。没有整体大框架的事实并不意味着不存在使其部分可以被欣赏的框架。我们以赫伯恩的一段论述为例:
假设我正在一片广阔的沙滩和泥地上行走。这一场景的审美品质也许是荒凉的、一种令人愉悦的空旷。但是如果我把知识带入这个场景:这是一个正在退潮的潮汐盆地。这种认识在审美上并非无关紧要。因为我现在把自己看作是在有半天时间是海底的地方行走。一种令人不安的怪异可能会缓和这种荒凉的空旷感。(27)Ronald Hepburn, “Contemporary Aesthetics and the Neglect of Natural Beauty.” In The Aesthetics of Natural Environments.Edited by Allen Carlson and Arnold Berleant.Peterborough: Broadview Press, 2004, p.50.
赞格威尔分析了这个例子,他把其中平坦的沙地和泥地称之为A。这一领域可以被视为更广泛的整体的一部分,这个区域随后要被淹没。这个后面被淹没区域称为B。我们可以单独只考虑A的审美属性和B的审美属性。从整体来看,因为科学认识的介入,A还有其他审美属性,即A+B(令人不安的怪异)。但单个事物的这些属性并不会被更广泛的整体所抹去。这一片泥和沙的确有一种荒凉、愉悦的空旷感,但作为一个更广阔整体的一部分,它也有令人不安的怪异感。它可以既有科学类别指导下的美,也可以有形式属性上的美,既可以有作为环境之中部分的美,也可以有个体本身独立的美,自然事物的天然边界并没有使两种美产生冲突。
我们可以把赫伯恩的例子看作是看待自然部分和整体审美属性有机结合的一般原则。尽管因为单个事物对更广阔的审美整体有所贡献,从而在更广阔的整体中看它们具有审美属性,但它们仍能保持自己作为个体本身的审美特征。自然事物在自然大环境、整体中的审美属性并不会与它作为事物本身独立的审美属性相冲突。正如一个徒步旅行者发现了一朵偶然掉落在她口袋里的花,当她把花拿在手里翻看的时候,她注意到花朵的各个部分奇妙地交织在一起,其颜色的微妙层次,核心部分的坚固,精致的卷须、触感,淡淡的香味。此时她的审美判断,并不需要诉诸花朵的科学类属和自然环境背景。她对美的判断,是由这个事物本身的物理边界所决定的。
基于以上论述,有框审美是自然审美实践中不可避免的,人们在欣赏自然的过程中确实会无意识地进行各种框定行为和框架内的欣赏。在扩大了的新框架概念中,自然审美中的框架与艺术品中的框架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具有较大的抽象性、渗透性和变动性,且已经不拘泥于二维平面的形式。如果框架的真正含义是选择某个审美对象或对象的组合以引起审美注意,那么关于有框自然和无框自然的对立主张就只能被看作是审美选择无尽标尺上的可变标记。要将浩瀚的环境整体中的一块框起来,并不意味着要将选定的部分转化为准艺术作品。在这个标尺的一点上,我们可以选择运用自然科学的适当范畴或者想象力或者参与等方式按其所是地欣赏自然,并把它作为一个个整体,在更大的背景下呈现出来。而在标尺的另一个点上,对自然事物的框定可能形成的是一个难以命名的体验概观,而不仅仅是一处风景或自然肖像。在这种意识的结合中,无论产生了什么样的构成,都不应被认为是种种构成要素的强制结合,而应该是在审美意识聚焦的情况下对其关系的实现。自然的有框审美与环境美学家提倡的环境模式、参与模式等只是揭示了自然美学的不同方面,正如以鉴赏家的眼光审视自然和以孩童般的惊奇观察自然都是自然审美的恰当方式,自然有框审美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其合理性,这为自然美研究打开了另一个思考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