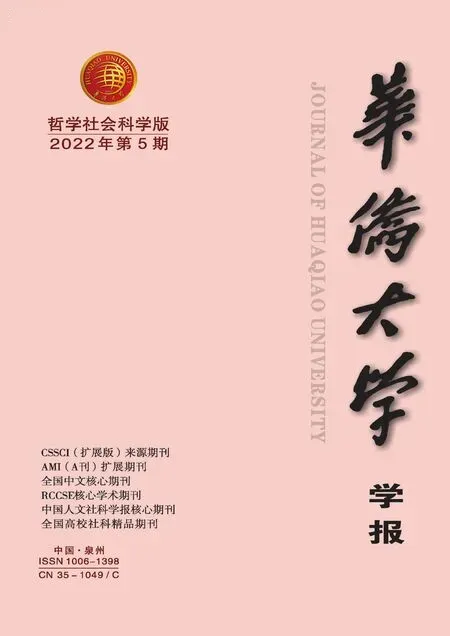沈从文新诗创作流变论
○田文兵 张俊琦
沈从文的小说、散文成就已然得到学界公认,但对其诗歌创作却关注较少。实际上,沈从文的文学生涯始于诗歌创作:“四十年前,最初用笔写作,表示个人情感和愿望,也是从作诗启始的”(1)沈从文:《我怎么就写起小说来》,《沈从文全集(第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03页.。尽管沈从文起初创作的是旧体诗,但他在五四思潮的感召下来到北平后开始白话新诗创作,在《京报·国语周刊》《晨报副刊·诗镌》《新月》《现代评论》《大公报·文艺副刊》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诗歌和诗论文章,在从事编辑工作时也身体力行地扶持和鼓励青年诗人。即便沈从文后期从作家转而专事文物研究,也从未放弃诗歌创作。为何在沈从文创作生涯中极其富有特色的诗歌没能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在诗歌创作和实践上颇有心得的沈从文为何将文学创作重心转向小说和散文?沈从文三四十年代发表的诗歌一反前期明白晓畅风格,诗风渐趋隐晦,是什么原因导致沈从文在诗歌创作的数量和风格上发生如此突兀的变化?如何准确评价沈从文现代时期的诗歌创作?本文将从沈从文诗歌与中国现代诗潮的交互、沈从文与新月派的关系,及其诗风转变等方面考察和探讨沈从文的新诗创作。
一 呼应与探索:新文学语境与沈从文现代诗试验
1920年代初,沈从文离开家乡湘西,只身来到北平。这个时期正值现代新诗从“尝试时期”进入“创作时期”,也是沈从文认为中国新诗成绩最好的时期。(2)沈从文:《我们怎样去读新诗》,《沈从文全集(第1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57页。出于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向往以及现代新诗成就的认可,沈从文自觉地跟随现代新诗潮流,在内容与形式上多维度地探索诗歌创作。
1926—1927年,沈从文陆续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筸人谣曲》和《筸人谣曲选》,这是他托家乡表弟代为搜集的镇筸歌谣,经其整理并作了较详尽的考证和注释。为何沈从文的新诗创作会起始于民间歌谣?时代转折期,新旧文化骤然断裂,各文类均面临破旧立新的问题。中国诗歌的发展道路该将如何?白话口语如何入诗?为打破旧体诗的语言束缚,探索新诗的表达方式,五四知识分子向民间寻求最朴质的情感表达,积极探索现代新诗的民族化路径。1918年2月1日,《北京大学日刊》发表《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向全国征集歌谣,蔡元培发出《校长启示》,邀全体教职员工及学生积极参与歌谣搜集运动,这一天成为“‘中国歌谣学运动’的缘起日。”(3)徐新建:《民歌与国学 民国早期“歌谣运动”的回顾与思考》,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17页.1920年10月26日《晨报副刊》开辟“歌谣”专栏刊载民间歌谣,“不但有详细的注释,还对一些方言词汇进行注音、解释,甚至进行了一些民俗学的考证。”(4)张弢:《传统与现代的激荡:报刊中的“歌谣运动”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30页.沈从文搜集整理湘西民间歌谣的同时,还创作一系列的民歌体诗,这源于他对当时欧化语充斥诗坛现状的不满:“至于最新的什么白话诗呢,那中间似乎又必须要加上‘云雀,夜莺,安琪儿,接吻,搂抱’才行。”(5)沈从文:《乡间的夏(话后之话)》,《沈从文全集(第15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7页.面对新诗创作因袭、虚浮的僵化风气,沈从文决定要做一种新尝试,“若是这尝试还有一条小道可走,大家都来开拓一下,也许寂寞无味的文坛要热闹一点呢。”(6)沈从文:《乡间的夏(话后之话)》,第7页.沈从文之所以对欧化语持如此拒斥态度,一方面固然来自于五四新诗自身的缺陷,然从其心理层面考察,这源于诗人来到都市以后对“乡下人”身份的强烈认同。
沈从文初到北京时,生活穷困潦倒,得到郁达夫、徐志摩等人的帮助,后来经林宰平托梁启超致书熊希龄,在北京香山慈幼院得到图书管理员的职位。在《筸人谣曲》的“前文”中,作者从个人视角叙述了他搜集家乡歌谣的起因。沈从文在香山感到寂寞、无聊,“长住下来,清闲得正如同做和尚模样”(7)沈从文:《筸人谣曲》,《沈从文全集(第15卷)》,第14页.,故乡的民间歌谣时时对他进行声音招魂,沈从文不无眷恋地回望故乡,又对此刻所处的都市发出暗讽:“我想起在我乡下,这样天气,适当挖蕨折包谷的时节,工作的休息里正不知是给了若干年青男女们的娱乐的方便!在这里却连借此来表示两者希望的山歌也不能闻,很是可怪的事。要说这类人是没有这种需要呢?我可不敢相信。”“也许是近于都市的人,都学到了在‘温的接吻’中应守着死样的沉默吧,那可就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事情了。”(8)沈从文:《筸人谣曲》,第17页.此外,他还讽刺都市教授对民间艺术认识的浅薄,与只会吹嘘、喝彩的虚伪。沈从文将自己对都市与乡村的态度写入《筸人谣曲》的“前文”中以作说明,足可见其介绍镇筸歌谣的另一重用心,那便是把这些真诚而不矫饰的歌谣介绍到都市中来。沈从文以歌谣作为媒介,目的在于呈现并向都市中人传播湘西这种自然健康的生命形式、男女大胆真诚的热烈情意,以作为对都市虚伪风气的抵拒,引起都市文化场域内读者的关注与反思。
《乡间的夏》是沈从文所作的第一首民歌体诗,是他对新诗创作方向的一次开拓性尝试。诗歌首节便以都市的夏与乡村的夏作对比开头,彰显他对乡村的怀恋与亲近,这可侧面窥探其创作的心理动机,诗中对乡间自然风景与人事场景的描摹多运用方言词句,《镇筸的歌》更进一步展示出民间语言的讥诮幽默,成为沈从文民歌体诗的鲜明特征。根据作者于诗后所附的“话后之话”中,可以得知这种“新鲜、俏皮、真实”的语言风格与贴近生活、自然朴质的诗意传达在当时诗坛别具一格,令人耳目一新。又如沈从文以镇筸土音改写《诗经》中的《伐檀》而成的《伐檀章今译》,《伐檀》中劳动者对剥削者的讽刺和对现实不公的控诉,在沈从文的改写下显得更加真实平易,增添了一分幽默感:“秧不插,田不耕,哪那捡得这禾线三百根?”诗人以通俗朴实的农家口语讽刺剥削者好吃懒做的习性和生活方式,重章叠句的句式加强了讽刺效果。沈从文亲身证明了那些为旧文人鄙夷的民歌俗语一样可以表达严肃主题,甚至效果可以更生动、更有力。诗人不只是单就语言进行创新,还在形式方面寻求变革,在《还愿——拟楚辞之一》中描绘出家乡酬傩神时的祭祀场面,是骚体与格律体形式的结合体,各节对称,每句由11音节5音步组成,句末押韵,各节换韵,形式严谨,句式均齐,沈从文将骚体与格律体融合为一,体现其在新诗领域的开拓创新精神。沈从文的民歌体诗中,爱情题材最为丰富动人,包括其搜集整理的《筸人谣曲》和《筸人谣曲选》也多属情歌,主题涉及男女对唱歌、诱战歌、单歌、自咏歌、男女分手时节唱的歌等多个方面,呈现出丰富的湘西情歌地理图景。《春》是沈从文自己创作的一首男女对歌长诗。诗中既有沈从文对湘西原始歌谣的直接引用,又有他在原始歌谣基础上融入白话的分解改造,同时又在唱词中运用比喻的修辞手法,体现出诗人丰富的艺术创造。
如果说最初沈从文积极响应歌谣运动是为了掌握并运用白话文来表情达意,那么经由时间沉淀,其白话语言功底已比之前大有进步,他不再依赖方言土语彰显地方特色,而是把民间元素自然融入现代语言文字的使用中,进而连缀诗篇。《黄昏》作为沈从文1932年创作的一首苗族男女分手时对唱的民歌体诗,已无生僻字眼,整体诗风更加清新自然。沈从文对于民间歌谣的搜集整理与创作是其自觉融入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一种方式。初入文坛的民歌经验对沈从文个人也影响深远,锻炼了其对白话工具的熟练运用,为其文学创作确立自身特色、走向成熟奠定基础。沈从文借民间歌谣书写湘西优美、健康、自然、真诚的生命形式,一定程度上对都市男女异化的情感和虚伪的社会风气起反拨作用。
民间歌谣为沈从文进入新诗创作提供了学习和借鉴的体式,而五四时期的现实主义诗潮是其创作大量现实题材诗作的思想资源。1922年,文学研究会创立了中国新文学史上的第一个新诗专刊《诗》,将胡适等五四新诗开拓者所提倡的“写实主义”(9)茅盾在《论初期白话诗》中说,早期新诗“最一贯而坚定的方向是写实主义”,概括了从《新青年》到文学研究会的诗歌创作的主要精神。创作方法进一步深化,形成诗歌中的为“人生派”,直面现实的黑暗与残酷,他们同情底层人民被压迫与剥削的处境,以诗鼓动人民奋起反抗。沈从文仍在家乡之际,便想要以诗来表达对丑恶现实的不满,在《我怎么就写起小说来》中表示他厌恶部队吸食鸦片、秩序混乱的环境,但是由于“年龄又还不成熟到能够显明讽刺诅咒所处社会环境中,十分可恶可怕的残忍、腐败、堕落、愚蠢的人和事,生活情况更不能正面触及眼面前一堆实际问题。”“写诗主要可说,只是处理个人一种青年朦胧期待发展的混乱感情。常觉得大家这么过日子下去,究竟为的是什么?实在难于理解。难道辛亥革命就是这么的革下去?”(10)沈从文:《我怎么就写起小说来》,《沈从文全集(第12卷)》,第408页.沈从文自身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忧虑,与五四时期的现实主义诗潮遥相呼应,创作出众多现实题材诗作,如《旧约集句——引经据典谈时事》由《圣经》中的章句组合而成,目的在于抨击北京女师大风潮中的教育界人士,抨击教育制度的腐朽,赞扬学生的爱国行为;《失路的小羔羊》以儿童视角、独白体形式,对人与人之间隔膜、虚伪的交往关系发出质疑与反思;《到坟墓去》中,诗人把假革命者和凑热闹的看客比作“蛆虫”加以讽刺,表达他对五卅惨案的悲愤之情;《到坟墓的路》《余烬》则以“小诗体”形式,讽刺人性的虚伪、谄媚、与趋炎附势等问题,希望生命可以回归自然、真实与纯粹。
与此同时,顺应了五四狂飙突进时代精神的浪漫主义诗风,尤其是注重个性解放与表现自我,与沈从文的内倾型性格产生化合反应,激励着他勇敢向内挖掘、表达自我,如《希望》《悔》《爱》等对情爱的向往与对自我个性的歌颂,“我将用诅咒代替了我的谦卑,诅咒中世界一切皆成丑老!我将披发赤足而狂歌,放棹乎沅湘觅纫佩之香草”。五四时期破旧立新、向往自由与光明的情感呼之欲出,不乏郭沫若《女神》般大胆而狂放的色彩。然而,“浪漫主义与感伤主义如一对孪生姐妹,相亲相近,尤其在‘五四’落潮以后更为明显”(11)龙泉明:《中国新诗流变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101页.。沈从文出于对国家前途命运的迷惘与自身的情感压抑,也难免陷入到这种感伤主义的窠臼当中,如《春月》既未脱旧体诗词的痕迹,情感上又带有一种无名的悲哀;《痕迹》反复重复“石上的淡淡悲哀痕迹泯灭了”一句,使得全诗呈现出一股浓烈的感伤色彩;《其人其夜》更是陷入一种顾影自怜、自哀自叹的消极情绪之中,似为情而伤,情感较无节制。除此之外,沈从文还受到1920年代中期的象征主义诗潮影响,如《囚人》:“报时大钟,染遍了朋友之痛苦与哀愁,/使心战栗,如寒夜之荒鸡,/捉回既忘之梦。”诗歌在欧化句式、节奏韵律上与李金发《弃妇》有相似之处,模仿迹象明显。
然而,沈从文与中国现代诗潮的呼应并非是其随波逐流的表现,而是“情绪的体操”,是一种“扭曲文字试验它的韧性,重摔文字试验它的硬性”(12)沈从文:《情绪的体操》,《沈从文全集(第1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16页。的体操,最终目标指向于学习借鉴,在大量试笔的基础上不断提升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与文学创作水平,以更好地表情达意,形成独具特色的诗学理念与新诗作品。
二 诗艺与诗意的交融:沈从文新月派诗人身份的探讨
沈从文的京派文人身份成为学界共识,但其与新月派的关系存在较大的争议。划分作家的派别归属,主要由其创作所展示出来的特点来判断,作家的交往以及接受的影响也是重要依据。“尽管作家写作时并不想到他要当什么派,但他的审美趣味、他的文艺观点、他过去接触的作家、作品、思潮、流派的影响,无形中还是会支配着他,使他写出可能接近于这派或那派的作品。”(13)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增订本)》,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沈从文新诗创作(包括民歌体诗)大致有50余首,近半数都发表在新月派刊物《晨报副刊》或《新月》上。诗论方面,沈从文在《职业与事业》《致灼人先生二函》等文中均鼓励青年多向徐志摩、闻一多、朱湘、陈梦家等新月派诗人学习,可见沈从文与新月派关系之密切。
1925年,沈从文与林宰平等新月派诗人相识,在《谈朗诵诗》中,作者自述林宰平介绍他认识徐志摩的场景,“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天真纯厚才气横溢作家时,是在北平松树胡同新月社的院子里,他就很有兴致当着客人面前读他的新作。”(14)沈从文:《谈朗诵诗》,《沈从文全集(第17卷)》,第244页。沈从文于《回忆徐志摩先生》中更表示“和他第一次见面,就听到他天真烂漫自得其乐,为我朗诵他在夜里写的两首新诗开始,就同一个多年熟人一样”(15)沈从文:《回忆徐志摩先生》,《沈从文全集(第2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36页。,直陈“年纪最轻,帮助最多,理解最深,应数徐志摩先生。”(16)沈从文:《回忆徐志摩先生》,第434页。徐志摩在主编《晨报副刊》期间,大量刊载沈从文的小说、散文、诗歌作品,使得初登文坛的沈从文能够以写作赚取稿费、维持生计。此外,沈从文于1930年相继在中国公学与武汉大学任教,主要讲授以新诗发展为内容的新文学课程,其讲义中多数是对徐志摩、闻一多、朱湘这些新月派诗人诗歌的讲述与赞赏。可见,作者从初入文坛,到1930年代成名之期,都与新月社紧密联系在一起。
徐志摩对沈从文的发现与提携可谓影响了其一生的命运轨迹,在《习作选集代序》中,他对胡适、林宰平、郁达夫等人对他的鼓励与帮助表示感谢,尤为感激徐志摩,表示“没有他,我这时节也许照《自传》上说到的那两条路选了较方便的一条。”(17)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全集(第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7页。沈从文从徐志摩那里“接了一个火”,告诉读者“你得到的温暖原是他的”(18)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第7页。,认为纪念徐志摩唯一的方法,便是“应当扩大我们个人的人格,对世界多一分宽容,多一分爱。”(19)沈从文:《三年前的十一月二十二日》,《沈从文全集(第12卷),第203页。沈从文何来如此感受?首先,徐志摩对世界“宽容”与“爱”的品质影响着沈从文的行为方式,沈从文对后辈多有提携,力所能及地帮助、扶持青年的文学事业,并为他们提供创作指导与发表渠道。其次,徐志摩的文章对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理念影响颇深,“第一次见到徐志摩先生,是我读过他不少散文,觉得给我崭新深刻动人印象,也正是我自己开始学习用笔时。就不知道不觉受到一种鼓舞,以为文章必须这么写。”(20)沈从文:《回忆徐志摩先生》,第436页。徐志摩执着地追寻“从性灵深处来的诗句”(21)陈从周:《徐志摩年谱》,上海:上海书店,1981年,第70—71页。,“在诗里真诚地表现内心深处真实的情感与独特的个性,并外射于客观物象,追求主、客体内在神韵及外在形态之间的契合”(22)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第117页。,而这也正是沈从文于诗歌中所要追寻的艺术境界。如《颂》以一系列客观物象表达诗人内心对爱的赞颂与渴求,在视觉与嗅觉上将情人之于他的感觉以自然意象化之,尤其是最后一节:“你是一株柳;有风时是动,无风时是动:但在大风摇你撼你一阵过后,你再也不能动了。我思量永远是风,是你的风。”其中叠词叠句的运用,使音节自然和谐,将情人比作“柳”,将“我”比作“风”,风与柳永远相知相伴,表达出诗人对爱人的脉脉情意,整首诗歌与徐志摩的诗风极为相似。
沈从文在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教授“各体文习作”课程时,作《从徐志摩的作品学习“抒情”》一文,认为“徐志摩作品给我们感觉是‘动’,文字的动,情感的动,活泼而轻盈”(23)沈从文:《从徐志摩作品学习“抒情”》,《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258页。,他的文字“清而新,能凝眸动静光色,写下来即令人得到一种柔美印象。”(24)沈从文:《从徐志摩作品学习“抒情”》,第254页。沈从文的不少诗歌受到了徐志摩“飞动飘逸”“自然清新”诗风潜移默化的影响。如爱情诗《悔》:生着气样匆匆的走了,这是我的过错吧。旗杆上的旗帜,为风激动;飏于天空,那是风的过错。只请你原谅这风并不是有意!”文字轻巧灵动,天真活泼,自然清新,具有青春的活力。徐志摩认为,“一首诗的字句是身体的外形,音节是血脉,‘诗感’或原动的诗意是心脏的跳动,有它才有血脉的流转。”(25)徐志摩:《诗刊放假》,《徐志摩研究资料》,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72—173页。徐志摩的诗歌总是在自由的形式中寻求内在的法度,而综观沈从文的新诗,大多也都是不受严谨格律所缚,自由中带有法度、自然流淌诗意的诗作。于是,陈梦家在《新月诗选·序言》中这样评论沈从文的新诗:“我希望读者看过了格律谨严的诗以后,对此另具一风格近于散文句法的诗,细细赏玩它精巧的想象。”(26)陈梦家编:《新月诗选》,上海:新月书店,1931年,第29页。显然,在诗歌形式方面,沈从文更认可徐志摩的观点,虽讲求格律但却少刻意雕琢的痕迹,而是致力于追求诗艺与诗意的自然浑融。
新月诗派主张“本质的醇正”与“格律的谨严”的诗风,而最能直观反映沈从文受其新诗格律化理论影响的诗作是《梦》,这是他对闻一多所提出的诗歌“三美”理论的直接实践:
我梦到手足残缺是具尸骸,
不知是何人将我如此谋害!
人把我用粗麻绳子吊着顶,
挂到株老桑树上摇摇荡荡。
仰面向天我脸是蓝灰颜色,
口鼻流白汁又流紫黑污血;
岩鹰啄我的背膊见了筋骨,
垂涎的野狗向我假装啼哭。
全诗共分为两节,每节四行,形式严整,句式整齐,具有建筑美;每句由11音节5音步组成,句末押韵,2句一换韵,具有音乐美;“蓝灰颜色”“紫黑污血”,具有绘画美。诗作以“梦”为题,梦中是一个颓废腐败的世界,这个灰暗的梦象征着沈从文对现实的认知,人与人之间相互残杀、利用,“我”备受黑暗现实的摧残,小人横行于世,整个世界呈现出一片绝望、颓败、残酷的画面。这首诗创作于1926年4月8日,也可以理解为沈从文对段祺瑞政府制造“三一八惨案”的愤懑回应,满含作者的爱国主义之情。受新月派影响,沈从文开始在诗歌创作中有意识地讲求韵律形式规范,寻求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诗艺与诗意的融合,进而生发出自我特色,形成其个性诗风——“象征性”“泥土气息”与“湘楚风味”。
《“狒狒”的悲哀》全诗共8节,每节4行,形式严整均齐,句末押韵,两句一换韵,作者以狒狒的经历象征诗人对民族健壮的渴望,富有新意。《云曲》全诗共2节,各节对称,化用楚词体,形式上具有湘楚地域特色,诗中通过对“云”自然形态的书写,象征诗人心中的理想生命状态,“爱月而不遮月,近山而不倚山”有与舒婷《致橡树》相似的情感价值导向,即对自由独立之人格的倡导,沈从文在古典与现代双重形式的化用中,运用自然意象,赋予其现代象征义,极具创新性。此外,沈从文善于以平白朴实的语言意象表情达意,在《一首诗的讨论》中,认为现代抒情诗应当“充满土气息,泥滋味”,“对农村原有的素朴和平具有深刻诚挚的爱”(27)沈从文:《一首诗的讨论》,《沈从文全集(第17卷)》,第461页。,这种诗观可谓贯穿其创作始终,是其新诗最鲜明的特征。如《月光下》全诗共8节,每节4行,各节基本对称,句末押韵,两句一换韵,以“水车”“猪”“老枭”“田坎”“蛙”“村砦”“狗”“蚱蜢”“鸬鹚”等田园意象连缀诗篇,引用原始歌谣,具有乡间泥土气息。月光象征希望,“我”追逐月光便象征诗人对希望和理想之境的追求与对心中理想信念的坚守。《薄暮》分两节,各节对称,句末基本押韵,以自然意象书写苗乡薄暮场景。诗人将薄暮的天空比作农家“绸子”,将月亮比作农家剪纸剪成的“亮圆”(苗语月),蕴含地方色彩。《觑—瞟》具有湘楚大地孕育下的浪漫主义气息,诗分4节,各节基本对称,交错押韵,各节换韵,形式严整而富于变化。诗人对情人的眼睛进行特写,“莫让星儿独擅其狡猾,汝亦有此闪忽不定之聪明。荷面上水珠不可捉拿,你眼睛比那事物更活更灵!”诗歌同样以以自然意象作比,表现情人双眼的光亮、润泽与神气,诗人沦陷在情人的眼神当中,在对视中二人两心相知。最后一节,沈从文运用通感手法,将这“觑—瞟”的眼神魅力比作“音乐魔力”和“柠檬汁鲜味”,化虚为实,富有新意与感染力。
新月派“戴着镣铐跳舞”的格律倡导不只影响着沈从文同时期的诗歌创作,甚至影响了他20世纪30—40年代的诗学观,其诗论文章多次强调语言形式与韵律节奏的重要性,如沈从文在《新诗的旧账——并介绍诗刊》强调“新诗在辞藻形式上不可偏废”(28)沈从文:《新诗的旧账—并介绍诗刊》,《沈从文全集(第17卷)》,第96页。,诗歌韵律、辞藻、形式有其存在价值;在《谈朗诵诗》中认为,即便是朗诵诗,其文字处理也不可极端自由,否则将会无从朗诵,认为真正便于朗诵的,是诗形“‘带了些脚镣手梏’的。如徐志摩、闻一多、朱湘”(29)沈从文:《谈朗诵诗》,第239页。等人的作品;在《致今是先生》中强调“诗应当是一种比较精选的语言文字,在有限制的方式上加以处理的艺术”(30)沈从文:《致今是先生》,《沈从文全集(第17卷)》,第453页。;在《谈现代诗》中更是直接夸赞新月派诗人“把格律提出作为欣赏的尺标”(31)沈从文:《谈现代诗》,《沈从文全集(第17卷)》,第477页。可以作为一个共通标准,以建立起读者与诗人之间有效联结。
从诗歌本体观出发,新月派除了对新诗格律化运动的倡导,还提倡“理性节制情感”的诗学主张,反对情感的无节制流露,这一观点也影响了沈从文的诗歌创作理念,他在《给一个写诗的》中强调写诗“应当极力避去文字表面的热情”(32)沈从文:《给一个写诗的》,《沈从文全集(第17卷)》,第186页。,不能把写诗当成一种“感情排泄的痛快。”(33)沈从文:《给一个写诗的》,第184页。新月派对此的实践方式之一便是进行新诗的小说化、戏剧化,沈从文《叛兵》《“狒狒”的悲哀》《曙》《絮絮》等诗作是他学习新月派新诗戏剧化理论的自觉尝试。
新诗戏剧旁白体,如《叛兵》描绘出一幅行刑场面,人物涉及法官、被行刑的少年、观众、刽子手;同时融入场面描写,黄土坡的凄凉、悲壮的歌声、群众的和鸣、病叶的零落;再加上戏剧表演中的唱和词,营造出一派悲壮的行刑画面,表现出沈从文对芸芸众生的悲悯;又如《“狒狒”的悲哀》将戏剧化与格律化融为一体,全诗共分8节,每节4句,句末基本押韵,两句一换韵。这首诗透过对狒狒心理的描写,表达诗人对民族摆脱羸弱、重新健壮起来的渴望。新诗戏剧独白体,如《曙》运用男子第一人称的独白形式,讽刺都市现代绅士小姐因金钱利益的需要而结合的虚伪,赞美妓女的纯粹与真诚;又如《疯妇之歌》,以第一人称“我”讽刺“小姐、奶奶和太太”等贵族家庭天生就拥有特权,对社会的不平等现状发出强烈控诉,在“我”的反讽中彰显作者的情感倾向;《絮絮》则运用女子第一人称独白体的形式,“我”是妓女身份,对男子吐露自己身不由己的娼妓生涯、生不如死的生命状态,和对真诚爱恋的渴望,极力表现妓女的善良。正是因为对上海文人“写‘性史’、无病呻吟、枪炮加女人之类作品的不屑”(34)吴世勇:《沈从文年谱》,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3页。,沈从文以一位渴望爱情的妓女入诗,用诗歌来讽刺都市上层社会的不平等以及都市男女虚伪情爱,开启其以自然生命状态审视现代都市病的乡土叙事先声。
沈从文的新诗创作得到徐志摩、陈梦家等新月派诗人的肯定,陈梦家于1931年出版的《新月诗选》中收录沈从文新诗多达7首,数量上仅次于徐志摩,排名第二,超越闻一多、朱湘等被历史所公认的新月派诗人。陈梦家评论沈从文诗歌“极近于法兰西的风趣,朴质无华的辞藻写出最动人的情调。”“所惜他许多写苗人的情歌,一时无法尽量搜寻,是我最大的遗憾。”(35)陈梦家编:《新月诗选》,第29页。由此可见,即便沈从文的新月派诗人身份颇有争议,但毫无疑义的是,沈从文的诗歌创作艺术已具有较高水平,在1930年代的中国诗坛占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位置。
三 历史振荡与心灵沉潜:沈从文诗歌沉寂与诗风转变
1930年代以后,沈从文仅有十余首新诗发表,数量与20年代相比大幅减少。其由何自?其一,沈从文的诗歌创作理念无法满足中国当时的抗日救亡需求。随着抗日战争的打响,民族救亡运动高涨,诗歌的政治宣传功用被无限放大,新诗标语化盛行。然而,沈从文却对诗歌的这一发展趋向持警醒态度,在《谈朗诵诗》中否定了当前多是以革命为题材的口号诗做法。其二,192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白话新诗的探索阶段,五四先驱者们积极探寻新诗的表达与形式规范,诗学理论层出不穷,加之沈从文自身对诗歌的兴趣,共同推动着作者学习与创作的欲望。1930年代后,新诗创作规范渐趋成熟,但沈从文却对自己的诗歌写作并无信心,内含一种自卑心理,他在1931年11月13日致徐志摩的信中说:“你怎么吿陈梦家去选我那些诗?我不想作诗人,也不能作诗人,如今一来,倒有点难为情。一看到《诗选》我十分害羞。”(36)沈从文:《致徐志摩》,《沈从文全集(第18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48页。沈从文大多只是将诗歌作为个人的兴趣爱好,并非是其文学事业的重心所在。与此同时,这一时期沈从文的小说、散文创作也进入成熟期,《边城》《湘行散记》《从文自传》等作品的成功给他的文学之路带来信心,作家成名后大多也会将重心放在带给他声名的体裁上,因此诗歌创作渐趋沉寂。另外,沈从文既担任大学老师,又主编《益世报·文学周刊》《大公报·星期文艺》等刊物,忙碌芜杂的事务也是其诗歌创作数量骤减的原因之一。
更重要的是,沈从文对于诗歌与小说的不同功能定位,成为他这一时期将精力放在小说而非诗歌的主要因素。沈从文于1931年发表的《窄而霉闲话》反映了作者这一时期的文学观念。沈从文反对当时文坛迎合商业的做法,指责那些“玩”文学,将文学当作“玩具”的人,反对“白相文学的态度”(37)沈从文:《窄而霉斋闲话》,《沈从文全集(第17卷)》,第40页。。因此,他提倡“文学的功利主义”,“这功利指的是可以使我们软弱的变成健康,坏的变好,不美的变美”(38)沈从文:《窄而霉斋闲话》,第40页。,即着眼于文学对民族品德建设的有益方面,认为这较之那些“在朦胡里唱唱迷人的情歌,功利也仍然还有些功利的好处。”(39)沈从文:《窄而霉斋闲话》,第40页。同时作者表示,这种“注重文学的功利主义,却并不混合到商人市侩赚钱蚀本的纠纷里去”(40)沈从文:《窄而霉斋闲话》,第41页。的希望,应由“创作小说来实现”(41)沈从文:《窄而霉斋闲话》,第40页。,“事实上这里的责任,诗人原是不大适宜于担任的。一个唯美诗人,能懂得美就很不容易了,一个进步的诗人,能使用简单的字,画出一些欲望的轮廓,也就很费事了。”(42)沈从文:《窄而霉斋闲话》,第41页。诗歌难以有效地表达出自己的“事功”想法,小说才可以担任这个角色。联系1930年代沈从文的个人活动,我们可以看到,沈从文不再仅仅局限于埋头创作,而是发表大量议论文章,如1932年在《上海作家》一文中提倡一种新的人生观,“力避衰弱无力的牢骚,小巧无聊的杂感,以及那种上海趣味最坏的一种造谣风气。”“应当奖励征求能使国民性增加强悍结实的一切文学作品。”(43)沈从文:《上海作家》,《沈从文全集(第17卷)》,第44页。1933年发表《文学者的态度》告诫作者要“诚实”的去做,不造谣、不说谎,不投机取巧。1934年凭《论海派》一文更是挑起了“京派”与“海派”的论争,痛斥海派文学是“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的结合,是投机取巧,见风使舵的代表。较之1920年代,沈从文对文坛局势关心更甚,随着作者社会责任感日益趋重,诗歌这种更着重于抒发心灵之声的体裁便被沈从文置于边缘位置。
然而,创作数量的降低并不代表诗人创作才气的枯竭,经过沉淀,沈从文的诗艺更趋圆熟,诗风经历了由明白晓畅的具象抒情到形而上的抽象哲思的变化,其背后有多重因素影响。首先,沈从文1920年代的诗歌创作便已初具象征意味,1930年代,他对象征手法的应用更加娴熟,意象与象征义之间的联系不再明晰,意义趋于抽象。其次,沈从文语言文字运用能力的提升与诗学观的成型影响着其诗风变化。1929年沈从文在中国公学的教书经历成为其语言文字进步的重要阶段,“学习过程中有个比较成熟期,也是这个时候。写作一故事和思想意识有计划结合,从这时方启始。”(44)沈从文:《总结·传记部分》,《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85页。整体而言,沈从文20世纪30—40年代的诗歌语言更趋精炼隽永。另一方面,沈从文在中国公学教授新文学课程的经历,促进了他对新诗理论的总结与认识,独立诗学观的成型是影响他诗风变迁的重要一环。1930年代初,沈从文在《给一个写诗的》中,提醒诗人在语言上要组织,劝诫他莫要“随便”写诗,“应当节制精力,蓄养锐气,谨慎认真的写”(45)沈从文:《给一个写诗的》,《沈从文全集(第17卷)》,第184页。,1940年代在《谈现代诗》《致今是先生》等文章中更是反复强调同一观点,“诗其所以成为诗,必出于精选的语言,作经济有效的处理”(46)沈从文:《谈现代诗》,《沈从文全集(第17卷)》,第476页。,要“以约见著,能于少分量文字中解释并表现发生较深较持久的效果”(47)沈从文:《致今是先生》,《沈从文全集(第17卷)》,第453页。,由此反观其1920年代的部分诗歌创作,便会发现其用词用语的野性和自由无拘,与诗歌感情的坦白、直露。如果说,沈从文1920年代的诗歌创作,其试验与探索的成分更多,那么1930年代以后,他便是在其已然成熟的诗学观指引下进行的艺术创造。
沈从文所处的现实境遇与历史环境也是影响其诗风变迁的重要因素。1930年代,国家局势动荡,战争的残酷与现实的挫折把他引向对人类命运、生命意义等问题的形而上思索。如《北京》,诗人对人类的生存状态作形而上思考。恢弘壮阔的北京城背后,是千万劳动人民“血与泪”般的生存。诗人对上层阶级与底层人民的生活作对比,关心平民的生存状态,“谁派王回回作羊屠户,/居庸关每年跑进五十万肥羊,/给市民添一分暖和,添一分腥?”这份思索贯穿古今,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杜甫隔空对话,体现出沈从文的现实关怀。但这首诗已与其1920年代创作的现实讽刺诗不同,时空意识更为博大,抽象意味初显。《时与空》中,诗人借爱在四季的孕育、滋长、成熟与枯萎,表达美不可追逝的迷惘,正如诗题:“—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时间自然流逝,不受人为控制,诗人表露出一种虚无主义心境:“思量从虚无证实自己生命存在”,题目中的“空”不是指代“空间”,而是意为“虚空”“虚无”,时间的虚无意味着人存在的无意义,人的存在就是虚无的,而与此诗仅相隔12天所作的《忧郁的欣赏》更可见诗人的消极情绪,海鸥虽最终总是面临被海水吞噬的结局,但它却永远会不离开大海,“忧郁和它一样/从不会由我心上挪开。/一千个日子里,/忧郁的残骸沉积在我的心上”,正如海鸥与海的永恒相伴,忧郁与诗人也是连体共生。
进入1940年代,沈从文诗歌的抽象性更进一步,这一方面是由于作者当时身处西南联大,受校园内现代主义诗风环境的熏染,然内在因素是,这一时期,沈从文屡屡受到文坛攻击,作者时常陷入自我怀疑与自我解剖之中。几乎从1935年前后,沈从文的“关注中心从个人的文学事业扩大到他置身其中的新文学的命运和前途,更推至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和前途。”(48)张新颖:《沈从文的前半生》,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第172—173页。几年间,沈从文大量抒发自己对文学、文坛、政治的看法,如《论读经》反对国家倒退的愚行;《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反对文学趋从于政治的文学创作倾向;在《一般或特殊》中提出自己的文艺观,却被文坛评为“与抗战无关论”。沈从文越挫越勇,继续发表《文运的重建》和《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等文,反对文学的商品化和政治化。沈从文尽管屡屡被攻击、污蔑、批判所包围,但他对文学独立性的坚持却未曾改变,固执抒发着他的文艺见解。尽管沈从文深知自己的文艺观在举国抗战的背景中大都无法被认可,但他为何仍要固执发声?从其《莲花》中可窥见一二,沈从文不愿像猪耳莲一般沉默,“我也应当沉默?/不,我想呼喊,想大声呼号。我在爱中,我需要爱。”他想要大声呼号,希望自己的呼号可以得到时人的认可。然而,诗人也知这只是妄念而已,“火熄了,剩一堆灰。/妄念和幻想消失时/并灰烬也无剩余。”诗人借莲自剖心境后,又陷入绝望之中。《看虹》一诗有与之相似的意蕴传达,思维的复杂化与线团化与中国新诗派的诗风趋近,这首诗运用对白体的形式,以“希望”的生成、破碎三重回旋结构组合诗篇。“希望”的象征物不断变化,虹上有梦,然而梦掉落;“我”索要星子照亮荆棘的路,却被对话者拒绝;“我”需要“一点孤单,一点静,在静中生长,一点狠”,然而“我”又自我否定,“又像什么都不需要,因为/有一片坪芜在眼中青”,再次否定了希望存在的可能性。诗人在对希望的肯定/否定、肯定/否定、再肯定/再否定之间纠结、徘徊,表现出沈从文对希望存在的渴望,与对希望只是一种幻梦的现实认知的绝望。
1940年代初,沈从文已渐渐堕入消沉与虚无,而经由周遭环境的进一步恶化,精神危机在1949年达致顶点。1948年,冯乃超在《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一文中,将沈从文的文章视为“今天中国典型地主阶级的文艺,也是最反动的文艺。”(49)吴世勇:《沈从文年谱》,第296页。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将沈从文视为“存心要做一个摩登文素臣”的“桃红色”作家。”(50)吴世勇.《沈从文年谱》,第297页。北大校园甚至出现学生用大字报转抄的《斥反动文艺》,教学楼挂出“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51)吴世勇.《沈从文年谱》,第308页。的大幅标语,学生的背叛使沈从文的精神彻底陷入紊乱当中,“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52)沈从文:《题<绿魇>文旁》,《沈从文全集(第14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56页。沈从文自觉不被新政权接纳,作品也将被全部否定,这对其是致命打击。《乐章》中的三首诗反映了沈从文这一时期的精神状态:从《第二乐章—第三乐章》中“我在搜寻丧失了的我”的迷茫、孤独与愤怒,到《从悲多汾乐曲所得》中,在音乐的帮助下正常理性得以回复,心“很真实贴近了地面”的个体,再到《黄昏与午夜》中经由生命回溯而生发积极生活渴望,作者终于确立了自己生命得以存在的支点,那便是在“融群”中为祖国散发生命的余热。沈从文在对个体存在的反思中确立起未来的人生走向,“我”逐渐让位于“群”,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在最后一首新诗《黄昏与午夜》后也进入停滞期,全身心地投入到文物研究工作当中。沈从文1930年代以后的诗歌创作可以看作其心灵之声的私语,对于了解其这一历史时期的精神变化轨迹有无法替代的参考价值,是考察沈从文后半生事业转向的重要研究材料。
四 结 语
当然,沈从文的新诗创作并非是对中国现代诗潮的亦步亦趋,也不仅仅只是一种“情绪的体操”而已,而是在于探索新诗表达方式,寻求形式与内容的融洽,以更好地表情达意。沈从文1920年代基于乡土伦理背景的写作方式,与五四时期基于人道主义和启蒙姿态的现代诗人的美学观点相比别具一格。在以启蒙为创作旨归的时代,诗人极力赞美乡村的民风民俗,以妓女入诗描写其内心独白的新诗创作实践独具特色。沈从文与新月派中人交往甚密,在诗学观与诗歌创作上受其影响颇深,在形式的规范中自然融有其个性特征,成为新月派的代表诗人之一。20世纪30—40年代,在诗学观的成熟、历史环境的变迁、语言驾驭能力的提高等多重因素影响下,沈从文诗风转向抽象,诗歌创作渐趋沉寂。但沈从文所发表的大量诗论文章,以历史的、发展的、比较的眼光考察新诗发展演变,在评价诗人风格的同时表达自己的诗学理念,对中国新诗发展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其主编《大公报·星期文艺》期间,发表了中国新诗派成员的作品多达40余篇,可见其独具慧眼。正如沈从文对诗的理解“诗应当是一种情绪和思想的综合,一种出于思想情绪重铸重范原则的表现。容许大而对宇宙人生重作解释,小而对个人哀乐留个记号,外物大小不一,价值不一,而于诗则为一。”(53)沈从文:《致灼人先生二函》,《沈从文全集(第17卷)》,第436页。沈从文的诗歌及其诗学理论是研究其小说和散文的对举互证、互为补充的材料,也为探讨沈从文创作美学观的形成提供了另一种研究视角和重要参考,然而各类现代文学史论著却忽视了沈从文的诗人身份,其诗歌成就也仍处于被遮蔽状态,显然难以全面认识和评价沈从文的文学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