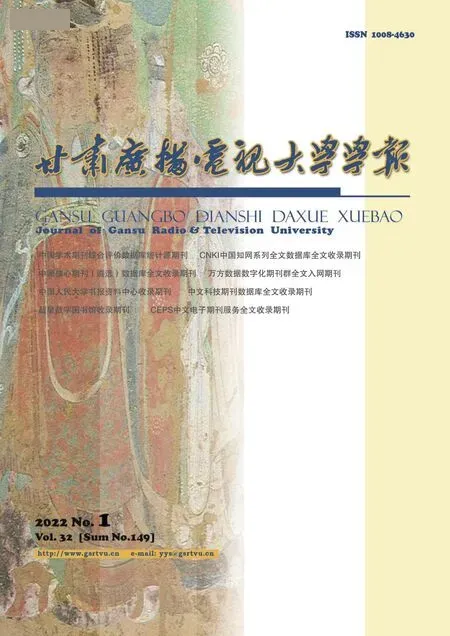渐进式政治发展模式的人性基础探微
叶长茂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政法系,广东 广州 510303)
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各国政治发展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激进式,一种是渐进式,其他政治发展模式要么是二者结合,要么是其变种。激进式政治发展可以推动社会进步,但往往需要付出比较大的代价。选择渐进式政治发展模式的国家虽然进步缓慢,却能通过长期的制度改进以较小成本取得突出成就。在近代顽固的专制势力比较强大的时候,选择激进式政治发展模式有其合理性,激进式政治发展所追求的理想、价值及所取得的成就是不能否定的,但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人类主旋律的时代,在人民主权已得到宪法确认的国家,渐进式政治发展模式显然是一种更优的选择。渐进式政治发展之所以能持续推动人类进步,是因为其植根于人类的本性。深入探讨渐进式政治发展模式的人性基础,有助于后发展国家的精英与民众树立渐进主义信念,自觉选择通过和平、协商、非暴力方式推动政治进步。
一、人性发展的两种可能性
人的自然本性不适合用善、恶来评价,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已指出,人的潜能是自然生成的,美德和邪恶不是人的潜能,“我们不能说一个人天生是善的或恶的”[1]。善、恶不是人性固有的本质,只是人性中潜在的倾向[2]。人们一般所说的善、恶是用特定的社会道德标准对人的行为所作的价值判断。
人的基本特性可以概括为道德上中立的自利性,也就是人所共有的趋利避害的自然天性。政治思想史上关于人的自利特性有许多深刻的论述。休谟指出,在自然性情方面,每个人爱自己都会超过爱其他任何一个人,所以我们应当认为自私在其中是最重大的[3]527-528。没有一种激情是能够完全无私的,即使是最慷慨的友谊,也只是自爱的另一种形式[4]。斯密也认为:“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每个人更加深切地关心同自己直接有关的、而不是对任何其他人有关的事情。”[5]101-102马克思主义人性论承认人既是一定社会关系中的社会存在物,也是一种具有物质利益需求的“自然存在物”[6]。人追求利益的天性来源于人的动物性本能。恩格斯指出:“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7]人要在自然界和社会中生活与发展,首先必须努力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就像马克思所说:“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8]生存理所当然是人类的第一需要,所以人的行为取向自然倾向于自我保存,逃避危险,追求能够满足自身需要的利益、荣誉和权力。
自利是人的自然本性,人先天具有的这种自利倾向不能用善恶来进行评价。人的自利行为只要不伤害他人及公共利益,便是正当的。人性发展实际上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向善,一种是作恶。一个人向善还是作恶,关键取决于外在的制度环境。人的行为是个体选择与制度环境互动的产物。外在的制度环境如果崇善抑恶,大多数人就会成为良善的公民。外在的制度环境如果不能保护善良,惩罚恶行,即使有少数人选择行善,但大多数人只能变成苟且冷漠的小人。
鼓励人们抑恶从善需要稳定的社会秩序和制度环境。在一个秩序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人性中的作恶倾向通常被严格限制在社会可容许的范围之内。一旦制度和环境突然产生变化,在缺乏约束的情况下,个体作恶的可能性则会大大增加。虽然有少数人在恶劣环境中也能行善,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无约束易为恶则是常态,这是由人的生存本能决定的。正是人性中存在的这种自保与自利的倾向使人在缺乏外在规范和约束的条件下很容易伤害他人,谋取私利。斯密曾形象地描述了这种侵害他人的倾向:人们很容易接受诱惑,去恃强伤害一个人,如果没有在人们中间确立正义的原则,如果没有使人们慑服而敬畏的力量,人们就会随时准备向他人发起攻击[5]106-107。
人性的制度约束一旦松懈,就会产生大量恶行。正因如此,对人性的理性态度是不能过于乐观,不能寄予过高期望,而是应该保持警惕和防范。张灏曾用幽暗意识来概括这种对人性较为谨慎的看法。幽暗意识是一种低调的人性观。所谓幽暗意识是对人性中与生俱来的种种黑暗势力的正视和省悟,正是由于这些黑暗势力根深蒂固,人的生命才有各种丑恶,世界才不会圆满。这种幽暗意识珍视人类的个体尊严,正视人的罪恶性和堕落性,但是其在价值上否定人的私利和私欲,然后在此前提下防堵和疏导人们为恶之潜能[9]2。这种对人性的审慎态度不能等同于性恶论,而是承认每个人都有堕落趋势与罪恶潜能,必须用制度化的东西加以约束[10]。人的自利性以及潜藏的作恶倾向对于人的后天行为具有深远的影响。防范人性中的作恶倾向膨胀进而规范人的自利行为成为文明社会道德与制度建构的第一要务。对待人性较为客观的态度,是构建人性良性发展的制度条件,防范人性可能为恶的一面,同时鼓励人性中积极向善的一面。
二、从人性视角看政治发展的模式选择
政治发展是世界各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发生的趋向进步的政治变迁,通常会对社会政治环境产生较大影响。如果一个国家选择激进式政治发展道路,就会急剧改变社会个体的生存环境,很容易造就制度真空,使人性失去基本的约束,从而改变人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对道德规范和社会秩序产生严重冲击。法国思想家勒庞认为,一旦社会环境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例如突然发生严重的动乱,那么个体人格与社会环境的平衡就会被打破,对人性的束缚就会全然解除。在摆脱了所有传统和法律的约束之后,人的本能就失去了羁绊,留在人们身上的就只有原始的兽性了[11]195-208。同一个个体的人格将发生惊人变化,前后判若两人。一个在平时温文尔雅的人可能变得残忍好杀[11]51-52。休谟在《人性论》中也表达过同样看法,他认为人类的贪心和偏私如果不受某种一般的、不变的原则所约束,世界就会混乱不堪。当约束民众原始野性的规范体系被轻率地打破之后,在人类社会中就会产生无限纷扰,爆发激烈的冲突[3]572-573。
在社会失范状态下,不仅个体的性格特征和行为模式会发生严重变异,而且平时沉默的群体也会行动起来,参与各种政治与社会冲突。动荡时期,当民众大规模参与政治生活时,政府可能会丧失部分或全部权力,一部分权力转移到临时组织起来的民众手中,难以受到有效约束。不完善的人性和不受制约的权力相结合,很容易冲破各种制度规范。人性中潜藏的恶的因素会在失去约束的群体中急剧膨胀,人的性格会畸形发展,失去理性、判断力和责任感,对社会造成严重的危害。孤立的个人因为担心受到惩罚,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能够自觉抵制各种犯罪的诱惑和冲动。当个人集聚在一个庞大的群体中时,就会出现完全不同的情形。恰如勒庞所指出,当个人加入一个不负责任的群体时,因为很清楚不会受到惩罚,所以约束个人的责任感会彻底消失,人多势众使个人感觉到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他们很容易放纵自己的本能,犯下各种罪行[12]。柏克也认为在民众普遍参与的政治状态下,没有人会害怕自己可能要受惩罚,因为民众整体不能成为惩罚对象[13]。
从人性的视角看待政治发展问题,后发展国家的最佳方略是选择渐进式政治发展模式,通过渐进改革的方式推动政治体系的演进和更新。后发展国家的政治发展面临不利的国际环境,很容易受到外部势力的干预和影响,国内民族、宗教、地区、阶层矛盾比较突出,如果选择激进式政治发展道路会对社会秩序造成颠覆性破坏,政府权威弱化,法律和制度失去约束力,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危害极大。人性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没有法律和制度的约束,在政治发展过程中更是如此。为阻止人性向恶的方向发展,需要延续道德传统来训导人的精神,保持法律的稳定性以规范人的行为,才能在变动社会中使人们的权力滥用和贪婪的权力欲求有所收敛[14]。政治变迁本来就对现存的法律秩序构成威胁,如果选择激进式政治发展道路,摧毁制约人们行为的规范体系,就会导致各种恶行泛滥。在政治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对人性中所隐藏的作恶可能性保持高度的警惕,始终保持制度和规范的稳定性,确保政府的权威和基本的法律体系能够约束人性的弱点。政治发展不能借助全面改造人性与制度来实现,不能轻易地抛弃社会原有的制度体系,而是要通过审慎的改革消除旧制度的弊端,使新制度在旧制度基础上逐步生长,在避免社会动荡的前提下实现新制度取代旧制度的目标。
三、渐进式政治发展模式的制度设计
因为人性发展有两种可能性,所以思想史上出现了性本善与性本恶两种对立的人性预设,并且对政治制度设计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两种人性理论都是片面强调了人性在某一方向发展的可能性,误把后天生成的德性当作人的原初本性,以此为据推导出的制度设计必然存在重大缺陷。例如,中国古代的儒家对人性的主流看法是性本善[15]。人性善的假定应用于私人领域和一般社会生活领域,有其可取之处。但若根据儒家的人性假定设计政治制度,则难免会失效。儒家的政治设计是由圣人掌握最高权力或者寄希望于掌权者自觉提升德性以实现良治,却未对掌权者滥用权力设置有效的制度性防范措施。这种性善假定与绝对权力的结合在实践中只能导致披着道德外衣的专制统治。中国古代的法家认为人性本恶,并且推崇绝对“性恶论”,主张以严格的法律与统治权术控制官员和百姓。但是法家式的性恶论有两大缺陷,一是在社会生活与私人生活领域也贯彻绝对的性恶论,对百姓实施严刑峻法,不能为人性向善、自由选择提供充分的空间,摧毁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失去了创造良好生活的可能性;二是在公共政治领域,性恶论的假定不包括最高统治者,最高统治者掌握了绝对权力,又不加以系统性的制度约束,必然为暴政打开大门。马基雅维利是西方近代性恶论的代表人物,但是他所主张的性恶论和中国古代的法家有相似之处,都把君主排除在外,只强调君主可不择手段控制臣民,却忽视了对掌权者的制约。显然,在政治生活领域,片面的性善论或者性恶论都不能构建良好的政治制度,创造良好的政治生活。
一个国家若要成功推进渐进式政治发展,国家的制度设计必须充分考虑人性的两重性。在私人领域及一般社会生活领域,除以法律防止个人侵犯他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外,制度设计应相信人性具有向善的可能,侧重以道德教育、榜样示范引导人向善,政府权力恪守界限,不过分干涉私人生活及社会交往。在公共政治领域,制度设计应重点关注人性趋恶的一面,始终着眼于对人性蜕变与权力滥用的防范和制约。在体制转型过程中防范掌权的政治人物或群体人性蜕变尤为重要,不能因为政治体制的新旧交替而对权力的制约稍有松懈。在人性中潜藏着作恶的可能性面前,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政治人物也不例外。“当个人由市场中的买者或卖者转变为政治过程中的投票者、纳税人、受益者、政治家或官员时,他们的品性不会发生变化。”[16]341制定法律和掌握政府权力的人也和普通人一样,同样是被难以控制的情感和直接的利益所驱使,并且因为掌握着强制性的公共权力,政治人物更容易受到人类弱点和情感的支配,更容易滥用手中的权力。不仅位高权重的个人有受权力腐化的趋势,特殊时期掌握了政治权力的民众也容易受到权力的腐蚀,利用手中的权力欺凌其他群体[9]10-11。普通人大规模直接进入政治生活领域,成为活跃的政治行动主体,在一定程度上掌握政治权力时,其人性中所潜藏的恶的可能性也会集中爆发。多数人掌权如果不受制约同样有滥用权力的危险,并不会因为人数众多而改变人性蜕变与权力变质的基本规律。
推进政治发展的政治主体,无论是少数人抑或多数人,都有可能滥用政治权力,因此防止任何政治力量滥用权力应是渐进式政治发展过程中政治制度设计的首要任务。虽然人性本身并非注定为恶,但政治制度设计的逻辑必须着眼于人性的约束,对恶的发生预先防范,必须从假定人人皆可滥用权力的角度进行制度设计。休谟对此曾提出著名的“无赖假定”,即“在设计任何政府体制和确定该体制中的若干制约、监控机构时,必须把每个成员都设想为无赖之徒,并设想他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谋求私利,别无其他目标。我们必须利用这种个人利害来控制他,并使他与公益合作,尽管他本来贪得无厌,野心很大”[17]。经济学家布坎南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立宪政治的一个重要的原理是要作如下的假定——掌权者将滥用政治权力去促进特殊的利益;这不是因为情形常常是如此,而是因为这是事物的自然趋势,这是自由制度特别要加以防止的。”[16]342
这种逻辑前设并非是指所有的政治人物都是坏人,必然要做坏事,而是寻求一种制度上的防范和控制,其目的是为了最大程度地防止最坏结果的出现。控制权力滥用的手段是在民主与法治基础上建立有效的权力制衡体系。麦迪逊指出,正是由于人性总是不完善的,所以人类社会才需要政府以及对政府的控制,才需要遏制政府专权之企图,而“防止把某些权力逐渐集中于同一部门的最可靠办法,就是给予各部门的主管人抵制其他部门侵犯的必要法定手段和个人的主动”[18]。建立权力制衡机制的政治体系不仅在内部结构上是稳定的,能够使政治权力恪守适当的界限,而且具有很强的适应性,能够满足政治发展过程中剧增的各种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的要求。当政治体系面临多重挑战时,各个政治机构可以相互配合,都在维持政治体系的稳定和发展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只有通过基于法治的制衡机制使政治权力受到严格制约,遏制任何个人或者集团滥用权力的企图,向民主政体过渡的过程才能以和平的渐进的方式进行。
人性是不完美的,因此人类不可能在短期内通过激进变革完全消除政治生活中的弊端。政治发展的合理目标不是基于人性本善去追求一个完美的理想国,也不是依据人性本恶去构建一个法家式绝对专制的权力体系,而是通过持续的制度创新纠正现有制度体系的缺陷。致力于实现现代化的后发展国家政治上的最佳选择是走渐进式政治发展道路,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惩恶扬善,更好地约束人性,控制权力,减少现代化进程中的动荡和破坏,为国家发展提供稳定安全的政治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