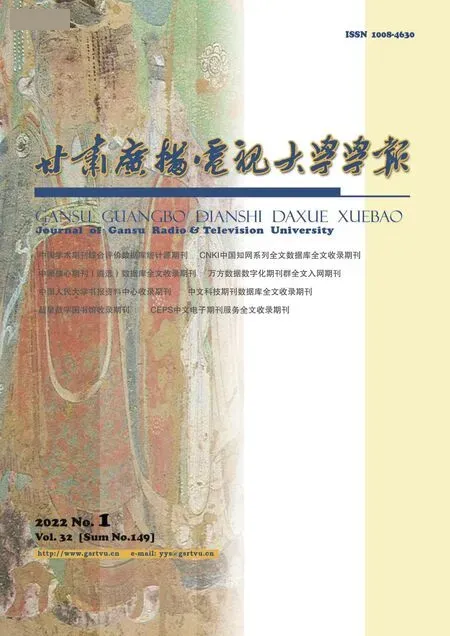拜伦创作与“浪漫主义的根源”
倪正芳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文学院,湖南 娄底 417000)
诗人拜伦的创作实践所体现出的高高飞翔的想象、澎湃汹涌的激情以及无与伦比的创造性才能,还有他的文学作品与社会活动在那个革命热情空前高涨时代所发挥的鼓舞作用和战斗意义,都印证了他不愧为浪漫主义文学代表性人物。在借用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的书名(《浪漫主义的根源》,The Roots of Romanticism)作标题的本文里,我们希望着重探讨的则是,拜伦浪漫主义创作倾向受到过那些因素的影响,他那鲜明的浪漫主义创作风格是如何形成的。
一
我们首先必须看到,英国本土文化传统特别是早期浪漫主义文学传统对拜伦的影响是直接的,这可以从苏格兰“农民诗人”彭斯说起。彭斯是英国浪漫主义的前驱,他收集、整理了约三百首苏格兰民歌并通过加工赋予其新生命,正是这种对民歌传统的复兴后来成为英国浪漫主义的特征之一。除了歌唱自由和爱情的民歌型抒情诗,彭斯还擅长讽刺诗、叙事诗等。彭斯的诗,“不是庙堂、学院和客厅的产物,而是法国大革命风云激荡的历史时刻由几种从不同方面要求解放人性的思想趋势形成的”,他“使得这个新的诗歌运动不至于过分理智化、抽象化,不至于轻飘飘,而是有坚实性、强韧性,同时又有朴素、生动而持久的美”[1]220。他的诗学主张是:“我只求大自然给我一星火种,我所求的学问便全在此中!纵使我驾着大车和木犁,浑身是汗水和泥土,纵使我的诗神穿得朴素,她可打进心灵深处!”[1]219他的这种对民间风味与本土属性的主张及其创作实践,犹如一股清风,搅动了陷入沉闷、刻板的伪古典主义盘踞的文坛,特别是给英国诗歌创作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作为曾在苏格兰山地度过一段童年时光的拜伦,对这个苏格兰平民出身的浪漫主义文学开路人充满了理解与敬仰,对他的诗歌风格也是认同的。叶利斯特拉托娃说:“(拜伦)这位未来的诗人从童年起就非常热爱苏格兰的大自然,他常常把苏格兰当作自己的故乡。多山的苏格兰一向为彭斯所歌颂,在那里,农民当时的生活还保留着资产阶级形成前的宗法氏族关系的一些习俗,因此,在拜伦的记忆中它永远是自由的象征。”[2]13早在1806年,拜伦在编自己的诗集《即兴诗集》及后来正式出版的《闲散的时光》时,就按照彭斯的风格写了若干首诗,如《勒钦伊盖》《我愿做无忧无虑的小孩》《我曾是一个年轻的高地流浪者》等。18世纪的一些诗人们喜用古典主义的抽象词藻,以华丽、浮夸、冷漠的哀诗和书信表达所谓“崇高”的热情;而世俗爱情的喜悦则多半成为“滑稽的”、轻浮的、自然主义的粗野诗歌的主题。是彭斯首次成功地克服了这种分离,并在诗歌中恢复了民间创作所固有的灵与肉的统一性,因而他才能写出像《我的爱人像朵红红的玫瑰》这样清新温柔而极富地域特色的爱情诗。拜伦对彭斯的热爱,还表现在以他为榜样,使抒情诗的情感得到自然的表达,比如《她走在美的光彩中》就是一篇这样的范例。此外,彭斯富于社会热情,在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社会思想感召下,再加上固有的苏格兰民族主义情绪,使得诗人创作了不少带有“颠覆”性和叛逆性的政治诗及讽刺诗。如《不管那一套》:“国王可以封官,公侯伯子男一大套。光明正大的人不受他管——他也别想梦想弄圈套!管他们这一套那一套,什么贵人的威仪那一套,实实在在的真理,顶天立地的品格,才比什么爵位都高!……”[1]212而我们已经知道拜伦的《路德分子之歌》等也是表现下层民众反叛情绪的力作。
成名比拜伦早的司各特,在很长时期里都是英国文坛的领袖之一,他还是拜伦尊敬的朋友。从司各特作品宝贵的民间风格因素中,拜伦受到了很大启发。他从不讳言自己对这种风格的借鉴,如他在《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第一、二章序言中申明:“第一章开头部分的那首《晚安歌》则是受了司各特所编的《边区歌谣集》中的《麦克斯威勋爵的晚安歌》的启发而写成的。”[3]拜伦在《贝波》中对那些“比下流更差”的在贵族沙龙里无病呻吟的作家们表示厌恶时,也表达了自己对司各特等人的好感:“此外也还有通达世情的诗人,例如司各特,罗杰斯,摩尔,以及较好的作家,除了耍笔杆,也还能想到其他;……”[4]339(《贝波》第76节)司各特给拜伦摸索中的早期创作以方向性影响,及至拜伦成名后,司各特又以宽广的胸襟甘愿为之腾出浪漫主义抒情诗人的王座,并对其后期创作给予一如既往地支持和鼓励。如在《唐璜》第一、二章刚出版就受到各方攻击时,司各特却这样说:“(《唐璜》)像莎士比亚一样地包罗万象,它囊括了人生的每个题目,拨动了神圣的琴上的每一根弦,弹出最细小以至最强烈最震动心灵的调子。”[4]8
曾被称作消极浪漫主义代表的“湖畔派”与拜伦虽然在政治观点上有很大分歧,但同为浪漫主义的诗人,他们在创作主张进而在实际文学风格上有不少相通之处。如作为浪漫主义基本特征的想象、天才和情感便都是他们共同强调并竭力追求的。实际上,作为“后生”的拜伦在与湖畔派交往的过程中,并未对湖畔派尤其是对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的艺术成就视而不见,相反,他赞赏他们的才华,甚至在自己的创作中借鉴过其中的长处。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就承认华兹华斯“偶尔”也对拜伦发生过影响。莫洛亚《拜伦传》也记载,1816年在日内瓦的时候,雪莱曾让拜伦欣赏“一小段一小段华兹华斯的诗”[5]239。华兹华斯被刚出道时的拜伦在《英格兰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中责骂过,而且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拜伦一直拒绝读这位诗人的诗。可是在1816年日内瓦湖畔这样难得的宁静而优美的环境中,在知心的朋友身边,他对华兹华斯的诗渐渐产生一定的兴趣。在饱尝了世道辛酸之后,在这幽静的湖光山色中,接触到华兹华斯的高雅温柔的作品,他也许一度体会到了内心的平和,而这种情感变化又可能在作者当时的创作中反映出来。所以我们看到在《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第三章中,那位孤独傲世的旅行者的情绪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澄澈、透明、镜面似的莱蒙湖!你同我曾居住的茫茫人世相异迥然,你似乎在静静地告诫我,向我叮嘱:应抛弃尘世的烦恼水,寻求洁白的泉。好像无声的翅翼;我曾经爱过,曾经爱过那翻腾吼啸着的波澜,但湖水的温柔耳语像姐姐在责怪我:究竟是为了什么要那样喜爱危险的风波。(《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第三章第85节)
对另一位湖畔派诗人柯勒律治,拜伦也并非总是抱着厌弃态度。他不仅在社交场合与柯勒律治保持着交往,还与其有过书信往来。1815年3月31日,在一封致柯勒律治的信中,拜伦表达了对后者的敬意及自己过去在作品中可能对他造成的粗暴伤害的悔意:“很多年来我们还没有写出能与您的《悔恨》相提并论的作品,我应该认为那部戏的接受程度是足够能鼓舞起作者与观众的最高的希望的。我们坚信您所从事的一项大业必定会获得成功,……您提到我的‘讽刺的’讽刺诗文,或无论您或其他人高兴称它什么。我只能说它写于我十分年轻气盛的时候,……涉及您的那部分太冒失、太粗鲁、也太肤浅了。”拜伦甚至有时还赞扬柯勒律治的作品,针对别人的批评还主动替他作辩护:“我听说《爱丁堡评论》对柯勒律治的《克利斯塔贝尔》进行了抨击,并攻击我对它的赞扬(‘狂热的和有独创性的美妙的诗’)。我赞扬它首先是因为我认为它好;……我为杰弗里对他的攻击深感遗憾,因为,可怜的伙伴,那会使他的心灵受到创伤,经济上受到损失。至于我,我是欢迎他的——我决不会因为将来他会说什么反对我的著作的话而对他有更低的评价。”[6]出发点可能复杂了一些,但还是能看出拜伦对柯勒律治诗歌某些方面的认同。拜伦还很欣赏柯勒律治的《忽必烈汗》,并亲自劝其发表它。
其实,即使是拜伦的老对头骚塞,也并非对拜伦的诗学思想没有任何影响。比如骚塞的东方题材的作品比拜伦写得早,(骚塞的《萨拉巴》出版于1801年,《克哈马的诅咒》出版于1810年)尽管拜伦看来那不过是一种“疑似”东方题材的作品,但它们毕竟和穆尔等人的作品一道引发了民间的阅读兴趣。之后拜伦才以自己的优势和特点通过《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和“东方故事诗”等作品远远地超越了他。拜伦对吸血鬼题材很有兴趣,而这也与骚塞较早涉及并影响了拜伦有关。“东方故事诗”之《异教徒》中有这样的诗句:“当吸血鬼被遣送到人世间来,他首先会把你的尸体从坟墓里朝外硬拽……”接着诗人在这里特地作了个注,介绍他对骚塞引用同一故事的关注:“骚塞先生在他的《萨拉巴》的注释中引用了这个故事。”[7]43类似的情形还有拜伦戏仿骚塞《审判的幻景》写出了他精彩的同名讽刺诗,以致勃兰兑斯这样调侃:“我们感谢骚塞写的《审判的幻景》引出了拜伦的那篇同名作品——而且为了他的这项‘功劳’,我们愿意宽容他的《克哈马的诅咒》和《萨拉巴》这两部作品。”[8]115无疑,这也表明,骚塞与拜伦之间多少存在一个题材启发、灵感触动的事实。
二
当时欧洲的社会变革及文学传统也对拜伦浪漫主义倾向产生了非常明显而积极的影响。
就英国浪漫主义发生发展的社会背景与时代契机而言,英国的浪漫主义是在受到法国革命的影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一点我们在谈论欧洲浪漫主义对拜伦的影响时不能不首先指出。罗钢说:“英国浪漫主义运动紧接着法国大革命爆发,绝对不是时间上的偶合,没有法国革命中对人的尊严权力和精神价值的充分肯定,没有法国革命触发的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没有法国革命带来的人的主观精神的蹈厉发扬,就不可能有纵情抒发个人怀抱,自由地驰骋想象,彻底打破新古典主义清规戒律的浪漫主义文艺的诞生。”连一向被称为“消极浪漫主义”领袖的华兹华斯尚且声称法国革命是“高贵的双亲——自由和慈善的爱的孩子”[9],那些被称为“法国革命的产儿”的所谓“积极浪漫主义”诗人如拜伦、雪莱们,其身上法国革命的思想烙印就更加深刻了。
欧洲大陆启蒙主义时期的文学对包括拜伦创作在内的浪漫主义文学也产生了显著影响。这种影响首先应该是思想观念上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一些作家创作中的情感倾向、题材内容、具体技法等与后来浪漫主义气质相同或相近的要素的积极作用。当时法国、德国等一批作家们就以自己敏锐的感受和超越时代的眼光,奋笔疾书,大声呐喊,他们的思想遗产与创作成果从许多方面都起到了催生不久之后将横扫欧洲的浪漫主义滚滚洪流的作用。
卢梭,这位“返回自然”的倡导者、人性解放的先驱和敏感的思想家,曾给拜伦、雪莱等人以丰富的思想资源、热烈的情感鼓舞、强大的精神支撑和创作动力。他的《新爱洛绮丝》等作品体现了新的时代资产阶级乃至整个第三等级争取个性解放的民主主义思潮,表明一批文艺家们开始格外迫切地要求从封建的“理性”精神束缚下彻底解放出来,获得心灵的自由舒张,而且他们已把这种诉求通过对人类情感、本能的描写传达出来。拜伦不仅在作品中经常引用卢梭作品,还不止一次地直接表达对这位精神导师的敬意。在瑞士日内瓦一带游历时,这个卢梭的诞生地和伏尔泰的避难地引起了拜伦对法国启蒙主义者的回忆。触景生情,拜伦在《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第三章描绘了他们的形象。在第77节他专门写到卢梭,这仿佛也是拜伦自己的写照:
狂放的卢梭,那作茧自缚的哲人,就从这地方开始他那不幸的生涯;他用魔力美化了那种痛苦的热情,从悲苦中涌迸出无敌的辩才,……他所用的语言就好像眩眼的日光,人的眼睛立刻流下同情的泪,一读他的文章。
拜伦还将其中的第81—82节献给卢梭和他的同志们,宣称卢梭的预言“让全世界燃起了熊熊的火焰,直到所有的王国全都化为灰烬”。1816年6月27日,拜伦在致默里的信中说:“我已详细考察了卢梭的地方,《新爱洛绮丝》就在我的眼前,在某种程度上,我惊异于他描绘的准确与其现实中的美丽所产生的那种力量。”在晚期的一部悲剧性长诗《岛》中,拜伦所描写的太平洋小岛上那种乌托邦式的社会生活,映射出人类的黄金童年时代,也正是以前卢梭所憧憬的。
歌德是拜伦心目中整整一个时代的文坛上的君王。在去希腊参战途中收到歌德的《论拜伦》、一些给拜伦的短诗及其感谢拜伦将悲剧《沃纳》题献给他的一封信后,拜伦于1823年7月24日回信,表示对歌德的由衷敬意与崇拜,称歌德“50年来一直是欧洲文学无可争议的君王”,还虚心地说“能得到歌德先生亲笔写的一个字,都是我无可比拟的好兆头与惊喜。”其兴奋激动之情,溢于言表。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等作品,拜伦不仅阅读,还在作品中引用。维特的烦恼,是一种渴望冲破旧世界旧观念的牢笼、释放青春的激情而暂时不可得的烦恼。他对周围环境的窒息感,对庸俗的社会秩序的绝望感,何尝不是拜伦同样遭遇着的呢?所不同的是,维特的时代,革命的精神还未成气候,他看不到个性解放的前途,所以只能绝望地自杀,而拜伦生活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拿破仑在历史的舞台纵横捭阖之际,人类历史正因此上演着一幕幕惊天动地的大活剧。人们获得了有力的精神鼓舞、广阔的情感空间和相当程度的表达自由。加上拜伦身为贵族,拥有一般人所无法比拟的行动特权,他可以更加大胆地、并相对安全地抒发自己的理想,表达自己对社会的批判,开展自己对未来的追求(尽管如此,拜伦在社会上还是碰了不少壁,受了不少伤)。《浮士德》中的浪漫因素给予拜伦的影响也是明显的。莫洛亚《拜伦传》这样介绍拜伦与《浮士德》的相遇:
(1816年)8月里,《修道士》的作者马修·路易斯来到狄沃达蒂拜访他。马修·路易斯为他翻译了歌德《浮士德》中的一些片段。它的主题打动了他的心!浮士德提出的关于宇宙的这些古老的问题,与魔鬼订的契约,失去玛格丽特——这些难道不是他自己的问题吗?但是,假如拜伦自己创作了浮士德,他会将他描绘得更大胆,更悲惨。为什么在幽灵面前发抖呢?一个人,一个真正的人,蔑视幽灵,蔑视死神。
这样,“《浮士德》的阅读和阿尔卑斯山脉的风景震动了他,于是从中产生了一部伟大的诗剧《曼弗雷德》”[5]249。确实,当我们看到作品第二场,魔女提出帮助曼弗雷德的条件是要求后者发誓服从其意志方可实现自己的愿望,我们会马上联想到魔鬼靡菲斯特与浮士德的赌约。所不同的是,曼弗雷德拒绝了魔女的要求,因为他还有强大的魔术去求助于阿里曼(伊朗神话中的罪恶与黑暗之神)。甚至歌德本人也从拜伦的作品中看到了自己作品的影子,并为他构思作品时对《浮士德》的借鉴表示理解和支持。他说:“拜伦笔下的变了形的魔鬼(指拜伦的《变形的畸形人》中的主角——笔者注)也是我写的靡非斯特的续编,运用得也很正确。如果他独出心裁想要偏离蓝本,就一定弄得很糟。所以,我的靡非斯特也唱了莎士比亚的一首歌。他为什么不应该唱?如果莎士比亚的歌很切题,说了应该说的话,我为什么要费力来另做一首呢?我的《浮士德》的引子也有些像《旧约》中的《约伯记》的引子,这也是很恰当的,因此我不该受到谴责,而应该受到赞扬。”“拜伦只有在写作的时候才是伟大的,一旦他进行思考时,却是—个孩子。所以当他的同胞对他进行类似的无理攻击时,他就显得束手无策。他本来应该向他的论敌们表现得更强硬些,应该说,‘我的作品中的东西都是我自己的,至于我的作品是来自生活还是来自书本,这是无关紧要的,关键在于我是否运用得恰当!’”[10]
三
在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中,异域背景是一个极具特色的创作兴奋点,而“东方”更是几乎成为“异域”的同义词。对拜伦而言,“东方”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那片神奇土地上的文学遗产也给了他创作上的诸多教益和启发,尤其是对形成其个性化的浪漫主义风格发挥了作用。
萨义德说:“‘东方的’(Oriental)一词由来已久;它曾出现在乔叟……和拜伦等人的笔下。从地域、道德和文化的角度而言它指的都是亚洲或广义的东方(the East)。”[11]作为与拜伦生活经历和创作密切相关的“东方”概念,从地理意义上说,它当然是指欧洲大陆以东的广大亚细亚地区,包括拜伦诗歌中东方元素的重要体现地、跨越欧亚两大洲、曾影响广大欧洲地区的伊斯兰国家土耳其。如果从历史文化渊源讲,北非的埃及等地也应被纳入“东方”的范畴。我们要探讨的对拜伦浪漫主义创作风格发生了影响的东方及其文学主要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
拜伦6岁就由母亲聘请了家庭教师指导阅读。“《旧约》,史书,各种旅行记给了他无穷的愉悦,并激发起他对东方的兴趣。”[12]18拜伦在中学和大学时更是广泛接触了东方历史、宗教、文学与文化。求学时期的拜伦曾开列过一份所读书籍的清单,其中有关东方文学与文化的作家和作品有:
阿拉伯:穆罕默德,其《可兰经》包含了最庄严的诗性段落,远胜于欧洲的诗歌。
波斯:菲尔多西,创作了波斯的《伊里亚特》——《王书》。萨迪。哈菲兹,不朽的哈菲兹,是东方的阿拉克瑞翁……
缅甸帝国:这个国家的人民狂热地喜爱诗歌,不过他们的诗人还不够著名。
中国:除了乾隆皇帝和他的《茶颂》,我还没有了解其他任何诗人。……
非洲:非洲有些地方的歌曲,音调悲凉,歌词朴素而动人……[12]25
看得出,在杰出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东方诗人当中,拜伦推崇菲尔多西(941—1020)、萨迪(约1203—1292)和哈菲兹(1300—1389)。令人吃惊的是,他居然关注到缅甸诗歌和中国历史上的诗歌“冠军”(指产量意义上)乾隆皇帝的作品。此外,“他感到惋惜的是,由于对梵文了解不深,以致不能使欧洲人对印度古代的诗歌创作有所领略”[2]17。这是青年拜伦对“世界文学”视野内的东方文学的感想。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这些诗人的创作(乾隆皇帝作为一个特殊“诗人”可以不列入讨论),也并非完全是浪漫主义风格,也有反映现实、同情民众、批判暴政、揭露丑恶等现实主义内容,但拜伦所主要关注的无疑既不是浪漫的抒情,也不是严肃的批判,而是因为“他们”和“它们”来自遥远陌生的东方,诗人借助于这些东方要素进行创作可以产生新奇感、神秘性和吸引力。在实际创作中,拜伦在题材、背景及情调、构思等方面浪漫特色的形成均得益于东方文学很多,东方元素的实际作用也基本在于此。
虽然英国早就拥有东方大片的殖民地,但对这个岛国的多数民众来说,那片遥远而辽阔的土地一直是神秘而令人向往的。19世纪初期,“东方”在英国尤其是在社会上层的阅读圈里曾成为一个时髦的概念。在文学创作界,作家们也以表现东方题材为时尚。其实“喜欢描绘东方题材是各国浪漫主义作家的一个共同点”[8]110。由于求学时期对东方及东方文学的接触,还由于1809—1811年的“东方”(此处还包括了东南欧一些山地国家)之行,拜伦在这个潮流中后来居上,占领了制高点。可以说正是以神秘、新奇甚至怪异等浪漫情调为特征的“东方”书写对铸就拜伦最辉煌的诗名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813—1815年,拜伦创作出了轰动一时的所谓“东方故事诗”。当然,他的东方故事的背景实际上还是伊斯兰教文化与希腊、阿尔巴尼亚等东南欧地理环境结合的产物,以致他自己给《异教徒》和《阿比多斯的新娘》加的副标题就是《土耳其的故事》,而他的同时代人,在“东方”行走期间与拜伦结识的英国文学家约翰·高尔特则把这两篇及《海盗》叫做《希腊的故事》。然而,尽管“东方故事诗”很大程度上是诗人对东方的一种想象,但毕竟诗人还是到过像土耳其这样的伊斯兰国家,而且当时欧洲有的国家还处在伊斯兰世界的统治下,有的国家还残留有伊斯兰势力统治过的痕迹,更何况还有诗人天才的想象和对真正东方文学的间接经验呢。因而,诗人的“东方”固然有些真真假假、似是而非,但对英国多数读者而言,东方味儿(或不如说是非英国文化味儿、异国情调味儿)已足够浓了。比如在《异教徒》里他用一些有东方特色的典故、比喻及习俗描写来增添作品的“东方”气息:蕾拉的双眸“乌黑迷人”,“像杰姆希德的宝石那样明亮耀眼”——这里就用了一个中古波斯的传说。相传中古波斯杰姆希德苏丹有颗著名的红宝石,光芒四射,人们还叫它“夜之炬”“日之杯”。诗人还把玫瑰称作“夜莺的公主”,理由是他知道,“夜莺对玫瑰的恋情在波斯语言中是人所熟知的”[7]9。在这篇作品中,拜伦还充分显示了他对阿拉伯世界或伊斯兰教经典的了解。安拉、宗师之类形象,石榴花的隐喻,《古兰经》的教义,土耳其人的丧葬习俗,阿拉伯世界传说中的魔鬼,等等,似乎足以予取予求了。诗人为了西方读者的阅读方便,还不厌其烦地(大概也在炫耀自己作品东方题材的正宗与地道吧)作了许多关于东方的注释。
其他作品中,他也努力地营造着一种尽可能浓厚的“东方”语境。《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中的“一个人的颔下有了灰白的长须,并不妨碍他心中有青年似的热忱;爱能战胜老,哈菲兹说得有根据,……”(第二章第63节)诗句表明拜伦对波斯诗人哈菲兹的热爱不是一时的冲动。从《曼弗雷德》第二幕第四场以伊朗(波斯)神话中罪恶与黑暗之神阿里曼为中心的构思我们可知拜伦对波斯神话的借重。拜伦在中学就熟读《天方夜谭》,“《天方夜谭》对拜伦的文学创作的影响是重大的”,它“不仅唤醒了儿时拜伦的想象而且拓宽了他想象的空间,并促使他阅读和了解更多的东方”[12]20-21。后来,《天方夜谭》之类的东方元素也成为他作品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如“阿拉伯故事所传说或梦想的/财宝”(《海盗》第三章第5节),“现洋本来是阿拉丁的灯烛”(《唐璜》第十二章第12节)等诗句,表明作者对这类阿拉伯民间故事熟悉到了随手拈来的程度。如此等等异域的情调和文化特征,既是拜伦作品浪漫主义风格的体现,也表明了这种风格所具有的相当的东方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