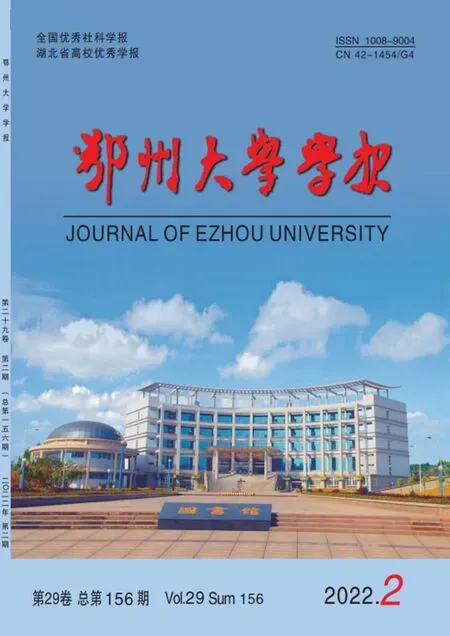大股东控制权、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避税行为研究
——来自民营上市企业的证据
胡素华,冯敏,董烘霞
(绍兴文理学院商学院,浙江绍兴 312000)
随着现代化市场经济的发展,许多公司通过避税手段来降低税负以增加公司的收益。虽然不同企业都有避税行为,但不同企业间的避税程度却存在差异。Slemrod(2004)[1]、Desai 与Dharmapala(2006)[2]、Armstrong et al.(2012)[3]、Rego 和Wilson(2012)[4]、Graham et al.(2014)[5]、Powers et al.(2016)[6]、董烘霞与胡素华(2018)[7]等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研究了管理层激励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但研究结论并不一致。笔者引入大股东控制权以及大股东控制权与高管股权激励交互项,同时利用分位数回归方法,试图从避税行为全分布情况下研究大股东控制权、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避税行为间的关系。
一、文献回顾及研究假设
1.文献回顾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如果避税可以使企业流入更多经济利益,那么所有者对管理层进行适当的激励使管理者站在企业的层面上,做出于所有者有利的避税决策(Slemrod,2004)。之后,众多学者对此展开深入的研究,但对激励与企业避税的影响相关结论却不尽相同。Desai 与Dharmapala(2006)指出随着企业避税程度激进所带来的成本增加,管理层的寻租行为就越弱。陈信元等(2009)[8]认为避税所带来的现金流入很可能进入了管理层的口袋,这种现象在治理机制不完善且管理层的薪酬又相对较低的企业中尤为明显。
在公司治理理论中,控制权配置与激励安排都占有重要地位,大股东控制权在进行企业避税决策时也有着不容小觑的影响,Chen et al.(2010)发现,由于控制权集中的特殊性,大股东可以对高管施加压力或者进行激励进行控制,让其做出符合大股东期望的避税决策。但Chen Shuping(2010)发现高管需要承担的风险相比股权激励之前要大很多,所以他们不会愿意去承担避税带来的各种风险。
另外,相关文献的实证结论都是基于OLS 等传统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公司治理与避税分布的条件均值之间的关系,并没有研究避税程度全分布的其他分布情况,笔者基于分位数回归方法试图获得避税程度全分布情况下,尤其是在极端避税情况下两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可以更好解释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避税的影响。
2.研究假设
从大环境来看,税收征管水平的提高使企业激进的避税产生高额的代理成本,高管往往会采用减少避税的方式来减少因避税带来的成本问题。因此,随着对高管的股权激励增加,高管为了降低整体风险,会更加不愿意在避税方面承担成本,进而会选择较为保守的避税措施。在对企业高管股权激励后,高管自身的收益报酬会与企业价值和绩效相关联,这使高管与所有者的利益目标更加一致。因此,企业管理层如果受到了较高的股权激励,管理层的目标与大股东的目标就趋于一致,他们往往会选择不避税或选择较低的避税程度。基于以上分析,笔者提出假设1:
H1:民营企业中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所得税避税程度呈负相关关系,且随着企业避税水平的增加,股权激励与企业避税程度的负相关关系逐渐增强。
如果企业股权结构比较集中,就意味着大股东可以绝对控制企业的经营决策。对于税收激进程度低的企业来说,他们更加关注企业整体的稳定,希望降低风险来保证自身权益。他们更加关注潜在的危险和成本,所以他们对避税的热情并不高涨。大股东的控制权越强,企业的所得税避税程度就会被降至较低水平。相反,在税收激进程度高的企业中,当激进避税方案的收益大于其成本,大股东更愿意选择此类方案以留存更多利润与现金流入企业,对高管的股权激励使其与大股东的目标趋同,让高管做出与大股东意愿相一致的避税决策。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2a:当企业避税水平较弱时,大股东控制权正向调节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避税程度的负相关关系。
H2b:当企业避税水平激进时,大股东控制权负向调节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避税程度的负相关关系。
二、实证研究设计
1.变量选择
由于企业避税活动具有复杂与不透明性,在对避税进行衡量时往往会存在比较大的差异,国内外主要采取以吴联生(2009)、Fariz 和Bonnie(2012)等学者选用的有效税率、Manzon 和Plesko(2002)选用的会税差异以及金鑫和雷光勇(2011)等学者采用会税差异与应计项目的回归残差来作为避税的衡量方式。笔者采用最后一种衡量方式。
实施股权激励可以有效解决企业的委托代理问题,高管持股是管理层激励的主要形式。结合文献,笔者选用了高管前三名的薪酬总和来代表企业普遍的高管薪酬水平。该衡量计算公式如下:
高管股权激励(MSR)=(高管持股数*股票价格*1%)/(薪酬最高的三名高管的薪酬和+高管持股数*股票价格*1%)
为控制其他因素对企业避税产生的影响,笔者选用了公司治理因素、企业规模、经营盈利能力、负债水平、非负债税盾以及在职消费作为控制变量。
2.模型设计

模型中MSR 为高管股权激励水平,FSR 为大股东控制权,MSR*FSR 为交互项,control 为控制变量向量组。
三、实证分析
1.样本的选取
笔者选用2013-2018 年为数据样本时间区间,但是为了数据更准确,更具有说服力,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了处理,分别剔除了以下几个部分:(1)ST与PT 企业,(2)近5 年中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非无保留的上市企业,(3)信息缺失,数据不全面的上市企业,(4)金融保险企业,(5)存在极端值的上市企业。经处理后得到样本观测值4190 个。
2.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
为了验证假设1,最小二乘回归法回归结果见表1。首先,从民营上市企业的回归结果中可以明显发现,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避税水平呈负相关关系,并在1%水平上显著。

表1 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
文章相关的控制变量,如企业非债务税盾、盈利能力、高管在职消费都处于1%水平上和企业避税水平呈正相关关系,由此验证了假设1。
3.分位数回归分析
综合数据的分位数回归结果如表2 所示,交互项分别在0.1 分位点与0.9 分位点表现为负交互作用与正交互作用;在避税水平较弱的企业,大股东控制权负向调节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避税程度间的负相关关系。相反,在避税水平较为激进的企业中,大股东属于风险偏好者,大股东控制权会正向调节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避税程度的负相关关系。
综上,大股东控制权的调节效应在避税水平较弱与避税水平激进的企业中,它的调节作用与笔者的假设相一致,随即验证了假设2a 与假设2b。
笔者从公司控制权配置角度研究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所得税避税程度关系的影响,结合我国现有企业现实状况,即一股独大较为普遍的现象,选取了大股东控制权这个内因因素作为调节变量,试图从本质上解析其对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避税水平的调节作用。通过实证分析可以发现:第一,避税本身是税收收益与税收成本相权衡的过程,管理层会鉴于避税带来的业绩下降、声誉受损等原因,更倾向于投资收益大于或者等于避税收益的项目,以减少避税风险;因此高管股权激励的增加会减弱企业的避税水平。第二,在风险规避型企业中,大股东控制权正向调节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避税的负相关关系;而在风险偏好型企业中,大股东控制权负向调节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避税的负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