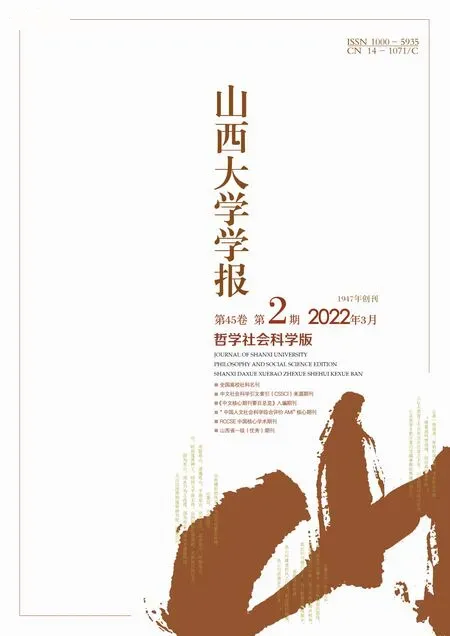文学阐释差异性的限度
寇鹏程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近年来有关阐释学的各种讨论成了中国文学理论界的一个热点。自从张江教授发表《强制阐释论》以来,国内一批老中青学者如朱立元、丁帆、王宁、周宪、高楠、陆扬、李春青、金惠敏、丁国旗、谷鹏飞、段吉方等都先后参与到这场阐释学的论争之中,一时间“中国阐释学”成了学界的一个热词(1)参见:张江.强制阐释论[J].文学评论,2014(6):5-18.论争涉及的其他论著,此处不再一一罗列。。中国文学理论界近年来像这样持续聚焦同一个问题的情景还不多见,阐释学是其中少有的焦点。学者们就强制阐释、理论的场外征用、前见与立场、文本角色、确定主题、普遍意义、阐释模式的统一性、公共阐释、阐释边界、“阐”“诠”之辨等有关阐释学的各种问题展开了精彩论述,把中国的阐释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这些讨论中,有一个问题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那就是如何控制文学阐释差异性的限度问题。不同读者对文学作品的阐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已是关于文学艺术的一个常识。问题的关键不是有没有差异,而是这个差异在多大范围内是合理的、正常的,多大范围内是不合理、不正常的呢?也就是说,这个差异到什么时候才是尽头呢?换言之,这个差异有没有限度呢?如果有,要怎么控制这个限度呢?我们能忍受的文学阐释差异的极限到底在哪里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阐释的巨大差异性
阐释对于文学作品来说非常重要。作品的价值固然在于作品本身艺术性与思想性的含量,但同时也来自对作品的阐释,因为作品还是那个作品,但对它的评价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甚至可以是截然不同的。阐释作品就是赋予作品以意义,一定程度上我们怎样阐释作品,作品就怎样存在,作品的命运会因为不同的阐释而像过山车一样跌宕起伏,既可能从无人问津到炙手可热,也可能从众星捧月到销声匿迹,同一部艺术作品的这样一种变化,很多时候是由于对作品的阐释造成的。
艺术史上因为不同的阐释而命运跌宕起伏的例子非常多。凡·高、高更生前作品无人赏识,他们自己也生活困顿,穷愁潦倒,要靠亲戚朋友接济才能勉强过活。但是现在他们都被看作是现代绘画的艺术大师,作品被人们争相抢购,一件作品动辄就能卖到上千万美元。司汤达的《红与黑》刚出版时,无人问津,社会评价低迷,出版商怕亏本,一共才印刷了750本。而现在司汤达已经成为19世纪法国文学的代表人物,成为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而另一些大师的经典之作还一度被列为禁书或被法院起诉,比如雨果的作品就被沙皇列为禁书,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以及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都曾被法院起诉。中国也是一样,我们今天视为经典的《诗经》《尚书》《论语》《孟子》《庄子》《山海经》等在秦代都是禁书,甚至在商鞅变法中被付之一炬。《红楼梦》《西厢记》《牡丹亭》《水浒传》等在清朝也都是禁书。而张爱玲、沈从文、周作人、朱光潜、徐志摩等人的作品曾因被批评为只是形式主义的落后之作而束之高阁,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们的作品却逐渐红火起来,几乎都成了畅销书。当其被禁之时,这些作品还是这些作品,但被当时人们看来价值不大,或者只有反面的价值,而现在却都成了受人追捧的名著。作品本身没有任何改变,但其价值却有了很大的变化,这是不同阐释的结果。
上述现象是艺术作品由于我们的重新阐释而从“冷宫”被发掘出来,变得大红大紫;还有一种现象是一些作品一开始被给予极高的评价,后来却由于阐释标准的变化而一下子从高处掉入冰窟。电影《武训传》刚上映时盛况空前,上海、北京和各地的报刊都对此片作了高度的评价,但随后却掀起了一场全国范围内对《武训传》的批评,这部电影也从一部艺术精品变成了一个反面教材。而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海河边上》也有过类似的命运,作品刚一发表的时候引起轰动,被认为是新中国文坛第一只报春的燕子,宣告了中国文坛一个反映新生活、塑造新典型时代的到来。当时各种报刊纷纷转载,《海河边上》还被一些地方团组织定为团员课本或必读书,《我们夫妇之间》也被搬上了银幕。但是两部作品很快就遭到了一致性的批评,一时间萧也牧的小说成了众矢之的,那些曾经高度赞扬萧也牧的人也开始检讨,重新评价萧也牧的小说。像这样红极一时而又迅速跌落神坛的文艺作品在文学史上是很多的。那么作品本身并没有什么变化,为什么会有这样截然相反的评价呢?这只能是我们阐释的标准发生了变化的缘故。
想让文学阐释从古到今或者不同的读者之间没有差异是不可能的,问题的关键只能是这样的差异要控制在什么范围之内才是合理的?要不要规约这种差异性,又怎样规约这种差异性呢?文学作品的阐释存在着差异并不稀奇,因为读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前理解”与“期待视野”,而文学作品本身也是富于修辞的“召唤结构”,存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含蓄蕴藉,余味曲包,有很多的“空白”等待读者去“具体化”。这样,每个人面临同样的作品时都是一个“视界交融”的过程,得出的结论势必不尽相同,在这一点上大家并不存在争议。需要思考的是,既然每个人都可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阐释作品,那么每个人得出的结论是不是都有同等价值呢?如果允许阐释的差异性无限扩大,每一个个别的阐释都具有同等价值的话,那么将只有差异性而没有共同性,人们之间就会无法实现交流共鸣,每个阐释也将是自说自话,这样的阐释也必将是无效的阐释。因此,这个差异性就必须控制在某一个范围之内。那么,怎样控制这个阐释的差异性?解决这个差异性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二、作者原意控制着差异性的限度
在传统文论中,解决这种阐释差异性的一个重要标准是作者的原意。阐释者都以寻求作者的原意为目标,符合作者原意或者最接近作者原意的解释就是最好的,如我们通过知人论世来以意逆志,通过笺注传疏来寻求作者原意。这确实可以引导阐释减少差异性,把目光都集中到作者的原意上来。20世纪的读者反应批评为了反对接受美学中个人解读的泛滥与“误读”,提出了“保卫作者”的命题,就是要求作品解读以作者的原意为基础。但是这里也有很多问题。
第一,作者否定读者所阐释的意图。我们通过各种方法好不容易寻找到的作者原意,作者却说他根本没有这个意思。茅盾在《从牯岭到东京》中就指出:“对于《幻灭》,有人说这是描写恋爱与革命之冲突,又有人说这是写小资产阶级对于革命的动摇。我现在真诚地说,两者都不是我的本意。”[1]针对有人把胡国光当作《动摇》的主人公,以为这篇小说是对于机会主义的攻击,茅盾说自己听来非常诧异,因为他写这篇小说的时候,自始至终头脑里没有“机会主义”这四个字。读者的解释让作者都感到很“诧异”,那我们寻找的作者意图不是非常尴尬了吗?赵树理的《邪不压正》发表后,评论者以为作品的主题是软英和小宝的婚姻问题,但赵树理在回应这些评论的《关于〈邪不压正〉》中却说自己的真正意图是:“想写出当时当地土改全部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使土改中的干部和群众读了知所趋避”[2]94,根本不是什么恋爱故事。像这样的例子在中外文学史上是很多的。屠格涅夫发表《前夜》后,评论家杜勃罗留波夫非常兴奋,认为这是对俄国革命“前夜”的寓言。但屠格涅夫认为自己根本没有这样的意思,并要求《现代人》杂志不要发表杜勃罗留波夫的这篇评论,如果发表就要断绝和杂志主编涅克拉索夫的关系。涅克拉索夫最后不顾屠格涅夫的反对,还是发表了杜勃罗留波夫的论文,而屠格涅夫也真的断绝了和涅克拉索夫的关系。可见读者费尽心机去阐释作者之意,但作者却不以为然。
第二,作者的意图无从求证。当作者还活着的时候,他可以现场否认读者的阐释并不是他的本意,但是当作者已经死去,并没有留下任何关于作品意图的材料,那如何确定作者的意图呢?我们通过书中人物的种种言行等蛛丝马迹来按图索骥推测作者的意图其实并不可靠。比如俞平伯先生从探求《红楼梦》的主观意图出发,认为《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全书实质是色空观念,用贾宝玉的言行来证明曹雪芹就是贾宝玉,贾宝玉就是曹雪芹,《红楼梦》乃是一部情场忏悔之作。但是在对自己的研究进行初步反思检讨后,俞先生本人也疑惑道:“我自命为了解作者真意的一个人,但究竟我有没有了解他的真意呢?我所谓原作的庐山真面目,到底是不是庐山真面呢?”[3]俞先生指出,很明显书中人物宝玉的想法,不必等于作者曹雪芹的想法,《红楼梦》有多少色空观念,也不等于曹雪芹有同样的色空观念,贾宝玉虽然做了和尚,但曹雪芹并没有做和尚,因此用贾宝玉的种种言行去探求作者的意图是不可靠的。正如茅盾先生曾经指出过的那样:“如果把书中人物的‘落伍’就认作是著作的‘落伍’,或竟是著作者的‘落伍’,那么,描写强盗的小说家就是强盗了么?”[4]由此看来,我们通过种种索引考证得出的作者意图,很多时候也只是自说自话、比较牵强的,究竟是不是作者原意,其实难以求证。
第三,作者并没有明确的意图。文学作品与政论文章并不相同,作者的意图很多时候本来就是含混的,并不是那么明确唯一。作家在创作时往往只有一个大致的意图方向,有时甚至自己也并不是很清楚,他并不是主题先行地对意图进行形象化图解,不是先有“一般”再去找“个别”。在柏拉图看来,诗人是失去平常的理智而“代神立言”,而弗洛伊德则认为艺术作品是作者无意识的转移与升华,是作者的“白日梦”,作者对自己说了什么也不是全部清楚。且不说这种神秘的无意识创作,就是从通常所说的理性创作的创作实践来看,文学家的意图很多时候也具有模糊性。郭沫若在谈到自己写《凤凰涅槃》的时候说:“伏在枕头上作寒作冷,连牙关都在打颤,就那样把那首奇怪的诗写了出来。”[5]写出的诗作者自己都觉得“奇怪”,可见文学作品并不是机械复制作者的构思。在谈到《雷雨》的主题时,有的人说是宗教性的,有的人说是家庭性的,有的人说是人性的,有的人说是社会性的,等等,而曹禺自己觉得这些都是自己的意图,也都不是,自己创作的时候并没有一个绝对清晰的目的。而且作者的意图在创作过程中也往往会发生变化,如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时,最初要把安娜写成邪恶和淫乱的化身,但小说实际上远远超出了原先的狭窄范围,变得非常复杂了,托尔斯泰自己明显动摇于恶与罪如何处理的问题上,可见作者意图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客体。
第四,作者的意图束缚不了读者的创造。那么,作者明确表明了自己意图的作品,作者的意图是不是就是读者阐释的最后标准呢?读者是不是就被束缚住手脚了呢?新批评派认为,以作者的意图作为阐释作品的标准是犯了“意图谬误”的错误,作者有明确的意图,但在作品中未必就明确表达出来,作者没有的意图,作品本身未必就没有包含。所谓形象大于思维,语言、叙事本身的张力会使作者原意变形甚至扭曲,作品内蕴会大于或者小于作者的原意,作者意图与表达效果之间并不是完全重合的。而且作品一旦面世,作者自己也只是一个读者,所谓“作者死了”,作者无权对自己的作品指手画脚。赵树理写《邪不压正》的意图是想写出当时当地土改全部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但是赵树理也指出自己所谓的意图“说的是自己主观上的意图和安排,至于客观效果与主观愿望相差多远,我一时还得不出准确的结论”[2]97。也就是说,作者主观上想的是一回事,而在作品里表现出来的客观效果如何,作者自己也“得不出准确的结论”,读者完全可以从作品本身的字里行间、故事情节、结构修辞里发掘出作品超乎作者意图的意义来。同时,每一个读者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各自主体情况千差万别,自然会带着自身的“前见”来“妙悟”作品,其主观性、能动性与创造性表现在作品阐释上,阐释结果必然会与作者原意之间有一定的差异。由此看来,作者意图是控制阐释差异性的一个重要参考标准,但是作者原意对读者阐释差异性的控制是有限的,如果只以作者的意图来作为阐释文学作品的标准,那它作为控制或者消弭阐释差异性的根据在理论和实践中都难以实现。
三、文本控制着差异性的限度
除了作者原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控制阐释的一些差异性之外,文本本身对阐释的差异性也有一定的控制。阐释作品的差异性之所以不至于无限大,还因为我们都基于同一部作品。文学阐释固然是我见青山,但同时也必然是青山见我,以我观文本,也要以文本观我。
第一,阐释必须是文本基础上的阐释。文学阐释的依据应该奠基于作品文本,文本是意义阐释的源泉和出发点,不能离开文本夸夸其谈、任意发挥,这会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差异性的范围,使这种差异保持在一定的限度之内。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毕竟还都是哈姆雷特,不会一千个读者读了《哈姆雷特》却有一千个孙悟空,文本是阐释相对稳定的基本保障。文本中的哪怕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可能都大有深意,增一字减一字其意义大为不同。欧阳修写《相州昼锦堂记》一文时,将诗句“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改成“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前后两个文本看上去只是增加了一个虚词“而”,但将相风范的那种从容不迫却在这个虚词上面得到了充分体现,文章的气势节奏也因此大为不同了。再如将“古道西风瘦马”改成“古道西风骏马”,其意义完全两样。中国古代特别重视炼字,很多诗人作家“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精雕细琢文本,留下许多“一字之师”的佳话。阐释的创造性正是要把文本背后的这种精妙之意阐释出来,而阐释的差异性也正是来自文本的这种高超艺术。为了强调文本的重要性,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以及结构主义都强调文学阐释要与作者、世界及其他读者脱钩,认为只在作品内部就可以获得作品的意义,如果以作者意图为参照,就犯了“意图谬误”,如果以读者反应为参照,就犯了“动情谬误”,他们不关心文本之外的世界而专注于文本本身。这种纯粹的“内部研究”确实强调了文本的第一性,保证了阐释都围绕着文本展开,这对于控制阐释的差异性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二,脱离文本的阐释差异是非正常差异。文学文本本身常常一字褒贬,微言大义,意义精微,所谓文学阐释的差异应该与文本背后的这种蕴藏的深意相关而不是穿凿附会地任意罗织意义。但是在阐释的实践过程中,脱离文本的非正常阐释却时不时地搅扰着文坛,比如“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这样的诗句竟被阐释为嘲笑清朝,作者因此而被处死。这种文字狱式的阐释与我们一般的文学阐释之间有着天壤之别,是非正常的差异。古代文学史上这种非正常的阐释差异还不少,它们在作家的作品里捕风捉影地给作家构陷各种罪名,这不是文学阐释差异性的表现,而是别有用心地利用文学作品达到某种目的的错误做法。比如杨恽腰斩案、苏东坡乌台诗案、戴名世《南山集》案,等等,其作品被判大逆不道、讥讽朝政等,已不是文学阐释而是一种政治话语的权力斗争,很可能对文学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从文学史上众多文案的案例来看,要关起门来做纯粹文本的内部研究往往是很困难的,文学阐释常常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外部要素联系在一起,从而产生更加复杂的阐释环境。这种外部阐释虽然是非正常的阐释,但却又是难以完全杜绝的阐释。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文学圈内部的阐释者不看文本就进行阐释的现象也时不时存在,这种阐释造成的差异也是非正常的。没有看过对方的作品却堂而皇之批判起对方来,这种完全脱离文本的阐释,其阐释的合理性、可靠性就值得怀疑了,由此产生的阐释差异性是非正常差异。作家阎连科曾经批评有些批评家不看作家的作品就开始评论作品,没想到有批评家还反诘说:“你们作家不看书一写就是几万字,几十万字,一拿就是一大笔稿费,凭什么要求评论家一看就是几万字、几十万字、上百万字,一写也就几百字、上千字、一万多字,辛辛苦苦就拿几包烟钱?”[6]从中可以看出不看作品就进行文学批评阐释的现象现实中依然存在。这样不看原著而做出的阐释与评判,其随意性自然很大,如果都不看原作就开始阐释,阐释之间的差异性自然就不可控了,文学阐释完全成了“庄子注我”,那么这种阐释的共性也就比较薄弱。可见很多时候文学阐释的差异性是没有真正以作品为基础造成的,要控制阐释的差异性就必须真正以作品的文本为基础,要以“保卫文本”为第一性,而尊重文本是差异合理的先决条件。
第三,文本本身的差异导致的阐释差异。当然文本本身也是非常复杂的,这也会带来阐释的差异性。作家的草稿、手稿、家人朋友的抄本,出版的初版、删节版、修订版以及更多版本的文本都是“阅读副本”,正如斯蒂林格在《多重作者与孤独天才的神话》中指出的:“一部作品的印刷文本通常是许多参与者的共同产物,除了人们通常视为其唯一作者的人之外,还包括朋友、家人、誊写人、文稿代理人、编辑、出版商等。”[7]在这众多参与者以及众多版本的文本汇总中如何确定最可靠的、最权威的“理想文本”,本身也是一项有差异性的工作。老舍在谈到自己的《骆驼祥子》时说:“此书在广州印成单行本,或者还在桂林印过,我都没有看到,因为广州桂林也相继陷落敌手,大概此书也被敌人毁灭了。我看到的‘初版’是在四川印的土纸本。”[8]由于特殊原因,印出来的作品作者自己都没有看到,这样的文本可靠性究竟怎么样,自然有值得怀疑的地方。而《骆驼祥子》在《宇宙风》杂志发表后,又有1939年人间书屋发行的版本,1941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版本,以及1950年上海晨光出版公司版,1951年开明书店版,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等等。这些不同版本的《骆驼祥子》,其文本本身就有着很多差异,比如1955年版的《骆驼祥子》就修改了初版中的90多处,删除了一些与性描写有关的内容以及阮明的故事和祥子的堕落等情节。作者本人不断修订自己的文本,再加上出版时的种种原因,造成同一个文本不同版本之间存在着差异,在文学界是一种常见现象。这种由文本本身的差异引起的阐释差异是难以避免的,也是正常的。
第四,文本的意义结构导致阐释的差异。文学文本本身的意义结构是多层次的,有物质实在层,也有形式符号层;有意象意蕴层,也有哲学超验层;有表层的意义,也有深层的甚至神秘的意蕴,所以文本本身也是多义的,不可能依靠文本来杜绝阐释的差异性。但丁在阐释《神曲》时就指出它有多重意义:“第一种意义是单从字面上来的,第二种意义是从文字所指的事物来的;前一种叫字面的意义,后一种叫做寓言的,精神哲学的或者秘奥的意义。”[9]而波兰当代美学家英伽登则指出文学文本的多层次构造包含四个层次:“(1)字音及其高一级的语音组合;(2)意义单元;(3)多重图式化方面;(4)再现客体。”[10]
总之,文学文本本身是一个多重意义的客体,这也必然带来一定的阐释差异性。同时,文本即使固定,但阐释者本人的个人经历、教育水平、审美趣味、审美经验等各不相同,其做出的阐释也必然是有差异的。所以,文本只是控制阐释差异的一个要素,希望单靠文本来终结阐释的差异性也是不可能的。
四、公共理性控制着阐释差异性的限度
除了作者原意、文本本身可以部分控制阐释的差异性之外,还可以用什么来控制这个差异呢?还有公共理性与个人理性(2)关于公共阐释本身,参见:张江.公共阐释论纲[J].学术研究,2017(6):1-5.。文学阐释的公共理性包括时代文明的总体认知程度、时代总体的审美范式、理想读者群、时代权力话语等。
第一,时代文明的总体认知程度控制着差异的范围。任何一个人总是生活在具体的历史时代的,他是当时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时代思想意识形态的总体认知水平,每一个时代的阐释者只可能在自己时代文明程度的阈限范围之内进行阐释。“地球中心说”时代的人们阐释世界之间的差异都是在地球为中心的前提下的差异,而当有阐释者不以地球为中心而以太阳为中心,那就意味着一场革命的到来,意味着时代整体认知范式的变革。中世纪文学阐释的中心就是人们的言行是否符合上帝的旨意,而文艺复兴阐释的中心是人的爱欲的合法性,现代主义阐释的中心是科学压抑下的个性,而后现代主义则阐释意义的虚无,这种时代总体精神气候下的个人阐释虽各有差异,但却有时代共同精神的影子,这保证了每一个时代的阐释差异性不会是无限大的。1917年,当杜尚把一个被翻倒放置在底座上的小便池送到卢浮宫展览时,完全是惊世骇俗的行为,但到了20世纪末,他的这件被命名为“泉”的作品却已然被看作世界上影响最大的现代艺术品。达利就曾经说,在早些时候的巴黎只有17个人懂得杜尚,“现在”有1 700万人懂得了杜尚;当然到我们现在懂得的人就更多了。这种对《泉》的阐释差异是受时代整体认知水平变化的控制的,是合理的。只要时代整体认知水平发生了变化,我们的阐释也会随之变化。个体阐释的差异与时代整体认知水平的变化成正相关的关系。
这里的关键就是个体的阐释往往就是时代精神的显现。无论是文学的创作、欣赏还是批评阐释,首先都是个人的创造性工作,因此文学艺术的千古之谜就是个别的如何具有普遍的意义。康德讲的“判断力”就是将个别归于一般的能力,他认为既然大家都是“人”,那么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们先天就具有共同的人性,个别人也就和所有人有了共性。黑格尔用具体情境与一般世界情况来串联个别与一般;海德格尔用“亲在”与“共在”把个人此在与群体连在一起;荣格用“集体无意识”把个人和其他人的共性连在了一起;而马克思则用社会关系把个人和其他人连在了一起,这样个人的也就是集体的,集体的也就在个人身上显现出来了。无论这些思想家提供的解决个性与共性分歧的方式是什么,它都启示我们个人不可能与时代共同体分离,两者之间是有“共在”的和可“通约”的地方的。因此,这种社会与时代的共性决定了阐释不可能是毫无共性的。
第二,时代审美的总体范式控制着差异的范围。对于文学艺术来说,每个时代都有自己总体的审美认知范式,这决定着人们对这一时代艺术作品的整体阐释方向。即以我们熟悉的凡·高、高更来说,并不是有人要故意摧残贬低他们,而是因为当时人们整体的审美范式还是古典美学的和谐整一、优美悦目而不是躁动灵魂的狂放不羁,因此人们欣赏安格尔而对凡·高的评价不高,不接受他,这是合理的。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现代工业文明的大发展,现代性的压抑与异化加强,非理性思潮膨胀,个人内在心灵的狂放表达逐渐成为时代之声,凡·高那种艺术方式被新时代的审美范式接纳,由此他也就身价倍增。这是由于时代整体的审美价值范式的差异所导致的对凡·高阐释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对于各自不同的时代审美范式而言,却是正常的。再如陶渊明,在其所处的东晋以至南北朝后很长时间,人们对他的评价并不高,钟嵘《诗品》只将其列为中品,刘勰《文心雕龙》虽然提到各类文人名字300多人,但却自始至终没有提到陶渊明,只是到了宋朝,陶渊明才受到追捧,变成了上上品。这种差异仍然是时代审美范式差异的结果,并不是某个人的翻云覆雨。南北朝崇尚“绮丽华美”的骈文与“宫体诗”,这时候清新淡远的陶渊明自然是个异类,对他的评价也不可能高;而宋朝则崇尚淡雅虚空,平淡高远,对陶渊明的阐释也就顺理成章走高了。这是在时代总体审美范式之下的差异阐释,是在合理范围之内的差异。个体阐释的差异与时代整体审美范式的变化成正相关的关系。
第三,阐释者的理想群体控制着差异的范围。虽然面对一部文学作品,人人都可以是一个阐释者,但有的人是文学的理想阐释者,而有的人却是文学的陌生人。文学的理想阐释者群体的阐释是保证作品阐释正确与否的重要力量,担负着维护阐释稳定、合其正轨的职责与使命,对于控制文学阐释差异性的范围来说尤其重要。文学的所谓“理想阐释者”就是积淀了丰富的文学史知识与文学审美经验,懂得文学规律的人,比如声誉卓著的作家、文学批评家,高校的文学教授、学生,人文学者以及其他文学工作者。懂得文学的这一群体就是文学阐释的理想群体,他们的审美趣味、审美辨识能力、审美经验是一个作品能够保持其应有文学价值的“压舱石”与“校正器”,他们的阐释具有方向的引导性,他们是防止对文学进行任意阐释或者恶意阐释的约束性力量。对于什么是文学的,什么不是文学的,这个理想的文学阐释群体凭其经验往往可以一眼即见,乔治·迪基说“艺术即习俗”,杜威认为“艺术即经验”就是这个意思。这个理想读者群的阐释具有相对集中性和稳定性,它可以调节、修正、改变那些任意的、非文学的差异阐释,可以批评把《红楼梦》当作药方的做法,可以防止文学内的兴风作浪,使阐释的差异性保持在一定的限度之内,使其不至于太偏离作品本身。理想读者群的阐释是保持文学阐释正常前进的重要力量与标尺,在控制阐释的差异性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他们是文学正义的主要力量。左思的《三都赋》写成后反应平平,而被文坛泰斗皇甫谧推荐后却一时“洛阳纸贵”;刘勰写成《文心雕龙》后仍寂寂无闻,而经沈约夸赞后却一下声誉鹊起,这说明理想读者的阐释会被大众尊崇和认同。理想读者对于发掘、保障文学的价值至关重要,因此,要特别重视理想读者的阐释。
但是如果不幸这个理想读者群中的成员不按照文学自身的规律来阐释文学,不是按照自己的文学经验来正常阐释文学,而是由于种种原因曲解作品,那么对文学的伤害将会非常大,将会成倍增加文学阐释的混乱,使其偏离正常的文学阐释方向。比如在“乌台诗案”中,恰恰就是那一群最懂诗歌的文人组织成一个庞大的团队,处心积虑收罗苏轼的诗歌,牵强附会一定要从中找到罪证,这与正常的阐释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对于文学的恶劣影响非常深远。所谓“堡垒最易从内部攻破”即是此意。在轰动一时的对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的批评中,湖畔派大诗人、深谙文学之道的冯雪峰竟然化名为李定中首先发难,批评萧也牧的作品散布低级趣味,认为作者是小资产阶级,应该去改造。(3)冯雪峰在《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中说:“假如作者萧也牧同志真的也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分子,那么,他还是一个最坏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冯雪峰.冯雪峰论文集:中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18.而且冯雪峰还在文章中说自己对于文艺理论平日缺少研究,甚至一窍不通,以此掩藏自己的身份,这说明他对自己这种大棒批评的非正常性还是有所认识的。试想,假如不以“李定中”而是以“冯雪峰”的大名发表这篇评论,一定会是另一番情景,因为“冯雪峰”已经是一个理想读者的符号,而“李定中”则是一个可以对文学任意言说的门外汉,“门外汉”可以任意言说,“理想读者”却不能,理想读者有自己的约束力,这是冯雪峰要用李定中这个笔名的深层次原因。像冯雪峰这样的“理想读者”不会真的不懂得《我们夫妇之间》作为文学作品的价值,他之所以要那样批评《我们夫妇之间》,说明他偏离了自己作为“理想读者”的身份或者完全出于非文学的动机而为。理想读者造成的这种差异性与偏离尤其值得关注,因为理想读者本身影响力大,这种偏离造成的恶劣影响就更大。所以即使是所谓的理想读者的阐释之间也往往会有很大偏差,只依靠他们来控制阐释的差异性也是不全面的。
第四,时代特定的话语权控制着差异的范围。控制着文学阐释差异性的范围,使其固定在一定限度之内的还有当时时代特定的话语权,特别是同时代的政治话语权对于文学阐释的差异性具有巨大的约束作用。文学是一种精神形态,是属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它虽然也受生产力水平、经济基础的影响,但更直接地受上层建筑的政治、哲学、宗教、法律等的影响。同一时代的政治话语权直接影响着文学阐释差异性的范围,引导文学阐释的方向,压缩阐释的空间,使这种差异不至于任意扩大。如清朝实行严苛的文字狱,文学阐释的空间极其有限,因此文学阐释的差异性就不大,其活跃程度也就有限。再比如假如整个时代整体的价值话语是阶级革命话语,强调阶级之间的差异与斗争,而人情论、人性论、共鸣论的文学阐释就偏离了这一方向,那么这种有悖于时代整体价值范式的阐释就会受到强势话语的批判与引导。通过批判,那些异于时代整体价值话语的阐释逐渐式微,阐释的差异性也会逐渐缩小,所有的阐释又会围绕在核心话语周围。当然,言为心声,书为心画,文学艺术本来是言志缘情的,时代的话语权虽然可以控制压抑一些不同的阐释,但这种一体化也不利于文学的多样化与创新,一些挑战这种单一强势话语的新阐释还是会不断出现。比如晚清各种侠邪小说、言情小说、公案小说、黑幕小说等就是冲决清朝严苛文字狱的新文学,浪漫主义就是冲决古典主义权威话语的文学新阐释,这些新阐释会逐渐挣脱特定话语权的束缚而滋生更多新思想,从而又会诞生出新的阐释模式。所以单靠特定话语权来控制阐释的差异是不可能的,同时也不利于文学的创新发展。
第五,个人理性控制着阐释的差异。文学阐释活动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个人创造在阐释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这个个人创造不是感性冲动的意气用事,不是利欲熏心的任意妄为,而是遵从个人理性良知来阐释作品。如果每个人都按照理性要求来阐释作品,文学阐释的差异性就会受到一定的控制,所以个人理性也是控制文学阐释差异性的一股重要力量。那么什么是个人理性呢?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说:“要这样行动,使得你的意志的准则任何时候都能同时被看作一个普遍立法的原则。”[11]也就是说我们的行为是个人的意志,但这个个人意志同时就是符合普遍意志的,个人精神同时就是符合集体精神的,这样的行动原则就是个人理性原则。个人理性的得来不管是经验变先验,历史建理性,还是心理成本体,总之它要求阐释者按照文学的规律,遵守道德的律令,保持高尚的情操,无私于轻重,不偏于爱憎,以追求真理、阐发思想为宗旨来进行文学阐释,这对于个人理性而言应是一个不虑而知的前提。陈寅恪在王国维的墓志铭中说,知识分子读书治学追求的是“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而发扬真理,他赞扬的王国维的自由思想与独立精神这种品质就是个人理性的内涵。别林斯基对果戈理的早期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但是当果戈理晚年发表了有落后保守思想的《与友人书信选集》时,别林斯基又毫不犹豫地发表公开信批评果戈理,别林斯基的阐释就是遵从个人理性的阐释。文学阐释者遵从个人理性的声音,坚持真理而不屈从于流俗,像屈原那样“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12]正是每一个阐释者应有的品格,只有这样才能对艺术负责,对读者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巴金晚年在《随想录》中对自己有一段时间随波逐流的文学表现表示了反思,他批评自己没有独立的思考:“别人‘高举’,我就‘紧跟’。”[13]巴金的这种反思精神正是我们每一个文学阐释者需要的个人理性精神,这种精神也会控制我们对文学文本的随意化阐释,以这种精神进行阐释,文学阐释的差异性就会受到一定的控制。当然,仅靠个人理性来控制文学阐释的差异性显然是不可能的。且不说个人会变心变节或受外界的诱惑与压迫而放弃原则随波逐流,宗派主义、利益至上会导致文学阐释差异混乱,即使一个人完全坚持个人理性,忠于艺术,刚正不阿阐释文学,但是由于个人的境界水平有限,同时个人与整个文学世界的力量相比势单力薄,单靠个人理性来力挽狂澜控制文学阐释的差异性也是不现实的。
五、限度内的差异
可以看出,作者原意、文本本身、时代整体的认知水平、时代整体的审美范式、理想读者群体、时代话语、个人理性等要素是控制文学阐释差异性的主要力量,但是任何一种单一的力量都不是文学合理阐释的唯一力量,文学阐释保持在合理差异限度内是这些力量之间的相互制衡,正是在这些要素的动态平衡之中才使得文学阐释的差异性不会走向任意性的混乱。如果只有一种要素起绝对的支配作用,那么文学阐释的差异性就不会大,但文学阐释的创造性和多样性会因此受到限制,这样的阐释往往会陷入机械主义之中。而文学阐释的实质是合理限度内的差异性阐释,只有在这些要素控制下的差异性阐释才能既发挥文学的创造性,又不至于产生虚无与混乱,文学阐释的空间与自由正是在这种限度之内的空间与自由。理想的阐释正是在文学各要素力量动态制衡下的阐释,如果各种力量之间比较平稳,这时候的阐释可能就比较平和;如果这些力量之间失衡了,只有某一种力量占据绝对中心的位置,那么阐释之间就可能没有差异或者出现巨大的差异。那种单纯的文本至上、作者至上、读者至上或者影响至上等阐释原则,或者单纯强调“作者死了”“读者死了”等都是不全面的。因此建立从作者原意、文学文本到时代话语、时代审美范式、理想读者以及个人创造之间的动态协调机制,维护各要素之间的力量平衡,是文学阐释的一个重要任务。
从文学阐释的实践来看,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来简单规定文学阐释的唯一答案,而应该以文学文本为基础,以作者原意为参照,以时代整体认知水平与审美范式为指导,发挥理想读者群的创造性,调动阐释者个人的审美积极性,以此进行文学阐释的交流与对话,这才是文学阐释的理想模态。这种由各要素组成的动态平衡的阐释圈就是文学阐释的生态,在这个生态中,文本是底线,由时代认知水平与时代审美范式构筑起来的时代理性是极限,由其他各要素力量相辅相成形成一个生态系统。在这样的阐释生态下产生的差异性是正常的差异,有效的差异,是可以接受的;脱离这种生态的别有用心的阐释差异是非正常的差异,无效的差异,应该排除在正常的文学阐释之外。良好的阐释生态是保证文学阐释合理差异的基石,突破底线和极限的文学阐释是我们难以接受的。如果说对于时代整体认知、时代审美范式、时代话语权、作者原意、文本本身、理想读者群等,我们作为单个的阐释者不能立刻改变,但是我们作为一个理想的读者可以控制我们自己,可以要求自己真正按照文学的方式阐释文学,遵守文学的规律,在文学内部阐释文学,可以要求自己按照时代公共理性与个人理性的原则阐释文学,这样阐释即使差异性很大,但对文学本身不会造成致命的伤害,同时对其他文学阐释者也不会造成伤害,因此不会破坏文学阐释的生态。这种限度内的差异才是我们所需要的,才是文学阐释的创新。
对于限度内的阐释差异我们要持开放的态度,不可简单地把差异等同于异端,只要是差异限度内的文学阐释,我们就应当欢迎,从而共同维护良好的文学阐释生态。比如对《红楼梦》的阐释,有的说是自叙传,有的说是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有的说是爱情故事,有的说是人生悲剧,有的做索引,有的做考证……其实只要根据文本,有理有据地就文学论文学,无论怎样新奇不同的差异都可聊备一说,不必盲目拒之于千里之外。有人说贾敬就是嘉靖;有人说《红楼梦》中的“花”代表着明朝,因为“花”是红色的,“红”即“朱”,而“朱”为明朝的国姓,《葬花词》就是悼念明朝的一篇祭文;有人说蘅芜苑里的“水上落花”喻指清军铁骑下大明百姓的尸骨,而蘅芜苑里的“朱栏板桥”的“朱”就是指明朝国姓的“朱”,“板”就是“反”“木”,暗指反叛明朝的吴三桂等人;有人说宝钗影射清朝,黛玉影射明朝,宝玉影射国脉,宝钗扑蝶扑的那对玉色蝴蝶就是黛玉和宝玉,就是隐喻清朝要扑灭明朝的国脉……像这样的阐释把《红楼梦》解读为反清复明的一部政治书,确实令人惊异,有的人为此非常气愤,有的人大骂这是过度阐释,是牵强附会,有的人觉得忍无可忍,认为这是亵渎《红楼梦》,已经达到我们能够忍受的文学阐释差异的极限了。实际上这种阐释的差异性对于《红楼梦》本身来说,不算什么十恶不赦,它还是奠基于文本之上的文本细读,并非毫无道理,还是在允许的限度之内的,还没有突破我们能够忍受的阐释《红楼梦》的底线,我们应该以宽容的态度与之对话,以另外的阐释与之进行竞争,而不能简单粗暴地将之视为异端,以仇视的态度对待合理的差异阐释。
蔡元培先生曾说对于文学的解读应是“多歧为贵,不取苟同”,只要不是为了不同而不同,不是单纯地想要惊世骇俗,不是为了打倒其他阐释者,只要言之有据,持之有故,都不必灭之而后快。只要把文学阐释交给文学,文学阐释言之成理的差异是应当受到尊重的,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毕竟不能没有差异。阐释限度内的差异是创新,差异限度之外的阐释则是对文学的伤害。作为理想读者群体内的一员,要欢迎并为这种限度内的差异性阐释而努力,以此扩张文学阐释的空间,丰富文学阐释的世界,推动文学阐释的创新,提升文学阐释的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