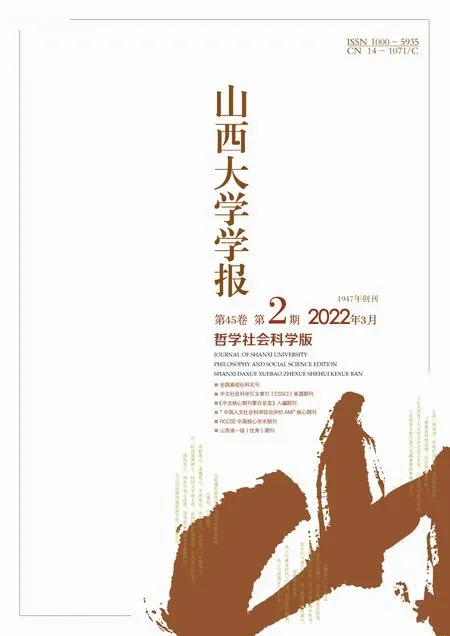21世纪语境中如何理解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
王凤才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433)
“现代性”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在21世纪语境中,如何理解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这是一个既有重大理论价值又有重要现实意义的问题。要想理解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第一步是要澄清什么是现代性;在此基础上,第二步是揭示人们对待现代性的不同立场;第三步是本文的重心,即具体分析马克思对待现代性的态度;最后,得出我们自己的结论。
一、什么是现代性?
关于现代性,可谓众说纷纭——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学者赋予“现代性”以不同含义,即使同一个时期、同一个国家,甚至同一个学者也会对“现代性”作出不同阐释;但有一点似乎是共同的,那就是都承认“现代性”与“现代”“现代化”密切相关。
当然,对于“现代”“现代化”也有各种不同阐释。关于“现代”(Neue Zeit/modern)一词的起源,不同人有不同说法。例如,在《历史研究》中,英国历史哲学家汤因比将人类历史(人类文明史)分为:黑暗时代(675—1075),中世纪(1075—1475),现代时期(1475—1875),后现代时期(1875—至今)。这样,“现代时期”就是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在《美学标准及对古代与现代之争的历史反思》中,接受美学创始人、德国美学家姚斯(Hans Robert Jauss)认为,“现代”一词最早出现在公元10世纪末,是指从古罗马帝国到基督教世界的过渡时期。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学术领袖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指出,最早出现于公元5世纪的“现代”(modernus)概念,在欧洲被反复使用——尽管在内容上有所不同,但都表达了一种新的时间意识,强调古今之间的“断裂”。可见,人们对“现代”概念的界定是不同的。
对于“现代”,尽管有不同看法,但主流观点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开启了西方文明的“新时代”(现代)。再严格一点说,从笛卡尔到黑格尔属于“现代早期”;黑格尔之后,西方世界进入了“现代后期”。至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后现代”,那也许并不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毋宁说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与“现代”相关联,“现代化”(Modernisierung/modernization)也有各种不同理解,但M.韦伯的理解几乎成为范本。在M.韦伯那里,现代化=合理化=解放+奴役(“铁的牢笼”);而艺术则具有两重性,即商品化+救赎性(“诸神纷争”)。在《交往行为理论》(1981)中,哈贝马斯说,虽然M.韦伯研究了合理性的不同形式,将合理性区分为形式/目的合理性和实质/价值合理性,将合理行为、合理生活指导与合理化世界观联系在一起,但在M.韦伯那里,目的合理性行为概念才是理解合理性概念的关键。因为他认为社会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与现代国家的分离,或曰社会现代化就是工具理性合理化,所以他并没有真正解决合理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既没有找到现代文明危机的根源,也没有指出通向未来文明的出路。鉴于此,要想恰当地解决M.韦伯提出的极为紧迫的社会合理化问题,那就需要一个交往行为理论[1]。
如果说“现代化”是一种客观发生的历史过程,那么“现代性”(Modernität/Modernity)就是对这个客观历史过程的逻辑概括。在《后民族状况——政治文集》(1998)中,哈贝马斯在谈到“现代性”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哲学话语时指出,17世纪后期,法国古典主义美学领域的“古今之争”,奠定了审美现代性观念的基础。自18世纪后期开始,“现代性”已经成为一个哲学话语。“现代性的自我理解不仅是通过理论的‘自我意识’、通过针对所有传统的自我批判立场刻画的,而且也是通过‘自我规定’和‘自我实现’的道德观念和伦理观念刻画的”。[2]199
其实,早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1985)中,哈贝马斯就将笛卡尔确立的主体性原则视为现代性的基本原则,同时断定这个原则使现代世界进步与异化并存。所以,哈贝马斯断定,关于现代性的最初探讨中就包含着对现代性的批判。18世纪末,黑格尔首先提出了现代性的自我批判与自我确证问题,创立了启蒙辩证法原则。而一旦有了这个原则,现代性的自我确证问题就能做到万变不离其宗。所以说,尽管黑格尔不是第一位现代哲学家,“却是第一个意识到现代性问题,并清楚阐释现代性概念的哲学家”[3]51。
可以看出,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界定,尽管与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批判理论家有所不同,但也继承了《启蒙辩证法》(1947)的基本精神。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阿多尔诺(Theodor W. Adorno)视阈中的启蒙纲领,就是使世界祛魅、消除神话,并用知识推翻幻想。在他们看来,启蒙并非专指西方文明中的理性精神;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启蒙追寻进步思维的目标,努力使人从恐惧中摆脱出来,并将人确立为(自然和社会的)主人。[4]
众所周知,《启蒙辩证法》的核心问题就是:为什么在科技进步、工业文明发展似乎可以给人们带来幸福的时候,在理性之光普照世界大地的时候,“人们没有进入真正的人性完善状态,而是深深地陷入了野蛮状态”[5]?在这里,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以人与自然关系为主线,以神话与启蒙关系为核心,对启蒙理性进行了深刻地批判。他们不仅揭示了“神话已经是启蒙,启蒙倒退为神话”的过程,而且阐明了启蒙精神的实现过程就是进步与倒退相交织、文明与野蛮相伴生的过程。因此,启蒙精神最终走向了自我毁灭。
如此一来,根据《启蒙辩证法》的精神实质,我们就可以将“现代性”内涵界定为:所谓启蒙现代性,就是一种以征服、支配自然为出发点,以科学知识万能、技术合理性至上为特征,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以历史进步为目标的文明乐观主义。简言之,启蒙现代性的核心价值就是理性至上、科技万能、个体中心、文明进步[6]。对于这样一种“现代性”,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除了激进地批判之外,似乎也没有其他的处理方式。从《启蒙辩证法》中,既可以看出本雅明对霍克海默、阿多尔诺的影响——“从来没有一座文明的丰碑不同时也是一份野蛮的文献”[7],也可以看到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对待“现代性”悲观立场的最终确立。
二、对待现代性的四种立场
在《后民族状况》中,哈贝马斯不仅考察了“现代”概念的历史演变,界定了“现代性”的内涵,还区分了现代性的两个传统。一是古典现代性概念(从黑格尔、马克思,经过M.韦伯、青年卢卡奇,一直到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在哈贝马斯看来,古典现代性概念立足于规训社会与被伤害的个体主体性之间的抽象对立,与总体化的理性批判纠缠在一起,因囿于意识哲学框架,最终走进了死胡同。二是语言哲学转向之后的现代性概念——这里又有两种不同的对待现代性的态度,即后现代主义的“告别现代性”和哈贝马斯本人的“重建现代性”[2]195。这样,在哈贝马斯视野里,对待现代性实际上有三种不同态度:(1)“古典现代性”——在这里,现代性的自我确证与自我批判结合在一起,即既坚持现代性又批判现代性,或者说,在“批判”现代性中“确证”现代性。因而甚至可以说,古典现代性观念,实质上就是“现代性批判”。(2)“告别现代性”——致力于现代性的规范自我理解的“克服”,从而从理性批判走向“理性的他者”(Das Andere der Vernunft)。(3)“重建现代性”——致力于对有歧义的古典现代性概念进行主体间性转化。
事实上,根据人们对待现代性的不同态度,我们可以区分出对待现代性的四种不同立场。
第一,坚持现代性(现代主义者)。现代主义者,尤其是现代自由主义者,大都坚持现代性,即承认启蒙现代性的核心价值——理性至上、科技万能、个体中心、文明进步;他们大都是理性主义者、科技进步主义者、个体中心主义者、文明乐观主义者。我们知道,自从文艺复兴尤其是启蒙运动以来,文明乐观主义或乐观主义文明论一直是近代西方文化的主流。例如,培根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成为肯定技术理性的启蒙精神的标志,在笛卡尔主义精神氛围中逐渐形成了一种进步理论;伏尔泰等人有着以科技理性重建文明社会的梦想;康德、尤其是黑格尔把人类理性推向了顶峰,并相信人类历史是不断进步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提出“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高度评价科学技术对社会历史进步的推动作用。此外,冯特奈尔、孔多塞、达尔文、斯宾塞、泰勒、摩尔根等人,也是文明乐观主义者。所谓文明乐观主义或乐观主义文明论,实际上就是文明进步论或文明进化论,它认为人类文明是不断进步的,科技进步就是文明进步。随着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生产工具越来越先进,生产力与经济发展越来越快,文明形式也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的不断转型,社会制度越来越合理,文化越来越发达,人们的生活质量越来越高。总之,人类文明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8]。
第二,告别现代性(后现代主义者)。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哈贝马斯说,在黑格尔之后,现代性话语出现了三个视角,即黑格尔左派、黑格尔右派和尼采。然而,无论黑格尔还是嫡传左派或右派,都未曾对现代性成就提出过严肃质疑。只有尼采试图打破西方理性主义框架,认定人们对现代性已经无可奈何,故尼采放弃了对主体理性的再修正,并放弃了启蒙辩证法原则。换言之,尼采依靠超越理性视阈的激进的理性批判,最终建立起了权力理论的现代性概念。哈贝马斯指出,自尼采开始,现代性话语的讨论局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此以后,现代性话语不再坚持解放内涵,并在两个方向上被发扬光大:一是从海德格尔到德里达;二是从巴塔耶到福柯。“如果说尼采打开了后现代的大门,那么海德格尔与巴塔耶则在尼采基础上开辟了两条通往后现代的路径。”[3]121然而,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经过尼采到海德格尔和德里达,或巴塔耶和福柯,对现代性的批判始终没有走出主体理性批判模式。主体理性以及自我意识结构只是理性的一个侧面,而非全部理性[9]。
第三,重建现代性(哈贝马斯)。在《时代诊断:12篇短论(1981—2001)》(2003)中,哈贝马斯豪迈地宣称,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规划,现代性还要继续发展,但是必须用政治意志和政治意识加以引导,因而需要对现代性话语进行重建[10]。正由于此,哈贝马斯被誉为“最后一个现代主义者”。当然,即使是哈贝马斯,也不免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冲击——他不仅讨论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兴起与发展问题,而且还说“要澄清常常被人忽视的交往行为理论的多元主义特质”[11]——“多元性”“相对性”“非确定性”,这正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些基本特征。
第四,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阿多尔诺)。在现代性问题上,阿多尔诺既不同于哈贝马斯,又不同于霍耐特: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规划”,试图重建现代性;霍耐特(Axel Honneth)则试图揭示现代性悖谬,因为现代性具有“社会病理学”(Pathologien des Sozialen)特征[12];阿多尔诺则试图解构现代性,因为现代性主要是指主体首要性、同一性逻辑、等价交换原则[13]。不过,在《美学理论》中,尽管阿多尔诺始终贯穿着非同一性思维的否定性这条主线,但他在强调现代艺术自主性的同时,也承认现代艺术的社会性。当然,面对异化的社会现实,模仿“自然美”的“艺术美”,即具有真实性的现代艺术的意义就在于,对异化的社会现实具有反思、批判、否定的功能。其实,在阿多尔诺的美学理论中,“现代主义”是一个主音符。就像维尔默(Albrecht Wellmer)所说,阿多尔诺对主体的批判已显露出后现代主义倾向,但与后现代主义的区别在于,二者对和解哲学的态度不同。在对和解哲学决定性拒绝这一点上,“后现代主义似乎比阿多尔诺略胜一筹”[14]99。当然,在阿多尔诺那里,和解哲学视角最终并非意味着反对非理性主义而捍卫理性主义,捍卫永不终结的辩证法。事实上,阿多尔诺的例子已经表明,对主体进行语言哲学的解中心化会迫使理性批判相对化:主体理性批判并不触及话语合理性,而是触及理性的某种不充分的、坏的或反常的使用。当然,相对化更多地意味着划界(只有在这个界限内,理性批判才有意义),而不是批判必要性的减弱,不是陷入形而上学或玩世不恭中。通过对有意义的理性批判划界,理性本身以及主体就又一次获得了机会。不过,这个机会与启蒙理性曾经(向理性与主体)许诺的那个机会不同。“那么,这究竟是什么样的机会呢?这是一个带着我又回到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问题。”[14]100
三、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
在马克思视阈中,“现代性”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科技理性,二是资本逻辑。对于前者,马克思基本上持肯定态度。在他那里,“现代性”=启蒙理性。“社会地控制自然力以便经济地加以利用,用人力兴建大规模的工程以便占有和驯服自然力,——这种必要性在产业史上起着最有决定性的作用。”[15]当然,他也看到了“现代性悖论”,即启蒙理性在带来历史进步的同时,也受到了工具理性的支配。“技术的胜利,似乎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16]对于后者,马克思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在他那里,“资本”是一个肮脏的东西。当然,他也看到了“资本”的积极作用,即“资本”瓦解了等级制和等级观念,催生了自由平等的“等价交换”和“自由平等”观念。
首先,马克思坚持现代性的基本价值理念,是一个理性主义者、科技进步主义者、文明乐观主义者,基于这个原因,他可以被归入现代主义者的阵营。例如,马克思明确提出“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高度评价科学技术对社会历史进步的推动作用,认为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说,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料想到用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对此,恩格斯做了精彩阐述:“没有一个人能像马克思那样,对任何领域的每个科学成就,不管它是否已实际运用,都感到真正的喜悦。但是他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17]
其次,马克思又不同于一般的现代主义者,尤其是不同于现代自由主义者。他反对自由主义者所信奉的个体中心主义,因而并非毫无保留地坚持现代性。在《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中,英国学者R.N.伯尔基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属于欧洲政治思想与社会理论传统中的主流,它是自由主义政治观念、社会观念、哲学观念的发展。也就是说,R.N.伯尔基认为,马克思主义发源于自由主义,它接受并改造了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念。因而,如果没有自由主义这一广阔的背景,马克思主义将是不可思议的,也将不会存在。虽然现代社会主义(理论和运动)的早期阶段在马克思主义成型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些社会主义的激进思想遗产仅仅是附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外在形式。至于马克思主义的内核或实质,恰恰是由欧洲文化主流传统(即自由主义)发展而来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现代政治激进主义的产物,它根本上回到了自由主义最早阶段的民主要求。对于R.N.伯尔基的这些观点,撇开意识形态标准不谈,即使从学术上讲也是存在问题的。在我们看来,与其说马克思主义是自由主义观念的发展,毋宁说是共和主义(社群主义)的极致发展[18]。
再次,马克思不仅不完全赞同现代性,相反还极力批判现代性,尤其是现代性的拜物教特征——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论述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时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9]。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过程就是征服、奴役、掠夺、杀戮的过程。这一批判并非简单的道德评判,而是植根于对社会阶级结构和社会劳动决定性作用的社会学分析。
最后,马克思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是事实判断与道德判断、科学分析与价值评判的统一。“塔克-伍德命题”认为马克思没有从正义立场和道德角度批判资本主义,是一个“非道德主义者”甚至“反道德主义者”;G.A.科恩和胡萨米又认为马克思是从道德视角谴责资本主义非正义性的“道德主义者”。这两种看法都是非常片面的。其实,马克思是一个具有科学精神的道德主义者,也是一个具有道德信念的科学主义者。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20]11。马克思还说,的确,路德战胜了虔信造成的奴役制,是因为他用信念造成的奴役制代替了它。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因而,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20]18
毫无疑问,在马克思那里,政治经济学批判与伦理道德批判是有机统一的,二者缺一不可,过分强调一个方面而淡化、忽视、甚至否定另一个方面,都是不可取的,甚至是错误的。当然,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的传统阐释中,有过分强调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忽视伦理道德批判的倾向,以至于反向激发了许多学者对马克思思想的“道德维度”的强调。例如,在“再思马克思:哲学、批判、实践——缺少什么?”国际学术研讨会(柏林,2011)上,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学术领袖霍耐特指出,在历史文献和政治文献中,马克思设想的具体的社会群体或主体,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是变化的;但《资本论》缺乏道德维度,它仅仅是经济目的合理性的行为主体,包容着占据支配地位的资本主义自我增殖过程的线性膨胀和愚蠢的现实的力量。这样,历史过程的变化实际上就是不可能的。因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必须考虑到社会学或政治学维度[21]。当然,霍耐特的上述说法也有不准确之处,但他对道德维度、社会学维度、政治学维度的强调却是值得认真思考的。
四、结语
综上所述,“现代性”作为一个哲学话语,不同人赋予了它不同含义,从而导致人们对待现代性有不同态度,并出现了四种不同立场,即坚持现代性(与批判现代性融合在一起)、告别现代性、重建现代性、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马克思既是现代性的坚持者,又是现代性的批判者。在21世纪语境中,重新理解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这是一个既有重大理论价值又有重要现实意义的话题。
在马克思那里,“现代性”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科技理性(基本肯定,但也看到了“现代性悖论”),二是资本逻辑(基本否定,但也承认资本的积极作用)。从根本上说,马克思是一个现代主义者,坚持现代性的基本价值理念;但他又不同于一般的现代主义者,对现代性也并非毫无保留地坚持。他极力批判现代性的拜物教特征;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是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科学分析与道德评判的统一。因而,他既是一个具有科学精神的道德主义者,也是一个具有道德信念的科学主义者。
在对待现代性问题上,我们不能因为现代性的弊端而拒斥现代性,甚至重返前现代性,或走向后现代性;不能因为主体性的狂妄而拒斥主体性,甚至重返集体至上性;不能因为科学技术的消极效应而拒斥科学技术,甚至重返神话状态;而是要协调现代性、前现代性、后现代性的关系,协调个体主体性、集体主体性、主体间性的关系,协调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协调道德与伦理的关系,协调个体主义与共同体主义的关系。
换言之,我们既要承认现代性的普遍主义内涵,又要考虑中国的特殊情况(所谓“后发外生现代化”);既要有世界眼光,又要有中国立场;既要吸收、借鉴现代化的积极成果,又要减少、避免现代性的负面效应;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确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文明类型。也许,这就是在21世纪语境中重新理解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