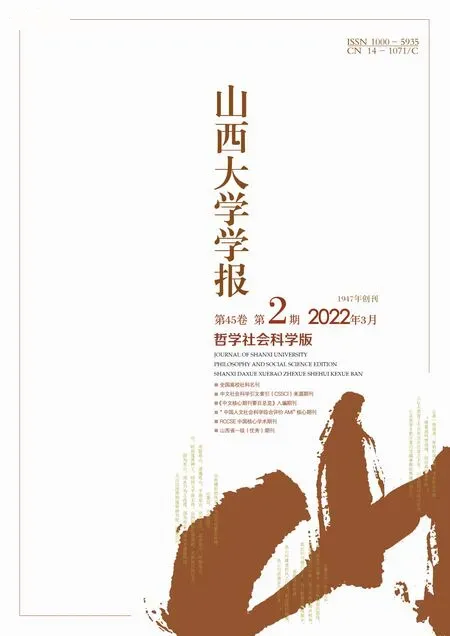此在、声音与废话的诗学:当代“口语诗”的语言哲学
赵黎明
(暨南大学 人文学院,广东 珠海 519070)
一、从“说”说起
“口语诗”是从第三代诗中萌蘖而出的一个新诗亚种,具有偏重日常生活经验、凸显“口说”价值、崇尚“事实的诗意”等特征。其来源和构成相当复杂,是多种诗体混合变异的产物,它有初期白话诗甚至晚清“我手写我口”的创作基因,但把口说推到了诗歌本体的地位;它延续了“第三代诗”的生活流本色,但把生活的抒情变成了“事实的诗意”。对于这种极端重视口语价值,甚至具有反书写色彩的“口语诗”,当代诗坛有不同的说法,伊沙认为诞生的标志是上海诗人王小龙1982年创作的《纪念》,后经“两报大展”推广而衍为“生活流”诗派,直到1988年前后“迅速升温终至泛滥”,而形成“口语诗的第一次热潮”。[1]405他认为口语诗诞生三十年间出现的许多先锋诗派,“从‘第三代’到‘后现代’,从‘身体写作’到‘下半身’,从‘民间协作’到‘诗江湖’,到目前如火如荼的《新世纪诗典》,无一不是以‘口语’为主体,以口语诗人为生力军”[2]396。而对于“口语诗”的内部构成,也有人做了前、后期划分,认为1993年伊沙的短论《饿死诗人,开始写作》发表,“标志着一个新的口语诗时代——后口语诗时代开始了”[3]440;并称“于坚的‘拒绝隐喻’和韩东的‘诗到语言为止’以及杨黎的‘废话’等主张,基本代表了前口语诗。伊沙的‘事实的诗意’必然代表了后口语诗”[3]435。还有人举出具体例子,对前后期口语诗的特征做了详细区别,认为前口语诗是“生活流”“我们的”“概述的”“抽象的”“情境的”“抽离的”“精英的”“仪式的”“情怀的”等;后口语诗是“生活片段的”“我的”“个别的”“具体的”“情景的”“在场的”“平民的”“戏谑的”“情趣的”等[4]431-432。
如此繁琐的细分,其实并无多少必要,因为前后尽管有一些变化,不同诗人之间也存在风格差别,但作为诗学流派,其整体特征还是一致的,如:拒绝诗歌隐喻,避免过度修辞;突出口语价值,颠覆书写霸权;提倡平民主义,抵制贵族意识;倡导日常经验,反对超验主义;打破抒情结构,崇尚“事实的诗意”;等等。对于白话诗的这些特点及意义,学界已从不同角度进行过探讨,本文不再赘述。本文特别关注的是它对“说”“声音”以及“废话”的重视,认为这三者触及了诗歌的根本,也触及了语言的本质,因此拟从这三个关键词入手,沿波讨源,追根问底,在弄清历史与哲学根源的基础上,讨论其存在的合法性、合理性以及积极的诗学意义。
“口语诗”顾名思义是注重口语的诗,是“说”的诗而不是“写”的诗,是用于“听”的诗而不是用于“看”的诗。“口语诗”的命名似乎预示着一种诗歌语言制度的转变,语文的“书面性”被拉到幕后,而“口头性”则被推向了前台。
口语诗人不仅把口语放在第一档位,“口语是第一语言,也是诗歌的语言”[5]109,还把动作主体“说”,单独掂出并予以强化。伊沙有一篇有名的宣言,题目就叫《有话要说》,说的虽然是一些有关诗的“杂话”,但其中“说话”这个动词倒是无意中道出了其中玄机。在另一个场合,他把“说话”直接换成了“叙述”,声称口语诗人“只说‘叙述’而不说‘叙事’……在一首口语诗中,‘叙述’不是工具,它可以精彩自呈”[2]398,因而把“叙”和“述”提高到本体地位。尚仲敏更用一首论诗诗点破了口语诗“行动”的实质:
有很多朋友
为诗所苦
在书桌前
挑灯夜战,日渐消瘦
还有一些朋友
所谓的学院派
拿着外语词典
搜肠刮肚
用遍意象和隐喻
写一些连自己都不懂的
翻译体
我从十七岁开始写诗
直到今天才知道
诗歌就是
你喜欢一个美女
就对她说
有什么事
我们躺下再说
(《诗是什么》)
种种迹象显示,口语诗是在向诗的源头即语言的原始状态,做一次有意的返回。
在中国最古老的诗学典籍中,诗的最初含义可不是什么文字书写,而是“言”“歌”等口舌动作。“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尚书·尧典》),班固对其中“诗言志,歌永言”的解释是:“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汉书·艺文志》),发声运动占着第一义的位置。“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毛诗序》)孔颖达亦做这样的释解:“诗者,人志意之所之适也。虽有所适,犹未发口,蕴藏在口,谓之为志。发见于言,乃名为诗。言作诗者,所以舒心志愤懑,而卒成于歌咏。故《虞书》谓之‘诗言志’也。”(《诗大序正义》)可见,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付诸口舌才是由“志”到“诗”的铁门限。
而在西方诗坛情形也大致如此。据海德格尔考证,德语的“作诗”(Dichten)在古高地德语和拉丁语中就是“口授”的意思,直到17世纪才限定在现在poetische即“书面拟就”行为上;而poetische一词在希腊语中,原意是将某物弄出来、制作出来、显示出来。所以,作诗就是一种“作为指引着的令敞开的道说样式”[6]36。而在另一个德国哲学大师洪堡特看来,诗歌的本性是从嘴里涌出的声音,而不是毫无生气的文字记录,文字记录“同诗歌的本性是相逆的。诗歌从诗人的嘴中涌流而出,或者由一批接受了诗人的创作精神的歌手唱出,它是一种伴有歌唱和器乐的朗诵”[7]242。
因此,对于口语诗的“说”千万不要小觑,它可能就是诗的本真状态。朱光潜在谈到民歌本质的时候,曾有一个判断云:“民歌都‘活在口头上’,常在流动之中。它的活着的日子就是它的被创造的日子;它的死亡的日子才是它的完成的日子。”[8]21这个说法按到一般诗歌头上其实也合宜,书写只是诗歌的完成形式,“说”之时才是它“活着的日子”,亦即“被创造的日子”。
诗歌如何说话?类型大约有两种:一是自言自语的“表现”:情动于中而行于言,情不能已而付诸咏;一是与人分享的“表达”:模仿一种现象,模仿一个事件,把信息传递给对方。中国古诗大体属于前者,抒情被称为其“道统”;西方诗大致对应后者,以致史诗、剧诗特别发达。口语诗大约摇摆于两个传统之间,它弃绝抒情、意象而转向叙述、故事,表现出对东方抒情传统的有意背离:“‘后口语’便有了更明显的结构,通常是由一些事件的片段构成,所以,口语诗人写起诗来‘事儿事儿的’,‘很事儿逼’——在我看来这不是讽刺和调侃,而是说出其‘事实的诗意’的最大特征。”[2]397后期口语诗的骨架,大体就是由这种“事儿”支撑着,如阿煜的《探监记》:
在一排光头中
妹妹一眼就找到了
我们的爸爸
他蓝色的狱服外
套了件醒目的马甲
那是别人家的爸爸
所没有的
回来的路上
妹妹兴奋不已
“爸爸一定是当官了
对吧”
又如西毒何殇的《医院最好看的女人》:
唐都医院住院部
十七层呼吸科
上来的女人
是我今天早晨
遇到的最好看的女人
她说那个叫崔凯的
男医生长得很帅
是护士们的男神
她和闺蜜旁若无人
嬉笑了一阵
才说
“我早就把自己
判了死刑了,
今天来医院
就是听他宣判的。”
口语诗人宣称,要“到语言发生的地方去把意义还原为一次事件”[9]145,“呼唤源头性语言去叙述或描述‘一次事件’”[3]435。从这些实践与理论的诉求看,口语诗至少存在着两种革命性冲动:一是返本的冲动,从书写、书面、纸上、文化到说唱、口头、现场、朴野的回归;一是偏离抒情传统的冲动,离开自语式的情感表现而走向互动式的信息表达。
把“事儿”说与你听,“说”是一种直接的交流,它以口耳相传的方式,把说话人与听话人连为一体。它不仅是语言最初的形式,“我们把这两个人,即语言的发出者和接受者分别称为说话人和听话人,这是考虑到说出的话和听到的话是语言的最初形式,比书写(印刷)和阅读这一派生形式更加重要”[10]3,也是语言之根本,因为语言不单在说话中成其本质,也在说话中使说者在场,“说话者在场于何处呢?在说话者所与之说话的东西那里,在说话者所依寓而栖留的东西即总是已经与说话者相关涉的东西那里”[11]249。与海德格尔这种说法相仿佛,口语诗人也以“现在进行时的史诗”[9]145创作而追求诗的“在场”,并把“语言毫无语感,回到日常却回不到现场”[12]172视为典型的非诗倾向。
对“现场”的追求,对“此在”的追求,既涉及诗对现实的敏感程度,也牵涉到诗的本质属性,具有深邃的哲学背景,需要略加申说。关于诗及语言与存在的关系,海德格尔有一系列精辟的见解。他认为诗是一种纯粹的语言,它与语言一样也有“显-隐”二重性。如何让诗呈现这二重性呢?与语言一样,是“道说”,也就是“让显现”。在他看来,这是语言的本质,也是诗的本质:“我们猜度,语言之本质就在道说中。道说(sagen),在古代斯堪的纳维亚语中叫sagan,意思是显示(zeigen),即:让显现,既澄明着又遮蔽着之际开放亦即端呈出我们所谓的世界。”[13]193按照他的描述,在这混沌未开、乍明还暗的世界中,诗人以一道亮光参与了这一创世工程。这光就是语言,亦即诗。而语言或诗又是如何创建世界的呢?他认为靠的是源始性命名,“诗乃是对存在和万物之本质的创建性命名——决不是任意的道说,而是那种首先让万物进入敞开域的道说”[14]47,显然,这种命名乃是一种召唤,一种令物到场,在物的到场中语言“绽出性地直临存有”[6]43,进而“创建”存有。如此,诗、语言与存在,既具有功能关系,又具有同一关系。诗或语言又是如何导入了人的存在呢?在他看来是对话,对话规定了人的此在,他说:“我们是一场对话。这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语言构成并规定了我们的存在。”[6]80又说,“我们——人——是一种对话。人之存在基于语言;而语言根本上唯发生于对话中。……对话及其统一性承荷着我们的此在。”[14]41-42这里,他把“说”即“对话”,置放于与存在并列的位置,存在就是“此说”,也就是“对话”,“‘相互说话’意味着:彼此道说什么,相互显示什么,共同相信所显示的东西。‘共同说话’意味着:一起道说什么,相互显示在所讨论的事情中那个被招呼者所表明的东西,那个被招呼者从自身而来带向显露的东西”[11]252。存在、在场、说、对话、显示等,在此取得了同一关系。理解了这一层关系,再来看于坚的一些看法可能就不至于跌入云里雾里。他认为,口语诗对立于书面语,根子并不仅仅在于前者先于后者,即书面语发生于口语之后,而是书面语根植于口语,正是口语这个“根”接近于“存在”,才使本真的显现成为可能,所以他提倡诗人要用口语去“表达存在”,要“在根上写作”而“不能去树尖上写作”。[5]101
二、“声音”的文化考古
与“说”关联的是“声音”。如果“说”是一种口舌运动,那么“声音”就是这一动作制造的响声,即动作的直接后果。不过按照索绪尔的观点,作为语言符号的能指部分,它“不是物质的东西,纯粹物理的东西,而是这声音的心理印迹”[15]101。鲜为人知的是,口语诗人进行语言探索,足迹已经抵达语言最原始的部位。伊沙指出汉语诗歌的语言板结硬化——“高度词语化和高度人文化”——已经到了结石的程度,非“将其从词语的采石场中拉出来”,不足以恢复语言“流水一样的声音的本质”,并批评台湾诗人将“诗”与“歌”分开,“他们简单地以为‘歌是歌,诗是诗’,并未意识到声音(而不是词语)才是语言的本质”。[12]171-172而在实践中,他也有意识地进行“声音”还原,创作出实验之作,如:
哩哩哩哩哩哩哩
以吾腹作汝棺兮
哩哩哩哩哩哩哩
在吾体汝再生
哩哩哩哩哩哩哩
以汝肉作吾餐兮
哩哩哩哩哩哩哩
佑吾部之长存
哩哩哩哩哩哩哩
汝死之大悲恸兮
哩哩哩哩哩哩哩
吾泪流之涟涟
哩哩哩哩哩哩哩
汝肉味之甘美兮
哩哩哩哩哩哩哩
吾食自在快哉
哩哩哩哩哩哩哩
(《实录:非洲食葬仪式上的挽歌部分》)
诗歌选择非洲部落祭祀仪式歌舞形式,杂以中国同样具有巫祀色彩的楚辞语式,以原始单调的发声展现“我的‘食葬’”,体现诗人“一次语言的狂欢”,[16]148具有深刻的文化意蕴和丰富的阐释空间。
这里涉及“声音”在语言中的初始地位,也关联到诗歌与声音的本体关系。先说西方文化中的声音。人们知道,西方语言哲学中素有“语音中心”传统,德谟克利特是语言音节起源论的第一个提出者,亚里士多德字母符号关系论影响更为深远。在《解释篇》的开篇,亚氏便断言,“字母乃是声音的符号,声音乃是心灵的体验的符号”(1)汉语一译为“口语是心灵的经验的符号,而文字则是口语的符号”。亚里士多德.范畴篇;解释篇[M].方书春,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63.,几千年的西方哲学和语文学基本就是对这一论断的阐释和演绎。即使到了现代,相对于文字符号,语音仍被认为是更为原始也更为根本的东西。索绪尔就持这一观点,不仅认为语言与文字二分,而且坚持语言决定论:“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15]47他把语言和文字比作真人与照片,宣称语言学的研究,“只限于表音体系,特别是只限于今天使用的以希腊字母为原始型的体系”[15]51,反映了西方语言学根深蒂固的语音优先传统。
体现在诗学领域,“声”的问题一样占据关键位置。仅以海德格尔为例。在一般人眼里,海氏是一个对形而上学具有“解构”取向的哲学家,但当其论及语言和诗时,语音中心论的倾向便在无意中流露。在解读亚里士多德《解释篇》时,他毫不掩饰对这段文字的赞美,谓其“包含着一种明智清醒的道说,它揭示了那种始终掩遮着作为说话的语言的经典结构。文字显示声音。声音显示心灵的体验。心灵的体验显示心灵所关涉的事情”[11]242。而在对诗的解释中,他也表现出对“音”之显现功能的无比倚重,“音(das Lauten)从鸣响中发出,从那种召唤着的聚集中发出,这种对敞开者敞开的聚集让世界在物那里显现出来。这样,声音的发声者就不再单单被归为肉体器官方面的事情了。这就摆脱了对纯粹语言材料作生理学—物理学的说明的视界。语言的发声者,语言的大地因素(Erdige),被扣留在调音之中,后者使世界构造的诸地带一起游戏而相互协调。”[13]203这段意涵丰富的文字,既包含了其既往对语言存在的一般理解,也包括了他对语言结构的重新认识。语言被其进一步“还原”,一直被溯到声音结构。在他那里,正是这种声音结构,才使天、地、神、人之四方世界“一起游戏而相互协调”。
再看中国诗歌中的声音。中国诗歌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声诗”,声音所占的位置十分显赫,但此声非彼声,其意义与西洋语言中的所指不尽相同。“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汉语诗歌最古老的训示同样把“声”放在起始的地方,但是它的源头并不指向逻各斯或形而上学,而是指向“气”——一种充满“唯物”意味也颇具神秘色彩的东西。“气”本于自然,也源于生命,所以在诗文中它直接就指向生命。在中国古代文人墨客的世界观里,这是一种不言而喻的常识,刘勰说:“夫音律所始,本于人声者也。声含宫商,肇自血气,先王因之,以制乐歌。故知器写人声,声非学器者也。故言语者,文章神明枢机,吐纳律吕,唇吻而已。古之教歌,先揆以法,使疾呼中宫,徐呼中征。”(《文心雕龙·声律第三十三》)音律始于人声,人声肇自血气,关于诗乐起源论的这种逻辑认知,历代诗人似乎深信不疑:
昔伶伦造律,盖为文章之本也。是以气因律而生,节假律而明,才得律而清焉。[17]352
情者,心之精也。情无定位,触感而兴,既动于中,必行于声。故喜则为笑哑,忧则为吁嘻,怒则为叱咤。然引而成音,气实为佐;引声成词,文实与功。盖因情以发气,因气以成声,因声而绘词,因词而定韵,此诗之源也。[18]765
可见,尽管汉字被西方语言学家视为“表意体系”——“一个词只用一个符号表示,而这个符号却与词赖以构成的声音无关”[15]50,但声音在诗中仍然高居于源头性地位,正如萨丕尔所说的,正是靠着这种“出自语言的无意识的动力习惯”,中国古代诗人才创造出好像从“嘴里掉出来的”一样的诗歌节奏[19]206。
搞清了声音在中西诗歌中的源头关系,再回头看看口语诗的声音问题。无疑,口语诗人强调声音,多少都带有一定程度的“返回”意向,多少含有以“复古(元古)”为进取的志向。在他们那里,返回原初并不是一种逃避,而是跳过层层堆积的所指瓦砾,直接回到诗的初始状态。杨黎早期就有“让诗歌回到声音”的说法,认为只有“诗歌进入声音之后,才获得了诗歌自己的生命”,但为了避免误解,他对“声音”做了规定,把“语义的言说”、古人关于“音韵的诗歌道理”以及“音节的考量和把握”等都排除在外,认为声音的真实意指,“一是指语言自己的声音,二是指诗歌”[20]224。很明显,他所要求的声音其实就是原初意义上的音响能指。
海德格尔在探讨说话之源时,曾有这样一段论述:“分音节的有声表达是一种说话。语言在说话中表现为说话器官的活动,即嘴、唇、口、舌、喉等器官的活动。自古以来,语言就是直接从这些器官现象出发得到表象的……语言是舌,是口之方式。”[11]239嘴、唇、口、舌、喉、身体,乃至于它们赖以生存的大地,都被现象学家视为“还原”的最初源头,“口不光是在某个被表象为有机体的身体上的一个器官,倒是身体和口都归属于大地的涌动和生长——我们终有一死的人就成长于这大地的涌动和生长中,我们从大地那里获得了我们的根基的稳靠性。……语言是口之花朵”[13]200。语言是“口之花朵”,诗歌更是口之花蕊;口是大地(即根基)的出处,大地之音经由此处“涌现”,即用声音让世界显现。口语诗人中的先锋探索者如伊沙等,也像海德格尔一样开始抵达“舌头”等身体层面,典型的除了上面那首食葬挽歌外,还有这样一首颇有争议的“口吃诗”:
结结巴巴我的嘴
二二二等残废
咬不住我狂狂狂奔的思维
还有我的腿
你们四处流流流淌的口水
散着霉味
我我我的肺
多么劳累
我要突突突围
你们莫莫莫名其妙
的节奏
急待突围
我我我的
我的机枪点点点射般
的语言
充满快慰
结结巴巴我的命
我的命里没没没有鬼
你们瞧瞧瞧我
一脸无所谓
(伊沙《结结巴巴》)
诗中个别音节故意停顿、延宕或重复的地方,医学名称叫作“口吃”,俗语称之为“结巴”。
表面上看,它是一种言语障碍,一种典型的失语症候,但其实正是这种恶作剧式的口音拖长,不仅形成具有强烈带入感的声音节奏,更将诗语复原到口舌等肉体感官层面,因而造成一种绵延起伏而又跌宕有致的语感效果。
从口语诗人的相关宣示来看,从文化回到身体正是其十分自觉的艺术追求。口语诗出现后,有人一度将其贬为“口水诗”。对此贬损,伊沙不仅不以为忤,反而大加引申发挥,认为口语诗就是“要伴随我们口水,让语言保持现场的湿度,让飞沫四溅成为语言状态的一部分”[12]172,还宣称,“语言带有舌尖湿润的体温不是更具有生命的症候吗?”[2]398可见使用带有体温的“舌尖上的活性母语”写作,正是其进行诗歌感性革命的核心宗旨。于坚也认识到,1980年代以来口语诗运动真正深刻的地方,并不在于对“我手写我口”再次响应,也不在于推动了一场另类的语言游戏,而在于它对“纸上的东西”的抵制,对当下身体的尊重,“对汉语日益变硬的舌头的另一部分的恢复”[21]50。在他那里,回到口语就是使诗“重新获得身体、获得血肉”[5]110,而身体性的获得正是诗歌本能复原的重要途径。
三、“废话”的“废”
“废话主义”是口语诗派的一个重要口号,其主要倡导者是杨黎等人。参与发起过“第三代诗歌”运动的杨黎,曾与何小竹、韩东、乌青创办“橡皮先锋”文学网站,于2000年前后祭出了“废话写作”的旗帜,并展开了相关艺术实践。什么叫“废话”?在一般意义上,“废话”指没有用的话、没有意义的话,但在“废话主义”语境中则另有所指,专指诗歌超语义、超文化、超价值、超功利的某种属性。杨黎在事前事后不同场合描述过诗歌的废话本质:
我从来没有说过写废话,而是说废话就是诗歌的本质。诗歌是什么?诗歌就是废话,这是我对诗歌的描述。[22]16
世界上永远没有真正的废话,有不了的,谁要是能够说出一句这样的“废话”,那他就完全改变了这个世界。所以,我说诗歌是废话,是说诗歌它的本身,是一种在更深意义上的比喻。[23]659
为什么写诗,在我来说是简单的,也是唯一的,就是要把字(语言)写得没有意义。它的落脚点就是超越语言,让我们把自以为已经理解的意义重新组装成没有意义的(语言的声音)诗歌。[24]128
有用的东西是语言的东西,而无用的东西是诗歌的东西,这是我言说诗歌的前提。我强调废话,就是强调诗歌的唯一性。[23]312
而在实际创作中,他也用“流水账”的方式,故意“把字写得没有意义”:
我们站在河边上
大声喊河对面的人
不知他听见没有
只知道他没有回头
他正从河边
往远处走
远到我们再大声
他也不能听见
我们在喊
(《大声》)
声称要用这种方式“把写作上升到自己的本学语境”,“让语言还原到最基础的结构中去”。[22]11他还把这种语言态度用于其他诗歌的评价中。作者“竖”曾有一首比较有争议的诗歌《妈妈和妓女》:
陶阳听见自己说:
女人分两种
妈妈
和妓女
他知道
一部电影的名字
叫妈妈和妓女
这时候他想起来了
他还知道
妈妈和妓女
都是女人
这句话的声音
在空气里
被他自己听到
几乎同时
徐严笑了起来
一路上
他笑过好几次
这时候
他又笑了笑
所以
陶阳不光听见
自己说:
女人分两种
妈妈
和妓女
还听见
一个人的笑声
虽然很轻
但是他还是听见了
在一般世俗观念里,“妈妈”和“妓女”是关于女人的最具价值取向的两种命名,它们分居于社会道德的正负两极,然而在这首诗歌中,诗人不仅让二者在价值天平上平行排列,还让无谓的“一个人的笑声”加剧了天平的倾斜。对于这样的“去价值”之作,杨黎谓其“每一句话都是废话,简单,直接,说了等于没说,但看了肯定是看了”,“这首诗没有情绪,没有道理,但空间却很大,大得什么也没有”。[23]310实际上,这里的“没有”是不存在的,它不仅“有”,而且还很强烈——该诗以“中性叙述”祛除“妈妈”和“妓女”的价值取向,本身就是有意为之的价值行为,所以从精神谱系角度看,“废话主义”与“非非主义”实乃一脉相承。1986年,周伦佑、马非在深圳两报诗歌大展上发表《非非主义宣言》,提出诗的“三还原”(“感觉还原”“意识还原”“语言还原”)原则,誓言要摒除语义障碍、文化语义,对语言进行“去语义”“去价值”的能指还原,[25]33-34曾引起诗坛持续的震荡。杨黎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废话理论”,显然是想把它推行到极致。
无疑,“废话”的“废”首先是作为动词使用的,是功能性的文化行为。那么,他要“废”的重点是什么呢?仍然是所谓“语义”。语义(semantic)大体指语言符号的所指部分,是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尽管“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15]102,但经由广大人众长时间的习得,所指部分往往深铆人心牢不可破,形成十分稳固的社会意义。语义堆积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但于诗而言并不是一个好兆头,因此,以创新为职志的先锋诗人就把批判的锋芒对准语言的这个“概念”部分,试图通过对其惰性成分的消除,达到新奇即陌生化效果。“废话主义”运动大约也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展开的。杨黎说:“废话真正要废的,是语义。这个世界的本质,就是意义化……我们生了,这是一个意义。我们必须死,这又是一个意义。事实上我的怀疑,就是从这里开始。我认为,意义化,它肯定不应该是唯一的和绝对的。如果我们改变了它意义的‘密码’,它是不是就该是另外的样子呢?所以说,我更喜欢有中生无,那就是消除语义、超越语义。”[22]16-17不仅要消除语言的“意义化”成分,甚至连“语感”也开始反对,在他眼里,语感是文化的,因而是最为本质的语义,“我认为语感是最后的语义,也是最大的语义,更是最本质的语义,在这个前提下我开始反语感。语感是文化的,肯定是语义的。对我们来说,要彻底地、全面地清除语义,就必须反对语感。”[22]14
杨黎所倡导的“废话主义”,总起来看仍然未脱“非非主义”的藩篱,都是从语言入手切入诗的核心层面,试图通过对语言之价值及文化成分等的清除,对诗进行一场彻底的艺术还原。稍有不同的是,杨黎非常明确地提出诗的本质乃在于“废”(即无用性),提出对诗的工具性、功利性的质疑,进而体认到诗语的自我指涉性,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观念进步。需要指出,这些诗学观念的获得、诗学实践的展开,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深厚的思想和艺术背景,其中现代语言哲学的影响尤为显著。
罗兰·巴尔特是当代“废话主义”诗学绕不开的语言哲学家,其提出的零度写作、白色写作等观念,可以说是“非非主义”“废话主义”的理论渊薮。巴尔特曾这样描述“白色写作”:“摆脱了特殊语言秩序中的一切束缚……在某一对极关系(单数与多数,过去式与现在式)之间建立了第三项,即一中性项或零项。这样虚拟式和命令式之间似乎存在着一个像是一种非语式(amodale)形式的直陈式。比较来说,零度的写作根本上是一种直陈式写作,或者非语式的写作。可以正确地说,这就是一种新闻式写作,如果说新闻写作一般来说未发展出祈愿式或命令式的形式(即感伤的形式)的话,这种中性的新写作存在于各种呼声和判断的环境里而又毫不介入其中;它正好是由后者的‘不在’所构成。但是这种‘不在’是完全的,它不包含任何隐蔽处或任何隐秘。于是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毫不动心的写作,或者说一种纯洁的写作。”[26]61这段引文中的关键词如“中性”“零度”“不及物”等,直接启发了周伦佑、杨黎等,成为其诗学建构的核心部分。杨黎说,“‘废话写作’是无作为的写作”[27]200;又说,“废话其实就是诗歌的本质……废话,说一千道一万,不就是‘言之无物’吗?”[28]156周伦佑也提出“红色写作”“白色写作”诸说,其中意涵虽不无调整,但精神内核并无大异,可见其受影响之深。
关于诗语的本质,形式主义诗学家有一系列经典论述,这些论述很多也被“废话”诗论家直接改造,变成自己诗学话语的有机部分,比如雅各布逊说“纯以话语为目的,为话语本身而集中注意力于话语”[29]181乃是语言的诗歌功能;在杨黎那里就变成了:“我为什么说诗句是废话?它是这样的,它是说诗与一般的言说的差异。说话的目的,是为了沟通,是为了交流,是为了表达一个意义。……诗是什么?诗就是你把这个意义表达完以后,它还有意义。那个意义是什么?实际上一言以蔽之,就是诗意,它不关乎实用。”[30]169-170尽管这种理解并不准确,甚至有些望文生义,但关于诗的若干新观念如非实用、非交流以及自我指涉等,则被其移用并在当代汉语诗学中建立起来了。
从上述几个方面的简单梳理不难发现,“口语诗”并不是一下子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有着深厚历史与哲学基础的“有根的诗学”。不唯有根,而且有为,也就是说它还是一种功能性的诗学,同时具有解构与建构双重功能。作为解构的诗学,它的目的是否思诗歌的一切异化形式,如意象、象征、抒情、互文、语义、体制、书写等钝化变异的部分;而作为建构的诗学,其主要旨趣则是倡导一种诗的原始返回——返回在场、返回声音、返回身体、返回感性等所有的努力,“倡导身体性、人性的自然、积极入世、明澈赤诚、态度鲜明的积极性诗学元素,这些诗学观就是口语诗对古典诗学中消极元素的强烈矫正”[31]449。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对诗歌“书写霸权”的一次有力纠偏,也是对汉语新诗航线的一次重新调校,具有积极的诗学意义。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口语固然为诗歌之源,但口语只为诗提供了天然材质,它本身并不是天然的诗;口语为诗的成就提供了现实可能,然口语与诗语之间的距离不可以道里计,其中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性,稍有不慎口语就变成了“口水”。这里的核心问题仍是“诗性”,正如旧体的平仄对仗并不构成诗性的唯一表征一样,新诗的白话口语也不能成为诗的根本标志,二者面临的问题其实是一样的,那就是必须抛弃一些外在的表象,直捣诗之为诗的要害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将“可能的诗学”变成“现实的诗学”。因此,从口语到口语诗,其间是有漫长的道路需要诗人艰辛探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