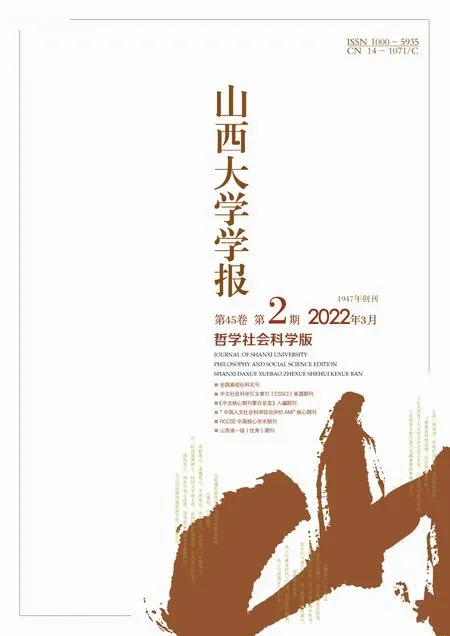深描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
——兼论深描在教育研究中的应用
王 鉴
(云南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云南 昆明 650550)
一、深描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创作的方法
深描(thick description)是一种方法,深描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呢?深描是人文社会科学较为普遍的一种创作与研究的方法。此论述或观点,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恐怕还是比较陌生的,许多的研究者并不熟悉作为方法的深描,甚至有不少的研究者还没有听说过有深描之研究方法。事实上,深描作为一种人文社会科学创作与研究方法,有着比较悠久的历史。古今中外有许多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把深描作为创作和研究的方法在广泛地使用,更有一些学者还专门论述了深描的方法论及其方法。因此,系统总结深描的原理与规则,对于深化人文社会科学的创作与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人文社会科学是相对于自然科学的,阐释学、现象学等一再强调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应该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深描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人类学者最早提出,在社会学、民族学、历史学、文学、艺术、教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中广泛使用。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里福德·格尔茨(Geertz,C.)在1973年出版的《文化的解释》一书中全面、系统、深入地论述了作为方法的深描与民族志的关系。该书第一章的内容便是“深描说,迈向解释的文化理论”格尔茨在本书中提及比他运用深描更早的学者是英国思想家吉尔伯待·赖尔(Gilbert Ryle),赖尔关于深描的经典案例是“眨眼”。赖尔根据不同的眨眼所隐藏的文化意义的揭示,阐明了深描之于文化研究的方法问题。格尔茨按照赖尔提供的方法,通过自己的田野研究案例,大量使用深描方法,最终总结出深描的方法论基础,系统论述了深描在人类学研究的应用策略。格尔茨得出结论:民族志就是深描[1]12。出版于1989年的由罗曼·邓金(Norman K.Denzin)撰写的方法论专著《解释性交往行动主义》一书中,更是在第五章专门把深描作为一种方法来论述,并对深描方法进行了分类,对不同类型的深描在不同研究中的效果进行了比较分析[2]99。由此可见,“深描”,即详尽的描述,与它相对的是“浅描”(thin description),即简明的描述。深描与浅描都是人文社会科学创作与研究的方法。深描和浅描在英文里面的表述是清楚的,但是这种表述不太适合于汉语的表达方式。深描在汉语当中一般表述为“浓墨重彩”,浅描则一般表述为“轻描淡写”。正是困惑于英语和汉语词汇的翻译问题,笔者专门对比阅读了不同版本的《文化的解释》译本以及大量的相关文献资料。发现目前学术界已经在较为普遍地使用深描与浅描。如果我们和汉语的使用习惯相对应,就会发现在中国的艺术与文学、历史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创作与研究中大量使用着深描与浅描的方法。
(一)艺术创作中的深描方法
中国绘画史上非常著名的一种画法称为“泼墨”与“泼彩”。相传唐代画家王洽,“以墨泼纸素,脚蹴手抹,随其形状为石、为云、为水,应手随意,图出云霞,染成风雨,宛若神巧,俯视不见其墨污之迹。”[3]清代沈宗骞《芥舟学画编》中已经描绘了泼彩画法:“墨曰泼墨,山色曰泼翠,草色曰泼绿,泼之为用,最足发画中气韵。”中国画中把这种笔酣墨饱,或点或刷,水墨淋漓,气势磅礴之画法,皆谓之“泼墨”。泼墨画法在现代社会因结合了西方绘画的技巧而出现了更为丰富的泼彩画法,这种以彩色为主的纵笔豪放的画法是中西绘画方法结合的产物。最著名的泼彩大师当属张大千先生了,他的一幅泼墨山水,2019年北京保利以成交价345万元拍卖,另一幅泼彩山水则以成交价114万港元于2006年在香港佳士得拍卖成功,创下中国泼墨和泼彩画拍卖价双高。这些激情创作的作品,其内容并不明确,但令人浮想联翩。但凡熟悉中国书画史的研究者,肯定对中国传统书法与绘画中的泼墨与泼彩的“书法”与“画法”并不陌生,而且这种创作方法更受创作者的书与画的基本素养及情境的限制,合乎人文的精神气象,如王羲之创作兰亭序之书法绝笔,又如张大千即兴创作之泼彩山水等。此中浓墨重彩者即为深描,轻描淡写者即为浅描。书法创作中,用笔之轻重缓急,犹吟猱之有阴阳徐疾,同时,墨之浓淡有度,犹如情绪之一张一弛,书者便是利用笔墨之变化来表达艺术之线条,一般而言,书法家常常以浓墨表现庄重与沉稳,以枯笔显示跳动与轻盈,张弛有度,轻重缓急,或密不透风,或疏可行马,以线条美呈现中国书法的无尽韵味。绘画创作中,画家常常以浓墨表达苍山之厚重,以留白展现云雾之缭绕,虚实结合,浓淡益彰,以黑白对比表现了中国书画在写真写意方面的独特魅力。艺术创作中的深描同样被广泛运用到艺术研究领域,对人物或作品的背景与内容的深描成为艺术研究者书写与绘画的重要方法。
(二)文学创作中的深描方法
如果艺术世界以色彩表达思想的话,文学创作则主要是通过语言来表达思想。语言的深描在文学作品中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成果最为丰富。翻阅中外文学名著或文学史,不难发现,文学作品离不开深描的方法。如果说小说中大量使用深描的方法的话,那么诗词中则更倾向于浅描的方法。
且说黛玉自那日弃舟登岸时,便有荣国府打发了轿子并拉行李的车辆久候了。这林黛玉常听得母亲说过,他外祖母家与别家不同。他近日所见的这几个三等仆妇,吃穿用度,已是不凡了,何况今至其家。因此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唯恐被人耻笑了他去。自上了轿,进入城中,从纱窗向外瞧了一瞧,其街市之繁华,人烟之阜盛,自与别处不同。又行了半日,忽见街北蹲着两个大石狮子,三间兽头大门,门前列坐着十来个华冠丽服之人。正门却不开,只有东西两角门有人出入。正门之上有一匾,匾上大书“敕造宁国府”五个大字。黛玉想道:这必是外祖之长房了。想着,又往西行,不多远,照样也是三间大门,方是荣国府了。却不进正门,只进了西边角门。那轿夫抬进去,走了一射之地,将转弯时,便歇下退出去了。后面的婆子们已都下了轿,赶上前来。另换了三四个衣帽周全十七八岁的小厮上来,复抬起轿子。众婆子步下尾随至一垂花门前落下。众小厮退出,众婆子上来打起轿帘,扶黛玉下轿。林黛玉扶着婆子的手,进了垂花门,两边是抄手游廊,当中是穿堂,当地放着一个紫檀架子大理石的大插屏。转过插屏,小小的三间厅,厅后就是后面的正房大院。正面五间上房,皆雕梁画栋,两边穿山游廊厢房,挂着各色鹦鹉、画眉等鸟雀。台矶之上,坐着几个穿红着绿的丫头,一见他们来了,便忙都笑迎上来,说:“刚才老太太还念呢,可巧就来了。”于是三四人争着打起帘笼,一面听得人回话:“林姑娘到了。”[4]
这段原封不动、不加注释的引文,选自小说《红楼梦》中“林黛玉进贾府”的精彩片段,因其深描贾府之雍容华贵与林黛玉之内心细腻敏感而成为经典深描,此内容也因此入选中学语文课本,成为中学生了解和学习《红楼梦》的一个窗口。这段深描,前面一部分给人一种气势煊赫,门禁森严的感觉,同时揭示了贾府荣华富贵的来源和社会地位。后面一部分深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封建贵族家庭的等级观念和礼规。作者不惜笔墨,旨在通过深描来呈现贾府的富丽堂皇与清规戒律,而这一生活环境、文化环境与林妹妹的敏感多疑的个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为人物命运安排埋下了伏笔。读《红楼梦》者,倘若不对这等细致的文字细嚼慢咽,而是只关注故事情节,恐怕永远也读不懂《红楼梦》了。红学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学科,除了它的内容之博大精深,语言之丰富优美,人物之特点鲜明,正如鲁迅指出的那样,《红楼梦》最大的特点是“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如《红楼梦》中如此的描述,可以说在文学作品中随处可见,不管是对一个家族或家庭,还是对某个人物,不厌其详的描述司空见惯,创作者有时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方法的存在,但确确实实运用了这种方法。由此可见,深描在文学创作中,就是作者将自己的观察真实地呈现给读者的一种语言表达方法,配以大量的修辞,便能活灵活现人物与情境,将读者带入作者设定的现场之中,体验故事与人物的情感与处境,达到读者读懂作者的写作意图之目的。
(三)历史创作中的深描方法
作为人文科学代表的历史学中,使用深描之鼻祖当追溯到司马迁及其《史记》。司马迁之《史记》,审择史料,创设体例,刻画人物,把先秦以来多方面的史实和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写成一部完整丰富的“通史”。从汉朝到清朝的许多史学家所接受并使用的方法,无形中都受了这种方法与范式的影响。《史记》全书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史记》内容丰富灿烂,包罗万象,而又融会贯通,脉络分明,成为通史之典范。《史记》中大量运用了深描,再现了司马迁所思所想、所闻所见、所读所写的历史真相。深描在本纪、世家、列传等人物的记述中运用得最为精彩和生动。如项羽本纪、高祖本纪中对历史人物的刻画栩栩如生,对同一事件的深描从当事人的角度各有侧重,展示了历史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的高度统一。
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范增起,出召项庄,谓曰:“君王为人不忍,若入前为寿,寿毕,请以剑舞,因击沛公于坐,杀之。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庄则入为寿。寿毕,曰:“君王与沛公饮,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项王曰:“诺。”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击。于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哙,樊哙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哙曰:“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项王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王曰:“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项王曰:“壮士,能复饮乎?”樊哙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不恐胜,天下皆叛之。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大王不取也。”项王未有以应,曰:“坐!”樊哙从良坐。坐须臾,沛公起如厕,因招樊哙出。
沛公已出,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辞也,为之奈何?”樊哙曰:“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于是遂去。乃令张良留谢。良问曰:“大王来何操?”曰:“我持白璧一双,欲献项王;玉斗一双,欲与亚父。会其怒,不敢献。公为我献之。”张良曰:“谨诺。”当是时,项王军在鸿门下,沛公军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则置车骑,脱身独骑,与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从郦山下,道芷阳间行。沛公谓张良曰:“从此道至吾军,不过二十里耳。度我至军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间至军中。张良入谢,曰:“沛公不胜杯杓,不能辞。谨使臣良奉白璧一双,再拜献大王足下;玉斗一双,再拜奉大将军足下。”项王曰:“沛公安在?”良曰:“闻大王有意督过之,脱身独去,已至军矣。”项王则受璧,置之坐上。亚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剑撞而破之,曰:“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5]221-223
此乃著名的“鸿门宴”,在项羽本纪中进行了如此详细的深描,司马迁不惜笔墨,详细描述了项王与沛公、范增与张良、项庄与樊哙等不同人物的心理活动与性格,通过鸿门宴不仅还原了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而且刻画了项王英雄气短的性格特点。同样的情节,在高祖本纪中则用了浅描的方法。
沛公从百馀骑,驱之鸿门,见谢项羽。项羽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沛公以樊哙、张良故,得解归。归,立诛曹无伤。[5]257
此处轻描淡写高祖的这段经历,一则是因为在项羽本纪中已经作了深描,高祖本纪就不能重复,而换了一种较为浅描的方法。读者不禁要问,同样的鸿门宴故事,为什么在项羽本纪中要深描?而在高祖本纪中要浅描呢?这恐怕与司马迁主观上对项羽与刘邦的态度有关,他心目中的英雄还是项羽,而描述高祖时他还得小心翼翼。在《史记》的世家与列传中,关于人物与事件的深描随处可见,同样的方法,在二十四史中,也相当普遍,不再赘述。
在现代史学著作中,黄仁宇的诸多著作受司马迁的影响最大,他亦大量使用纪传体及人物深描的方法。以《万历十五年》为例,作者在序言中明确提出铺叙的研究方法,所谓铺叙是文学与历史当中表现手法的一种,即不直接或简明扼要地讲述人物或故事,而是通过大量时代的呈现,故事的深描,人物关系的铺陈,将要表达的观点渗透于叙事之中,呈现在读者面前。
本书力图使历史专题的研究大众化,因而采取了传记体的铺叙方式。书中所叙,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因为叙及的主要人物有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即便是侧面提及的人物如冯宝,高拱、张鲸,郑贵妃,福王常洵、俞大猷、卢镗、刘綎,也统统没有好结果。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以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命,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6]
该书总共七章,写了明朝的七个人物:万历皇帝、首辅申时行、世间已无张居正、活着的祖宗、海瑞、戚继光、李贽。每个人物的写法不是直接的介绍,而是通过详细地描述他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重点刻画重大历史事件与人物命运的关系,进而让读者在故事的阅读中了解了明朝的历史,这正是一种大历史的写法,与黄仁宇所倡导的大历史理念相吻合。
通过上述考察,我们不难发现,深描作为一种人文社会科学的创作方法的历史非常悠久,可以说与艺术、文学、历史几乎同时存在。只是作为一种系统的方法被西方学者提出来以后,我们再审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此类方法,就发现它远远早于西方现代的深描方法。
二、深描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
深描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是现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们提出来的,在深描方法论的研究者中,有三位著名的学者做出了贡献,他们是英国思想家赖尔、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美国方法论专家罗曼·邓金。
(一)英国思想家赖尔的“眨眼”深描
英国思想家吉尔伯特·赖尔在他的两篇文章《思考与反思》《对思想之思考》(《赖尔文集》第二卷)中提出了一个文化范畴的“眨眼”现象,并用深描的方法呈现了这一现象的文化意义。
让我们细查一下两个正在快速张合右眼眼睑的孩子,一个是不随意的眨眼,另一个则是挤眉弄眼向一个朋友发信号。这两个动作,作为动作是完全相同的。如果把自己只当作一台照相机,只是“现象主义”式的观察他们,就不可能辨识出哪一个是眨眼,哪一个是挤眼。但是,眨眼和挤眼间的差别,无论多么不可拍摄入相,却仍然是非常巨大的。因为挤眼的人是在交流,并且确实在以一种准确特殊的方式在交流:(1)有意地;(2)向着特定的某人;(3)传达特殊的信息;(4)按照社会通行的信号密码,以及(5)没有受到其他在场者的察觉。
然而这才只是开了个头,赖尔接下去说,假设还有另外一个男孩子,为了给他的伙伴开个恶作剧式的玩笑,故意歪曲的模仿第二个男孩子挤眼的不当之处。只不过他既不是在眨眼,也不是在挤眼,他是在模仿他人挤眼时的可笑之处,这里,也存在着一个通行社会通行的信号密码。同时也传递了一个信息。只不过弥漫于空气中的,不是当事人的心领神会,而是嘲弄罢了,假如其他两个孩子以为他真的是在挤眼的话,他的整个努力就完全付之东流了。还可以进一步设想:一个想要模仿以嘲笑他人的人,如果对自己的模仿能力没有把握,或许会在家里对镜练习,那么他既不是在眨眼或挤眼,也不是在模仿,而是在排演。[1]7
显然,赖尔在这里为我们描述了不同类型的“眨眼”现象:作为生理反应的眨眼、作为交流眼神的挤眼、作为模仿搞笑的眨眼、作为演员练习的眨眼。这样便形成了“眨眼者”“挤眼者”“模仿者”“练习者”,如果我们用照相机把这些不同的眼睑张合的现象拍摄下来,恐怕难以发现他们之间的差别,而只有结合不同情境时不同的信息密码,才能真正理解不同的“眨眼”现象背后的文化意义。文化科学正是在这种情境与语言的深描中呈现其解释的意义,而非通过现象探寻什么普遍的规律。
(二)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的深描说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提出,人是悬在由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格尔茨也持相同的观点,“所谓的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制的意义之网,因此,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1]5
首先,格尔茨论述了民族志是深描。民族志学者在收集资料时对那些陌生的、无规则的以及含糊不清的资料,必须努力的把握它们的本真意义,然后加以翻译。民族志研究者访问合作对象、观察仪式、查证亲族称谓、追溯财产继承的路线、调查统计家庭人口及日记的过程中,关键在于弄清民族志对象的意义结构的分层等级,通过这些结构,描述所观察与访谈的文化现象,进而解释文化现象的不同意义。“从事民族志好似试图阅读一部手稿——陌生的、字迹消退的,以及充满省略的、前后不一致的、令人生疑的校正和带有倾向性的点评——只不过这部手稿不是以约定俗成的语音拼写符号书就,而是用模式化行为的倏然而过的例子写成。”[1]12民族志研究者阅读这部奇特的行为之书,就是在收集研究所需要的资料,这种资料可能是当事人提供的,可能是研究者自己获得的,二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而这一切必须通过深描来完成。“我们称之为资料的东西是我们自己对于他人对他们以及他们的同胞正在做的事的解释的解释,民族志的深描是多么异乎寻常地深。”[1]11
其次,格尔茨论述了民族志描述的四个特点。民族志是解释性的;民族志所解释的是社会性会话流;民族志的解释在于将这种会话“所说过的”从即将逝去的时间中解救出来,并以可代阅读的术语固定下来;民族志是微观的。
再次,格尔茨论述了从民族志描述收集微观资料的方法。格尔茨在论述人类学的方法论问题时指出,对于一门诞生于印第安部落、太平洋群岛以及非洲家族,后来变得野心勃勃的学科来说,方法论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主要是因为研究者常常受两种研究模式的影响,“琼斯村即美国”式的微观模式,“复活节岛即试验案例”式的自然试验模式。要么是一粒砂中的天堂,要么是遥远的可能性彼岸。对民族志来说,田野与记录是方法论的根本。研究的地点并不是研究的对象,人类学家并非研究村落,他们只是在村落里做研究。人类学家在田野登记社会性会话流,把它记录下来,这样做他就把社会性会话流从一件只存在于发生的那个时刻、转眼即逝的事件转变为一部存在于刻画它的可供反复查阅的记载。为此,格尔茨意味深长地说:“民族志学者干什么?——他写作。”[1]25
最后,格尔茨谈到了理论解释。一切拒绝解释的科学都将犯下共同的错误,它们似乎要有意识地将文化科学与生物或物理科学区别开来,而实质上,理论解释始终要保持与基础的联系,而不是像在科学中那样,趋于全力以赴地抽象。要么你理解一个解释,要么你不理解;要么你明白他的要点,要么你不明白;要么你接受他,要么你不接受。对于一个声称自己是一门科学的研究领域,这绝对是不行的。“理论建设的根本任务,不是整理抽象的规律,而是使深描成为可能,不是越过个体进行概括,而是在个案中进行概括。”[1]26
格尔茨在论述深描的方法时,是把它作为民族志而论述的,他的立场一方面抑制主观主义,另一方面抑制神秘主义。他认为解释人类学的根本使命,并不是回答我们那些最深刻的问题,而是使我们得以接近别人所给出的回答,从而把这些回答归于记载人类曾说过什么的记录中去。深描便是人类学家在田野中记录人类所说过的语言与行为的最有效的方法,当然这种记录少不了理论的解释与建构。
(三)美国罗曼·邓金的深描分类与应用
罗曼·邓金是美国质性研究方法的代表人物,主编过《质性研究手册》,出版了《解释性交往行动主义》《解释性民族志:21世纪的民族志实践》《研究行动:社会学方法论导论》等多部颇具影响力的方法论著作。作为方法论的研究者,他在《解释性交往行动主义》一书中,首次从方法论的角度系统总结了深描方法,该书的第五章为深描,第六章为解释,都是关于深描的专题讨论。与格尔茨不同的是,邓金不仅看重深描的方法,而且重视浅描的方法。这样,深描就从专门的人类学或民族志方法扩大到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围,使深描方法在质性研究中成为一种流行的方法。邓金认为,描述是用语言描写或者解释某事物。在解释研究中,深描是深入的、厚实的、详细的问题性经验的解释。这些解释通常是澄清一种倾向和组织行为所存在的意义。相反,浅描是缺少细节,只是简单的报道事实。深描的目的在于给读者情境再现或让读者身临其境把鲜活的经历带到读者面前,读者可以自然而然地意识到自己被捕捉到的那些经历就是深描,所以它是真实的。浅描并不是不及深描的研究方法,而是一种留有余地的研究方法,一方面浅描言简意赅,在新闻报道或诗歌中会经常使用,另一方面,浅描只是提供要点和线索,让读者更有想象力。
为了比较深描与浅描的差异,邓金以人类学家格尔茨描述他自己和妻子逃离巴厘岛斗鸡的情景为例进行了说明。
一辆满载用激情武装的警察的卡车咆哮而入。在人们发出的“Pulisi! Pulisi!”的尖叫声中,警察们跳下车冲进赛场中间,并开始来回挥舞他们的枪,就像电影中的匪徒那样,尽管并不真的开火,那个超机体的人团立刻像它组合时那样向四面八方散去。人们沿着道路跑开,许多人在墙壁后面,有人从平台下面爬过,有人蜷伏在柳条篱笆后面,或者有人急忙爬上椰子树。我和我的妻子也决定逃跑,我们跑向主城市的街道……中途另一群人落荒而逃,撞翻了一个桌子,连同桌布、三张椅子、三个茶杯,一切都陷入混乱恐慌之中。[2]86
在这里,格尔茨对自己经历过的事件进行了深描,这就是著名的巴厘岛人的斗鸡深描中的“钻狗窝”经历,格尔茨通过这样的深描叙述了作为研究者如何躲过“守门员”的防守而进入现场的偶发事件。此处如果用浅描方法,可能会这样写:“当警察来的时候,我们和当地一对情侣的茶都没喝完,就赶紧跑了。”
罗曼·邓金的另一贡献是对深描进行了分类,并分析了不同方法在研究中对应使用的范围与规则。邓金通过对深描的归纳,列出了不同类型的深描及其内容特征,主要包括:微观式深描、宏观历史深描、传记式深描、情境式深描、关系式深描、交互式深描、介入式深描、不完全式深描、注解式深描、纯粹式深描、描述解释深描。这11种深描可归纳为三大类,第1~6类描述为第1类。第7~9类为第2类,第10~11类为第3类[2]99。邓金不仅对不同类型的深描所适合的研究进行了案例说明,而且对优秀的深描和糟糕的深描进行了分析,由此而概括出优秀深描的方法规则。
三、深描在教育研究中的应用
深描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在各种人文社会科学中大量使用,当然也包括教育研究中对深描的应用。
(一)教育研究中如何处理深描的主观性与客观性问题
深描的主体是研究者,研究者的主观性是一种客观的存在,研究者是作为工具与方法的存在,其主观性不可否认。研究者从研究伦理上讲,应该持有中立的价值,力图体现研究对象的客观性。但是,研究者的主观性正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差异的表现,也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独特性的体现。研究者有智慧处理好研究中的主观与客观的矛盾问题,使其成果成为主客统一的认识成果。关于这一点,也恰恰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长期力图解决的问题,正如吉登斯在提出其社会结构化理论时指出的那样:“如果说各种解释社会学的确是主体的某种霸主地位作为自身的基础,那么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所提倡的则是社会客体的某种霸主地位。我之所以要提出结构化理论,基本目标之一就在于终结这些建立霸主体制的努力。”[7]教育研究者包括理论研究者与实践研究者,理论研究者研究教育活动,有“旁观者清”之优势,有一定的客观性,但其主观性同样存在,旁观者力求客观要求研究者不能将自己的主观加入研究结论之中。实践研究者身在实践活动之中,参与并体验实践过程,有“当局者迷”之困惑,其客观性需要保障。鉴于此,只有旁观者与当局者结合的研究,才能有效解决“清”与“迷”的问题,同时解决主观与客观的矛盾问题,形成主位与客位统一的研究。
(二)教育研究中深描是方法论还是方法的问题
关于深描到底是方法论还是一种方法的问题,笔者在几篇相应的文章中已经进行了阐释。深描作为方法使用,必须有其理论的基础。解释学、现象学、扎根理论、叙事研究等均为其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持,从中可以寻找到人文社会科学中使用深描的依据。深描作为方法使用同样还有一定的规则,笔者提出了两种思路,一种是作为一种专门方法的独立使用,另一种是作为与其他质性研究方法的结合使用。如在课堂研究中提出使用观察、访谈、深描、解释的课堂志研究方法。
(三)教育研究中深描与叙事的关系
许多研究者在使用了深描之后,会产生一个困惑,即深描和叙事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在某种程度上二者确实有相似性,二者之间的共同点是:首先,二者都强调语言的价值,用语言来表达研究的过程与结果。其次,二者都需要通过故事或案例来完成。再次,研究者都是作为主体参与研究过程,对研究者的研究素养有较高的要求。二者之不同点表现在:深描是研究者建立在自身的观察、访谈的基础上的描述,深描的过程中伴随着理论的解释,最终形成一个多元视角的案例。叙事研究强调关键事件和关键人物,并通过专门的故事情节揭示内在的关系,一般以第一人称的叙述为主,研究者作为旁观者客观真实地记录下来,在厘清其时间、地点、人物、关系的基础上,叙述出一个完整的故事。从本质上讲,二者均属于人文社会科学中常用的研究方法,教育叙事研究中有深描的应用,深描研究中最终也会形成一定的案例。深描作为一种方法在教育研究中应用起来更方便,可以体现教育研究的独特性,所谓学校志、课堂志本身就是深描的方法,它具备质性的、微观的、直观等特点。
(四)教育研究中某一类型深描的单独使用
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应该与自然科学有所不同,自然科学是实验科学,人文社会科学是实践科学。教育学属于人文社会科学,深描旨在以解释学为方法论,在研究中体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独特性,不是探寻规律的科学,而是寻求解释的科学。教育研究中的深描方法,根据研究的需要,以不同的深描类型,完成对教育活动及其主体的呈现,深描总是伴随一定的理论解释。
情境式深描,一般应用在对学校或课堂教学活动的呈现。情境式深描一般将教育活动的主体置于一定的环境之中,这一环境是立体的、丰富的,主体在这些环境中的活动与周围的物质条件、声音、他者等均有关系。情境式深描通常以周围环境与条件的描述来衬托人物的特点与处境,教育活动就是在此情境中发生。一些教育的经典著作中都不难发现对情境的深描。如李书磊在《村落中的国家》一书中,为了呈现胡麻营乡村学校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作者对这所学校所在的村及周边的环境以及学校内容的环境进行了深描,让人了解了这所学校之偏僻及条件之有限,然而,正是这所偏僻而遥远的乡村学校,却忠实地落实国家的课程并有序地开展教学活动,再现了国家教育意志的乡土根系。
传记式深描,一般应用于人物的描述与呈现方面,让读者面前站立一位活生生的老师或学生,进而对他的教育故事进行叙述。
王小刚个子不高,瘦瘦的身躯上挂着一套肥大的西装,脚上蹬着一双厚厚的旅游鞋(我当时的第一想法是:这孩子穿着他爸的西装来了。后来问他,他说是他自己的,故意做得大一点,可以穿得久一些)。他的面部表情看起来比他同龄的孩子要更成熟:长圆的双眼透着精明和一丝幽怨。当金校长告诉他“北京来的专家们想和你谈谈,了解你的一些情况”时,他立刻回答:“可以,没问题”,可是他带一点漠然的眼神和紧咬着的嘴角告诉我:这是一个精明、倔强,而且有主见的孩子。[8]
这是陈向明《王小刚为什么不上学了》中的一个片段,她用传记式深描呈现了第一次见到的王小刚同学的具体形象,与后面同学、老师、家长叙述中的王小刚同学进行比较,由此铺垫了王小刚不上学的真正原因。
微观式深描,在教育研究中常常用来深描教育活动中具体的、微观的人或事,以小见大,解剖麻雀,进而洞察现象背后的真相并作出合理解释。
有的学生等教师的问题刚提出,他们便很快地举手了,其中有的学生还举得特别高,希望教师能注意到他。有的学生在举起手的同时,还伴随着申请回答问题的声音,如“老师,让我来回答!”或者“老师,我!我!我!”等等。有的学生不但举着手,还伴随着击打桌子的声音以引起教师的重视,为自己争得回答问题的机会。当然还有的学生不举手,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想回答问题,也许他们想通过这种独特的方式引起老师的注意,从而获得回答问题的机会。[9]
这是笔者在课堂研究中深描的一个普通的举手现象,举手者与不举手者只是表面的现象,用照相机拍下来,看不出本质的区别。可是当研究者通过访谈了解了不同的举手者真实的心理想法时,才能明白不同的举手者背后的文化意义。研究者将这种过程详细客观地呈现出来,就是微观式深描。
邓金所总结的十一种深描都可以在教育研究中单独使用,使用时可结合他提出的几个重要维度来选择不同的方法,如传记性、历史性、情境性、关系性、互动性等维度,这种单独使用的方法仅举上述三例,不再赘述。
(五)教育研究中深描与其他质性方法的混合使用
笔者在长期的课堂研究中,提出了一种课堂志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将观察、访谈、深描、解释结合起来使用,形成组合优势[10]。研究者在听评课活动中,通过专业的观察发现问题,对问题的当事人进行深度访谈,以印证观察者观察到的现象的真实性,将观察所见与访谈所闻,通过语言的深描与理论的解释叙述出来,进而形成一个案例。这种课堂志的研究方法,经过十多年的完善已经相对比较成熟,成为研究者和一线教师听评课活动中形成案例的主要方法。教育案例的积累为教育研究和教师教育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成为教育专业化的有效支撑体系。
总之,深描作为一种人文社会科学创作与研究的方法,由自在的使用逐渐发展成为自为的应用,在方法学中已经有它专门的地位。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在不同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开始使用深描的方法,并将这种方法与现象学、解释学的理论结合起来,形成不同于自然科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独特方法。教育学的研究,也应加强其独特性,将深描的方法应用到课堂志与学校志的研究之中,积累大量的研究案例,建构以实践质料为基础的新教育专业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