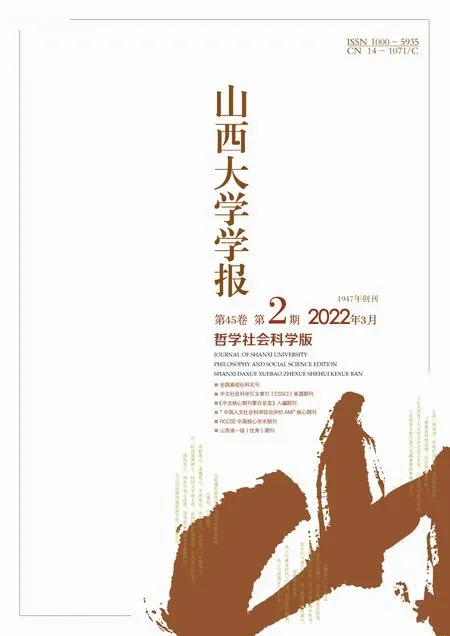本体、文体与主体:黄庭坚的词学理论
彭国忠,刘泽华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241)
目前,学界对黄庭坚的研究,存在三个不平衡:一是就文学与非文学而言,对黄庭坚的文学成就研究相对充分,非文学成就诸如书、画的研究相对不足;二是就诗文创作而言,对黄庭坚诗歌、诗学的研究较为充分,对黄庭坚文的研究相对不足;三是就词学领域而言,对黄庭坚词的研究较为充分,对其词论、词学观、词学思想的研究相对不足。本文集中讨论黄庭坚的词学理论。黄庭坚的词学理论,集中体现在著名的词学专题文章《小山集序》中;此外,还大量出现在词序、诗文题跋、尺牍中。黄庭坚的词学理论,包括本体论、文体论、主体论三个方面。
一、词的本体论
词的本体论,是对词之为词在本质特征和规定性方面的认识和看法。黄庭坚的本体论,表现在三个方面。
在词之根本上,黄庭坚提出词为“诗之流”的词学观,认为词是诗歌的分支、流衍,本质上与诗歌一致。在写给外甥徐俯的书信中说:“所寄诗,度超今人以千百,但恨不及古人耳。……漫寄乐府长短句数篇,亦诗之流也。观一节,可知侏儒矣。”[1]2028-2029(《答徐甥师川》)在这里他明确称自己所作词是“诗之流”,如同这位外甥徐俯寄给他的诗歌一样,可以表现出他的创作情况。汉代桓谭《新论·道赋》引谚语云:“侏儒见一节,而长短可知”[2]。钟嵘《诗品》曾引以论诗:“《团扇》短章,词旨清捷,怨深文绮,得匹妇之致。侏儒一节,可以知其工矣。”[3]由部分知全体,黄庭坚于此传达的是词可以代表他与外甥别后的创作情况,而称词为“诗之流”,正可与苏轼评张先词的“诗之裔”说等量齐观,与苏轼“诗之裔”说高度一致。苏轼“提出词为诗裔,标举‘古人长短句诗’以揭示词之渊源。这一方面是为了把词由‘艳科’‘小道’提高到与诗并驾齐驱的正统地位而在思想观念上廓清谬误,正本清源,提供其历史依据;另一方面也是借此揭示词之创作应予以努力的方向,倡导词之诗化,向诗回归,为其革新词体、词风的实践张扬旗帜,开辟道路。”[4]黄庭坚还直接把词称作诗,其《书玄真子〈渔父〉赠俞秀老》云:“金华俞秀老,物外人也。尝作唱道歌十章,极言万事如浮云,世间膏火煎熬可厌,语意高胜,荆公乐之,每使人歌。秀老又有与荆公往返游戏歌曲,皆可传。长干、白下舟人芦子或能记忆也。此《渔父》诗,秀老必喜之,辄因清老远寄,幸可同作。”[1]721唐代张志和号玄真子,所创作的“西塞山前白鹭飞”等五首词,最早就被称为《渔父》(1)参见曾昭岷、曹济平等《全唐五代词·正编》卷一张志和《渔父》题注,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5页。,所谓“此《渔父》诗”,即题目中所言其所书“玄真子《渔父》”词,这是显而易见的。俞紫芝字秀老,弟澹字清老,二人皆与王安石交往,秀老名更甚,所作《唱道歌》十章,及与王安石往返歌曲皆不存,王安石词中保留有《诉衷情·和俞秀老鹤词》数阕。《答郭英发帖》之三云:“东坡公听琵琶一曲奇甚。试用澄心纸写去,因诗句豪壮,颇增笔势。或有嘉石,试刊之斋中,亦一奇事也。”[1]1831书中所说苏轼“听琵琶一曲”,即苏轼隐括韩愈《听颖师弹琴》诗而成的词,苏轼曾记欧阳修辨别韩愈所写其实不是听弹琴,而是听琵琶(2)苏轼《水调歌头》(昵昵儿女语)序云:“欧阳文忠公尝问余:‘琴诗何者最善?’答以退之听颖师琴诗最善。公曰:‘此诗最奇丽,然非听琴,乃听琵琶也。’余深然之。建安章质夫家善琵琶者,乞为歌词。余久不作,特取退之词,稍加隐括,使就声律,以遗之云。”;苏轼隐括而成的词《水调歌头》,被称为“诗(句)”。黄庭坚深知诗词之别(3)黄庭坚《渔家傲》(踏破草鞋参到了)序云:“余尝戏作诗云:‘大葫芦挈小葫芦,恼乱檀那得便沽。每到夜深人静后,小葫芦入大葫芦。’又云:‘大葫芦干枯,小葫芦行沽。一住金仙宅,一住黄公垆。有此通大道,无此令人老。不问好与恶,两葫芦俱倒。’或请以此意倚声律作词,使人歌之,为作《渔家傲》。”所谓“倚声律作词,使人歌之”,指词文体。可知他已有独立的词体意识。,其“诗之流”说,称词为诗,亦与苏轼一样,旨在推尊词体,提高词的地位。
王灼《碧鸡漫志》卷二称黄庭坚词韵致得苏轼十七八,窥见其师生间词创作的消息相通;山谷也以其《水调歌头》(瑶草一何碧)被人评为不减苏轼《水调歌头》中秋词而自喜;晁补之《评本朝乐章》认为黄庭坚的词是“着腔子唱好诗”[5],没有与苏轼一致的诗化的词学观,很难“当得”这样的评价。
在词的体式上,黄庭坚持长短句说,即词的句式长短不齐,而非近体格律诗的齐言句。长短句是晚唐五代新兴的一种诗体,从七言歌行中分化而来,以五七言为主,渐渐过渡到曲子词(4)参见:施蛰存.词学名词释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8:10.,到北宋中后期,得到苏轼、黄庭坚的大力揄扬,遂成为词体之称。黄庭坚的《西江月》(月侧金盆堕水)序云:“崇宁甲申,遇惠洪上人于湘中。洪作长短句见赠云。”[6]167序中所言惠洪长短句,指《西江月》词,见载于《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八引《冷斋夜话》。然黄庭坚更喜将表示句式的长短句,与表示诗性的“乐府”(5)施蛰存先生指出:“到了唐代,古代的乐曲早已失传,或者不流行了,诗人们虽然仍用乐府旧题目作歌词,事实上已不能吟唱。这时候,‘乐府’几乎已成为一种诗体的名词,与音乐无关。”见:词学名词释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8:13.合在一起,兼有诗性与句式。在《答王观复》书中云:“见和东坡《七夕》长短句,及‘可惜骑鲸人去’之语,既嘉足下好贤,又深叹古来文章之士,未尝不尔也。草草和成二章,言无可采,当面一笑耳……但有乐府长短句数篇,漫往。”[1]2004苏轼有七夕词多篇,如《渔家傲·七夕》《鹊桥仙·七夕》《鹊桥仙·七夕和苏坚韵》等,黄庭坚亦有《鹊桥仙·次东坡七夕韵》《鹊桥仙·席上赋七夕》,此文前部单称长短句,后部复用乐府长短句之称。故“东坡七夕长短句”即指苏轼七夕词,“漫往”的乐府长短句指自己的词。又其《念奴娇》(断虹霁雨)云:“客有孙彦立,善吹笛,援笔作乐府长短句,文不加点。”[6]8前引致徐俯书亦称自作词为乐府长短句。《与宋子茂书》云:“闲居亦绝不作文字,有乐府长短句数篇,后信写寄。”[1]1789这是在党争激烈、旧党遭受迫害时,因惧怕类似苏轼“乌台诗案”式的境遇而讳言作诗作文,却于小词不讳,苏轼、陈师道等皆如此,故乐府长短句指词。《答王观复》:“承索鄙文,岂复有此?顷或作乐府长短句,遇胜日,樽前使善音者试歌之,或可千里对面,故往手抄一卷。”[1]1971上述皆称词为乐府长短句。《跋知命弟与郑几道驻泊简二》称“知命作乐府长短句及小诗”[1]1636,乐府长短句与“小诗”并举,亦指词。黄庭坚对“长短句”“乐府长短句”的称类远比苏轼为多,而与苏轼的“古人长短句诗”一致。
在词与音乐关系上,黄庭坚认为词是合乐可歌的。换言之,把词认同为诗歌,并不妨碍黄庭坚对词之音乐性的认识。乐府本即指音乐机关和入乐的诗歌,长短句也是因为所配之乐节奏不一而产生的句式变化(6)施蛰存先生指出:“中晚唐时,由于乐曲愈趋于淫靡曲折,配合乐曲的歌诗产生了五七言句法混合的诗体,这种新兴的诗体,当时就称为‘长短句’。”见:施蛰存.词学名词释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8:10.,无论是“乐府”还是“长短句”,都有合乐可歌性在。黄庭坚能歌是毋庸置疑的,连论词持苛刻标准的李清照也把他置入知词“别是一家”的词人中。故歌唱性对于黄庭坚是必然的要求。其《答人简》云:“琅琊秀惠,清歌常有出蓝之声。比得数新曲,恨未得亲教耳。但鄂渚亦有二三子可与娱,毎至樽前,未尝不怀英对也。”[1]2254-2255自己最近得到几只新曲,恨不能亲自教给擅长清歌的秀惠。则其懂音无疑。《诉衷情》(一波才动万波随)序:“在戎州登临胜景,未尝不歌渔父家风,以谢江山。”[6]211这是他自歌的证。《答从圣使君》云:“有数篇乐府,谩录呈,新旧相半。彼营妓有可使歌者乎?此乃有三二人,亦可教,但病懒,又不饮,亦少味耳。”[1]1969表示不知道自己寄给对方几篇歌词,彼处的营妓是否有可歌的。《答王观复》云:“顷或作乐府长短句,遇胜日,尊前使善音者试歌之,或可千里对面,故往手抄一卷。”[1]1971是说自己不能与对方见面,将所作的词寄给他,当良辰美景饮酒时,请会唱歌的人歌唱,就如同双方会面一般。《与运使中舍书》云:“正辅携去新《渔父》篇,尝经匠者一按之否?”[1]1810所谓匠者一按,就是请懂音的人弹奏,弹奏他新作的《渔父》词。《与韦深道简》中,再次对自己的词可歌而无人可以写谱表示遗憾:“欲写二三新乐府去,适伤冷物倦甚,后未能耳……近又得数篇,亦前三篇之流,稍安快当录去,恨此陋邦,无人能写谱耳。”[1]2197写谱,即将谱子写出,其词原是可歌的。这些表述,一方面表现出黄庭坚懂音律能歌,另一方面显示出他的词可歌。所以,他有时称词为曲。《答王子厚》云:“往尝作建溪茶曲,不审见之否?”[1]1763建溪茶曲,即他所写《满庭芳》茶词。《与东川路分武皇成乐共城》云:“有戎州旧曲数阕,到泸州得暇,当写寄也。”[1]2058旧曲,指以前作的词。也正是从歌唱性出发,他对苏轼隐括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入《哨遍》,罕见地表示否定的态度。在《与李献父知府书》中,他说:“遍观古碑刻,无有用草书者,自于体制不相当,如子瞻以《哨遍》填《归去来》,终不同律也。”[1]1774古碑刻没有用草书者,他认为是二者体制不相称;而苏轼之隐括,是因为二者“不同律”,律,可以理解为“体制”,也可理解为格律、音律,而《归去来兮辞》与《哨遍》“体制”之别,亦包含“辞”与“词”之体式、格律在内。苏轼隐括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成《哨遍》,获得很多称赞,黄庭坚是宋代第一个指出二者不同律的人。
概括而言,可歌的长短句诗,就是黄庭坚对词的本质属性的认识。
二、词的文体论
黄庭坚对词的文体特性有充分认识,他的文体论表现在对词的文体定位、词“道人意中事”的抒情性、以“清丽”为词美之标准、词要“体物浏亮”的形象描写四个方面。
首先是对词的文体定位,他明确提出词体兼有“缘情绮靡”“体物浏亮”的特性,也就是介于诗、赋之间。在《与郭英发帖》之二中他说:“昨日辱手笔,留来使取答,会彭守报过,遂不得遣,经昔伏想,日用轻安。所作乐府,词藻殊胜,但此物须兼缘情绮靡”“体物浏亮,乃能感动人耳。辄拟作三篇,不知可用否?又奉为写得文字两轴,须行日作送路也。”[1]1831所谓“缘情绮靡”“体物浏亮”,出自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7]99在黄庭坚看来,词兼有诗和赋两种文体的特征。“陆机本意,‘缘情’的情,显然是指感情,旧来所谓‘七情’。《文赋》说:‘信情貌之不差,故每变而在颜。思涉乐其必笑,方言哀而已叹。’以乐、哀包举‘七情’而言,可见这‘情’也并非像有些人所理解的,只限于消极哀伤一个方向……‘绮靡’连文,实是同意复词,本义为细好……原来‘绮靡’一词,不过是用织物来譬喻细而精的意思罢了。”(7)周汝昌《陆机〈文赋〉“缘情绮靡”说的意义》,张少康先生指出:“周汝昌先生对‘缘情’的解释,是比较符合陆机原意的”,关于绮靡的解释“与李善所注相一致,深得《文赋》所言本意。”参见:张少康.文赋集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11,112.而“陆机关于诗赋的‘缘情’‘体物’的论述,我们应当看作是一种互文见义的说法。事实上,赋也是要‘缘情’的,诗也是要‘体物’的,不过在当时的创作中,诗歌‘缘情’更突出一些,辞赋‘体物’更突出一些。所谓‘体物’实质上是一种形象的描写,它比较明显地反映了文学的形象特征。所以,陆机对诗赋的‘缘情’‘体物’的特征的论述,已经触及了文学艺术的两个根本性特点:形象和感情。它充分说明陆机对文学艺术的特征有很深刻的认识。”[7]131-132套用这个说法,黄庭坚的词“兼缘情绮靡、体物浏亮”,已经揭示了词体的文学性特点。纵观唐五代以来之词史和批评史,还没有哪一家像黄庭坚这样关注词的文体性问题。苏轼重视的是词的“诗化”,提出词为“诗之裔”说,以推尊词体,某方面恰恰忽略了词体自身特性。与黄庭坚同辈的李之仪,从风格角度区分诗词,认为长短句“自有一种风格,稍有不合,便觉龃龉”[1]3264;而秦观则将歌唱性放在第一位,文学性所谓“好文章”次之(8)参见:彭国忠.秦观词论刍议[M]∥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24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而这个好文章甚至根本不是那么重要。所以,黄庭坚对词体文学性的提倡,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
黄庭坚认为词是“道人意中事”的抒发情感、披露情怀的文体。其《跋马中玉诗曲字》云:“至其作乐府长短句,能道人意中事,宛转愁切,自是佳作。”[1]1638马中玉即马瑊,《全宋词》录其《玉楼春》(来时吴会已残暑),作者署“马成”,误,参孔凡礼先生《苏轼年谱》(9)孔凡礼《苏轼年谱》卷二十九:“瑊字中(一作忠)玉,庐州合肥人……《山谷全书·别集》卷十六与瑊第四书……卷八《跋马中玉诗曲字》赞瑊翰墨颇有劲气。《淮海集》卷八、《宗伯集》卷七有次瑊韵。”与苏轼、黄庭坚、秦观等交往,且字中玉的合肥人,不可能另有马成其人。见:孔凡礼.苏轼年谱: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8:924,925.。苏轼有《木兰花令》,题曰“次马中玉韵”[8],可知马瑊确实能词。黄庭坚称赞马瑊乐府长短句“能道人意中事”,即说出人心中所欲言。《又书自草〈竹枝歌〉后》云:“刘梦得《竹枝》九篇,盖诗人中工道人意中事者也,使白居易、张籍为之,未必能造也。”[1]1634高度评价刘禹锡贬谪湖湘期间所作《竹枝词》九首,长于抒发作者内心情感,这一点是白居易、张籍可能达不到的。对自己所作《醉落魄》词二篇呈吴元祥、黄中行,他自评亦是“似能厌道二公意中事”[6]103。意中事,并非一般所认为的仅仅指心事,当是内心种种情感的集合体,观评马瑊词意中事的“宛转愁切”,可见其偏于作者内里深处幽微深曲之情感。个人抒情,也不与时代、社会隔绝,政治怀抱、身世遭际之感,也属于“意中事”范畴。在《跋王君玉〈定风波〉》中,他提出“王君玉流落在外,转守七郡,意不能无觖望。然终篇所寄,似为执政者不悦,上独怜之耶?”[1]1637王琪《定风波》词一方面表达自己“春来秋去苦茫然”的觖望愁绪,一方面描写“风雨满枝花满地”“却教纤草占流年”的现实,而首句点出“把酒花前欲问天”自屈原以来的问天姿态,结句归于“却疑春色在婵娟”[9]的深忧,所以黄庭坚评论说执政者不悦,而希望皇帝能够怜悯王琪。他评秦观的名作《踏莎行》(雾失楼台)“少游发郴州,回横州,多顾有所属,而作语意极似刘梦得楚蜀间诗也”[1]1636(《跋秦少游〈踏莎行〉》),多顾,多所顾望、盼望,是与陶渊明的“悠然见南山”无意所见完全不同的一种目标性行为,多顾而有所属,何属?虽未明言,但说作意极似刘禹锡谪居于楚蜀间的诗歌,便是回答,是肯定秦观《踏莎行》流露出贬谪途中的兴怀,一种政治感慨。
黄庭坚以词写人“意中事”,与苏轼“诗化”词学观一致,或者可以看作是对苏轼的响应或者呼应。值得注意的是,在如何抒情上,他也与苏轼一致。苏轼曾评张先“微词宛转,盖诗之裔”[10](《祭张子野文》),谓张先词委婉曲折。前引黄庭坚评马瑊词“能道人意中事,宛转愁切”[1]1638(《跋马中玉诗曲字》),宛转亦是对词体抒情的美学规范,不是直抒更不是叫嚣。在这一点上,二人都有深刻体认且高度一致。
在词体审美上,黄庭坚以“清丽”为词美之标准。他提出词“须兼缘情绮靡、体物浏亮,乃能感动人”,绮靡是对整体抒情效果而言,要华美、要感染人。具体到词的审美,“清丽”是他的最高标准。他评其弟知命“作小诗乐府,清丽可爱”[1]693(《题知命弟书后》);评王观复“乐府长短句清丽不凡,今时士大夫及之者鲜矣”[1]1402(《书王观复乐府》),王观复的词清丽而不凡,或者说因为清丽而不凡,在当时很少有士大夫能够达到;称赞驸马都尉王诜“其作乐府长短句,踸踔口语,而清丽幽远,工在江南诸贤季孟之间。”[1]1634(《跋王晋卿墨迹》)认为王诜的词清丽悠远,甚至认为可与南唐君臣的词相媲美。《答人简》云:“寄惠中秋歌头,清丽可喜。欲和去,以久不作文,遂井泥不食矣。”[1]2217称赞对方的词清丽可喜。凡此可见,清丽是他对词的最高评价。我们知道,作为文学批评范畴的“清丽”,同样出自陆机《文赋》:“或藻思绮合,清丽千眠,炳若缛绣,凄若繁弦”[7]145,是说文章的才思如绮之组合,清新而华美;其鲜明美丽如五色缛绣,其凄哀如琴瑟之繁弦。黄庭坚借用《文赋》的概念,建立词作为文学体式的审美标准。而以“清”论词,又是对词学自身资源的取用。早在五代后蜀时期,欧阳炯《花间集序》已经提出“清绝”的标准,黄庭坚在其他场合,也以“清”为论:《跋知命弟与郑几道驻泊简》再论其弟词云:“知命作乐府长短句及小诗,皆清苦愁绝,可传可玩,非今号能文者所能仿佛也。”[1]1636清苦,清俊寒苦,这是兼论知命遭际及词的内容而言,而“清苦愁绝”应该包含欧阳炯的“清绝”在内。在《书船子和尚歌后》中,他对船子和尚《渔父》词的评价,亦以清为标准:“船子和尚歌《渔父》,语意清新,道人家风处处出现,所以接得夹山水洒不着。”[1]1645“接得夹山水洒不着”,乃宗门公案可不论,“语意清新”亦合其词内容与语言特点而论。
黄庭坚主张词要“体物浏亮”,要鲜明地描摹事物、景物、人物的形象,以形象抒情显意。他评论苏轼隐括词《醉翁操》,称其“词与声色相得”[1]1482,文辞与声音、色彩相称相宜。他与苏轼关于改写张志和《渔歌子》词的争论,存在作者意图与读者接受错位的问题,宋人有不同说法,《苕溪渔隐丛话》载苏轼语:“问其得意,自言以水光山色替却玉肌花貌”[11]330,释惠洪《冷斋夜话》则引黄庭坚自述语,有“独谢师直一读知吾用意,谓人曰:‘此郎能于水容山光、玉肌花貎无异见,是真解脱游戏耳’”[12],自评或借他人语评论的“水容山光”与“玉肌花貌”,皆是形象性描写,前者系自然景物,后者乃人物形象。黄庭坚论词的“体物浏亮”,尚有描写社会生活、反映风俗人情之意,他尤其对地方风俗非常在意。他评刘禹锡在夔州所作《竹枝歌》云:“刘梦得作《竹枝歌》九章,余从容夔州歌之,风声气俗皆可想见。”[1]1633(《跋〈竹枝歌〉》)认为《竹枝歌》反映了夔州的风俗民情,几百年后他到夔州,歌其词还可以想见当时的风俗民情,又称赞《竹枝》九首“词意高妙,元和间诚可以独步。道风俗而不俚,追古昔而不愧,比之杜子美夔州歌,所谓同工而异曲也。”[1]657(《跋刘梦得〈竹枝歌〉》)撇开对《竹枝》艺术价值的评论,“道风俗”正如前一篇跋语所言刘禹锡《竹枝》反映夔州的风土人情。他曾经向南方僧人请教《牧护歌》何意,对方不能回答;后来听到有人唱刘禹锡任夔州刺史时所作《牧护歌》,似乎是赛神曲,也不能理解,“及在黔中,闻赛神者夜歌,乃云听说侬家牧护,末云‘奠酒烧钱归去’,虽长短不同,要皆自叙致五方之语,乃知苏傒嘉州人,故作此歌,学巴人曲,犹石头学魏伯阳作《参同契》也。”[1]648(《题牧护歌后》)《牧护》,或作《穆护》,而穆护是唐代对祆教传教士之称,《旧唐书·武宗纪》:“勒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还俗,不杂中华之风。”[13]606事涉外来宗教,黄庭坚先向僧人请教,恐怕有循穆护之名以责实之意,但“侬家牧护”及“奠酒烧钱”,应该是外来宗教已经与本土风俗同化了,而终归于地方赛神风俗的描写。
三、主体论
黄庭坚的词学批评,具有很强的主体意识,他是宋词批评中较早建立主体意识的批评家。他很少孤立地论词评词,更多的是与词人其人、与词人其他文体的创作一起论说。在少数的词作专论中,他同样与词人或者词人的其他作品相联系。为苏轼词作跋,他指出苏轼曾经为陈慥的《无愁可解》词作序引,世人遂认苏轼为龙丘子,而不知那是陈慥的别号,他称之为“所谓盖有不知而作之者”[1]1638(《跋东坡长短句》),可见他主张“知而作”,知人论世是他评词论词的前提。评论晏几道的《小山词》,对晏几道身世遭际的极大关注,也就是晏几道平生“四痴”说,使这篇《小山集序》与晏几道的自序,构成宋代词学主体批评的经典文本。他评王诜词,与王诜书画合论,说其所画水石云林“缥缈风尘之外”[1]1634,将来不愧于小李将军;其词清丽幽远,在南唐君臣之间;其所书《戒坛院佛阁碑》“文句与笔画皆顿进”[1]1634(《跋王晋卿墨迹》);评马瑊词,也是与其书法、诗歌一起,认为他的书法有劲气,似李建中,而缺少妍丽;诗句不草草,有古人诗歌贮藏在胸中,再评其词(《跋马中玉诗曲字》)。评其弟知命之词,先论其为人豪放,以意气是否相投与人交往,犹如《庄子》中的人物支离疏,“攘臂于稠人广众中”[1]693,然后论其诗词(《题知命弟书后》)。一方面,表面上这些人的词与诗歌、书法是一个艺术集合体,深层原因是诗词书画皆属于“艺”,而其人之性格、人品等属于“德”,德为本根艺为末器;另一方面说明他对词创作主体的优先关注,也反映他把主体的创作活动看作整体,可以说,对词创作主体的重视,是黄庭坚异于他人、超越他人的地方。
黄庭坚的词学主体论,包含三个层面:读书深思,有自己独立见解,不取媚于世;人格高逸脱俗,不依傍权贵求取功名富贵;有超凡的文学表现能力和独立的文学标准,不受世俗左右。前二者属于道德伦理层面,后者为才情艺术层面。
首先,他主张词人要读书深思,有独立见解,不取媚于世。黄庭坚非常看重读书功夫,他曾经教人“闲居当熟读《左传》《国语》楚词、庄周、韩非,欲下笔略体古人致意曲折处,久久乃能自铸伟词,虽屈宋亦不能超此步骤也。”[1]2287(《书枯木道士赋后》)读书目的在于体会古人用笔致意曲折,自铸伟词。论词,他一面称赞王观复“乐府长短句清丽不凡”,一面要他“熟读元献、景文笔墨,使语意浑厚乃尽之”[1]1403(《书王观复乐府》)。晏殊、宋祁皆以词名显称于时,但黄庭坚未直言读二家词,而是“笔墨”,所指不仅仅是词,而是全部文字。所谓语意浑厚,不只是词作中有典故、有意境,还有来自主体内部的学养、涵养等深层的特质,当然,学问也是其中之一。这与李清照《词论》中对晏殊等人的评论恰成对照:“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11]254李清照是反对以学问为词,坚持词“别是一家”,而黄庭坚主张词人多读书,另有深意。在他看来,晏几道“平生潜心六艺,玩思百家,持论甚高,未尝以沽世。”[1]413六艺,儒家的六部经典,《礼》《乐》《书》《诗》《易》《春秋》。他认为晏几道潜心阅读儒家六艺之外,还研究探索百家之说,形成了自己的独立见解。晏几道持论甚高,一则不屑于世人知道,一则亦不为世人所知,所以说“未尝沽于世”。读书对于黄庭坚不是为了把自己高价售于帝王家,而是提升个人的修养,具有独立的思想、独到的见解。
其次,要求词人人格高逸超俗,是黄庭坚主体论的另一内涵。他论晏几道的四痴,其中“仕宦连蹇,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是说晏几道仕途蹭蹬,但从来不曳裾于贵人之门,向权豪摇尾乞怜;“费资千百万,家人寒饥而面有孺子之色”,称赞晏几道为他人不惜破资千百万,而自家人则饥寒相迫;“人百负之而不恨,己信人终不疑其欺己”[1]413,赞其待人诚恳,即使遭人反复背叛、被人辜负欺骗,他都不怀疑不怨恨。被他多次评论的知命弟,也是晏几道一般人物:“知命弟,江西豪士也。意气合其臭味,极力推挽之不遗余力,有味其言之也。至不合其意,虽衣冠贵人,唾辱之如矢溺。亦自以废疾,如支离疏攘臂于稠人广众中,物亦不能害之。”[1]693(《题知命弟书后》)豪士、意气云云,与晏几道非常接近,是他所看重的词人品质。这种人品,他更多时候用不俗、脱离尘俗、高妙超逸形容。在《跋东坡乐府》中,他评苏轼《卜算子》(缺月挂疏桐)词云:“东坡道人在黄州时作。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跋东坡乐府》)[1]660称赏苏轼胸有诗书、笔无俗气,不是吃人间烟火的人所能写出,词人品性、胸襟之高可见一斑。在《跋子瞻〈醉翁操〉》中又说:“人谓东坡作此文因难以见巧,故极工。余则以为不然,彼其老于文章,故落笔皆超轶绝尘耳。”[1]659同样注目于词人超越尘俗的德性。《跋秋风吹渭水词》云:“三十年前,有一人书此曲于州东茶园酒肆之柱间。或爱其文彩指趣,而不能歌也。中间乐工或按而歌之,辄以鄙语窜入,睟然有市井气,不类神仙中人语也。十年前,有醉道士歌此曲广陵市上,童儿随而和之,乃尽合其故时语。此道士去后,乃以物色逐之,知其为吕洞宾也。”[1]1579市井气、鄙语,都与神仙人、雅士格格不入。他还借僧元之口,评论苏轼隐括欧阳修《醉翁亭记》而成的《醉翁操》词有精深微妙的意旨,不是尘俗的弹奏者和听众所能轻易领会的(10)见《元师自荣州来,追送余于泸之江安绵水驿,因复用旧所赋此君轩诗韵赠之,并简元师从弟周彦公》,《年谱》引黄庭坚跋。(任渊,史容,史季温,注.刘尚荣,点校.黄庭坚诗集注:别集卷下[M].北京:中华书局,2003:1482.)。虽然是从读者接受角度立论,但作者之高怀雅意是前提,凡此,都强调词作者超逸脱俗的人格、人品、人生境界与词创作之间的关系。
再次,词人要有超凡的文学表现能力和独立的文学标准,不受世俗左右,是黄庭坚主体论的第三层要义。文学是文人慧业,文学能力决定作品高下,与众不同决定作品独创性。黄庭坚评王观复词“今时士大夫及之者鲜矣”[1]1403,评其知命弟词“非今号能文者所能仿佛也”[1]1636,评刘禹锡《竹枝词》九首,“使白居易、张籍为之未必能也”[1]1634,皆着眼于词人的独创性而言。他反对苏轼隐括词《醉翁操》是“因难以见巧”之说,而认为苏轼“老于文章”,故“极工”,这是从苏轼整体文学能力、表现才华立论。他在《小山集序》中,先是运用传统文学批评方法,知人论世,以人论词,说晏几道满腹不平之气,为人奇谲超逸,然后称道他“文章翰墨自立规模,常欲轩轾人,而不受世之轻重。”[1]413自立规模,就是有自己的程式、标准,自己的风貌和特色;不受世之轻重,就是不接受世人的轻重标准。晏几道有自己的文章文学标准和文学特色,并准备以此衡量评价他人,而不受世人标准的影响。这一点被黄庭坚放在晏几道“四痴”之前陈述,可见其重要。而四痴之二,黄庭坚再次予以强调:“论文自有体,不肯一作新进士语,此又一痴也。”[1]413先说晏几道论文自有体式规格,然后才是不肯写出新进士风格的作品,甚至不出现新进士语。科举时代,读书人实现自我价值的出路在于参加地方和朝廷举行的各种类型的考试,平时也要模拟考试的文体进行训练,写作程式文。黄庭坚生活的北宋中后期,朝廷以王安石三经新义为统一教材,士人接受的是王安石对经典的阐释,录取的都是歌颂新法的士人。黄庭坚强调“不肯一作新进士语”有其时代语境,但要求词人有自己的文学标杆,则具有普遍意义;前后两次提出文学标准,也足见他对词人首先必须在文学上独立的重视。独立的文学标准,黄庭坚有具体阐述。他评论王诜的词“踸踔之语,而清丽幽远,工在江南诸贤季孟之间”[1]1634(《跋王晋卿墨迹》),踸踔之语,谓其词之语言独特与众不同;又论郭英发词“词藻殊胜”[1]1831(《与郭英发帖》),评《秋风吹渭水》词“文彩指趣”[1]1579令他喜爱,重在词人独特的语言表达和文字运用能力。
词体产生以后,经过五代到北宋中期的漫长发展,一直处于托体不尊、广被轻视的境地,这与创作主体有着很大关系,从晚唐温庭筠的“士行尘杂,不修边幅,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13]5078,到宋初柳永“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辞”[14];从五代和凝平时为文章长于短歌艳曲[15],为相后将词集《香奁集》“嫁其名为韩偓”[16],到“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意于此者,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17],创作主体自身及其对待词作的态度,都让词饱受非议。黄庭坚致力于主体道德人品建设,以提高词体词格,堪与苏轼的开拓题材、改革“艳科”格局之功相媲美。
四、余论
与苏轼、秦观、陈师道、李之仪较为单线式相对明晰的词学思想、词学观相比,黄庭坚是北宋时期词论最丰富、词学观最复杂,也是最具时代性的一位词学家。他的“诗之流”的诗化词学观,与苏轼的“诗之裔”高度一致,是对苏轼革新词坛的大力支持。他对苏轼及其词作也多正面肯定,但在合乐可歌以及具体词作看法上,又存在一定分歧。他提倡词人要高逸脱俗,致力于创作主体人格、词格的建设,但他的词学观中也有实用性的一面,把词当作祝寿、酬赠之物,用于人事交往、人情联络的手段。其专题性词论《小山集序》中所说:“余少时间作乐府,以使酒玩世,道人法秀独罪余以笔墨劝淫,于我法中当下犁舌之狱,特未见叔原之作耶?虽然,彼富贵得意,室有倩盼慧女,而主人好文,必当市购千金,家求善本,曰:‘独不得与叔原同时耶?若乃妙年美士,近知酒色之娱;苦节臞儒,晚悟裙裾之乐,鼓之舞之,使宴安酖毒而不悔,是则叔原之罪也哉?’”[1]413笔墨劝淫固然是对黄庭坚作词的误解,而“鼓之舞之”云云,含有以词为人性服务工具之意[18]。他还把词当作交往的工具,词序中大量出现以词为人祝寿、与人赠答唱和的表述,还有不少词的题序中含“戏”字,如《鼓笛令》的“戏咏打揭”[6]149,《减字木兰花》的“戏作”[6]207,《定风波》的“请作送汤曲,因戏前二物”[6]95,《望远行》的“戏及之”[6]42等等。游戏,在他是一种创作心态,如绘画中的“解衣磐礴”,亦是一种词学观。他称苏轼误解他隐括自张志和《渔歌子》词的《浣溪沙》,只有谢师直一读知其用意,还涉及作者意图与读者接受的阐释学、接受美学命题,在宋代词学批评史上具有一定的时代超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