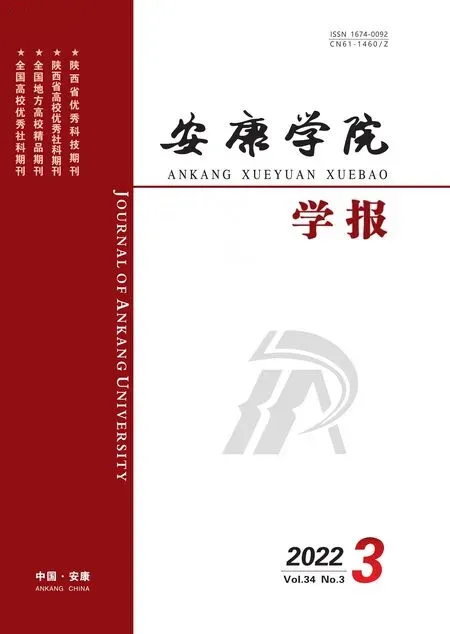论杨时“反身以诚”的逻辑前提
魏 涛,魏弋贺
(郑州大学 历史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0)
杨时作为程门四大弟子之一,同时也被称为“闽学鼻祖”,对其思想的探究一直是洛学研究工作的重点,相关的研究成果也非常丰富,包括其在洛学传承中的地位、社会政治思想、学术思想、文学思想、哲学思想等方面。但总体来讲,对于杨时思想的研究与其实际的学术地位仍不匹配,关于杨时内倾的修养工夫方面,牛耀峰提出了其杂融诸家理论,开辟了一条独特的内向的政治求诚道路[1],刘京菊则指出杨时修养工夫思想内部存在的内外对立矛盾[2],李敬峰指出了杨时修养工夫对于二程思想的继承与突破[3],王巧生则详细阐明了杨时在本心论上的创建及其由此产生的内在体验工夫[4]。但总体来看,学者们对于杨时修养工夫的探讨仍是就其本身呈现的体系来进行评价,且多认为他所架构的一种探求路径存在着内部的矛盾。本文试图从杨时提出这种独特的修养工夫背后的逻辑前提出发,尽力提升其工夫论呈现的立体性,以期帮助学者们对杨时整体的思想体系进行客观的评价。
作为洛学传承的重要人物,杨时先后师承大程、小程,兼容二者思想,杂学诸说。在工夫论层面他提道:“然而非格物致知,乌足以知其道哉?大学所谓诚意、正心、修身,治天下国家之道,其原乃在乎物格,推之而已。若谓意诚便足以平天下,则先王之典章文物皆虚器也。”[5]566假如圣学的体悟不从格物致知开始,就是视儒家经典、礼仪制度等的存在为虚无,这在杨时看来是舍本逐末、舍体而求于用的行为,其实这是遵循了程颐以知为先,将格物作为明德善之首要的思想。同时他却说:“‘致知格物’,盖言致知当极尽物理也。理有不尽,则天下之物皆足以乱吾之知,思祈于意诚心正远矣。……但于喜怒哀乐未发之时,以心验之,时中之义自见,非精一乌能执之?”[5]535外物繁多,追逐于索求外理却又人心思动,距离“诚敬”的状态只会越来越远,而在静默中体悟则可以与“中”的状态产生一种联系,这其实已经偏离了程颐所强调的格物积累的方法,而采用了程颢即体即用的内求路径。这种修行思想其实就是将向外的格物与向内的求诚结合,构成了一个具有一定前提的内倾的“反身格心”之说。在杨时看来:“某窃谓学者以‘致知格物’为先。知之未至,虽欲择善而固执之,未必当于道也。”[5]580虽然圣学的学习确实以格物致知为先,但杨时认为学者们均未理解格物的正确内涵,杨时所谓正确的格物即是这种向内的格心之路,而这种正确的格物成立的基础,便是杨时修养工夫提出的逻辑前提。
一、万物皆备于我
从杨时思想体系的架构来看,他仍旧是继承了二程的天理论作为其理学思想的最高范畴,同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挥,提出了“盖天下只是一理”[5]376的说法。“理”是天地万物、自然道德的最高准则,又贯通于人与物之中,“理”是杨时哲学体系中的根本概念。在杨时的哲学体系中,“理”主要是指所谓“性理”、道德之理,此“理”贯通物我,不离人本身而存在。而“气”则是天地万物包括人生成的基础,对于“气”的描述杨时说道:“通天下一气耳,天地其体也。气,体之充也”[5]181。“夫通天下一气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盈虚常与天地流通。”[5]536在对“气”生万物的诸多论说中,杨时对于人的强调或者说对于人本身的一种独特承载的认识值得我们重视。他提道:“惟天地万物之母,惟人万物之灵,……人者,物之灵而已。”[5]90“今或以万物之性为不足以成之,盖不知万物之性所以赋得偏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性特贵于万物耳,何常与物是两般性?”[5]394“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盈虚常与天地流通,宁非刚大乎?人惟自梏于形体,故不见其至大;不知集义所生,故不见其至刚。”[5]536杨时认为人即是万物之灵,这种灵动也体现在人所受的禀气之正,使得人有着与天地之理更加紧密的联系。杨时提出人是所有关系的总和,他说道:
明善在致知,致知在格物。号物之多至于万,则物盖有不可胜穷者。反身而成,则举天下之物在我矣。……凡形色具于吾身者,无非物也,而各有则焉,反而求之,则天下之理得矣。[5]494
其实杨时的这种认识与二程思想有着一定的继承关系。一方面,尽管二程整体的思想多是在探讨宇宙本体的哲学性问题,但是在很多概念上,二程的基本落脚点还是在人的身上。同样的,在对修养工夫的阐述中,不论是程颢还是程颐都将封建秩序以及儒家传统的人伦关系作为关注重点。如程颐在对仁的论述上提道:“仁推之及人,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于民则可,于物则不可。统而言之则皆仁,分而言之则有序。”[6]364程颢也有类似言论,他说:“孝弟本其所以生,乃为仁之本。孝弟有不中理,或至于犯上,然亦鲜矣”[6]378。因此可以理解,杨时作为分别跟随过二程进行受学的程门弟子,这种对于人或者说人伦关系、社会秩序的重视态度也必然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有所体现。另一方面,这种对人伦的重视也体现在了知识论的层面。对于“知”的认识,杨时同二程一样更重“道德之知”而轻“闻见之知”,也就是说,人本身的道德性才是“理”的根本,格物致知而后明德至善即是一种与理为一的状态,这样就使得自身成为了事物是非判断的标准。那么,作为人伦秩序的构成者以及道德的体验者、实践者,人内心先验的道德原则就是“理”,人本身也就能够成为万理的交汇点。杨时曾引用过释氏言论:“总老言经中说十识,第八庵摩罗识,唐言白净无垢;第九阿赖耶识,唐言善恶种子。白净无垢,即孟子之言性善是也。言性善,可谓探其本。”[5]393以此来论证性善说。在这里杨时为了强调性善,不惜借用他一直排斥的佛教说法,这便是因为他极力地想要强调道德价值,追逐一种道德理想。同时他还常引用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的提法来阐述这种理念。他说:
凡形色之具于吾身,无非物也,而各有则焉。目之于色,耳之于声,口鼻之于臭味,接乎外而不得遁焉者,其必有以也。知其体物而不可遗,则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则物与吾一也,无有能乱吾之知思,而意其有不诚乎?由是而通天下之志,类万物之情,赞天地之化,其则不远矣,则其知可不谓之至矣乎?[5]693
至于这种物我之理的联系具体如何存在,则可以在杨时对“理一分殊”的解释中看出。杨时对于“理一分殊”的认识是在与程颐的多次辩论后逐渐明了的。针对《西铭》这篇文章,杨时认为它仅仅谈及了“理一”而未及“分殊”,恐有流入墨氏兼爱的危险。但是在程颐的开导下,杨时改变了最初的认识,他进一步提出了对“理一分殊”的新的阐释。他正式将“理一”解释为“仁”,而将“分殊”解释为“义”。他提出:“河南先生言‘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所谓‘分殊’,犹孟子言‘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无差等。”[5]297同时他也将“理一分殊”与“仁义”两个概念内部存在的这种体用关系用人的身体来进行比喻,如:“用未尝离体也。且以一身观之,四体百骸皆具,所谓体也。至其用处,则履不可加人于首,冠不可纳之于足。则即体而言,分在其中矣”[5]297。这样的话,在讨论“理一”和“仁”的时候,“分殊”与“义”之用已经蕴含于其中,体用不离,用在体中。针对“理一分殊”这个概念,理学家们有着不同的认识。朱熹对此解释为:“论万物之一源,则理同而气异;观万物之异体,则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7]也就是说,在朱熹看来,人与万物在禀赋天理之初就有所差异,万物生成时所承载的就不是本源之理,而是已经“分殊”的所谓不同之“理”,而“理一”则是究其本源一致。但是杨时并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理一”即指主宰万物的本源之理,此“理”含于人与万物之内,人与物所禀赋之理均是这本源之理,而“分殊”则是“义”,杨时对此解释为“称物平施”。他提道:“理一而分殊,故圣人称物而平施之,……何谓称物?亲疏远近各当其分,所谓称也。何谓平施?所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谓平也。”[5]452“分殊”的概念在杨时看来指代的是现实中各个具体的秩序,是“理”在现实中各事物内部的发用。事物之理无不与人之感官体验相联系,天下之理则“通乎天地”。一方面人与物有这种天然的联系,道德规则不离人而存在。杨国荣先生在讨论王阳明思想时曾将这种哲学思路理解为:
这种存在从逻辑上看始终无法离开主体意识的范导;相应地,它们也只有在意识之光照射其上时,才获得道德实践的意义。……意义世界作为进入意识之域的存在,总是相对于主体才具有现实意义。不难发现,这种意义世界……首先形成并展开于主体的意识活动之中,并与人自身的存在息息相关。[8]
尽管说杨时可能并没有完全意义上的这种意识世界的架构以及价值赋予的觉悟,但是他毕竟已经有了一种用以人为主体的伦理秩序来诠释“理”以及诠释物我联系的尝试。另一方面,人只要能认识到自己耳目口鼻之体验与事物的这种联系,体悟到物我的本来一致,则能“通天下之志”“类万物之情”“赞天地之化”,这便是与“理”达到真正的统一,即内向的格物致知在先,体验此身与物的一致,则能最终真实无伪,内外合一,达到贯通。
二、诚则贯通内外
“理一”在杨时的哲学体系中与“仁”一致。程颢将“仁”解释为:“仁者,浑然与物同体。”[6]16即“仁”是把自己与宇宙万物看作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杨时继承并发挥了这种思想:“余从容问曰:‘万物与我为一,其仁之体乎?’曰:‘然。’”[5]283同时杨时进一步阐述道:“大抵须先理会仁之为道,知仁则知心,知心则知性,是三者,初无异也。”[5]358“理”“仁”“心”“性”四者一致,“理一”即是万物与我为一,是仁之体,是此心之诚。在他看来,“仁”“心”“性”三者就其本源来看是一致的,三者在表达上的不同源于语境的不同,或者说是因为要描述的对象不同才产生了这种差异,因此三者之间可以实现贯通,“诚”就在这里扮演着贯通的角色。“诚”在杨时的思想体系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杨时关于“诚”有许多论述。比如他提道:“私意去尽,然后可以应世。老子曰:‘公乃王。’”[5]232“或问:‘经纶天下,须有方法,亦需才气运转得行。’……然观其作处,岂尝费力?本之诚意而已。”[5]310“无诚意以用礼,则所为繁文末节者,伪而已。”[5]313这样看来,“诚”即是内心主动地趋于与“理”为一。将杨时关于“诚”的思想展开,我们可以看出他在强调“诚”时,认为这个概念能够对人之道或者是现实之道产生独特解释。杨时对“诚”有其独特的定位,即诚者贯通内外。正如他所提到的:
大学一篇,圣学之门户。其取道至径,故二程多令初学者读之。盖大学自正心诚意至治国平天下只一理,此中庸所谓“合内外之道也”。若内外之道不合,则所守与所行自判而为二矣。……孟子曰:“其身正而天下归之。”皆明此也。[5]305
在这里杨时实际上是将《中庸》的思想与《大学》的思想通过“诚”的概念进行联系。他又说:
知合内外之道,则颜子、禹、稷之所同可见。盖自诚意、正心推之,至于可以平天下,此内外之道所以合也。故观其意诚心正,则知天下由是而平;观其天下平,则知非意诚心正不能也。兹乃禹、稷、颜回之所以同也。[5]276
这就是说,圣人以“诚”为本,故可以贯通内外之道。二程同样对“诚”的实现意义有所强调,“诚者合内外之道,不诚无物”[6]9。那么反过来说,正因人之道重点在于“诚”,故人可以感通道德,践行人道,这也为贯通内外提供了前提,向内的求索实际上就有了成就现实的合理性。又如杨时对于“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概念的阐述,他说道:
易曰:“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夫尽其诚心而无伪焉,所谓直也。若施之于事,则厚薄隆杀,一定而不可易,为有方矣。“敬”与“义”本无二。所主者敬,而义则自此出焉,固有内外之辨。其实,义亦敬也。故孟子之言义,曰“行吾敬”而已。[5]291
杨时认为以“敬”事心就是“直”,则施与外物必然能够对应分殊之理,也就是“义”。这样就是说,由内部的“直”可以推出外部的“义”。与之前诸多概念的论述相同,杨时在这里强调将“直”与“义”产生直接性的联系,使得自己对于“诚敬”之重视显得合情合理。《北溪字义》在对“道”的诠释中提道:“但不知其体本具于吾身,故于反身内省处殊无细密工夫。”[9]杨时同样如此认为,心之诚敬如一,则“反身而诚”,从而体悟“万物与我之为一”,道器不离,吾身吾心即是“理一”,所以向内格求,本来备于我的“理”也会被发掘出来。
此种与万物一体的诚然境界可以结合冯友兰先生对于“有我”“无我”问题的讨论来认识。冯友兰先生认为在“道德境界”可以达到真正的“真我”,达到一种真正“有我”的境界[10]。陈来先生基于此,又结合佛教理论进一步界定“有我”与“无我”两种境界的区分。“无我”境界是至高境界,此境界内一切差别对立都会消失,而“有我”或“有大我”的境界内则我即是宇宙全体,我与宇宙合一,与宇宙事事物物合一[11]。杨时所认识的本有的“理一”以及后来人能达到的“诚敬如一”的境界便类似于这种,但是这当然不能简单等同。冯友兰先生“道德境界”中的“真我”具有强烈的主宰意味,这种“有我”与“无我”的讨论都是基于价值层面或者一种境界的讨论,而杨时的思想理论还并未达到这样的高度,他也并没有明确关注人作为这种价值主宰的境界,而仅仅是先将“理”限定在道德伦理,随后看到了这种道德性与人存在的紧密联系。但是杨时毕竟已经有了这种自觉,不论是他对人与物禀受一理的理论阐释,还是最终“诚敬”下这种“万物皆备于我”、万物与我为一的状态的理解,都是在试图调和二程理论的基础上,对于“理”的概念进行一种解释,同时基于此寻找一个可行的修养工夫。
三、真知即行
知行观是理学家们关注的又一重要内容,它是解决人性本身达到与宇宙本体重新统一的问题的一种范畴。二程认为“知”必实践于“行”方为“真知”,也就是说,达到了“真知”以后,“行”便成为了必然的事情。杨时作为二程后人也继承了这种统一的知行观。杨时提道:“知止而至之,在学者力行而已,非教者所及也。”[5]571达到“真知”以后,学者便自然而然的身体力行。“真知”也是人们与“理”产生真正的联系,是人们在内心上对于“理”的认同,其在具体的精神气象上则与我们之前讨论过的“诚敬”状态相联系。“无诚意以用礼,则所为繁文末节者,伪而已。”[5]313这是指“诚敬”是一种人发自内心的真实无伪的状态。在杨时看来,格物致知如果根究繁文末节则永远也抓不住明德善的正确路径,而能以诚意为主,内求而格心,则能达到最终笃信于“知”,再进一步就自然达到“诚敬”的状态。按照杨时“反身以诚”的修行路径,当达到“诚”的状态以后,推而便能实现修齐治平。“自修身推而至于平天下,莫不有道焉,而皆以诚意为主。若无诚意,虽有其道,不能行也。”[5]566特殊的历史时期使得杨时一直致力于现实性的实践,家国天下是身处乱世中的杨时无法逃避的。对于“诚”发用的可能性,杨时也多以现实政治作为依归,在这里杨时还专门列举了一个例子,当别人问到他为将之道时,他说:
君子无所往而不以诚,但至诚恻坦,则人自感动。……诚动于此,物应于彼,速于影响,岂必在久?如郭子仪守河阳,李光弼代之,一号令而金鼓旗帜为之上明,此特其号令各有体耳。推诚亦犹是也。[5]257
在杨时的论述下,“诚”的现实意义是巨大的,将领能做到诚心为国,则士兵又怎么不尽心用力,甚至乱世亦可因此而平。同时杨时也力图以这种理念劝谏皇帝,期盼皇帝能够了解诚意正心的作用,假如人主能保留一颗恻隐之心,敬天保民,以仁心施政,天下便可大治。“则人君所以奉天者,亦因诸民而已。民之所弃,天实讨之。”[5]20“夫民者,邦本也,一失其心,则邦本摇矣。不可不虑也。”[5]4“一失民心,其患有不可胜言者,不得不虑也。”[5]546民心便是天意,对于皇帝而言,顺应民心即是顺应天意,这也是实现“诚敬”与天理的联系。可见,“诚”作为根本状态是一贯的,而“诚”的发用则是因时因事而多样的。对于修行学者们这就主要指代贯通天地,达到与天地为一,对于统治者则是指代能以一颗仁心敬天保民。
杨时着力于对人这一层面的“心”“性”“仁”等概念进行探讨。他提出,人应该首先明白“仁”之道,明白“仁”是何物,缘由即在于知仁则可知心,然后进乎知性。这里杨时抬高“心”的地位,也促使工夫本体化现象的出现。在阐述“心”的作用时,他提道:“六经之义,验之于心而然,施之于行事而顺,然后为得”[5]266。在批判当时的许多读书人时,他也提道:“盖以其学得之文字之中,而未尝以心验之故也。若心之所得,则曰吾所以为己而已。是故心迹常判而为二。心迹既判而为二,故事事违其所学”[5]261。杨时提出了在意识未萌动、喜怒哀乐未发之际去体认,在他看来这便是人之自身与“道心”的合一过程。针对这种倾向,朱熹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他认为程门后学诸人由于对“气质之性”的认识不足,没有分清心的未发、已发只是不同的状态,从而忽略了恶的一面,其实在现实中,心未发之际气质就已经混于其中,诸人未能认识到这种情况,故执着于在未发之际识体,从而期望实现连贯的融通。他批判到:
然人之一身,知觉运用,莫非心之所为,则心者,固所以主于身,而无动静语默之间者也。然方其静也,事物未至,思虑未萌,而一性浑然,道义全具,其所谓中,是乃心之所以为体而寂然不动者也。及其动也,事物交至,思虑萌焉,则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谓和,是乃心之所以为用,感而遂通者也。[12]
虽然说朱熹的这种认识是建立在他对于“心”“性”“情”关系的重新划分的基础上,是在补充了“情”这个概念后将“心”与“性”的关系重新界定后所提出的,但应该说,朱熹对于程门后人对“心”的地位逐渐抬高的趋势是有着清醒认识的,同时他也看到了二程以后工夫内倾化以及工夫本体化的思想苗头。反过来说,朱熹提出这样一套批判逻辑,其实也就是杨时工夫内倾所创设的一个重要逻辑前提。正是这样一种即工夫即本体的贯通过程,使得内外不仅有了联系,也使得以这种联系为前提的修行有了可以看到的结果。
四、结语
从思想体系的最高范畴来看,“理”是杨时哲学体系的主宰,是最高层次的概念,人与物禀赋同样的天理,“理一”是人与物本有的天理,而人则得气最正,与天理有着天然的紧密联系。而与人相关的伦理道德、社会秩序也是“理”的根本内容,这种道德秩序不离人而存在,因人而有意义,同时又与万物沟通,这里所谓万物便是事事物物之具体规则。同时“理”又与“仁”实为一物,即一种与万物同体、万物皆备于我的联系,认识到这种“仁”就需要人经过向内探求格心从而达到“诚敬如一”的状态。当达到“诚”后,人与物的统一则能进入一种自然通透的状态,内在的诚敬可以体现出外在诸多形式的具体规则。“反身以诚”的向内求索工夫是在此心未接物时感受一种与物为一的状态,这是一种无法讲明的境界,只能依靠体验来感悟,但当求得“诚”的状态,也即得到所谓“真知”后,则自然发用于行。
杨时先后求学于程颢、程颐,二人的学说均在杨时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过程中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在杨时的思想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反身以诚”是杨时在着力调和二程修行路径之后所开辟的一条独特的体验工夫。针对“反身以诚”,学界多强调其中包含的无法调和的矛盾,同时也对杨时在继承发扬师说的理论贡献上评价较低。本文从三方面入手,经过对杨时“反身以诚”提出的逻辑前提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杨时在理论创造上亦有其独特的思路,而并不是将二程思想简单杂糅。作为程门四大弟子之一,杨时致力于发扬师门思想,为后来学者寻找一条可行道路的努力应当予以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