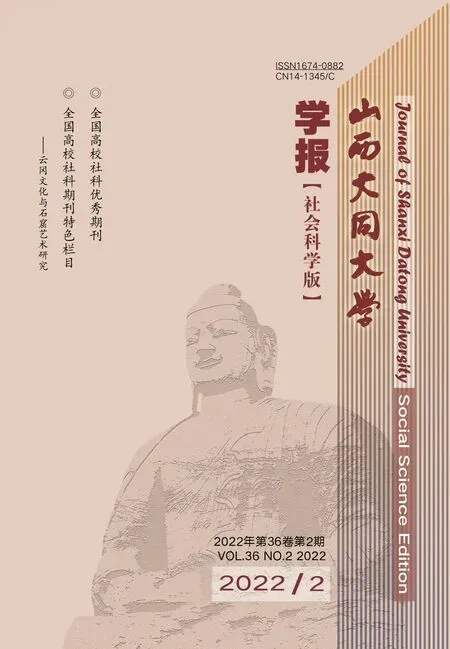光荣与屈辱:明代科举考试官的科场历程
王榕烽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7)
考试官又称主考官,是“负责统领同考官完成一科三场考试的出题、阅卷和取士的全部工作,并掌握考生去取权的重要官员”,[1](P145)在科举考试的运转过程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终明一世,科举考试共产生进士24586人,举人群体更是达到了10万人之多,这与科举考试官的卓越贡献有着重要联系。①而正如郭培贵先生所言,在科举考试中,“考官因赏识考生答卷而录取之,属履行职责,但对被录考生来说,则是天大的恩赐”。[2]因与此,科举考试官自然也受到人们的尊崇。但科举考试官在主试过程也即从其被任命为考官、在科场中主试、考试揭榜后这一过程中所面临的压力和处境也远非常人可以想象。他们可能在一瞬间从高处跌落到低谷,由万人敬仰变成遗臭万年,在光荣与屈辱之间转换。目前,学术有益的界对此已有一定的论述,②笔者拟对此作补充,不当之处,请方家就教。
一、考官入试前的荣与辱
在科举时代,如若说科举中式可以光宗耀祖,让世人所艳羡,那么出任科举考试官则更是一件光耀宗楣之事,无数科举士子的命运由考试官决定,无数兴国安邦的人才也由考试官选定,可谓荣耀之至。清末著名大臣李鸿章“生平最遗恨者一事,曰未尝掌文衡”,[3](P112)可见科举时代人们对科举主试的看重。事实上,明廷对科举考试官的选任极为严格,能出任考试官者均非等闲之才,也就确立了其自身的尊崇地位。
因考试官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其选任也自然引起了朝廷上下的特别关注,如成化年监察御史许进就曾上奏说:“国家以科目取士,慎选考官。”[4](P3475)嘉靖年给事中黄亢白也说:“京闱乡试伊迩,宜慎选主考官。”[5](P6817)明廷对于科举考试官的选任极为重视,要求其人德才兼备,而又特别注重对考试官个人品德修养的考察,如洪武十七年,明廷在颁行《科举成式》就规定“考试官皆访经明公正之士”,[6](P2467)对考试官的个人品行有着严格规定,这是由科举考试官的特殊性质所决定。
科举考试是以“程文来决定去取”的人才选拔方式,也就决定了考试官个人的学养也极为重要。[7](P67)明廷对科举考试官的个人学识也有着严格规定,如景泰年间,景泰帝就曾下诏曰:“其考试官,惟聘精通于经学者为之。”[8](P3725)明代实行两京制度,我们从其对两京乡试考试官的选任就可看出其对考试官个人学养的要求,如永乐十五年,明太宗就“令北京行部及应天府乡试考试官、命翰林院春坊官主考”,也即两京乡试主考官皆由翰林院春坊官出任。而在明代后期有着“非进士不入翰林”的说法,[9](P1702)其才学可谓代表了明代文官群体的最高水准,可见明廷对考官学识的重视。
为了使考试官的选拔更为公平客观,明廷对科举考试官的选任还很注重选拔的程序。如四川按察副使朱与言在宣德八年上奏提议:“今后考官必先会同巡按监察御史、按察司官,从公访求素有学问老成之士。不许引进轻薄无学之徒,庶得衡鉴公平侥幸路绝。”[10](P2319)这就更说明能够充任科举考试官真的是万里挑一,光荣之至。
从明政府对科举考试官的任命也可看出其所处的荣耀地位,“京闱主考官由京府官上请钦命,外乡试考官则由各布政司自行聘请”。[11](P449)而顺天乡试考试官被任命以后,还会受到“官出币帛,先期敦聘”、主文考试官二人“文币各二表里”、“赐宴于本府”的优待。由皇帝本人亲自赐宴接待,可谓规格之高,待遇之优,这一时刻也算达到了人生的巅峰期。
但是,当科举考试官还沉浸在任命时的喜悦时候,这一时刻也有可能转变成为其人生中最为屈辱的时刻,成为考试官本人的屈辱记忆。如永乐十五年八月,明廷已任命翰林侍讲王洪为北京行部乡试主考官。但王洪为人“自负矜己傲物,醉輙出忿语,斥同列,以不得为学士,中怀怏怏,尝密疏诬学士胡广”。而此次王洪能够充任顺天府乡试考试官,与胡广本人的极力推荐有着重要关系。因此,明太宗朱棣对王洪这样的行为非常愤怒,曰:“此小人,岂可以在侍近!”[12](P2022)“命礼部追所受礼币而改命英考试,出洪为主事”,剥夺了王洪出任考试官的资格。又如嘉靖三十一年,有人奏言:“司经局洗马黄廷用素行不谨,恐序当及之有玷文衡。”[5](P6817)世宗因此“诏以廷用调南京别用,遂改南京兵部车驾司员外郎”。也是剥夺了黄廷用的乡试考试官资格。文献记载,王洪在被剥夺考试官资格之后,“饮恨,未几,病死”。可见这一屈辱时刻所带来的实质性伤害。
由此,也显示出考试官在光荣和屈辱之间的转换。方才还是受人敬仰,德才兼备、掌握考生命运,受皇帝亲自宴请的重要官员。随之不久,自身命运也已发生重大转变,成为受人唾弃、钉在历史耻辱柱的罪人。从此事也可看出考试官个人所承受的巨大压力。
二、考官在科场中的荣与辱
明代科举形成了“包括科考、乡试、会试、殿试和庶吉士考选在内的五级考试体系”,[13]乡、会试分别在子、午、卯、酉的八月和辰、戌、丑、未的二月进行。科举考试官的工作主要是在这段时间的科场内进行。科场是科举考试官群体大显身手、崭露头角的重要场所。在这里,考试官是考场中的第一责任人,负责出题、阅卷,决定考生的命运。而在科场期间,考试官也时刻面临着光荣和屈辱的转换。
蜀汉丞相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曾提出“鞠躬尽力,死而后已”的千古名句。事实上,在生活中,没有什么比恪尽职守更让人值得尊敬,科举考试官亦是如此。明代科举“承袭唐、宋、元之制,实行锁院制度,也即为保证考官能够独立、公正地阅卷取士而对其实行锁闭隔离制度”。“锁院时间从考官入院开始,一直到揭榜结束”。[1](P211)考官在锁院期间“祗勤夙夜,殚厥心力”,[14](P231)极为辛苦,如洪武五年应天府乡试考试官曾鲁,“入院之后,忽吐血一升,公犹力疾阅卷不息,自是遂奄奄不振”。[15](P504)有很多考官也因此而在科场内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如永乐四年,翰林院修撰徐旭就在主持礼部会试的过程中,“得暴疾卒于试院”。[12](P764)嘉靖甲辰,“主考礼部尚书学士张潮卒于试院”,[16](P149)这些考官恪尽职守,极为光荣,自然也受到了皇帝的特别恩赏。如明太宗朱棣得知徐旭去世的消息,就即刻“赐棺及遣官赐祭”,以示尊崇。而在科场内,考试官如果稍有不慎,更多的是受到责罚,成为其屈辱的记忆。
在科场内,考试能够顺利进行并完成,对于考官来说也是一种荣耀。但若因考官原因而导致考试不能按期、按时举行,则考官必须背负一定的责任,这是作为考试官的一种屈辱。最常见的当属火灾的影响,如正统三年八月,顺天府乡试,“初试之夕,场屋火”,[17](P201)“焚东南席舍……命于本月十五日为始再试”。[8](P871)又如天顺七年二月会试,“晚试,院火,举人死者甚众……上命改试于八月”。[8](P7020)事情发生以后,“以试院火,下知贡举及监试等官……于狱”。[8](P7021)这就使考官成为当科考试的罪人。陆容因此而感慨道:“回禄如何也忌才,春风散作礼南灾。碧桃难向天边种,丹植翻从火里开。豪气满场争吐焰,壮也一夜尽成灰。曲江胜事今何在,白骨棱棱漫作堆。”[18](P12)而火灾在一定程度上还属于不可抗拒因素,相对而言,对考试官的处理状况还会好一点,但因考题颁布迟慢而影响考试的顺利进行,则完全是考试官本人的屈辱。嘉靖十三年,廖道南、张襄在担任顺天府乡试考试官时,“初场进题迟慢”,[5](P3657)嘉靖皇帝极为生气,不仅对当时的顺天府尹胡铎进行处罚,还对主考官处以“罚俸一年”的处置。
如果说以上两者还是因为考官本人初次入场经验不足还尚且可原谅外,那么考试出题出现严重错误则应该罪不容恕,因在考试中,“拟题是考官的职责,也是一项严肃细致的工作”,[19]出题出现错误即是考官自身渎职的结果,而且还会严重影响选才的质量。明代科举试题中“乡试与会试的出题道数一样,三场共37道。其中首场23道,包括《四书》义3道和《易》、《诗》、《书》、《春秋》、《礼记》等五经义各4道;第二场9道,包括论1道,判语5条,诏、诰、表各1道;第三场策5道”。[1](P362)明廷对考试出题有着严格要求,洪武二十四年定,“凡出题、或经或史、所问须要含蓄不显、使答者自详问意、以观才识”。正统六年,又令“出题不许摘裂牵缀、及问非所当问”。[11](P448)而对于科举的出题也引起了朝廷官员的重视,如成化十三年,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黎淳就奏“科场出题作文定式,洪武年间已尝颁降。近年,有司多有不遵,任情行事,所刊程文,除两京外其余纯粹者少,驳杂者多,甚至犯庙讳及御名。乞移文所司将提调监试并考试、同考试官究治,考官如例追夺表里,仍查墨卷”。[4](P3127)天顺三年,浙江温州府永嘉县教谕雍懋也曾上书曰:“朝廷每三年开科取士,考官出题多摘裂牵缀,举人作文亦少纯实典雅。比者浙江乡试春秋摘一十六股配作一题,头绪太多及所镂程文乃太简略而不纯实,且春秋为经属词比事变侧无穷,考官出题往往弃经任傅甚至参以已意,名虽搭题,实则射覆。遂使素抱实学者,一时认题与考官相左,即被黜斥。乞敕自后考官出题举子作文一惟明文是遵,有弗愋者罪之。”[8](P6471)正德十年,南京礼科给事中徐文溥也上书说:“近日主司务为谲惟,命题摘掇一句、二句,或割裂文义,或偏断意旨。”[20](P2630)而因为科举考试试题的原因,明初还曾经给予严厉惩罚,如景泰七年,少保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兼东阁大学士王文言:“尝闻洪武三十年,礼部会试贡士考官刘三吾等出题内有讥讽朝廷及凶恶字并考试有不公,御史劾奏治以重罪,”“又永乐七年礼部会试,贡士考官邹缉等出题有《孟子》节文及《尚书》洪范九畴偏经论题,被御史劾奏亦罪考官”。但科举考试官在出题方面一直都存在较大问题,如《万历野获编》载:“嘉靖十六年丁酉,顺天乡试,次题为‘天地之道博也’一节,则犯御名上一字。次年戊戌会试,出‘博厚所以载物’一节,又犯御名。十九年庚子,福建出‘至诚无息’五节,凡四犯御名。然是时犹未逮治考官也。至二十八年己酉,浙江题为‘博厚配地’一节,亦犯御名,是年山东以‘无为而治’,程文语涉讥讪,逮按巡御史叶经,死于杖下。”[21](P861)又如,崇祯十二年乙卯科,主考张维机“眊不省事,所出论策题皆浅俚不成文,为通场士子所笑”。[22](P403)显然,以上种种显示出了考试官出题的一些问题,而出题犯错自然应该是考试官的屈辱时刻。
考试官出题以后还要注意保密,避免漏题。因此,甚至规定三场考题皆“不许主考官预构,以防奸弊”。[5](P2980)而明代最大的科场腐败案恰恰就是因为漏题而产生。弘治十二年,孝宗皇帝亲自任命“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程敏政,为会试考试官”。[23](P2578)而在开科不久户科给事中华昹就上奏:“国家求贤以科目为重,公道所在,赖此一途。今年会试,臣闻士大夫公议于朝,私议于巷,翰林学士程敏政,假手文场甘心市井士子。初场未入,而论语题已传诵于外;二场未入,而表题又传诵于外;三场未入,而策之第三四问又传诵于外”。[23](P2592)这件事情对明代科举的声誉造成了严重影响。最终结果“下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程敏政于狱”。[23](P2634)皆因考试官一时的贪念,成为了科场的罪人,最直接的影响是开榜日期的推迟,也使明代最有名的才子唐寅成为了后人哀鸣的对象。
考生在答题交卷以后,是考试官在科场中最为忙碌的日子,而这也是其荣耀和屈辱并存的时刻。明代科举为防范考生舞弊,“继承前制行‘糊名易书’之法”,这就是弥封和誊录制度。[24]而“考卷经对读之后,仍未被帖出,则会经收掌试卷官送入内帘,然后考官便开始阅卷工作”。[25]这时,主考官就决定考生的最终去取。在这一过程中,考官若能够慧眼识珠,则对于其名望和声誉来说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正统十三年,会元岳正的考卷本已被“礼部同考误置落卷”中,只因主考官“侍讲杜公宁见之”,遂擢第一。[26](P751)又如嘉靖元年壬午科,名臣徐阶卷先被同考官黜落,后主考董玘“阅而改品题焉,且将以为第一属有沮者,乃以为第七”。[27](P751)再如万历二十五年,主考叶向高,“主应天试,比折卷,不见顾名,谓此佳士,试寻看,所制执甚佳,为一老学究涂抹之矣,即取前列”,[28](P667)所取之人正是当科会元。而一些考官因为个人能力不及或者徇私舞弊而造成阅卷不公,就是作为考官的耻辱。如万历二十年,礼科都给事中胡汝宁参“顺天举人张大典,学义字不满三百,首策腹心讹作愎心,白若鹭首义结内缨駴语涉关节。应天举人李应杰,卷中别字太多”。[14](P4548)虽最后并没有追究这件事,但对于考官名誉的损失也是很大。又如万历三十四年,“罚山东主考官彭遵古、张汝霖、丁遂俸各三月”,原因在于“山东中式第七十一名举人李衍赏,第七义短促无章,仅二百余字”。[14](P8052)再如万历四十三年,山西乡试“取中第四十名举人李希清,墨卷表题匹字误写疋字;六十三名举人任道统,经题元字误写无字”。[14](P10218)最终处理结果对山西布政司韩策罚俸三个月,考官免议,但也给考官带来困扰。
科举考试完以后,考官还要撰写当科的科试录,这就是我们常提到的《登科录》。③其一般在撤棘揭晓日之前就已撰写完成并刊刻。而在这一过程中也容易发生意外。如正统十二年,“山西乡录内《诗经》题“维周之桢”,以“桢”字犯楚昭王讳,为礼部所纠,上宥之,但令罚俸”。[2](P857)又如成化十三年,“礼部会同翰林院等衙门学士等官覆奏,《成化十三年乡试录》,浙江等布政司中有犯庙讳、御名及亲王讳。其嫌音及偏犯一字者,如例不坐外;其犯二字及文理差谬行文有疵表失平侧字画差错者,宜如淳言究治。但犯亲王讳及文疵平侧不顺字画差错者,比与文理差谬者不同,宜止治其罪”,[4](P3127)嘉靖十六年,“应天府进呈乡试录考官批语失填”,[5](P4271)考试官也受到了惩治。
由上可知,在科场中,考试官所面临的压力和处境可见一般。其作为考场中的第一责任人,任何的麻痹大意,均可能造成严重后果,影响自己的声誉。严重者还可能受到一定的责罚。这也反映出了科场的残酷,不仅是士子之间竞争的残酷,也是对考官的一种严厉考验。
三、科举散场以后的荣与辱
科举考试散场以后,按理来说应是考官得到喘息,进行修整的时刻,应是其深藏功与名,门生们向“座主投‘门生刺’,并‘拜谒’和‘贽见’座主,以确认座主、门生关系”的光荣时刻[2],应是其声名远扬的时刻。但在明后期科举散场之后还要对中式举子的试卷进行磨勘和覆试,以此来督促考官在考试中谨慎录取,秉公办事,而这也可能成为考官的屈辱时刻。
对于科举考官来说,为国家选拔人才,恪尽职守,才不负皇帝的重托,不负国家的期许。而所取得当即是其作为考官的光荣时刻,如曾担任南京礼部尚书的王英就因其“屡为会试考官”而所取“多得名士”而受到时人的称赞。[8](P4010)另一著名大臣王直也因其“在翰林三十余年屡为考官,得人为盛”而被人们礼赞。[8](P6965)这是作为一个考试官而获得的最高称赞。很多考试官在散场以后,还会获得升官的旨令,如礼部右待郎兼翰林院学士薛瑄在主持完天顺元年丁丑会试以后,“事竣,转左侍郎”。[29](P184)这也是皇帝对其科场贡献的赏赐。
随着明代磨勘和覆试制度的发展完善,考试官在科举散场以后还会被追究科场中的失责,成为其屈辱记忆。[30]明代乡试的磨勘制度确立于嘉靖年间。嘉靖四十三年,礼部奏准实行磨勘制度,即乡试揭晓后“将中式朱墨卷解送到部,以凭稽查”。[5](P8648)而在这时,如果核查出中式试卷存在问题,则对于刚刚从繁忙科场中解脱出来的考官也是一种屈辱,如万历四十四年,“礼部左侍郎何宗彦奏磨勘试卷,摘参举人之违式失体者,吴炳真草不同,应行严勘,冯洪业等文字谬误宜停一科,而对读及考官亦宜议罚”。[14](P10302)又如万历四十七年,“以磨勘试卷违式循例,摘参各省直主考赵师圣等,夺俸一月”。[14](P11053)在万历三十五年,磨勘制度又扩大到了会试。
万历十三年,明廷又发展完善了覆试制度,增加了礼科参与磨勘考生试卷的程序。该年二月,礼部奏准“各省直乡试于揭晓三日之内,将朱、墨真卷解部”,由礼部官员会同礼科官员“辨验是否原卷,通行严阅,如有文理不通者,量行奏斥一、二,以示戒惩”。[16](P1589)这对于对于促进明代科举制度发展完善有着重要意义,使得取士更加公平,也促使考官在科场中要秉公办事,去取得当。但考试官在士子覆试时,也常常受到责罚,如万历四十七年,考中上年应天乡试第六十五名的举人许士柔覆试后罚一科。[31](P790)即在当年六月“先是以磨勘试卷,各省直房考、举人奉旨各夺俸罚科有差;其应覆试者礼部会同礼科严加评品。看得许士柔之卷才情不乏,但以临时矜持之过,不克舒展未足,为士柔病也,第落字之罚似难,即以此番之不入试相准,仍应罚一科者也”。[14](P11089-11090)
与此同时,很多不经意间的疏忽,仍会追究考官的责任,将其钉上历史的耻辱柱,如“戊子顺天场事竣后,失去朱卷数卷。礼官高桂,纠场弊,归罪于主考作奸,先去以灭其迹”。[21](P390)此事实情究竟如何,文献中也没有记载下文,但也表明科举考试官在散场以后,仍然还会因为考场的事务而被责罚。
余论:明代科举考试官饱受屈辱的原因
作为明廷钦命、掌握考生去取权的科举考试官,本应其重要职责受到人们的尊崇,但其却时常陷入屈辱而成为人们的笑料。这与其所面对的环境有着重要联系,而又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明代科举制度进入其发展的鼎盛阶段。而这也意味着“功名体系的空前完备”和“取士地域广泛性的空前增强”,使科举士子的竞争压力变得更为激烈。据郭培贵先生统计,明代“乡试录取率,明初一般在10%上下;成、弘间定为5.9%;嘉靖末年又降为3.3%;而实际录取率又低于此。会试录取率,自洪武至万历中平均为8.6%;其中,洪武至永乐二年平均为21.7%,永乐四年至万历中期平均为8.4%”。[32]可见,在明代科举竞争激烈的状况下,科举录取率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渐下降,又因为科举中式又有着一定的偶然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士子们为了取得功名就不得不采取一些非正常手段。如《明史》中所记载的作弊手段就有“贿买钻营、怀挟倩代、割卷传递、顶名冒籍,弊端百出,不可穷究,而关节为甚。事属暖昧,或快恩仇报复,盖亦有之。其他小小得失,无足道也”。[9](P1705)对于考试官来说,其在科场中虽恪尽职守,但仍应接不暇。而这些多样的作弊手段自然会使考试官受到指责和牵连,成为其屈辱的记忆。
其次,考试官位卑职轻,往往受到官场的连累。考试官的选任要求其人德才兼备,在两京乡试中,多从翰林官中任命。但明代翰林官设“学士一人,正五品;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各二人,并从五品;侍读、侍讲各二人,并正六品”。[9](P1785)可谓位卑职轻。因此其往往受到其它高级官员的排挤,一些势要高官凭借自己的权势,使自己的子弟高中,破坏了考试的公平,如景泰七年,刘俨、黄谏为顺天府乡试考试官,在乡试考试完之后,“少保太子太傅户部尚书大学士陈循、少保吏部尚书大学士王文,御考官刘俨等不取其子王伦、陈瑛。遂奏俨等出题讥讪,并违制不取翰林院考中译字官诸罪及乞将伦、瑛并中式诸举人墨卷会官,品第优劣”。虽最终皇帝认为“俨等之罪,不出于私,悉置不问”。[8](P5718)又如嘉靖二十三年,“大学士翟銮以内阁首臣,二子汝俭、汝孝既联中乡试又连中会试”。事发以后,“追论顺天乡试主考秦鸣夏、浦应麒,阿奉翟銮之罪”,处以“杖六十,革职闲住”的惩罚。[5](P5568)由此可见考官的处境之难。
第三,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的影响。中国古代社会经历长期而艰难的跋涉,“至明代后期已经开始起步向近代社会转型”,[33](P1)使社会生活等方面发生了巨大变革。而“科举辅导、科举图书、作弊等一批依附于科举考试”的行业也在不断发展[34],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科场管理的难度。尤其是伴随着印刷行业的发展,士子怀挟作弊风险也在增加。针对于此,明政府也极为重视,如隆庆元年,礼科给事中何起鸣奏申饬科场事宜第一条即为“重怀挟之罪”。[35](P278)隆庆四年,“礼部覆南京河南道御史王嘉庆奏请令今后…两畿乡试宜增设御史二人,缉治怀挟诸弊”。[35](P1169)可见明代后期,随着社会的转型,科举考试中对科场管理的难度也在不断上升。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科举考试官饱受屈辱的原因。
注释:
①关于明代进士总人数,参见郭培贵《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明代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95页;明代举人总数至少达102389人,参见郭培贵《明代乡试录取额数的变化及举人总数考述》,《东岳论丛》,2010年第1期。
②相关成果有:张德信:《明代科场案》,《明史研究》,2001年8月;张晓峰:《明朝“国考”轶事》,《文史月刊》,2011年第11期;王凯旋:《明代科举制度研究》,万卷出版公司2013年版;李义英:《明代乡、会试考试官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白金杰《清代科举民俗考论》(武汉大学2015年博士学位论文),郭培贵:《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明代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牛明铎《明代科举防范与惩治作弊制度研究》,福建师范大学2017年博士学位论文;裴家亮:《明代应天府乡试研究》,福建师范大学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
③关于《登科录》的相关论述,参见陈长文:《明代进士登科录研究》,浙江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