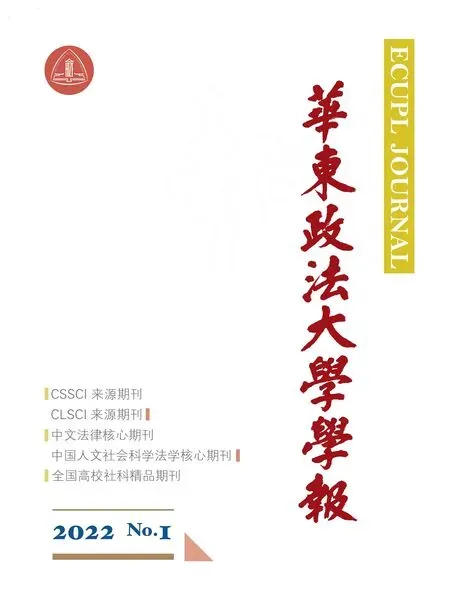论数字行政法——比较法视角的探讨
于 安
目 次
一、数字行政法的兴起背景
二、数字行政法的形成条件
三、向数字行政法的转型
四、数字行政法的系统化
五、未完的结语
2021年8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印发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提出了“全面建设数字法治政府”的国家法治建设新命题,在2021年至2025年的阶段性重点任务中,明确要求 “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数字法治政府正在成为法治政府现代化建设的主导性新方向。对传统行政法进行制度更新和构建数字行政法体系,是我国行政法发展的新使命,推进和完成这一使命是行政法学研究的一个时代性任务。如果说数字化正在造就一种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新文明,那么包括数字政府法治在内的数字化法治无疑应当是这一文明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数字行政法的研究是对一个新型行政法体系的变迁及其框架和基础的探讨,以整体地解决数字行政的正当性和合法性问题。2021年意大利学者发表了从整体上研究数字行政法的文章,〔1〕See Stefano Civitarese Matteucci, “The Rise of Technological Administration and Ragged Rout towards a Digital Administrative Law”, in Domenico Sorace, Leonardo Ferrara & Ippolito Piazza eds., The Changing Administrative Law of an EU Member of State: The Italian Case, Springer Nature Switzerland AG and G. Giappichelli Editore, 2021, pp.127-146.提出和分析了数字行政法的一些重要命题,代表了这方面研究的新进展。这些问题涉及对既有行政法制度的系统改造和全面更新。人们对于这种大型变革的实际需求及其变革的条件和途径等制度形成问题,需要有一个达成共识的过程。本文试图从比较法的视角,对数字行政法的兴起和形成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数字行政法的兴起背景
数字技术的应用、新产业革命和信息社会及其公共行政数字化新范式所产生的影响,为数字行政法的兴起提供了重要的驱动力和时代背景。
(一)数字技术在公共行政中的应用
数字行政法的提出,首先源于在公共行政中新型数字技术日益广泛的应用。尽管在国家和公共行政的演化进程中,技术应用及其相关设施和设备的支持作用一直是醒目的,如造纸、印刷、交通、通信和计算等方面的技术及其应用,但是它们对于制度变革的作用没有像数字技术那样深刻和广泛。无论是法国狄骥教授在《公法的变迁》〔2〕参见[法]莱昂·狄骥:《公法的变迁》,郑戈译,载[法]莱昂·狄骥:《公法的变迁:法律与国家》,辽海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二章“公共服务”。一书中所说的从公共权力行政法到公共服务行政法的转型,还是美国斯图尔特教授在《二十一世纪的行政法》〔3〕参见[美] L. B. 斯图尔特:《二十一世纪的行政法》,苏苗罕译,毕小青校,载《环球法律评论》2004年夏季号,第166-168页。一文中对美国行政法五种模式递进发展的阐述,或者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新行政法或者新公法的各种讨论,都没有像现在谈论数字技术应用那样将行政法的转型与技术应用如此密切地联系起来。如果将行政法分为放任主义、福利主义、管理主义和技术主义四种类型,那么在前三种类型的历史变迁中,社会变革和全球市场的驱动作用更为突出,至少技术应用都不是最为关键或者必不可少的。
在行政法的发展历史上,数字技术引发的制度变迁是最为广泛和深刻的,它不限于工具性地提供信息化技术支持以提高行政效率,更重要的是通过组织变革和运行机制创新,大幅度地改变公共行政的体制和制度。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得到广泛应用以后更是如此。按照休斯的观点,信息通信技术对政府的真正革命性作用,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在政府运行中的使用。“信息通信技术的革命改变了一切。只有每张办公桌上都有个人计算机,计算机的运用在政府成为普遍现象,且与局域网链接并可进入互联网的时候,技术才会对组织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共部门的运行方式开始发生转变:现在技术正被看作公共部门改善其管理水平和为公民提供服务方式的关键因素。”〔4〕[澳]欧文·E. 休斯:《公共管理导论》(第4版),张成福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06页。这一判断为认识公共行政数字化进程的阶段性提供了依据。
对于数字化引发的公法革命性变化的深刻性,新近出版的《信息技术革命对国家、宪制和公法的影响》(2021年)一书在其导论中做了如下代表性的阐述:“我们现在正处于信息和技术革命中。这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革命事件,它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道德、人类和社会支柱的本质。它正以其经济、社会、政治和法律基础对我们共同生活的关键概念提出挑战。我们社会的道德、政治、经济和法律基础受到了深刻的动摇。它们的概念支柱,植根于理性主义和启蒙主义,植根于国家领土,植根于公私分界,植根于界定好与坏、正义与非正义、合法与不法的基本概念,正受到进行中的信息和技术革命的深刻挑战。”〔5〕Martin Belov ed., The IT Revolution and its Impact on State, Constitutionalism and Public Law, Hart Publishing, 2021, p.3.就行政法而言,数字行政法对传统行政法变革的深刻程度高于以前任何一次历史类型的变迁,包括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管理主义新行政法,后者的重心是在效率导向下引入市场机制和企业管理规则,以及公共职能的外包和民营化。
(二)新产业革命和信息社会的影响
公共行政组织及其行政法与第四次产业革命及其信息社会形态的关系,正在成为评价公共行政组织合理性和行政法正当性的一个标杆。这里举出运用这一标杆进行评价的两个例子。一个是美国的一项研究中提到:“2010年美国参议院在一份关于加强网络弹性的立法报告中称:‘我们的政府仍然是为工业时代、为生产线和大规模生产组织的。’它是一个庞大和层级分明的企业集团,当跨越机构边界线时获取信息和做出决策的成本很高。然而行政程序法却规定必须根据工作过程记录中确定的事实做出决策。”〔6〕Tom Wheeler, Phil Verveer & Gene Kimmelman, New Digital Realities; New Oversight Solutions in the U.S., The Case for a Digital Platform Agency and a New Approach to Regulatory Oversight, The Shorenstein Center on Media, Politics and Public Policy,Kennedy School of Harvard University, August 2020, p.60.另一个是以研究语境法学著称的英国资深行政法教授卡罗尔·哈洛和理查德·罗林斯所强调的,行政法所依托的社会类型已经从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他们在影响极大的《法律与行政》一书新版的第七章“信息国家”中,将国家定义为信息管理者,提出了从信息自由法、数据流动与隐私权保护到数据性监视与人权相遇的研究思路。〔7〕See Carol Harlow & Richard Rawlings, Law and Administration, 4th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2, pp.261-300.这些论述提示我们,无论行政法的自主性及其体系性达到什么程度,行政法对产业形态和社会形态的依存程度都相当高。如果说这种依存度和一致性是衡量行政法正当性的重要尺度,那么,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已经使行政法到了重新评价其既有体系正当性的转型时刻。
(三)公共行政新范式的影响
在现代行政法的发展历史上,公共行政改革常常是行政法变迁的前提条件,公共行政变革及其形成的新行政范式也总会构成对行政法的挑战并促使其创新发展。这不但因为公共行政改革总是根植于行政运行的效率需求,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往往更直接和更迅速地反映时代变迁中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需求。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行政改革以及随后管理分析型行政法的出现,就是公共行政促使行政法变迁的一个重要例证。根据信息技术对公共行政的影响,英国的一个研究项目提出了数字时代公共行政新范式的主张,这一项目曾对英国、美国等七个发达国家中央政府的电子政务进行了历时五年的考察。他们在《数字时代的治理》(2006年)一书中分析了信息技术对公共行政的影响方式:“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的影响在当前的公共部门管理中是突出的,因为它们是当代韦伯合理化过程的基础。我们认为,IT系统的这种影响的产生,不是以任何直接的技术确定的方式,而是通过与信息系统相关联的认知、行为、组织、政治和文化变化的方式。”〔8〕Patrick Dunleavy, Helen Margetts, Simon Bastow & Jane Tinkler, Digital Era Governance: IT Corporations, the State, and E-Govern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217.如此看来,该研究主张判断数字化影响公共行政变化的视角,是公共行政的组织变化或者韦伯式组织模式的变化。在这一认识基础上,他们进行了公共行政新范式的提炼,意在为整个公共行政适应信息革命的变革提供指引。
该书的两位主要作者在2013年发表的《数字时代治理的第二个浪潮》一文中,从新旧对比的视角对数字时代公共行政治理范式进行了更明确的阐述:“新公共管理(NPM)最初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是一种有效的行政现代化手段,但在21世纪初,它先是僵化,然后陷入重大危机。数字时代治理(DEG)变化的第一波代表了政府现代化轨道的交换转变。自2010年以来,社交网络的发展使公共行政现代化主线进一步偏离了新公共管理模式,并使数字时代治理的三个主题(再整合、整体化和数字化)与之前的准范式有了更强的区别。”〔9〕Helen Margetts & Patrick Dunleavy, “The Second Wave of Digital-Era Governance: A Quasi-Paradigm for Government on the Web”, Published by the Royal Society 2013, rsta.royalsocietypublishing.org., p.3. 国内对数字治理理论的介绍和研究,参见韩兆柱、马文娟:《数字治理理论及其应用的探索》,载《公共管理评论》2016年第1期,第92-109页。这三个主题比较集中地代表了数字技术应用中创造的所谓公共价值。这里阐述的数字治理新范式旨在替代新公共管理治理范式,但是替代的程度和实践的可能仍然值得继续研究。整体化政府在我国实践中的应用场景,在政务服务提供方面表现为“一站式服务”“一网通办”或者“跨域通办”〔10〕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政务服务“跨省通办”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35号),强调提供政府政务服务的统一、协同和合作。等。
由上可见,数字行政法的兴起受到诸多方面的影响和制约,行政法体系性变革将具有明显的被动性。同时,由于新技术革命、新产业革命、社会形态转变和公共行政变革都在持续的演进中,数字行政法的兴起和成长可能充满不确定性,所以在制度形成方面,需要以发展的目光和不断更新的视角进行观察和评价。
二、数字行政法的形成条件
数字行政法的形成需要一些基本条件,其中数字政府的规模、数字化行政时空和数字化时代法律体系的新结构方面的重要程度比较高,它们共同为数字行政法提供了基于数字技术的统一行政环境和数字法治的法律体系环境。
(一)数字政府的规模和时空
数字政府达到一定规模或者实现全面性数字政府是形成数字行政法的基础条件,这里所说的“一定规模”相当于意大利学者所说的“电子政府的扩散水平和倡导数字化议程的成功”。〔11〕Stefano Civitarese Matteucci, “The Rise of Technological Administration and Ragged Rout towards a Digital Administrative Law”, in Domenico Sorace, Leonardo Ferrara & Ippolito Piazza eds., The Changing Administrative Law of an EU Member of State: The Italian Case, Springer Nature Switzerland AG and G. Giappichelli Editore, 2021, pp.133-134.由于数字化法律的实施对技术应用能力、支持性设施设备和专业人员的高度依赖性,脱离数字政府的数字行政法几乎是纸上谈兵,更不用说人工智能深度学习产生的特殊时空和算法对普遍性制度规则的超越。因此,数字政府至少包括支持数字行政的基础设施、平台实体、专业组织和人员、大数据资源、计算能力和算法及其相关标准和相关规则等。为了达到上述必要因素的要求,除了消除制度性和意识性障碍以外,财政支持和管理能力是至关重要的,这又将极大地约束数字政府的建设进程。所以,数字政府建设成为推进政府现代化和提升管理水平的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领域。
目前来看,以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应用为特征的数字化向公共行政各个领域扩展的趋势非常明显。比较而言,发达国家较早和持续不断地推进了数字政府的建设。美国总统2019年2月11日第13859号行政命令,明确提出了以人工智能改革几乎所有行政部门和机构的目标。〔12〕See Executive Order 13859 of February 11, 2019, Maintaining American Leadership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ederal Register Vol. 84, No. 31.英国在2012年提出政府数字战略,随后又制定了2017年至2020年的数字政府转型战略,其着眼点是政府与公众和企业的关系。澳大利亚在2018年发布了面向2025年的转型战略,提出以人的需要为核心,倡导利用数据分析来改善公共政策。我国电子政务的国际排名,到2020年大致位居四十多名。从我国目前对数字政府的推进政策,尤其是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中关于数字国家建设的政策来看,建设数字政府的规模和速度有望加快,这包括对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和在公共行政的应用领域。公共部门数字化建设规模有代表性的地方是浙江省。2021年2月公布的《浙江省数字化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提出“在根本上实现全省域整体智治、高效协同”并“贯穿到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浙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先行省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其做法具有示范和引领作用。
规模化数字政府的发展目标,是根据行政统一制度和数字行政技术标准,通过推进政府数字化平台的互联互通,实现上下级政府之间的有效统一领导和同级政府机构之间的协同合作,建立基于数字技术的整体型政府。所以,数字政府的规模化建设也是新型政府结构的形成过程。
基于数字技术应用的公共行政新时空,是形成数字行政法的约束性条件。大卫·约翰逊和大卫·波斯特在《法律与边界:网络空间中的法的兴起》一文中呼吁“认真对待网络空间”。他们认为网络空间挑战了法律对领土边界的传统依赖,这一新的网络空间需要并可以创立自己的法,需要有明确的在线交易规则和有效的法律制度。〔13〕See David R. Johnson & David Post, “Law and Borders: The Rise of Law in Cyberspace”, 48 (5) Stanford Law Review 1367-1402 (1996).所以,依托行政时空生成的各类行政管理制度,在数字化新行政时空中几乎都有重塑和新建的任务。
数字化政府的新时空引发的公共行政及其法律制度变革的最新例证,是2021年7月10日召开的二十国集团财政部长与央行行长第三次会议就15%的全球最低企业税达成共识。这一共识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接受了“价值创造地”征税原则,改变了依照企业实体设立地原则征税的传统制度。这一改革为对在虚拟空间从事跨越国家边界经营的企业进行征税提供了依据。国际税收制度变革的情形,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在其他公共行政领域。在自动化政务服务领域,政府提供的身份和企业证照等基础性服务,在技术上已经具备异地和全时提供的能力,可以不再受行政区和法定工作时间的限制。应用人工智能产生的去中心化格局和自主机器学习的新时空,对于传统行政法体制和法律制度则具有更深刻的变革意义。
数字化行政新时空的建设,包括数字技术和标准规则两个方面,以便为现实行政时空向虚拟行政时空的转换和利用提供技术可能及行为准则,也为适应虚拟时空的数字行政法提供必要的条件。因此,统一的技术标准是建设高度协同和统一的整体化数字政府的基础,应当对分散的或者各行其是的部门信息化建设体制进行调整。
(二)法律体系的新结构
公法与私法二元化的法律结构是行政法存在的前提。在数字化进程中,电子商务与电子政务的分向发展反映了工业时代形成的法律体系的现实影响力。同时,传统法律体系对数字化经济社会的不适应也日益凸显。伴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数字平台企业和商务大数据的内在公共属性,使传统的民商法和反垄断法悖论迭出,传统私法内公共因素的激增已经突破了公法和私法交叉和融合的通常程度。在公法与私法一体性不断增强的情形下,传统的民商法和行政法都难以完全独立地实现法律规范功能,全球和民族国家的网络法正在悄然改变着传统的法律原则和制度。〔14〕See Michael L. Rustad, Global Internet Law in a Nutshell, 3rd ed., West Academic Publishing, 2016. 该书从全球互联网的角度阐述了数字化对多个法律领域带来的重大变化,其对传统的合同、侵权、知识产权制度的改变的案例分析尤其值得关注。
解决数字化时代新型公法与私法二元化结构问题的依据,首先是宪法方面的基本立场。从比较法上看,优先解决宪法基础问题也是欧盟在发展数字法方面的一个重要经验。〔15〕2016年欧盟“数据保护条例”以前的相关立法,是1995年的“数据保护指令”。面对要求修订该指令的意见,直至“2007年3月7日欧盟委员会通过的通知,还明确该指令不应当予以修订”。但是2010年11月4日欧盟委员会在它的新通知中改变了这一立场,认为“修订是需要的”。欧盟委员会立场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在于有关宪法方面的情况发生了重要改变。相关研究指出:“2009年的《里斯本条约》给欧盟的法律结构带来了重大的宪法变化。这些变化包括:引入数据保护权利并为在《欧洲联盟运作条约》(TFEU)第16条的数据保护立法提供了具体法律依据;消除《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支柱结构的大多数方面(本质上意味着相同的基本法律保护应适用于所有类型的数据处理);加强对欧洲议会制定数据保护政策的监督和参与;将《欧盟基本权利宪章》(CFR)提升至宪法地位,其中包括数据保护的具体权利(CFR第8条);以及欧盟加入《欧洲人权公约》(ECHR)的义务。”See Christopher Kuner,Lee A. Bygrave & Christopher Docksey eds., Laura Drechsler(Assistant Editor),The EU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 A Commenta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3-4.数字化时代最突出的宪法议题是对公民信息权和隐私权的保护。德国行政法学者认为,“数据保护法应当保护公民对个人数据的控制,限制或者排除特定的使用方式。依据是《德国基本法》第2条第1款有关人人享有个性发展权的规定,即‘个人原则上自行决定公开个人生活情况的时间和范围的权利’”。〔16〕[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39-440页。该页脚注中说明所引用的德国联邦行政法院判决源于《德国联邦行政法院判决汇编》第80卷第367页和第373页。
我国关于个人信息权益与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的关联性,直到《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的第三次审议稿才开始明确起来。2021年 8月17日至20日在北京举行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是一个重要的转折,该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下简称《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条明确规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关于这一重要变化的认识,见于2021年8月17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提交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在该报告中,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提出的“主要修改意见”第1项写道:“有的常委委员和社会公众、专家提出,我国宪法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制定实施本法对于保障公民的人格尊严和其他权益具有重要意义,建议在草案二次审议稿第一条中增加规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赞同上述意见,建议予以采纳。”〔17〕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来源: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108/a528d76d41c44f33980eaあe0e329あe.shtml,2021年8月20日访问。全国人大常委会采纳了宪法与法律委员会的上述建议,为《个人信息保护法》成为数字国家建设的重要基本法奠定了基础。
2021年《个人信息保护法》将个人信息权益与宪法保护的人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权直接联系起来,对确定信息权益的法律属性和国家的保护义务具有重要作用。此前关于个人信息权益法律属性的确定停留在《民法总则》和《民法典》等关于个人信息的规定中,《个人信息保护法》终结了在单向度的认识中徘徊的局面。王锡锌教授分析了个人信息权益的宪法保护问题,他认为“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对应着‘个人信息受保护权’,但此种权利并非民法意义上的权利,而是国家履行其保护义务的价值基础与宪法依据,其功能主要在于对抗和缓解‘数据权力’对个人信息造成的侵害风险”。〔18〕王锡锌:《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及展开》,载《中国法学》2021年第1期,第146页。由此看来,《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的个人信息权益与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对个人信息权益的宪法关联性的确定,为数字社会新型法律体系的构建提供了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条关于“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个人不得侵害自然人的个人信息权益”和该法关于政府处理个人信息的规定说明,对个人数据信息权利与数据的公益功能进行划分仍然是必要的。因此,在数字化时代实行新型公法与私法的法律结构和发展数字行政法的必要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数字化时代的公法与私法二元化法律结构必须具有新的内涵。如果说数据信息权益对于公民个人的法律地位具有特别的重要性,那么国家和政府对个人权利的保护也就担负着更重要的职责。同时,个人信息也具有极大的公共意义和公共价值,因为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和数字政府对大数据尤其是个人信息具有极大的依赖性。所以,公法与私法分离基础上的融合和共生也是势在必行的,但是应当不断寻找和尝试新的内容和形式,例如,对具有集中性和公益性的平台企业进行规制的新方式、新组织和新制度。
三、向数字行政法的转型
(一)向数字行政法转型的途径
向数字行政法转型的途径,大致上可以有行政改革回应型、个人信息权益保护型和行政法结构再造型三类。
第一类是对数字化行政改革做出法律回应,为行政组织变革和新型公共服务供给方式进行法律确认并提供新的制度化安排。前述提到的数字治理新范式中,整体型公共行政和基于需求的公共服务供给方式,为公共行政提供了新框架,增加了新价值,反映了数字化过程中公共行政的主要变化。意大利学者认为,行政组织整体化和以公民为中心的行政供给是政府数字化的标志。〔19〕意大利学者的论文对政府数字化过程进行了分析。文章将这一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并提出转入赋权性法治议题的节点。(1)建立一个制度化的网站,通过网络进行运作,按照可接近原则,提高了可用性、获得性和残疾人友好性,在信息化、内部运行的,可靠和易于使用的。(2)进行双向的信息交流,但是不包括任何在线处理,没有与用户完整的互动。只是考虑了官员与用户的信息交流。服务提供仍然是传统的方式,即文件的方式。(3)处理和整体化是成熟的两个阶段,服务在线上提供,以大文件的方式进行信息通信技术的运行。这里出现了网络平台运行的数字程序,用精细的数据软件生产了可以形成法律关系的决策,包括支付罚款,复杂的可以包括许可或者给予福利。整体化更多地强调专门的组织性工具,追求完全的后办公室(back-oきce)实践的转型。它的意义在于,开始一个以公民为中心的新时代,而不是一个以行政官僚为中心的传统模式。前两个阶段仍然是信息化阶段,是新管理运动的伴随物,是鞘里的剑,后面两个才是数字化。所以这是两个模式和两个时代。See Stefano Civitarese Matteucci, “The Rise of Technological Administration and Ragged Rout towards a Digital Administrative Law”, in Domenico Sorace, Leonardo Ferrara & Ippolito Piazza eds., The Changing Administrative Law of an EU Member of State: The Italian Case, Springer Nature Switzerland AG and G. Giappichelli Editore,2021, pp.132-133.但是这种法律转型路径不能全面反映数字化对传统行政法的系统性挑战,它的可取性是有限的。
第二类是以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为中心,为公共行政应用数字技术设立条件和界限,设立以最小和必要为特征的法律原则和相关规范。国内外都有这类内容的立法例。我国2020年10月2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就是一例。该修订稿规定在防治和控制传染病传播中应用数字技术,应当按照必要且最小化原则开展信息采集、病例识别、传染源追踪等工作。〔20〕该稿第四章“疫情控制”第48条:“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立即组织力量,按照传染病防控预案进行防治,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染病的传播途径,必要时,报经上一级人民政府决定,可以采取下列紧急措施并予以公告……(八)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按照必要且最小化原则开展信息采集、病例识别、传染源追踪等工作。”这类转型思路是将数字行政的规范功能大量地留给了行政机关本身,它的可取性依然是有限的。
第三类在行政法学领域受到关注的程度相当高,它致力于解决数字化对既有行政法的系统性挑战。由于基于人工智能的自动化行政决策和行政规制对象的数字化属性,使既有行政法的正当性解释和行政规制的专业化运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对此行政法必须做出回应并对行政法体系进行结构性再造。
(二)数字行政法转型的主要场景
行政规制是当代行政法的主要应用领域,也是向数字行政法转型的主要场景。对市场的行政规制是当代政府的基本职能,回应市场失灵是行政规制的基本依据。在数字化的演进过程中,政府对数字市场的监管不再限于基于微观经济学的专业化监管框架。能否对信息资本进行有效规制,防止信息资本通过投资平台企业达到垄断市场和控制社会运行的目的,已经成为数字化时代政府规制的重要方面。
行政规制领域发生的重大变化,是无形财产对有形财产的嵌入并形成对各类财产的主导力。由无形财产主导的新型市场及其财产关系正在形成。传统的行政规制是以有形财产市场交易活动为主要对象的。政府对市场的规制是以克服市场失灵为宗旨的专业化行政活动。由于微观经济规制具有经济管理的专业性,法律上对行政规制的实体性决策给予尊重,行政法对规制机构的法律约束重在行政程序方面,特别是根据正当程序为当事人提供程序权利上的保护。随着财产主导形态从有形财产向无形财产转移,政府的行政规制及其法律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使既有的行政法体系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首先,信息化的无形财产权及其行使方式不限于经济性权利,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延伸到人格权(隐私权)、政治权利(公民表达权)和其他重要利益。这一问题原来在知识产权方面就本质性地存在,但是由于国际规则等许多制度将知识产权定义为私权利,还由于有的知识产权长期依托于有形财产存在,所以它的法律权利的多面性问题并不突出。随着知识产权信息化程度的提高,信息化产品的增多以及电子商务的发展,相关权利不但在财产法律属性上发生了多元延伸,而且在网络交易过程中产生了大量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问题。这些变化强化了政府规制数字市场的政治性因素,赋予政府规制数字市场新理由,要求以规制为重点的行政法制度进行重大调整。
其次,在政府规制过程中出现了程序与实体并重的新结构。众所周知,当代行政法的特点是行政程序法占据主导地位,透明度、公众参与和法律问责制都来自行政程序法。突出行政程序法的重要原因在于政府规制职能的微观经济属性和规制专业化的法律定位。随着数字经济中财产属性和政府规制属性的变化,对政府规制行为的法律规范和司法审查也就不再局限于行政程序法,宪法性实体法规范正在成为评价政府行政规制活动的新依据。〔21〕See Jon M. Garon, “Constitutional Limits on Administrative Agencies in Cyberspace”, 8 Belmond L. Rev. 499 (2021).这不但使行政法中的实体性问题得到突出,而且继续了行政法宪法化的路径,形成程序法与实体法并重的行政法新结构。
数字化进程中行政规制的上述变化,使行政法关于行政规制的合法性假设的基础发生了动摇,这些假设包括规制机构、人员、业务的专业性和行政裁量的正当性。法律上正在对这些变化做出回应以推进转型。目前来看,程序与实体并重的混合型规制是一个重要趋势,它将是数字行政法系统化的基本内容。
(三)数字行政法转型的关键议题
基于人工智能的自动化行政决策,是目前行政法学数字化问题研究的重点。其中最新的代表性著述有二:一个是2021年意大利学者编辑出版的《一个欧盟成员国的变迁中的行政法:意大利的案例》一书,其中以《技术行政的崛起和走向数字行政法的崎岖之路》为题的文章认为,伴随数字技术引入的规则正在影响行政决策及其程序,这是行政法的核心,也是该文进行深入讨论的对象;〔22〕See Stefano Civitarese Matteucci, “The Rise of Technological Administration and Ragged Rout towards a Digital Administrative Law”, in Domenico Sorace, Leonardo Ferrara & Ippolito Piazza eds., The Changing Administrative Law of an EU Member of State: The Italian Case, Springer Nature Switzerland AG and G. Giappichelli Editore, 2021, p.134.另外一个是同年出版的《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学报》,〔23〕Se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 Sciences, Summer 2021. Dædalus Summer 2021 issued as Volume 150,Number 3 by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 Sciences.其以“二十一世纪的行政国家:解构或重建”为主题,登载了关于行政自动决策及其与行政法关系的两篇文章,即伯纳德·W. 贝尔的《用自动化巫师们取代官僚?》和卡里·科格连斯的《自动化国家中的行政法》。这些著述都对人工智能自动化行政决策给行政法带来的重大改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用自动化巫师们取代官僚?》一文评价说:“但人工智能的两个特点,即不透明性和非直观性,威胁着行政法的核心价值。行政法所体现的价值性原则包括:(1)根据公布的标准对个人进行单独处理;(2)行政法体现了某种手段和目的的合理性;(3)行政决定必须接受外部行为者的审查,并对公众透明。人工智能对这三个关键规范都有负面影响。”〔24〕Bernard W. Bell, “Replacing Bureaucrats with Automated Sorcerer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 Sciences 89(Summer 2021).这一说法有代表性。在行政决策中引入人工智能,以机器自动化方式来形成法律关系和决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这对当代行政法的核心部分提出了挑战。还有研究者认为,“行政国家合法性的前提,源于我们对机构专业知识的信任”,“自动化丢弃了为行政国家提供正当性的专业化和灵活性,动摇着机构存在和权威的重要前提”。〔25〕Ryan Calo & Danielle Keats Citron, “The Automated Administrative State: A Crisis of Legitimacy”,70 (4) Emory Law Journal 798 (2021).行政机关以行政裁量权进行专业化规制、解决社会问题和进行实验主义治理,是应对市场失灵和风险社会所必需的制度安排,对于行政裁量的法律约束可以通过行政程序中的公众参与、透明度和监督问责来实现。但是,目前基于数字算法规则的自动化机器决策难以有效地实现行政法的上述使命。
政府利用人工智能的重大实践性问题,是与个人数据信息权益保护之间的关系。智能化决策以数据作为驱动力。政府根据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形成的行为数据,对人的行为性质及其特征进行评估,继而采取的预测性和预防性行政措施是否合法存在严重争议,这其中以利用人工智能生物识别技术对人的监控形成的行为数据的争议尤甚。2021年10月7日,欧洲议会通过决议,呼吁对警方使用AI进行预测性警务活动实施严格限制措施。〔26〕参见欧洲议会民事自由、司法和内务委员会提交给欧洲议会的报告(Committee on Civil Liberties, Justice and Home Aあairs,Report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Criminal Law and its Use by the Police and Judicial Authorities in Criminal Matters [2020/2016(INI)],A9-0232/2021, 13.7.2021, p.15.)。这意味着欧洲议会对于普通行政中利用对人的行为的大数据采取预测性措施的合法性基本上持否定立场。在政府应用人工智能的领域中,获得法律包容最多的无疑是安全领域,包括追究刑事犯罪的社会安全和国家安全领域。如果在刑事领域都受到谴责和限制,那么普通行政对此种技术的应用就更应当受到限制。因此,这一立场对于人工智能在普通行政中的应用将产生广泛影响。
行政机关利用人工智能进行决策的合法性基础,包括人工智能的可控性、可信性、可解释性和透明度。如果能够满足这些要求,将人工智能应用于辅助性行政决策、为公众提供政务服务、采取普遍性行政措施等方面的前景仍然乐观。为流动人口提供身份证明服务,进行生态环境监测、公共安全生产监测和自然灾害监测等,都可以是优先实行数字化转型的行政领域。对以人工智能为中心的数字行政的高度可控性和可信性,也有可能通过技术发展实现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如研究者们提出的可解释的人工智能。〔27〕See Alejandro Barredo Arrietaa, Natalia D’ıaz-Rodr’ıguezb, Javier Del Sera, c, d, Adrien Bennetotb, e, f, SihamTabikg,Alberto Barbadoh, Salvador Garciag, Sergio Gil-Lopeza, Daniel Molinag, Richard Benjaminsh, Raja Chatilaf & Francisco Herrera,Explainabl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XAI): Concepts, Taxonomie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ward Responsible AI, Preprint submitted to Information Fusion, October 23, 2019.不过即使达到了上述要求,行政机关在法定的行政裁量的领域进行人工智能自动化决策也应当遵守必要的条件。
在自动化决策的合法性问题上,卡罗尔·哈洛和理查德·罗林斯提出了平衡性问题:“自动化决策修正了行政法上关于裁量权的传统。计算机讲的是规则的语言,很难适应自由裁量权或为特殊情况做出规定。按照行政法的传统要求,要在一致性和个人处理之间取得平衡,在计算机化系统中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就是为什么数据主体可以选择退出完全自动化的决策过程,或者要求重新考虑已经做出的决定)”。〔28〕Carol Harlow & Richard Rawlings, Law and Administration, 4th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2, p.258.从上述分析来看,政府在行政裁量领域利用人工智能进行自动化决策的必要性和风险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在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进行行政规制的行为特点和正义标准。数字行政法只能为更高程度的行政正义提供支持,而不应当降低行政正义的质量和水准。如果行政正义建立在行政裁量之上,那么就不应当放弃行政裁量。所以行政机关进行人工智能自动化决策,应当获得行政裁量相关利益关系人的同意,或者只能限于利用人工智能进行辅助性决策。总之,自动化决策将成为数字行政法系统化建设的中心议题。
四、数字行政法的系统化
系统化是数字行政法的重要形成方式,也是行政法对整体化数字政府的制度性反应。系统化的途径如何选择,是形成数字行政法的基本问题。
(一)传统的行政法教义学体系的作用
对于数字行政法的系统性构建途径,意大利学者认为,它源于德国等大陆法国家行政法教义学框架所具有的对数字行政法的接纳力。〔29〕See Stefano Civitarese Matteucci, “The Rise of Technological Administration and Ragged Rout towards a Digital Administrative Law”, in Domenico Sorace, Leonardo Ferrara & Ippolito Piazza eds., The Changing Administrative Law of an EU Member of State: The Italian Case, Springer Nature Switzerland AG and G. Giappichelli Editore, 2021, p.144.尽管这种可能性不能忽视,但是德国式教义学在实践应用上对实证法的依赖性过强,对价值性法律原则的提炼过于迟缓,这限制了它在数字化时代行政法变化中的作用。德国新行政法学的研究曾一再提起德国行政法教义学的不足。由于德国行政法的宪法化日盛,行政法教义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已经式微。所以,在数字行政法形成中,考虑采用德国式行政法教义学时不宜过于狭窄和局限。
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传统行政法体系,体现着德国行政法教义学的构造逻辑和工业化时代的法学体系构造因素。这一体系把现实空间、有形财产、成文法源、主体意志及其责任形式作为进行体系化构造的主要因素,而它们在数字化进程中纷纷受到挑战。例如,在法律渊源方面,德式行政法教义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托成文法生存的。如果代码成为行政法的法律渊源,那对传统的行政法将是一个重大的改变。对此,英国资深行政法专家哈洛和罗林斯以赞赏的语气表达了乐观的看法,她们写道:“最近,英国央行和英国金融市场行为监管局都进行了实验,利用新的数字技术以计算机代码取代本来的法律语言编写规则。监管机构不是用法律英语编写规则,而是用机器可读的英语编写规则或规定特定的软件应用程序。这种新工具将使合规变得更容易,并缩小受监管实体采取错误做法的空间。如果取得成功,这一工具将得到更广泛的应用。例如,它将有助于编纂和协调复杂的移民规则。然而,不那么积极的是,存在翻译错误的风险,而且输出几乎不透明”。〔30〕Carol Harlow & Richard Rawlings, Law and Administration, 4th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2, p.255.在此,两位教授乐见计算机代码发挥的积极作用,指出了需要改进的缺陷,支持了代码在数字行政法形成中的作用。
产生于工业化时代的行政法教义学框架,是否可以适应数字化行政问题的答案正在逐渐地清晰起来。一个基本的判断是,它对数字化行政的适应性是相当低下的,尤其是对不确定性和阶段性发展的适应能力不够。
(二)不确定性和外部驱动型因素的作用
数字化政府是一种基于数字技术应用的公共行政转型过程。这一转型过程存在着现实性、持续性和不确定性,它对构建结构稳定的数字行政法体系带来了难度。
2020年欧盟委员会印发了科学和知识服务部门联合研究中心(JRC)做出的一份名为“探索欧盟数字政府转型”的报告,指出了政府数字化转型的不确定性及其后果。该报告在结论部分指出:“数字政府转型不会以直接或线性的方式朝着一个明确的目标发展。这意味着,任何概念化都必须反映出这一过程的不确定性和多向性,这可能导致与政策制定者的预期截然不同的结果……转型可能导致根本性的变化;然而,这些变化可能不利于民主、信任和公民参与。”〔31〕Egidijus Barcevičius, Cristiano Codagnone, Luka Klimavičiūtė & Gianluca Misuraca, Exploring Digital Government Transformation in the EU: Expert Consultation and Stakeholder Engagement, Publications Oき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Luxembourg,2020, ISBN 978-92-76-21064-1, doi:10.2760/621165, JRC121494, p.29.德国和奥地利的研究分析了这种转型的外部驱动性特征:“数字转型是一个受到外部驱动因素(例如公共行政部门利益相关方使用的新技术)严重影响的过程。虽然专家们对数字化转型的潜在最终结果有一定的了解,但他们很少能够强调数字化转型后的公共行政会是什么样子。这表明,数字转型被认为是一个没有结束状态的过程,不像以前设计的电子政府项目,有开始和结束日期,可测量和定义的结束状态,以及固定的预算。相反,数字化转型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需要经常根据外部需求调整其流程、服务和产品。”〔32〕Ines Mergela, Noella Edelmannb & Nathalie Haug, “Defin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Results from Expert Interviews”, 36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10 (2019).如果上述对数字化政府转型的判断成立的话,那么适应数字政府转型的数字行政法就必须面对长期性和不确定性的挑战。这是过去的行政法变迁所没有经历过的情形,也是数字行政法体系的特殊形成方式。尽管过去的行政法变迁也存在技术变革的背景性因素,但是变迁的主要推动力是外部的社会运动、公共部门的内部改革或者两者的相互作用,现在数字政府和行政法的制度改革则主要源于数字技术应用的驱动。
基于数字政府发展的长期性和不确定性特点,数字行政法的系统化构建,可以考虑采用双价值体系和阶段性制度体系两个方面,形成数字行政法体系的发展路径。双价值体系是指行政法一贯坚持的价值和在数字化过程中产生的新价值;阶段性制度体系则是指基于数字技术应用更新期形成的制度体系。
本文对价值性原则问题已经有了一些涉及和讨论,这里需要强调的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对数字经济驱动性资本的行政规制在数字行政法价值原则中居于首位。即使在法律上可以确认市场在数字化发展中的创新作用,但是为了确立公共利益取向的数字社会主导权,引导行政规制的价值性原则仍然是数字行政法的中心所在。其次,价值原则的形成方式已经不再限于过往的做法,数字技术应用的过程中会产生或者提出新的价值原则,尤其是虚拟空间的扩大以及人工智能的机器学习能力的提升,它们都是产生新的行政价值和法律价值的过程。最后,要通过价值原则的提炼和表达方式的多样性来适应技术应用不断迭代的需要。成文法的表达作用将会下降,基于个案提升的法律决定和战略性政策文件因灵活度比较高,在价值原则的表达上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在我国数字行政法价值原则的表达方面,合宪性审查的决定和战略性政策文件都可以成为合适的方式。
五、未完的结语
在结束这篇以比较法为主的文章时,有以下两个问题值得提出并作为展望未来的结语。
第一是数字行政法的系统性框架问题。数字行政法尚在演化形成之中,目前还难以形成清晰稳定的框架。由于大数据、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型数字技术的应用具有越来越强的去中心化趋势,一个类似传统行政法的稳固的制度体系可能难以完整地呈现和持续存在。同时,目前数字化中出现的新的法律问题也极有可能通过技术发展得到化解,而不是单纯地依靠法律制度变革来解决。
第二是我国数字行政法的发展条件。由于我国行政法存在行政争议解决导向的问题,致使行政法发展的主要关注点长期集中于纠正行政侵权方面,对公共行政领域的问题关注度不高。但是,近年来,我国合宪性审查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取得了很大进展,这将极大地促进我国行政法发展的敏感度和集成度,这也包括数字行政法的系统化进程。在我国行政法的特殊性和回应性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议题一直是有待充分开发的关键领域。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和数字政府建设,将为形成基于数字化的发展型行政法体系提供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