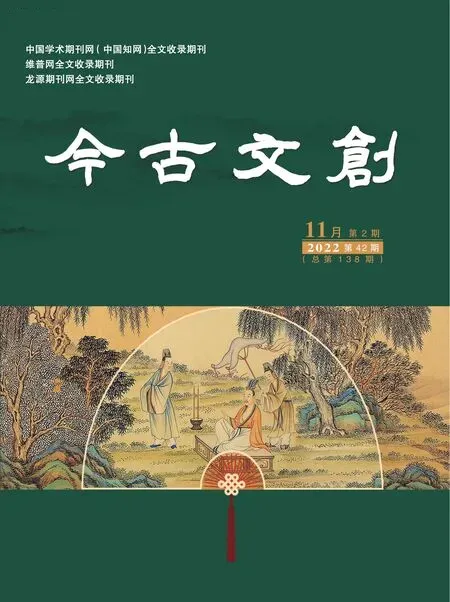以对话理论透视《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替身与自白
◎黄艳芳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广西 崇左 532200)
一、对话理论与替身设计
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中,发现了一把进入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世界的钥匙——对话理论,认为陀氏小说是一种“全面对话小说”。对话是自我与他人语言的相遇,巴赫金所言及的“对话”,并非指小说中的所有对话,而是指两个成对的人物之对话可使人物自评自己的思想。对话理论基本原则就是:“我”需要通过“他人”来认识“自我”。①从小说中的多处情节,可以一窥作者远超同龄人的文学审美品位。比如伊纹教思琪、怡婷读书的情节,就能看出作者十分熟悉并推崇苏联文学大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的主要人物,与陀氏小说的人物们一样,都卷入了生活的旋涡甚至跌入罪恶的渊薮。读者能从小说中看到不少对于人物心理和自我意识的描写,她们在痛苦挣扎中思索,在惶惑不安中质问,在黑暗深渊中呼号。人物彼此通过或隐或显的对话形式,展现自己的内心,认识自我。本文将借助对话理论工具,通过分析文本细节,对《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独特叙事进行解构,试图了解主人公内心深处的自我意识,一窥小说文本所展现的人类心灵的矛盾与隐秘。
台湾学者赵旻祐在运用巴赫金的文艺批评理论分析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时提出,为实现小说的对话原则,小说可以存在两种特殊的独白与对话,所谓特殊是此处的独白与独白式小说中的自说自话、自言自语有所不同,而需要“镜子”“替身”等素材使人物分出另一个人物,通过“镜子”看到“镜中之我”,通过“替身”看到“这世上的另一个我”,使一个人分成两个人物,形成重迭或互补的对应关系,使人物从外部观察自己的形象或思想,完成通过“他人”论述“自己”的对话理论。《红楼梦》中就存在小说人物之间的重迭或互补的特殊对应关系。只不过,中国古代文论中就这种平行对应关系称为“影”。脂砚斋就曾在评点中指出甄宝玉为贾宝玉之影,晴雯乃林黛玉之影,袭人乃薛宝钗之影。此处的“影”,意即西方文论中的“重像”或“替身”概念。②
刘纪蕙在《女性的复制:男性作家笔下二元化的象征符号》一文中引述罗伯特·罗杰斯对于文学作品中替身手法的区分。文学作品中人物的替身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显性替身——外貌相似却独立存在,身世相似或对立;另一种是隐形替身——外貌不同,但身份处境相似,命运个性相似,书中随时将此二人对照比较,以衬托彼此。由此可见,能否形成替身取决于二者身份处境、命运个性是否相似,而长相是区别显性或隐性的关键因素。③以《红楼梦》为例,甄宝玉是贾宝玉的显性替身,晴雯和黛玉、袭人和宝钗就是隐性替身的关系。按照罗伯特·罗杰斯的区分方法,《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主人公房思琪替身有两个:刘怡婷是隐性替身,许伊纹是显性替身。
二、 房思琪与替身的对话
(一)隐性替身——刘怡婷
刘怡婷可以说是房思琪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重像。首先,二者容貌不同,刘怡婷生的并不好看,“扁平的五官上洒满了雀斑,脸几乎可以说是正方形的”④, 而房思琪是长着一张犊羊脸的搪瓷娃娃小女孩,两人的外形是美与丑的两个极端;但是,两人自有记忆以来就是邻居,生活环境相同,家庭境况相似,一样的年纪,同样是冬天出生的小孩,一起上学一起玩耍,用绒毛娃娃打架,一起弹钢琴,“在转骨的中药汤里看彼此的倒影”⑤, 在彼此的倒影中一起长大。
与外表相异所不同的是,二人的个性惊人的相似,在灵魂层面高度一致,小说中多次提到,房思琪和刘怡婷是思想上的双胞胎,精神的双胞胎,灵魂的双胞胎。二人精神和灵魂的默契集中体现在文学品味上,她们在别的小孩还在读《波德莱尔大遇险》、看九品芝麻官时,就已经在读波德莱尔和包法利夫人了。“不是一个爱菲茨杰拉德,另一个拼图似的爱海明威,而是一起爱上菲茨杰拉德,而讨厌海明威的理由一模一样。不是一个人背书背穷了另一个接下去,而是一起忘记同一个段落。”⑥两人在文学才华上也是平分秋色、不分伯仲,就连分别写的作文,也像是换句话说。
这种灵魂的默契,在外人看来都觉得惊奇和羡慕。许伊纹给她们两个说书的时候,就曾对她们说,“柏拉图说人求索他缺失的另一半,那就是说两个人合在一起才是完整,可是合起来就变成一个了,你们懂吗?像你们这样,无论缺少或多出什么都无所谓,因为有一个人与你镜像对称,只有永远合不起来,才可以永远做伴。”⑦作者借许伊纹之口,直接点明了房思琪和刘怡婷“镜像对称”的替身关系。在许伊纹眼里,这种精神上的契合,灵魂上的共生关系,有别于甚至是高于男女间的恋爱关系的。
从以上文本证据来看,刘怡婷是房思琪的隐性替身。可以说,刘怡婷是不那么好看、没有遭受过性侵的房思琪。这是作者面对房思琪的境遇所做出的思考和假设:假如房思琪不那么好看,是否能够幸免于难?假如受伤害的是刘怡婷,那么作为她“灵魂双胞胎”的房思琪会怎么做?如果我们承认房思琪是同样经历过性侵伤害的作者本人在小说中的投射,那么作者或许想透过这个替身设计,引起每一位读者的沉思:假如我们的好友、我们身边的人遭遇了这样的痛苦和不幸,我们应当如何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感同身受、去理解、去帮助?这个问题,作者借许伊纹之口已经做出了回答。怡婷上大学前,伊纹让怡婷“选择经历所有思琪曾经感受过的痛楚,学习所有她为了抵御这些痛楚付出的努力”“替思琪上大学”,“经历并牢牢记住她所有的思想、思绪、感情、感觉,记忆与幻想、她的爱、讨厌、恐惧、失重、荒芜、柔情和欲望”,“紧紧拥抱着思琪的痛苦”,“变成思琪,然后,替她活下去”⑧。
刘怡婷被看作是这场社会性的暴力伤害中的幸存者。每一个侥幸躲过了伤害的人,都可以选择对这样的事情视而不见,对受害者的痛苦视而不见,在虚伪的安全里过和平安逸的日子,但是,她也可以选择对暴力愤怒,牢牢记住、紧紧拥抱受害者的痛苦。这是许伊纹对刘怡婷的期许,也是作者林奕含对整个社会的期许。许伊纹还建议刘怡婷把这一切都写下来,以写作的方式来表示对忍耐的决裂,对暴力和伪善的愤怒,让人不用接触就可以看到这个世界的背面。刘怡婷身上被赋予了某种与暴力抗争、与黑暗决裂的责任。这份救赎的使命需要通过写作来完成。刘怡婷最后是否写下来了,作者没有说。但是作者本人,却完成了这项工作。她是受害者,亦是救赎者。
(二)显性替身——许伊纹
许伊纹是房思琪和刘怡婷的邻居,是两位懵懂少女的文学启蒙导师,也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小说中许伊纹甫一出场,作者就描写了她惊为天人的美貌:鹅蛋脸,大眼睛长睫毛,高鼻梁,白皮肤。但是她的美貌又是脆弱易碎的,“眼睛大得有一种惊吓之情,睫毛长得有一种沉重之意”⑨, 就连皮肤的白都“隐约透露着血色”。房思琪也有着与许伊纹一样晶莹脆弱的美貌。小说描写到思琪和伊纹共处一室的画面,常常把她们比作一大一小的俄罗斯套娃。房思琪的挚友刘怡婷,许伊纹的丈夫钱一维,以及李国华都觉得两人的长相非常相似,从眉眼到轮廓到神气都很像。以至于在怡婷眼中,钱一维、许伊纹和房思琪三个人一起时仿佛是一家人。就连许伊纹本人,看到房思琪哭泣,便想到自己流泪的样子,看到病中房思琪的笑容,也觉得那很像以前还没跟一维结婚、还不曾被家暴伤害过的自己,那是一种还没看过世界背面的天真笑容。
除了外貌相像,两人的个性与品位、人生境遇以及面对伤害时的思维模式也很相似。思琪和伊纹在文学方面都有着极高的品位和才华,思琪与怡婷在别的小孩还在读《波德莱尔大遇险》、看九品芝麻官时,就已经在读波德莱尔和包法利夫人了。许伊纹是比较文学博士,小说中多次描写到许伊纹带房思琪、刘怡婷两人读书的片段。在两个小女生面前,许伊纹扮演的是文学启蒙老师的角色。房思琪文学审美的品位很大程度上是受许伊纹影响。这部小说的故事主线是围绕房思琪展开的:少女房思琪被补习老师李国华性侵犯长达五年,身心备受摧残的思琪不得不说服自己爱上施暴者,最后精神彻底崩溃。而小说另一条隐隐的故事线则是关于许伊纹:在张太太的介绍下,许伊纹与钱一维相识相爱,于是中断学业与其结婚,然而婚后钱一维多次对许伊纹拳脚相向,甚至把伊纹殴致流产。房思琪和许伊纹一样,都经历过残虐的暴力侵害,她们都是,或者说都曾是男权暴力阴影下默默啜泣的受害者。面对危及生命和尊严的伤害,两人最初都选择隐忍而非抗争,以致生存处境每况愈下。
由是观之,许伊纹乃房思琪的显性替身,许伊纹是少女时代不曾经历过性侵、能够安然幸福地长大的房思琪。房思琪和刘怡婷多次表现出对于许伊纹的崇拜与羡慕,她们都曾在许伊纹身上幻想自己的未来。许伊纹生日时,房思琪在写给许伊纹的信中就直言梦想成为像伊纹姐姐那样的人——美丽、坚强、勇敢。作者通过设计许伊纹这样一个替身人物想要追问的是:假如房思琪没有遇到李国华,不曾经历过性侵,按照一般女性的步调安然长大了,她能否一直幸福下去?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成年后的许伊纹遇到了把她打到流产的钱一维。男权社会的阴影之下,一个美丽、坚强、勇敢又脆弱的女性,即便少女时代侥幸逃过了性暴力对于身心的蹂躏、毁灭,成年后还是可能会在婚姻的围城里遭受暴虐对待,文学理想被婚姻打死,对生活的希望被暴力折断。好在许伊纹后来离开了钱一维,遇到了温柔美好的毛毛。毛毛的存在于伊纹而言,是这张由权力和暴力罗织的社会巨网中透出来的唯一光亮,是这场社会共谋的暴力之下的一点点渺茫的希望。
三、“镜子”前的自白——日记中的“红”与“蓝”
小说中房思琪被补习老师李国华性侵的往事,是透过刘怡婷的阅读思琪的日记而慢慢展开的。刘怡婷发现思琪的日记有蓝色和红色两种字体,蓝色是小房思琪写下的日记正文,红色是长大后的房思琪对过去的日记的注解。蓝字与红字是不同时期的房思琪的内心独白,通过日记这个载体形成了一组对话结构——小房思琪和大房思琪的对话,就像照镜子,自己与自己对话。但是这场对话并不平等,大房思琪冷眼旁观、冷言讽刺、冷面诘问着已经无法争辩的小房思琪。在李国华的暴力伤害和精神控制之下痛苦不堪的房思琪,想通过日记上红字的质问,追溯这场灾难的源头。“为什么是我不会?为什么不是我不要?为什么不是你不可以?”⑩房思琪的羞恶之心和身上冲不掉的伦理,让她无法开口与他人倾诉。但是痛苦需要出口,因此她在日记上宣泄。她从小受到的顺从、忍耐的教养让她甚至无法把自己受到的伤害归罪于人,因此她永远在苛责自己,并把造成这场悲剧的根源归结在自己身上。房思琪的每一次自我表述,都是把自己和盘托出。她的自我意识,总是以别人对他的感知为背景。她的日记看来就像一场无止境的论辩,或是自我对自我的诘问,或是自我与他人的对话。社会伦理加诸其身的屈辱感,使她内心深处的惊惧顾盼和争论诘问表现得直接而明显。
房思琪这些自白式的自我表述,无不贯穿着她对他人看法、语言的紧张揣测。她的内心时刻都在关注别人对自己的评价,担心别人发现自己与李国华不伦关系。小说描写到房思琪在与李国华同乘出租车时,年轻的出租车司机看他们的眼神有如钝钝的刀。他人的批判的目光会刺痛她的羞恶之心。在房思琪与妈妈的一次交谈中,小心翼翼地试探妈妈对师生恋的态度,在听到妈妈带着嫌恶语气的回答后,思琪不再说话。这种察言观色的小心谨慎,在小说中表现为房思琪与自我及他人沟通的持续断裂,以致到最后坠入孤立无援、万劫不复的深渊。
房思琪是个早慧的精致少女,有着过人的美貌智慧和优越的家庭教养。这些条件同时也赋予了她超出同龄人的敏感和骄傲。敏感与骄傲熔铸成“一根伤人伤己的针”——自尊心。自尊心过强的人对于自己要求严苛,对自己犯的错误容忍度极低,与生俱来的敏感令她时常能感到他人投来的或是责难或是嘲讽的目光。正是在他人目光的逼视之下,房思琪的内在自我开始扭曲变形以致分裂,最后无法统一而走向毁灭。
四、结语
这部小说通过“镜子”“替身”等工具实现的对话性,呈现主人公内心的自卑与自尊、惶恐与自慰、狂笑与哀哭,全面展现这场“社会性的强暴”之下受害者自我意识的矛盾、冲突与斗争。作者想要通过对话性强调的,不是房思琪在世界上是什么,而首先是世界在房思琪心目中是什么,她在自己心目中是什么。这是我们理解房思琪的关键。作者在痛苦中写下这部与自身经历高度一致的小说,不仅仅是要控诉暴力和伪善,而是要借房思琪,来向世人展示一个性侵受害者内心世界的挣扎。当读者面对现实生活中的更多的,有着与房思琪相似经历的受害者时,我们应当关心的不是,受伤害以后的小女孩在世界上是什么——在传统社会评价上是否完整纯洁如故,而应报以最大的同理心去理解她的内心的痛苦。
注释:
①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43-344页。
②欧丽娟:《大观红楼 欧丽娟讲红楼梦(第3卷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5-68页。
③刘纪蕙:《女性的复制:男性作家笔下二元化的象征符号》,《中外文学》1989年第1期,第118页。
④⑤⑥⑦⑧⑨⑩林奕含:《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版,第8页,第62页,第19页,第20页,第220页,第11页,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