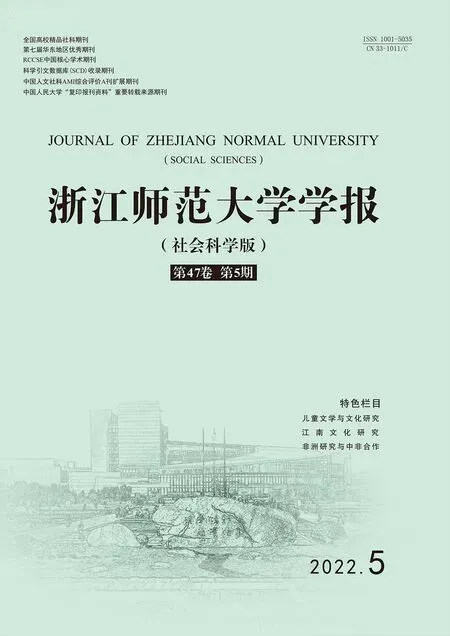清末亚洲亡国叙事中的英童想象
田 野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重庆 北碚 400715)
蒙学读本、歌谣、故事,纵观清末的儿童读物,可以发现认识“亚洲”是儿童启蒙中的重要一环。儿童的“字课”中有与“亚洲”相关的字图,“蒙学读本”“教科书”与“白话报”里有与亚洲相关的儿童故事,歌谣里也有与“亚洲”相关的意象。不论是字、歌谣还是故事,当中对亚洲的描述普遍呈现出亚洲面临灭亡的危机局面,而少年英雄拯救亚洲、拯救黄种也成为彼时文学的主题。为何清末常见亚洲亡国故事?儿童的养成、启蒙中为何常伴随着亚洲亡国事例?小说为何要想象儿童拯救亚洲、拯救黄种?这些问题的答案里不仅蕴含着与民族、国家、殖民相关的深刻意味,也与知识分子改良救亡的途径、心理相互关联。何为“英童”?英童是对知识分子理想中儿童的概括,他们是能拯救中国、亚洲的文明种。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有许多英童形象、清末时期的文学作品里也有众多亚洲亡国故事。分列来看,这两者均有不少研究成果。关于“英童”,虽未有此种提法,但却有与之含义相近的研究。部分研究从文本内部出发,以儿童视角、儿童形象为依托,分析不同时期社会文化背景、政治启蒙思潮下儿童文学的特征,指出清末救亡保种的思潮中,儿童受到重视,被当作未来之国民,儿童形象也因此多是“拯救国家以瓜分之厄”的少年英雄姿态,带有明显的成人化特征;①部分研究从外部出发,借用后殖民、民族国家等话语体系来阐释儿童文学与国家、种族、殖民的内在联系。②从清末亚洲亡国书写的研究来看,研究者大多围绕着一个国家的亡国史书写进行讨论,揭示亚洲亡国史书写与中国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互动关联。③本文在此基础上,发掘亚洲亡国叙事与儿童启蒙、儿童形象的联系,并从亚洲这个独特视角出发,讨论清末儿童文学活动中的特殊现象:亚洲亡国叙事中的英童想象。
一、清末自编教科书与英童启蒙
蒙养教育,中国古已有之,先生私塾授课,讲授四书五经。垂髫童子“未尝识字”“即授之以经”[1]“讲之既不能通,诵之乃徒强记”,[2]这种蒙养方式缺乏对儿童成长过程的考量,而传统的蒙学读物《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等亦缺乏灵活性、知识性与趣味性。随着西学东渐、知识革新,清末知识分子关注到教育启蒙为变法改良、救亡图存中的重要一环,进而号召各地开设蒙养学堂,编排出中国近代蒙学读本。1897年,南洋公学师范生陈懋治、杜嗣程、沈庆鸿自编的《蒙学课本》(三编),成为“第一本真正带有近代意味的自编教科书”。[3]1898年,江苏无锡三等公学堂吴眺、丁书宝、俞复、杜嗣程等自编《蒙学读本全书》(七编),此书1902年经由文明书局出版,成为风靡一时的儿童启蒙读物。此外还有上海三等公堂的《字义教科书》(1898),上海澄衷学堂编录的《字课图说》(1901)等,这些蒙学课本作为新式教科书的代表,开启了识字—文法—篇章的近代儿童培养模式。
“字课”是近代蒙学的第一阶段,所用教科书以字为主,辅之以图,图附说明,再以“反切法”注音,浅显易懂。字的范围包含天气、地理、国家、植物、动物、器物等多个方面。字的释义具有普及知识、启蒙观念和认识世界的作用。上海澄衷学堂的《字课图说》选通行浅近字3 224个,以独特的编辑体例成为清末识字书的代表。而后的《最新官话识字教科书》《国民字课图说》都是以它的体例为蓝本编撰而成的。《字课图说》中有不少字与“亚洲”相关,帮助儿童形成了关于“亚洲”的最初认识,是最早的亚洲舆地启蒙。
何为“亚”,[4]31凡次于最者曰亚,今洲名。这是《字课图说》中对“亚”的主要释意,“亚洲”是“亚”的现代含义,该书继而说明了亚洲词源、地理、国家与内外关系。亚细亚本是土耳其地名,后欧人将其地域以东皆称为亚细亚,并以名洲。亚细亚在五洲中为最大,三面环海,西边接欧罗巴洲,以乌拉岭、乌拉河和高加索山为界。《字课图说》将亚洲内部区域国家分为三类:“为国者”有五:大清、日本、高丽、暹罗、波斯;“自主半自主者”有四:安南、爱乌罕、俾路之、阿拉伯;印度、缅甸、西比利阿、中亚细亚诸回部皆为“属国”,俄属之布哈尔尚存虚名。其对亚洲国家的分类初具现代意味,即主权国家、半殖民地与殖民地。该书进而指出,亚洲整体处于危局,俄“雄于北”,英“竞于南”,法“据安南”,德国、意大利“觊觎其侧”,[4]31岌岌可危,亚洲国家共同面临来自欧洲的亡国威胁。
亚洲与欧洲多国具有从属关系,内部也几经更替。《字课图说》以字释义了每个亚洲国家的历史处境与现代境遇,一方面建立起“中国”与“亚洲”的关系网络,另一方面结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国家观念(包含国家属性、国家关系、亚洲秩序)。它以“臣属”和“入贡”两种关系将亚洲旧国分为“藩属国”与“朝贡国”。“藩属国”有韩、缅、越。韩“世臣于我”;[4]33“缅”亦“臣属于我”;安南国名为唐朝所设都护府发展而来,历世“职贡”;“朝贡国”有暹罗和阿富汗。暹罗“常入贡于我朝”;[4]34“爱”即阿富汗,亦在“朝贡之列”。[4]35而如今,朝“称自主”,但“大权尽失”“民气不振”,亦无“自全之术也”。[4]33缅甸被英人灭;越南被法人占领;暹罗差点被英国侵占,但因暹罗人“励精图治”而免于亡国;[4]34阿富汗在光绪四年抗英失败,归为受英国保护的国家。这里“保护国”和“朝贡国”关系等同,是否为属国以内政外交自主与否进行判定,中国朝贡观念与西方殖民观念在此对接。旧国新景中,中国知识分子情绪复杂,不仅有昔日荣光作为国民自信的来源,也蕴含着深刻的连带性亡国体验。已亡国的人民成为奴隶,未亡国家也处于危急时刻。回部大国波斯,物产丰富,可近年来北边被俄国觊觎,东边被英国窥视,“岌岌不支矣”。[4]35
祝我国,巩金汤,长欧美,雄东洋。陆军海军炽而昌。全球翻映龙旗光。帝国主义新膨胀,勿谓老大徒悲伤。印度灭,波兰亡,请看我帝国,睡狮奋吼剧烈场![5]
“印度灭”“波兰亡”,但我国会“雄东洋”“长欧美”,蒙学课文借他国危亡处境反衬出中国的“国荣”。南洋公堂的《蒙学读本》④中,有一课为《国耻说》,“琉球、越南我属国也,而为所灭”,[6]可见,亚洲旧属国也成为我国国耻的一部分。“国荣”“国耻”的情绪鼓动中隐藏着知识分子对童子的观念启蒙,同洲国家亦变成引导童子体悟的最好案例。另一篇课文《记智度事》,讲述了印度的亡国惨象。英人灭印度后,印度“政虐税重”,此词不便童子理解,于是课文将其拓展为“吃盐”的故事,以童子易于理解的方式传递灭国感知。灭国意味着民众受苦,受苦等同于不能吃盐,“淡食终身”。当然,亡国国家也有反抗的人民,有一位印度壮士者智度,就背着英兵偷偷取盐,不过却不幸被英军发现,关入牢狱。但他即便“身受百刑”“体无完肤”也“坚不承认”,[7]直到其妹纵火焚狱,智度才得以逃脱。这种启蒙方式直观而又形象,循循善诱,适宜童子,既有亡国处境的负向书写,也有抵抗强权的正面启发。
“亡”和“未亡”成为亚洲国家的两种状态,中国以此为“鉴”,规约童子思想、启迪情感。免于被灭的国家,大抵“工商并行”,如日本;“励精图治”,如暹罗;地域特殊如土耳其,地跨两洲,“赖欧洲诸国保持”。[4]36英童们要“鉴”日本,也要“鉴”印度。印度是佛教之国,开化得早,如今却被英人蚕食。印度亡,所以佛教不能“鉴”。《蒙学课本》中有一文《浮屠论》,讽喻佛教的生死轮回观,佛教在丧事时诵经使死者得以入天堂,可“佛教未入中国之前,人固有死而复生者,何故竟无一人见彼所谓十王者耶?其不足信明矣”,且“不知死者形既朽灭,魂亦飘散,试问剉烧舂磨,将施于何处耶?”[8]课本里对待耶稣教的态度就与对佛教不同,“土耳其”在亚洲属地,“有西里阿布,为耶稣故里,西人称圣地,盖诸教所自起也”,[4]36耶稣故里在亚洲土耳其也成为一种亚洲荣光。
清末的蒙学读本将亚洲亡国图景作为认识国家、国际关系,养成童子爱国心与国土意识的蒙学资源,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这一倾向在1912年以后的教科书中就不复存在。地理连带出对国家、文明、文化、种族的启蒙与思考,“亡国”这一核心叙事呈现出多层面的亚洲构型,成为“英童”成长中的“舆地启蒙”。
二、颂俚歌以铸国魂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然而,清末诗界却一派“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于是,梁启超等知识分子提出诗界革命,以再兴诗歌,重建国魂。歌谣之于儿童,“易于上口”[1]而又“感人性情”,[9]适于诵读,也益于教化,利于童子精神养成。知识分子们纷纷“搜欧亚”以“造新声”,儿童歌谣一时间蔚然大观,而“印度”“土耳其”“黄种”等亚洲意象频频出现在诗歌中。梁启超、黄遵宪等人作《爱国歌》《幼稚园上学歌》《小学校学生相和歌》以启蒙童子,诗中不乏“最大洲”“最大国”等亚洲象征;张之洞、曾志齐、沈心工、李叔同致力于创作学堂乐歌鼓舞学风,其中也有“日本强”“越与缅”“权利全被他人攘”等亚洲表述;书局竞相出版儿童唱歌集:上海越社录《最新妇孺唱歌书》(1904),作新社编《教育必用学生歌》(1904)等,所录歌谣中有诸多作品将“印度灭”“安南亡”作为警醒孩童的事例,以亡国感叹来激发儿童的爱国热情。
国魂是国家存亡之根本,“国失魂乎,非狂则亡”,[10]亚洲国家因“无魂”而亡,才被“戮之”“斩之”。[11]所以中国为避免亡国,“今日所最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12]诗歌以其独特的体例“时时熏蒸,时时刺激”,使童子“发生爱国心”[9]铸得国魂。而什么是国魂?中国魂与“亚洲亡国”有何联系?如何塑造国魂?是需要探讨的问题。
梁启超最早谈论国魂。他于1899年在《清议报》发表《中国魂安在乎》一文,以日本“大和魂”具有武士精神,鼓舞中国国魂。梁启超认为“国魂”是“兵魂”,由“爱国心”与“自爱心”引起。[12]日本有“大和魂”,那吾中国魂是何?知识分子纷纷加入制造国魂的行列,《浙江潮》的《国魂篇》从国魂的发生、定义、陶铸国魂之法等方面,全面讨论了国魂问题。国魂之根本在“统一力”与“爱国心”,[11]铸造国魂的方法为“察世界之大事”“察世界今日之后关于中国者”“察中国今日内部之大势”;[13]观欧美,可将国魂分为“冒险魂”“宗教魂”“武士魂”“平民魂”,除了“宗教魂”,其他“魂”中国古已有之。这四类国魂分法也出现在其他文章里,但在中国是否具备这一点尚有争议,《国民日日报》有一社说《中国魂》遵循此四类分法,并将“冒险魂”等同于“贸易魂”,但却认为此为其他国家之特色。中国均没有。[14]69《江苏》刊载的《国民新灵魂》将国魂扩展为“山海魂”“军人魂”“游侠魂”“社会魂”“魔鬼魂”。国魂也被看作“国民精神”,[15]或被作为“民族主义”,[14]70它也的确很快被国民性、民族精神所代替。再至“五四”时期,“国魂”与“国粹”相连,在“国粹”的含义里几经周折。不过,如同清末时期的多元讨论一样,那时的“国魂”与后来所说的“国魂”不同,它含混又丰富,起于对周边国家的兴亡镜鉴。梁启超在《新民说》中言“专务青年教育,唤起国魂”,但对于蒙童而言,与其说“唤醒国魂”,不如说是“铸造国魂”。
1.多媒体应用到高职韩国语教学是新时代的要求。当今是高度信息化的时代,高职韩国语师生只有不断学习,扩大知识面,更新知识观念,才能够紧紧跟上时代的步伐,而传统的授课方式已经很难满足这些要求。为了使学生更快速、全面地接受前沿的韩国语知识,需要大胆突破原有的课堂教学模式,寻求更优化的教学方式,多媒体教学能有效满足这种需求。
融铸国魂有两种主要方式:一为从历史中追寻国魂;二为鉴周边以融合国魂。国魂既是“民族之魂”,也是“国民之魂”,民族源于文化,国民起于国家。先说“民族之魂”。中国的国魂在哪?“吾登昆仑之山巅溯黄河之流域,求吾神圣祖宗皇帝之遗烈”,[16]“昆仑山”“河流”是儿童诗歌中的常见意象,它们作为文明和文化的发源地,是中国种族、民族的源头。知识分子们以此建立起“黄帝”的始祖神话,将童子们称为“黄帝贵胄”“轩辕子孙”,常有这样的诗句:
黄帝之胄神明种。风虎云龙,万国来同,天之骄子吾纵横。[17]
芸芸哉!吾种族。黄帝之胄尽神明,寖昌炽遍大陆。[18]
狮兮狮兮,尔乃上帝至爱首出之骄子,供汝东海之上,昆仑之下……数千年历史有文化有武烈之荣光。[19]
黄帝神话融合了中国血统论与西方种族优劣观,并以类似于“嫡长子继承制”的观念表述中国与亚洲。黄帝不仅是中国人的始祖,也是黄种人的祖先。中国人是黄帝血统中最为正统的一脉,作为黄帝的嫡长子,理应承担起抵御外侮的责任,在“白种日兴黄种危”[20]的境遇里,代表亚洲在“天演界上竞生存”。[21]童子们是黄帝后裔、黄种的正统血脉,因此“天赋良能”,天演论和命定论的观念在此也相互交织。在古代中国的制度里,伴随“嫡长子继承制”的是“分封制”。皇帝的嫡子继承了中心区域的政权与土地,并将周边地域分与其他“庶子”,以此逻辑,周边国家是中国“父亲”的“庶子”。面临亡国处境时,“安南觅来哭阿爸”,[22]儿童诗歌中形象的比喻、热烈的语言鼓舞着童子们“毋自弃”“尽天职”,拯救黄种。
“民族之魂”也取自亚洲周边国家。清末有关“国魂”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冒险魂”“武士魂”和“宗教魂”,且指向明显,“冒险魂”以西方为参照,“武士魂”以日本为代表,“宗教魂”与印度对应。一派知识分子溯源传统,以证中国曾有“冒险魂”和“武士魂”,另一派主张学习并发扬二者。“宗教魂”这一方面并无争议,以往未有,之后也不提倡,“佛经耶约能救世?宗教神权今半废。”[23]吸取周边文化融于中心,是中国民族文化一直以来的发展模式,从而形成“文化之族名”。中国人一直以来认同的也是“由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24]
“国民之魂”从国家起。清末并无现代意义上的实体国家,自先秦以来,王朝历代更迭,一直承袭着一种文化(天下)秩序,只要“王朝代表了天下的秩序”,便具有“正统性”,[25]大清和其他朝代并无差别。“国民之魂”一方面从历史中寻找认同传统的文化秩序,另一方面萌生了亚洲“大国民”的意识,李叔同的《祖国歌》是学堂乐歌的代表,广为传唱。“国是世界最古国,民是亚洲大国民。”[26]不论是从“历史”还是“周边”,“国民之魂”都来源于抽象层面,并非实体的国家或政权。
“醒”“警”“爱国”“合群”“出军”是清末儿童诗歌的主题。从历史中寻找并唤醒国魂,从周边国家“警”“鉴”国魂,知识分子以此养成儿童的“爱国心”“冒险精神”与“合群意识”。此举使清末儿童诗歌不仅有统一之精神,也容纳了历史、民族的风土与特性。
三、讲兴亡以育国民
故事是儿童喜闻乐见的又一形式,启蒙读物中常见亚洲亡国故事,在清末影响较大的几种白话报刊、儿童刊物中均可察见,《绍兴白话报》连载了《亡国话》,讲述安南亡国的故事;《童子世界》连载了《印度灭亡史》;《杭州白话报》《京话报》连载独头山人的《波兰国的故事》;《启蒙画报》《蒙学报》等刊物也辅以插图讲述亚洲国家的风俗及亡国故事。在亡国故事里,“波兰”与“印度”是常提到的国家。“印度”与“中国”同为亚洲文明古国;“波兰”在“欧洲”,等同于“中国”在“亚洲”。“印度”“波兰”与中国情状相仿,面积、文明、历史地位也与中国相当,比之朝越缅等国,更具借鉴意义。
亡国大抵因为民不知有国,或国之专政不取民意。亡国故事里,印度是前者,波兰为后者。《童子世界》所载《印度灭亡史》,讲述了印度灭亡的故事。印度以前也是一个大的文明国,现在是英国人的奴隶。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国人没有自立的心”“指望外国人保护他帮助他”,他们“全不想想国是谁的国,为什么要把那主权双手捧着送与那不同种族的人呢?”[27]故事以与孩童对话的方式展开,娓娓讲述灭国因由,以激起童子的国家意识、承担国家责任和义务的意识,养成他们自主自立的国民心态。在关注本国事务外,文本中也常提到关注同洲国家的处境形势。《印度灭亡史》的开篇即有此意:“我们是中国的童子,考究中国的事情,是我们应该的,但是除了中国之外,地球上的国是多得很,即如立国在亚西亚洲的,也有几国。”[28]言语之中意在引导童子成为亚洲大国民。
波兰国的民众与印度国不同,他们有群体意识,懂联合抗敌,波兰的百姓“你联我,我联你”,“再拿出无数金银宝物,结识那一班有力量的人”,众筹救国。可是波兰的国王却下旨不许他们商量国家的事情,若再“聚集拢来”,“便要定罪”。[29]波兰亡国的事迹里反映出中央集权和专制政体是灭国的原因,知识分子以此启发童子们应有参与国家事务的决心。亡国故事传达了国家的关键要素:主权、人民和土地三样,被外国占夺去了就算是亡国。[30]
讲故事的方式往往是贴合儿童心理的,讲故事的人将国家的危难具化为个人感受,启蒙儿童,使他们认识到自身与国家之间的紧密关系。波兰国亡国故事中,有一个抓小孩的情节。波兰国亡了,波兰的小孩子就被送到了西伯利亚,那里不仅寒冷,而且“连饭也没得吃,无非靠着那粗而且冷的馒头”充饥度日,[29]有不少小孩都饿死在那里了,来不及吃的食物就放在尸体旁边。触目惊心的故事启发儿童要承担起国民的责任,行使国民的权利,参与国家事务,保护本国利益。
周边国家为中国知识分子教育儿童提供了一种行为规范,他们以此规训童子的行为。《启蒙画报》就擅长描述亡国民的行为以反向启蒙童子。印度人风俗最多,率先成为众矢之的。印度人吃饭讲究“吉凶”,在参加英皇的加冕典礼时,他们只吃自己带去的食物,不吃别人的东西。不仅如此,只要有人影落在饭中,他们就不吃这碗饭。印度人“严守这个规矩,可谓荒谬极了,如何再能有为,所以把国也亡了”。[31]印度还有拜牛的风俗,富贵人家要拜一种脊骨上长一小峰的牛,故事里顺便连带抨击中国“拜驼拜狐”的风俗,并且称“印度乃一大国,今竟不振,都为此等人所误”,警示“中国人赶紧醒悟了罢,要笑话印度人,先想想自己”。[32]亡国故事里,风俗行为被等同于亡国行为。除此之外,《启蒙画报》还抨击了缅甸、安南的虚文,选取官员“专尚文词”,举国之人,“皆喜吟咏”,而缅甸的“文人陋习”[33]更甚于安南。知识分子在对安南的借鉴中,倡议改中国的旧八股积习。不仅如此,参与国事也成为评价英童的标准,十三四岁的童子在戏台上宣讲中国贫弱、抵制外货、不做亡国奴,得到的评价即“这个小孩子倒这样热心国事”。[34]
四、《鱼丽水冒险记》与《瓜分惨祸预言记》
《鱼丽水冒险记》(吴忆琴)连载于《童子世界》1903年第24至32期;《瓜分惨祸预言记》托名“日本女士中江笃济”,实为南社文人郑权作,1903年于广智书局出版。两本同年创作的小说,一本将成人愿望诉诸儿童故事,另一本以儿童视角写亡国灭种危机,双向展现了“儿童政治小说”中的两大主题:“去冒险吧!”“去救国吧!”而创作政治性的儿童文学也成为知识分子缓解救亡焦虑的途径。
《鱼丽水冒险记》开篇即言地理之重要,“大凡要晓得古今的事迹,一定要晓得古今的历史”,而要知晓历史,必须要“晓得些地理”,并且说“这部小说,没有地理,是万万不能讲的”。[35]引子部分以五大洲的地理概述开篇,内容方面虽非讲述亚细亚洲的故事,却以文明古国为连带,存在着“欧洲之希腊”与“亚洲之中国”的潜在定位。小说先言巴比伦国王刘毅达、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等知名英雄,绘声绘色地叙述他们以一己之力开创一个帝国的拓殖故事。历史故事是小说展开的前序,主人公并非这些知名历史人物,而是一非知名英雄“鱼丽水”,小说也正是讲鱼丽水的故事。察主要情节:一为“木马计”,一为“海洋冒险”,可知“鱼丽水”实际上就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奥德修斯”。小说虚拟一“鱼丽水”,将其塑造为特洛伊战争中“木马计”的献策者、海洋冒险的主导人,可见清末知识分子对无名英雄的呼唤。小说改塑了“奥德修斯”,去姓名、去背景、去神话色彩,将其塑造为平民、普通人,其中寄寓着清末精英知识分子对后辈的期待,并非渴求“英童”是一二能力气运出众者,而是渴望“英童”皆为无名英雄。一方面,有名之英雄自无名之英雄出;另一方面,一二人之力不足以救国,国事也非“一二人之事”,而是“千万人之事”。[36]《鱼丽水冒险记》以儿童化的名字、儿童化的叙事,传达成人诉求,鼓舞英童“坚忍耐苦、百折不挠”,去冒险,即便“辛苦艰难”,也要在“山穷水尽的地位开辟一条新路起来”。[37]
“方今中国民人,尚在醉梦之中。瓜分之事,已迫近矣。中国亡,日本亦必不保。吾不忍见全洲黄种尽为白人奴隶。”[38]455这是小说《瓜分惨祸预言记》的开篇,故事伊始便设立在亡国灭种、保国保亚洲黄种的语境之中,小说出版的1903年也正是中日“同文同种联合,共保亚洲黄种”言辞高昂的时刻。主人公黄勃为一十四岁的儿童,他幼时就富有思考能力和批判意识,“专好摘出书中古人言语,恣意批驳”。[38]448与《鱼丽水冒险记》中肯定鱼丽水的“普通”身份不同,《瓜分惨祸预言记》中的儿童天资聪颖,是成人理想的反映,即希望儿童均能天生聪慧、无教自通,自发明白事理、自发救国。童子军也是作品中反侵略的中坚队伍。小说介绍了这支自发组成的童子军,这些孩童年纪不一,组成了一个120人的童子军,其中,84人在13岁以上,36个是小孩子。小说表现出孩童自发的救国意识和牺牲精神。王爱中是爱国学生群体里的一分子,在听闻亡国消息后,持剪子自杀,“免待那洋人来辱我,我是不愿作亡国的人”,儿童人设尽显成人心理。小说增加了家长劝说童子的情节,王爱中的旧式官僚派父亲王本心阻拦女儿并劝说:“中国的人多着呢,难道只是我们的事?”[38]473代际冲突的情节设置,为儿童行为选择指明了方向。《瓜分惨祸预言记》是“预言记”,它的核心在“预言”,预言是故事发生的契机、谋篇布局的关键。“预言”的具体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预言者讲话的腔调”。[39]腔调是态度、观念,牵连着我们所关切的要旨。小说源于《甲辰年瓜分惨祸预言》这一虚拟的预言文本,当中的核心话语:“漫著预言篇,书成涕泫然;民心如有意,人事可回天。”[38]454言辞模糊而又玄妙,悲凉凄切中又渗透着希望的微光。故事的结局非喜非悲,汉种排满成功,抗俄却失败了,居于一隅建立起“兴华邦”独立国,为汉种仅存一片土地延续黄帝的血脉。小说结尾仍然保留着预言的腔调,蕴藏着对未来中国和国民的期望。
儿童在知识分子的期待里,被塑造和想象为英童。在英童“救国”的故事里,“拓殖”与“反殖”相互交织,“文明”与“野蛮”也边界模糊。小说常常出现灭蛮邦是文明国的使命这类救亡情节。《鱼丽水冒险记》以希腊为中心进行海外拓殖,海洋冒险的情节蕴含着哥伦布开拓新大陆的精神。鱼丽水海外漂流时,遇到荒岛上的民众,往往将他们捉到船上,粗暴对待。《瓜分惨祸预言记》中有两处烧杀抢掠的情节,一次是外兵侵华,一次是满族兵败于华,他们一边谴责殖民者的酷刑,另一面又以胜利者的姿态进行着相同的行径。小说最后建立的“兴华邦”,收回了曾经土地的治理之权,“作为殖民地”,并且派遣郑成勋等人“出洋垦辟新地”。[38]553小说徘徊于“拓殖”与“反殖”之间,想象英童,是这一时期的弊病。此时的知识分子,并未认识到“尚武”“冒险”背后的侵略形态,而是将其作为救亡教育的组成部分。
“儿童群起而救国”是两本小说的共同理念,一本塑造榜样规训儿童,一本直观呈现英童形象。刊载《鱼丽水冒险记》的《童子世界》由上海爱国学社附设的蒙学班自治组织童子会主编。刊物所属的“爱国学社”,办于1902年,章炳麟、蔡元培、吴稚晖为主要负责人,其主旨为反帝和民主革命,是宣扬爱国思想的自治团体,后因《苏报》案解散。《童子世界》作为爱国学社的刊物,不免与爱国学社具有同样的理想。《瓜分惨祸预言记》虽与爱国学社无关,但是内容却与童子军相连,是“爱国学社”童子军理想的延续,也是“尚武精神”在小说中的畅想与实践。儿童如何救国这一主题在清末以“牺牲”为主,《瓜分惨祸预言记》里童子的牺牲触目惊心,120人的少年军仅剩几人,小说还附录名单作为荣誉的象征。如此匪夷所思的行为却被大力颂扬,可见彼时儿童文学的畸形发展。知识分子迫切地将国家的矛盾与危难一股脑地加之于童子。这种倾向在日俄战争前最为明显,《浙江潮》连载的小说《少年军》中,以美国学生在战争中英勇对敌为蓝本,奉劝同胞以此短篇为脚本,当“战云不久即布于亚细亚大陆”时,建立“支那少年军”,“以一十四龄少年,为祖国出死力”。[40]不过,在中国识破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后,这一倾向便不复存在。在1920年《时报》的一则故事《儿童救国》中,对儿童如何救国的思考就与清末完全不同,故事虽然设置了儿童集体请命保卫城中人的救亡情节,但是却以主将诺言的兑现结束,既不会伤害儿童的生命,又给儿童们提供了甜美的樱桃,救国故事里尽是温情的色彩。从日俄战争到抗日战争,从俄占东三省到日据东三省,及至1931年,与清末组建童子军、鼓励牺牲的做法不同,此时的知识分子对小学教育与救国有了规范性的指导。儿童文学作品《小学生的救国责任》中可以看出,这时候的小学生清晰地认识到,救国的要素是求学,革命的基础在高深的学问,对于日本的侵略行为,小学生现在能做的不是气而是记,铭记国耻日后图强。
总的来说,亚洲亡国图景为塑造和想象“英童”提供了反向参照、叙事资源。塑造“英童”寄寓了清末知识分子的富强心愿,“深知东西诸大国之富强由于兴学,而小学校为尤重”;想象“英童”反映了清末知识分子的心理境遇,缓解了戊戌变法失败带来的救亡焦虑。而富强救亡中不免过多含有政治教化的色彩,以儿童视角抒发成人理想。清末借鉴日本,把儿童文学的叙事政治化、殖民化的倾向并不适宜孩童的成长。这种倾向在近代教育的发展中渐渐被改正,民国以后的识字课本里,亚洲和亚洲国家不再具有政治含义,教科书也不会蕴含明显的煽动意味,而是转向花鸟虫鱼的自然界,兔子与熊、大象与蚂蚁的动物界,开始真正意味上的英童养成。
结 语
“亚洲”在清末具有包含种族、文化、地理、文明在内的多重含义,它作为一个综合性的话语体系,不同于以往中—西对立的单一视点,形成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彼此参照的多元视角。而比起西方对中国的冲击,邻近国家日本的崛起,同为文明古国印度的沦亡,曾为中华属国的朝鲜、越南、缅甸相继被侵吞,才引发中华大国真正的危机意识。在亚洲整体式微的亡国图景中,精英知识分子们率先走上启蒙救亡之路,寻找亚洲积弊的因由,以此内省改良、变革国家。儿童因其年龄幼小、知识结构质朴,易于成为新知识的载体、权力锻造的对象,因此,启蒙英童寄托着知识分子们的强国梦,想象英童群起而救国也成为缓解精英们救亡焦虑的途径。也正如此,亚洲亡国故事在英童的养成与想象中意味深刻,成为亚洲视角中文学研究的新问题。
注释:
①参见胡从经:《晚清儿童文学钩沉》,少年儿童出版社,1982;孙建国:《清末民初: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起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5期;谈凤霞:《启蒙思想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之发生》,《南京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王黎君:《儿童的发现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②参见Jon L. Saari, Legacies of Childhood: Growing Up Chinese in a Time of Crisis, 1890—1920, Ha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Ann Anagnost, “Children and National Transcedence in China”, Construcring Chine: The Interaction of Culture and Economics,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7.[加]诺德曼:《隐藏的成人:定义儿童文学》,徐文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吴其南:《后殖民视域中的中国儿童文学》,《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③参见俞旦初《中国近代爱国主义的“亡国史鉴”初考》,《世界历史》1984年第1期;陆勇:《“亡国灭种”的想象与近代民族国家话语霸权的形成》,《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卡尔·瑞贝卡:《世界大舞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的民族主义》,高瑾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李帆:《浅析清末民初历史教科书中的“国耻”与“亡国”话语》,《人文杂志》2017年第2期。
④目前所能找到的版本为光绪二十七年(1901)的新定版,并非陈懋治、杜嗣程、沈庆鸿所编初版,这一点夏晓虹在《〈蒙学课本〉中的旧学新知》,《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一文中考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