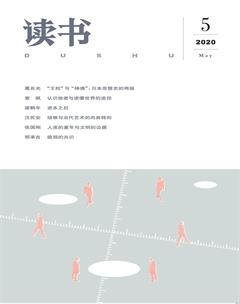“亡国”与“亡天下”的金石学
缪吾
一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时尚,学术和衣服一样,也有自己的时尚与潮流。时尚不仅是学术史中的观点与著述,更是鲜活的学术活动与鼓荡在学人心头的文化热切。在清代学术史的叙述中,方法的开拓、材料的更新、成就的高低、观念的转移常常是重要的说明对象,而薛龙春先生的新书《古欢》,虽以乾嘉知识界为对象,其研究重心却没有放在学术成绩的描述上,而是更看重乾嘉金石圈的时尚景观及其背后的文化生态。通过大量一手信札文献的探赜索隐,《古欢》复原了由不同阶层构成的金石共同体—学者、官员、幕僚、商人、掮客、古董贩子,这些人一起推动了金石的“时尚”热潮。其中,以发现、著录金石文献闻名于世的黄易,则是最为出彩的弄潮儿。
黄易(一七四四至一八0二年),号小松,是书、画、印俱佳的“西泠八家”之一,他是武梁祠画像石刻的发现者,被称作乾嘉访碑第一人,是时人心中的“碑痴”。有趣的是,这位“中心人物”在金石研究上并没有很大的成就,也不是翁方纲、毕沅那样位高权重的学术领袖,然而正是他凝聚起乾嘉时期的金石共同体,通过自己的运作让金石学不断登上“时尚”舞台。想要理解这样的反差,便要充分了解,金石对于乾嘉士人而言意味着什么。
在《古欢》描述的乾嘉金石世界中,金石不仅可以证经补史、裨益书学,作为可供赏玩的艺术珍品,金石也是欢愉的源泉、时尚之趋鹜,甚至是获取功利的方式。翁方纲在写给黄易的一封信中提到“彼此各有新得,时时通问,亦天下第一快事也”,他们把金石拓片的交流、分享与收藏视为“天下第一快事”。在乾嘉崇古之风的背景下,这种以金石为欢愉的心态,被他们称为“古欢”。“金石古欢,世有几人,能不神依左右耶?”古欢如同今日的“小确幸”一般,给收藏者带来极富宽慰的幸福感。“所谓‘古欢,是说在金石拓片的摩挲与研玩中,他们获得无限的乐趣,而正是这种乐趣,将黄易与乾嘉金石學以及那个伟大的时代紧紧联系在一起。”(《古欢》,2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这种欢愉带有一定的席卷效应,在整个乾嘉知识圈蔓延开来,进而形成一种共同的时尚,如果一位文人对金石文字没有辨识与利用能力,仿佛没有掌握进入学界的密码一样。在《古欢》中,毕沅、翁方纲、朱筠、王昶、钱大昕、桂馥、王念孙、孙星衍、阮元等都是“时尚”中人,其中不乏乾嘉时的一流学者。至于黄易主持的武梁祠重建,更像极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公益”派对。官员学者纷纷为重建武梁祠“众筹”,黄易不仅组织了诗歌唱和及参观旅行,还“求当代巨公撰碑垂后,仿汉碑例曰‘某人钱万‘某人钱千,详书碑阴,以纪盛事”,只要捐了银子,他们的名字就能永远留在这场“时尚盛宴”的记录中。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时尚?为什么黄易能成为时尚风暴的暴风眼?薛龙春认为,乾嘉时的金石收藏尚未形成完善的市场供给,需要通过懂行的“中间人”来获得,能够胜任这一角色的,未必需要高官显位,而要掌握更为丰富的社会资源、与不同的阶层进行紧密合作。《古欢》刻画出黄易长袖善舞的形象—他官位不高,却拥有极为复杂的身份:“幕僚、官员、河道专家、学者、收藏家、艺术家、出版家,他甚至还是采购者与销售员。”(234页)这样独一无二的复杂角色,让他拥有了拓本和人脉的双重资本,从而获得了最多、最新的金石收藏。这成为他与翁方纲、阮元等名流结交的敲门砖,货源丰富的黄易迅速成为圈中的香饽饽,谁都想通过他丰富自己的收藏;作为回报,这些官吏也会积极为黄易提供帮助—人力、食宿、工具、信息,对他们来说,这些不过是顺水推舟的“小事”而已。
我们看到,整个乾嘉金石圈结成了一个利益交织的文化共同体,支撑起金石考据与文人“古欢”的,恰恰是各种类型的“交易”—金钱的、实物的、人情的、权力的,这让金石“时尚”萦绕着功利的气息。而黄易作为一个资本雄厚的弄潮儿,更在金石交易的世界中成为最大赢家,获得了名声、成就、实惠与莫大的欢愉。那么,最终又是谁来为这种“欢乐”买单呢?
二
《古欢》让我们看到一个金石“发烧友”,通过自己的长袖善舞,在他维系的共同体中享受着金石带来的欢愉与认同。而当我们将考察视域由乾嘉上溯到明末清初,则会看到另一位访碑人怀着完全不同的心绪,和黄易站在了同一块碑刻面前,那就是顾炎武(一六一三至一六八二年)。
顾炎武的一生,是救世变夷、治学读书、以游为隐的一生。他走遍大江南北,在名山巨镇、寺庙伽蓝之间踏访寻碑,留下了《金石文字记》《求古录》《石经考》等重要著作。亭林访求碑刻,对其进行文字考释,详尽著录碑刻的时代、内容、书者姓名,以期证经补史。他的工作为乾嘉学人导夫先路,被誉为清代金石学的开山大师。在金石研究上,乾嘉学者延续着亭林开启的范式,二者之间并无本质区别;但在精神气质上,以黄易为代表的“古欢”一代,与亭林却有着根本不同—在顾炎武的访碑之旅中,我们看到的是亡国遗民孤独而凝重的身影,唯见沉痛,未曾欢愉。
“深情好古,意在阐幽,自有不能已者。”顾炎武无疑是“好古”的,但他的“好古”并非追求乐趣,而是一种阐发幽情孤诣的方式。在碑文的著录与考证背后,时或流露出深沉的文化思考。江山易代的彻骨之痛,让亭林格外关注碑文背后的历史细节。在真定府龙兴寺访《龙藏寺碑》时,他发现碑石虽为隋开皇六年所立,但立碑人的署名还是“齐开府长兼行参军九门张公礼撰”,齐亡入周,周亡入隋,张公礼虽经两度改朝换代,但犹以前代“齐官”自居,这不正是“君子不降其志”吗?这份孤守深深触动了同为遗民的顾炎武:“兴亡迭代,为之臣者,虽不获一节以终,而心之所主见于称名之际者,固较然不易如此。然则今人之不及古者,又岂独书法之陋、文字之讹而已哉?”这些鼎革之际耿耿不忘的小人物,在金石所载的历史缝隙里,与亭林形成了幽微痛切的精神相会。
抒发遗民情怀的同时,亭林也在不断反思明亡的原因。在他看来,这与士人的高谈心性、空疏无学密不可分。在山东邹平,他访得《中书侍郎景范碑》,传主是后周的景范,却被《山东通志》等书误认为晋人景延广,甚至景氏后人都不知先祖为谁。亭林不禁慨叹:“近代士人之不学,以本邑之人书本邑之事而犹不可信,以明白易见之碑而不之视,以子孙而不识其先人。推之天下郡邑之志,如此者多矣!”士人空疏不仅导致亡国,更会遗忘历史,如果连祖先都能遗忘的话,千百年后,又有谁能记得自己的故国?又有谁能坚守基于种姓的华夷之辨呢?
面对令人窒息的时代,亭林孤独地坚守着,这份孤独与他只身访碑的形象默契相映。在乾嘉的金石“时尚”中,黄易的拓碑活动有众多地方官的支持,作为“访碑第一人”的他有大量帮手,即便不去实地亲访,也能通过绘画来“建构”他访碑者的形象。而《金石文字记》中的亭林却似乎一直在踽踽独行,访碑对他来说并非易事,他笔下常有“时值雪后,空山无人,未及遍访”的寂寥。李光地在《顾宁人小传》中描述亭林“骑驴走天下,所至荒山颓阻,有古碑版遗迹,必披榛菅、拭斑藓读之,手录其要以归”,更有一种荒野中孤独旅者的气质。在亭林身边,没有多少地方官员可以伸出援手,“登危峰、探窈壑、扪落石、履荒榛、伐颓垣、畚朽壤”,多半只能依靠自己;或有“一二先达之士”一同访碑,但也大抵是“栖栖世事迫,草草朋侪聚,相与读残碑,含愁吊今古”的相对凄凉。
其实,亭林也未必得不到官员的襄助,作为“昆山三徐”的舅氏,他一直很忌讳这份显赫背景。即便爱好金石,他也不希望看到学术、收藏、功利与权势的结合,从而成为民生的重负。在金石学远未成为“时尚”的时候,他便不乏洞见地做出了批评:
今之君子,有世代之不知、六书之不辨,而旁搜古人之迹,叠而束之,以饲蠹鼠者。使郡邑有司烦于应命,而工墨之费计无所出,不得不取诸民,其为害已不细矣。或碑在国门之外,去邑数十武,而隶卒一出,村之蔬米、舍之鸡豚,不足以供其饱,而父老子弟相率蹙,以有碑为苦。又或在深山穷谷,而政令之无时,暑雨寒冰,奔驰僵仆,则工人隶卒亦无不以有碑为苦者,而民又不待言。于是乘时之隙,掊而毁之,以除其祸。(《西安府儒学碑目序》)
官府旁搜古迹,方便应酬,以致西安碑林的百姓皆以“有碑为苦”,在蹙愤怒之余,干脆趁机毁碑!唐昭陵的墓碑在崇祯十一年犹有二十余通,至康熙二年,亭林在二十五年后亲至其地,却只见到《卫景武公》一碑,其余不是毁坏不存,就是已被磨去字迹。于碑,惋惜古物之不存;于民,感念黎庶之多艰。亭林不禁慨叹:“民亦何仇于石?所以然者,岂非今之浮慕古文之君子阶之祸哉!……有识之君子,慎无以好古之虚名,至于病民而残石也!”
遗憾的是,亭林期待的“君子有取焉”并未实现,百年之后乾嘉金石学兴盛,让“好古之虚名”走向了群体的欢愉。尽管黄易们的筆下不会记录“父老子弟、工人隶卒”的颠连勤苦,但我们都清楚,为“古欢”买单的只有那些无力发声的底层民众。
三
顾炎武永远不会知道,自己的“金石事业”会在百年后成为某种“时尚”。而将亭林作为理解“古欢”的坐标,也能为我们提供更为深刻的启示。需要说明的是,就学术研究而言,乾嘉的金石学者是亭林的后继,他们看到的碑刻更多,考释亦更为缜密;如果将顾炎武与翁方纲、王昶、孙星衍等人加以对比,我们可以看到金石学的内部演进。至于黄易,他的工作集中在金石的发现、收藏与著录上,与亭林并不完全处在同一层面。但作为乾嘉金石学的中心人物,黄易的精神气象及其所代表的士人风貌,则与亭林形成了鲜明反差。我们对二者的对比,也主要集中在精神气质与历史形象的层面—前者慷慨悲歌,后者欢愉自得;前者是踽踽独行、满腔孤愤的访碑者,后者是长袖善舞、以古为欢的金石活动家。
同样一种学术传统,仅仅相隔百年,学者的精神气象竟有如此不同!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回到文章的题目了。在《日知录·正始》篇中,亭林有一段极为沉痛的议论:“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这是一组极具阐释张力的概念,“亡国”是华夏内部的政权更替,“亡天下”则是蛮夷猾夏与文明传统的断绝。就本文讨论的士人精神而言,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读书人的精神萎缩与“去政治化”—政权更替并不影响“匹夫”担当天下的责任,从而呈现出忧患沉郁的气质;异族统治的文化高压则让读书人不敢关心“天下兴亡”,而是蜷缩在各自的安逸中,享受“小确幸”的文化欢愉。在这一角度上,亭林的金石学可谓“亡国的金石学”,凝聚着遗民对天下民生的关切。章太炎在一次革命演讲中曾说:“古事古迹,都可以动人爱国的心思。当初顾亭林要想排斥满洲,却无兵力,就到各处去访那古碑古碣传示后人,也是此意。”堪称亭林的知己。而以黄易为代表的乾嘉金石学则是“亡天下的金石学”,在获得乐趣的同时与天地世界渐行渐远。《古欢》中有一个很值得玩味的细节,黄易的朋友赵魏拓得十二字延年汉瓦后,写信向黄报喜:“突然想到此时的家乡荒旱终年、米珠薪桂,他们却以翰墨为缘,剜苔剔藓,虽然日有所得,实在不值外人一笑,只有素心人才会为之千里首肯。”(107页)这里的“素心人”充满了反讽意味,尽管目睹生民多艰,但依旧掉头不顾、沉浸在唯有“自己人”才能读懂的欢欣中,这不正是“亡天下的金石学”吗?
有意思的是,薛龙春似乎并未充分认识到这一区别。正如他认为人们对金石学中的乐趣“关心甚少”一样,他对金石学中的悲慨也关心甚少。在他看来,“古欢”是一个延续和成长的过程,而它的起点,正是顾炎武所处的晚明—“这种兴趣的成长,即使从晚明算起,也已经历了一个多世纪”(22-23页)。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与《古欢》的研究理念密不可分。在他看来,用政治、世风等外在因素来理解金石学,是一种“外缘性的解释,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是最有力的历史解释”,他更倾向于用“内在理路”说来探讨乾嘉金石学的学术风貌与历史成因。诚然,“内在理路”能够说明金石趣味的延续、金石考证方法的继承,但却不能充分说明金石学者在精神气象上由“亡国”到“亡天下”的转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只能去叩问“外在”的时代及其对士人的影响。
在《古欢》中,清朝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它鼓励金石收藏、支持士人对文化欢愉的追寻。但在我们更为熟悉的历史叙述中,清王朝展现出另外一种历史形象—专政、高压与文字狱。这两种形象并不矛盾,王汎森先生在《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一文中细致入微地探讨了清代文化高压对读书人的影响机制。文字狱不仅镇压不幸的当事者,更如投石入池塘一样产生“涟漪效应”,促发着无涯无边的自我禁忌,无论治学、议论、著述还是刊刻,都不断传导出绵绵暧暧的文化压力。“清代政治对文化领域之压制最大的影响,是因涟漪效应带来各种文化领域的萎缩、公共空间的萎缩、政治批判意识的萎缩、自我心灵的萎缩,形成一种万民退隐的心态,‘非政治化的心态。”(406页)在这种心态下,知识界出现了大大小小的“网格”,它们规定着什么是可以的,什么是不可以的。这些“网格”割裂着天下的整体关切,也留下了任人欢愉的狭小空间—在任何一个专制的时代里,都有一些欢快的角落,那里的歌声、笑声如此真切,以至于遮蔽了后人对历史的认知。从顾炎武到黄易,清代金石学的变化恰恰印证了这种严重的精神萎缩。在清代的文化生态中,金石学不过是其中一隅,还有其他让人忘却“天下”的忧患与责任、在同好中获得乐趣的文化角落。
基于“内在理路”的《古欢》,让我们看到一种十分难得的“活的文化史”。薛龙春对乾嘉金石时尚细致入微的呈现,极大程度地还原了那个时代真切的乐趣,以及乐趣背后乾嘉学术群体栩栩如生、鲜活有趣的文化面貌。通过艺术社会史的研究进路,《古欢》充分拓展了对乾嘉时期社会文化丰富性的认识,弥补了已往研究的不足。与此同时,忽略了“外在影响”的《古欢》,在明清士人文化剧变的大视野中又缺少了些历史的深度与宏阔,未能将艺术史的新视域与传统史学的批判精神有机结合。《古欢》 的得失之际是值得深思的—“内在理路”说的基本动机在于凸显学术超越于政治的自身传统,可这一旦发展为淡化甚至忽略世风士气的根本意义,从而沉浸在某个小圈子的文化逻辑中不能自拔,其中蕴涵的样本价值,确实值得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