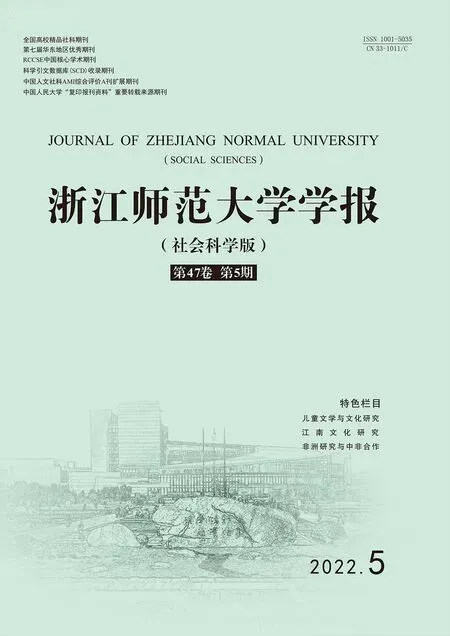从“地域”到“省域”:清代江南士人身份认知的转型
宋可达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边疆研究所,北京 100101)
引 言
作为地域意识的一种,省域意识实质上是省域人群文化心理的具体反映。①它的产生,与行省制度的发展、成熟息息相关。自秦罢侯置守以来,中国古代的地方行政制度,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至元代,因“前代郡县之制损益之”,[1]开创了沿用至今的行省制度。由明入清,行省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现行诸省份的省域范围亦大致奠定。
随着清代行省制度的长期稳定,省级政区在政令传达、经济活动、文化取向等诸方面逐渐形成了强大的内向制约性,并对省域内部文化要素的整合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张晓虹在进行陕西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时,观察到自元代起,陕西高层政区建置一直相对稳定,“在政区的整合下,(陕西)内部文化现象从歧异极大发展到清代以后相似性逐渐增强,与周围的三晋、巴蜀、陇东文化已有明显的差异”。[2]换言之,在省级政区的整合、规范下,清代的陕西,已开始成为具有更多相似性的文化综合体。无独有偶,刘影在研究晚清以来山西文化的形成时,指出:“省作为一级政区,经过元明清三朝的巩固,不仅是一种行政规范,业已成为一定地域的文化规范,使全省文化心理日益趋同”,乃至像“背离性最强的河东,自元代开始,该区的中心移向临汾盆地,体现了由省会自北控南的趋势”。[3]在省域文化要素包括省域人群文化心理不断趋同的时代背景下,清代以降,一种立足于特定地域认同的省域意识不断兴起。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若干一体化程度较高且兼具深厚历史文化传统的地域来说,当地人早已形成了深刻的地域意识。但因清代省级政区的长期设置以及地方行政力度的日趋加强,其原有的地域意识不免受到了一定的冲击,进而开始对其地域意识与身份认知进行建构和重塑,以适应省制时代的社会环境。在这些地域之中,清代的江南,即存在典型的身份认知的转型现象。
江南,是帝制中国版图内的重要地域。从社会经济层面来看,自唐宋全国经济中心南移以来,迄至明清,位于太湖河网平原的江南地区,一直是这个南移的重心所在。随着传统社会后期全国市场的逐步形成,江南进一步将周边区域纳入了自身经济的辐射范围,而其内部的经济联系亦随之加深。
但是,在明清江南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提升的同时,其政治一体化的进程,却遭遇了重大挫折。明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以“直隶嘉兴、湖州二府隶浙江”,[4]向来属同一政区或自成一单位的江南地区,由此发生了分裂。历明至清,在江南地域长期分属江、浙两省的政治背景下,江南当地人尤其是处于社会上层的江南士人,其原有的身份认知受到了持续的冲击,开始其缓慢的异变与重塑。
在以往明清江南史的研究视阈里,经济、市场、城镇等研究视角备受关注,是现有研究不可撼动的绝对重心。而对于省制时代江南士人身份认知或身份建构的研究,则相对薄弱。相关成果中,胡晓明探讨了历史时期江南认同的形成过程,并将清代视为江南认同的成熟时期。[5]汤志波依据明清江南士人编刻的《江南春》,在分析江南具体地域指向的同时,探讨了当时江南士人的心态及身份认同。[6]张伟然《从吴地到越地:吴越文化共轭中的湖州》则以湖州为例,对其文化归属在明清时期发生出吴入越的变迁过程作了一番梳理。[7]孙杰从明清浙西“山区州县”的方志编纂入手,考察了当地士绅群体的自我认知及其表现。[8]
总体而言,现有成果主要侧重于考察这一时期江南士人身份认知的相似性和共通性,或多或少忽视了江南地域长期分属江、浙两省给当地士人身份认知和身份建构带来的深刻影响。进一步而言,以往的研究,尚未将江南行政区划的长期割裂与江南士人身份认知的嬗变两者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如果我们仅仅强调明清是江南认同的成熟时期,而对这一阶段江南士人身份认知的建构、转型过程缺乏必要的关注,显然难以把握明清江南地域的全貌。有鉴于此,本文将重点探讨这一问题,试图揭示有清一代时人省域意识兴起、强化背景下江南士人在身份认知层面发生的微观变化,以裨益于我们对明清江南地域社会的认识。
应该说明的是,所谓“江南”的空间范围,学界历来有不同的意见。本文所论清代江南,乃以太湖流域为言,涉及苏、②松、常、镇、杭、嘉、湖七府。
一、江南行政区划的分裂及其固属江、浙两省
为明确清代江南士人所处的地域背景,有必要对江南行政区划的变迁过程作一番梳理。从政区沿革来看,地处太湖流域的江南七府,明以前经常同属于一个政区。秦与西汉属会稽郡。东汉顺帝永建四年(129),以钱塘江为界,分会稽郡为吴、会二郡,[9]太湖流域属吴郡。六朝属扬州。唐前期属江南东道;肃宗乾元元年(758),“置浙江西道节度使,领苏、润等十州,以昇州刺史韦黄裳为之”。[10]到北宋,太湖流域属两浙路;南宋属两浙西路。元代,杭州路、湖州路、嘉兴路、平江路、常州路、镇江路、松江府等六路一府之地皆隶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司,统属于江浙行省。[11]
至明洪武十四年(1381),诏以嘉、湖二府自直隶改属浙江,历代皆属同一政区或自成一单位的江南地区,其行政归属遂呈长期分裂的态势。在此以后,朝廷基于统一管理江南税粮、水利事务的需要,一度将该地域重新统属于一种新型的地方行政区划——巡抚辖区。洪熙元年(1425)八月,宣宗“命广西按察使胡概为大(理)寺卿,同四川参政叶春巡抚直隶及浙江诸郡”。[12]卷八76这一巡抚,即为明代应天巡抚的前身。
但是,好景不长,宣德五年(1430),诏“升行在吏部郎中赵新为吏部右侍郎,兵部郎中赵伦为户部右侍郎,礼部员外郎吴政为礼部右侍郎,监察御史于谦为兵部右侍郎,刑部员外郎曹弘为刑部右侍郎,越府长史周忱为工部右侍郎,总督税粮。新江西、伦浙江、政湖广、谦河南、山西,弘北直隶府州县及山东,忱南直隶苏松等府县”。[12]卷七十1639-1640赵伦以户部右侍郎衔总督浙江税粮,标志着此前设置的南畿浙西巡抚被析分为二。浙江杭、嘉、湖三府属浙江巡抚辖区,直隶苏、松、常、镇四府则属应天巡抚辖区。
之后,浙江巡抚置废不常,“或巡视或督鹾,有事则遣”。[13]至嘉靖,朝廷定置浙江巡抚一员,包括杭、嘉、湖在内的两浙十一府皆为其固定辖区。苏、松、常、镇、杭、嘉、湖等江南七府在行政归属上遂完成了剥离。因此,除特殊情况外,苏、松、常、镇与杭、嘉、湖的民政、军务基本互不相涉,时松江人莫如忠总结称:“今各院所临地方,得兼苏松、浙江者,惟巡盐御史。”[14]以干系甚重的水利治理为例,嘉靖十四年(1535),应天巡抚侯位奏云:“旧以浙江佥事兼管苏、松(常、镇)等四府水利,至是太仓添设兵备,不但水利宜属兵备,及四府钱粮俱宜令其管理,庶事体归一。”[15]部覆从之。
清承明制,延续了前明对江南七府施行的“分而治之”思路。顺治二年(1645),改南直隶为江南省;[16]康熙六年(1667),分江南为江苏、安徽二省。[17]卷二三315苏、松、常、镇四府先属江南、后属江苏;杭、嘉、湖三府,则固属于浙江省。值得注意的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八月,乾隆帝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决策:“江苏钱谷殷繁,安徽布政使远驻江宁,所办专系上江事务。莫若于江苏添设藩司,分职管理,方为有益……将江、淮、扬、徐、海、通六府州,分隶江宁藩司管辖。苏、松、常、镇、太五府州,分隶苏州藩司管辖。”[18]卷六一九965次年二月,正式分铸“江、淮、扬、徐、海、通等处承宣布政使司之印”及“苏、松、常、镇、太等处承宣布政使司之印”。[18]卷六百三十33以此为标志,江苏省境内遂形成了“苏属”和“宁属”两大布政使辖区,这在某种意义上,进一步强化了苏、松、常、镇四府在政治空间上的紧密联系。至于杭、嘉、湖三府,清廷常置有杭嘉湖道一职,隶浙江布政使。
根据以上论述,可以看到,明洪武十四年(1381)以后,江南地区被人为地分割成苏、松、常、镇与杭、嘉、湖两个相对独立的地域。到了清代,苏、松、常、镇与杭、嘉、湖在政治地理层面的分裂态势更已完全成型。那么,对于清代的江南士人而言,江南七府一直分属江、浙两省的行政区划格局,对他们的身份认知又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呢?
二、清代江南士人身份认知的建构过程
身份认知,实质上是主体对于其身份或角色合理性的确认,其体现的是主体对于自身角色包括角色所处地域社会的认同。明代以前,由于江南地区一直属于同一高层政区,加之其在自然、经济层面固有的紧密联系,因此对当时的江南士人群体来说,几乎不存在地域归属和身份认知上的差异。
但是,明洪武十四年(1381)以后,同属江南地域的苏、松、常、镇与杭、嘉、湖,从此分属两个不同的省级政区。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江南士人的身份认知不能不受到影响。明代松江人顾汝绅在送友人回浙时,即称:“浙、直殊省,吴、越异邦。”[19]到了清代,随着时人省域意识的兴起和强化,江南士人的身份认知较之前更发生了明显变迁。
具体来看,清代江南士人有一个再塑身份认知的过程,这一过程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苏、松、常、镇士人对“三吴”地域概念的重构
就地域文化层面而言,地处太湖流域的江南七府,在风俗、方言、信仰等文化要素上有着较高的相似性,并长期被视为一个不分彼此的文化地域共同体。尤其自六朝以来,兴起了一个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三吴”概念,③《水经·渐江水注》云:“汉高帝十二年,一吴也,后分为三,世号三吴:吴兴、吴郡、会稽其一焉。”[20]随着历史的演进,北起长江、南滨浙水的江南七府之地,一直被世人视作“三吴”的重心所在,典型的如明人杨文《泰伯墓碑记》称:“泰伯遭商周之际,以让德,逃之荆蛮,寓无锡之梅里,号句吴。东南抵浙(即钱塘江),西北抵江,方千里之间,古谓之三吴者,皆以沾化而名也。”[21]不过,到了清代,情况却发生了变化。在当时江南士人尤其是苏、松四府士人的认知中,“三吴”这一地域概念,很多情况下仅仅被用来指代江苏省之苏、松、常、镇四府。与之相对,行政上隶于浙江的杭、嘉、湖三府,则常被排斥在“三吴”之外。
清初,苏州人徐与乔《三吴田赋议》有云:“三吴田赋甲于天下,而苏、松之赋,又甲于常、镇。”[22]明确将“三吴”与苏、松、常、镇四府画上了等号。康熙时,帝南巡江、浙,松江人周金然作《允犹翕河赋》称:“由三辅而经千乘,历两浙而返三吴。”[23]其意念中的“三吴”,显然不包括苏、松以南的两浙之地。与之相似,苏州人李书吉《禀浙江蒋中丞》谓:“前阅邸抄,欣悉大人秉钺三吴,嗣复移旌两浙,望风踊跃,向日欢腾。”[24]亦将“三吴”与“两浙”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地域。
之后,太仓人袁翼《江南提督陈忠愍公殉节记略》称:“浙、吴接壤,而三吴重地,非威望素著者不能任。”[25]差相同时,常州人薛福成《上曾侯相书》云:“推毂群帅,选将分兵,则两浙、三吴,相次恢复”,[26]表达了和袁翼类似的认知。至清末,松江人冯金伯在所撰《国朝画识》中写道:“吾宗樗崖先生(沈廷瑞)喜游历。尝之三吴,之两浙,之金陵、淮阳,之豫章、荆楚、夔门、巴巫之间,登山临水,辄寄吟咏。”[27]可以清楚地看到,上述苏、松四府士人所谓的“三吴”,皆排除了行政上隶属于浙江的杭、嘉、湖三府。
而从清代杭、嘉、湖士人的认知来看,也存在着类似的现象。嘉庆间,江苏巡抚、杭州人陈桂生在为新修《松江府志》作序时称:“余藩江苏二载,旋奉命抚三吴。”[28]在他看来,“三吴”的地域范围即同于苏、松、常、镇乃至江苏一省。湖州人刘锦藻云:“浙江北顾三吴,南瞰七闽,右连饶歙,左控沧溟。”[29]同样把包括杭、嘉、湖在内的浙江省与“三吴”地域进行了剥离。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这种以“三吴”指代苏、松、常、镇四府或江苏一省的说法,并不是清代江南士人群体所独有的,而是当时社会各阶层中普遍流行的一种观念。
以统治者的认知为例:
康熙三十八年(1699)三月,康熙帝在南巡江、浙两省途中,谕户部:“朕以省方问俗,巡历三吴。比至浙省,见沿路农桑虽遍陇亩,而地有肥硗,时有丰歉。”[17]卷一九二1040
乾隆十六年(1751)二月,诏曰:“朕问俗观风,南巡江、浙,清跸所至,广沛恩膏。更念三吴、两浙,为人文所萃。”[18]卷三八二22同年三月,又谕:“朕省方观民,茂求上理,前因浙省士庶,谊切急公,正供概无宿逋,颁谕嘉奖,诞布特恩。顷翠华涖止,周览土风,虽与三吴绣壤相错,而闾阎趋尚,较吴稍朴。但浮竞之习举所不免,其盖藏之未裕均也。”[18]卷三八四51
可以看到,在康熙、乾隆等统治者意念里,“三吴”的空间范畴并不包括杭、嘉、湖等浙省地域。无独有偶,官修《清朝文献通考》在描述浙江省的山川形势时亦称:“总全浙之形势,北通三吴,南引七闽,而浙水实中络其间。”[30]我们很难判断,有清一代以“三吴”特指苏、松、常、镇四府或江苏一省的认知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流行开来的,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认知在当时社会中具有重要的舆论影响力。
特别有意思的是,从“三吴”地域概念的本义来说,以其专指苏、松、常、镇四府,尚情有可原;至若将地处江苏省长江以北的淮、扬、徐、海、通等地统一纳入“三吴”范畴,则无疑背离了“三吴”的本义,正如乾嘉时人周广业在《循陔纂闻》中所指出的:“(三吴)诸说虽不同,要无以今苏、松、常、镇、淮、扬、徐、泗为三吴者。十数年前,见江苏学使刊刻试卷颜曰:‘三吴试牍。’”[31]
尽管杭州人周广业认为以“三吴”指代江苏全省之地,似与“三吴”的本义不符,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这种认知在当时的官僚士大夫阶层中相当多见。例如,乾隆二年(1737),两江总督庆复上疏称:“江、浙接壤,风土大略相同。浙省蚕桑之利甲天下,而三吴组织所需,皆资市贩,应令各州县官查勘该处地方。”[18]卷五一874疏中所谓“三吴”,应指与浙省并称“江浙”的江苏省。光绪间,原籍江苏常州的恽毓鼎奏云:“以臣原籍江苏而论,三吴赋税之重,甲于天下。山陬水澨,无不垦之田。自经刚毅办理清赋,民田无复隐匿,是江苏一省,似可无庸重议丈量矣。”[32]其亦视江苏一省为“三吴”之域。
由此可见,受行省制度及其所催生的省域意识的制约,在以苏、松四府士人为代表的清人认知中,“三吴”这一地域概念,被普遍用来指代苏、松、常、镇四府乃至江苏一省。至于同属江南地域的杭、嘉、湖三府,则日趋被排除在“三吴”之外。甚至传统意义上同于太湖流域——江南七府地域的“吴中”一词,在此时也常被苏、松士人用作苏、松、常、镇四府的代称。如苏州人叶方蔼《送成侍御视鹾两浙序》云:“我国家财用岁仰给东南,而吴中之赋甲天下,外此则两浙诸郡。壤错趾接,其赋之所入时,与吴相表里。而榷盐之政,则吴之四郡独隶于两浙。”[33]叶氏笔下的“吴中”,即“吴之四郡”苏、松、常、镇,并不涵盖杭、嘉、湖等“两浙诸郡”。常州人秦松龄在《遂宁张公书院记》中写道:“乙亥秋,公试事既竣,吴中四郡之士,构书院于江阴学宫之东偏,中奉公位,相与讲习其中。”[34]语中独以“吴中”指代苏、松、常、镇四府,而不涉杭、嘉、湖之地。
(二)杭、嘉、湖士人“越地”认知的觉醒
在提及清代苏、松、常、镇四府士人对“三吴”地域概念进行重新诠释的同时,还应注意这一时期杭、嘉、湖士人的“越地”身份认知正在觉醒。
如前所述,明清以前,江南七府地区普遍被视作“三吴”或“吴地”。而横亘两浙的钱塘江,则常被世人视为吴、越的地理分界线。唐僧处默有诗云:“到江吴地尽,隔岸越山多。”[35]宋人陈师道《钱塘寓居》诗亦谓:“声言随地改,吴越到江分。”[36]不过,随着洪武十四年(1381)以后江南行政区划的长期分裂,江南士人对于属吴、属越的身份认知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如明代杭州人张瀚在《松窗梦语》中写道:“自金陵而下控故吴之墟,东引松、常,中为姑苏。”[37]其虽未明确把杭、嘉、湖排除在“吴墟”之外,但语中以苏、松、常(镇)为全吴重心是显而易见的。入清以后,在时人省域意识日趋形成并不断强化的背景下,杭、嘉、湖尤其是杭、嘉士人对于“浙越”④之地的归属感不断增强,进而开始对江南七府皆属“吴地”的传统认知进行辨正。
早在康熙年间,嘉兴人沈季友在《槜李诗系》卷三七《越人》中考证道:
《越语》:“勾践之地,北至御儿。”《越绝书》:“语儿乡,故越界,以为战地,置石门为限”,在今桐乡县西北二十五里。及越败夫差,增封勾践地,北至平原,在今海盐县北平湖境。柴辟与槜李界,乃吴南境也。顾、新、于、主四城,暨射襄、胥山、伍塘、练浦、游屯泾、千乘乡、千步路、走马冈、纪目坡,皆吴地;何、萱、晏、管四城,暨马嗥、长营、千人坡、烽火楼、范蠡坞,皆越地,并在今嘉兴、海盐、石门、桐乡诸县境上。则吴越分界,本在我郡,故前人谓“到江吴地尽,隔岸越山多”,与吴越一江分二诗,未足深据也。[38]
沈季友以《国语·越语》及《越绝书》记载为本,指出吴、越分境本在嘉兴而非钱塘江。在其意念里,浙水以西的杭州包括嘉兴部分地区是当仁不让的“越地”。
稍后,杭州人杭世骏在所著考证笔记《订讹类编》中,直截了当地指明“嘉兴是越地”,其引王士禛《香祖笔记》的观点称:
唐诗曰:“到江吴地尽,隔岸越山多。”(按此释处默《圣果寺》句,《后山诗话》云吴僧《钱塘白塔院》诗)予读《吴越春秋》,阖闾五年,哭南伐越,破槜李,《左传》《史记》亦然。《越绝书》:“语儿乡,故越界,名曰就李。”然则春秋之时,嘉兴本越之北境。初不隶吴,唐诗云云,非也。⑤
案汉顺帝分会稽之半为吴郡,孙皓时,分吴郡为吴兴郡,兼杭、秀、睦之地,则嘉兴正隶吴郡。但唐诗以越对言,则指春秋之吴越,非指后汉之吴郡,于地理未深考矣。[39]
与沈季友的相较,杭世骏的态度更为激进,其以嘉兴全属越之北境。并且,杭世骏指出唐僧处默作“到江吴地尽,隔岸越山多”之句,缘于其对吴、越的地理沿革未进行深入考证。
同一时期,杭州人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记云:
昔人以钱塘江为吴、越二国之界,故唐释处默诗有“到江吴地尽,隔岸越山多”之句。宋陈师道《后山集》亦有句云:“吴越到江分”,盖仍《史记》之误。以《春秋内外传》考之,吴地止于松江,非浙江也,浙江乃越地。故《国语》曰:“勾践之地,北至于御儿,西至姑蔑。”[40]
梁玉绳将后世人以钱塘江为吴、越分界的错误认知归结于《史记》的错误记载,⑥并据《春秋内外传》考“吴地”止于松江。按其所述,春秋吴、越两地分界与清代江、浙两省省界近乎一致。
清代杭、嘉士人对吴、越地理分界线的积极重构,似乎也影响到了江南以外人士的看法。如扬州人汪中在《述学·内篇三·广陵曲江证》中即提到了吴、越分境的问题,其谓:
越之北境至今之石门,浙江非吴地。故《越语》:“勾践之地,北至御儿。”韦昭注:“今嘉兴语儿乡也。”《吴语》大夫种谋伐吴曰:“吾用御儿临之。”韦昭注:“御儿,越北鄙,在今嘉兴是也。”《尔雅》释地:“吴、越之间有具区”,其言审矣。[41]
汪中不仅指明杭、嘉为“越地”,且引《尔雅》“吴、越之间有具区”之说,认为吴、越分界在太湖而非钱塘江。
除上述外,在《湖壖杂记》《西湖志纂》《冷庐杂识》等清代杭、嘉士人的著述中,亦就吴、越分界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且皆以杭、嘉(湖)为“越地”,[42-44]在此不一一详述。
随着清代杭、嘉、湖士人“越地”身份认知的觉醒,分属江、浙两省的太湖,日益有取代钱塘江、成为江南七府士人心目中“吴地”和“越地”分界线之势。苏州人沈德潜《登穹窿绝顶望震泽》云:“惊涛白茫茫,吴越势交汇。”[45]作为沈德潜的同乡,吴俊在《荒庄感旧图歌为张瘦铜舍人作》诗中有句谓:“具区一水限吴越,清梦时堕菰城烟”,[46]明明白白地以太湖为“吴地”与“越地”的分境之处。嘉兴人李明嶅《晓发太湖》曰:“七十二峰碧,一帆渡太湖。地迷吴越界,身入水云区。”[47]无独有偶,常州人清瞿源洙《望湖》诗亦称:“中江趋震泽,巨浸表名都。远岸微分越,连山尽入吴。”[48]吴、越虽地域相连,但在李明嶅、瞿源洙等人看来,其间仍存在“太湖”这一清晰的界限。
亦有将地居江、浙省界附近的平望、盛泽视作吴、越的分界所在。嘉兴人彭孙贻有句云:“吴越水分平望驿,荆蛮天尽洞庭山。”[49]湖州人叶绍本《平望》诗称:“一水分吴越,苍茫远望余。”[50]苏州人周灿《盛泽》诗吟道:“吴越分岐处,青林接远村。”[51]
须提请注意的是,自外界看来,明清时期的“吴地”与“越地”是几无差异的共同体。但事实上,两大地域在相互交融的同时,亦存在一定的对立、竞争关系。如明初常州人谢应芳曾作《论吴人不当祀范蠡书》,批评以苏州吴江为代表的“吴地”人祭祀“吴之大仇”范蠡的现象。[52]谢应芳的观点获得了弘治《吴江志》撰者——吴江人莫旦的深切认同,并表示:“人之有家,自开辟以来,即有此家,岂可谓蠡灭吴时,吾祖宗不与其难。以是言之,则吴人不当祀蠡了然矣。”[53]
更有意思的是清代常州人顾岱在杭州知府任上时为康熙《浙江通志》所作的序,序称:
自禹会诸侯于会稽,而越疆始启。斯时取涂所经,舍航从陆,故州以杭名。呜呼,何声教之早被与?逮乎少康封其支裔无余于兹土,似宜如朝鲜之得箕子,荆蛮之有泰伯,化荒服为醇俗矣。乃《鲁史》定、哀之末,于越始见于春秋,而勾践君臣沼吴之谋,皆诟机巧术而大远乎道,计利而不计义,是以汉江都王称越有三仁,而董仲舒非之。迄今览少伯援桴之语,不阅。数传遂灭于楚,非不幸也,岂越水曲折,因字为浙,亦风气使然耶?其所由来远矣。[54]
作为“吴地”士人,顾岱对勾践等越国君臣以机巧术灭吴之举显然耿耿于怀,故其称越灭于楚,“非不幸也,岂越水曲折,因字为浙,亦风气使然耶”,对浙越风气隐寓批评之意。从这一角度来看,清代江南士人在身份认知上表现出来的属吴、属越之异,似不能等闲视之,其中隐隐包含着吴、越乃至江、浙两省文化竞争和文化角力的意味。
三、省域意识对清代江南士人身份认知建构的影响
地域是人们生活的自然居所,共同的地域生活往往会使人们产生强烈的地域意识和身份认同。清代,随着行省制度的成熟,省级政区在居民日常生活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不断形塑着时人的地域意识,从而使得清人的身份认知常常在行省层次上言说,这对参与公共生活的士人阶层而言更是如此。关于这一点,施坚雅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曾指出:“大部分中国人想到中国的疆域时,是从省、府和县这一行政等级出发的。根据行政区域来认知空间在明清时甚至更为明显。那时,人们不可避免地用行政区域来描述一个人的本籍——表示其身份的关键因素。”[55]
具体到江南这一地域,由于明清两代苏、松、常、镇与杭、嘉、湖长期分属不同的省级政区,行省制度与科举制度日趋成熟,江南七府士人的学习和举业被严格控制在省籍所在地,以此形成了由科举考试产生的籍贯观念和地方利益观念。这在清代江南士人身份认知的建构过程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从清代江南士人特别是杭、嘉、湖三府士人的言行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突出现象:其对于所属省级政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正在不断增强。如湖州人许宗彦言:“吾浙夙称人文渊薮。”[56]杭州人丁澎谓:“我浙素称东南奥区,通吴会,控闽粤,带江襟海,士马精研,财粟盈溢。”[57]更具典型意义的是嘉兴人沈曾植在《强邨校词图序》一文中的表述:
吾浙山川名在《山海经》,而至今可指其所在、按图了然者,东惟会稽,西惟浮玉、苕水为最古。上强为浮玉,支麓而埭溪与施渚,则苕水西源也。禹、益所经,夏少康、帝杼封巡之墟,越王勾践铸剑之迹,山水清绝,云物泱漭,往往令人俛仰古今,悲思感慨而不可止。居士虽家在强邨,用生出入中外,退而寄居他郡,图中风物,梦想所寄耳。而长楸、夏首之思,感不绝而菀莫达。[58]
通过以上史料记载不难发现,于时杭、嘉、湖士人对浙江省已有颇强的省域认同,往往口称“吾浙”“我浙”,矜夸浙江的文教成就、悠久历史和山川风貌。值得注意的是,于时杭、嘉、湖士人所谓“吾浙”“我浙”之“浙”,基本上是指浙省十一府地区,而不包括明代以前同属两浙的苏、松、常、镇四府。如杭人杭世骏开谈即云:“吾浙十一郡。”[59]湖人俞樾更常提及:“吾浙凡为府者十有一,上八而下三”,[60]“吾浙东西为郡者十一”。[61]
考察苏、松四府士人的认知,亦存在类似的现象。苏州人冯桂芬《上海果育堂记》文云:“今世善堂义学之法,意犹近古。能行之者,惟我江苏为备。”[62]常州人沈同芳在所撰《武进阳湖同乡致苏省京官徐中堂等书》中称:“吾苏襟江带海,形势便利,甲于他省。”[63]
基于以上现实背景,清代江南七府士人在表达自身的地域归属与身份认知时,相当大程度上会受到省域意识的制约。无论是其对“三吴”地理概念的全新诠释,抑或是其对传统吴、越地理分界线的质疑和重构,皆深刻地反映了这一点。
传统上,由于太湖流域水网密布的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江南地域得天独厚的空间交流优势,在这样的有利条件下,苏、松、常、镇、杭、嘉、湖,向来被视作一个紧密相连的地域共同体。不过,同样应该看到,随着明初将江南七府在行政上割属两省,在明清两朝长期稳定省级政区的整合、规范下,分属江、浙的苏、松、常、镇四府与杭、嘉、湖三府,在身份认知层面已隐隐形成了两个相对独立的地域系统。正如清代嘉兴人钱陈群在《张东侯郡守屏风记》中指出的:“江、浙同为财赋重地,浙东、西十一郡,计财赋所出,浙西三郡实可曹郐余郡。国家转漕,每岁贡天庾者,数溢平江四郡。”[64]钱氏在点明江南七府为天下财赋所聚的同时,亦以省为认同单位,将此七府区分为“浙西三郡”和“平江四郡”。无独有偶,常州人储掌文《陈宅三时文叙》称:“吴、越人文甲天下,越之有杭、嘉、湖,犹吴之有苏、松、常、镇也。”[65]江南七府虽并称文薮,但在储掌文认知中,其内部显然存在着吴(江苏)、越(浙江)之分。
甚至在自然景观层面,苏、松、常、镇与杭、嘉、湖在时人看来亦有着若干差异。常州人钱泳曾对比道:“杭、嘉、湖三府,桑麻遍野,菱芡纵横,有弃地如苏、松、常、镇四府者乎。”[66]
由此可见,江南七府之间虽有着难以分割的地域联系,但在清人省域意识逐渐兴起、强化的时代背景下,分属江、浙两省的江南七府士人,在表达自身的身份认知时,颇热衷于对彼此作省籍层面的区分。要之,本文对清代江南士人身份认知的研究,只是一个初步的探索。在深度辨别明清江南地域分异、复原江南士人身份认知建构过程的问题上,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注释:
①关于省域意识或省籍意识的研究,近年来学术界已经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刘伟《晚清“省”意识的变化与社会变迁》(《史学月刊》1999年第5期,第59-65页)论述了晚清新政背景下各省省域意识的形成、变化及对清政府的影响;张晶萍《省籍意识与文化认同:叶德辉重建湘学知识谱系的努力》(《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第45-49页)通过对叶德辉重建湘学新传统的考察,分析了近代省籍意识强化背景下地域学术文化之间的互动与竞争;陆发春《安徽建省与省域认同》(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13)从省通志的编辑、官员籍贯的填写以及省级会馆的兴建三个角度出发,呈现了清代安徽省域认同的形成过程;胡凤《分解与重构:安徽近代白话报刊中的行省意识研究》(《安徽史学》2016年第6期,第157-164页)以近代安徽的白话报刊为切入点,探讨了其在建构安徽省域意识上所起的作用。
②辖域包括雍正二年(1724)升为直隶州的太仓州。
③关于六朝时期“三吴”具体所指,目前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的看法。王铿《东晋南朝时期“三吴”的地理范围》(《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1期,第71-76页)一文持“吴、吴兴、会稽”为“三吴”说;余晓栋《东晋南朝“三吴”概念的界定及其演变》(《史学月刊》2012年第11期,第114-117页)认为“吴、吴兴、丹阳”为“三吴”;杨恩玉《东晋南朝的“三吴”考辨》(《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第72-80页)则以“吴、吴兴、义兴”为“三吴”。要而言之,以太湖流域为“三吴”的重心,乃学界共识。
④清人常用“浙越”一词来指代浙江,如吴省钦《恩科浙江乡试录序》文云:“我皇上十六年辛未,幸浙越,今四十余年。”(《白华后稿》卷四《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44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535页)郭棻《诰授朝议大夫候补布政使司参议前提督浙江学政按察使司佥事刘公潜夫暨原配许宜人继配任宜人合葬墓志铭》谓:“(刘潜夫)督学浙越,甄拔有造,不可胜数。”(《学源堂文集》卷九,清康熙刻本,第38a页)
⑤此节为王士禛《香祖笔记》所述。
⑥此处所谓《史记》之误,盖指《史记》卷四一《越王勾践世家》言:“(楚威王)杀王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中华书局,1963,第17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