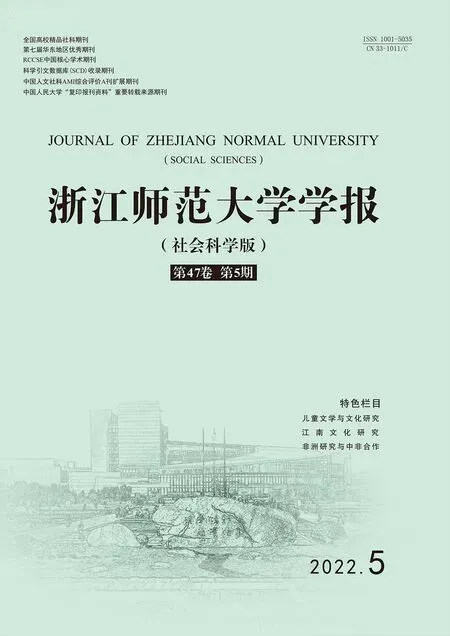满汉涵化视野下的清代宫刑
李毅婷
(浙江师范大学 边疆研究院,浙江 金华 321004)
宫刑又称腐刑,是肉刑的一种。汉文帝废肉刑后,宫刑一度作为闰刑存在。东汉永初后,宫刑便鲜见于史籍记载。①北魏神嘉中,宫刑再次被作为正刑适用于大逆不道的缘坐犯。[1]卷111《刑罚志》,2874学界一般认为,隋《开皇律》正式废除宫刑,此后除辽穆宗时曾适用外,宫刑已经不复存在。②实际上,宫刑在清乾隆后期再次被适用于缘坐男犯,且形成条例,直至清末改律才被彻底废除。到目前为止,鲜有学者关注该现象。直接研究者仅魏道明《清代的宫刑》一文。该文简略地梳理了清代宫刑适用条例的演变及部分相关案例,指出清代恢复宫刑,是受“绝对的法定主义”影响,“一定意义上讲,是过度追求罪刑均衡的结果”。[2]另有吴杰专著研究“杀一家三人”条,从家本位着眼,认为“条例规定将凶犯的子嗣进行阉割,是朴素的‘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正义观念的体现”。[3]上述研究均从法制史层面探讨了清代恢复宫刑的原因,观点独到。然而,一个条款的订立往往与时代的发展密切相关,讨论清代宫刑立法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背景。究竟是哪些时代因素促使清王朝恢复宫刑以加强统治?清代宫刑是中原地区传统法律文化的重现,还是满族入关前法律文化的延续,抑或满汉民族文化涵化的结果呢?到目前为止,尚未见到学者就此进行探讨。
本文拟梳理清代有关适用宫刑条例的变迁过程,从起源上清晰地分析其出现的背景及原因,并针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进而揭示清代恢复宫刑的时代因素,尤其是满汉文化在其中的作用。
一、清代适用宫刑之沿革
清律虽然承续明律,但通过修例仍有相当多的变化。③尤其是乾隆朝“一代法制,多所裁定”。[4]卷142《刑法志》,4181宫刑的恢复,即发生在这一时期,先是适用于“杀一家三人”缘坐男犯,后又扩至谋反大逆的缘坐男犯。
在对“杀一家三人”缘坐男犯适用宫刑之前,乾隆朝已经多次修例,更改该罪缘坐男犯的适用刑罚。乾隆二十九年(1764),将“未同谋加功者”之刑罚由流刑加重为充军。[5]卷26《刑律·人命》,790乾隆四十一年(1776),重新定例,首次以被害人是否绝嗣为标准惩处缘坐男犯,将刑罚进一步加重为斩立决、斩监候,并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增修入律。[5]卷26《刑律·人命》,791乾隆四十四年六月,乾隆帝命刑部定例,要求“嗣后如有杀一家四命以上之案,悉按其所杀人数,将凶犯父子照数定罪,俾多寡相当”。[6]卷1085“乾隆四十四年六月己卯”,第22册,582下-583上十月,又因他案下诏,命区分缘坐男犯年龄进行惩处。[6]卷1093“乾隆四十四年十月丙寅”,第22册,668上乾隆四十八年,综合乾隆四十一年、乾隆四十四年两例,纂修成例,规定:杀一家四命以上,被害人已绝嗣,将正犯之子照所杀之数拟斩立决,如有浮于所杀之数,将其幼者改发伊犁给厄鲁特为奴;如未绝嗣,将正犯之子照所杀之数拟斩监候,十一岁以上者于秋审办理,十岁以下者永远监禁,不许赦免,如有浮于所杀之数,将其幼者给死者之家为奴。[7]卷77《刑律人命》,1233显然,兼顾公平、恤悯乃清廷更改“杀一家三人”从坐犯适用刑罚的重要原则。
乾隆四十八年(1783)三月,清廷首次在司法实践中适用宫刑。在“赵成杀死一家六命”案中,长子赵友谅早已携眷迁避且代为认罪,情节可矜,乾隆帝下令改赵友谅的刑罚为宫刑,待百日平复后,再发遣乌鲁木齐,以示法外施仁。[6]卷1176“乾隆四十八年三月庚子”,第23册,767上之后,宫刑逐渐成为“杀一家三人”“未及岁”之缘坐男犯的适用刑罚。乾隆五十三年(1788)三月,因魏玉凯杀主人一家五命,着令:“除将年已及岁者照例办理外,其子孙内有年未及岁者,即解京加以宫刑,以供外围扫除之役。”[6]卷1301“乾隆五十三年三月己丑”,第25册,508下-509上同年七月,又因他案,下令行知各督抚,嗣后凡遇杀一家三人案,均将正犯年幼之子解交刑部监禁,待十岁时阉割。[6]卷1309“乾隆五十三年七月庚辰”,第25册,640上五十四年五月,刑部又提出,凡杀死一家三四命以上者,无论被害人是否绝嗣,“凶犯之子无论年岁大小,俱着送交内务府一体阉割,以示惩创所有”。[6]卷1328“乾隆五十四年五月己巳”,第25册,989上当年即照此处置河南“张文义杀一家三命”案。乾隆五十五年(1790),清廷正式定例:“杀一家非死罪三四命以上之案,不拘死者之家是否绝嗣,凶犯依律拟以凌迟处死,凶犯之子……其实无同谋加功者,无论年岁大、小,俱送交内务府一体阉割。如年在十岁以下,俱牢固监禁,俟年至十一岁时,再行解京办理。”[7]卷77《刑律·人命》,1235至此,宫刑正式成为“杀一家三人”条缘坐男犯的附加刑。
乾隆五十六年(1791),宫刑延伸适用于谋反大逆案缘坐男犯。当年正月,在林湿谋叛案中,其两子均在十五岁以下,依例应发遣为奴不准出户,改解送进京交由内务府阉割。④三月,因何东山谋逆案,正式定例:凡“反逆案内律应缘坐男犯,除十六岁以上仍照律例办理外,如犯事时年未及岁并不知情者,送交内务府阉割,派在外围当差,不许日久渐移内围。其年在十岁以下者,牢固监禁,俟至十一岁时解京,送内务府办理”。[7]卷53《刑律·贼盗》,838即谋反大逆案之缘坐男犯年十六岁以上者仍处以斩刑,年十六岁以下且不知情者处以阉割之刑。
缘坐男犯被阉割后一般派往内务府外围当差。基于安全考虑,乾隆五十八年(1793)内务府上奏建议,杀死一家三四命凶犯之子嗣阉割后,“年在十五岁以下者,始准派在外围当差,不准日久渐移内闱。如年在十六岁以上者,拟发黑龙江,赏给索伦、达呼尔为奴”。[7]卷77《刑律·人命》,1236嗣后依此议定例,于乾隆六十年(1795)正式辑入律例中。嘉庆二年(1797),定大逆缘坐人犯发黑龙江给索伦、达呼尔为奴例,已经未提及阉割。[8]卷22“嘉庆二年九月乙酉”,第28册,280下-281上嘉庆四年(1799),正式取消“杀一家三四命”、谋反大逆缘坐男犯适用阉割,并于嘉庆六年(1801)正式辑修入律例中。[7]卷77《刑律·人命》,1237;卷53《刑律·贼盗》,840
尽管嘉庆四年已取消宫刑,但不到二十年,清廷又先后恢复对“杀一家三人”、谋反大逆案缘坐男犯适用宫刑,嗣后一直沿用,直至清末重定新律时才废除。道光八年(1828)九月,下谕:“嗣后杀死一家三四命以上之案,审明被杀之家,实系绝嗣,将凶犯之子年未及岁者送交内务府阉割。”[9]卷142“道光八年九月辛亥”,第35册,183上并令刑部纂入例册,循照办理。道光九年(1829),再次定例规定,在被杀之家绝嗣的情况下,对正犯年十五岁以下子适用宫刑:杀一家非死罪三四命以上之案,凶犯之子“其实无同谋加功”者,如被杀之家未绝嗣,十五岁以下者就近充军;“若被杀之家实系绝嗣,将凶犯之子年未及岁者,送交内务府阉割”,“十六岁以上者,仍照前例发极边足四千里安置”。[7]卷77《刑律·人命》,1244在司法实践中恢复对谋反大逆案缘坐男犯适用宫刑,始于道光十二年(1832)。赵金陇反逆,因其“罪大恶极,未便仍留孽种”,其子赵满仔年方七岁,牢固监禁于刑部,待年满十一岁时送内务府阉割。次年,刑部奏请酌改逆案缘坐人犯发遣,议成新条例,于道光十四年(1834)颁定:“反逆案内律应问拟凌迟之犯,其子孙讯明实系不知谋逆情事者,无论已、未成丁,均解交内务府阉割,发往新疆等处,给官兵为奴。如年在十岁以下者,牢固监禁,俟年届十一岁时,再行解交内务府照例办理。”[7]卷53《刑律·贼盗》,843
综上,乾隆四十八年(1783)首次在“杀一家三命”案中适用宫刑,嘉庆四年(1799)取消,至道光八年(1828)又再次恢复,直至光绪末才彻底废止。在此时间内,条例仅规定“杀一家三四命以上”案及谋反大逆案之部分缘坐男犯适用宫刑。在实践中,比照谋反大逆律定罪拟凌迟之正犯子孙也有适用宫刑。⑤如道光十三年(1833),马新民“焚烧抢掠,拒敌官兵”,被判处凌迟,其子迪格子“牢固监禁,俟年届十一岁时,解交内务府阉割发往新疆等处给官兵为奴”。[7]卷5《刑律贼盗·谋反大逆》,250-251又如,同治九年(1870),张汶祥刺杀马新贻,比照谋反大逆问拟,因情节重大,其子年十一岁不知谋情,“应照例解赴内务府阉割,发往新疆给官兵为奴”。[10]
纵观清代“杀一家三人”缘坐男犯适用刑罚的变革,被害一家是否绝嗣一直是至关重要的考量因素。此外,谋反大逆案适用宫刑的缘坐男犯一直都是需满十一岁才行刑,而在道光八年后“杀一家三人”适用宫刑的缘坐男犯凡十五岁以下一体阉割,不用满十一岁才行刑。实践中,甚至缘坐男性胎儿亦须行刑,不过可待三岁时能够自行进食才交由内务府办理。[7]卷8《刑律人命·杀一家三人》,430对幼子实行宫刑,未免过于残忍,但这也正显现了清廷恢复宫刑背后的朴素公平正义观。
二、清入关前法律文化遗存
宫刑是传统肉刑的一种,起源于“杀人者死,伤人者创”的原始同态复仇论。所谓同态复仇,指“虽然露骨地显示出复仇意识,却又将复仇限止在与被害相同的程度上,在这种意义上是种大体公平的而且是规定了限度的制裁手段”。[11]78同态复仇是世界各地氏族社会时期普遍存在的一种形式,在奴隶社会的法律中仍保留其痕迹。最为典型直观的同态复仇,为施加于罪犯肉体的惩罚——肉刑。无独有偶,宫刑并非清代唯一的肉刑。史称:“国初有割脚筋、贯耳鼻之法,乃即古刖、劓之刑。世祖章皇帝诏除之,而天下自是无肉刑。诚不忍其断肢体,剥肌肤,至仁极厚之隆典也。”[12]卷75《刑法略一》事实上,肉刑在清代大量回魂,成为中国古代适用肉刑的又一个高峰期。因而,清代宫刑恢复,首先应置于肉刑回魂的社会背景下考量。
大体而言,清代大抵还长期存在着3种肉刑:刺字、割脚筋、贯耳鼻。
刺字刑长期存在于清代的律例之中。《清史稿·刑法志》载:“刺字,古肉刑之一,律第严于贼盗。乃其后条例滋多,刺缘坐、刺凶犯,刺逃军、逃流,刺外遣、改遣、改发,有刺事由者,有刺地方者,并有分刺满汉文字者。”[4]卷143《刑法志》,4196薛允升亦云:“律云:盗贼曾经刺字。则非盗贼即不刺字,可知。近则条款极多,或刺臂,或刺面。其始不过为盗贼而设,继则非窃盗而亦刺面,且有刺地名及外遣改发等名目。”[13]可见刺字原本只适用于盗窃之类的罪行,经过清代的发展,已经遍及刑律中的大部分罪行,适用范围十分广泛。⑥
割脚筋刑在清代则几经兴废。顺治二年(1645),应刑科都给事中李士焜之请,废除割脚筋之刑。[14]卷18“顺治二年闰六月乙未”,第3册,163下到了康熙末年,清廷又恢复了割脚筋刑。康熙五十二年(1713)十一月,定窃贼割筋例,对在皇城内外偷窃、白昼抢夺以及偷盗牛、骡、驴等物者实行割断懒筋的刑罚。[5]卷二四《刑律·贼盗中》,722康熙五十三年(1714)二月二十四日,又定例:嗣后应将私刨人参为首者割断两边懒筋,为从者割断一边脚筋。[15]据步军统领隆科多奏报京城所获案情,康熙五十六年(1717)四至九月,平均每月割脚筋案例都高于十例。[16]雍正朝又废止了割脚筋例。先是于雍正二年(1724)停止康熙五十二年例。[5]卷24《刑律·贼盗中》,722后又于雍正三年(1725)二月直接下令停止窃贼逃人等割脚筋例,废除康熙五十三年例。[17]卷29“雍正三年二月辛未”,第7册,430下不过,雍正年间仍有其他罪行适用割筋刑,如略人略卖人条。⑦到了乾隆三年(1738)四月,经刑部提准,清廷正式将割筋刑剔除出律例。[18]然而,割筋刑并未就此消失,直至清末仍在司法实践中适用。⑧大体而言,清代割筋刑作为一种法律制度主要适用于盗窃、逃人、偷刨人参、略人略卖人等罪行,后期在司法实践中虽有扩大适用,但仍然主要适用于上述罪行以及教匪、贼盗等,并未大规模适用于其他罪行。莫理循在记述其1894年游历中国的游记中写道:“毁伤肢体的惩罚是普通的刑罚……挑断脚筋或敲碎膝盖骨是常见的刑罚。这种惩罚,常常用于监狱逃犯。”[19]或可为一证。
贯耳鼻虽未被纳入国家律例制度,但偶有适用。顺治元年(1644),摄政王多尔衮下令:“凡强取民间一切细物者鞭八十,贯耳。”[14]卷5“顺治元年五月癸巳”,第3册,58上但是,到了三年四月,便以顺治帝名义下旨:“耳鼻之在人身,最为显著。贯穿耳鼻之刑,永行革除。”[14]卷25“顺治三年夏四月戊子”,第3册,215下可见,贯穿耳鼻作为一种刑罚制度,早在顺治初年已被废除。不过,在实践中仍有适用,且适用于满人、民人。如,康熙三十年(1691),处置乌朱穆秦亲王苏达尼之妻顺附噶尔丹一案各案犯,其中“护卫巴扎尔、伊白葛尔俱从宽免死,并籍没,着穿耳鼻示众,鞭一百”。[20]卷151“康熙三十年五月壬辰”,第5册,676下又如,四十六年,对造成营东失火的二格处以“耳鼻穿箭,游营示众”,待回京后再定罪。[20]卷230“康熙四十六年九月戊午”,第6册,305下再如冯舜生在宣统年间任云南鹤庆县令,“治盗严,有犯赃,虽无多,辄割脚筋、钉耳示众”。[21]这是同时实施了割脚筋及类似贯穿耳鼻的钉耳。
必须指出的是,贯耳鼻、割脚筋均是入关前盛行的肉刑。根据多种文献,后金入关前仍然盛行着多种残忍的肉刑,如贯耳鼻、割耳鼻、割脚筋、裂嘴、以小刀划腰等,带有明显的氏族血族复仇、同态复仇的残余。⑨这些残忍野蛮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式的刑罚,一般适用于贼盗、逃人之类的刑罚。如天命四年(1619),努尔哈赤下令:“微贱者窃大物,黥其耳鼻;窃其次者,射髋箭十;窃小物者,掴脸十次。”[22]23又如天命七年(1622),“硕托阿哥旗下所属牛录之一人,因盗骡,鞭责二十七,刺其耳鼻。汤古岱阿哥旗下尼隆阿牛录之一人,因盗诸申人之鞍辔,乱刺耳、鼻、面、腰等处,杀之”。[22]120皇太极在位期间,肉刑逐渐规范化,贯耳鼻、割脚筋、裂嘴成为常用的肉刑。其时实行“盗马韂者,以小刀划其腰;盗绊者割足筋;盗辔者裂其嘴”。[22]493偷盗其他物品者,常被施以贯耳鼻。如天聪六年(1632),“三人因盗窃箭罩子、雨干套子、皮条、偏缰,各鞭责八十二、贯耳鼻”。[22]661又如崇德元年(1636),道兰因偷盗貂皮等物,鞭一百、贯耳鼻并罢管牛录。[22]712值得一提的是,入关前已开始对缘坐犯适用肉刑。在努尔哈赤看来,盗贼被捕,往往只处罚本身,未及亲人,这种刑罚不足以震慑盗贼,且所盗财物为妻子所取,怎能不处罚妻子。因而,天命七年(1622),其要求:“嗣后,男丁偷盗,则令其妇足蹈炽炭,头冠红锅,刑而杀之。倘惧此刑,则各劝其夫,不从,即首告之。”[22]205同样地,为了威慑逃人,崇德三年,“将逃犯巴哈塔杀之,其妇女鞭五十,割脚筋”。[23]
贯耳鼻、刺耳鼻和黥耳鼻本质上应是同一种刑罚,都是用箭刺贯穿耳、鼻。天命七年七月,诸贝勒曾议定废止刺耳鼻之刑。[22]140然而,刺耳鼻仍在频繁使用中。次年出现了以银赎刺耳鼻刑的案例:家奴偷盗仓粮,奴与主子均拟鞭七十三、刺耳鼻,主子罚银九两以赎刺耳鼻之刑。[22]173入关后,清廷曾一度废除贯耳鼻、割脚筋,为史臣所称颂。然而与入关前一样,不久便又死灰复燃。可见,这种具有氏族时代同态复仇残留的肉刑,在清代仍有其滋长的土壤。
此外,清代刺字刑亦蕴含着满洲特性。一般认为清代刺字刑沿袭自明律。⑩然而清代适用刺字刑的罪行数量远远高于前代,且规定繁复。清代刺字内容规定精确,明确区分了犯罪情节、发遣地。如清末谋反大逆缘坐遣犯左脸刺“缘坐”、右脸刺“伊犁”,缘坐发驻防为奴者,则只刺“缘坐”,不用刺地名。[24]卷2《刺字条例》又如,同是盗窃,民人、旗人刺“窃盗”,回人刺“回贼”。[24]卷2《刺字条例》这种精确的刺字内容无疑十分便于有司管理犯人,因而被视为一种行政管理手段。[25]这种特质很可能来自入关前管理官牛的思路。努尔哈赤时期,在辽东城、牛庄分别设诸申都司一人、汉都司一人管理官牛,要求将“官牛烙盖印记,并造册登记牛之毛色、牛身大小及交牛之人姓名”。[22]125对罪犯刺字以便管理,与对牛马骆驼烙盖印记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还有,清朝对“杀一家三人”与谋反大逆缘坐男犯适用宫刑的历史时间,正是清廷“满洲意识”高涨、重塑满洲历史根源性活动结束的前后。不难看出,清代肉刑的恢复与大规模的使用,乃是入关前法律文化的延伸。
三、传统中原法律文化因素
自汉文帝废肉刑后,废除肉刑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因而,除了五代起恢复刺字刑,其他肉刑大多在清之前都未在立法中正式恢复。那么宫刑等肉刑在清代恢复适用且不断扩大适用范围,除了入关前法律文化的影响外,与中原地区的传统法律文化是否亦有关联?
首先,清代鼓吹肉刑的思想影响较大,恢复肉刑的舆论阻力极小。对正犯、缘坐犯适用肉刑,虽然本就是满洲法律文化固有的因子,但并不意味着入关后必然能够继续保留甚而广泛适用。
其一,东汉以降,每当名儒、大臣力主恢复肉刑时,常伴随着强烈反对的声音,而清代的情况则完全不同。
清前期,残忍野蛮的肉刑曾一度遭到汉人士大夫的反对。顺治二年(1645),刑科都给事中李士焜奏请除割脚筋法,指出“从来按律定罪,情法庶可两协”,而割断脚筋致终身残疾甚而伤生,且“稽之于律,既未合例;揆之于情,亦觉太刻”。[26]康熙年间,王夫之亦强烈批判宫刑道:“今夫殄人之宗而绝其世,在国曰灭,在家曰毁。罪不逮此,而绝其生理,老无与养,死无与殡,无罪之鬼,无与除墓草而奠杯浆。伤哉!宫乎!均于大辟矣!”[27]他还曾数次论及肉刑不可复,强调“肉刑之不可复,易知也”。[28]在李士焜、王夫之的眼中,肉刑违逆人情、刻薄寡恩,不可施行。然而,这类言论迅速陷于沉寂,直到清末才再次出现。
与此同时,理学家们又再次呼吁恢复肉刑。颜元认为必须恢复宫刑,究其根本乃因“宫壶之不可无妇寺,势也,即理也”。[29]朝廷忍心阉割无罪之人充当宦官,却不忍阉割有罪之人,可谓“仁而愚”。其弟子李塨主张:“仍令以今之五刑为律,但去其烦苛,增其不足,别附肉刑数条,以禁贪暴、止淫邪而厉廉耻,使天下不得议吾之非,庶存古圣人明刑之道,而令行禁止,教化可大行耳。”[30]卷13《刑罚第九》,91李塨还设想了一套恢复肉刑的方案,如对贪污者实行墨刑,对贼盗实行墨刑和刖刑,对奸淫者适用宫刑等。值得注意的是,他还建议,可由罪犯自行选择是否适用宫刑:“有罪入于绞,而情可矜者可宫以宥之也,有流于烟瘴边外而愿宫以自赎者,亦可听其愿而宫之也。”[30]卷13《刑罚第九》,93显然,在颜、李二人看来,肉刑是三代圣王之制,乃仁德之制,应当恢复。
已见的文献中,乾隆、道光年间先后恢复宫刑,以及割脚筋、刺字等肉刑的不断扩大适用,不仅未听到反对的声音,反而还有颂赞之论。薛允升曾赞割筋法道:“虽则过严,究使人不敢犯窃之意,亦古法也。”[31]卷28《刑律之四·贼盗中之二》并批判后来一味从宽,导致窃贼不知戒惧。他还认为,反逆正犯子孙发遣、禁出户的旧例与阉割之新例,目的均是“不使逆恶余孽仍得窜籍为良民故也”。[31]卷2《名例律上之二》在其眼中,宫刑与禁止出户的用意等同,自然无须批判。《清朝通志》的撰著者也认为“汉魏以来区区诏除肉刑与议复肉刑,皆未喻仁至义尽之旨者也”,赞颂乾隆帝复宫刑为“法外之仁”,“适符协中之治,又有为亘古之所不逮者”,“有以杜亿万年复肉刑之议矣”。[12]卷75《刑法略一·刑制》
其二,发展至清中期,统治者的法律思想已发生明显的转变。入关后初期,为了统治中原大地,统治者积极地吸纳前代的法律文化,沿袭明制。废除肉刑,可谓是该历史背景下的产物。然而随着政权的稳固,统治者的理念也发生了转变。康熙帝认为“盖法令禁于一时,而教化维于可久”。[20]卷34“康熙九年冬十月癸巳”,第4册,461上因而主张以教化为先、尚德缓刑、慎狱恤刑。雍正帝则清晰地认识到康熙宽缓政策带来的积弊,强调“且猛做去,宽之一字乃上天之恩,若容宽时得有可宽之日,乃尔我君臣之大福,天地神明之殊恩也”,主张以严猛纠宽。[32]卷125之5《硃批鄂尔泰奏折》“雍正五年九月十六日”,387下乾隆帝也秉承了明刑弼教的思想,与其父的观点较为一致。[33]
事实上,乾隆帝奉理学思想为圭臬,将理学之天理、人情作为纂修律例的准绳。他命律例馆汇集编纂律文及递年奏定成例,应“揆诸天理,准诸人情,一本于至公,而归于至当”。[34]卷首,《御制〈大清律例序〉》,5而理学之集大成者朱熹不仅是明刑弼教法律思想的再阐发者,也是肉刑的重要鼓吹者。他曾言道:“所谓墨、劓、剕、宫、大辟,五刑之正也,所以待夫元恶大憝、杀人、伤人、穿窬淫放,凡罪之不可宥者也……今徒流之法既不足以止穿窬淫放之奸,而其过于重者则又有不当死而死,如强暴赃满之类者。苟采陈群之议,一以宫、剕之辟当之,则虽残其肢体,而实全其躯命,且绝其为乱之本,而使后无以肆焉。”[35]
综上,无论是朱熹抑或清代的理学家无疑都为清廷恢复宫刑等肉刑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其次,宫刑的恢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传统立嗣观念在清代达到顶峰。立嗣,作为传统宗法制度重要的一环,关涉香火延绵、宗祧继承,历来深受统治者关注。尤其是宋代以降,新型宗族社会兴起,立嗣的重要性更是进一步凸显。除了理学家们纷纷阐释立嗣观外,国家也通过增修律令以规范立嗣行为。清代“立嫡子违法”条的变化是历代之最。其不仅延续前代的相关条文、明确前代法律精神,而且增加了数个条款,使得该条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细密。其一,延续明律异姓不可为后的规定,并明确了即使无子亦不可收养三岁以下小儿为嗣。顺治三年编修的《大清律例》,在收养三岁以下弃儿的规定中,增加了“但不得以无子遂立为嗣子”一语。[34]卷8《户律户役》,409乾隆二年(1737),刑部奏请定例:“其收养三岁以下遗弃之小儿,仍依律即从其姓,但不得以无子遂立为嗣,仍酌分给财产,俱不必勒令归宗。”[34]卷8《户律户役》,409其二,出台独子出继禁例。乾隆四年(1739),刑部核议定禁独子出继条:“凡民间本非独子,方准出继。如止一子,虽系期功得继,亦不得过房。如贪产不顾宗祀,事发,除继子断归宗外,本生父母照不应重律,杖八十。倘独子借已继为名,恋财不念本生者,除改正归宗,仍照奉养有缺律,杖一百。”[6]卷106“乾隆四年十二月庚辰”,第10册,590下-591上其三,确立独子兼祧制。乾隆四十年闰十月,初步赋予独子兼祧合法性,是中国历史上国家层面首次真正承认独子兼祧制。[6]卷995“乾隆四十年闰十月己巳”,第21册,301下-302上乾隆四十三年,纂定成例:“如可继之人亦系独子,而情属同父周亲,两相情愿者,取具同族甘结,亦准其继承两房宗祧。”[5]卷8《户律·户役》,410至此,独子兼祧制正式确立,独子应是同父周亲之内,大功、小功、缌麻及远房、同姓等均不在列,严格限制选立对象,确保血缘的纯正。
清代增改相关“立嫡子违法”条例大多发生于乾隆年间,尤其是独子兼祧制出台的时间与适用宫刑的时间相距仅五年。这些新增条例均是基于相同的伦理思想:注重宗祧继承,试图确保宗嗣延绵。这种理念,在乾隆帝下诏修改“杀一家三人”缘坐男犯适用刑罚时屡屡展现。乾隆指出,被害人全家俱被杀害,子嗣断绝,而凶犯之子尚能存活于世,为其延绵后嗣,“于天理人情实未允协”。[6]卷1016“乾隆四十一年九月丁丑”,第13册,633上他又指出,凶犯之子长大后,仍能婚配,传宗接代,“将何以昭示平允,并何以慰死者之心”?[6]卷1093“乾隆四十四年十月丙寅”,第22册,668上因而他强调:“此等凶残之犯,既绝人之嗣,不可复令其有嗣,自当不留遗孽,方足蔽辜。”[6]卷1328“乾隆五十四年五月己巳”,第25册,989上总之,乾隆帝认为,从天理、人情着眼,绝人子嗣者理应也绝嗣,所以一再调整“杀一家三人”缘坐男犯之适用刑罚。
至于宫刑与子嗣延绵之关系,在道光帝主张恢复对谋反大逆缘坐男犯适用宫刑的言论中,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当时刑部仅建议逆案缘坐人犯发遣,未及宫刑。道光帝指出:“其子孙不概予骈诛,贷其一死,已属宽之又宽。若如刑部所议,到配后禁其婚娶,不过徒托空言,有名无实,必致孽种潜生,殊非所以示惩创。”[7]卷53《刑律·贼盗》,842宫刑既不剥夺生命,又可防止罪犯传宗接代、“孽种潜生”,自是不二之选,正如乾隆帝所强调的,适用宫刑乃“俾凶恶之徒不得复留余孽,以示除恶务尽,仍寓法外施仁之意”。[6]卷1301“乾隆五十三年三月己丑”,第25册,509上
仁井田陞指出,在发展程度较高的中国刑罚中,同态复仇可表现为“使刑罚与实际受害的程度相对应”。[11]79从乾隆帝的诏令不难看出,由充军改为斩立决、斩监候,到改为将正犯之子照所杀之数拟斩立决,再到改作发遣附加宫刑的过程中,“杀一家三人”缘坐男犯之刑罚一直体现着绝人子嗣者应绝嗣的同态复仇理念。可以说,清代宫刑正是一种从子嗣延绵角度着眼的同态复仇。
在此之前,清代已经在“犯罪存留养亲”条新增了一种类似精神的条例。雍正二年(1724)十月,下谕刑部:“奏请免死留养,然亦须查明被杀之人有无父母、是否独子。若系亲老又系独子,一旦被杀,以致亲老无人赡养,而杀人之人反得免死留养,殊与情理未协。”[17]卷27“雍正二年十二月丁丑”,第7册,413下依此,律例馆于次年奏准,载于律后,乾隆五年(1740)纂为定例。[5]卷4《名例律上》,243-244乾隆二十一年(1756),又“通行各督抚,凡遇独子杀人之案,查明被杀者之父母别无子嗣,不必计年老与否,即照例治罪,不准声请留养”。[6]卷515“乾隆二十一年六月癸丑”,第15册,505下嗣后经乾隆五十四年(1789)、嘉庆六年(1801)、嘉庆二十四年(1819)、道光四年(1824)增修,形成条例如下:“杀人之犯,有秋审应入缓决、应准存留养亲者,查明被杀之人有无父母,是否独子,于本内声明。如被杀之人亦系独子,但其亲尚在,无人侍奉,不论老、疾与否,杀人之犯皆不准留养。”即是说,杀害独子、断人子嗣而导致被害人父母无子嗣孝养者,其父母也不当享受子嗣的孝养,不可适用“留养”。可见,“杀一家三人”及“犯罪存留养亲”条的上述变化,均是从子嗣延绵角度着眼的同态复仇。
综合上述分析不难看出,清代恢复宫刑、广泛适用多种肉刑并非偶然,既有入关前法律文化的遗留,亦有儒家法律思想的要素。
余 论
由于清承明制,学界一般认为清代律例亦是儒家文化的体现,乃清王朝汉化的表现。如瞿同祖先生曾指出,清代条例变化虽多,但“都不违背儒家礼教原则,亦即不违背中国的道德和法律传统,可以说条例的变化仅仅是在道德和法律传统范围以内的变化,因而保持了延续性”。[36]又如张仁善亦认为:“清朝对明朝法律的继承和接受,完全是民族文化同化的结果;在有关等级伦理的例文上,清律、例比明律走得还远。”[37]新清史专家则强调满汉畛域。罗友枝否定汉化论,强调清代的满洲特性,认为清朝统治取得巨大成就的关键是融合了内亚地区和汉族地区意识形态等因素,且不同民族地区实行不同政策,将满人和汉人视作泾渭分明、非此即彼的关系。欧立德虽然同意汉化论,但更关注满洲认同,强调八旗与民人在司法上的不平等。[38]
从清代律例的整体特征着眼,汉化说无疑更为合乎历史实情,如从具体条例着眼却又不尽然;从肉刑相关条例及司法实践层面着眼,新清史学者强化清朝满洲特性、强调满汉之别的观点,无疑背离历史事实。表面上看,割脚筋、贯耳鼻的直接法律渊源为入关前的满洲法律文化,宫刑、刺字则是中原王朝固有刑罚,并未存在于入关前的满洲刑罚体系。然而进一步探究则不然。
首先,入关后,割脚筋刑的法律精神发生变化,不再是单纯的肉体惩罚。雍正元年(1723)四月,两广总督杨琳以“恐释放回家,凶性不改,仍复纠伙行劫,即再捕治正法,而良善已被其害”为由,未经奏准,割断129名盗犯两肢懒筋,“使其不能跑走,即终身不能为盗,既全其性命,复制其凶性,觉恩法两尽”。[32]卷14《硃批杨琳奏折》“雍正元年四月初二日”,66下-67上雍正皇帝朱批道:“朕深嘉之。果与民生有益,因地制宜,于例款之中,斟酌损益,只管请旨施行。”[32]卷14《硃批杨琳奏折》“雍正元年四月初二日”,67上此时,官员实施割脚筋刑的思路,是强调其保全性命且令罪犯戒惧之作用。
其次,除了刺字刑带有满族特性外,清代恢复宫刑,亦不能排除少数民族特性的影响。东汉以降曾经实施宫刑的政权,均是少数民族政权:北魏鲜卑、辽契丹、清满族。这种巧合不禁令人怀疑其少数民族因素。北魏的规定如下:“大逆不道腰斩,诛其同籍,年十四已下腐刑,女子没县官。”[1]2874将宫刑适用于“大逆不道”罪行的缘坐男犯。“杀一家三人”自汉代起已属“大逆不道”罪行。可以说,清代宫刑适用范围近似北魏。富谷至曾指出,宫刑虽是中国自古以来的刑罚,然而北魏“神嘉律中的腐刑与绞杀一样,可以说是胡族的刑罚,是胡汉融合的一个环节”。[39]推而论之,清代宫刑背后或许亦有满族因素,可能也有满汉融合的可能性。
最后,在刑罚适用上,上述肉刑都表现出了满汉互化的倾向。陈兆肆从割脚筋刑适用对象的变化入手,认为“清代满汉法律一体化的进程,实际上是互涵互化型的,而非单向度的一方同化另一方”。[40]就肉刑的适用对象变化而言,此说无疑是正确的。宫刑、刺字两种中原王朝古代已有的刑罚,在清代统一适用于旗人、民人。割脚筋、贯耳鼻两种入关前的满洲刑罚,在入关后适用对象亦拓展至民人。大体而言,在这些肉刑的适用中,旗人并没有特殊的豁免权。如《刺字集》收录了数十条免刺条例,涉及旗人仅有“旗人正身逃脱者”“旗人初次犯窃罪”等数条。[24]卷3《免刺条例》
总而言之,部分满洲法律在入关后得以延续,被纳入条例中,同时适用于旗人、民人,精神内容也渗入了儒家文化;而中原王朝固有的法律被清朝承袭后,也存在满汉文化相互涵化的现象。在任何历史时期,立法都必须适应一国当时的道德文化水准,刑罚体系也必然适应一国当时的刑法文化。清王朝统治着多个民族,这些民族的道德文化水准、刑法文化各不相同。这种历史事实,决定了清朝必然以更为先进的汉文化为主、涵入其他文化为辅,其本身未彻底褪去的氏族部落特质也难免被涵入。因而,彻底否定清朝汉化论,显然并不符合历史实情,而忽视清代律例中的满洲元素亦不可取。满汉互相涵化,是清代多民族国家构建应有的题中之义。
注释:
①参见沈家本:《历代刑法考·刑法分考六·宫》,邓经元、骈宇骞点校,中华书局,1985,第190-191页。
②参见李甲孚:《中国法制史》,联经出版社,1988,第170页;李明德:《中国古代的复肉刑之争及其对刑罚制度的影响》,《黄淮学刊(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宇培峰:《关于肉刑体系的沿革及废复之争》,收于韩延龙:《法律史论集》第3卷,法律出版社,2001,第113页;富谷至:《从终极的肉刑到生命刑:汉至唐死刑考》,周东平译,收于范忠信、陈景良:《中西法律传统》第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1-48页;陈银珠:《中国肉刑的废除过程对死刑废除的启示》,《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③参见瞿同祖:《瞿同祖法学论著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第426-442页。
④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七一“乾隆五十六年正月己亥”,《清实录》第26册,中华书局,1986,第396页。行文中提到“例应送京阉割”,然而此时谋叛缘坐犯适用宫刑并未定例。
⑤也有未适用的,如道光十二年,尹老须比照谋反大逆律凌迟处死传首示众,家属免其缘坐。参见祝庆琪:《续增刑案汇览》卷四《礼律祭祀·禁止师巫邪术》,尤韶华点校,法律出版社,2007,第210-211页。
⑥参见于雁:《清代刺字刑考略》,《历史教学》2008年第12期。
⑦雍正五年(1727)十二月初一日,署理贵州布政使印务按察使赫胜额奏论捆掠贩卖最为黔省之患,言道:“缘捆贩与兴贩皆借窝隐之人为之贩卖,实与开窑子无异,若无此辈窝隐,自无贩卖之事,定例止将伊等割断脚筋……请嗣后窝隐贩卖之人,照开窑子光棍例,将为首之人拟斩立决;获送牵合及用银兴贩之人,俱照为从例,发往宁古塔等处给披甲人等为奴。”参见《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一九三《朱批赫胜额奏折》,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2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第194页下。
⑧参见陈兆肆:《清代“断脚筋刑”考论:兼论清代满汉法律“一体化”的另一途径》,《安徽史学》2019年第1期。
⑨参见张晋藩、郭成康:《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第529-530页;王千石、吴凡文:《清入关前的法律文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第116页;杨明:《中国少数民族法史通览》第4卷《满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赫哲族》,陕西人民出版社,2017,第48-49页。
⑩参见南玉泉:《清朝的墨刑制度与沈家本对于墨刑的研究》,见中国政法大学、浙江省湖州市人民政府合编的《沈家本与中国法律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册)》,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第567-578页;于雁:《清代刺字刑考略》,《历史教学》2008年第12期,第15-19页;张本照:《清代的刺字刑》,《文史知识》2019年第12期,第75-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