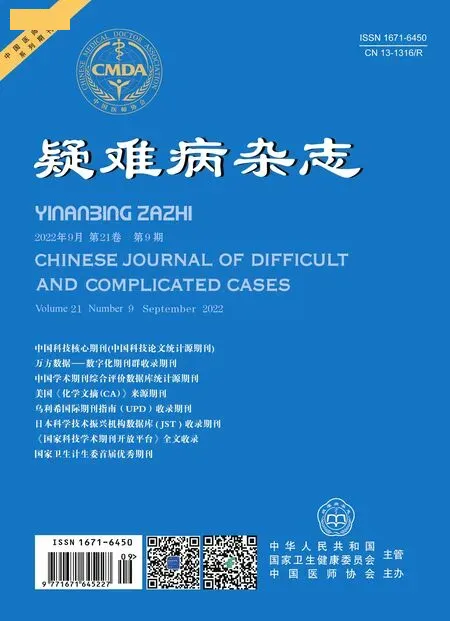胎儿型肺腺癌的研究进展
周瑞婷,李文新,何桂媛,黄婷苑综述 曾凡军审校
胎儿型肺腺癌(fetal adenocarcinoma of the lung,FLAC),因其由类似于胎儿肺的管状腺体构成而得名。FLAC是肺腺癌中的一种罕见类型,发病率仅占肺癌的0.1%~0.5%。关于FLAC的文献资料以小样本的病例报道为主,缺乏系统性的综述。随着分子检测技术和方法的出现,人们对FLAC的认识逐渐深入,其定义和分型也不断更新,但尚存争议。本文从FLAC的定义、组织病理学、分子遗传学、临床特征和诊断、治疗及预后等方面进行综述,报道如下。
1 FLAC的定义
早在1945年,Barnard等报道了一类由间充质成分包绕上皮成分构成的、形似胎儿肺组织的肿瘤,并将其命名为“肺内胚胎瘤”。1961年,Spencer将其命名为肺母细胞瘤(pulmonary blastoma,PB)[1]。20世纪80年代,Kodama等发现在PB中存在着一些“异类”,它们仅由排列整齐类似于胚胎的腺上皮细胞组成,缺乏间叶成分,并于1984年首次将这类肿瘤命名为胎儿型肺腺癌(FLAC)[2]。1999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将FLAC归类为肺腺癌的一种变异型;但同时,它仍被视作PB的一种亚型,并被称为“上皮型肺母细胞瘤”。随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指出,胎儿型肺腺癌的发病机制、临床表现、组织病理学和预后与PB不同[3-4]。在2011年由国际肺癌研究协会、美国胸科学会和欧洲呼吸学会共同制定的国际多学科肺腺癌新分类将FLAC归为浸润性腺癌的变异型,并进一步分为低级别 (low-grade fetal adenocarcinoma, L-FLAC)和高级别(high- grade fetal adenocarcinoma, H-FLAC)2类[5]。但这种分类方式存在争议,Morita等[6]认为,虽然L-FLAC和H-FLAC都具有胎儿肺样形态,但二者在免疫组化和基因组学中的相似度并不高,这表明它们可能是形态相似但起源不同的2种独立肿瘤,而非分化程度不同的相关肿瘤。2015年WHO肺癌分类中将FLAC作为肺腺癌的一种独立亚型列出[7]。对此,也有研究者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FLAC只能作为一种形态学类型,因为各个研究中病例的免疫组化和基因突变特征较为分散。Zhang等[8]回顾性分析了我国45例FLAC病例,除β-连环蛋白(β-catenin)外,未发现其他特征性或有诊断价值的标志物。笔者认为,过去关于FLAC的研究受限于样本量少,以及各独立研究中的方法学差异,可能不足以揭示FLAC特征性的分子遗传学改变。此外,过去的研究方法多限于免疫组化及单个基因的检测,准确率高但检测范围有限,随着全基因组测序等高通量检测技术的广泛应用,有望找到特征性的分子遗传学改变。与此同时,常规肺腺癌的基因突变(如KRAS、EGFR等)在FLAC病例中极少出现,并且FLAC PD-L1和PD-1表达低,对免疫治疗反应差,从基因诊断和治疗2个方面来看,将FLAC归为肺腺癌的一种独立亚型是合适的。
2 FLAC的病理学特征
FLAC瘤体通常孤立、边界清楚且多为周围型,偶有肺门支气管受累[9];切面呈白色或棕褐色,可伴出血或囊性变;镜下可见癌组织由复杂的、多分支的管状腺体构成,其内衬富含糖原的、无纤毛的柱状或立方状细胞,类似于胎儿肺小管;胞质透明,呈嗜酸性,胞核透亮,可见特征性的核上或核下空泡[10-11]。L-FLAC以低度核异型性和“桑葚体”的形成为特征,“桑葚体”是指在腺体基底部或腔面上,由鳞状细胞样细胞形成的实性球体。H-FLAC则缺乏“桑葚体”形成,并且具有明显的核异型性,核仁明显,核分裂相多见[12]。L-FLAC通常为纯组织学模式。最近,Liu等[13]和Xiong等[14]各自报道了1例混有肺原位腺癌的L-FLAC和1例混有大细胞神经内分泌癌成分的L-FLAC,这是目前为止仅有的例外。相比之下,H-FLAC通常具有至少50%的胎儿肺形态,同时瘤体中也存在贴壁型、微乳头状和实心型等其他常见的肺腺癌类型,甚至混有非肺癌类型(如肝样腺癌等)[12,15]。在免疫组化特征上,L-FLAC和H-FLAC最显著的差别在于β-catenin和P53的表达。L-FLAC存在β-catenin的异常核/质表达,这一特征在P53低表达的肿瘤“桑葚体”中更明显;H-FLAC则与传统肺腺癌相似,β-catenin主要表达于细胞膜,且通常过度表达P53[12]。此外,H-FLAC中也表达甲胎蛋白和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3,这些免疫组化特征可用于H-FLAC的辅助诊断[10]。
3 FLAC的分子遗传学特征
3.1 EGFR、KRAS 常规肺腺癌的EGFR突变频率为32%~64%,KRAS突变频率为13%[16],FLAC中KRAS和EGFR的突变率非常低。这些常规肺腺癌中的主要驱动基因突变似乎与FLAC无关,提示FLAC是一种具有独特分子特征的、独立的肺腺癌亚型[9]。
3.2 P53 H-FLAC存在P53基因的过度表达,其较高的突变频率与常规肺腺癌相似;而L-FLAC的P53低表达,有报道称L-FLAC良好预后可能与其低P53基因突变频率相关[6, 12]。H-FLAC与L-FLAC的P53基因的差异表达是鉴别二者的重要依据。
3.3 β-catenin Wnt信号通路与许多肿瘤的发生密切相关,Wnt信号通路的激活导致转录因子β-catenin移位至细胞核调控靶基因表达。在正常情况下,腺瘤性息肉病蛋白(adenomatous polyposis coli protein,APC)会降解多余的β-catenin。β-catenin或APC的突变可导致β-catenin在核内积累,这将激活癌基因如c-myc和细胞周期蛋白D1[17]。Nakatani等[18]发现大多数L-FLAC在β-catenin基因的第3个外显子磷酸化位点上存在突变,该突变会干扰β-catenin的降解,导致其在细胞核/质中积累。而在β-catenin野生型的L-FLAC病例中,β-catenin的细胞核/质表达异常可能由APC或PTEN的突变失活引起。同时,在上述研究中,H-FLAC病例β-catenin基因均未突变。此外,β-catenin的突变在普通肺癌中少见[12, 19],因此,β-catenin基因突变可以作为L-FLAC的诊断工具。
3.4 DICER1 DICER1编码来自RNaseⅢ家族的核糖核酸内切酶,在微小RNA生产中起重要作用[20]。DICER1基因突变导致机体易患各种肿瘤,称为DICER1综合征。Wu等[21]报道了1例DICER1突变(T1180*)携带者患有L-FLAC、Sertoli-Leydig细胞瘤和家族性多结节性甲状腺肿。随后,在Li等[10]研究中发现4例L-FLAC病例均存在DICER1突变,这表明L-FLAC可能是DICER1综合征的具体表现之一,并且DICER1突变可作为诊断L-FLAC的分子标志物之一。
此外,Caruso等[22]在肝癌相关研究中发现DICER1突变和β-catenin突变之间存在显著关联,这2种突变可能在肝脏肿瘤发生中具有协同作用。在Wu等[21]和Li等[10]报道的DICER1突变的L-FLAC案例中也存在β-catenin突变,但二者对L-FLAC的发生是否有协同作用,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揭示。
3.5 TSC2 结节性硬化症复合亚基2(tuberous sclerosis 2,TSC2)是一种抑癌基因,Fu等[23]通过二代测序在1例H-FLAC中发现BRCA2和TSC2(F408V)2个基因突变,随后又有研究者在L-FLAC病例样本中检测到另一个TSC2(R1032*)突变[10]。根据Jozwiak等[24]的研究,TSC2突变可能会消除其抑制Wnt/β-catenin通路的能力,这表明TSC2和β-catenin突变可以协同激活L-FLAC中的Wnt/β-catenin通路。由于β-catenin突变广泛存在于多种肿瘤之中,相比之下,TSC2的突变共存对L-FLAC诊断更具特异性。
3.6 KMT2C PARP是一种DNA修复酶,PARP抑制剂可抑制肿瘤细胞DNA损伤修复,增强肿瘤细胞DNA对损伤因素的敏感性,尤其在BRCA基因突变导致的同源重组修复缺陷的细胞中效果显著[25]。Chang等[26]研究发现,KMT2突变在非小细胞肺癌(non 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中频繁发生,其高突变负荷和低生存率相关,并且KMT2C/D突变会提高NSCLC对PARP抑制剂的敏感性,这表明高频KMT2C/D突变可作为NSCLC和其他BRCA突变罕见的癌症PARP抑制剂治疗中的生物标志物。Suzuki等[11]在对16例H-FLAC样本的全外显子基因测序中发现,KMT2C呈现出较高突变率(6/16),由此,推测PARP抑制剂具有治疗KMT2C基因突变的、包括H-FLAC在内的NSCLC的潜能。
3.7 MYCN MYCN是原癌基因MYC家族的成员。它编码转录因子MYCN,协调胚胎发育的基本过程。Li等[10]和Zhang等[2]先后在L-FLAC中发现了MYCN的错义突变,提示这种错义变体可能与L-FLAC的发展有关,表明MYCN也可以作为L-FLAC辅助诊断的分子标志物。
4 FLAC的临床特征和诊断
FLAC发病率占原发性肺部肿瘤的0.1%~0.5%,病死率低于15%,发病年龄高峰在30~50岁[27-28]。本病无特异性临床表现,25%~40%的患者表现为无症状起病,大多数病例是通过胸片偶然发现而诊断。咳嗽、胸闷胸痛是最常见的症状,也有咯血、呼吸困难、盗汗的报道,罕有胸腔积液[8, 28-29]。影像学表现也无明显特异性,常见位于周边界限清楚的膨胀性肿块,大小为 2~12 cm,具有周边放射不透性,其内可存在液化坏死区,很少累及周围肺实质,无明显空气支气管征[30-31]。L-FLAC和H-FLAC 有不同的临床特征。L-FLAC属低度恶性肿瘤,多见于无吸烟史的中青年女性,确诊时常处于Ⅰ~Ⅱ期[2]。H-FLAC多见于有重度吸烟史的中老年男性患者,2项关于H-FLAC的大型研究数据显示,男女比例为33∶3(92%为男性),吸烟率为93%[6]。相较于L-FLAC,H-FLAC恶性程度较高。确诊时常已出现区域淋巴结或远处转移,目前已有H-FLAC卵巢、眼睛和皮肤转移的病例报道[32-33]。FLAC的诊断主要依据术后切片病理学形态特征和免疫组化特征,术前很难做出明确诊断[8, 31]。部分H-FLAC瘤体中混合其他组织学类型,根据WHO规定,当胎儿组织占优势(>50%)时可诊断为H-FLAC。值得注意的是,有报道称约20%的H-FLAC合并高级别神经内分泌癌,因此在诊断H-FLAC的同时也应警惕高级别神经内分泌癌[30]。
5 FLAC的治疗及预后
手术治疗仍然是FLAC的标准治疗方式,手术方式以根治性肺叶切除加淋巴结清扫为主,亚肺叶切除在FLAC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上尚缺乏足够证据。Ⅰ~Ⅱ期L-FLAC常单用手术治疗,辅助放疗和化疗对早期L-FLAC疗效甚微,通常用于H-FLAC及较为晚期患者的治疗,然而目前尚无标准或推荐的化疗方案,现已报道的进行化疗的FLAC病例多数选择以铂类为基础的化疗方案[8, 34]。多项研究表明,术前新辅助化疗可降低肿瘤分期[35-36]。有研究报道1例T3N0M0患者接受了3个周期的依托泊苷联合顺铂方案治疗后,计算机断层扫描评估该患者的肿瘤缩小了12%[35]。Li等[10]报道1例L-FLAC多灶性骨转移(pT2aN2M1c)的患者接受了姑息性化疗,随访期内未发现疾病进展。上述研究表明,辅助化疗可使H-FLAC和晚期L-FLAC患者明显获益,因此,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选择手术联合化疗来延长患者生存期。目前尚无免疫治疗和靶向治疗有效的报道,Suzuki等[11]对16例H-FLAC患者进行外显子测序,结果显示PD-L1表达和肿瘤突变负荷率较低,表明H-FLAC对免疫治疗反应差。根据上述FLAC的分子遗传学特征,推断KMT2C、DICER1和TSC2可能是FLAC的潜在治疗靶点,PARP抑制剂可能是潜在的治疗FLAC的靶向药物。
FLAC的不良预后因素包括淋巴结转移和肿瘤复发,肿瘤的大小可否作为不良预后因素一直存在争议。第 8 版 UICC TNM 分类中强调以肿瘤的侵袭性而不是肿瘤大小来评估T分期[37]。然而,目前尚无FLAC肿瘤大小与其预后相关性的研究。Suzuki等[5]研究表明,H-FLAC的存活率显著低于除微乳头状亚型外的所有其他组织学亚型,不仅如此,混合高级别胎儿型成分(>5%)的其他类型肺癌的5年生存率也相对较低,因此,Suzuki等指出即使胎儿型成分不占优势,病理医师也需报告其存在,因为这种组织成分对患者预后有非常大的影响。相比之下,L-FLAC预后良好,其5年总生存率可达80%[2]。
6 小结与展望
目前对于FLAC的各项研究存在病例数少、诊断及分类标准不统一等问题,但这些研究也提供了关于FLAC的一些重要信息,同时也明确了FLAC后续的研究方向,通过免疫组化和全基因组测序等方法高效率地检测肿瘤存在的基因突变和特异性标志物,有助于明确FLAC的起源、分类和发病机制,找到合适的靶向基因,从而进一步实施个体化、针对性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