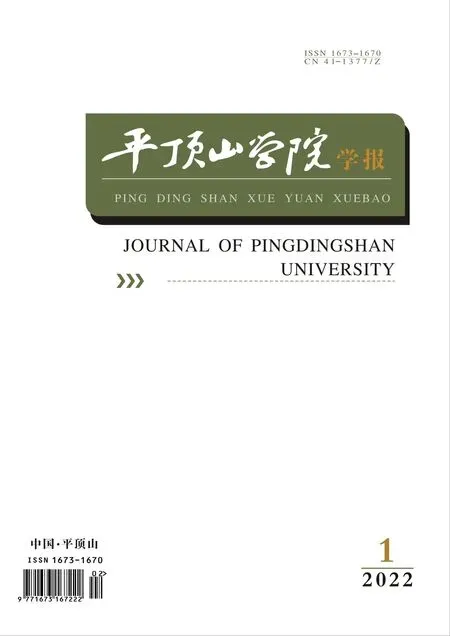从外官朝觐之制看清朝行政制度的简化
孔祥文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 中华文史网,北京 100080)
清朝建立后,在明朝原有制度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完备且独具特色的国家行政管理制度,但是清朝并不是把所承明制原封不动地照搬执行,而是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地改进,使之更适应本朝的实际情况。对于不适用的管理制度,清朝或进行简化,或直接废止。外官朝觐之制的废除就是清朝对国家行管理制度进行简化的一个例证。
一、外官朝觐之制的确立与作用
明朝的考绩制度主要分为考满和考察两种。考满是论全体官员“一身所历之俸”,具体办法是“三年给由,曰初考;六年曰再考;九年曰通考。依《职掌》事例考核升降”[1]1721。考察是“通天下内外官计之”[1]1721,又分为京察和外察,京察是对在京官员的考察;外察又称朝觐考察,指对京师以外的官员进行考察。
清初也对官员进行考绩。清朝的官员分为文官和武官,文官又分为在京文官(京官)和在外文官(外官)。对京官的考绩叫京察,对外官的考绩叫大计,对武官的考绩叫军政。与京察、大计和军政并行的还有考满。虽然清承明制,但并未原样照搬下来。《康熙会典》将康熙朝(1662—1722)以前对于官员的考核制度进行了概括:“内外官员考满之外,复有考察。外官考察,详见‘朝觐’。其京官考察,以六年为期,俱于二月内举行。”[2]109正因为如此,《康熙会典》把外官考绩列入“朝觐考察”的条目之下。而在《雍正会典》中,把“朝觐”列为单独条目,大计则列于“大计考察”的条目之下。这样记载是因为朝觐之制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被废除,但旧制仍载于其中,以备稽考。
据《雍正会典》记载,“国初,外官三年一朝,循例考察。……凡外官朝觐,顺治四年定,三年一朝。朝毕,吏部会同都察院、吏科、河南道考察,奏请定夺。来朝官引至御前,宣读诫谕,仍各赐敕一道”[3]713。《会典》中所记的“考察”就是从明朝继承下来的。在《清世祖实录》中记载,顺治三年(1646)七月辛酉,“吏部奏言:朝觐考察之期,既定于次年正月举行,其应行事宜首重五花册,臣部即照旧式,颁发各抚按,令其攒造赍送朝觐官员姓名、起程日期”,诏“从之”[4]228-229。 由此而知,清外官朝觐始于顺治四年(1647)。
另,顺治四年(1647)定,大计三年一举,永为定制。大计也是针对外官举行的,那么大计与朝觐的关系就显得比较混乱和复杂。在明朝的考绩制度中,大计泛指定期的、规模较大的考察活动,所以京察、外察和军政都被认为是大计。而清初,对于外官的考绩是用大计还是朝觐并未明确,经常使用“大计入觐”来表述。清名臣魏象枢在给顺治皇帝的奏书中称:“三年朝觐,名为大计,典甚重也。”[4]560朝觐与大计实际上是外官考绩制度的两个步骤,即外官三年举行大计,大计之后进京觐见皇帝以定计典之结果。在朝觐之制被停止后,大计作为专有名词用以定义对外官进行考绩的制度。
二、外官朝觐之制的规定
(一)朝觐官员的范围
在清朝,进京朝觐者的范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内地外省官员;一是国内边疆民族的王公、官员和喇嘛等;一是外国使者[5]。清初外省官员的朝觐主要是参加由吏部、都察院、吏科和河南道举行的三年大计。“国家定制,外官三年一朝。”[2]105这里的“外官”并不是指清代在地方任职的全部官员,而是有特别的规定,并随着情况的变化而不断变化。
清初定,“朝觐计典,藩、臬、府、州、县正官皆入觐”[6]3226。正官入觐时,势必要将办理衙署事务的权力委托给其他官员,其中有些官员便借机勒索百姓,拖累地方。为此,顺治九年(1652)调整朝觐官员的范围,取消旧例上述规定,只令藩、臬各一员和各府佐一员代觐[7]志7191。顺治十八年(1661),把奉天府属官列入朝觐之列[2]105。康熙元年(1662)免除布、按朝觐,改为“令各道官代行”[2]105。六年(1667)定,每省布、按各一员,每府佐贰各一员,赍册入觐[2]105。十年(1671),直隶守道、巡道,令照外省布、按例入觐[2]105。十二年(1673),从山西道御史马大士疏言“藩、臬总理一省钱粮刑名,熟悉地方利弊,嗣后请仍令藩、臬亲身朝觐”[8]566,改为布、按“亲身”入觐,其各道官代觐永行停止。二十五年(1686),布、按、府、州佐贰官来朝,概行停止[2]105。朝觐停止后,参照庆贺万寿表章例,每省委道官一员,赍册入觐,“至官员贤否去留,止以督抚文册为凭”,造五花册三本,分送吏部、都察院、吏科,其藩、臬两司所造册籍,俱行停止[7]志7192。 二十六年(1687),停止道员朝觐[3]715,这意味着外官朝觐之制至此被废除。此后,清朝只以大计来作为对外官的考绩,引见之制取代了朝觐之制。
虽然国家对朝觐官员的范围进行了明确规定,但是对于特殊情况也予以考虑,显示了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的灵活性和实用性。如顺治二年(1645)定,“顺治三年,虽系计期,但各省初定,新设之官,尚未满任,姑缓朝觐”[4]191。顺治九年(1652),布政使有“因军需紧急,势难离任者,许委各道代觐”[2]105。顺治十八年(1661),以“云贵地方初开,需员料理,应暂行免觐”[8]69。康熙六年(1667)议准,“其贵州东川府土人不通文教,应免来朝”[2]105。
(二)朝觐日期
进京朝觐的日期包括朝觐大计文册到京时间和朝觐官到京时间。顺治三年(1646)七月规定于顺治四年(1647)年正月举行外官朝觐,其重点是五花册的攒造。吏部要按照旧式颁发各抚按文书,让他们上报攒造赍送五花册的朝觐官员姓名、起程日期文书。各抚按上报文册的期限为十月到吏部,应朝觐官员俱限十二月到京[4]228。顺治十五年(1658)规定,“府、州、县各役赍册汇缴,布政司亲投,各役不许入城,违者拿究”,且册籍俱限十月二十五日到齐[3]715-716。康熙六年(1667)规定,朝觐文册俱限十月二十日以内赍到[3]716。
(三)朝觐过程
顺治四年(1647)定外官朝觐的过程:“三年一朝。朝毕,吏部会同都察院、吏科、河南道考察,奏请定夺。来朝官引至御前,宣读诫谕,仍各赐敕一道。”[3]713具体来说就是各抚按所攒造册籍到京后,吏部考功司会同吏科、河南道,“俱于开印次日,会同封门,详阅册籍”,后由吏部、都察院堂官再加察核。考察完毕,“考功司先期知会吏科、河南道,赴部开门,出示晓谕”[3]713-714。而进京朝觐各官要查照限期入城,先赴考功司投递职名,等候过堂考察[3]714。考察之后,外省朝觐官员在午门内向皇上行礼[4]521,并被“引至御前,宣读诫谕,仍各赐敕一道。若有廉能卓异、贪酷异常,则行黜陟之典”[3]713。
(四)宣读诫谕
朝觐各官每次觐见皇帝后,皇帝会颁布一道谕旨以示敕诫,由鸿胪官宣读,通常是根据当时的形势告谕官员。顺治四年(1647)二月,诫谕曰:“天下人民困苦极矣,朕既出之水火,而随与监司守令共图治平,盖四载于兹。奈明季之积弊难除,颓风犹煽,有司则贪婪成习,小民之疾痛谁怜?司道则贿赂熏心,属吏之贞邪莫辨,疮痍未起,朘削弥工。流离颠连,未见何方招抚,萑苻啸聚,不闻何道消弥。朝廷之德意时勤,郡邑之废格如故。优游日月,夤觊升迁,虽婪墨间有纠弹,而奸猾每多贿脱。朕甚愤之。”[4]251-252顺治皇帝的诫谕言辞相当激烈,痛斥明朝积弊,但对朝觐官员能有多少实际的触动作用,也无从探查。康熙十三年(1674)诫谕的语气则相对和缓:“朝觐官员各有职掌,俱宜实心任事,洁己爱民,安辑地方,消弭盗贼。钱粮不得加派,刑名务期明允,赈济蠲免必使民沾实惠,以副朕察吏安民之意。如不遵行,国法具在,尔等悉知。钦哉。”[9]147
康熙二十二年(1683),谕朝觐各官:“尔等各有职掌,关系国计民生,自宜实心办理。如奏销钱粮,采买米石,借端浮冒,希图侵克,审理刑狱,颠倒是非,稽延岁月,致累平民。皆因尔等因循怠玩,积弊未除。嗣后俱应洁己奉公,殚心尽职。诸凡公务,俱照在内各衙门事例勤慎料理,着实遵行,乃副朕察吏安民之意。尔等若谓道途遥远,所行弊端未必尽知,仍沿陋习,漫无省改,宪典具存,决不姑贷。尔等悉知!钦哉。”[9]957从此次诫谕的内容和用词来看,它相当于对朝觐的总结。至于哪些语句应该添入其中,必须经过皇帝应允。旧式敕谕语句简少,于是在本次的诫谕中奉旨添入诰诫之语。
康熙二十五年(1686)朝觐之际,皇帝要求禁饬之语简明,希望能把“居官以清廉有守为要,近见九卿会推督、抚、藩、臬时,每有奔竞营求,寅缘干进,希图升任者。伊等居官贤否,自有鉴别,若未任之先,既怀不肖之念,又安望其清廉有守,率属莅民耶?如有此等,必行重惩不贷”[9]1429等意添入敕谕内,于是就有了下述诫谕之语:“国家三载考绩,原以崇奖廉善,摈斥贪残,必吏治澄清,庶民生安乐。今当大计,已严饬所司,重惩贪酷,余俱如例降革。其有众论不孚,是非失实者,特黜一二,以警积玩外,姑准尔等仍服原官。尔等平日官评贤否,公论昭然,若值会推,辄钻营奔竞,以图侥幸,居心先自不肖,何以率属莅民?且凡朝觐之期,每因仍陋习,借端科派,大小相循,私通交际。是察吏本以安民,而反以扰民,甚非朕激扬清浊至意。嗣后务须洗涤肺肠,勉图自新,毋貌承心违,蹈常袭故。国宪具存,决不尔贷。钦哉!特谕。”[9]1430
三、外官朝觐之目的
左都御史徐元文曾疏:“三年大计,藩、臬两司,并令赴京朝觐,盖将以闾阎之利病上陈,而皇上因以鉴察其才能,为进退之地。”[10]这句话道出了朝觐的真正目的,即考察人才和了解地方利弊。
清初,朝觐计典虽言黜陟幽明,但仍以安抚奖励为主,被黜之官的数量并不多。顺治皇帝道出了其中的缘由:“自朕亲政以来,更张虑其太骤,而皇皇求治之心暴于天下者几三载矣。……姑准尔等仍服原官,宜各勉力,以图日新,毋谓涂饰可以久施。”[4]580考虑到国家急需用人,不宜把行政管理的政策执行得过于严格,所以清初的各项政策执行相对比较缓和。如顺治十六年(1659)召见朝觐藩、臬各官,皇帝斥问江南右布政使王无咎、总漕抚臣亢得时:“参尔开报计册,与被纠贪酷革职按察使卢慎言互举卓异,岂无情弊?”王无咎巧言支抵,不知服罪。当顺治皇帝再问,如此大贪异酷之人反开其卓异,显然是受贿徇私,而王无咎仍然强辩。顺治皇帝厌恶其“面欺遮饰”,遂命革职,“令阁臣同该部院严加刑讯”。在反复诘问之后,王无咎才理屈词穷,“服其与卢慎言徇私之罪”。顺治皇帝念“人谁无过?贵在能改”,王无咎“既经自认,将来尚可望其痛改前非,力图尽职,特命复其原官,用示宥罪恕过之意”[4]951。
朝觐过程还是发现问题的过程,特别是皇帝可以亲自面见地方官,通过官员陈奏和回答问题来考察一个官员称职与否。顺治时期(1644—1661),地方官朝觐时,各官疏册先投送到通政司,然后转奏。到了康熙朝(1662—1722),发现该进呈程序不利于皇帝了解地方事宜,于是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左都御史徐元文条奏:“朝觐布、按官员上言地方事宜不应投通政司转奏,应各令面陈。”这样一来,“其才具优劣,议论得失,难逃睿鉴”,同时,皇上也可以借此了解督、抚当年所举卓异者是否得当[9]945。皇帝采用其言,布、按及代觐道官条奏本章,“不必投递通政司,于各衙门启奏后面陈”,且“令通政司满汉堂官各一员指引,科道掌印满汉官左右侍班,提前一日知会都察院、通政司、吏科遵行”[3]716-717。
地方官疏册投送程序的改变,也是对朝觐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而进行的改进,使得朝觐官必须直接向皇帝面陈,然后皇帝可以亲自对他们进行考察,而不只是走个过场。如康熙二十二年(1683)二月,对于吏部、都察院、吏科公参因朝觐官江南按察使金镇足疾而令其休致一事,康熙皇帝认为情由不充分,所以令该督、抚明白具奏,到日再议。后又问:“金镇如何?”大学士明珠回:“臣等未识金镇,闻其足病,不能步趋。”在康熙皇帝看来,如果金镇系保举补用者且有才具,即使有足疾也可以使用,不能因为足疾而舍掉一个人才,所以,令吏部察明原保举补用的情由,且将金镇一并引见。那么其系坠马病足,还是素有残疾,“一见自不难知也”[9]950-951。五月,在讨论吏部题补员缺时,贵州参政杨大鲲因在朝觐时给康熙皇帝的印象是“甚优”,即得补缺[9]1002。九月,吏部奏补员缺时提到了朝觐官原任河南布政使薛柱斗,康熙皇帝给他的评价是“为人甚优,其朝觐启奏时,言论举止颇明白安详”,大学士勒德洪等奏曰:“薛柱斗为人果优。”[9]1062
皇帝将藩、臬各官召至御前,主要的目的是让地方官条奏地方利弊,并在考察过程中当场解决所发现的问题。所以,皇帝在召见各官的时候,一方面提出要求,如“尔等各有职掌,关系国计民生,自宜实心办理”[9]957,另一方面将发现的问题提出来让各官进行商讨。出于这种目的,允许官员“请期朝见,面赐诫谕”,而“其布、按各官,如有地方情形及兴利除弊诸事,各具本奏闻”[3]716。当然,皇帝也希望能够从各地朝觐官员的陈奏中尽可能多地获得地方的信息,故“凡三年中国赋之盈亏、民生之利害、官评之贤否、吏议之公私,许其逐一奏陈”[4]560。
那么实际情况如何呢?掌管地方钱粮、刑名的官员在觐见皇帝时都会陈奏些什么呢?康熙二十二年(1683)二月,康熙皇帝在乾清门面召由通政司引见的山西、陕西、浙江、湖广四省布、按官及代觐道员。山西布政使那鼐就本省采买米石估定价值一事陈奏,称前席兰泰已经估定过价值,后苏赫臣再估,但是核减太过,所以请令酌议,或照时价,或仍应照席兰泰前估价值进行采买[9]953。浙江布政使石琳陈奏,称浙省南粮向与漕粮同在十月征收,“今开征太早,请俟秋成免纳”。又奏称,“部行浙省采办银朱”,而本省不产之,所以请求改由产地采买。康熙皇帝认为其“应举民生利病当行当革事宜入告”,却以此等琐事“塞责”。石琳辩称:“臣职司钱粮,两事是臣所知,故尔奏闻。”[9]953同次还面召了山西按察使库尔康,陕西布政使麻尔图、按察使叶穆济,甘肃布使呀思哈、按察使索尔孙,浙江按察使教化新,湖广布政使李辉祖,湖南布政使薛柱斗,康熙帝一一详问,他们的奏章也“多全览”,并“有问至再三者”,“日午”方毕[9]953-954。康熙帝认为当日的朝觐与其期望相去甚远,对“随进御前取本”的学士张玉书、金汝祥说:“藩、臬一方大吏,所奏必关系国计民生,乃为有益。今日条陈,皆琐屑不堪,殊无可采。”[9]954翌日,通政司引见江西、福建、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七省布、按官及代觐道员。康熙帝详问朝觐官的出身履历及旗分、籍贯,至荫生授职者,问其父何官,“命各口陈事宜”[9]954。
对于这次朝觐的情形,康熙皇帝当然并不满意:“阅朝觐布、按等官所奏本章,于治民弭盗要事,如何为治则盗源可靖,如何预备则凶岁无饥,并未详晰敷陈。惟麻尔图所称,陕西拖欠钱粮应分四年带征等语,似属可行。朕轸念陕西地方被贼残破,及屡年运粮艰苦,所欠钱粮每欲蠲除,止因用兵未息,正当需用钱粮之时,遂未及宽免耳。龚佳育以江边芦田坍塌无常,应五年一丈量,其在内田地原无增减,请免丈量等语,亦属可行。其余俱系各衙门琐细之事,无甚紧要,若俱令议覆,徒多一番覆奏。”[9]958在皇帝看来,这些琐细之事与其想要了解的地方事宜相去甚远,且徒增奏章反复,是相当缺少行政效率的表现。
也有官员提出的问题则属小题大做。如康熙二十五年(1686),浙江按察使佟国佐奏称“饥民为盗,请宽减其罪”,皇帝却持不同意见:“天下焉有不饥不寒而为盗者?若以饥寒所迫为辞,将为盗者竟可不坐罪乎?”[9]1428同时,康熙皇帝还明白谕曰:“藩、臬条奏,应以地方利弊关系重大者入告,今伊等所言,大都皆职司之内平等事务,非甚紧要,于地方亦未有裨益。”[9]1428
四、外官朝觐之制的废除
康熙二十六年(1687),朝觐之制被废除了。实行朝觐之制的目的在于察人和了解地方利弊,但是在实践的过程中,并没有获得应有的效果。这只是其被废除的表面原因,真正的原因在于国家对地方权力秩序的调整——督、抚与布、按之间的权力分配和相互关系。
从清朝朝觐官员范围几经变动的过程来看,布政使和按察使是主要的朝觐官员。“盖以一方之政治,于藩、臬两司是寄,为群有司之纲领。”[11]藩、臬两司作为督、抚以下最重要的地方官员,掌管着一省的钱粮和刑名。清初藩、臬入觐过程较为简单,虽两司允许条奏地方事宜,但奏章由通政司投递,布政使和按察使被皇上引见一次后就辞朝回署地了。官员们不辞辛苦到京入觐的实际效果大打折扣,并未真正起到述职的作用,因此顺治朝(1644—1661)的吏科给事中魏象枢提出,在藩、臬两司朝觐时,皇上要详加询问:“问水旱频仍,有无救济招徕?所报地荒丁逃者,谁为致之?问钱粮混冒,官侵吏肥,每至数百余万者,谁为掌之?问劣员绌课蠹国,久列优评者,谁为纵之?问款项混开,征解淆乱,《赋役全书》屡饬不定者,谁为司之?问地方有藐法行私,纵贼窝盗,罪害及于职官百姓者,谁为制之?问法律不明,任情出入人罪者,谁为议之?问钦案沉阁,久不完结者,谁为诿之?问奸蠹盗折官粮成千成万,弊由夤谋滥差者,谁为主之?凡三年中,国赋之盈缩,民命之生死,官评吏议之是非,公私关系大纲者,逐一面奏。”[12]62这些建议的提出表明以魏象枢为首的汉族官僚主张以藩、臬两司监察督、抚,但是清政府在对地方政府的权力分配问题上,重督、抚的专权,不肯寄耳目于藩、臬。这一点可以从藩、臬考绩制度演变过程中非常明确地体现出来,而藩、臬两司造册籍权力的废除,最终标志着藩、臬两司完全被纳入督、抚权力之下,而且二者在大计中的考语也由督、抚填写。
督、抚与藩、臬两司这种权力的变化与其民族构成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清初,督、抚多为满人和汉军旗人[13],而藩、臬多为汉人,如果用藩、臬来监察督、抚,对满洲人来说意味着主导地位和统治权力的削弱,这也是民族自尊心所不能容忍的。清朝是以满洲贵族为首的封建政权,满洲皇帝与满洲贵族的利益是一致的,因此,维护满洲贵族的利益和权力必然是皇帝所要明确的立场[14]。
藩、臬两司权力的弱化并不意味着他们与督、抚处于对立的立场上,作为地方大吏,其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督、抚与藩、臬两司的署衙通常在同一个城市里,职责和利益使其紧密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藩、臬两司接受督、抚的监督和考察,反过来,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督、抚权力的无限扩张。
查康熙二十一年(1682)大计,“各省卓异五十余人”,藩、臬两司“多至一十七人”[12]204,将近一半卓异。针对此种情况,有官员“请停藩、臬卓异,以祛积弊”[12]204。第一,“杜徇私之嫌”[12]204。藩、臬与督、抚“官已相近,势得相亲”,相近则有结纳之私,相亲则多徇情之弊:“属吏之贤否,皆藩、臬所开报,保无以属吏为谄事之资,上官亦即以卓异为酬报之具?”[12]204可以说,“藩、臬之卓异一不当,则通省之卓异皆不当”[12]204。而且藩、臬掌管一省钱粮、刑名,仅以奏销支放没有失误、狱决律例详细而明确等分内之事不宜被开报卓异。另,藩、臬升迁的话,“内可以为京卿,外可以为巡抚”,其“选择任用何等郑重,岂一二督、抚之开报,遂可定其低昂”[12]204。第二,“昭吏道之公”[12]204。卓异为“计吏之特典”,而“藩、臬为封疆之大僚”,自非“平常之辈”,故“卓异只可行于道、府以下,而不必行于藩、臬两司”[12]204。也就是说,卓异是提拔地方府、州、县官的一条参照标准,毕竟府、州、县官人数较多,对皇帝而言不易详察其每个人为官政绩如何,主要依靠其上司督、抚和藩、臬的考核意见进行升选调补。藩、臬两司则不同,其任命权直接掌握在皇帝手中,皇帝可以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其具体情况,所以不需要参照卓异之典。康熙二十三年(1684),以藩、臬与督、抚亲近为由,停其卓异[6]3227。
随着藩、臬两司卓异资格的取消,他们由过去被督、抚考核的被考核者转换为与督、抚一同考核道、府等地方官的考核者。虽然朝觐权力的丧失意味着他们对督、抚监察权力的丧失,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皇权在这些权力转移的过程中也得到了加强。
五、结语
综上,大计入觐之制只实行了四十年就被废止了,这与清朝地方政权重心转移紧密相连。清政府要加强督、抚的权力,势必削弱藩、臬两司的权力,因此取消藩、臬两司的朝觐,将其纳入督、抚权力之下,由督、抚对其进行考核成为必然。
朝觐之制的停止也是清朝根据实际情况对国家行政管理制进行简化的结果。清初的考绩制度比较复杂,主要有京官的京察、外官的大计、武官的军政、全部官员的考满。考满之制于康熙四年(1664)被废除,主要原因如下:一是考满与官员升补无关,每当考满,部院大臣上疏自陈,不过是铺张履历功绩,博朝廷表里羊酒之赐;二是从正月到四月皆为自陈考满之日,一人一疏,以数千计,加之六部覆奏殷繁,官员无心办事,严重影响了政府行政效率;三是权力寻租,“即如州、县官,由府、厅至督、抚,经五六衙门”,有些上司难免会利用手中权力进行营私;四是武职考满会造成上司克扣粮饷,贻误封疆,不无隐忧;五是每次考满优等多、劣等少,基本丧失了“分别贤否,以示劝惩”的作用[15]。朝觐之制与考满之制一样,在执行过程中无法达到预期效果时,就会被终止。且在执行朝觐之制的同时,考绩后的引见也在执行,朝觐之制有地方官进京进行述职之意,而引见之制则是对考核结果的最终确认,二者在某些方面也是相互重复的。加之朝觐花费巨大,在直省每年存留银两中,仅“朝觐造册送册路费银”就有“一万七千六百二十二两”之巨[4]807。最终,朝觐考察随着藩、臬两司卓异的取消也被废止了,清代考绩制度最终以京官京察、外官大计、武职军政三种形式固定下来。
朝觐之制的废除实际上是清朝对考绩制度进行规范的结果,简化其中职能重复的部分并加以改进,取消没有实际效果且容易滋生弊端的步骤。这一点也体现在对考语(官员评价)以及八法(后改为六法)的规范上,简单实用是其宗旨。朝觐之制最终只作为旧例载于《雍正会典》,以备稽考,而大计作为对外官进行考绩的正式制度确定下来,并得到认真执行,一直持续到清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