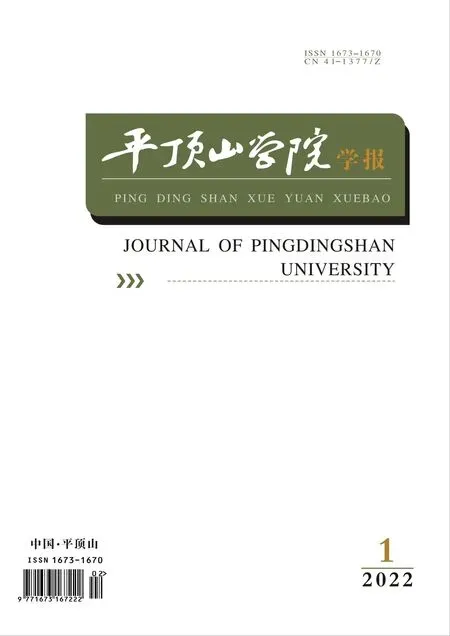老子生命道学诠释构想
李 健
(西安外事学院 人文艺术学院,陕西 西安 710077)
老子的智慧是生命的智慧,老子非常推崇生命体证。从老子本人的大道智慧来看,他是非常谨慎言说与著书的,“致虚极,守静笃”[1]35,悟道在生命的在场直观与实践之中,不在思辨与言说里。虽然《老子》一书成为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经典之一(1)西方最早的《老子》印刷译本是1842年儒莲法译本,截至2018年5月,之后出现的其他译本已达1 548种,涉及72种语言。详参邰谧侠:《〈老子〉的全球化和新老学的成立》,见《中国哲学史》,2018年第2期,第126页。,但这并非老子本意。老子本不打算著书,是关尹强迫他,老子不得已才为之。当然也要感谢关尹,使得后人能看到老子的著作。同时,还要防范人执着于语言文字,忽略生命的亲在性体验。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1]127-128、“绝学无忧”[1]46,都是在警惕执着于外在的知识追求,而遗忘了生命的切身体悟。即道本身不是知识,道是用生命亲证的互动性存在。《老子》一书又是通向道的有益桥梁,只是要注意“得意忘言”“过河拆桥”。这类似于神学与信仰的关系,神学本身不是信仰,通过神学这个桥梁可以进入信仰,但如果执着于神学的学术系统,而忽略生命亲证,神学知识反而阻碍了信仰。
老子生于楚苦县(今河南鹿邑),工作于洛邑(今河南洛阳),著书于函谷关(今河南灵宝),弘道于楼观台(今陕西周至)。传老子著书后,关尹跟随老子到了楼观台,老子向关尹传授生命修道智慧,后来道教继承了老子、关尹的修炼方法。修真源于老子与关尹,《庄子·天下篇》说:“关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2]关尹与老子(老聃)都是修真的“博大真人”,老子是生命养护的实践者。
生命的存在是一大奇迹,尊重生命是一切价值的元价值,也就是最基础的普世价值。老子讲道、自然、无为,但如何在具体情境中判定是否合乎道、合乎自然、合乎无为呢?其实就是以生命为坐标,凡是尊重生命、有利于促进生命完善的,都是合乎道、合乎自然、合乎无为的;如果是藐视生命甚至残害生命的,都是背离道、背离自然、背离无为的。老子道学根本上是生命道学,始终保持如何完善生命的问题意识(2)笔者言说的生命,特指人。人是具有精神性的主体存在,尤其重视个体生命的优先地位。生命不是狭义的身体,生命是生理生命、社会生命与精神生命的统一。。
在快节奏的当代社会,人容易产生焦虑、困顿心理,而道家是紧张社会的“清静剂”。如何利用深厚的道家文化资源帮助当代人进行身心调适、成全完善的生命,是一个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道家的立足点是成全个体生命,建构良好的社会同样是为了更好实现个体生命自由,因而我们推崇生命道学。生命道学倡导尊道贵身、和光同尘、慈俭处后的理念,致力于挖掘道家文化治愈资源,重建精神家园,实现生命的更新与完满。
笔者使用的道学,即老子开创的道之学(道学不是指宋明理学之道学,亦不是指宋明理学之前作为道教的道学)。生命道学紧扣生命之道,哲学领域的老子与道教领域的老子都重视生命之道。老子生命道学超越哲学与宗教的对立,立足《老子》文本,系统诠释出老子的生命智慧。老子生命道学具体涉及生命本原、生命目的、生命超越等内容。
一、学界关于老子生命智慧的探索
老子及道家思想研究有的从哲学角度展开,有的从道教角度展开,但无论是从哪个角度展开都有学者注意到了老子的生命智慧。
老子哲学方面,有多位学者使用过“生命哲学”的理念。李霞于2006年发表了题为《老子:中国生命哲学之父》[3]的论文;吴根友于2012年发表了题为《老子与庄子的生命哲学、养生思想及其现代启示意义》[4]的论文;周可真于2013年发表了题为《追求自然生命过程的正常进行——老庄生命哲学论要》[5]的论文;付粉鸽还于2010年出版了题为《自然与自由——老庄生命哲学研究》[6]的专著。有的学者虽然未使用“生命哲学”的标题,但从该角度进行研究。2006年,陆建华发表了题为《存在与超越:老子生命论》[7]的论文;同年,鲁庆中在论文《道:在“有”的向度上》[8]162-166里提出了“生命本体论”的概念。
老子与道教方面,有多位学者使用过“生命道教”的理念。谢清果于2009年出版了题为《生命道教指要》[9]的专著,认为生命道教是继生活道教等观念之后新兴的一种道教文化理念,旨在张扬道教养生智慧的独特魅力,发扬道教“生道合一”的价值理性,阐扬道教“道法自然”的实践理性,倡扬道教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自我身心全面和谐的圆融和合境界,从而为人类的健康、自由、和平、幸福提供弥足珍贵的思想文化资源;詹石窗等于2018年发表了题为《关于生命道教的几点思考》[10]的论文,认为生命道教是“以生命认知、生命护养、生命超越为思想内涵的教化理论”;杨普春于2019年发表了题为《“生命道教”哲学建构的三重张力》[11]的论文;盖建民主编的《生命道教暨卿希泰先生道教学术思想研究国际论坛文集》[12]于2020年出版。陈霞虽然未直接以“生命道教”为题,但其研究内容属于生命道教。2019年,她出版了专著《道教身体观——一种生态学的视角》[13],认为道教追求“长生久视”,特别看重身体,并发展出深刻的关于身体的思想以及提升生命质量的养生实践。
生命哲学、生命道教都属于生命道学的范畴,有的学者还直接使用了“生命道学”的概念。张丽娟于2009年完成了题为《〈关尹子〉与生命道学考论》[14]的硕士学位论文,又于2011年发表了题为《先秦道家的“生命道学”管窥》[15]的论文,认为以道为中心的生命道学是由老子初创、关尹传承、列子展开和庄子集成的,在谈到老子生命道学时,重点从“道生万物”和“道常且久”两个角度论述生命之道;唐少莲根据吕锡琛出版的专著《道学健心智慧》(3)吕锡琛未直接使用生命道学概念,但采用相关视角。详参吕锡琛:《道学健心智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于2010年发表了题为《道学的生命与生命的道学——读吕锡琛等〈道学健心智慧〉的几点体会》[16],用“生命的道学”来概括吕锡琛的道学思想;梁琛于2019年发表了题为《浅析〈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中所蕴含的生命道学思想及其现世价值》[17]的论文。
吕锡琛《道学健心智慧》主要从心理健康角度讲生命之道,进行道学与西方心理治疗学的互动研究;张丽娟《〈关尹子〉与生命道学考论》系统研究《关尹子》的生命道学智慧;张丽娟《先秦道家的“生命道学”管窥》具体研究了老子、关尹、列子、庄子等四大道家学派的生命道学;梁琛《浅析〈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中所蕴含的生命道学思想及其现世价值》主要通过健康养生角度讲河上公的生命道学。数位学者对道家生命道学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奠基贡献,但还没有专门针对老子生命道学进行系统性研究与诠释构建。这是笔者试图做的一点推进,即具体从生命本原、生命目的、生命超越等方面构建系统性的老子生命道学。
《老子》文本有多个版本,不同版本都在论述生命智慧,不同版本有不同的面向。学界整体上是在今本《老子》基础上讨论老子的生命智慧,做了有益的探索。今本《老子》作为经典化文本,对历史和世界的影响都很广泛,以今本《老子》作为诠释对象完全具有合法性。《老子》出土文献的面世,为了解早期《老子》的思想打开了一面窗户。楚简《老子》更古朴,一方面更接近“祖本”,另一方面为今本《老子》的演变与由来提供了线索,其早期文本的重大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今本《老子》代表经典化文本的思想,楚简《老子》代表古本(早期文本)的思想,笔者正是从此两个版本来系统构建老子生命道学。汉帛《老子》虽也被称为古本,但该本是汉代的文本,实际思想内涵与今本《老子》无根本差异,故笔者不对汉帛《老子》进行专门研究。
二、今本《老子》的生命道学建构
今本《老子》是经典化文本,也是后学参与编订、完善的精品文本,通过今本《老子》可以建构完整的生命道学体系。今本《老子》把道作为生命的本原,把成为圣人作为生命的目的,把“死而不亡”作为生命的超越。生命本原、生命目的、生命超越构成完整的生命道学内涵。
(一)道:生命的本原
关于生命道学之本原论可以从三个维度展开,即本原的性质、本原与人的关系、人与本原的连接。本原的性质维度上,老子认为道是无为的。本原与人的关系维度上,老子认为道生万物,道、人是同质关系。人与本原的连接维度上,老子认为道生德畜,德来自道,通过德而得道。
道是无为的,意指道不把意志强加给万物,“道常无为而无不为”[1]90。无为的根本义就是不强制、不干预,顺自然而为。作为本原之道如此,治国之道也应如此,这是老子“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方式。老子说:“为无为,则无不治。”[1]8道是无为的,执政者也应当无为而治。“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1]129,老子反对执政者把意志强加于百姓,应以百姓的意志为中心,“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1]150。老子主张民自化、民自富等,体现了其民本思想。从道无为、道不干预万物,到执政者应当无为、执政者不干预百姓,体现了老子的人文关怀。执政者不得伤害民,使得民自主、自由发展,这是对生命的充分尊重。因而,老子的本原哲学到政治哲学,都是生命的道学,以个体生命的充分自主与发展、最终生命完善为归宿点。
道与人的关系是生与被生,人由道所生,道是人之“母”,道“可以为天下母”[1]63。老子表达的是一种生命互动关系,道与人是“母子”关系,而不是死的对象化关系。所以老子还讲“贵食母”[1]48、“复守其母”[1]139。道本身作为智慧生命存在,人也作为生命存在,道与人就形成了一种主体间关系,道论即“生命本体论”[8]164。
道作为生命存在,具有养育万物的玄德,“道生之,德畜之”[1]137。道自身富有玄德(元德、根本之德),同时把德赋予人。人生而秉承道性——德,老子说“含德之厚,比于赤子”[1]145,人是通过德来连接道的。赤子作为初生的婴儿,其来源于道的德性没有被破坏,没有被社会污染,老子进而提出要“复归于婴儿”[1]73,也就是“复归于朴”[1]74。“复归于朴”也就是复归于道,因为道是“朴”的:“道常无名朴。”[1]81得道的过程就是返璞(朴)归真的过程,也就是减损欲望的过程,不被世俗的功利主义所捆绑,“为学日益,为道日损”[1]127-128。无疑,老子的生命道学是紧张社会的“清静剂”,有文化治愈功能,可以消解人的紧张感。
(二)成为圣人:生命的目的
关于生命道学之价值论可以从三个维度展开,即存在的根基、存在的目的、存在的价值。存在的根基维度上,老子认为是与道同在。存在的目的维度上,老子认为是成为圣人。存在的价值维度上,老子认为是见素抱朴。
老子主张与道同在,始终把人与道关联起来,人并非被抛在世界上的孤独存在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1]137老子虽然不主张人类中心主义,但并不是简单把人与万物等同。人毕竟不同于非精神性的万物,老子在“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1]64一句话中把人的独特地位给充分彰显了出来(4)王属于人的范畴(傅奕本、范应元本等直接作“人亦大”)。详见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71页。。万物如动物是不能与道同在的,人可以与道同在。人由于被欲望与智巧遮蔽,才导致与道的阻隔。人要通过减损欲望(“为道日损”),呈现生命本真的德性,重新与道连接,这就是老子说的“道者同于道”[1]57。但这里的人性回归是一次超越,是转智成圣。
能与道同在的人实际就是圣人。“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中的王是圣王,也就是圣人。因而老子把成为圣人作为生命的目的,普通的人不是完满的,圣人是完满的,圣人是道在人间的生命承载——道者(得道者)。圣人是贵重生命的,不追求外在的名利浮华,“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1]28,“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1]166。圣人是无私的,超越了小我而成全大我:“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1]19圣人投身社会建设,达成良好的社会治理——无为而治。“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1]6“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1]150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圣人并非一张白纸,而是忍辱负重,经历了各种磨难,最终成为厚重的天下担当者。“是以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1]187“大白若辱。”[1]112伟大人物往往遭受过不同寻常的苦难。孔子一生颠沛流离,被人称为“丧家犬”[18]1921;老子生逢乱世而出关,“不知所终”[18]2141,一个人在天地间探索真理,也伴随着深刻的孤独,很难找到知音,“知我者希”[1]176;苏格拉底追求真理、传播真理,被投票处死。他们经历的苦难促成其生命蜕变,最终实现了生命的永恒。
“道常无名朴”[1]81,老子把人的价值追求也归于素朴,即“见素抱朴”[1]45。推崇素朴其实是为了防范外在名利世界对内在生命的异化,当外在名利反客为主、人成为名利的奴仆,则生命被社会世俗所捆绑。素朴在老子那里也就是自然,与智伪相对。“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64,道、天地都是自然的,它们的存在是本然存在,不存在被文化所异化,人法天地、法道也就是法它们的自然。老子推崇自然,也就是通过回望自然来达到对文化异化的克制。文化异化的体现就是智伪,“慧智出,有大伪”[1]43,“故以智治国,国之贼”[1]168。
(三)死而不亡:生命的超越
关于生命道学之生死超越论可以从两个维度展开,即超越死亡的途径、超越死亡后的生命状态。超越死亡的途径维度上,老子认为是死而不亡,生命有死而价值不亡。超越死亡后的生命状态维度上,老子认为是虚静,虚静是合道的生命状态。
老子对生死的理解首先是冷峻的。孔子对死亡是有回避的(“不知生,焉知死”),而老子直面死亡:“出生入死。”[1]134死是一个确定的事实,生总是面向着死,犹如海德格尔说的“向死存在”[19],向死而生。不同的是,海德格尔把死作为生命的终结,老子认为人还能做到“死而不亡”[1]84。老子讲的不亡,不同于宗教讲的灵魂不死,而是人如果得道,他所承载的道不亡,也就是他的精神价值不亡,所以老子说:“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1]143善于建德抱道的人,则融入历史文化长河,后人会传承其道。建是建德,老子说“建德若偷”[1]112;抱是抱道,老子说“圣人抱一,为天下式”[1]56。抱一就是抱道,因为一就是道。道生一就是道生道,道生道是为了说明道已经是终极,道“自在永在”。一就是道,是有内证的。老子说“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1]31,其中“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就是在描述道。是道“混而为一”,一也就是道。“混而为一”的“混”也是描述道,与“有物混成……字之曰道”[1]62-63相应。“混而为一”的道是“惚恍”的,而老子在另一处说“惚恍”时正好是在说道:“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1]52这里的“惚恍”正是“惟道是从”,“惚恍”是道的特征。
超越死亡的得道者不会被死亡问题所困扰,他的生命是宁静的、虚静的,他致力于道的无限性,而不是执着于生理生命的有限性。俗人追求生理生命的长寿,而圣人则是“死而不亡者寿”[1]84,是精神永恒的永寿。
三、楚简《老子》的生命道学建构
楚简《老子》是战国时期的《老子》文本,属于早期《老子》文本。根据“近古必存真”的文献学原则(也符合概率原则),该本更接近祖本(5)当然这里说的祖本,并非说有一个五千言的祖本,而是指道家创始人、第一作者“老子”的文本。五千言实为学派著作,系后学进一步完善、整理而成。。地下文献出土之前以今本《老子》作为老子思想的诠释依据,地下文献尤其是战国的楚简《老子》出土后,对今本《老子》产生了较大的冲击。比如,今本《老子》中被认为有阴谋论、愚民论等内容者恰好都不在楚简《老子》里;今本《老子》对儒家仁义观念进行尖锐批评,但在楚简《老子》里对儒家仁义观念的批评比较温和;今本《老子》关于有和无的关系是“以无为本,以无为用”(无的地位高于有的地位),但楚简《老子》里是有无并举(并列)。郭沂主张改写中国思想史,陈鼓应主张改写中国哲学史,曹峰反对以出土文献来改写,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较大差异及其对传统文献的冲击客观存在。笔者立足楚简《老子》与今本《老子》的根本差异,对楚简《老子》也进行生命道学的诠释构建。内圣外王的概念最早由《庄子》提出,儒家借用了这一概念,至今提到内圣外王通常会想到其是儒家的重要观念,而笔者注意到,楚简《老子》甲本正是按照内圣外王(成为圣人与圣人治世)的结构秩序展开的,即它通过修身与治理来体现老子的生命道学。笔者还根据楚简《老子》甲本关于有和无的异文,诠释出“道体之有、道用之无”的体有用无之体用观。
楚简《老子》与今本《老子》都体现了老子的生命智慧,但具体思想上,楚简《老子》又有其独特性。可以从自然之道、修治路径、体用关系等三个方面呈现楚简《老子》的生命道学。
(一)道“恒自然”:自然之道
楚简《老子》用“恒”来表示道之恒定的、根本的、本质的特征,如“道恒亡(无)为也”[20]152、“道恒亡名”[20]187。“道恒亡为也”体现了道不干预万物,“道恒亡名”体现了道不执着于名位尊卑,它是自足的。道的亡为、亡名,在根本上又是由道的自然性决定的,故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0]208。在李零校正的竹简编排顺序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位于首章位置,今本《文子》引《老子》也放在了首章。该句蕴含“道法自然”的思想,但没有直接表达为道“恒自然”,而汉帛《老子》进一步把道“恒自然”的命题表达出来了,那就是道“夫莫之爵而恒自然也”[21]。在《尔雅·释诂》里,法与恒、常邻列,是义通的同义词,也说明“道法自然”即道“恒自然”(6)详参李健:《“道法自然”即道“恒自然”——从文本演变理解老子自然思想的自洽性》,见《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5期,第24—29页。。
道“恒自然”决定了“道恒无为”,两者有一致性,其实也有分疏。道“恒自然”是从本原之道上讲的,“道恒无为”是从治国之道上讲的。道有天道与治道之分,“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1]192也是按照天道和治道分疏的,天之道是天道,圣人之道讲的是治道。从道“恒自然”到“道恒无为”,是为无为之治建立本体依据——天道自然所以治道无为。老子主张无为之治,是基于尊重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充分自主与自由,警惕权力放任对民构成强制。老子讲“故无弃人”[1]71,体现了尊重生命的普遍性,在生命上,人人是平等的,人人都是宝贵的,人不是他者的工具,更不是统治的工具。生命来自道,因而任何人不能剥夺他者的生命。任何崇高的统治目的,如果以牺牲生命为代价,在老子看来都是无道的。老子反对战争,正是因为战争要牺牲生命。“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1]125,可以说老子是和平主义者。老子在政治学说里反复强调无为,主张不干预民,从而使得民自主、自由,这是通过善政的方式保证个体的自由。良善的社会最终是为了成全个体生命,集体的合法性在于更好地促进个体发展,所以老子政治学说同样是生命的道学。
对生命的绝对尊重,其实也就蕴含着人权思想。老子说“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1]179,反对剥夺老百姓的居住权和生存权,正是人权思想的根基。老子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1]170,把慈(爱)作为三宝之一。对每一个生命的尊重也体现了老子的慈爱(博爱)情怀。
(二)内圣外王:修治路径
楚简《老子》甲本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这个体系依照内圣外王的结构秩序展开,内圣即成为圣人,外王即圣人治世。内圣的具体路径是人法天地、人法道、人法自然,外王的具体路径是圣人欲不欲、圣人好静、圣人无为、圣人无事。老子的内圣是修身路径,体现在“天”人关系中;外王是治世路径,体现在君民的关系中(7)详参李健:《内圣外王:〈郭店老子甲本〉的结构秩序》,见《荆楚学刊》,2018年第2期,第5—16页。。
一般认为内圣外王是儒家的核心理念,实际上它最早由道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庄子提出,而老子是最早建构内圣外王体系(成为圣人—圣人治国)的思想家。老子建构内圣外王思想体系旨在成全完善的生命,内圣是个体生命的完满,外王是达成天下的人生命完满。
(三)体有用无:体用关系
道是老子道学的核心理念、逻辑起点,而道与有无的关系问题,以及有无与体用的关系问题,都是关涉老子道学的元问题。由于长期受到今本《老子》“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1]110的影响,把单一的无作为道的内涵,导致无的地位高于有的地位,与“有无相生”的原文相悖,从而遮蔽了道作为有无同构的向度。由于长期受到今本《老子》作为“道·德经”的影响,以及今本《老子》“道生之,德畜之”[1]136、“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1]137的影响,把道作为体、德作为用,从而遮蔽了道本身是道体与道用的二重性,尤其导致了有无问题与体用问题相割裂。笔者结合楚简《老子》甲本的“天下之物生于有,生于亡”[20]359等原文,重建检讨这些流行观点,从而自洽理解老子道学的有无与体用的关系——道作为有无同构的内涵、道作为道体之有与道用之无的有机统一(道体指向本原之道,道用具体指向治国之道)(8)详参李健:《有无新辨:道体之有与道用之无——〈郭店老子甲本〉的体用观》,见《中华老学》第1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9年版,第233—241页。。
体上贵有(9)如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详参楼宇烈:《老子道德经注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62页。,是突出世界有一个本原绝对者,它是人类存在与价值的依归,可以克服虚无主义。用上贵无(“无名”“无事”“无为”等),是主张生命做减法,举重若轻,从容不迫,不要被外在名利所捆绑,不要被世俗文化所异化,恢复生命本真状态,具有文化治愈功能。
四、结语
老子生命道学消解老子道家与道教的二元对立,其实老子道家与老子道教都关注生命问题,都是以成全生命为问题意识。老子是道家文化的创始人,同时老子被尊为道教始祖,道教把《老子》作为教义元典,历代道士的老子注也客观进入老学史。建构老子生命道学统摄道家与道教,以生命为关切起点,以生命本原、生命目的、生命超越为诠释框架,对当今新道学建构具有理论意义。
今本《老子》与楚简《老子》有一定的差异性,这本身体现了《老子》是学派著作,非一人一时之作。但不论什么版本的《老子》,最终以同一个名称《老子》来命名,这就决定了它们是同一个学派,有共同的思想旨趣。老子学派“言有宗,事有君”[1]176,其“宗”就是道,即都把道作为本原,同时都非常关切生命的成全,尤其是个体生命的自由。因为老子学派的道最终是落在生命之道上,这就是笔者以“老子生命道学”之名来统摄各大版本的缘由。
老子生命道学还回应了孔子与老子关系问题。笔者认同孔子先讲学、老子后著书,即孔学在前、老学在后。老子出道早,青年开始讲学,而老子是晚年出关才著书。孔学重视仁义礼,但仁义礼教在现实中又形成文化异化。老子解构性批判孔学之仁义礼教,是为了克服生命异化,呈现生命的本真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