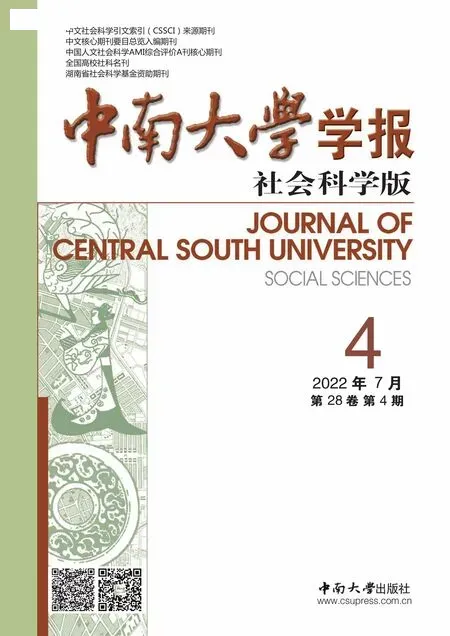“行权”与“尊君”的牵合
——论董仲舒“丑父欺晋”的诠释困境
张靖杰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上海,200433)
据《公羊传·成公二年》记载,鞌之战中,齐顷公率师亲征,为晋、鲁、卫、曹四国联军所败。在其被晋军包围之际,齐国大夫、任齐顷公之车右的逢丑父急中生智①,与顷公互换身份与衣物,并假命顷公取水,使之得以逃脱。而逢丑父则为晋军抓获,并被晋国大夫郤克斩于三军之前。董仲舒认为丑父有“贱君”“绝君”之罪,故《公羊传》对其有所讥贬。而何休《解诂》则认为,鉴于“王法”,丑父代君赴死的行为虽不得称贤,《公羊传》对其并无讥贬之意。徐彦在解释何休《解诂》序言中“至有倍经任意、反传违戾者”一语时,认为:“成二年逄丑父代齐侯当左以免其主,《春秋》不非而说者非之,是背经也。”[1](4)他认为董仲舒对于“丑父欺晋”的诠释有违经义。有必要追问的是:董、何对于“丑父欺晋”的不同看法究竟缘何而来?倘若讥丑父“不知权”为非,则作为《公羊》先师、深谙《春秋》经义的董仲舒何故为此“背经”之论?故本文试图以董、何对于“丑父欺晋”诠释的异同为切入点,探赜董仲舒在“丑父欺晋”一事上的诠释困境。具体而言,董仲舒将《公羊传》中于晋而言的“法斮”理解为抽去国家立场的“当斮”,以可能本不属于《公羊传》的贬抑态度评价逢丑父。而在“丑父欺晋”的诠释中引入“权变”一义,并试图将国君之尊荣——或抽象的“尊君”——设定为“行权”的边界,更引起了与祭仲专君却贤其知权的抵牾。
一、“丑父当斮”与“自齐当善”:逢丑父评价中的董、何异同
徐彦作疏大抵顺承何休之说,因此揭橥董仲舒“丑父欺晋”的诠释何以被徐彦归于“背经”之属,也就意味着分析董、何在这一问题上的异同。具体而言,又可以分别就经、传对于齐顷公与逢丑父两个人物的评价入手展开分析。
就《春秋》经义而言,董仲舒与何休均主张齐顷公战不能死难,理当绝其君位。《春秋·成公二年》记载:“秋,七月,齐侯使国佐如师。”《公羊传》:“君不行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佚获也。”[1](705-706)彼时齐顷公方从晋军的包围中逃归,派遣国佐与四国讲和,以免联军深入齐国,其行为似乎并无不妥。然而,《公羊传》依据“君不行使乎大夫”——国君不向大夫派遣使者——的原则,批评齐顷公派遣国佐与四国大夫结盟,有违“君臣无相适之道”的规定[1](706),必定事有蹊跷。由此引出了齐顷公在逢丑父的帮助下逃脱晋军围困的故事。何休《解诂》谓:“佚获者,已获而逃亡也。当绝贱,使与大夫敌体以起之。”[1](706)国君被抓获后逃亡,理当绝其君位,《春秋》经正是借由记录齐顷公向大夫派遣使臣这一有违君臣之道的事以见其当绝。对此,董仲舒的看法与何休相同。《春秋繁露·竹林》篇谓:“获虏逃遁者,君子之所甚贱。”[2](17)即贬顷公之“佚获”为可贱之事。又:“已反国复在位矣,而《春秋》犹有不君之辞。”[2](18)所谓“反国”,即齐顷公从晋军逃归回国。而其向四国大夫派遣使者的做法,有违君臣不敌体的礼制规定,非国君所当为,可见《春秋》并不以齐顷公为君,是为“不君之辞”。陈立《义疏》顺承董说,指出:“绝贱不君,故使与大夫敌体也。”[3]《春秋》记载齐侯向四国大夫派遣使者,即已将齐侯与大夫等而视之,有“绝贱”之意。
《春秋》止于绝顷公而未及丑父,《公羊传》则进一步叙述了逢丑父如何经由易服代君,得以让齐顷公逃出生天,自己则被郤克斮于晋军之前的始末:“其佚获奈何?师还齐侯,晋郤克投戟逡巡再拜稽首马前。逢丑父者,顷公之车右也。面目与顷公相似,衣服与顷公相似,代顷公当左。使顷公取饮,顷公操饮而至,曰:‘革取清者。’顷公用是佚而不反。逢丑父曰:‘吾赖社稷之神灵,吾君已免矣。’郤克曰:‘欺三军者,其法奈何?’曰:‘法斮。’于是斮逢丑父。”[1](707-708)不难发现,上述传文并未涉及如何评价逢丑父的问题,但董仲舒与何休均基于“王法”“正义”,认为丑父杀身存君的行为并不足取。何休《解诂》谓:“丑父死君,不贤之者,经有‘使乎大夫’,于王法顷公当绝。如贤丑父,是赏人之臣绝其君也。若以丑父故,不绝顷公,是开诸侯战不能死难也。”[1](708)也就是说,丑父虽然杀身存君,但其实质是绝君,若以丑父为贤,则不免于鼓励臣子怂恿国君违逆“王法”。依据《公羊传》“许人臣者必使臣”的常例[1](894),倘若因丑父死君为贤而不绝顷公,则又开诸侯不能死难之先河。在《观德》篇中,董仲舒以“天子之所诛绝,臣子弗得立”来评价逢丑父杀身以存君的行为[2](56),“天子之所诛绝”即可视作“王法”。在《竹林》篇中,董仲舒更以“正也者,正于天之为人性命也”为前提,经由将人之“性命”设定为“行仁义而羞可耻”[2](17),以论证逢丑父帮助齐顷公“佚获”的行为是羞社稷、辱宗庙,有违“性命”之正。
仅就上文所引经、传来看,《春秋》经义止于绝顷公,而未及丑父,则丑父之贤与不贤,与经义并无直接关系,且逢丑父欺晋存君的行为有违“王法”“正义”,董仲舒与何休的立场也并无不同。“背经”之说缘何而来,有待进一步探究。问题的关键或许藏在两人对于逢丑父的不同评价中。在董仲舒看来,丑父“欺三军为大罪于晋,其免顷公为辱宗庙于齐”[2](18),可谓于齐、于晋皆罪无可赦。而何休却认为,尽管出于“王法”,丑父不得称贤,但其能杀身存君,故“自齐所当善”[1](708),表达了对丑父的同情②。更为关键的一点在于,《公羊传》中,“欺三军”之说出自郤克,“法斮”二字也出自晋国的执法者之口。而到了董仲舒那里,欺晋国之三军成了齐国大夫逢丑父的罪过,基于齐晋为敌的于“法”当“斮”更被偷换为抽去国家立场的“当斮”。焦循就指出:“《公羊传》‘欺三军’之言出自晋,晋之斮之也固宜。”[4]可知,仅就传文所述来看,丑父之罪乃是自晋言之。有学者认为:“《公羊传》只是在叙述晋军对如何处置逄丑父的讨论过程,是晋军得出结论说‘该杀’,《公羊传》在这里只是客观叙述这个事件而已,并没有从自己的角度评论说‘逄丑父该杀’。”[5]可见,“《公羊传》于逄丑父之行为,似无明显褒贬”[6],“法斮”与“当斮”亦不可轻易等而视之。苏舆意欲回护董说,认为:“《传》以‘于是斮逄丑父’终,则其不与丑父可知。”[7](61)但《公羊传》究竟是“与”还是“不与”,并未明确形于文字,究竟能否将“当斮”视为《公羊传》的态度,仍然有商榷的余地。
当然,如果采取董仲舒“不在经而操之与在经无以异”的解经方法[2](12),则贬抑丑父或许可以视作对于经、传的合理引申。君臣之义互为表里,既已绝为君之顷公,则为臣之丑父当死也是理固宜然,在此意义上,甚至可以认为“董义优于何”[8]。然而,倘若将对于经、传的解释与对于人、事的评价稍加区分,则会发现:暂且搁置两人对于丑父的评价,无论是董仲舒的以“当斮”直断,还是何休的“王法”与“自齐”相分,由“法斮”而“当斮”的一字之转业已将其对经、传的解读附丽于传文本身了。若以“背经”为违背《公羊传》之义,则徐彦将其归于“背经”之属,似乎也能够成立。当然,我们可以进一步辩护:董仲舒所谓“当斮”也仅仅是对于丑父的态度或看法,而非对传文之“法斮”的偷换。既然作为评价,那么只要能自圆其说也就谈不上“背经”之误。结合徐彦所谓“《春秋》不非而说者非之”[1](4),董、何之异乃至“背经”之讥,似乎更像是围绕丑父评价的立场之争。
然而,以立场之争审视董、何在逢丑父评价上的不同犹有未尽之处,两者之间更为本质的差异在于“权变”范畴的引入与否。在董仲舒的分析中,“权”构成了评判丑父是否忠义的重要标准,而在何休的解读中则全然不涉及“权”字。因此,下文将围绕“权”之一义,展开进一步的分析。
二、作为“行权”边界的“尊君”
学界既往对于董仲舒“权变”观念的解读,往往顺承《公羊传》的思路,多以董仲舒对《公羊传》的“权变”观念有所发展为论,较少关注到两者的差异。一方面,与《公羊传》仅仅围绕“祭仲许宋”一事而论“权”不同,董仲舒以“比贯连类”的解经方法[7](36),将“权”之一义引申到对“隐代桓立”“目夷拒楚”以及“丑父欺晋”(作为“不中权”的反例)等事件的分析,并提出“经礼”“变礼”与“可以然之域”等范畴,事实上扩展并深化了《公羊传》的“权变”理论。另一方面,两者之间仍存在一些有待辨明的差异。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或许是:经由将“权”的范畴引入对“丑父欺晋”的分析,董仲舒试图将“尊君”(维护国君之尊荣)设定为臣子行权的边界,导致“祭仲许宋”与“丑父欺晋”诠释的扞格。
如前文所引,董仲舒认为丑父的罪过之一在于“免顷公为辱宗庙于齐”[2](18)。《竹林》篇中,董仲舒甚至设身处地假定丑父真有忠义,应当劝谏顷公一同赴死:“君慢侮而怒诸侯,是失礼大矣。今被大辱而弗能死,是无耻也而复重罪。请俱死,无辱宗庙,无羞社稷。”[2](18)更进一步,董仲舒从“不君之辞”推断:“其于义也,非君定矣。若非君,则丑父何权矣。”[2](18)齐顷公获虏逃遁不仅于道义上有所亏欠,实际上也自绝于君位,即不复为君。苏舆即指出:“非君,则丑父之死非死君也,故曰‘何权’。”[7](59)君即不君,则臣亦非臣。逢丑父不仅无忠义可言,董仲舒甚至勾销了丑父之死的合法性,可谓死不足恤③。
我们不妨将“可以然之域”与上述对逢丑父的评价进行一番比较。《玉英》篇中,董仲舒明确指出:“夫权虽反经,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虽死亡,终弗为也,公子目夷是也。”[2](21)仅就字面含义来看,“可以然之域”即在可以这样做的范围内才这样做④。不过,经由比较“目夷拒楚”与“莒人灭鄫”二事,基本可以断定,所谓“可以然之域”即国家社稷与宗庙的存续。可见,董仲舒借由这一提法为臣子行权划定了边界,超出此边界,即便死亡亦不可为⑤。以“可以然之域”衡量“丑父欺晋”一事,可以发现:丑父与顷公的所作所为即可归于“虽死亡终弗为”之属,而“辱宗庙”与“羞社稷”作为顷公之罪愆,同样也突破了“可以然之域”所划定的范围。或许可以推断:借由逢丑父一事,董仲舒试图将维护国君之尊荣,不使其自绝于君位,也视作臣子行权的边界之一。
如果说仅据丑父之“不中权”尚不足以说明董仲舒以维护国君之尊荣——或抽象为“尊君”——作为臣子行权的边界,那么,经由将其与“祭仲许宋”比而观之,董仲舒强化了这一观点。在《竹林》篇中,董仲舒分析祭仲与丑父何以一者“中权”、一者“不中权”的缘由。就君的一方而言,“去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贵;获虏逃遁者,君子之所甚贱也”[2](17)。《春秋》之中,兄弟夺权,不愿相争乃至相杀,自可出奔以避内难。在董仲舒的解读中,公子忽并非为祭仲所逐,反而成了难能可贵的谦恭避让。就臣的一方而言,“祭仲措其君于人所甚贵以生其君,故《春秋》以为知权而贤之。丑父措其君于人所甚贱以生其君,《春秋》以为不知权而简之”[2](17),则臣子行事是否中权的标准,即(部分)系之于国君之尊荣与否。然而,只需稍加思考便可发现上述立论之为难。如果维护国君的尊荣是臣子行权的边界,则祭仲之“出忽立突”作为“政在大夫”的典型对于君权的僭越与侵犯已至极致,又如何可谓“尊君”?无需细致的论证与推理,只需徵引见于《公羊传》中的文字便可知其难以自圆其说。《春秋·桓公十五年》记载:“郑世子忽复归于郑。”《公羊传》:“复归者,出恶,归无恶。”[1](187-188)且不论《公羊传》以公子忽出奔为恶的理由为何,至少可以断定:董仲舒以公子忽“去位而避兄弟”为可贵的说法,或为偏离《公羊》经义的以紫乱朱之说。
将“义”引入对董仲舒所谓“权”的分析,或许可以进一步论证他的上述观点。基于董仲舒评价逢丑父“欺而不中权,忠而不中义”的说辞,有学者认为顷公与丑父的行为是“以诈得生……背离了权变之本”[9];还有学者主张“‘义以为上’实为公羊家考论经权关系的首要原则”[10]。在董仲舒对于丑父的评价中,“义”确实是一个反复出现的字眼,若仅用以评价丑父的行为亦可谓自洽,但这并不足以构成比较与区分祭仲与丑父之行事的依据。以顷公获虏逃遁、见辱失尊为不义,则顷公与丑父一同赴死,不辱宗庙社稷则为义。在此意义上,将郑国国君的废立运于股掌的祭仲,和系于祭仲而或存或亡的公子忽,又何来“义”可言?何休注公子忽之“复归”为“出恶”时,即明确其出奔“不如死之荣”[1](188)。也就是说,公子忽若真有为君之“义”,则绝不会任由祭仲摆布,而应自裁以报社稷与先君,如此方可谓“义”。更何况,若将“义”视为“行权”的首要原则,即隐含了只要合乎“义”的规定,僭越国君之权力与尊荣也并非不可接受。祭仲之“出忽立突”即是如此。另一则典型的事例即鲁宣公十五年,楚国的司马子反出于恻隐之心擅自与宋国讲和。几乎可以断言:在《公羊传》的论域中,凡臣子行事可以被归于“权”这一类的,无不对君权有所侵犯,隐代桓立,目夷拒楚,皆可谓“篡”。齐桓、晋文专致、专封,纪季专地,皆可谓“逆”。易言之,行权势必意味着突破君权的限制,尽管理论上只应是暂时且不得已的。
当然,我们或许可以为董仲舒辩护。按照《公羊传》国君不可见辱失尊的立场,则绝顷公乃至绝使顷公受辱的丑父都合乎“正”义。《公羊传》维护国君的尊严仅仅是表象,其背后的逻辑是,国君受辱势必引起臣下与他国的轻慢,君权势必受到挑战,最终不免于君死国亡的惨痛结局。易言之,臣子行权不能突破“尊君”的限度,同样也是为了维护国家社稷⑥。但真正的问题在于:将《公羊传》中本应分属不同论域的“行权”与“尊君”糅合在同一事例中,并试图将国君的尊荣设定为臣子行权的边界,就导致了董仲舒将“权变”的范畴纳入“丑父欺晋”与“祭仲许宋”的比较诠释时的左支右绌。《春秋》学史上,祭仲的历史形象由“忠臣”而“逆贼”的转变[11],多少可以说明这一矛盾本就存在于《公羊传》的“权变”论述中。倘若接受“出忽立突”的祭仲是“知权”的贤臣,那么董仲舒借由“丑父欺晋”主张“尊君”作为臣子“行权”的边界,就不免有“背经”之嫌。
如果从公羊家惯用的“借事明义”的角度进行辩护或许更为有效。苏舆即认为:“《公羊》假祭仲以言权,董子复假丑父以明中权之难。丑父世之所贤,事又难于祭仲,不许以权,则其他之托言行权者,可知其比矣。”[7](61)依其说,则董仲舒不以“权”许丑父,亦不过一“假”尔。然而,公羊家“借事明义”之法,往往仅取一节,而搁置其余,如取祭仲之“权”,则不论其“专废置君”之“不忠”。因此,若将“祭仲许宋”与《春秋》之中大夫专君之事比而观之,则不能不矛盾,对于祭仲的辩护,也只能恪守其“权”的一面。以董仲舒所论丑父为“借事明义”,尽管多少可以起到辩护的效果,但同样也只能恪守于“丑父欺晋”一事所表达的君不可见辱失尊,及与之相应的臣不可贱君、绝君的君臣大义,而不能推扩至“权”。将其与“祭仲许宋”进行比较解读,则不免自相抵牾。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这一辩护同样难以有效处理将“尊君”设定为“行权”的边界所可能引起的矛盾。这或许也是《公羊传》与何休均未以“权”——即便是以“不中权”的评价——论逢丑父的缘由⑦。
三、“执权”而非“行权”:一种合理化解读的可能
从“法斮”到“当斮”的一字之转,董仲舒明确表达了对逢丑父的贬抑态度。而借由比较“丑父欺晋”与“祭仲许宋”,董仲舒将国君之尊荣设定为臣子行权的边界,引起了“行权”与“尊君”的抵牾。我们或许可以认为:“权变”作为春秋时期形成的观念,隐含了突破“尊君”限度的可能,是《公羊传》不可形之于言的“微旨”。身处太平之世的董仲舒自然更为看重“尊王”“尊君”的大义,但其未能摆正“尊君”与“行权”的关系,将两个理应分属不同论域的范畴置于同一事件中,才引起了后来者的“背经”之讥。不过,若仅从“尊君”的立场出发,则董仲舒的这一“误读”也并非全然不可理解。
在《王道》篇中,董仲舒对鲁隐公、郑祭仲、宋目夷之事有一番总结:“鲁隐之代桓立,祭仲之出忽立突,仇牧、孔父、荀息之死节,公子目夷不与楚国,此皆执权存国,行正世之义,守惓惓之心,《春秋》嘉气义焉,故皆见之,复正之谓也。”[2](27)其中,隐代桓立、祭仲许宋、目夷存国,皆在外敌入侵或内临大乱之际以权变的方法维系了国家社稷。而仇牧在南宫万弑君之后率兵欲诛之,却被万击毙;孔父受命而立与夷(即宋殇公),但直到被华父所杀也没有违背先君之命;荀息受晋献公之命而立骊姬之子,终其一生信守诺言,最终为里克所杀。仅就事件本身而言,仇牧、孔父与荀息的行为与权变似乎并不沾边,但董仲舒将之与另外三者均归于“执权存国”。苏舆注曰“以存国为主,故许其权”[7](114),亦仅论及“权变”的含义。段熙仲以“行权”与“死义”为相互补充的两节:“能如祭仲之所为则行权,不能如祭仲之所为则死义可也。何者?行权不可必者也……若死义则操之在我者也。”[12]值得追问的是:此处所谓“死义”之“义”究竟为何?《玉英》篇中,董仲舒在比较目夷、祭仲与荀息、曼姑在行事上的不同后指出,四者“事虽相反,所为同俱为重宗庙,贵先君之命耳”[2](21)。所谓“重宗庙”与“贵先君之命”正可视为“死义”之“义”。董仲舒由此强调在国君废立问题上的臣子之节:“《春秋》之法,君立不宜立,不书,大夫立则书。书之者,弗予大夫之得立不宜立者也。不书,予君之得立之也。君之立不宜立者,非也。既立之,大夫奉之是也,荀息、曼姑之所得为义也。”[2](21)依据君臣大义,国君废置非大夫所能染指,即便嗣君并非嫡正,但只要受命于先君,大夫亦当奉之,故荀息、曼姑的行为仍可谓“义”。由此可见,董仲舒以“执权(存国)”而非“行权”概括六者,正体现出其更关注对于国家权力的持守,而非仅限于权变的一面。
在嘉许上述六人能够“执权存国”的同时,董仲舒更奖掖其能“行正世之义,守惓惓之心”,并指出《春秋》之所以要著录其事,是褒其能够“复正”。若仅就结果而论,上述六件事中或许只有公子目夷最终还君位于宋襄公可谓“复正”,其余五人无一得善终。隐代桓立,终究被弑,且蒙桓公以弑君之恶;祭仲许宋,却在公子忽被弑后未行讨贼的义务;仇牧死节,亦未能令弑君之贼伏诛;孔父、荀息也与其所欲存之君一同赴死,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臣子行事的成或不成,董仲舒似乎并不在意,只要志在维系或返归于“正义”,《春秋》皆嘉许之。故基本可以推断:董仲舒所谓“正”,或为嫡子继位之正,或为受命先君之正,或为君弑贼讨的臣子之正,一言以蔽之,则是君、臣、父、子的名分之正。
《春秋繁露》中的黄老诸篇亦可佐证上述观点。董仲舒的思想本身就呈现出与黄老、法家的亲缘关系⑧,就“权”之一义来看更是如此。《经法·六分》探讨人君如何掌握位权,施赏罚、定名位以驾驭臣子。倘若主弱臣强,形成“六逆”之势,则有乱兵亡国之患[13]。可见权位对于国君治国的重要意义。法家重“权”更不待言,《韩非子·内储说下》:“权势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为百。”[14](240)此为告诫人君权威不可下放,谨防臣下擅权、专权。《亡徵》则提醒道:“凡人主之国小而家大,权轻而臣重者,可亡也。”[14](109)所谓“家”当指大夫家,大夫专君之事于春秋乱世中屡见不鲜,亦是《春秋》所深恶痛绝之事。
以上观念皆可在《春秋繁露》的黄老诸篇中找到对应表述,如《立元神》篇曰:“君人者,国之元,发言动作,万物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端也。”[2](37)可见国君是国家政治的主轴、中心。《保位权》篇则更为看重君之威权,如“作威则君亡权”[2](39)。苏舆《义证》引《管子·版法解》曰:“君若使威利之权不专在君,而有所分散,则君日益轻,而威利日衰,侵暴之道也。”[7](170)权柄只能为君所专有,若君权下放,则有侵凌、暴乱之虞。又《保位权》篇:“国之所以为国者德也,君之所以为君者威也,故德不可共,威不可分。德共则失恩,威分则失权。失权则君贱,失恩则民散。”[2](39)“威”,即“威势、权力”[15],“威”成了君的本质属性,失其“威”或分其“威”则不成为君。《深察名号》篇中,董仲舒又以“权科”予“君号”[2](60),可知“权”是“君”的应有之义。在《王道》篇中,这一对“权”的理解更将《春秋》事例与“执权”之道贯通起来:“观乎世卿,知移权之败。”[2](29)又:“未有去人君之权,能制其势者也;未有贵贱无差,能全其位者也。”[2](30)此均为《春秋》大夫专政以至君弑国亡的经验总结。《十指》篇所谓“强干弱枝,大本小末,则君臣之分明矣”[2](33),更是董仲舒深感于汉初诸侯尾大不掉、招致叛乱的惨痛教训。君权与臣守之间的严格界限,与“尊君”作为行权边界的立论相合,可知,董仲舒重视“执权”——对权力的持守——要多过“行权”。
上述对于董仲舒“执权存国”的主张及其与黄老、法家的关系的分析旨在说明:比之于“行权”,董仲舒更属意于“执权”。在“丑父欺晋”的事例中,董仲舒认为:“其于义也,非君定矣。若非君,则丑父何权。”[2](18)他显然将对于君权的持守视为臣子行权的前提。此处所谓“非权”的断语,即揭示出以国君保有其威权为前提的臣子行事的限度。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董仲舒将“尊君”设定为“行权”的边界。当然,以上所论并不能为董仲舒可能存在的“背经”之误开脱,但至少我们可以对董仲舒思想进行更为全面的考察,提供一个理解其“丑父欺晋”诠释的支点。
四、结语
贾逵在申明《左氏》之大义长于《公》《穀》时指出:“臣谨擿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纪纲。其余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简小异,无害大体。至如祭仲、纪季、伍子胥、叔术之属,《左氏》义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权变,其相殊绝,固以甚远,而冤抑积久,莫肯分明。”[16]其所标举的《左传》之所长,在于“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纪纲”。相形之下,祭仲专断、废置君主而谓之行权,纪季据邑以叛而褒之以存宗庙,伍子胥弑楚君而曰复父兄之仇,叔术以嫂为妻、悖天子之命而让国,均是对君臣父子之“正义”的背叛。但《公羊》却均嘉许之,故谓之“多任于权变”。贾逵的这一论断固然有其争立学官的现实考量,却也触及了公羊家对于“权变”的论述所隐含的逾越礼义法度乃至君臣正义的可能。董仲舒试图张大君权、限制臣权的主张尽管有合理的一面,但其以“当斮”来贬抑丑父,更将“行权”与“尊君”两个理应分属不同论域的原则置于同一个事件的评价中,以至于违背了《公羊传》一贯的立论。徐彦将之归于“背经”之属也并非全无道理。
注释:
① 《公羊传》作“逢丑父”,董仲舒《春秋繁露》作“逄丑父”,据阮元校勘记,“逄”或为“逢”之误字。为便宜计,行文中统一为“逢丑父”,引文则依从原字。
② 事实上,围绕“丑父欺晋”一事历来存在两套并行的叙事。《公羊传》与《说苑·敬慎》均认为逢丑父被晋国的郤克所杀,但《左传》却记载逢丑父于临危之际大声疾呼:“自今无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于此,将为戮乎!”逢丑父经由为自己舍身忠君的行为辩护,被郤克赦免,以奖掖能够代君任患的忠臣。而齐顷公在脱困之后更是三进三出,可谓君臣相得。参见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第二十五,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96 页。
③ 可以追问的是:对于国君尊荣的维护是否等同于“尊君”?在“丑父欺晋”的事例中,逢丑父实际上维系了国君的个体生命,且齐顷公逃归齐国后,能够“弔死视疾”,齐晋交好,百姓得其荫庇。不过,正如董仲舒所引曾子之语:“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视死如归。”且《公羊传》中一贯秉持“国君一体”的立场,认为国君理应死社稷。在国君个体生命与荣辱之间,显然后者更为重要,因此,“尊君”首先代表的是维护君尊,而非其生命。参见董仲舒:《春秋繁露·竹林第三》,第18 页。
④ 如钟肇鹏主编《春秋繁露校释》即注之曰:“‘可以然之域’,‘然’,如此。此句指权要在可以如此作的范围之内进行。”赖炎元《春秋繁露今注今译》之说亦类似:“在可以然之域:在可以这样做的范围内,就是合于正道的意思。”参见钟肇鹏主编:《春秋繁露校释·玉英第四》(校补本),第144 页;赖炎元:《春秋繁露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6 页。
⑤ 事实上,《公羊传》“舍死亡无所设”与董仲舒“虽死亡终弗为”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前者为行权设定条件,后者则为行权划定边界。惜乎前贤多以两者为顺承的关系。如苏舆注“虽死亡终弗为”曰:“《传》云:‘权之所设,舍死亡无所设。’此复推勘其义。”所谓“复推勘其义”,显然认为董仲舒是顺《公羊传》而为言的。参见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玉英第四》,第76 页。
⑥ 这一辩护策略也同样值得怀疑。《左传·成公二年》记载的孔子之语体现出相同的逻辑,其言曰:“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若以假人,与人政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弗可止也已。”此处所谓“器”,当然首先指的是“曲县、繁缨”等礼器,但其所代表的却是权势与尊卑。上述逻辑可以归于典型的“滑坡谬误”(slippery slope),至少在“丑父欺晋”的事例中,齐顷公受辱逃归,不仅没有动摇其君位,甚至颇得民心。参见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第二十五,第691 页。
⑦ 值得注意的是,徐彦即以“丑父权以免齐侯”作为齐人得以善之的理由。不过,本文旨在论证将“权”的范畴引入“丑父欺晋”的诠释并不合适,故徐彦此说亦不为无病。换言之,“丑父欺晋”不是中权还是不中权的问题,而是与权无涉,更不能推扩至对祭仲的解读。参见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成公第十七》,第708 页。
⑧ 《春秋繁露》中黄老诸篇的作者始终存在争议,在现有文献与材料不足徵的情况下,本文无力也无意处理这一复杂的问题。桂思卓的观点可资借鉴:黄老诸篇中诸种观点往往相互龃龉,其作者可能并非一人,董仲舒撰写了部分而非全部黄老诸篇的内容。具体而言,桂思卓所认定为“黄老编”的篇目包括《离合根》《立元神》《保位权》《考功名》《通国身》《循天之道》与《天地之行》诸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在她看来,“这些篇章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们对儒家经典缺乏兴趣。它们的关注点是统治术,尤其是君主实践其政治权威的手段。它们是以一种高度综合的方式阐发这一问题的,而这种方式则融合了道家、墨家、名家及法家的观点,并以各家观点之混合体取代了在《春秋繁露》的第一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格调”。参见桂思卓:《从编年史到经典——董仲舒的春秋诠释学》,朱腾译,中国政法大学2010年版,第9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