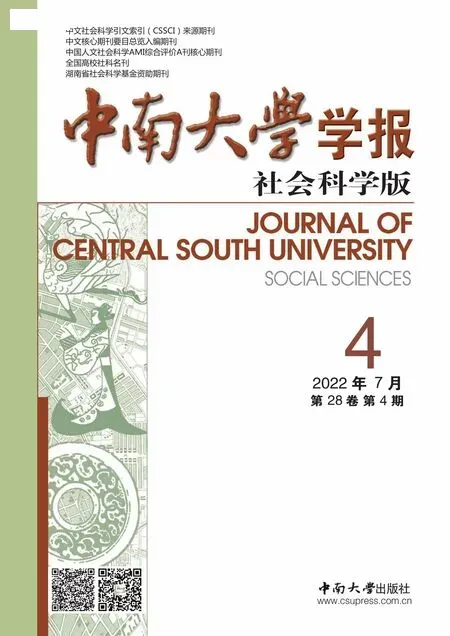反思罗马混合政体的兴衰
——波里比阿与马基雅维利的对照
陈浩宇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作为历史上一种理想政制的存在,罗马共和国吸引了古今政治思想家的关切。学界关于罗马共和政治的反思,构成了西方政治思想史的重要课题,而作为罗马共和政治之枢纽的混合政体,则成了具有典范意义的概念原型。作为一个被羁押在罗马的希腊人,波里比阿在《历史》第六卷留下了对罗马混合政体的经典描述,他将自己熟稔的希腊政体理论和政治思想,运用到罗马政治现实的分析中,通过考察罗马的政治体系来解释罗马共和国在军事行动和帝国扩张方面获得的巨大成就。历史学家莫米利亚诺在其研究中指出,波里比阿的著作在15世纪初被人文主义者莱奥纳尔多·布鲁尼(Leonardo Bruni)重新发现并开始传播;但是,他作为政治思想家的声名,特别是《历史》第六卷的重要性,直到16世纪初才首次得到马基雅维利和其他人的承认[1](19)①。马基雅维利是首位引述波里比阿混合政体理论的现代政治思想家,他基于这一理论在《论李维的前十卷史书》(Discorsi Sopra La Prima Deca Di Tito Livio,以下简称《论李维》)中就罗马兴衰阐发的不少观点,在现代政治理论的谱系中同样具有开创性。
混合政体被认为是罗马杰出的政治创造。波里比阿和马基雅维利均认为,正是混合政体中的权力制衡使得罗马政治体系保持稳健并富于活力,同时支撑了罗马共和国的持续扩张。那么,这一意在追求稳定和持存的政治制度为何最终走向覆灭,是需要许多思想家进一步探究的课题。波里比阿依循希腊政治理论及其背后的自然哲学,预判了罗马共和国的命运将无法摆脱自然的兴衰法则的制约;在罗马共和国覆灭后成长起来的基督教思想家奥古斯丁则断言,罗马共和国由内战走向灭亡体现了地上之城无法获得真正和平与正义的宿命[2](638-639);包括布鲁尼在内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围绕美德与自由概念,逐渐发展出一套对西欧历史世俗性质的叙说[3](168)。由此可见,马基雅维利是在吸取了人文主义探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罗马共和政体的覆灭提出了带有社会学意味的解释。与此同时,通过关注混合政体内蕴的可持续改进的可能,马基雅维利创造性地阐发了关于永久共和国的构想,开启了现代政治思想有关线性时间和持续进步的理念。
波里比阿和马基雅维利在针对罗马混合政体问题上的不同解释,为源自古典时期的概念、图式和原型如何曲折地进入现代政治理论提供了一个可资参考的案例,也会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马基雅维利与古典政治思想的关系。但是,学术界对这一问题众说纷纭,不少学者针对马基雅维利关于政治与道德的分离以及对古典道德观念和基督教的抨击,提出既然马基雅维利完成了与古典政治哲学的决裂,就应该被视为现代政治观念的奠基者②。与此观点相对应的是,有学者指出,马基雅维利政治思想背后的宇宙论框架和人性论预设有明显的前现代属性,因而质疑马基雅维利政治思想的现代性[4](153)。“剑桥学派”(the Cambridge School)的学者也强调了马基雅维利政治思想延续性的一面,认为马基雅维利在西方共和主义政治思想传统中扮演了承上启下的角色[5](121-142)。通过比较波里比阿与马基雅维利对罗马混合政体的讨论,将使我们对马基雅维利与古典政治思想的关系问题有更深刻的认识,并由此揭示出西方古今政治理论的一些重大差异。
一、从政体循环到罗马混合政体
波里比阿在《历史》一书中主要关注罗马在公元前3世纪末至2世纪中叶的崛起过程。在波里比阿看来,罗马对地中海世界的征服源自其持续稳健和充满活力的政治体系,这使得罗马在坎尼战败后能够迅速恢复,并最终战胜迦太基。因此,波里比阿将对政治事件的历时性叙述暂时中断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初期,选择在第六卷这个关键节点插入对罗马政治体系的分析。《历史》第六卷也便成了全书最受关注的篇章,在这一卷中,波里比阿依次讨论了六种简单政体构成的政体循环、罗马的混合政体及其各要素、罗马的军事体系以及罗马同其他共和国的政体比较。
马基雅维利认为,罗马在“整饬共和国”“扩张帝国”等方面树立了政治行动的范例,他因此选择评述罗马历史学家李维的《罗马史》,创作了《论李维》来将罗马共和国的范例呈现在世人面前[6](142)[7](56)。但我们必须指出的是,马基雅维利并不是在单纯复述李维等古典史家对罗马史的惯常看法,梳理罗马过往的政治实践。事实上,马基雅维利是将新颖的政治思考裹挟在对罗马史的回溯中,从而能够修正甚至挑战古典史家对罗马政治史所做的一般性判断[8](240)[9](157)。
在《论李维》第一卷的前两章,马基雅维利通过对共和国进行类型分析,迅速锚定了罗马在政治光谱上的位置。他特别指出,在法律与政制方面,与斯巴达的法律被莱库古(Lycurgus)一次性赋予不同,罗马的法律“是偶然地、多次地并且根据各种情势得到的”[6](148)[7](64)。马基雅维利认为,正是“由于平民与元老院之间的不和(disunione)”,使得单独某位统治者难以完成的创建混合政体的任务,“竟偶然做到了”[6](152)[7](68)。他的这一主旨判断正好与波里比阿相同。后者指出,与斯巴达的混合政体源自莱库古的精明筹谋不同,罗马人虽然为自己创造了相同的政体,但是“这绝不是理智而是许多斗争和试炼的结果”,他们是从挫折中吸取了经验和智慧,并最终使他们的政治体系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10](379)。
为了解释罗马混合政体的由来和特殊之处,马基雅维利回到了对六种简单政体和政体循环的讨论中,并以“一些著书论述过共和国问题的人说那些共和国是三种国家中的一种”开启了他对波里比阿不具名的引述。波里比阿详细地描述了每一种简单政体生成、发展和衰亡的自然循环,马基雅维利对此进行了精要的概述,却没有忽视其中的重点,特别是波里比阿特别关注的人的心理动机与社会行为之间的关联。基于这些理论细节,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马基雅维利引述的恰是波里比阿的文本③。马基雅维利论述说,在世界的开端,分散的居民为了更好地自卫,首先选举了一个更强健和勇敢的人成为首领。之后,随着人们意识到自身可能遭受恩将仇报等不义行为的侵害,为了施行法律和奖惩,就选举了更加谨慎和正直的人,由此产生了君主制。但当后来继承替代选举成为产生首领的方式,继位者很快就背离前人变得腐化堕落,这使得君主制蜕变为僭主制。对僭主的憎恨引发了反对他的阴谋,民众追随那些在地位和权势方面更为出众的人一起推翻僭主,并选择服从后面这些人的统治。对专制统治记忆犹新的经历使他们决定由自己制定法律实行自治,并且在各项事务中优先关照公共利益,从而建立了贵族制。但贵族统治者的后代很快也堕入了相似的轨迹,他们从未感受过不幸,也不满足于公民间的平等,而是转向贪婪与暴虐,由此产生了寡头制。民众的反叛使寡头制覆灭并建立了平民政体,但在这一制度之下,人民同样很快就变得肆无忌惮、各行其是,民主制蜕变为暴民政治,为了避免其中的放肆和损害,君主制重新得到了建立④。
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马基雅维利的概述没有失却波里比阿的论述重点。后者不仅意在描述政体循环的大体结构,而且尝试将政体的演变建基在人最基本的心理动机和行为倾向上,其中最重要的方面是,人对自身脆弱和不安全处境的感知。这种感知在很多时候源自对他人困境和苦难的感同身受。这促使人抑制自身的自利倾向以便采取互惠的行动,从而达到对他人和公共利益的尊重。具体来看,人最初是为了自卫才走向联合,并且是对不义行为可能加诸己身的忧惧才催生了法律和君主制,同样也是对此前暴虐统治的记忆维持了贵族制和民主制最初的良好局面。但是,当这种记忆消散,脆弱和不安全感被一种自得自满的状态所取代时,统治者便迅速放弃对自身行为的约束和对他人利益的尊重,变得贪婪、放肆,并由此推动了政体的转变。由于政体循环的机制最终可以归结到人这一普遍的心理动机,波里比阿由此可以认为,通过掌握这一理论,即使我们不能预测政体变动究竟会在何时发生,但假使我们不因“愤怒或仇恨形成偏见”,还是能够准确地判断出一个政治体系已经到达了“发展或是衰亡的何种阶段”,或是“它将在接下来遭遇何种转变”[10](378)。波里比阿对人的基本心理机制的描述与马基雅维利一贯持有的看法非常相似。马基雅维利将人的脆弱和不安全感理解为面对外在必然性的无能为力,人只在必然性的压力之下才会规范自己的行为。
波里比阿将政体循环看成是各种政治体系的发展、演变并重新开始的自然过程,它既是政体作为一个有机体不可避免的,也是历史图景的次序展开。但毫无疑问,六种简单政体都是不完美的,正如马基雅维利所说,三种坏的政体显然有害,即使是好的政体也是短命和易于腐化的。因此,马基雅维利指出,“在那些精明地制定法律的人认识到这个不足之后,就会避开这些方式各自本身,而选择一种可以将它们全都包括在内的方式,认为它更加稳定而持久:因为当在同一城邦内兼行君主制、贵族制和平民政体的时候,它们可以相互制衡”[6](151)[7](67-68)。和波里比阿一样,对于混合政体,马基雅维利强调的不仅是不同社会阶层皆被赋予权力而形成的职能分工,这种分工以制度化的形态体现在统治结构中,而且两人都着眼于不同政治行动者之间的相互制衡和牵制。唯其如此,每个行动者才能时刻意识到自己权力有限而不至于陷入自大自满,他的腐败倾向也才能被有效遏制。
对权力制衡的强调,使波里比阿与讨论过混合政体概念的希腊先辈们有了一些区别。修昔底德最早明确提到了政体层面的“混合”,在记述公元前411年雅典从寡头式的四百人政体转向更具包容性的五千人政体时,他认为,“现在,至少在我有生之年,雅典人首次拥有了一个好政体,它混合了少数人和多数人的利益,使得城邦从它曾经陷入的悲惨处境中开始恢复”[11](466-467)。希腊城邦一向面临着寡头和平民的纷争,与修昔底德类似,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也提倡一种调和民主制和贵族制的混合政体或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道政体。在考察了贵族派和平民派基于平等、血统、门第或财富提出的权力诉求后,亚里士多德指出,“他们的认识既不充分,所持的正义就都是不完全的,各人都只看到正义的某些方面”,正是这种偏狭的正义诉求带来了城邦内乱[12](136)。因此,亚里士多德对混合政体的讨论,更强调权力分配的正义性,以及对一种比例平等原则的贯彻[13](20)。波里比阿虽然袭用了希腊政治理论中的诸多概念,但是他在讨论罗马混合政体时,却更加关注权力之间的制衡及其达成的政治效果,而不是从预先设定的正义理念出发。因此,这种对政治机制和政治实效的关注,使得波里比阿与明显具有政治现实主义风格的马基雅维利更为相似。
虽然波里比阿探讨罗马混合政体具体形成过程的章节已佚失,但是马基雅维利对此有相关的讨论。虽然罗马最初建立的是王政,马基雅维利指出,“它的那些最初的体制,虽然不完善,但没有偏离可以将它们引向完美的正道”,因为罗慕路斯和其他诸王制定的许多法律也适应一种“自由生活”(vivere libero)[6](152)[7](68)。在罗慕路斯建立王国后,他便组建了一个提供意见咨询的元老院;而在罗马驱逐塔克文家族后,两个任期一年的执政官取代了终身制的王,因此罗马共和国已经综合了君主制和贵族制的元素,只待建立平民统治。
在共和国初期,平民和元老院保持团结,因为后者惧怕平民重新投向塔克文家族,马基雅维利指出,正是对塔克文的畏惧使贵族受到制约。但是随着塔克文一家人的去世,贵族的惧怕日渐消散,他们开始展露出对平民的嫌恶,并且用尽一切可能来侵犯平民。在马基雅维利看来,这恰好说明了他一直秉持的观点,“除非出于必要,人从来不做任何好的事情;但是在有充分的选择的地方,并可能利用放肆(licenza)的时候,每件事都立刻充满混乱和无序”[6](155)[7](70)。所以,在平民与贵族之间发生了许多混乱、争吵和冲突,这使得平民站起来反对贵族,而后者为了不失去全部的权力,被迫将平民所应得的那部分权力让与平民,并且为了保障平民的安全而创设了保民官。在这里,马基雅维利没有明确指出,保民官的创设来自公元前494年民众发动的第一次撤离,民众最初选举保民官是作为他们与贵族谈判的代表。在保民官创设之后,马基雅维利指出,“罗马共和国的体制变得更加稳固,因为在那里三种统治类型全都各得其所”,并且由于罗马“保持混合制,所以创造了一个完美的共和国;它到达这种完美状态是由于平民与元老院的不和”[6](153)[7](69)。
二、罗马混合政体中的权力互动:贵族与平民
由于波里比阿的相关讨论已经佚失,我们无从得知他是否也将保民官的创设视为罗马混合政体的初步形成。不过,我们可以发现,在波里比阿分析执政官、元老院和人民分别具有的权力时,保民官并未在人民权力中占据最显著的位置。虽然波里比阿提到保民官的立法否决权对元老院构成了重大制约,并且迫使元老院无法忽视民众在政治领域中扮演的角色,但是他认为人民的权力主要体现在对奖赏与惩罚的控制,这表现在进行审判、选举官职等方面[10](383)。这种奖惩权力的制度体现的是人民大会而非保民官。
我们并不意外波里比阿对保民官的评价不高。在西塞罗讨论罗马法律体制的《法律篇》中,我们甚至能发现有关保民官更为负面的看法。对话者昆图斯认为,保民官的权力“是一个有害的东西,它产生于国内的冲突,并趋于引发国内的冲突”;昆图斯细数了保民官犯下的各项“罪行”,包括“剥夺元老们的一切特权,它到处让最低等的人与最高等的人平等,并造成完全的混乱和无序”[14](233-234)。在昆图斯之后发言的西塞罗却认为,不应忽视保民官一职具有的长处。西塞罗为保民官一职辩护的方式带有强烈的精英主义色彩,他发言说,“我承认保民官的权力本身中就有恶的因素……但人民自身的权力更为残酷,也更为凶暴;与没有领导控制它相比,这种权力有时因为有领导控制而在实践上会更温和些”;保民官一职被视为一种怀柔的举措,是元老院以退为进的高明策略,“下层人相信他们被给予了与贵族的平等”并且被“引诱而服从贵族的权力”[14](235-236)。
马基雅维利虽然同样认为,民众需要一个头领对其进行领导,设立保民官能够以制度化的渠道来纾解民众的不满与怨恨。但是,与波里比阿和西塞罗不同的是,他提升了保民官的重要性,视其为民众一方阻止贵族侵犯、守护罗马自由、保障自身权利最重要的武器。马基雅维利指出,保民官“具有如此的声势和威望,以致后来他们总是能够成为平民和元老院之间的中间人,并阻止贵族的傲慢无礼(insolenzia)”[6](155)[7](70)。在权衡共和国究竟是应该把对自由的守护放置人民手里还是权贵的手里时,马基雅维利指出,罗马把对自由的守护置于平民之手,保民官便是为了守卫罗马的自由而设立的。
保民官的重要性可以从受它钳制的元老院和贵族的反馈中得到逆向证明。在《论李维》一书中,马基雅维利记叙了不少贵族试图限制和规避保民官权力的事例。如在第一卷第十三章,马基雅维利提到贵族借助宗教,反复拖延和规避保民官泰伦提利乌斯提出的限制执政官权力的法案;提到贵族一个常用的手段就是在保民官之间制造对立,收买某个保民官以反对其同僚试图推行的违反贵族意愿的计划。此外还提到一个值得注意的事件,就是发生在十人立法委员会(decemviri)引发的政治危机期间,罗马人为了制定法律选任了这个委员会,为了使他们能够毫无约束地进行工作,包括保民官和执政官在内的其他官职都被取消。十人立法委员会不受限制的权力使他们迅速演变为“罗马的专制统治者,并且肆无忌惮地压制它的自由”[6](243)[7](137)。外部战争的爆发使得十人立法委员会被迫召集元老院,在这种情况下,唯一保留了权力的元老院,尽管不满十人立法委员会的傲慢,却因为憎恨平民而不愿利用自己的权力来废除十人立法委员会。因为元老院认为,如果十人立法委员会自愿放弃自己的职位,可能就不会重新设立保民官了。之后,十人立法委员会中的阿皮乌斯又造成新的伤害,为了抗议,罗马平民进行了新的撤离,停留在圣山,“直到十人立法委员会放弃职位。保民官和执政官被重新任命,罗马恢复了其古老的自由体制。”[6](260)[7](150)
在马基雅维利对这一政治危机的叙述中,值得注意的不只有元老院为了宣泄自己的仇恨,限制平民的权力而置罗马自由体制于不顾的顽固,还能发现保民官一职的重建和其初创一样,都有赖于平民发动的政治抗争。因此,在马基雅维利笔下,贵族和平民的政治冲突,特别是后者对前者统治野心的对抗,在罗马混合政体初具形态后,仍在持续地型塑着罗马的政治体系,不断将它从对自由体制的偏离中矫正过来,并赋予这个政治体以新的生命力。在这个意义上,马基雅维利暗示了罗马混合政体的建构从没有真正完成,新的官职例如独裁官、监察官会被添加进去以应对形势的需要,而平民和贵族的冲突也使得政体的构建始终处于开放之中。如果罗马的混合政体始终处于未完成状态,并且具有持续改进的可能,那么我们似乎很难谈论这一政体的衰亡和覆灭。由此可见,马基雅维利突破了波里比阿将政体的兴衰看成是一种自然过程的界定,他对罗马混合政体的走向做出了全然不同的分析。
波里比阿和马基雅维利虽然都认为罗马混合政体的精髓就在于权力间的制约与平衡,但在具体描述罗马内部权力间的互动时,两人却做出了各有偏重的描述,体现出两位思想家在规范层面的不同取向。对于罗马共和国中的权力互动,马基雅维利更重视以保民官为代表的人民权力对贵族和元老院的制约,认为这种制约不仅必要,还更具正当性。马基雅维利将贵族和平民的冲突追溯到他们对立的倾向和脾性,其中贵族具有统治和压迫的欲望,平民则具有不受统治和压迫的欲望。在《君主论》第九章,马基雅维利认为,“在每一个城市里都可以发现两种不同的脾性,这都源于民众不愿意被贵族统治和压迫,而贵族则欲求统治和压迫民众。”[6](37)在两种欲求之中,马基雅维利指出,民众的欲求在一定程度上更具正当性。他指出,“自由的人民的欲求,很少对自由有害,因为这些欲求或者源于受压迫,或者源于担心就要受压迫”[6](157)[7](72)。与之相对,马基雅维利将贵族的占有欲和统治欲视为共和国纷乱和倾覆的根源。
马基雅维利的上述理解恰好与波里比阿的看法形成对照,后者更强调元老院或贵族在罗马政治生活中发挥的中枢作用。在波里比阿的讨论中,元老院的权力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对国库的控制,元老院对“所有国家收入和几乎全部开支”负责;其次是有权监督和介入所有需要公共权力处理的犯罪行为;最后则是在罗马接待使节或是派出使节解决纠纷,同时接受投降或是宣战[10](381)。波里比阿指出,正是权力的分工和制约,使得执政官、元老院和人民都不是自足的,“他们每一个的意图都能被其他方有效地抵制和阻碍”。但是,在波里比阿论述的不少细节中,我们可以察觉到他对三种权力的偏重。《历史》第六卷最后一部分是将罗马混合政体与其他共和国的政体相比较,以凸显前者的优越性。波里比阿认为,迦太基和罗马一样也是混合政体,但在进行第二次布匿战争时,迦太基的政治体系与罗马相比已经变得糟糕。因为民众是迦太基政治的主导力量,而罗马仍为元老院主导,因此罗马的政策便不是由大众而是由“最优秀的人”商讨形成的。波利比阿进一步认为,正是这一点就可以解释罗马为何在战争中最终击败了迦太基[10](408)。
除此之外,波里比阿认为,罗马人对待金钱的态度和宗教观念也优于迦太基人。正是宗教赋予了罗马以凝聚力,因为它深入了罗马人的公共和私人生活领域。宗教观念对普通民众尤其有用,基于此看法,波里比阿对民众进行了评论,他认为:“民众不论在何地都是轻浮的,因为他们被无法无天的冲动、盲目的愤怒和暴力的激情所驱使,所以唯一的选择就是用神秘的恐怖和所有这些精心设计的仪式来限制他们。”[10](411)
迦太基和罗马在权力分布和习俗制度方面的差异,也关联着波里比阿对政体自然生命过程的理解。政治体系和自然物一样会经历连续的成长、鼎盛与衰落的过程,处于鼎盛时期的事物无疑是最好的。迦太基和罗马处于不同的发展时期,迦太基在罗马之前变得强大和成功,现在已处于衰落阶段;罗马在布匿战争期间正处于鼎盛期。界定这一鼎盛期的标志,便是贵族在政治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由此可见,波里比阿眼中关于混合政体最理想的形态无疑是偏向于贵族的。处于衰落期的迦太基混合政体,偏离了这一理想形态,也预示了罗马混合政体的前景。
三、罗马混合政体的前景:民主革命或永久共和国
波里比阿将政体的兴衰更替视为一个自然的过程,作为混合政体的罗马也概莫能外。在波里比阿看来,罗马政体的“形成和发展始终是自然的”,在经历了发展和高潮之后,罗马的混合政体也会走向衰落,从而与自然法则相吻合[10](373)。罗马的未来不难预见,其衰落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外部的威胁悉数消失,罗马取得无可争议的霸权,由此安享一个相当长时段的繁荣。在这里,波里比阿敏锐地捕捉到了罗马可能面临的全新政治处境,也即由成功的军事征服和扩张带来的持久和平与安全⑤。他此前讨论政体循环时特别关注的人的社会心理机制,将同样作用于这个丧失了不安全感因而变得自满的世界帝国。民众的生活方式会变得奢侈,对政治职位的竞争也会变得异常激烈。波里比阿指出,民众要为政体的衰败负责,因为他们或者是为某些政治家的野心所伤害,或者是在其他人权力欲的激发和蛊惑下产生了虚妄的渴求,这使得“他们的所有决定都为愤怒和激情所激发,并且他们对于臣服于掌权者,甚至是与他们保持平等也不再感到满足”。民众希望自己掌控所有事情,诸如“自由”“民主”这类最具吸引力的词汇将会被用来描述这个新的政体,但实际上它是所有政体中最糟糕的暴民统治[10](412)。
波里比阿对罗马前景的预判,鲜明地体现出了希腊政治理论背后的自然哲学观念及其道德主张。罗马混合政体从生成、达到顶点、走向衰落并最后终结的过程符合亚里士多德式自然哲学对运动的理解。亚里士多德在对“自然”(physis)的分析中指出,“如果不了解运动,也就必然无法了解自然”。他将运动定义为潜能的实现,运动表现为一个过程,事物在这个过程中活动并实现,生与灭共同构成了一种重要的运动[15](68-70)。人事的生灭可以被进一步放置到一个循环论的宇宙观中,因为人类经验同样具有一种“自我实现和自我重复的‘自然过程’”[16](6)。
而当波里比阿将罗马混合政体的衰亡归结于随着帝国而来的民众权力的膨胀、平等原则的极端扩张以及道德失范时,他重复了希腊政治哲学家将政体类型与其生活方式紧密相连的看法,分享了他们对民主政体及其平等原则持有的批判性意见,也传达了希腊道德哲学用理性节制欲望、反对傲慢(hubris)和自满的主张。波里比阿预测这个民主政体坚持的极端平等原则甚至无法容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这一必要且基本的身份划分。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详细叙述了政体堕落序列中的“民主人”及其对应的民主制度,前者是平等主义的信徒,“他的生活没有秩序,没有节制”;民主人不允许任何管束或是等级区分,使得任何政治统治甚至是社会秩序都无法建立,这种对自由的过度追求导致了民主制的崩溃,极端的自由演变为僭主制中的极端奴役[17](338-342)。
文艺复兴时期的马基雅维利不是预判而是在现实中见识了罗马共和国的衰亡。在《论李维》第三卷第二十四章,马基雅维利指出,“由土地法激起的斗争(contenzioni)”和“治权(imperii)的延期”导致了共和国的瓦解[6](525)[7](529)。马基雅维利指出,土地法“在平民和元老院之间激起如此大的仇恨,以致最终演变为战争和流血事件,这超越了公民政体的一切规则和习惯的限度(fuori d’ogni modo e costume civile)。如此一来,由于公共官员对这件事无能为力,任何党派对他们都不再抱有希望,人们便诉诸私人解决办法(rimedi privati),每个党派都打算为自己选举一位首领来自保。”[6](249)[7](141)由此可见,平民和贵族的对抗一方面变得异常激烈,双方不再通过让步来妥协;另一方面也逸出了公共权威的框架,无法在现存的制度构架中加以解决,因此斗争从公共领域转向私人领域,对立双方均各寻首领以求自保。治权的延期则恰好为人身依附关系和私人派系的产生创造了条件。马基雅维利所谈的治权,主要是执政官的军事指挥权,随着罗马的征服半径日趋扩大,治权的延期也愈发显得必要。但是,治权延期一方面使少数几个首领长期掌握军事领导权并获得巨大声望;另一方面在长期的征战过程中,军队的士兵对将领产生了依赖,与罗马的公共生活和共和传统相脱离。马基雅维利从多角度通过阐发带有社会学意味的因果机制来解释罗马共和国的衰亡,这一部分的分析得益于他的人文主义前辈在历史探究方面的积淀,从而使他能够摆脱奥古斯丁的神学框架而提供一种带有强烈世俗性质的历史解释。
如果波里比阿将罗马混合政体衰亡的背景,设定为由混合政体支撑的军事征服带来的安全与繁荣,此种历史的悖谬特性在马基雅维利的分析中就会表现出另一个维度——罗马共和国的覆灭源自内蕴于混合政体结构中的权力对抗的激化。波里比阿预测某种民主革命将构成罗马混合政体的前景,认为民众要为政体的衰败承担责任;马基雅维利在判定责任时,仍然坚持了他的平民主义立场,同时对权力对抗机制进行了回护性的评论。他认为:“对平民来说,大人物的野心是如此大,如果在一个城邦里不通过各种手段和方法摧毁之,它很快就会使那个城邦毁灭。因此,如果关于土地法之争花了三百年的时间使罗马陷入奴役,那么,如果平民不是通过这个法律以及他们的其他欲望一直抑制着贵族们的野心,罗马陷入奴役可能会快得多。”[6](250)[7](142)
其实,马基雅维利不仅颠覆了关于罗马共和体制覆灭的责任的判定,他更试图突破波里比阿的作为一种自然过程的政体兴衰理论。在《论李维》第三卷第一章,马基雅维利一开始似乎重复了波里比阿的判断,他指出,“世间万物皆有其生命的限度,这是千真万确的事”,他接着论述说,为了完整地经历上天给它们指定的历程,“它们不使自己的机体紊乱,而是使之保持有序到如此程度,以至于机体要么不改变其形态,要么即使改变,这也是对它有利而不是对它有害”[6](439)[7](461)。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只有始终维持其原初秩序的机体才能够完整地经历其生命历程,这一判断也适用于“混合的机体”(corpi misti),比如共和国和教派(sètte),如果它们遭遇的改变能使它们回复到“初始状态”(principii)便是有益的。正是基于此,马基雅维利阐发了所谓“回到源头”的观点,他认为“这些机体如果不自我更新,就不可能持久”,而更新的方法“就是使它们回复到它们的最初状态。因为,所有教派、共和国和王国的源头都必然具备某些善(bontà),它们通过这种善重新获得最初的声望和发展能力。”[6](439)[7](461)与波里比阿不同,马基雅维利似乎在暗示,面对兴衰的自然法则,作为混合政体的罗马并非无能为力,政体的生命长度其实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只要罗马能够持续进行自我更新。
马基雅维利认为,共和国的自我更新可以由外部或是内部事件促发。外部事件指的是因为战败或其他灾难导致公民在德性层面自我检省和觉醒,内部事件可以区分为某个榜样人物的德行或是某种法律。马基雅维利指出:“使罗马共和国回到它源头的法律手段是保民官、监察官以及其他所有反对人们的野心和傲慢的法律。”[6](441)[7](462-463)保民官的重要性在这里又得到显现。其实,共和国达成自我更新的所有途径都是在限制人们的野心和傲慢,使他们回到政体初创时的心理状态,以便重塑对政治秩序的渴求、遵守与信赖。通过将政体中的人都暴露在联合与协作的必然性之下,迫使他们做出良好与互惠的举动。共和国的自我更新也意味着根据形势的需要,对法律制度做出调整,在这方面共和国优于君主国。马基雅维利指出:“共和国比君主国有更大的生命力和更长久的好运气,因为在一个共和国里,由于公民的差异性,它能更好地适应各种时机,而这是一个君主所不能做到的。”[6](481)[7](496)一个共和国能够推举出具备不同行事方式和才干的领导者,这会使它更好地适应变化的时代和处境。
在马基雅维利看来,罗马的混合政体蕴含着一种持续自我更新的机制。混合政体中的权力制衡与互动,特别是前文已经述及的平民和贵族的政治对抗,一方面发挥着纠偏的作用,另一方面则使政治体系始终处于开放状态,以持续回应民众的政治诉求。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即使共和国在其生命历程中面临着层出不穷的难题和意外,马基雅维利仍乐观地指出:“如果一个共和国如此幸运,以致它经常有人以身作则更新法律,而且不仅阻止它奔向毁灭,并且将它拉回,它将会是永久的。”[6](519)[7](524-525)回到源头是溯及政治体的过去,但通过回溯过去却指向了无限延展的未来,马基雅维利表明,罗马共和国可以是一个永久的共和国。
四、结论
波里比阿尝试从罗马的混合政体出发解释这个共和国在军事征服上获得的巨大成就,这是希腊政体理论面向政治现实的一次运用。在此之前,希腊政治理论家已经讨论过政体的不同类型、政体的演变等理论问题,波里比阿借助这些概念工具,对现实中的罗马政治体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当波里比阿从描述和解释层面向预测和理论阐发层面迈进时,他对政体兴衰必然遵循的自然法则的坚持,使其理论带有的希腊印痕更加明显。当然,波里比阿也敏锐认识到了罗马面临的全新政治处境,由成功的军事征服带来的安全和繁荣的帝国,超出了希腊城邦世界的构想。
作为历史事实的罗马共和国已为陈迹,但作为一种原型的罗马混合政体却持续生长在现代政治理论的构想中,成为一个被反复加以回溯的源头。在现代政治思想的开端处,马基雅维利发现并再度激活了波里比阿对罗马混合政体的讨论。他和许多后来者一样,虽然服膺波里比阿的基本解释,但在许多层面还是做出一些微妙的修改。例如,与波里比阿持有的精英主义偏向不同,马基雅维利展现了更强的平民立场,这使得他对罗马混合政体的界说更看重平民的角色和行动,并将贵族和平民的政治对抗置放在了核心位置。马基雅维利这种带有修正意味的解释,在晚近对罗马历史的研究中也得到了呼应[18](137-151)。
区别于古典政治哲学,在马基雅维利对罗马混合政体的论述中最具现代政治理论特点的,是有关政体能持续改进因而达至永久的判断。一个能够持续更新的混合政体,代表了一种持续改进和不断进步的乐观想法,并且不再承认自然法则对人事的限定性作用。政体不应按照古典政治哲学的教导本于“自然”,而应更多地依靠人力来维持[9](465)。依靠人力,也便意味着要充分发挥人的政治行动能力,甚至要有意调动人的扩张和获取欲望,而后者正是古典政治理论家试图加以节制的。从自然转向人力,同时意味着政治体丧失了某种确定的道德根基,不论这一根基表现为自然法、超越于城邦习俗之上的自然正当观念还是自然目的视野下的至善概念。正如马基雅维利对罗马平民和贵族的对抗性互动所预示的,现代政治的开放、多元和包容,以及经由妥协而达成的关涉全体公民的政治共识与共同利益,只能通过一种充满协商、竞争和对抗的政治过程本身来部分加以保障。
注释:
① 杰克·赫克斯特(Jack Hexter)发表于1956年的论文,开拓性地探究了马基雅维利获知《历史》第六卷具体内容的一个可能途径,参见J.H.Hexter,“Seyssel,Machiavelli,and Polybius VI: The Mystery of the Missing Translation,”Studies in the Renaissance,Vol.3,1956:75-96;晚近对赫克斯特论题的重述和捍卫,参见John Monfasani,“Machiavelli,Polybius,and Janus Lascaris:The Hexter Thesis Revisited,”Italian Studies,Vol.71,No.1,2016:39-48。对于波里比阿重现之前的混合政治理论,特别是中世纪的亚里士多德传统对马基雅维利的影响,参见James M.Blythe,Ideal Government and the Mixed Constitution in the Middle Ages,Princeton,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292-295。
② 代表性的研究参见施特劳斯:《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考》,申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Harvey C.Mansfield,Machiavelli's Virtue Chicag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22-24;Paul A.Rahe,“Situating Machiavelli,” in Renaissance Civic Humanism:Reappraisals and Reflections,ed.James Hankin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270-308。
③ 因此,虽然马基雅维利没有指明他引述的作者,但基于文段和论证思路的高度一致,可以毫无疑问地确定马基雅维利在这一部分的讨论源于波里比阿。对马基雅维利和波里比阿文本的细致对勘及相似性分析,可参见沃克尔(Leslie Walker)为其《论李维》译本所作的详细疏解,Leslie Walker,trans.The Discourses of Niccolò Machiavelli,Vol.2: Annotations,London: Routledge and Paul,1950:90。
④ 在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一部分,马基雅维利并没有完全使用传统上用来描述六种政体形式的希腊词汇或其拉丁及俗语转写形式:君主制(Principato)和僭主制(tirannico)比较明显是传统术语;马基雅维利用“gli Ottimati”称呼贵族制,“ottimate(i)”一词具有贵族、权贵的含义,对这个词汇的讨论可参见波考克:《马基雅维里时刻》,冯克利、傅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第108页;用“stato di pochi”称呼僭主制,字面含义为少数人的政制;用“il Popolare”称呼民主制,没有使用过“demokratia/democracy”等同源词汇;用“licenzioso”或“licenza”描述暴民政治,直译或为放纵、闲逸,马基雅维利用这个词描述了因民众对不受压迫或统治的过度欲求,导致的无统治、无政府的混乱状态。马基雅维利对术语的选用,一方面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追求纯正的古典拉丁语而避免使用希腊词汇有关;另一方面,马基雅维利或许受到了布鲁尼的亚里士多德《政治学》新译本的影响,例如布鲁尼使用“optimatium gubernatio”和“paucorum potestas”描述贵族制和僭主制,而非传统上采用的“aristocratia”和“oligarchia”,参见James Hankins,“Exclusivist Republicanism and the Non-Monarchical Republic,”Political Theory,Vol.38,No.4,2010:460-466。尽管马基雅维利没有使用和波里比阿完全相同的词汇,但两者试图表达的含义仍是高度一致的。
⑤ 可以对比政体循环中,波里比阿对民主制蜕变为暴民政治的讨论。按照我们此前的描述,波里比阿在这里强调的是民主政体下成长起来的新人已经遗忘寡头制的暴政,同时对民主制下的平等和言论自由原则习以为常。因此,人们(特别是富人)开始竞逐权力并带来腐化。波里比阿在这里的描述与希腊政治理论中对民主制蜕变的惯常描述更吻合,同时也不涉及罗马共和国因帝国扩张而面临的全新政治处境。参见Frank W.Walbank,Polybius,Rome and the Hellenistic world: Essays and reflec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