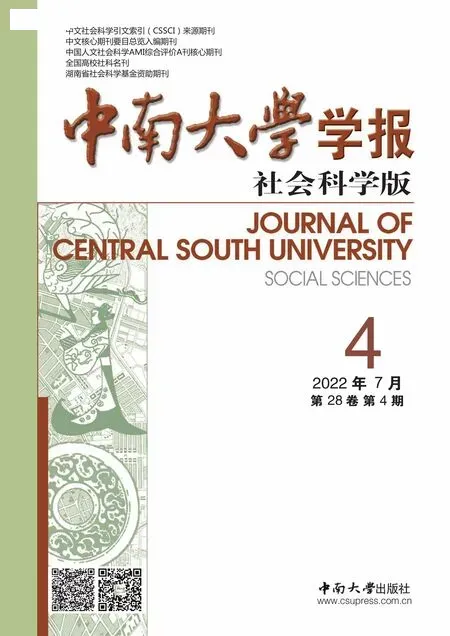纠缠的经典化评价历程:高启诗歌评论的传播与接受
晏选军,韩旭
(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在文学史中,一提及高启(1336—1374),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四库馆臣的一段话:
启天才高逸,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其于诗,拟汉魏似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似宋,凡古人之所长,无不兼之。振元末纤秾缛丽之习而返之于古,启实为有力。然行世太早,殒折太速,未能镕铸变化,自为一家,故备有古人之格,而反不能名启为何格,此则天实限之,非启过也。特其摹仿古调之中,自有精神意象存乎其间。譬之褚临褉帖,究非硬黄双钩者比,故终不与北地(李梦阳)、信阳(何景明)、太仓(王世贞)、历下(李攀龙)同为后人诟病焉。[1](1472)
这是关于高启诗歌创作具有典范性的评述,对后世影响深远,迄今的文学史书写依然大体延续这一观点。同时,这也是一番云遮雾罩的评述,有切中肯綮处,也有自相矛盾之处,结论更是似是而非,令人难以捉摸。一方面,四库馆臣说他革新元末纤秾缛丽之习而返之于古,允为明诗冠冕;另一方面,却又说不出这位诗坛巨擘具体风格为何。一方面,说他学汉魏学六朝学唐宋,兼备古人之格,似乎高启心摹手追的,全在汉唐风调;另一方面,又说他虽不能浑融自成一家,却又自具一种精神气象,非前后“七子”所能比拟。这些说法,均不免枝枝节节,难切其真精神。至于将“行世太早,殒折太速”作为高启诗歌来不及形成自家面目的理由,更显得宿命气息太重且缺乏逻辑:高启年三十九去世,诗作流传至今者凡两千余首,众体兼擅且佳作时见,又“据明一代诗人之上”,如此尚且不能“自为一家”,不知将置明代三百年其他诗家于何地,也不知将置文学史中行世殒身更早、作品存世数量更少的贾谊(33 岁)、谢朓(36 岁)、王勃(27 岁)、李贺(27 岁)、纳兰性德(31 岁)等人于何地?显然,这一评述有必要重新思考[2-3]。
中国传统的诗文评论,多构建在感悟式的阅读印象基础之上。感悟式的思维方式,重直观把握而轻理性分析,重过程体验而轻概念厘定,强调个体的审美感受和当下体验,将文本评论建立在审美经验的积累之上。四库馆臣对高启其人其作做出上述评价,正是这样一种典型的阐述形式,也是中国古典审美经验不断累积强化的结果。目前,古代作家、作品的经典化,引起了研究者越来越多的关注[4-6]。经典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往往与传播及接受过程中评价导向的不断强化有关,与评论者自身的背景与态度有关,而对于作家作品评论本身的这一经典化过程,则学术界的关注度似显不足。笔者以为,以对高启的这番评价为例,考察其渊源所自及构建过程,对解析文学传播过程中导向性评价的形成,对理解文学经典的生成机制,当有积极的意义。
一、复古与新变:历代关于高启诗歌的评价考述
从高启在世时将作品结集开始,历朝历代的评论者均注意到高启鲜明的复古拟古倾向,不论持肯定或者否定的态度,都认为这是高启诗歌创作的突出特点,其成败得失均与此密切相关。同时,评论者们大都认同高启诗众体皆备、学无常师,在变革元末诗风、首倡明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评论经过明清两代的传承与接受,最终以四库馆臣所说的“凡古人之所长,无不兼之”,成为高启诗歌风格的定论。
洪武初年高启还在世时,他的朋友为他的诗集作序,就多次指出他的作品和他的诗学主张均有意拟古和法古。如王彝(?—1374)说:“盖季迪之言诗,必曰汉魏晋唐之作者,而尤患诗道倾靡。自晚唐以极,于宋而复振起,然元之诗人,亦颇沈酣于沙陲弓马之风,而诗之情益泯。自返而求之,古作者独以情而为诗。今汉魏晋唐之作,其诗具在,以季迪之作比而观焉,有不知其孰为先后者矣。”[7]他称高启以汉魏晋唐诗作为典范,并以此去框定高启的诗歌风格,考察的结论是高启的创作实绩与他的主张完全吻合,认为他的作品置于汉魏晋唐作者之林亦不逊色。高启的朋友张羽(1333—1385)在京师赋诗以寄,即以复古相期:“新词典赡推摩诘,古体优长羡达夫”;“肯从大历开元已,重拟清谈学唾壶。”[8](778)洪武三年(1370)三月,王袆(1322—1374)序高启《缶鸣集》,认为高启诗作隽逸清丽、不假雕饰,可以“追古之作者以为并”,自成一家面目[9](980)。同年,高启多年的老友兼同乡、同僚谢徽(1330—1397)分别为《凤台集》和《缶鸣集》作序,称赏说:“季迪家姑苏,自少年之时,出语已惊流辈,及老,工于诗,厌世俗之体近凡,遂弃不复习,悉取唐诸家之作者师焉。每一篇出传,啧啧叹赏,于是古之习俗一变,而季迪之诗名亦因是而起矣。”[10](425)“始季迪之为诗,不务同流俗,直欲趋汉魏以还及唐诸家作者之林。每一篇出,见者传诵,名隐隐起诸公间。”[9](982)按照谢徽的说法,高启声誉鹊起的关键原因,就在于效法前人,专意以复古为高。
洪武七年(1374)高启被牵连入魏观案因祸去世,友朋纷纷赋诗作文以为悼念,也多从诗人积学师古故而积蕴丰厚的角度表达惋惜和叹赏之情。如张适(1330—1394)在诔文中叙及高启学诗的经历时说:“君谇砺于学,尤嗜诗。诗人之优柔、骚人之凄清、汉魏之古雅、晋唐之和醇新逸,类而选为一集,名曰《效古》,日咀咏之。由是为诗,投之所向,罔不如意;一时老生宿儒,咸器重之,以为弗及。”[9](1013)这是说高启学诗伊始即专意拟古仿古,通过涵泳古人以澡雪精神,最终得以卓然自成一家。又如张羽在悼诗中称:“赖有声名消不得,汉家乐府盛唐诗。”[8](792)金珉(生卒年不详)悼诗:“幸留名不朽,妙句逼唐音。”[9](1018)他们和王彝一样,都将高启诗与汉魏乐府及盛唐诗等同并列。高启在世时,友朋多强调其作具有鲜明的拟古倾向,同时代文人对高启诗作的相似性评价,逐步建构起后人的阅读印象。
高启去世之后,明代诸家论者继续从复古的方向评述其诗作,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印象。如林右(1356—1402)谈到阅读高启诗作的印象:“当今诗独盛于吴,吴之诗,独推高公季迪。余得其诗而读之,诚无愧于唐人者也。”[11](11)永乐元年(1403),周传论及高启,称其诗:“言选则入于汉魏,言律则入于唐。音响调格,宛然相合,而意趣或有过之。”[12]其时去高启生活的时代不远,二人均认为高启诗歌的高妙之处恰在于其音响格调仿佛汉唐。正统年间,释善启(1370—1443)指出:“季迪众作皆得体,如律仿刘长卿,选兼韦应物,皆人所不到,宜其为最。”[13]弘治、正德年间,李东阳(1447—1516)评价高启说:“国初称高、杨、张、徐。高季迪才力声调,过三人远甚,百余年来,亦未见卓然有以过之者,但未见其止耳。”[14](1375)廖道南(1494—1547)评价高启说:“其为诗也,波起云涌,颷号电掣,直超脱元宋而上宗盛唐,近代诗人未之能及。”[15](45)二人均将高启诗视为明诗的高峰,并且可以直接接续唐人。顾起纶(1517—1587)在《国雅品》中,开宗明义,列高启为“雅品”第一:“高侍郎季迪,始变元季之体,首倡明初之音。发端沈郁,入趣幽远,得风人激刺微旨。故高、杨、张、徐,虽并称豪华,惟季迪为最。”[14](1090)至于朱存理[10](57)、吴宽、穆文熙、李腾鹏、何白[16](142-169)等人的评论,也都是以高启诗歌拟诸唐调而略无愧色的角度,对其复古所达到的高度予以肯定性评价。胡应麟(1551—1602)认为:“高太史诸集,格调体裁不甚逾胜国,而才具澜翻,风骨颖利,则远过元人。昭代初,雅堪禘祢。”[17](342)许学夷(1563—1633)说:“季迪才情特胜,五言古唐体可二十篇,直逼李杜,国朝李、何而下所无;歌行多出青莲,而才力豪迈,当为称首无疑。”[18](397)他们或称高启独得风人之旨,或称其首倡风雅,言下的推尊赞赏之意很是明显。其实,诸家所说的意思有一点是一致的,即都肯定高启在首变元音、发轫明代文坛方面,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至清朝,这种观点更为论者所反复申说。朱鹤龄(1606—1683)以为高启诗歌“义合风雅,语兼哀艳,直可嗣响唐音,称骚人苗裔”[19](377)。缪泳(1623—1702)详举高启诗歌与古人的渊源,说:“季迪诗,自《古乐府》《文选》《玉台》《金楼》诸体,下至李、杜、王、孟、高、岑、钱、郎、刘、白、韦、柳、韩、张,以及苏、黄、范、陆、虞、揭,靡所不合,此之谓大家。”[13](143)这就将张适所说高启专意拟古而编《仿古集》的内容和做法具体化了。叶燮(1627—1703)认为高启成就的取得,就在于他复古而不尽为古所囿:“兼唐宋元人之长,初不于唐宋元人之诗有所为轩轾也。”[20](5)沈德潜(1673—1769)谓高诗:“上自汉、魏、盛唐,下至宋、元诸家,靡不出入其间,一时推大作手。特才调有余,蹊径未化,故一变元风,未能直追大雅。”[21](8)
至乾隆年间,四库馆臣继承了上述看法,并且对此观点作了更为全面的阐释发挥。《四库提要》在强调高启作品复古倾向的同时,也指出高启因师法前人、遍参古人而积蕴丰厚,得以一改元末纤缛秾丽之风,振而返之于古,成为明诗冠冕。换言之,在四库馆臣看来,高启积学师古而能不尽为古法所拘,“自有精神意象存乎其间”,避免了如前后七子一样食古不化的弊病,开有明一代风气。这种观点颇具辩证色彩,见解可谓深切,但实际上也没有脱离对前人阅读经验的继承和发挥。此后诸家的评论,多沿其波而循其轨[22](2098)。
二、分歧的焦点:高启是否因“复古”而“未能自为一家”
从明至清,虽然论者对高启众体皆备、变革诗风的努力都表示了充分的肯定,但对于高启诗歌取得的成就,则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分歧的焦点,就在于高启是否因“行世太早、殒折太速”而“不能自为一家”。一种观点认为高启因早逝故而未能摆脱摹拟的习气,其中又以四库馆臣的评价对后世影响最大;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高启在世时诗文创作即已臻化境,早逝并不能对其成就构成根本的影响。检讨其说,均有承续的痕迹可循。
第一种观点最早可溯至高启同时代的李志光的评价。洪武八年(1375)二月,距高启去世未及半年,李志光在《凫藻集本传》中论及高启诗,就有如下评说:
工于诗,上窥建安,下逮开元,大历以后则藐之。天资秀敏,故其发越特超诣,拟鲍谢则似之,法李杜则似之。庖丁解牛,肯綮迎刃,千汇万类,规模同一轨。……蹇连以殁,年甫三十九。嗟乎!使启少延,则骎骎入曹、刘、李、杜之坛,奚止此哉
虽然李志光并没有表示高启因早逝导致了不能自成一家,只是说限制了诗人能够达到的高度,但已然清晰流露出诗人因为早逝故不能摆落摹拟习气而得以圭臬诗坛的意思。
景泰元年(1450),刘昌(1424—1480)序高启诗集时,表达的意思和李志光大体相同,也对诗人天不假年的遭遇满怀惋惜惆怅之情,“先生死始三十有九,使少优游而待之,则得将止于是乎?言将止于是乎?行将止于是乎?呜呼!天实为之,谓之何哉!”[9](986)至成化、弘治年间,吴宽(1435—1504)为重刻高启《缶鸣集》作序:
独其胸中萧散简远,得山林江湖之趣,发之于言,虽雄不敢当乎子美,高不敢望乎魏晋,然能变其格调,以仿佛乎韦、柳、王、岑于数百载之上,以成皇明一代之音,亦诗人之豪者哉!所恨蚤死,未见其所止何如,君子为之慨叹。故庐陵杨文贞公评诸诗,独夸其乐府拟古及五言律为胜,其意亦可识矣。[23]
吴宽同样认为高启堪称“诗人之豪”,但诗人早逝直接影响了他的成就。他还引用杨士奇(1366—1444)对高启的评价,来说明杨之所以独夸高启的古乐府和五言律而不及其他,“其意亦可识”,实即别有深意在焉。杨士奇确实说过:“季迪近体,五言律胜;其古体,则乐府及拟古胜。”[24]但他并没有对高启的作品做总体评价,只谈及自己的阅读印象。显然,吴宽据此引申发挥,正指向了诗人因早逝而不能兼综众体,因此思之未免让人“为之慨叹”。清朝前期的李重华(1682—1755),则将刘昌、吴宽等人的言外之意说得更为显豁:“高青丘骨性秀出,最近唐风。惜其中路摧折,未入于室。”[25](927)他强调高启宗唐复古,却因中路摧折未能登堂入室,其中“未入于室”的说法,就很接近四库馆臣所谓“未能自为一家”的意思了。
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时,四库馆臣采用了这种看法,并作了经验式的引申发挥,既肯定高启“天才高逸,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又致憾于其“殒折太速,未能熔铸变化,自为一家”,隐含之意是高启在创作上本会有更辉煌的前景。可以说,四库馆臣的说法,可以从李志光开始找寻到清晰的沿袭承传处,且越往后其影响似乎越大。如对高启推崇备至的赵翼(1727—1814),也不免有此遗憾:“惜乎年仅三十九,遽遭摧殒!遂未能纵横变化,自成一大家。”[26](125)晚清时期的诗评家朱庭珍(1841—1903)的观点与沈德潜相近,都承认高启为变革元风的大匠,甚至达到了“超凡入圣”的境界,但又认为他所师虽广,所拟虽似,却因早逝未能融会贯通,致使他未能取得更大的成就:“青丘才力、天分、工候,皆极其至,所为诗,自汉、魏、六朝,及李、杜、高、岑、王、孟、元、白、温、李、张、王、昌黎、东坡,无所不学,无所不似,妙笔仙心,几于超凡入圣矣。惜不及四十枉死,未及融会贯通,聚众长以别铸真我,造于大成,亦可哀矣。”[22](2359)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高启生前就已卓然成家。如高启去世不久,其学生吕勉就在《槎轩集本传》中,对老师不幸早逝表达了深切的哀惋,对老师的成就作了极高的评价:
诗之高古类魏晋,冲澹如韦、柳,和畅如高、岑,放适如王、孟,质直如元、白;乐府多拟汉制,其新声虽张籍、王建所不逮。数千万言,兼乎众长,出人意表;不啻良金美玉,取重于时,布帛菽粟,可用于世。老杜所谓道眼前句,先正所谓随事命意、遇景得情,自唐以来,为世诗豪,而自成一大家者也。天何靳其才,年止于斯!设使登下寿,所就又可量耶?[9](997)
对比之前所列李志光的评价,作为门生的吕勉的判断则截然不同,他虽然也致憾于老师的早逝,但认为这无碍于老师在文坛“为世诗豪而自成一家”的崇高地位。李、吕两人的分歧,恰在于高启的拟古是否能够自成一家。
清雍正六年(1728)七月,金檀(1660?—1730)在编纂笺注高启诗集后,特意对天不假年而限制了高启成就的说法,作了一番辨析:
论者曾谓四杰诗名,先生视杨、张、徐三家实为独绝,苟天假之年,所得犹未止是。夫南渡尤、萧、范、陆四家,当时亦谓萧不早夭,不止诚斋敌手。然此皆深服其所造,深惜其不永,非以诗犹未诣其极。况萧诗几湮晦,而先生诗,人奉拱璧,所由使名齐者实出其下,是其才力岂易至欤
金檀历时四载详注高启诗歌,涵泳既深,手眼自高,其论说也别出心裁。他举宋“南渡四家”中早夭的萧德藻为例,如同方回在《瀛奎律髓》中说萧如不早逝虽杨万里诗格亦有不及一样,对普遍流行的高启中年横遭摧折而憾恨不已的看法提出了质疑,认为此一观点经不起事实的检验,只是读者敬服惋惜的情感投射,并不是高启诗歌造诣未至精深,恰恰相反,高启诗歌在创作上的“才力”已达到了难以企及的地步。强行将造诣与年寿牵扯到一起全无必要,还易形成误解。何况萧德藻的诗歌存世数量极少,尚且有论者为之鸣不平,“吴中四杰”中的杨基、张羽、徐贲三人,其成就公认远不如高启,加之高启诗作存世数量甚多,人人奉若拱璧,这些都与萧德藻的情况大不相同,更没有理由怀疑他足以自成一家。金檀的判断和高启的门生吕勉基本相同,而论述更为精辟。
同年十二月,陈璋(生卒年不详)序高启的《凫藻集》,也专门就此问题进行了讨论:
谓先生若不死而天假之年,其所得当不止于是,余窃以为非笃论也。夫文章之道,视乎才力。人之才力不同,大抵盛于壮而衰于晚。先生之诗与文,自少已工,洎中年而学识具足,著作大成;一时词人学士,罕有及者。天亦若恶其满而遽覆之,又何疑其犹未至欤!今观周氏(按指高启内侄周立)手钞之文,气体醇茂,何必不两汉?词章清丽,何必不六朝?文澜壮阔、思理精邃,何必不三唐两宋?洵可以为元、明之一人,而独有千古矣!即起先生于今日,而请之操觚,当不过是。[9](1025)
陈璋反驳天不假年影响成就的观点,提出即使起高启于今日也是如此,因为高启在壮年时即神完气足,诗文创作已臻大成,故而寿命的长短与成就的高下没有必然的正比关系。他和历代评家一样,全面肯定高启表现出的浓郁复古拟古色彩,不仅独步元、明,更可称“独有千古”罕有及者,遭厄早逝不影响他的杰出成就。
在四库馆臣的评论出现百余年后,吴仰贤(1821—1887)对这一看法提出了异议:“虽然,诗者易为而难工者也。有终身为之而不工者,有为之即工、急于行世而自悔少作者。若年不及中寿,其诗卓然成家而传于后世,以予数之,如谢宣远(朓)年三十六、王子安(勃)年二十八,高季迪、何大复(景明)年皆三十九,高子业(叔嗣)年三十七,宗子相(臣)年三十。历代不过数人,即谓之享大年可也。”[27]因为诗歌易为而难工,所以有得者有不得者,与年寿关涉不大,王勃、高启等人年虽不及中寿,但并不妨碍他们以诗卓然自成一家,与诗坛得高寿、享盛誉者并无二致。
通过上文的梳理可以看出,对高启的复古拟古和元明之际变革诗风的成就,历代评论家均无异议,但对于高启早逝与能否卓然成家之间的关系,论者的看法则呈现出两极分化的倾向。整体而言,持吕勉、金檀类似观点的人并不多,而四库馆臣之说迭经流布,影响深远,俨然成为评价高启的定论。
三、高启诗评接受过程中的文学生态与历史语境
高启的诗歌在明后期被“人奉拱璧”,与他被视为“有明第一诗人”的地位相关,而这一地位的确立,也是历代文学评论者在不同的文学生态和历史语境下,逐步推尊的结果。
元明易代之际,高启的知名度远远小于同时期另一位吴中巨擘杨维祯(1297—1370),他在文坛获得显著的名声和影响力,是入明之后的事情。按谢徽的说法,洪武三年左右,高启才开始“名隐隐起诸公间”,而经过洪武一朝后,高启已被林右推为吴中第一诗人:“当今诗独盛于吴,吴之诗,独推高公季迪。”其声名鹊起的背后,是明初官方对文艺的引导与意识形态的建构。明王朝建立伊始,朱元璋等人对儒家思想作了反复的强调,以力矫元末弥漫着的不加约束的世俗化和个性化倾向,并有意识地在文艺领域倡导所谓的“盛世之音”。于是,温柔敦厚、怨而不怒、含蓄蕴藉等崇儒复雅的审美趣味,成为文艺与意识形态的共同诉求,而高启中和典雅的诗风恰好符合官方意欲重新建构文学评价体系的要求。高启宗唐复古、众体兼擅的诗格足以扭转元风、振刷文坛,这是他们众口一词推崇高启的原因。
到了成化年间,高启已从“吴中四杰”“北郭十子”的群体评价中脱颖而出,一跃成为东南文坛第一诗人。如果说同时期文人对高启的评价还带有友情、地缘因素,或是出于意识形态构建的需要,那么几经朝政更迭后,高启则凭借自身的创作实绩,逐渐脱离了时代语境的束缚,得到了文人群体的普遍认可。这从张泰(1436—1480)的一段话中可见端倪。张泰,苏州府太仓人,号称“娄东三凤”之一。张泰自述初入翰林院时,“院长南阳李公、永新刘公谓余言:‘尔苏之诗,在当朝惟高太史为然,独言文必举金华宋学士也。’比修《一统志》,已疏其为郡之第一人矣。”“南阳李公”指李贤(1409—1467),官至少保、吏部尚书兼大学士、知经筵事,以功业闻名于世,史称“自三杨以来,得君无如贤者”[28](4677)。“永新刘公”指刘定之(1409—1469),历官翰林编修、礼部左侍郎,尤以文名享誉一时。二人在当时均有较大影响力,他们共同推崇高启为吴中第一诗人,显然带有一种权威认可的意味,而作为后辈的张泰自然地接受了这一评价,称“余服膺二公确论,后莫有能易此”[9](988)。在精神领域,人们普遍有一种“权威崇拜”的意识和习惯,与权威人物的论调保持一致更容易获得心理上的安全感。在这种心理的综合作用下,就有了事实上的权威效应。
弘治、正德年间,内阁首辅李东阳评价高启为明朝百余年来“未见卓然有以过之者”。李东阳主持文坛数十年,论诗主张宗唐复古,又是当时“茶陵派”的领袖人物,他对高启的评价显然已超越吴中或者东南的地域性范畴,而将之提升到整个明代文坛的视野之下。在其后的评论中,跟随李东阳的论调者甚众,如胡应麟肯定高启“诗家者流正宗巨擘”的地位[29];明清之际的卢世㴶(1588—1653)认为“明诗当以高青丘为大宗”[30];叶燮认为“有明之初,高启为冠”[20](5);王士祯(1634—1711)称高启为“明三百年诗人之冠冕”[31](56)。赵翼《瓯北诗话》论明三百年诗坛,惟取高启一人,“高青丘后,有明一代,竟无诗人”,推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惟高青丘才气超迈,音节浏亮,宗派唐人,而自出新意,一涉笔即有博大昌明气象,亦关有明一代文运。论者推为开国诗人第一,信不虚也”[26](124-130),赞赏高启独得风人之旨,革新流弊而返之于古,故允为明诗冠冕。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入明以后,论者对高启复古与新变的诗风总体持肯定性评价,肯定他独特的才情和清新雅致的诗风,肯定他在元明之际拯偏救弊的努力。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倾向不断被强化,高启在文坛的地位也一路走高。与之相应,高启诗歌在明初的影响力主要还局限于吴中与浙东地区,其后渐渐突破地域性限制而波及全国。这与时代知识流动方式的变化密切相关。尽管高启生活的元明之际出版业较为活跃,但受个人经济条件、藏书空间、行迹流动的限制,以及书商在利益驱使下选择性出版的制约,文人能够获取的书籍相对有限,知识流通相对较为缓慢。书籍是文人间主要的沟通媒介,书籍互借、赠送、交换、传抄等形式是文学接受最主要的形式[32]。高启同时代的文人,也就只能靠这样的形式才能一窥其作,换言之,文本流通的局限性,限制了高启诗歌向更广阔的地域传播。例如,洪武初年,高启的同乡谢徽曾说:“予访之吴淞江上,季迪出其诗示予,盖取旧所集诸诗,益加删改,汇粹为一,总名曰《缶鸣集》。”[9](983)金华人胡翰(1307—1381)也在此时才得读高启诗集:“吴郡高君季迪,少有俊才,始余得其诗于金华,见之未尝不爱,及来京师,同在史局,又得其所谓《缶鸣集》者阅之,累日不倦。”[9](979)可见,当时与高启有着密切文学互动的文人,多来自同一地域,这也可以从高启诗歌的早期评论者这里得到印证,如王彝(嘉定)、张羽(吴兴)、王袆(金华)、林右(临海)等,都是活跃于东南地区的文人;谢徽、张适、李志光、刘昌都是高启同郡长洲人,吕勉是高启的门生,应当也生活在此一地区。成化以后,诗集的阅读评论者地域渐殊,如邓州李贤、永新刘定之、茶陵李东阳、蒲圻廖道南、德州卢世㴶等。这恰与其时出版行业的繁荣保持同步,开放的社会风气和活跃的商业氛围促进了知识的传播和流动,也为文人文集传播和影响力的扩大提供了便利条件。
发展至乾隆年间,四库馆臣对高启诗歌的评价,几乎成为不刊之论,且影响至今。刘衍文先生认为:“人以青丘为明代第一诗人者夥矣。又以后之神似太白者,无有及乎青丘者也。青丘自是天姿颖发,且巧于仿效,而自身之面目则犹未成长定型也。”[33](454)20世纪60年代,游国恩先生在主编《中国文学史》时,评价高启说:“他的诗歌,众体兼长。摹拟取法,不限于一代一家。虽然因为死于壮年,未能熔铸洗练,自成一家,内容也不够广阔深厚。但才华横溢,清新超拔,不愧为明代成就最高的诗人。”[34](60)进入21世纪,章培恒、骆玉明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虽高度肯定了高启诗歌表现出的尊重自我、追求个性的精神,但依然不无遗憾地说:“假如他不是在朱元璋的屠刀下过早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沿着这样的创作道路走下去,也许会在诗歌创作中取得更大的成就。”[35](14)刘衍文先生和章培恒、骆玉明先生都在论述中提到了四库馆臣的评价,游国恩先生对高启的评价更是这一论说的复述。人天生具有认知能力和思考能力,在思考过程中,借鉴他人经验是自主获取知识的首要方式,他人的经验或评价有助于确认或否定自己的想法。在一代代文人对高启诗文的阐释中,不断累积的阅读经验和印象评述,开始逐渐表现出某种趋同性,使得后世对高启诗歌的评价有走向刻板的倾向。刻板印象一旦形成,就成为一种导向性的解读,伴随着文学史的发展而反复强化。
四、致中和:高启的诗学思想与审美品格
对高启诗歌的评价历程,正是其人其作不断走向经典化的历程。在这个传播与接受的过程中,主导性的评价一旦形成,就会发挥恒久稳定的影响。即便人们在解读高启自身的文学思想的时候,也难免会受到以四库馆臣为代表的评述的影响,自觉不自觉地强化这种印象。
笔者以为,抛除刻板印象的影响,仅就高启而论,其人遭际乱离,又不幸死于非命,留存下来的理论著述并不算多,也缺乏系统性,但这并不能掩盖其文学思想的丰富性,如《缶鸣集自序》《娄江吟稿自序》等篇,其精辟独到之处仍时时可见。被后世评述称引最多的,是他的《独庵集序》:
诗之要,有曰格,曰意,曰趣而已。格以辩其体,意以达其情,趣以臻其妙也。体不辩,则入于邪陋,而师古之义乖;情不达,则堕于浮虚,而感人之实浅;妙不臻,则流于凡近,而超俗之风微。三者既得,而后典雅冲淡,豪俊秾缛,幽婉奇险之辞,变化不一,随所宜而赋焉。如万物之生,洪纤各具乎天,四序之行,荣惨各适其体,又能声不违节,言必止义,如是而诗之道备矣。夫自汉、魏、晋、唐而降,杜甫氏之外,诸作者各以所长名家,而不能相兼也。学者誉此诋彼,各师所嗜。……故必兼师众长,随事摹拟,待其时至心融,浑然自成,始可以名大方而免夫偏执之弊矣。[9](885)
这是高启在洪武三年为好友释道衍(1335—1418)诗集所作的序文,其中的关键是拈出格、意、趣三要素,认为三者俱不可偏废,格以辨师古之体,意以达感人之情,趣以臻超俗之妙。创作之时,三者俱备且彼此相济相融,则多种艺术风格,无往而不达。按照高启的理解,汉魏以降,诗坛虽然名家辈出,但除了杜甫之外,诸家因无法做到格、意、趣相兼,均不免于偏执。杜甫之所以迥异流俗而兼备众体之长,即源于他能实践自己“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的创作主张。基于此,高启明确提出,创作需“兼师众长,随事摹拟”。只有转益多师,拓宽取法的途径,挫笼参会诸家之所长以扩充己意,如此,才能在遍参古人的基础上自成一家,并昭示自己独特的价值。从理论上看,高启的这一见解确实有见地,因为任何艺术创造都离不开对前代丰富遗产的继承,况且,“兼师众长,随事摹拟”并非目的,而是手段和方法,仅仅做到这两点尚且不够,还需“待其时至心融,浑然自成”,博采众家之长,力求圆融贯通,方可成为大方之家而避免偏执之弊。很明显,高启崇尚的是一种致中和之美,一种集大成之美。
从创作实绩来看,高启兼综博采,学无常师,这些特点在他的诗作中多有表现。许多作品不唯形似,而且神似,其迈往高逸之致,自见于楮墨之外。学古而不泥古,高扬主体精神,挫笼万有而神完气足,正是诗人高启的成功之处。他的很多诗歌,均跳脱了简单的摹拟因袭,而真正达到了他努力追求的“时至心融,浑然自成”境界,别具一家面目。这与后来风行明文坛的复古论者袭古人体貌、仿前人声调,却神理索然的优孟衣冠作风,是有着很大的差别的,而与其时会稽杨维祯法古以师心的主张,则有着内在根本的一致。杨维祯为高启前辈,且两人活跃于同一地域,也是易代之际最为重要的两位诗人,面对杨维祯追求奇崛雄健之风太甚,时有陷入险怪纤秾、粗豪放荡流弊的负面倾向,高启强调格、意、趣三者,要求澡雪精神,全面提升诗歌的美学品味,其中应当不无拯偏救弊的用心。
高启的诗歌创作,不仅实践、印证着自己的理论主张,而且在某些方面还深化乃至拓展了他的这种审美理想,今存《高青丘集》中的名篇杰作时见。以其代表作《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为例,历代吟咏金陵兴衰的传世名篇很多,如刘禹锡的《金陵怀古》《金陵五题》,王安石的《金陵怀古》〔桂枝香〕,萨都剌的《登石头城次东坡韵》〔念奴娇〕等,高启的这首诗取法前人,而又能自出机杼,堪与前贤把臂,亦自具豪迈雄健和沉郁苍凉的风格。此诗作于洪武二年(1369),虽以称颂明王朝统一天下作结,但全诗横亘今古的历史时空感使它显然有别于一般的承平颂圣之作,是饱经战乱之苦的诗人对和平生活强烈期盼及由衷喜悦的自然表达。像这样的佳作,终明之世,鲜有能与之匹敌者。又如其七古《明皇秉烛夜游图》(卷八),七绝《期诸友看范园杏花风雨不果》(卷一七)、《客越夜得家书》(卷一八),七律《吴城感旧》(卷一四)、《谒伍相祠》(卷一五),五古《见花忆亡女书》(卷六),等等,都是意象浑成的上乘之作,且风格多样,呈现出不同的风貌,难作整齐划一之论。
很明显,无论是高启的创作主张还是其创作实际,他追求的都是一种自然的美、中和的美,而不单单偏嗜某一种或某一类风格。或许正因为缺乏像杨维祯的“铁崖体”一样带有强烈个性标志的主导风格特征,才造成了后世对他“未能熔铸变化,自成一家”的负面评价。事实上,高启的诗歌,很难说似汉魏还是似唐宋,否则,他既不可能雄踞明代诗坛冠冕的宝座,也不能在文学史上享有如此崇高的地位,任何低估他的创造性的看法,都是失之公允的。
在一代代评论者反复讨论高启诗歌“复古”与“新变”、是否“自我一家”的过程中,高启的文坛地位也在不断提升,直至获得“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的冠冕。一方面,历朝历代对高启的评述都强调高启取得的突出成就和在元明易代嬗变之际的地位;另一方面,诗人在易代之际英年早逝的命运、诗人复古以创新的创作倾向、诗人风格的多样性等因素综合在一起,又促使部分评论者理所当然地认为,高启未能摆脱摹拟窠臼进而自成一家,限制了他的文学成就。这样一种纠缠夹杂、似是而非的观点,从高启去世一直延续至今,经过评论者的反复强化得到广泛传播,迄今仍然影响着高启的文学史书写和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