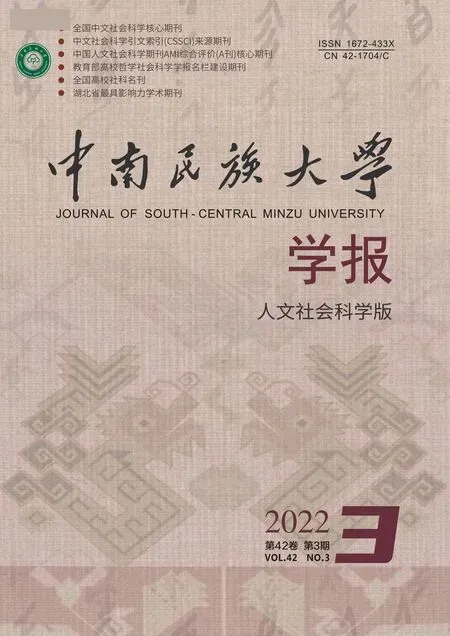王逸“所作《楚辞章句》只有十一卷”说辨证
——兼论《七谏》“以下五篇”亦王逸注无疑
力 之 岑贞霈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就笔者目力所及,“王逸……所作《楚辞章句》只有十一卷”说,出自黄灵庚[1];《楚辞章句》的《七谏》“以下五篇”——黄先生所说的《七谏》《哀时命》《九叹》《惜誓》《大招》之注,其出自王逸之手向无异议(1)此前,学者多仅认为《九思》之“序”与“注”非王逸作。其实,《九思》之“序”与“注”同样均为王逸所作,详参岑贞霈、力之《〈楚辞·九思〉序/注作者辨及辨之方法问题》(《中国诗学》,2019年第7期)。;异议亦始于黄先生,即其王逸未注《七谏》“以下五篇”说。黄先生认为:“王逸所辑《楚辞》本有十六卷(篇),但是其所作《楚辞章句》只有十一卷,依次为《离骚》、《九辩》、《九歌》、《天问》、《九章》、《卜居》、《渔父》、《招魂》、《招隐士》、《九怀》。有可能王逸作《楚辞章句》未竟而卒,故但存十一篇,而《七谏章句》以下五篇皆阙然未注,故六朝时期流传《楚辞章句》只有十一卷。今本《七谏》以下五篇的注释,恐非出自王逸,盖深得王逸注《楚辞》微旨奥义者所作。大概为其子王延寿或王逸之后、东汉一无名氏所作,然仍托名为‘校书郎中王逸作’。”[1](2)黄先生后已注意到“王延寿死在王逸之前”,参其点校《楚辞章句》(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之《前言》。又,黄先生此《前言》与其《楚辞章句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之《增订版前言》二者,其相关观点一仍《〈楚辞〉十七卷成书考辩》一文。其理由主要有二:一,据唐前相关文献,王逸《楚辞章句》只有十一卷/十一篇;二,“《七谏章句》以下五篇”与“只有十一卷”之“六朝时期流传的《楚辞章句》”存在差异[1]。
黄先生之文献功力殊为深厚,于“《楚辞》学”作出过杰出的贡献,尤其是于王逸之学,向为笔者所十分敬重。然笔者认为其说虽大启吾人之思,却难以成立。而这些问题本身,关涉到《楚辞》最重要注本——《楚辞章句》之整体性等十分重要的学术问题,故殊有进一步研讨之必要,而迄今为止,尚未见有学者对黄先生上述观点作系统之辨证。另外,关于《九思章句》,黄先生之“《九思序》及其注,绝非东汉时人所作,而作于六朝之世,极有可能在南朝刘宋之后”[2]说同样是难以成立的,然此前笔者已为文说之[3],故兹主要是辨证其王逸“所作《楚辞章句》只有十一卷”说与王逸未注《七谏》“以下五篇”说。
一、六朝流传的王逸《楚辞章句》十一篇说辨证
黄先生认为,六朝流传的王逸《楚辞章句》十一卷十一篇,范晔《后汉书》王逸本传没有说《楚辞章句》篇数“有问题”,而《文心雕龙·辨骚》所说“当是刘勰当时所据《楚辞》本子的篇目”,《隋志》之“屈原……著《离骚》八篇”包括《九辩》[1],等等。而在笔者看来,这些问题均甚有进一步商榷之空间与价值,兹别而说之。
(一)关于《后汉书》王逸本传之“二十一篇”所指
为了证明六朝流传的《楚辞章句》是十一卷十一篇,黄先生引《后汉书》王逸本传之“王逸……著《楚辞章句》行于世。其赋、诔、书、论及杂文凡二十一篇”后说:
令人不解的是,王逸所著赋、诔、书、论、杂文以及《汉书》皆有篇数,唯独《楚辞章句》语焉不详,未著其篇数。……说明范氏著《王逸传》时,并不存在《楚辞章句》有“十六卷”或“十七卷”的本子。但是,范氏没有具体记载《楚辞章句》的篇数,只笼统地说“其赋、诔、书、论及杂文凡二十一篇”。这段文字是有问题的。好在今有六朝遗物《王逸集》的“象牙书签”得以参证,这个疑案也由此可以破解。“象牙书签”记载云:“初元中,王公逸为校书郎,著《楚辞章句》及诔、书、杂文二十一篇。……”所谓“二十一篇”者,原来包括《楚辞章句》在内。这正是范氏《后汉书》记载疏误之所在。[1]
“‘二十一篇’者,原来包括《楚辞章句》在内”云云,显非圆照。张政烺《〈王逸集〉牙签考证》说:“此牙签与本传之文繁简虽殊,而大端则一。”[4]204这当是符合实际的。在引姚振宗之“案史言赋、诔、书、论,论或即此《正部论》,当时编入本集二十一篇中。《意林》载王逸《正部》十卷。十卷者,别有集二卷见下《别集类》。盖阮氏《七录》分此八卷入此类,馀二卷入《文籍部》,本《志》仍之也”之说后,张先生“按”云:“姚氏之说是也。”[4]205笔者亦认为姚说近是。而此“象牙书签”所说的“二十一篇”不可能“包括《楚辞章句》在内”。黄先生于此恐百密一疏了——没有注意到范晔说到传主注书/文与著书/文之不同:前者往往不说多少篇,如黄先生上揭文所引《马融列传》之“注《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所著赋、颂、碑、诔、书、记、表、奏、七言、琴歌、对策、遗令,凡二十一篇”[1];而后者则多说之,如卷八十上《文苑列传》之“杜笃……所著赋、诔、吊、书、赞、《七言》《女诫》及杂文,凡十八篇。又著《明世论》十五篇”[5]。其实,整部范晔《后汉书》无一处是将所注诗文之篇数与所著诗文之篇数相合的。概言之,据范氏未著《楚辞章句》“篇数”,那是无法说明其“著《王逸传》时,并不存在《楚辞章句》有‘十六卷’或‘十七卷’的本子”的。黄先生又说:
《隋书·经籍志》:“梁有王逸《正部论》八卷,后汉侍中王逸撰。亡。”又有“《王逸集》二卷”。……《正部论》八卷本,虽在隋、唐之世已佚,然至今尚有遗文残简,如,《艺文类聚》卷八三《宝玉部》上“玉”条引王逸《正部论》云:“或问玉符,曰:‘赤如鸡冠,黄如蒸粟,白如猪肪,黑如纯漆。玉之符也。’”据此可以断定,《正部论》八卷(即八篇)属于“杂文”之类。《王逸集》二卷(即二篇)当是包括“诔”“书”“赋”“论”等的王逸的诗文总集。如果《隋志》记录可靠,在“二十一篇”中除去《正部论》八卷,再除去《王逸集》二卷。则六朝时期所流传的王逸《楚辞章句》应为“十一卷”本(即十一篇)。[1]
此可谓“百密一疏”——“《王逸集》二卷”怎么可能“即二篇”,而其“当是包括‘诔’‘书’‘赋’‘论’等的王逸的诗文总集”?何况,即就今存文献言,如“赋”,古书尚引有其《荔支赋》《机妇赋》与《瓜赋》(3)前二者,分别见《艺文类聚》卷八十七“菓部下·荔支”与卷六十五“产业部·机”;后者,见《齐民要术》卷二“种瓜第十四”。等。概言之,范氏这段文字根本没有问题;而此“象牙书签”记载对证明《楚辞章句》有多少篇没有任何意义。换言之,这里的“六朝时期所流传的王逸《楚辞章句》应为‘十一卷’本(即十一篇)”云云,乃缘说者于相关文献之“关键处”解读存在疏忽所致。
(二)由《辨骚》无法辨“十一篇”之下限及《释文》序次如何
在据“象牙书签”记载而“已解决了”《后汉书》王逸本传之“二十一篇”如何后,黄先生接着究“六朝时期流传的王逸《楚辞章句》十一卷本,包含了哪些篇目?其篇次先后又是怎样的”等问题。其云:
刘勰《文心雕龙·辩骚》则透露出一条很重要的信息:“故《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远游》《天问》,瓌诡而惠巧;《招魂》《招隐》,耀艳而深华;《卜居》标放言之致,《渔父》寄独任之才。……自《九怀》已下,遽蹑其迹,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自《骚经》至《九怀》凡十一篇,当是刘勰当时所据《楚辞》本子的篇目。“自《九怀》以下”(今按:引文作“已”)云云,则指《七谏》、《九叹》、《哀时命》以下汉人的《楚辞》作品,不包括《九怀》一篇在内。那么,刘勰所依据的《楚辞》本,《九怀》一卷殿其后。值得注意的是,刘勰以《招魂》、《招隐》两篇同类并列,且《招魂》在《招隐士》之前,这与《楚辞释文目录》前十一卷的篇次稍有区别,这就是:《离骚》、《九辩》、《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魂》、《招隐士》、《九怀》。说明《楚辞释文》虽为五代的王勉所作,但是《楚辞释文》的篇次,基本上保留在南朝萧梁之前王逸《楚辞章句》的旧貌,确实要比以作者时代先后为次的今本目录古奥。[1]
于此,“自《九怀》已下”即以“《九怀》”为“已下”之上限,故刘勰不评及“自《九怀》已下”各篇。因之,“不包括”云云乃思欠周之所致也。故“自《骚经》至《九怀》凡十一篇,当是刘勰当时所据《楚辞》本子的篇目”说显然是不能成立的。何况,即使“不包括”云云能成立,由于还存在“已下”数篇,“刘勰所依据的《楚辞》本”便自然不止十一篇。此其一。其二,黄先生辨刘勰合《招魂》而论者为《招隐》而有注云:
《招隐》,原作《大招》,据《楚辞章句》明正德黄省曾、高第刻本与明隆庆朱多煃刻本改。《楚辞释文目录》以《招隐士》为第九、《招魂》为第十,故刘勰《招魂》、《招隐》合而论之。说明刘勰所据《楚辞》目录的篇次,与《释文目录》同。后人据以作者时代先后为次的今本,易《招隐》为《大招》,讹也。[1]
这可谓就部分说部分而忽视就整体以考察部分,如就《辨骚》之“故《骚经》《九章》……《渔父》寄独任之才”说作整体性的考察,便不难看出:刘勰“合而论之”者,乃缘其内容与风格方面之共性而非关乎“篇次”。即据此仅知其所本为王逸《楚辞章句》,而对考察是书篇次如何则没有意义。“与《释文目录》同”云云,非是。试看:
①《骚经》,②《九章》,③《九歌》,④《九辩》,⑤《远游》,⑥《天问》,⑦《招魂》,⑧《招隐》,⑨《卜居》,⑩《渔父》(《辨骚》);
①《离骚》,②《九辩》,③《九歌》,④《天问》,⑤《九章》,⑥《远游》,⑦《卜居》,⑧《渔父》,⑨《招隐》,⑩《招魂》(《释文目录》)。
两相比较,更易明白《辨骚》之与《释文目录》,难有什么关系。而由于后面有“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招魂》《招隐》”之“《招隐》”显然是如唐写本作“《大招》”(4)杨明照先生说:“‘招隐’,徐火勃校作‘大招’。冯舒云:‘“招隐”,《楚辞》本作“大招”。下云“屈宋莫追”,疑“大招”为是。’按徐校冯说是。唐写本、张乙本、训故本、广广文选并作‘大招’,未误。”(氏著《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8页)显而易见,杨说是符合刘勰之意的。——“屈、宋逸步”自然以“屈、宋”之作为范围,如何会涉及淮南小山之文?总之,无论如何,据《辨骚》所说,都是无法得出“自《骚经》至《九怀》凡十一篇,当是刘勰当时所据《楚辞》本子的篇目”这样之结论的(5)龚红林先生之“黄灵庚依据出土的魏晋或北朝文物之‘象牙书签’,证实六朝时期流传的是‘王逸注《楚辞》十一卷’本,并依据《文心雕龙·辩骚》文得出《楚辞》十一卷的篇目及顺序:《骚经》(注:《离骚经》)、《九章》、《九歌》、《九辩》、《远游》、《天问》、《招魂》、《招隐》、《卜居》、《渔父》、《九怀》。亦推论《隋书·经籍志》著录屈原‘《离骚》八篇’之篇目:《离骚》《九辩》《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屈原作品篇目及真伪探究的疏理与思考》,《云梦学刊》2018年第4期)之说,未为圆照。。
(三)关于《隋志》“《离骚》八篇”是否包括《九辩》
关于这一问题,黄先生指出:
《隋书·经籍志》说:“楚有贤臣屈原,被谗放逐,乃著《离骚》八篇。”《隋志》这个说法,与汉代“屈原赋二十五篇”又不相同。如果据《楚辞释文目录》来观照,其实也不难理解。汉人尊《离骚》为“经”,居于篇首,故六朝以后凡屈原《离骚》以外之作,皆以《离骚》称之。如,宋晁补之作《重编楚辞》十六卷,“首篇曰《离骚经》,后篇皆曰《离骚》,余皆曰《楚辞》”。《释文》目录,自《离骚》至《渔父》为八篇。《隋志》所谓“乃著《离骚》八篇”,正是指《离骚》《九辩》《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八篇。《九辩》本是宋玉之作,以其次于《离骚》之后。之所以如此……是依据屈原作品的内证。《离骚》:“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天问》:“启棘宾商,《九辩》《九歌》。”两例《九辩》皆在《九歌》之前。所以,尽管《九辩》为宋玉所作,王逸还是据此排列,置《九辩》于《九歌》之前。近从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得见王国维手校汲古阁《楚辞补注》本,发现王氏在《楚辞目录》下有批语说:“按《九辩》、《九歌》,皆古之遗声。《离骚》云:‘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故旧本《九辩》第二、《九歌》第三。后人以撰人时代次之乃退九辩(引者按:“九辩”应加书名号)于第八耳。”其说与吾若桴鼓相应。可见,《楚辞释文》的目录篇次,确是保留了王逸《楚辞章句》的旧貌。正因为如此,六朝人遂目《九辩》以为屈原所作。《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引屈平曰:“国有骥而不知乘,焉皇皇而更索。”这两语明明是出于《九辩》的诗句,非屈子所作,而认定为“屈平曰”,就是一个显证。《隋志》“八篇”说,说明《九辩》一篇不次《渔父》之后,而在《离骚》之后、《九歌》之前,混杂在屈原作品之中。六朝时期流传的王逸《楚辞章句》是十一卷本,其篇目排列的先后次第,除《招隐士》一篇外,与《楚辞释文》的目录篇次基本相同。[1]
在笔者看来,这同样未免“百密一疏”。其一,《隋书·经籍志》集部《楚辞》类小序之相关文字如下:
楚有贤臣屈原,被谗放逐,乃著《离骚》八篇,言己离别愁思,申杼其心,自明无罪,因以讽谏,冀君觉悟,卒不省察,遂赴汨罗死焉。弟子宋玉,痛惜其师,伤而和之。[6]
这里明明说的是“屈原……著《离骚》八篇”而“宋玉……伤而和之”,故此“《离骚》八篇”者断不可能包括《九辩》。即《隋志》所说的“《离骚》八篇”之“篇次”与《楚辞释文》的篇次不可能相同。而此“八篇”指的应为《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及《大招》。理由是,王逸《大招序》曰:“《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7]清姚振宗云:“此以景差《大招》一篇为屈原作,故云‘八篇’。”[8]近是。至于黄先生所引王氏之“批语”,其对佐证这“《离骚》八篇”是否包括《九辩》无任何意义。又,晁补之撰《重编楚辞》十六卷,确如其《离骚新序中》说的那样——“首篇曰《离骚经》,后篇皆曰《离骚》,余皆曰《楚辞》”。问题是,晁氏此“皆曰《离骚》”者,不包括宋玉之《九辩》而含其认为是屈原所作的《大招》。即其与黄先生所说之意正相反。试看晁氏之说:
刘向《离骚楚辞》十六卷,王逸传之。按八卷皆屈原遭忧所作,故首篇曰《离骚经》,后篇皆曰《离骚》,余皆曰《楚辞》。……《大招》古奥,疑原作,非景差辞,沉渊不返,不可如何也,故以终焉。为《楚辞》上八卷。《九辨》《招魂》,皆宋玉作,或曰《九辨》原作,其声浮矣。……至刘向最后作,故其次序如此。此皆西汉以前文也,以为《楚辞》下八卷,凡十六卷,因向之旧录云[9]。
这里有二点值得注意:第一,“屈原遭忧所作”之“八卷”者有《大招》;第二,“曰《离骚》”者,均为屈原“所作”。因之,黄先生据晁氏之“首篇”云云只能佐证其说无法成立。
其二,“依据屈原作品的内证”云云,或可以说明前人“置《九辩》于《九歌》之前”具有某些理由。问题是,既然“《九辩》为宋玉所作”,其便不可能置之于屈原所“著”者中。即此“内证”对证“《离骚》八篇”是否包含《九辩》,起不到任何作用。另外,说“置”者为王逸,也缺乏根据。总而言之,“《隋志》这个说法”,对“《楚辞释文》的目录篇次”是否“保留了王逸《楚辞章句》的旧貌”一事,毫无意义。因之,“六朝人遂目《九辩》以为屈原所作”说便失去了应有之支撑。至于曹植《陈审举表》引宋玉《九辩》“国有骥”云云而称“屈平曰”,盖因《九辩》为代屈原设言之作所致(6)参力之《楚辞学三题》,《广西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需要注意的是,代屈原设言之作与屈原之作非完全是同一回事。
一言以蔽之,“《隋志》‘八篇’说”完全没有包括《九辩》之可能,故以其包括《九辩》来展开研讨所得的结论均不能成立。如这里的“六朝时期流传的王逸《楚辞章句》是十一卷本,其篇目排列的先后次第,除《招隐士》一篇外,与《楚辞释文》的目录篇次基本相同”说,即一显例。
二、“两种书在魏晋六朝以前并行”说与二者注者不同说辨证
黄先生认为,“《七谏章句》以下五篇”独立为书而非王逸所注,至于六朝时期所流传的王逸《楚辞章句》则“应为‘十一卷’本(即十一篇)”。其云:
这两种书在魏、晋六朝以前并行存在,各自独立,没有混合为一书。理由是:王逸作《楚辞章句》,重点注释《离骚》。故《离骚章句》一篇最为详赅,始释字义,次释句意,终讲明章旨,是一篇标准的“章句”体。《九歌》、《天问》、《招魂》三篇内容比较庞杂,也以“章句”体注释其义。《九辩》、《九章》(《惜诵》一篇除外)、《远游》、《卜居》、《渔父》、《招隐士》、《九怀》诸篇内容相对较为简单,皆用韵文形式释义,极少单独释字义。此为王逸所独创,或三言,或四言,或七言,言简意赅,错落有致。皆非标准的“章句”体。颇为值得深味的是,《七谏》以下五篇,内容要比《九辩》、《九章》等更为单纯、明白,若为王逸所注,则必用韵文的形式。恰恰相反,自《七谏》以后,注文皆一律用“章句”体,注文的行文风格与前十一卷也略有差异,截然为两种不同的书。或许这种韵文式的“章句”,继作注释者并不擅长,或是做不好,或是做不出来。[1]
确实,《七谏》以下五篇没有“用韵文的形式”。然尽管如此,黄先生之《七谏》以下五篇王逸“皆阙然未注”说之种种理由仍均难以成立。首先,如上所说,《文心雕龙·辨骚》之“自《九怀》已下”包括“《九怀》”,而其“耀艳而深华”前之作品为《大招》而非《招隐》。其次,就《九章》注言,《橘颂》《怀沙》“以‘章句’体注释其义”;《涉江》《哀郢》“以‘章句’体注释其义”比“用韵文形式释义”多;《抽思》“乱曰”20句除2句无注外均以双句为一释而“以‘章句’体注释其义”,主体部分以一句为一释而有连续的6句“以‘章句’体注释其义”;《悲回风》“用韵文的形式”与“以‘章句’体注释其义”大略各半。再次,“更为单纯、明白”云云恐只是黄先生之看法,至于王逸是否如是观则不得而知。另外,在历来公认这五篇同样为王逸注之前提下,“若为王逸所注,则必用韵文的形式”云云说明不了任何实质性的问题。况且,就“用韵文形式释义”言,《九怀》比《远游》更纯粹。
黄先生又认为“《七谏》以下五篇”与前十一卷的文字注释多毫无必要的重复,乃因二者所出非同一人之手。其云:
特别是文字的注释,多与前十一卷出现毫无必要的重复。王逸《楚辞章句》十一卷注义虽然也有重复现象,但是,若所注词义相对比较重要,故才不厌其烦。……而《七谏》五篇的注义重复,多不在此列。如,《离骚》“唯昭质其犹未亏”,注云:“昭,明也。”《大招》“白日昭只”,注云:“昭,明也。”《天问》“何冯弓挟矢”,王逸只在《章句》中以“挟箭矢”注明之,没有单独为“矢”字作注。《七谏·谬谏》“机蓬矢以射革”,注云:“矢,箭也。”《大招》“执弓挟矢”,注云:“矢,箭也。”这种重复注释就显得繁芜、臃肿,完全没有必要。如果出自一人之手,似乎没有这种可能。又如,《七谏·初放》:“平生于国兮,长于原野。”注云:“平,屈原名也。高平曰原,垧外曰野。言屈原少生于楚国,与君同朝,长大见远弃于山野,伤有始而无终也。”《九叹·离世》:“兆出名曰正则兮,卦发字曰灵均。”注云:“言己生有形兆,伯庸名我为正则以法天;筮而卜之,卦得坤,字我曰灵均以法地也。”如果按前十一卷体例,必皆省略,但注:“皆解于《离骚经》。”决无作如此累赘的重复。这只能说明是出自另一人之手,才有可能造成这种不该重复出注而重复出注的情况。[1]
“出现毫无必要的重复”“如果出自一人之手,似乎没有这种可能”与“如果按前十一卷体例,必皆省略”云云,孤立地看,似甚有道理。然当我们用就整体以考察部分的方法考察时,便恐其说明不了什么实质性之问题。事实胜于雄辩,试看《楚辞章句》下面之例子:
(1)《离骚》“朝搴阰之木兰兮”与《九歌·湘君》“搴芙蓉兮木末”下,注分别云:“搴,取也”与“搴,手取也”。(2)《离骚》“指九天以为正兮”与《九歌·少司命》“登九天兮抚彗星”下,注分别云:“九天,谓中央八方也”与“九天,八方中央也”。《天问》“九天之际”下,注云:“九天,东方皞天,东南方阳天,南方赤天,西南方朱天,西方成天,西北方幽天,北方玄天,东北方变天,中央钧天。”(3)《离骚》“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与“苟得用此下土”下,注均云:“苟,诚也。”(4)《离骚》“忳郁邑余侘傺兮”与《九章·惜诵》“心郁邑余侘傺兮”下,注分别云:“侘傺,失志貌”与“侘,犹堂堂立貌也。傺,住也。楚人谓失志怅然住立为侘傺也”。(5)《离骚》“女嬃之婵媛兮”、《九歌·湘君》“女婵媛兮为余太息”与《九章·哀郢》“心婵媛而伤怀兮”下,注均云:“婵媛,犹牵引也。”
其实,此类例子可谓举不胜举——限于篇幅,兹不赘举。概言之,以此例彼,思过半矣。
黄先生还说:“表面上看,《七谏章句》五篇之所以作得似与《九怀章句》以前十一篇一样的整齐、划一,这当然是由于继承者体会得王逸《章句》的原意;但是,最终还是体例或行文风格、习惯方面反映出前后的差异,透露出了前后注者在学术作风上有所区别的真相。如,《七谏·初放》:‘往者不可及兮,来者不可待。’注云:‘谓圣明之王尧、舜、禹、汤、文、武也。欲须贤君,年齿已老,命不可待也。’以‘往者’为‘圣明之王尧、舜、禹、汤、文、武’六人。其实这样的诗句内容同样出现在前十一篇,《远游》:‘往者弗及兮,来者吾弗闻。’注云:‘三皇、五帝,不可逮也。后虽有圣,我身不见也。’则以‘往者’为‘三皇五帝’。前后差异如此之大,令人不可思议。”问题是,此若“令人不可思议”,笔者上面所举之第2、4例,不更同样如此?因之,“透露出了前后注者在学术作风上有所区别的真相”云云,与客观之整体观照所得显然不符。
另外,黄先生据《隋志》集部《楚辞》类小序之“后汉校书郎王逸集(7)据王逸《楚辞章句叙》之“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说,此“集”字不当——或类《汉志》“杂家类”著录“《吕氏春秋》二十六篇”,原注:“秦相吕不韦辑智略士作。”然而,《隋志》“杂家类”著录是书,原注则作:“秦相吕不韦撰。”屈原已下,迄于刘向。逸又自为一篇,并叙而注之。今行于世”而云:
魏征说“今行于世”,“今”者,是指初唐,或许魏征已见到这样的本子,所以才说这样的话来。即是说,初唐时期,已将王逸《楚辞章句》十一卷与他人的续作《七谏》五篇章句合为编,于是才开始有《楚辞章句》十六卷本。在此以前,绝无此本。故《隋志》“楚辞类”下未见著录王逸《楚辞章句》十六卷本,因为隋代未见此书。《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皆始著录王逸《楚辞章句》十六卷,说明此书始于唐代。[1]
问题是,其一,正如黄先生所说的“《七谏章句》以下五篇,在魏、晋六朝之世确乎存在,其作者也确乎标明为东汉的王逸”[1]。其二,“逸又自为一篇,并叙而注之”云云,说的乃后汉王逸《楚辞章句》全部为十七篇。即就“今行于世”言,“今”显非“行于世”之始,而是其持续。其三,例以黄先生“因为隋代未见此书”云云,那么果真存在“《七谏》五篇章句”本,则“《隋志》‘楚辞类’下”何以没有著录?
总而言之,据王逸《楚辞章句序》之“今臣复以所识所知,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作十六卷章句”(8)黄先生上揭文认为这“十六卷章句”仅指《离骚》一篇,非是。另文详之,兹不赘。、黄先生之“梁顾野王《玉篇》唐钞本残卷引《楚辞》及《章句》,出于《七谏》《九叹》《哀时命》《惜誓》《大招》诸篇者甚多”[1]、《文心雕龙·辨骚》之“《骚经》《九章》……《九歌》《九辩》……《远游》《天问》……《招魂》《大招》……《卜居》……《渔父》……自《九怀》以下”与《隋志》集部《楚辞》类小序之“后汉校书郎王逸集屈原已下,迄于刘向,逸又自为一篇,并叙而注之”等说,便可推知:《隋志》集部《楚辞》类著录的“《楚辞》十二卷”“并目录。后汉校书郎王逸注”者,虽“卷”作“十一”(不含“目录”),然“篇”断非“十一”,最有可能是包括屈原、宋玉以至王逸之《九思》在内的十七篇。
综上所述,所得结论有二:
其一,范晔《后汉书》王逸本传尽管“唯独《楚辞章句》语焉不详,未著其篇数”,然无任何问题;“象牙书签”记载的“王公逸……著《楚辞章句》及诔、书、杂文二十一篇”,其篇数不包括《楚辞章句》;据《辨骚》,得不出“自《骚经》至《九怀》凡十一篇,当是刘勰当时所据《楚辞》本子的篇目”的结论;而“《隋志》‘八篇’说,说明《九辩》一篇……混杂在屈原作品之中。六朝时期流传的王逸《楚辞章句》是十一卷本,其篇目排列的先后次第,除《招隐士》一篇外,与《楚辞释文》的目录篇次基本相同”云云,亦非圆照。概言之,凡此种种根据均既无一能证明“六朝时期所流传的王逸《楚辞章句》应为‘十一卷’本(即十一篇)”,亦无法断其时“不存在《楚辞章句》有‘十六卷’或‘十七卷’的本子”。
其二,黄先生以“《七谏章句》以下五篇”非王逸注之主要理由有二:一者,“王逸作《楚辞章句》,重点注释《离骚》”而以“标准的‘章句’体”为之,“《九辩》、《九章》(《惜诵》一篇除外)……诸篇内容相对较为简单,皆用韵文形式释义”,而“《七谏》以下五篇,内容要比《九辩》、《九章》等更为单纯、明白……注文皆一律用‘章句’体,注文的行文风格与前十一卷也略有差异,截然为两种不同的书”。二者,“是文字的注释,多与前十一卷出现毫无必要的重复。……这只能说明是出自另一人之手”。然而,其前者更多的只是黄先生主观之看法,说明不了什么实质性的问题;其后者为重点,然黄先生将前后“两部分”置于整体中考察似有未细者在。况且,(一)王逸《楚辞章句叙》有“今臣……作十六卷章句”说;(二)据《玉篇》所引,正如黄先生说之“梁代的顾野王之前,《楚辞章句》旧本有《七谏》以下五篇,其以注文为王逸所作”[1];(三)《隋志》有“王逸集屈原已下,迄于刘向,逸又自为一篇,并叙而注之”说。一言以概之,“《七谏章句》以下五篇”非王逸注说不能成立。
于此,笔者虽不同意黄先生之说,然对其为“《楚辞》学”所作出之杰出贡献与为在更高的层面上求是而勇于创新、探索之精神,深表敬意。至于拙文之不当,则祈黄先生与海内外之方家不吝以斧之。
——王逸书法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