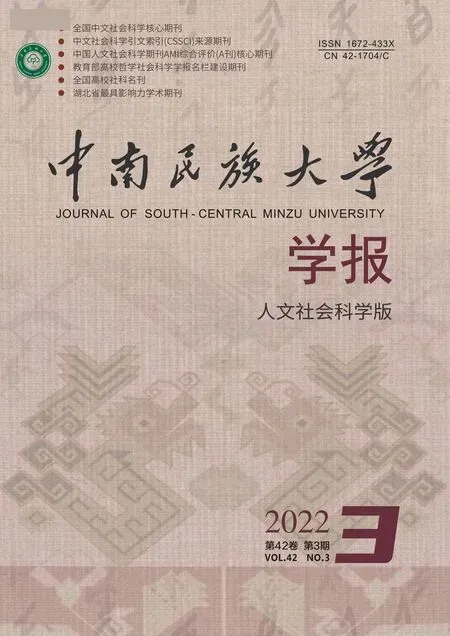民族志电影生产的三个维度:视觉、日常生活与情感
陆 敏
(中南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民族志电影毋庸置疑具有人类学观察视角,但其载体是运动影像。影像诉诸视知觉的特质,使人类学电影在蕴含理性内涵的同时,却又天然具有感性色彩。这种视觉的感性特质可以给民族志电影带来怎样的知识生产特点?使其具有怎样的知识生产机制?本文将从视觉、日常生活、情感三个层层递进的维度进行探讨。
一、视觉转向:从隐喻成为现实
人类学家越来越意识到,民族志电影不再仅仅是复制的工具或研究方法,而是以影像提供一种超越惟智主义的观看方式。事实上,民族志原本就充满视觉的隐喻,“人类学调查中占据优势的方法,是参与观察、数据收集、文化描述,所有这些都预先假定了一个外部立足点——看、对象化……西方的分类想象本质上是极为视觉至上的”[1]40,而当民族志电影真正以运动影像这一视觉方式来呈现他者文化时,视觉的隐喻成为了现实。对于文化的认识已然进入到一个有别于以概念、文字进行叙述的路径。相较于文字语言,运动影像体现出的视觉方式具有截然不同的表达特质,使民族志电影首先在视觉层面产生了不同的人类学知识生产机制。
首先,运动影像精准复制现实的能力使承载文化的个体及其所处的时空直观可见。在每一个长镜头影像片段中,时间与空间均呈现出连续的状态,个体面貌、表情、语言及行为亦得以连续呈现。在不考虑画帧丢失信息的前提下,生命个体及其外在环境能够相对完整地在一个连续时间内出现在观众面前。Caterina Pasqualino对此深有体会:“与传统的笔记方式相比,影像视频重要的优势在于它能纪录最快速的身体表达。而这些素材构成了至关重要的研究。”[2]89虽然,语言文字同样能进行描述的工作——甚至是非常细腻的描述,例如格尔茨阐释学意义上的民族志撰写模式“深描”——但因文字抽象概括的本性、普遍适用的目的,文字民族志所表征的世界,仍与影像书写的民族志所表征的世界有着本质的区别。如泰勒所言,“电影不仅包含着符号和图像,还包含着一系列的索引 。电影画面与其所指物有一种动机上或物质上的因果关系,用符号学家的话说,就是能指与所指之间具有一种自然的联系(而文字书写民族志的文字与符号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人为的)……电影的这种指索性,特别是其对于经验的使用,使其具有天然的反身性,即它同时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没有其它媒介或者艺术可以做到如此精确的还原”[3]75-79。《四季轮回》正是在摄影机长时间不停机的纪录下,因高原反应极度痛苦的女子备受折磨的状态令观者震撼。
更为重要的是,在强烈地呈现事物细节之时,视觉能够有效激发其它感官的感受能力。由影像以近景或特写的方式对局部进行细腻表达,诸如触觉、嗅觉、味觉等其它感官的体验被渐次唤起,随之引发身体的整体感受。由此,拍摄时人类学学者的身体体验,借由影像充满质感的呈现,完整地由视觉传递出来,实现从感官的单一维度向多元维度的转化。此即“体感视觉”。“‘体感视觉’强调通过影像传递事物的物质存在方式,它是一种与身体感受联系更为密切的视觉表达。”[4]在《假期》中,人们轻松愉悦地准备着节日的食品;画面不仅呈现出烹制食品的细节,同时也成功启动了观者的触觉、嗅觉与味觉,给观看者带来了身临其境般的身体体验。
面对他者文化,运动影像的视觉方式展现了更高的还原度和忠实度,文化的种种细节更为直观、细腻和完整地呈现。在民族志影像中,人类学家的身体经验可通过“体感视觉”得以传递;身体经验的共鸣使得观看者以贴近性的方式更真切地理解他者文化和与之相关的生命个体,跨越时空的界限,实现了生命与生命之间的交流。《食人录》大量特写镜头使观众无法窥见佐川一政的全貌,流动失焦的画面进而令观众产生与主人公的共情以及内观反省。此时,他者成功地避免被客体化,观看主体与客体不再绝对分立,生发出主体间性的意味。“由此产生的交互主体性知识是一个由最具个体意义、被个体最深刻地体会着的经验的综合体,也就是主体内部的知识。”[5]36无论是连续、细腻、完整的视觉具象,还是能够转换为身体经验的视觉经验;无论是“目观视觉”还是“体感视觉”,其所带来的直观、原生的经验很好地弥合了文字抽象表达的距离感,具有重要的知识生产价值。人类学家里弗斯逐渐意识到“早年对原生经验的压抑其实是一种缺失…..实际上它们都属于一个探索人的状况的计划, 而且都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6]。当视觉由隐喻成为现实,人们的行为得以更直观地被观察,文化得以更有“浓度”地被感受。人类学知识生产获得了一种距离生命原生状态更近的方式,就此开启一种新的认知模式。而当运动影像复制的生活片段被呈现、被连接后,承载文化的日常生活逐渐浮现出来,提供了更深层次的人类学知识生产的影像空间。
二、日常生活:共时性与开放性
在运动影像的复制现实之后,民族志电影面临着影像片段的选择与并置。正是在这样的影像选择与并置中,观看者细腻直观地感受到人们的日常生活状态。如格里姆肖所说,“这个世界并非主要通过语言、解释和归纳等方法得以接近,而是通过成为重新感受日常生活基础的自我再现而得以接近的”[7]。日常生活的影像直观表达判然不同于语言文字的概括表意,产生了影像在日常生活层面的独特知识生产机制。
首先,日常生活的影像表达具有同一空间下的共时性特质。在一个长镜头影像片段中,尤其是较大景别的画面中,每个瞬间的空间里每个个体的状态及其之间的关系都能够共时性地呈现出来。由于这种共时性,影像不仅能同时展现日常生活中不同生命个体的表情、言语、肢体行为,更能在同一时刻展现个体与个体之间微妙的关系与互动,以及不同个体、物体之间的空间关系。相较而言,语言文字则只能历时性地一一展开对同一空间下不同物体、生命个体关系的描述,无法将状态的呈现、关系的描述在同一时刻实现。麦克杜格认为,“视觉媒介使用‘暗示、视觉共鸣、辨认,以及变换视角’的原则,这与大多数人类学书写方法截然不同。”[8]220可见,日常生活的影像呈现并非是枯燥的、程式化的、镜像式、图解式的生活呈现,而是充满生活气息的、细节的、情绪的、交流的生命个体的日常生活呈现。在《北方纳努克》中,纳努克给孩子暖手、教孩子射箭的情景共时性地表现了两人的表情、交流与肢体语言,传递出浓厚的父子亲情;在《神堂》中,舍米湖村支书与干河沟小组组长的争论场景,全景式展现了中国乡村里微妙的博弈和权力关系。
其次,单个运动影像片段经过选择、组接形成民族志电影的段落,最终成片。相较于语言文字抽象、概括、归纳的方式,民族志电影因其具体性、贴近性和完整性,能够更为原貌地呈现异文化的日常生活,有效规避了文字抽象表达时丢失细节的风险,因而也相对减少了作者的主观意义阐释(绝对意义上不可避免)。因此,相较于文字书写的民族志,民族志电影也仍具有更大的开放性与多义性。“它们让观察者参与启发式过程和意义创造,这与口头陈述、联系、理论形成和推测截然不同”[8]220。尤其是观察模式的民族志电影,以旁观观察为主要方式,尽可能减少声画对位的解说、旁白的存在,而以声画合一的现场场景为主要段落。此时,作者的主观观念更为隐蔽淡化,作者对于意义解读的霸权进一步降低,将日常生活所携带的意义的理解和评价更多地交由观看者进行。“观察美学在民族志电影制作者中享有很高的地位,这种美学热爱长镜头、同步记录谈话、忠实于真实生活的节奏,不鼓励剪断、导演、再现、采访。这样的民族志电影对于多元阐释非常开放。”[3]75
观察模式的民族志电影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弱化叙事。作者不仅不断隐去作者的主观观点,也减少对于影像片段组接逻辑的介入和控制,使影片结构的封闭性不断下降。日常生活极少纳入到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典型戏剧性叙事线索中,而是以更粗粝和原始的状态呈现,从而展示出更为开放的格局。于是,民族志电影中的矛盾冲突常常源自日常生活内在的内容张力。麦克杜格与怀斯曼的作品是将“弱化叙事”极致化的观察模式民族志电影典型代表。如《甘地的孩子》以段落式的呈现,印度流浪儿童收容所孩子们的窘迫、孤独、无助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渐次体现,引起人们对流浪儿童生存状态的关注。在《灵长类》中,国家实验室对灵长类群体的长期窥探与操控,在日复一日的各种生物应激实验中累积,最终引发人们对于物种与物种之间关系的质疑和反思。
可见,弱化叙事对于被观察的人物和事件具有相当的尊重。这种制作方式,既不同于维尔托夫极力运用影像探索主观运动与客观运动的关系、对影像充满反身性的思考,亦不同于格里尔逊将大量充满主观观念的解说铺陈于其作品中,也并不同于弗拉哈迪运用长镜头对北极生活的纪录——弗拉哈迪刻意回避北极与外界业已存在的多种交流,而是以强烈的主观性、选择性并充满戏剧元素地呈现他心目中纯粹的理想国,因而具有相当程度满足自身凝视的意味。如果从观看方式来理解,此类民族志电影作者的观看之道既非边沁“监狱式监视”的权力凝视,亦非中世纪“剧场式欣赏”的权力凝视。相反,对于研究对象,观察模式民族志电影努力摆脱权力的凝视,采用更为平等的观看方式;作者最大限度向后隐退,仅在连接影像片段时以最低的程度介入。这一特征使民族志电影知识生产的意义建构与阐释更具开放性,观者有更多机会进行属于自身的意义解读,作者霸权得以较大程度的消解,主体间性进一步增强。同时,异质文化的价值观、习俗、伦理、仪式等内容,亦直观地在生命个体的日常生活影像中呈现,具有相较于文字民族志更开放的意义解读空间。
三、回归情感:让个体可见
对于情感,苏珊·朗格说:“……这样一些东西在我们的感受中就像森林中的灯光那样变幻不定、互相交叉和重叠;当它们没有互相抵消和掩盖时,便又聚集成一定的形状,但这种形状又在时时地分解着,或是在激烈的冲突中爆发为激情,或是在这种冲突中变得面目全非。”[9]难以把握的情感,长时间来都不曾是人类学领域的理论焦点。“情感在社会进程中的经验性作用要么被轻视,要么被模糊地认为是根本性的。对于情感,人们与其说是如同‘盲人摸象’般地把握,毋宁说是如同无视‘房间里的大象’一般忽视其明显的存在。至少,“盲人摸象”还表现出了一种探索性的兴趣。”[10]然而,情感是人们的思想、言谈、行为中不可分割的元素;人类学者在面对异文化时,在进行田野调查时,无可避免地会感受到其中的情感。逐渐的,人类学者的民族志书写开始触碰和描写情感,例如20世纪后半叶,格尔茨就以阐释学的深描模式描摹巴厘岛上人们斗鸡时的情感状态,虽然这一描写后来被批评为他的主观想象,而非人们自身的情感[1]104。1986年,卢茨和怀特正式提出“情感人类学”。他们认为:“人类学应对人的情感进行文化上的分析;其认识论基础是,人的情感不是纯粹的心理学和生物学意义上的,它是镶嵌在社会关系中的文化习俗。”[11]118
此时,区别于文字的抽象性与概括性,影像“迫使人们直面生活最为原初的模样;用最为直观的方式暂时放下人们有条不紊的理性,唤起对生命久违的体验。如此直接的感性特质,使摄影影像不仅诉诸感官,还能够将对于生命情感表达得十分深入”[12]17-18。运动影像作为诉诸视知觉的载体,观照内在生命,点点滴滴呈现生命情感。《哭泣的骆驼》讲述了一只因难产不愿哺乳刚出生的幼崽的骆驼,在蒙古族古老的音乐仪式帮助下接受幼崽的骆驼。在《雨果的假期》中,酗酒的母亲对在外念书的儿子雨果的思念煎熬,等待雨果归家的焦急期盼,真实质朴却又直击观者内心。相比之下,语言文字虽然同样可以描摹情感,但不可避免地失去部分细节,无法全然展现浑然一体的某一瞬间的情感;诉诸视知觉的直观力量由此可见。《杜卡的两难困境》的作者Jean Lydall说:“尽管语言能够显示出Gardi(研究对象)的部分情感,然而她的大部分感受是通过非语言的方式传递,例如声音的语调、面部表情和手势。”[13]41可见,对于这些非语言的方式所承载的情感,运动影像恰能更完整地予以呈现。“民族志电影可以让视觉的调查方式打破经典的文献叙事结构,重新建立对亲密和情感的关注。”[2]86
以诉诸视知觉的感性特质为基础,运动影像表达情感的能力在画面剪辑中继续体现出来。在创造力的支持下,画面与画面组接成为段落,成为能够传递情感的表现性形式。“‘表现性形式’是一种充满着意味的抽象逻辑形式,它抽象出来的是艺术品各个部分之间排列方式和有机联系,张弛与呼应的关系;因而充满生命的动感,也蕴含着生命的情感。”[12]21具体来说,影像中的表现性形式源于实在之物(画面)构成的具体形象(画面段落),充满生机、能够被感受到却直观不可见。在民族志电影中,画面若能通过蒙太奇的作用,建构出包含在画面段落中的抽象逻辑形式,即是生成了属于这一民族志电影的“表现性形式”。这种形式能够传递出观察对象的生命情感,触动观众并引发共鸣。由此可见,如同音乐音符、和声的组合,绘画光线、色彩、影调的搭配,创造性对于影像成为艺术、传递情感至关重要。这一点,常常被民族志电影作者忽略。
《船工》将妻子在家门召唤谭邦武老人回家吃饭的资料画面与妻子去世后老人孤独一人的现实画面进行了闪回剪辑,这段画面的交叠生成的“表现性形式”使观看者深深感叹于两位老人朴实而真挚的夫妻情感。《尘土一样的生命》使用越南战争的新闻电影资料、越南乡村的电影资料,与越南童党现实的暴力生活进行蒙太奇的闪回剪辑,“唤起观看者对纯真沦丧的哀叹,对人性异化的心酸与绝望,以及对越南童党自我营造的替代家庭中所弥漫的犯罪和暴力气息的惊悚与畏惧”[14]。
贝拉·巴拉兹评价影像的力量:“这并不是一种代替说话的符号语言,而是一种可见的直接表达肉体内部的心灵的工具。于是,人又重新变得可见了。”[15]曾经,民族志书写中的“人的形象”是苍白甚至是缺失的。“作为人类学家关注的对象,个人却总是对于人类学的读者保持很大范围的不可见性,这多少有些奇怪。”[8]213在一些文字民族志中,文化样貌以概述、罗列的面目出现,流于泛泛之言,不能使读者真正深入地理解异质文化。令人遗憾的是,甚至部分民族志电影也未能有效利用影像的直观性,使影片成为情感无涉的画面铺陈,成为某种异质文化的“看图说话”的附庸和工具,宗教仪式、经济制度等抽象概念的简单图解,实属对于影像潜能的极大浪费。民族志电影作者若能充分发挥影像的直观感性特质,无论是以画面直接呈现观察对象的情感,抑或是以蒙太奇剪辑建构“表现性形式”来传递情感,个体的形象都可重新鲜活可见。观看者可以从民族志电影中真切地看到作为文化承载者的生动个体,而“个体可见”恰恰能使观者更深入地理解其所代表的文化。
《杜卡的两难困境》成功呈现了埃塞俄比亚南部哈马尔族人非常私密的内心世界以及他们的私人生活。导演自述道:“影片让观众以非常个人和亲密的方式了解哈马尔族的人们,这是一个让观众产生同理心与参与感的好途径。”[13]39影片既不单调乏味,亦没有营造所谓“奇观”,而是以前所未有的贴近性观察和交流使来自非洲族群的个体真实呈现,让观看者意识到镜头前的人们实际上和自己有多么相似。同时,影片中的个体以及他们情感的呈现使观众非常直观地感受和理解哈尔马族的文化价值观、道德、婚姻及政治权力制度。情感不仅仅是情感本身,也不仅仅归属于个人,它还折射出情感背后复杂的社会文化因素的共存和相互作用。民族志电影通过情感使个体可见,又通过富有情感的个体使文化可见。正如卢茨所说:“情感对于个人而言具有双重性:在文化层面,情感是价值体系的一部分,对于个人而言,它又是理解个体的创造、个人与社会制度以及习俗之间关系的重要因素。”[11]121
揭示民族志电影表达情感的潜力,可以开启人类学新的认知模式与认知领域。其知识生产的意义不仅在于方法论,更具有认识论的价值。在这个领域,过去被有意无意忽略的情感应获得应有的研究地位,并生产出与之相应的曾经缺失的重要人类学知识类型。情感在文化中发挥着积极作用,纳入情感研究,才能使人类学研究获得一个更为完整的全貌。Caterina Pasqualino在其民族志电影实践中感受到这一点:“这部(关于吉普赛人的)电影寻求捕捉吉普赛人的亲密、力量、幸福与痛苦,尽可能的诚实、直接,并充满同情。电影并不是要尝试去描述一个仪式的结构,而是意图去再现吉普赛人的精神状态。拍摄影像的经验可以让我更深刻广泛地分析吉普赛人的社会现实。这比我仅仅拿笔在本子里做记录的收获要多得多。”[2]87
一直存在于田野中的情感,终于作为“房间的大象”渐渐被正视。这是对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的以理性的单一逻辑认识事物的一个纠正。如果说文字书写的科学性文体压抑了文字的诗性追求;那么在民族志电影中,科学理性亦曾对视觉影像的诗意表达有所抑制。事实上,如果民族志电影的情感力量能够得以释放,相比于仅有单一理性进行的知识生产,将能对异文化做出更全面、更深刻的阐释。强调民族志电影的情感维度,并不意味着放弃理性的人类学思考,而是使认知文化的路径更加均衡,更契合于事物的本真原貌,也能更深入地把握文化。“发扬科学同时实践诗学,不会产生混乱——而会导致更加艺术的科学,或者,会产生更为严密的艺术……这不仅是现代共识所要求的,而且是人类理性知识和感官感受所要求的。学界也应接受新的形式和媒介来表达田野经验。”[5]21可见,情感维度的加入,对于民族志电影乃至人类学的知识生产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民族志电影在视觉、日常生活、情感三个层层递进的维度上实现人类学的宗旨:“向属于一个文化的人们解释属于另一个文化的人们的行为。”民族志电影不应是记录、图解某种文化的工具,而是具有独立性的人类学知识生产的有效路径。民族志电影意义被建构的方式与文字书写截然不同,知识生产的机制也判然不同。民族志电影通过运动影像实现研究对象日常生活的高度还原性的复制、时空间与个体关系的微妙呈现、情感的细腻表达、开放的意义阐释空间,具有独特的认知对象、采用独特的感性认知方式,具有不可替代的认识论价值,最终使人类学知识更加全面、完整。
民族志电影的本质在于以艺术和科学的融会贯通来阐释文化。作者进行创作时,需要具备人类学或科学的视角;但非常重要的是,也需要了解画面语言,熟知影像从视觉、日常生活到情感层面进行知识生产的具体方法,包括影像的拍摄、剪辑技巧以及对运动影像创造性地运用,从而使影片从“资料”到“作品”。这些方法的欠缺,不仅不利于民族志电影真正释放出其知识生产的能力,反而会导致其陷入枯燥单调的铺陈式影像的泥沼,使质感消失、日常生活空洞、个体亦不可见。
胡塞尔说: “直观是无法演证的;一个想看见东西的盲人不会通过科学演证来使自己看到什么;物理学和生理学的颜色理论不会产生一个明眼人所具有的那种对颜色意义的直观明晰性。”[16]当异质文化的生活世界以直观的方式呈现时,我们应该怎样面对这样的直观现象?是否仍坚持单一维度的理性思考?我们如何确定,以这种单一的理性思维,能准确地把握一个丰富、复杂、立体的文化?借用现象学的思考,我们应将现象与我思分离、进行悬置,把现象还原到一种自明的明见性的自身被给予性;我思也还原到先验的自我,悬置理性的科学思考,悬置对于唯一存在的客观世界的信念。那么此时,悬置的现象将被运用直觉来把握其本质。
一方面,“悬置了事物的存在之后,剩下的是一个摆脱了独断论束缚的无限广阔的现象领域,一个真正自明的而又无所不包的显现领域。因此,悬置不是限制了、而是扩大了哲学考察的范围: 想象、幻想、情感、信念、希望、意志、活动……”[17]68。而“悬置”让曾经被忽视、漠视的、与生命个体有关的“诸现象”也进入观察视野,产生一个更广阔的研究范围,让世界重新恢复新的平衡。另一方面,“直觉”亦为人的创造性提供了空间。“直觉”未必是非理性的,而是包容了人类的理性活动,同时“消除了对于人性的异化和压迫这种悖谬,回归到人性的根(自由),因而实际上更“合理”、更是严格意义上的“理性”[17]69。
这一悬置的过程对于考察民族志电影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如上所言,悬置人们的生活世界,使生命个体可见,扩大了人类学知识生产的领域;而面对这一生活世界,如果能以融合理性与感性的更为平衡的思维方式(即更严格意义上的“理性”)来进行直觉认知,是否更能直抵文化的本质?“人类学因此具备一个跳出来看的视角,具备一个从外部视角对象化具体生活世界、对其进行整体性观察、思考和表达的基点。”[18]所以说,民族志电影提供的直观的生活世界,似乎给了我们一个契机,提醒我们修正长久以来人类学研究认知对象的偏狭和坚持单一认知方式的傲慢,进而既理性又诗性地考察生命个体的生活世界,以更全面的方式认识更全面的异质文化。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通过改变关于事实的概念,改变描述这些事实的语言,我们可以改变游戏本身的性质”[5]21,文化从而可以获得更有包容性、更人性化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