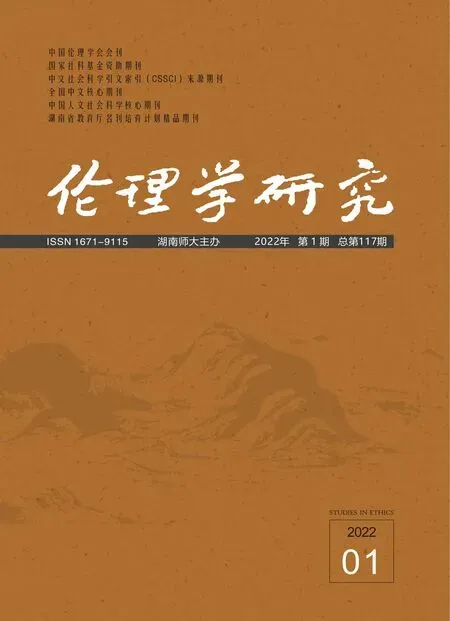董仲舒经权观对道义论立场的回归
赵清文
儒家关于“权”的学说始于孔子。在孔子和孟子等先秦儒家的论述中,与“权”并提的往往是“道”“礼”等概念。在中国思想史上,将“经”与“权”对举是从成书于汉景帝时期的《春秋公羊传》开始的。公羊家提出的“反经为权”的观点,一直到宋代之前,都是经权观上的主流思想。从伦理思想的角度来说,不同的经权观不但反映着学者们对具有原则性和普遍性的道德准则与具体情境中主体道德选择的灵活性和能动性之间的关系等具体问题上的看法,而且也体现了他们伦理思想上的基本倾向。
一、背反于“经”还是返归于“经”:字义训诂背后的伦理思想倾向
《春秋公羊传·桓公十一年》在评价郑国的祭仲“出忽而立突”一事时说:“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权之所设,舍死亡无所设。行权有道,自贬损以行权,不害人以行权。杀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为也。”这是中国思想史上关于经权关系的最早的直接阐述,也是《公羊传》中唯一一处直接对经权问题的论述。这段论述中,涉及了“经”“权”“善”“道”等几个中国传统经权观中核心的概念,并且通过这几个概念,对“经”与“权”的关系、“权”的合理性限度以及行权的条件和一般原则等问题进行了阐述。
关于“经”和“权”之间的关系,《公羊传》认为,“权者反于经”。对于这句话中的“反”字,学者们有着不同的解读。历史上,大部分学者都是将其理解为“背反”或“违背”之义。但是,清代之后,有人认为,这一“反”字应是“返”的通假字,意思是“返归”“回归”。最早明确提出这种见解的是俞正燮,他说:《公羊传》中的“‘反经’之‘反’,为‘十年乃字,反常也’‘尧舜性之也,汤武反之也’之‘反’,为反归之反,非背反之反”。他还认为:“以背反于经为权,汉以前经传笺注实无此说也。”[1](63)现代的一些学者也沿袭此说。比如,蔡仁厚曾经说:“《公羊传》云:‘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无经则权无所用,故必须反(返)于经而后乃能成其善。由此可知,一个不能守经的人,根本不足以言‘行权’。”[2](345)在引用《公羊传》的论述之后,他特意对“反”字加了一个“返”的注解,来说明他所理解的行权和守经的一致性。李新霖不仅认同俞正燮的观点,而且进行了补充论证。他以“《公羊传》中言及‘反’而有‘返’意者,所在多有”为论据,通过对《公羊传》中其他部分出现的“反”字的分析,总结认为:“无论‘反’接虚词再接实词,或‘反’接实词而虚词而实词,皆有‘返’意。故用是而观,《公羊传》云:‘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意指道有经有权,若经立大常,权则用以应变。但经权虽不同,却不相反,甚至通变之权原本于经。”[3](195-198)
当然,也有许多学者并不赞同这种观点,认为将“权者反于经”的“反”字解释为“返”的论据本身是有问题的。尽管在传统典籍中,“反”常用作“返”义,甚至有可以将“反经”解释为“返经”的先例,如《孟子·告子下》中的“君子反经而已矣”中的“反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公羊传》中“权者反于经”的“反”字也必然训为“返”。针对李新霖等人的观点,林义正反驳说:“《公羊传》文中,‘反’字并非皆作‘返’意,如‘反袂拭面’之‘反’即作‘背反’解。”[4](139)由此可见,《公羊传》及其之前的经典文本中没有释为“背反”的“反”,本身就是不符合事实的。退一步讲,即使汉代之前的经典及笺注中真的没有这种先例,仅仅因此就认为公羊家们“反经为权”的“反”字也不应释为“背反”,这种观点未免过于狭隘,所得结论也过于草率。
“权者反于经”中的“反”字究竟作何解释,最重要的还是应当从这一观点本身来进行分析。有学者论证说,依据《公羊传》中的传文,“权若‘归返’于经,又何必再次强调必须‘有善’?且若以‘归返’释权,则权亦只是经,又何必再拈出‘权’字,徒增理解之困扰?……传文所谓之‘有善’,实乃《公羊传》对于‘权’之行使所设之限制。之所以另设条件限制,盖不欲世人误以权既可违反经之原则,遂乃‘滥权’妄为,此固圣人之所不乐见者。准此,‘权者反于经’之‘反’实当作‘违反’解,如此方符传文之旨意”[5](173)。这一分析是有道理的。汉人的著作在论及经权问题时,都是在与“经”相对的意义上来使用的。比如,《韩诗外传》中说:“夫道二,常之谓经,变之谓权。”[6](34)“经”和“权”是在“常”和“变”两种情境下实践“道”的不同方式。这里的“经”,既是指一般情境下普遍适用的道德准则本身,也表明一般情境下普遍适用的道德准则在具体情境中的应用限度,即,这些准则仅仅被视为是在一般情境下适用的,在此之外,则需用“权”。作为公羊家的董仲舒继承了《春秋公羊传》中“反经为权”的观点,并进一步解释说:“夫权虽反经,亦必在可以然之域。”[7](79)这里特别突出强调“权”“亦必在可以然之域”,如果董仲舒也将“权”理解为“返于经”,这种强调则全无必要;之所以做这种强调,是因为“权”是要违背一般情境下普遍适用的准则的,如果没有一定的限制,就有可能溢出“可以然之域”。因此,姑且不论汉儒观点之是非,单从汉代学者的论述可见,他们所主张的“权”,就是与“经”相反的。
之所以会将汉儒的“权”的含义理解为返归于“经”,直接的原因,是误解了汉人所说的“经”字。汉儒经权观中的“经”,指一般情境下普遍适用的道德准则,它是“道”落实于具体的实践生活的体现,而不是“道”本身。在道德准则体系中,“道”是最高的原则,它的普遍约束力是具有绝对性的,而“经”则源于对现实中合乎“道”的行为的概括和总结,它是有限的,不可能涵盖“道”与现实情境相结合的所有可能。因此,当遇到以前未曾经验过的情境,或者与一般性的情境不一致的特殊情况时,“经”对行为的普遍约束力就会暂时失效,因而必须回到“道”本身,去寻找合宜的行为方式。这种处理方式,就是汉儒所说的“权”。因此,“权”的合理性依据之所在,并非是“返于经”,而是“合于道”。将“反于经”理解为“返于经”,关键原因就是混淆了汉儒经权观中的“经”与“道”,将“经”看作与“道”等同的概念。蔡仁厚有一种观点,他说:“常理常道虽然永恒而不可变,但表现理、表现道的方式,则必须随宜调整,因时制宜。一般人把‘理道’和‘表现理道的方式’混为一谈,所以引出许多无谓的夹缠。”[8](154-155)如果按照这种区分,汉儒所说的“经”,应为“表现理道的方式”,而非“理”或“道”本身。正是将二者混为一谈,所以才导致在对汉儒经权关系的理解上出现了偏差。
对于“权者反于经”中的“反”的解释,从表面看只是一个文字训诂的问题,但其实质却体现了诠释者伦理思想上的基本倾向。如果承认“权”可以背反于“经”,并且仍然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那也就意味着承认暂时抛开道德准则而仅仅根据行为后果进行道德选择的合理性。总体来说,在道义论和结果论之间,儒家是倾向于道义论的立场的。宋代之后,程颐等理学家之所以激烈抨击汉儒“反经为权”的观点,并提出了经权统一的理论,正是在于他们认为如果没有坚定的道义原则,承认“反经”的“权”的正当性就极有可能会造成权术、变诈的流弊。近代之后的学者以返归释“反”,正是继承了这种观念,认为“一般人既无所守,而又侈言通权达变,不过是‘饰非自便’的说辞而已”[2](345)。认为“反于经”就是“返归于经”,无疑最大限度地维护了道德准则的普遍约束力。但是,以此作为《公羊传》中提出的经权观的基本立场,却未必合适。况且,在宋代之后坚定地坚持道义论立场的理学家们的眼中,公羊家的经权观主张的也是“权”背反于“经”。从程颐提出“权即是经”的经权统一理论开始,汉儒的经权观都是他们抨击的对象,恰恰说明,他们认为,汉儒的“权”就是违背“经”的。否则,如果认为汉儒的经权观强调的就是“权”返归于“经”,则程颐就不必再感慨“自汉以下,更无人识权字”[9](295)。因此,将“反于经”之“反”字解释为“返”,从基本观点上说,是继承了宋代理学家经权统一的观点和倾向于道义论的立场,但是,如果要因此而否定《公羊传》所说的“权”字就是背反于“经”之义,并以诠释者自己在伦理思想上的立场取代公羊家的倾向,则全无必要。
二、董仲舒的经权观对道义原则的坚持
《公羊传》中“反于经,然后有善”的“权”表现出明显的重后果的倾向,董仲舒继承了《公羊传》中“经”“权”相对的思想,但他又极力试图将对经权问题的理解拉回到儒家重道义的立场上来。《公羊传》谈到祭仲行权的效果时,说:“君可以生易死,国可以存易亡。”生死存亡之间,行为给君和国所带来的“以生易死”“以存易亡”的结果,彰显了行权的正当性和可取性。但是,在董仲舒看来,能否称为“知权”,不是单纯以“生其君”或“存其君”来判断的,如果以不合“义”的方式使其君得以生存,也是不可取的。
在《春秋繁露》中,董仲舒对比了祭仲和逄丑父的行为。在齐国和晋国的鞌之战中,齐顷公被围。作为车右的逄丑父为了帮助国君脱困,与其互换位置,假扮齐顷公迷惑晋军,结果被晋军俘获,齐顷公则趁机逃脱。董仲舒认为,虽然祭仲和逄丑父都是“枉正以存其君”,逄丑父为了“存其君”而被杀,所作所为难于祭仲,但祭仲却因“知权”而值得称赞,逄丑父的行为不但不能称为“知权”,反而应当受到谴责。这是因为,祭仲让郑昭公“去位而避兄弟”,是“君子之所甚贵”的行为;逄丑父帮助齐顷公“获虏逃遁”,则是“君子之所甚贱”的行为。祭仲用将他的国君置于“人所甚贵”的位置来使其免于灾祸,所以在《公羊传》中得到赞扬;逄丑父用将他的国君置于“人所甚贱”的位置来帮助其逃脱,所以在《公羊传》中被认为“不知权”而受到贬低。所以,董仲舒说:“其俱枉正以存君,相似也;其使君荣之与使君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为也,前枉而后义者,谓之中权,虽不能成,《春秋》善之,鲁隐公、郑祭仲是也。前正而后有枉者,谓之邪道,虽能成之,《春秋》不爱,齐顷公、逄丑父是也。”[7](60-61)在这里,董仲舒依然认为“知权”与“不知权”的判断是看行为的结果,但是,他所指的结果并非是生死存亡这样的功利性的后果,而是结果是否合乎“义”的要求。如果一个行为初始时违反共识性的规则,但结果却是合乎“义”的,这就叫作“中权”;这样的行为即使没有获得成功,在《春秋》中也是被称道的。相反,如果一种行为初始时看似合乎正道,但最后的结果却不符合道义原则,这就叫作“邪道”;这样的行为即使成功了,在《春秋》中也不会得到褒奖。
由此可见,在董仲舒看来,在行为是否合乎“权”的判断中,结果是重要的,但对结果最终的判断依据却是它能否使行为整体符合“义”的要求。在儒家的思想中,“义”是一个比“经”与“权”具有更高的价值优先性的标准。孔子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一直到宋代之后,程朱理学在论及经权关系时,依然坚持“义统经权”的主张。经权观中对“义”的强调,是儒家重视道义的一贯原则的体现。从《公羊传》中的“反于经然后有善”,到董仲舒的“前枉而后义”,“把‘权’和荣辱、义不义、正邪的关系联系起来,使经权关系不仅关系到生死存亡的问题,而且跟孔子的‘杀身成仁’、孟子的‘舍生取义’统一起来”[10](286)。《公羊传》中的“权”是权变之义;既然权变,就必然是出于结果的考虑。董仲舒将结果好坏的判断依据设定为“义”,可以看出他在经权问题上回归重道义立场的努力。
董仲舒不但将“义”与“权”直接联系起来,而且还将“道”或“天道”作为“权”的合理性判断的最高标准。《公羊传》中将“有善”作为行“权”的正当性依据,是将这一判定标准置于现实的实践之中。董仲舒则试图为“经”“权”的正当性判定寻求一个形而上的终极标准。在他的“天人合一”的理论体系之中,这一标准就是天道。在董仲舒看来,“经”和“权”的依据,都在“天”那里。“天之道有伦、有经、有权。”[7](340)也就是说,“经”和“权”,本身都是内在于“天之道”的。根据这种理解,在实践之中,无论是“守经”,还是“行权”,都可以是遵循天道的体现。值得注意的是,董仲舒这里所说的“道”,与孔子和孟子思想中多用“道”来指称人们实践中所追求的最高价值标准不同,也不同于《公羊传》中“行权有道”的“道”和《韩诗外传》中“夫道二,常之谓经,变之谓权”的“道”,而是将“道”的根源寄托在“天”那里,强调了道德原则和标准的客观性。秦汉之后,列国纷争局面结束,大一统的国家的建立对稳固的社会秩序的需求突显出来,在伦理思想上必然要求道德标准日益规范化、客观化,并且被赋予越来越多的神圣性和权威性。董仲舒思想中具有主宰者和监督者的意义的“天”,便承担起赋予道德行为判断的标准以客观化和权威化的任务。
因此,在董仲舒那里,对行为的合道德性判断的最终依据,不是人性,也不是人心,而是具有客观性的“道”。“《春秋》有经礼,有变礼。为如安性平心者,经礼也。至有于性,虽不安,于心,虽不平,于道,无以易之,此变礼也。”[7](74)“经礼”和“变礼”的区别在于,前者因与礼的一般性要求相一致,所以行为者依此行事,会感到心安理得;而后者因为是与礼的一般性要求相违背的,所以行为者依此行事,会产生不安的感觉。但是,二者本质上又是一致的,他们都是在各自不同的情境之下遵循“道”的要求的行为,因而都是正当的,合乎道德的。因此,董仲舒说:“明乎经变之事,然后知轻重之分,可与适权矣。”[7](75)所谓“明乎经变之事”,最为关键的,就是能够在具体的情境之下做出如何行动才是符合“道”的要求的理智判断。合乎“道”的要求,既是“经”和“权”的共性,又是行“权”的界限。“权”虽然表面上看似违背了共识性的道德准则,但从根本上说,它与作为最高原则的“道”仍然是一致的。“权谲也,尚归之以奉巨经耳。”[7](80)这里所说的“巨经”,指的其实就是作为“第一原理”或者最高原则的“道”。
董仲舒的这一思想,就是后人概括汉儒经权观时常用的“反经合道为权”。董仲舒发展了《公羊传》中“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的观点,将“经”与“权”的合理性依据建立在“天道”这一客观且至上的基础上,从而为“经”“权”相反相成的经权观的道义论立场找到了一个相对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董仲舒的经权观回归道义论立场的理论路径
在西方伦理学中,道义论与结果论在观点上往往是两相对立的。“道义论从基于规则之上的视角出发,对伦理进行探讨。在这种探讨中,道德原则具有绝对的、无条件的规定性地位。”[11](42)道义论认为行为的道德价值取决于它所遵循的道德准则,而与行为的结果无关。结果论则以结果的好坏作为行为道德价值的判断标准,它认为:“判断道德意义上的正当、不正当或尽义务等的基本或最终标准,是非道德价值,这种非道德价值是作为行为的结果而存在的。”[12](28)然而,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虽然也一直有“义”与“利”、道义与功利等问题的争论,却很少有将道义与结果完全割裂对立的学说。思想家们虽然所主张的侧重点不同,却都试图在二者之间寻求一种统一或平衡。
从总体上说,儒家在道德问题上是强调道义准则的指导和约束作用的。结合《春秋公羊传》中引出“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这一观点的史实,即祭仲“出忽而立突”一事,可见《公羊传》中作为行“权”的正当性判断依据的“有善”,是直接从结果的意义上来说的。但是,从《公羊传》中对经权问题的完整论述可见,它的作者尽管试图以权变的方式来化解道德生活的复杂性与道德准则缺乏应变的灵活性之间的矛盾,却不想放弃儒家重道义的基本立场。可是,仅仅通过“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这一定义,是无法明确地体现出重道义的立场的。为了避免直接以结果为正当性依据的行为背离具有共识性的道义原则,《公羊传》中的处理方式,只能是根据儒家的道德观念,为行权的实践加上种种限制。首先,《公羊传》为行权设置了严格的情境约束。“权之所设,舍死亡无所设。”它将合理的“权”限制在生死存亡的紧急情况之下,明确了“权”所适用的前提条件,大大限制了“权”的使用范围,目的就是强调,一般情况下,不能轻易用“权”,守“经”才是合理的行为。其次,《公羊传》还为行权规定了明确的原则,为其设置了道义上的界限。“行权有道,自贬损以行权,不害人以行权。杀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为也。”行权虽然意味着为了取得好的后果而违背一般性的准则,但是,这种后果的考虑不是为了迎合行为者自身的某种利益要求,而是为了满足他人或者整体的利益。与此同时,对于行为主体来说,行“权”往往会造成自身利益的损失。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通过损害他人利益,甚至伤害他人生命来保全自己,是不具有道德上的合理性的。
董仲舒对于“反经为权”观点的最重要发展,是将道义原则贯彻于“权”的含义和经权关系之中,从而弥补了《公羊传》中的经权观只能在经权关系之外设置实践限制的方式来避免行权可能违背道义原则的弊端。
在对于“权”的基本含义的理解上,董仲舒明确了“道”和“义”对于“权”的正当性判断的根本性意义,强化了“权”以“合道”为特征的观念。他认为,人与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不是仅仅为了生存或利益而活着;单纯为了生存或者利益而违背道义,蒙受耻辱,并不是真正的权变行为。在对逄丑父帮助齐顷公逃遁一事的分析中,董仲舒说:“夫冒大辱以生,其情无乐,故贤人不为也,而众人疑焉。《春秋》以为人之不知义而疑也,故示之以义,曰国灭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正于天之为人性命也。天之为人性命,使行仁义而羞可耻,非若鸟兽然,苟为生,苟为利而已。”[7](61)正是由于此,董仲舒认为逄丑父“枉正以存其君”的行为虽然难于祭仲,但却不可称其为“知权”。
“苟为生,苟为利”的变通行为不值得称道,值得称道的变通是以仁义为质、扶危救难的行为。春秋时期,楚庄王围攻宋国都城,派司马子反探查宋国都城内的情形。子反从宋国大夫华元口中得知宋国已难以支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于是动了恻隐之心,不仅告知了华元楚军已仅余七日之粮的事实,而且力劝楚庄王撤围退兵(事见《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关于此事,有人提出疑问:“司马子反为君使。废君命,与敌情,从其所请,与宋平。是内专政而外擅名也。专政则轻君,擅名则不臣,而《春秋》大之,奚由哉?”董仲舒的回答是:“为其有惨怛之恩,不忍饿一国之民,使之相食。”他认为,子反这样做完全是恻隐仁爱之心的自然流露,推己及人,不忍心让宋国整个都城的人落到人吃人的悲惨境地,从而不再考虑宋国人和楚国人之间的利益区分,因此是非常崇高的行为,《春秋》才予以赞扬。他又进一步解释说:“今子反往视宋,闻人相食,大惊而哀之,不意之至于此也,是以心骇目动而违常礼。礼者,庶于仁、文,质而成体者也。今使人相食,大失其仁,安著其礼?方救其质,奚恤其文?故曰‘当仁不让’,此之谓也。”“礼”,本质上应该是仁爱之心的表达,是外在形式和实质内容的统一。如果看到人相食的惨状而不知道同情,这就是失去了仁德;仁德这一本质丧失了,礼节也就没有了意义。所以,子反的所作所为,是为了挽救实质的丧失,在这样的特殊而紧急的情境之下,当然也就无法再顾及那些作为形式的东西。总之,在董仲舒看来:“《春秋》之道,固有常有变,变用于变,常用于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故说《春秋》者,无以平定之常义,疑变故之大则,义几可谕矣。”[7](51-55)用于“变”的“权”之所以具有道德上的合理性,正是由于它是以仁义为质的。
不仅如此,为了强化重道义的立场,在“经”与“权”的关系上,董仲舒运用阴阳五行学说,论证了“经”和“权”之间存在着尊卑关系。他说:“阳行于顺,阴行于逆。逆行而顺,顺行而逆者,阴也。是故天以阴为权,以阳为经。阳出而南,阴出而北。经用于盛,权用于末。以此见天之显经隐权,前德而后刑也。”[7](327)董仲舒认为,“阳”的顺着常道的方向而行,“阴”的是逆着常道的方向而行。这样,“经”与“权”的属性和“天道”的“阳”与“阴”就是一致的。根据阴阳五行学说,属于“阴”的范畴的“权”是末节,而属于“阳”的范畴的“经”则是根本。同时,天之道“贵阳而贱阴”“近阳而远阴”,阳尊而阴卑,所以上天是显扬“经”而隐匿“权”的,以“经”为常道,以“权”为变通,“先经而后权”[7](327)。也就是说,在现实中的大部分情境之下,人们的行为都是遵循“经”这一体现着“常道”的要求的一般行为准则的,只有在偶然的、非常的情境之下,才可以使用“权”。同时,不同于“经”具有的普遍性价值,“权”是“一用而不可再”的,任何一次权变的行为都因与特殊的情境相联系,其正当性价值只存在于这一孤立的事件之中。
总之,在中国传统的思想之中,合乎道德的行为,必然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而要“顺乎天”,就不得不重视体现着“天道”“天理”的道义准则,而要“应乎人”,就不能背离人的特殊生活方式、生活情境、生活需要和幸福追求。经权问题的讨论,正是为了弥合遵守具有抽象性、确定性的道义准则与具体生活情境中行为结果的具体性、变动性之间可能会出现的缝隙。经权理论承认基于结果的考虑而暂时违背一般情境下应普遍遵循的道德准则的权变行为的合理性,同时又警惕着道德相对主义甚至道德虚无主义的风险。基本的途径,就是在坚持重道义的基础上,把道义与结果有机地结合起来,努力地将道义准则寓于行为结果的判断之中,从而避免二者产生根本的对立以至于出现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的局面。大一统的封建国家建立之后,从《公羊传》到董仲舒,经权观中道义论立场的明确和回归,反映的正是经权关系理论提出初期儒家学者对道义和结果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的调适与平衡。
——基于SZH的案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