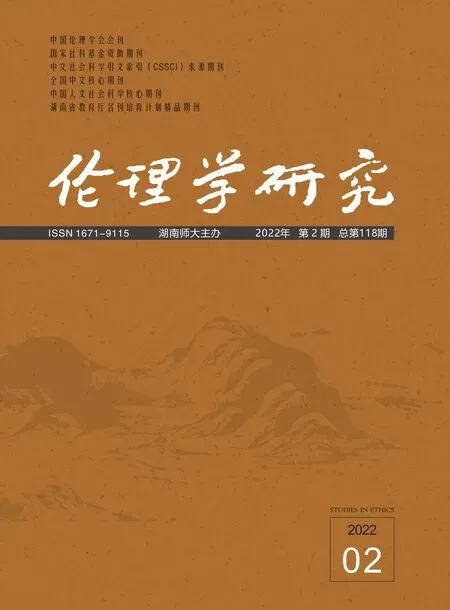“法天”以“利人”,“修身”以“为义”
——墨家天人关系视域下的伦理思考
王 正
传统中国伦理学对墨家的研究过于强调其功效主义甚至功利主义的一面①如梁启超认为:“质而言之,则利之一字,实墨子学说全体之纲领也……故墨学者,实圆满之实利主义也。”(梁启超:《梁启超论诸子百家》,商务印书馆2012 年版,第264 页)又如王讚源言:“墨子的兼爱和贵义思想,是基于功利主义。”(王讚源:《墨子》,东大图书公司1996 年版,第252 页)再如方旭东虽然改称墨家为后果论,但后果论的代表正是功利主义(方旭东:《从后果论看儒墨会通的一个可能》,《孔子研究》2021 年第1 期)。相近论说非常之多,乃是学界主流,但近年来开始出现反思这一倾向的讨论。参见郝长墀:《墨子是功利主义者吗?——论墨家伦理思想的现代意义》,《中国哲学史》2005 年第1 期;韦正翔:《墨家和法家思想与西方趋利思想的关系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年第4 期;张耀南:《论“大利”之作为“中华共识”——兼及“西式功利主义”与中国“大利主义”之比较》,《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4 期;陈乔见:《正义、功利与逻辑:墨家非攻的理由及其战争伦理》,《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3 期等。,而比较缺乏将之放置于中国先秦伦理思想发展的整体脉络下进行研究。如果我们将墨家伦理学放入中国先秦伦理思想的整体脉络来看,则可以发现,墨家伦理学是一种在天人关系视域下来进行伦理建构的哲学思想。而由这种视野出发,我们一方面可以发现墨家伦理学也是在“推天道以明人事”的中国传统思想模式下进行的,其之所以形成比较重功效的伦理倾向是与其天人关系论分不开的;另一方面可以发现,墨家的“十大主张”虽然与儒家迥异,但墨家的很多伦理思考路径与儒家非常相近,墨家和儒家的同与异构成了墨家伦理思想的独特性与复杂性所在。正是在这样一种思考背景下,我们可以更加恰当地反思,以功利主义这样一种西方近现代的伦理学派标签来定性墨家伦理学是否恰当②关于功利主义的一个清晰而简短的介绍,参见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刘莘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 年版,第12—66 页。。
一、墨家的天人关系论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墨家的天人观既有与儒家、道家等相似的地方,又有其独特性。于同者,墨家也认为人应当效法天;于异者,墨家对天的效法之强调要“强硬”得多,较诸儒家的天人以德贯通、道家的天人皆自然无为,墨家的天是以赏罚来“强制性”要求人行德的①关于儒家、道家、墨家在天道观上的差异以及墨家对儒家、道家相关思想的批评,参见高华平:《墨学四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 年版,第21—57 页。。之所以墨家在天人关系上采取了这种“强关联”的方式,在于墨家思想中对有效性的极度强调②如张纯一指出,儒家和墨家虽皆重视天道和道源于天,但儒家未如“墨者为人之多,救世之勇”,即墨家具有更强的用世追求。参见张纯一:《墨子间诂笺》,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 年版,第153 页。。
如所周知,墨家是极富改良社会、拯救百姓之意识的,所以其理论凸显了具体有效性和现实应用性,而其对天的理解正是从这方面切入的:“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既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然而天何欲何恶者也?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1](23)在墨家看来,无论人的个体生活还是社会治理、政治改良都必须效法于天。那么,天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墨家认为,天表现出来的状态是大公无私、善对万物、德行深厚而不自我夸耀,且它的这种状态是恒常如此而不会改变的;由此可以推出天是以爱万物、利他者为内容的,故而天的意志是希望人也如它一般兼相爱、交相利;所以人在社会生活和现实政治中,应当顺从天志,贯彻“兼相爱、交相利”的原则,不可互相伤害③葛瑞汉就此指出,墨家是具有统一的道德原则的,且其伦理学是具有普遍性的,即“墨家对利与害的权衡是为了所有的人,由‘兼爱’原则所主导”。参见葛瑞汉:《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张海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128 页。。
在墨家的这种理解中,天和人都应当是大公无私、兼爱互利的,即天是以兼爱互利为考察原则来审视人们的诸种行为并进行赏罚的:“今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此以莫不犓羊牛、豢犬猪,洁为酒醴粢盛,以敬事天,此不为兼而有之,兼而食之邪?天苟兼而有食之,夫奚说以不欲人之相爱相利也?故曰:‘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曰:‘杀不辜者,得不祥焉。夫奚说人为其相杀而天与祸乎?是以知天欲人相爱相利,而不欲人相恶相贼也。’”[1](22-23)天下的邦国无论大小,在天看来都是平等的;天下的人无论贫富、贵贱,在天那里都是一样的;因此无论大国小国、还是贫人富人,只要肯诚心祭祀,天都会接受他们的祭品而予以福佑。由此可见,天是兼爱天下而不分大小、贵贱的。故而人必须效法天的无私、兼爱,否则就违背了天的志欲,天就不会再福佑之,反而会降下灾祸以惩戒之。为了更好地论证这一点,墨家与儒家同样援引了历史上的圣王来为自己的理论作证明:“昔之圣王禹、汤、文、武,兼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为天子,天下诸侯皆宾事之。暴王桀、纣、幽、厉,兼恶天下之百姓,率以诟天侮鬼,其贼人多,故天祸之,使遂失其国家,身死为僇于天下,后世子孙毁之,至今不息。故为不善以得祸者,桀、纣、幽、厉是也。爱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汤、文、武是也。爱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恶人贼人以得祸者亦有矣!”[1](23)在儒家那里,禹、汤、周文王、周武王等是因为兴善除恶、彰显德性与德政而为天子的,他们身上的宗教色彩被弃去了很多,基本只在天人以德贯通的角度上来讲;而在墨家这里,这些古代圣王除了具有高尚德行外,更重要的是他们既能兼爱百姓,又能率领百姓“尊天事鬼”,所以天才赐福于他们,使他们成为天子。同样,桀、纣、周幽王、周厉王在儒家那里是因为虐民、丧德而被认为是暴君,所以失去天下;在墨家这里则被添上了“诟天侮鬼”这一条极富宗教色彩的重要罪名。显然在墨家看来,统治者能否被天所承认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他们是否大公无私地兼爱百姓,这是统治者能否得到天之福佑的根本原因;二是统治者是否对天、鬼予以很好地祭祀,这也是决定统治者能否得到天之青睐的重要原因。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墨家和儒家的一个重要区别:墨家和儒家虽然同样重视祭祀,但是儒家的祭祀、事天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对自我之超越性的延伸肯定和对外在无限而不可知者的敬畏;墨家的祭祀和事天、鬼则是从人的希求现实幸福与天、鬼可对人进行赏罚之意义上来讲的。这样看来,前者更多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带有一定宗教性的行为,后者则是一种世俗意义上的宗教性行为,两者存在着重要差异。正是由于这种差异,墨家在天人关系中更多强调了人的被动而又“强制”性地效法天志、鬼神之意义①正如罗哲海指出的,墨家“对于天的信仰,建立起凌驾于社会权威的客观、终极之标准,而不只是以实用目标来诱发行为的一种手段而已”,即“天志”这种至高无上的标准以更强的力度使人们践行“兼爱”。参见罗哲海:《轴心时期的儒家伦理》,陈咏明、瞿德瑜译,大象出版社2009 年版,第304 页。。
另外如上所言,天是无私、兼爱的,那么天对待人是否在所有方面都是没有差别的呢?并不是的。“故古圣王以审以尚贤使能为政,而取法于天。虽天亦不辩贫富、贵贱、远迩、亲疏,贤者举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废之。”[1](60)天在人的贫富、贵贱、亲疏等这些外在方面是无私的,但是在人的德行方面则是对待的,即只有有德者才会得到天的福佑,丧德者则会受到天的惩罚。其中赏罚的标准就在于人是否顺从、实行了“兼相爱、交相利”的天之志欲。“然则天亦何欲何恶?天欲义而恶不义。然则率天下之百姓以从事于义,则我乃为天之所欲也。我为天之所欲,天亦为我所欲。然则我何欲何恶?我欲福禄而恶祸祟。若我不为天之所欲,而为天之所不欲,然则我率天下之百姓,以从事于祸祟中也。然则何以知天之欲义而恶不义?曰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然则天欲其生而恶其死,欲其富而恶其贫,欲其治而恶其乱,此我所以知天欲义而恶不义也。”[1](193)天之志欲被墨家理解为义,即人对待事事物物时应当遵从的标准与法则。由此,义在墨家哲学中被推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成为与仁并称对举的重要德目。可以说,墨家在推动中国传统伦理学之形成仁义并重的特色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即它特别突出了义的重要价值②如朱伯崑所言:“墨子推崇仁义,是对孔子伦理思想的继承,其仁义并提,更早于孟子。”参见朱伯崑:《先秦伦理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年版,第149 页。。墨家还认为,是否有义是人能否持续生存、变得富贵和社会秩序逐渐优良的根本原因。可见,天的志欲是义,天是以义为标准来赏罚众人的。
那么什么是义呢?“顺天意者,义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1](196)“天为贵,天为知而已矣。然则义果自天出矣。”[1](198)“天之志者,义之经也。”[1](220)义是源于天的,因此其根本内容在于天的志欲,而天的志欲就是希望人们兼爱互利、厌恶人们互相残害——“天之意不欲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此天之所不欲也。不止此而已,欲人之有力相营,有道相教,有财相分也”[1](199)——,天赏罚众人的根本标准就是人们是否做到了兼爱、互利。所以,墨家的天人关系乃是天一方面大公无私地兼爱万民,另一方面又以兼爱、互利的原则来监察万民、赏罚众人;人则必须按照天的志欲去生活——在生活实践中按照兼爱、互利的原则去做,才能得到天的福佑,获得现实幸福,否则便会受到天的惩罚而不得幸福③墨家这种对天志、鬼神的信仰显然继承了上古泛神论的宗教观;但墨家在这种宗教观中又贯注了极强的人文色彩,即天志、鬼神之赏罚的决定权实际在于人本身,即人是否按照兼爱、互利的原则去行为(参见李卓:《从天志明鬼看墨子道德思考的二重向度》,《中国哲学史》2020 年第6 期)。而这样一种具有极大张力的天人观,为笔者下面所论述的人的认知、修养等主动性内容开辟了空间。。
可见,墨家的天人关系和人效法天乃是一种人对天比较具有“强硬性”的服从,那么为什么现实中还总是有人违背天的志欲而行互相残害的行为呢?墨家对此给予了一种认识论的解释:“天下之所以乱者,其说将何哉?则是天下士君子,皆明于小而不明于大。何以知其明于小不明于大也?以其不明于天之意也。何以知其不明于天之意也?以处人之家者知之。今人处若家得罪,将犹有异家所,以避逃之者,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慎之,处人之家,不戒不慎之,而有处人之国者乎?’今人处若国得罪,将犹有异国所以避逃之者矣,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慎之,处人之国者,不可不戒慎也!’今人皆处天下而事天,得罪于天,将无所以避逃之者矣。然而莫知以相极戒也,吾以此知大物则不知者也。”[1](208-209)人们之所以会违背天志,在于人在认识上对生活中大大小小的界域未能有真正清楚明白的了解,即未能从根本上认识到自己是生活在整个天下——天的志欲之下的,而并非仅仅生活在一家、一国之中。墨子举例道,现实中的人们一般能认识到自己生存在一国之中,因此知道仅仅按照对一家有利的自私标准是难以持续生存的,所以人们会对此有所认知,从而服从国家的众多规定。但是人们常常无法认识到自己从根本上来讲是生活于整个世界之中也就是天之下的,是无法逃脱天的监察、赏罚的,所以便会产生自己可以逃脱天的惩罚的侥幸观念,这样人就因着认识的不当而犯下了互相残害的错误,最终招致天的惩罚。“故子墨子置天之,以为仪法。”[1](219)此处的“天之”当即“天志”。墨家因为发现了人无所遁逃于天,所以认识到天的志欲便是人的行为标准,因此在天人关系中,人必须遵从天的志欲去兼爱、互利,这样天才会福佑人,否则便会惩罚人。这种带有“强硬”色彩的人“法天”理论,乃是墨家天人关系的特质所在。
二、“法天”视野下的墨家人论
如上所述,在墨家的天人关系中,人处于一种被天监察而比较“被动”的位置。但这是否意味着人在现实生活中就是绝对被动而毫无自主性的呢?墨家对此的理解是比较复杂的。因为在墨家的天人关系中,人之受到赏罚与否全看人自身的行为如何,所以人自身的主动性、主体性也在此得到展现。因此与儒家通过人禽之辨来将道德性内在地赋予人一样,墨家虽然不认为仁义等道德是人禽之辨的根本,但同样以严肃的人禽之辨来为人的道德主体注入了内容,只不过其内容是“力”。
墨家也将人丧失道德的行为称为禽兽的行为,并加以贬抑与反对:“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臭馀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1](74-75)天下人不“兼相爱、交相利”而互相荼毒残害的行为导致了天下大乱,这就如同禽兽的互相攻击、捕食一般无二。显然,墨家认为人和禽兽之间是有重要差别的,这种差别即墨家理解的“良道”。但与儒家将“良道”理解为道德,进而将道德本原归于“本心”“良知”等不同,墨家将“良道”理解为“力”。即在墨家看来,人禽之间的根本差异在于“力”:“今人固与禽兽麋鹿、蜚鸟、贞虫异者也,今之禽兽麋鹿、蜚鸟、贞虫,因其羽毛以为衣裘,因其蹄蚤以为绔屦,因其水草以为饮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树艺,雌亦不纺绩织,衣食之财固已具矣。今人与此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君子不强听治,即刑政乱;贱人不强从事,即财用不足。”[1](257)这里的“力”并不是力量、暴力等意,而是“强”的意思,亦即勉力而为、努力行之的“强”:禽兽鱼虫是只以自身所具有的自然生命能力为根本功能而进行简单生物性生存的存在,所以它们并不需要从事生产生活就可以自然生存了;人类则不同,人类一定要依靠自身的能力而勤勉生活,统治者要努力于治理的工作,否则刑罚政令就会混乱,被统治者要努力于生产活动,这样生活资料才会丰富。显然,禽兽们过的是一种自然而无意识性的单纯生命存活层面的生活,人类则过的是一种含有丰富维度的具有自主意识的有价值意义的生活:他们既有男耕女织之分工复杂的生产生活,也有政令刑罚等政治秩序生活。在墨家这里,“力”具有了深刻的哲学意义:它既指人的生活是有意识、有自主性的,否则谈不上勉力而为;也指人的生活是富有积极的人文性的,因为人从事的生活中有意义赋予、秩序建设等方面的内容;更指人的生活是具有道德价值的,因为其生活的原则是“兼相爱、交相利”。总之,“力”是墨家人禽之辨的核心观念。而由这个观念出发,墨家认为在人的道德生活和社会实践中需要反对那些对人的“力”之发挥具有障碍或消耗性的内容。
对这种意义的“力”,墨家有专门定义:“力,形之所以奋也。”[1](314)努力、勉力就是人积极主动地运用自身的形体来进行具有价值的实践活动。墨家认为人人都应尽“力”而为,在自己所当努力的事情上竭尽所能:农夫农妇当竭力于耕织,贤人当竭力于辅佐君主,君主当竭力于治理国家以顺从天、鬼之意。这个由人人竭力而形成的社会,即上面所述的“义政”:一方面墨家认为“夫义者政也,无从下之政上,必从上之政下”[1](193)。在“义政”的社会治理模式中,平民、各层治理者乃至天子都要既竭力于自己的职责所在,又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并接受更上一层对自身的管理、纠正,而最高的管理者是天;另一方面,“是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义也,是故选择贤者,立为天子……是故古者天子之立三公、诸侯、卿之宰、乡长家君,非特富贵游佚而择之也,将使助治乱刑政也”[1](91)。天为了使纷杂混乱的世间归于同一的理想社会而立人间的贤者为天子,天子及各级治理者皆意识到自身智慧和力量的不足,于是又层层设立下级组织来共同实现对社会的治理。因此上到天子,下到乡里之长,这些治理者并不是为了享受人间利益而产生的,而是为了竭力于社会治理才产生的。在墨家理想的“义政”社会中,层层治理者都既要竭力于自己的职责所在,又要服从于上层的管理,分权于下层的他者,根本上是要依从天“兼相爱、交相利”的意志而行事。这样一个社会乃是墨家意义上“力”“义”结合的社会①需要指出的是,“力”在墨家的使用中除了正面的勉力、努力含义外,还有暴力的含义。当然,对暴力意义上的“力”,墨家是极度贬斥的,此即上文所引“反天意者,力政也”(孙诒让:《墨子间诂》,孙启治点校,中华书局2001 年版,第196 页)。。显然,墨家以“力”为核心观念构建了由人禽之辨生发出的人生之应然状态与社会之理想状态。
可以说,墨家思想继儒家而起,对人禽之辨进行了另外一种模式的论说——以“力”为核心的论说,并由此展开了其关于人生与社会的诸多思考。但因为墨家的天人关系和儒家的天人观迥然不同,因此与儒家在人禽之辨视野下进行丰富的人性论思考不同,墨家并没有沿着人禽之辨进一步发展出深厚的人性论考虑,它仍旧是从效法天的角度提出了“所染”这样一种比较简单的人性思考②徐复观曾通过统计《墨子》中的“性”“情”出现的次数及具体用法,指出墨家在心性论上不及儒家透彻。参见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196 页。。
《墨子》中明确谈到“性”并进行讨论的内容其实很少,其中一处为:“为暴人语天之为是也而性,为暴人歌天之为非也。诸陈执既有所为,而我为之陈执;执之所为,因吾所为也。若陈执未有所为,而我为之陈执,陈执因吾所为也。暴人为我为天之以人非为是也而性。不可正而正之。”[1](404-405)这节文字的句读是有一些可讨论之处的,但整体来说,墨家在这里讨论的人性并不是一种确定的人性,而是一种人们通过自身对之赋予含义而构建的人性,另外也是一种对他人进行陈说性的可变的人性。虽然这里对人性的讨论并不是墨子人性论思想的核心内容所在,但这里的讨论仍旧对我们理解墨家人性论有两点提示:第一,墨家认为人性一定是符合天意的,所以暴戾等不符合天意,必然不是人性;第二,墨家对人性的思考乃认为人性是由后天的“诸陈执”所影响而成,所以在其理论中,人性不是先天固定的,而是后天受各种环境和行为之影响而不断变化的。
因此,最能代表墨家人性论的仍是《墨子·所染》篇所言:“子墨子言见染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1](11-12)墨家以染丝来比喻外在因素对人性和人的各类生活的影响:对于丝来说,用不同的颜色进行浸染,就会有不同的结果;对于国君来说,是受贤臣良人的影响,还是受奸臣佞人的影响,结果完全不同;对于一般的士人来说也是如此,身边的人若都是崇德行、遵法纪的人,则自己会变得德名荣显,身边的人若都是败德无行的人,则自己也会声名狼藉。显然,墨家所持的是一种后天环境影响论的人性论,这和儒家尤其是孔子、孟子所持的先天人性论是大为不同的①朱伯崑明确指出,墨学“承认人没有与生俱来的善与恶,其善恶的品质是后天形成的,即人们所处的环境影响的结果”。参见朱伯崑:《先秦伦理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年版,第166 页。。但是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丝虽然可以染成不同的颜色,但是它的材质毕竟还是丝,而如果其材质是棉、麻等则将如何呢?对于逻辑问题十分敏感的墨家,不可能完全对此问题毫无感觉,所以他们事实上还持有一种带有一定先天意义的人性论。
墨家这种带有一定先天意义的人性论,其实是一种当时一般人都持有的人性论:人都是好生恶死、趋利避害的。“民生为甚欲,死为甚憎,所欲不得而所憎屡至,自古及今未尝能有以此王天下、正诸侯者也。”[1](65)人们爱惜的是生,厌恶的是死,这是人生存的基本诉求。而人为什么会如此呢?墨家认为这正来自天志:“天欲其生而恶其死,欲其富而恶其贫,欲其治而恶其乱,此我所以知天欲义而恶不义也。”[1](193)天是希望人生存而不希望人死亡、希望人富贵而不希望人贫穷、希望人间为治世而不希望为乱世的,正因为天是如此,所以效法天的人也便如此。可见,墨家认为好生恶死、趋利避害是人的先天人性。然而这种先天人性却是一种变化的、缺乏实质内容的人性,其中尤其没有具体的善恶价值观念。故而墨家认为,“故时年岁善,则民仁且良;时年岁凶,则民吝且恶。夫民何常此之有?”[1](27-28)不同年景、不同环境都会对人性产生影响,甚至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可见,墨家始终认为人们是没有恒常的价值意义之人性的,人的先天人性只是一种趋利避害的意欲。
可见,墨家一方面认为人是有普遍人性的,即人性都是好生恶死、趋利避害的;另一方面这种人性又是没有恒常的善恶价值内容的,所以在人的生活中最重要的是后天影响。回到染丝的比喻上来,墨家认为重要的不是最初的材质,而是后天的所染,是后天所染决定了布的美丑(善恶),所以关键的问题在于后天之影响。故而在墨家的思想中,着重探讨的是后天影响之问题,而不是先天的人性问题。
但这种理论是否和墨家对义的重视构成冲突呢?为什么墨家认为将人性定义为好生恶死、趋利避害就够了呢?笔者认为这恰恰与其天人关系论有极大关系。如上所述,儒家的天人观是一种天以德命人而人具有积极主动性的理论,而墨家的天人观是一种天以赏罚来主宰人而人根本上只要效法天即可的理论。所以在儒家那里,先天人性极为重要,因为它是人一切行动的根本动力与方向所在;而在墨家这里最重要的是天志,人只要根据认识了解到的自己应当遵循的天志之内容去生存便可以了,人本身的人性内容并不重要。对于墨家来说,人性并不是一个重要的伦理学问题;人遵从天志而生存并获得幸福的生活,才是墨家伦理思想的关注点所在。
三、墨家的修身理论
既然人的生活应当遵循天志,那么在墨家看来,人只要能按着天的标准来努力、作为,就可以获得幸福。然而这种努力、作为并不是简单就能实现的,它也需要个体的修养、修身,因此墨家也同儒家一样重视人的自我修养与自我养成。当然,因为墨家在人性论、心性论上没有进行丰富的建构与论述,所以其修养论的丰富度不如儒家。
在墨家看来,“君子战虽有陈,而勇为本焉。丧虽有礼,而哀为本焉。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1](7)。人的各种行为都应以德行为根本,所以德行的养成乃是成就君子的根本所在。这种以德行养成为君子的思想,不得不说是受到了儒家的影响。而且与儒家相似,墨家也特别重视人的自我反省:“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迩来远,君子察迩而迩修者也。见不修行,见毁,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修矣。”[1](8)君子发现自己不被他人理解甚至被他人诋毁,却并不怨恨别人,而是反躬自省自己的道德品行是否有不足,这样通过不断地自我反思和自我修养,自己的品德就会日益高尚,他人的诋毁也就会逐渐消失。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讲的先王与君子的“察”之行为,其中一个隐含前提是从先王到君子都是进行了自我反省和自我修养的。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2](12)之观念。
墨家还认为,“君子力事日强,愿欲日逾,设壮日盛。君子之道也,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四行者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藏于心者,无以竭爱。动于身者,无以竭恭。出于口者,无以竭驯。畅之四支,接之肌肤,华发隳颠,而犹弗舍者,其唯圣人乎!”[1](9-10)首先,墨家强调人自我修养的“日强”“日逾”“日盛”。这种修身观与儒家一样,应当受到了古代圣王“日新”等思想的影响①《礼记·大学》载“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唐文治:《大学大义》,载《唐文治四书大义》,张旭辉等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版,第23 页),则熟悉“商周虞夏之记”的墨家对此很可能也有了解。,即认为努力行动、坚定志向、完善品德等是君子每天都需要进行的,不可有一日懈怠。其次,墨家认为自我修养是以心发动、以身显现、以言表达的,所以墨家也很重视身心的一致性以及德行在身体发肤上的外在表现。这和儒家的身心关系论也有一定相似性,即都肯定了内在修养和外在气象的统一。最后,墨家在这段表达中也呈现了一个从君子到圣人的个人修养目标脉络,即君子是自我修养的初步,继而君子通过不断的身心修养最终达到内外一贯而气象极佳的圣人境界。
当然,因为墨家的人性论是比较简单的,尤其没有在心性论上深入展开,所以墨家的修身工夫欠缺深刻、精微的心性维度,而更多强调言行合一、学行一致等方面。墨家认为:“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务言而缓行,虽辩必不听。多力而伐功,虽劳必不图。慧者心辩而不繁说,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誉扬天下。言无务为多而务为智,无务为文而务为察。故彼智无察,在身而情,反其路者也。善无主于心者不留,行莫辩于身者不立。名不可简而成也,誉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思利寻焉,忘名忽焉,可以为士于天下者,未尝有也。”[1](10-11)墨家在关于修身之具体内容的讨论中,特别强调立志、言行合一、守道、笃学博闻、反身、辨义利、成智等种种修养项目。然而因为欠缺一种系统性的心性体系和修养理论,所以墨家未能将这些项目整合成一个逻辑贯通的修身系统。这就如墨家的“十大主张”虽有一个大概的脉络,但更多是平铺式的关系,而欠缺一个逻辑推演的思想系统。就此而言,墨家虽然极其重视逻辑,但它并没有形成一整套的逻辑体系,这是其逻辑观的重要欠缺②王讚源引述钟友联、陈孟麟的研究,指出“墨子逻辑有反对形式化的倾向,重视语意关系,甚于重视语法关系”;当然他认为这并不妨碍墨家的逻辑有一个实质上的体系。但逻辑的实质体系不同于哲学的实质体系,它需要严格的形式为基础,而墨家在这方面的缺失使其逻辑无法真正体系化。参见王讚源:《墨子》,东大图书公司1996 年版,第141—144 页。。回到修养方面,尽管墨家提出了多种修身项目,但这些项目乃是一种平铺式的陈列,如果一定要从中提炼出一些纲领性的内容,或许言行合一、学以成智、明义以成德是墨家修养论中最为核心的三点。
言行合一是墨家修养工夫论的基础,因为墨家认为人禽之辨在于“今人与此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1](257),所以努力行之、勉强而为乃是墨家最为看重的德行。但墨家也知道,行动是要以思虑和表达为配合甚至是前提的,因此能正确地思虑和表达也是墨家颇为强调的。“嘿则思,言则诲,动则事,使三者代御,必为圣人。”[1](442)在墨家看来,人能够不断地进行沉默而不受干扰的思考、言语能教导他人、行动能符合道义,即思虑、表达、行动皆正确而一致,这样便可趋近于圣人。所以思虑上的产生真正的智慧、言语上的符合正确的道理、行动上的按照道义而行,乃是墨家修养工夫的三条重要法则。
因此墨家特别强调学习,而学习的目的在于获得真正的智慧:兼爱、非攻、天志、明鬼、非乐等“十大主张”。《墨子》中有很多关于三代之道的记载,包括很多《尚书》《诗经》的内容,这表明墨家非常重视对三代文献的学习。这与儒家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墨家对三代文献的认识与理解却和儒家迥异,即面对内容相近的文献,墨家解读出了和儒家不同的内容,这就是他们所提倡的“十大主张”。需要指出的是,墨家虽然认为人的智慧可以达到“十大主张”这十个在墨家看来具有真理性的认识,但是人的这种对于真理的认识并不是至高的,因为至高真理是由鬼神掌握的:“鬼神之明智于圣人,犹聪耳明目之与聋瞽也。”[1](422)故而人必须跟随鬼神的意志才能始终保持自己的智慧是符合真理的。由此,人的智慧和鬼神的智慧就产生了一种张力。墨家之所以在此形成了一种张力性的认识,仍在于其对天人关系的理解:人对天是一种带有“被动性”的效法之关系,天对人则具有监察与奖赏的根本权力。而“效法”正意味着人可以通过自身的“力”(勉力而为)实现对鬼神的意志——“十大主张”——的认识,所以墨家事实上又将鬼神的智慧与人的智慧统一起来①正如方授楚所言,“天之意志,即墨子之意志也”,墨家之知和鬼神之明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参见方授楚:《墨学源流》,山东文艺出版社2018 年版,第121 页。。而且墨家认为人会因为“所染”等原因造成“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1](74)等现实状况,所以人只有理解了自身智慧并不是真理后才能勉力而为地进行“尚同”——同于天子并最终同于天志、鬼神,即让自己的智慧统一于鬼神的智慧。
除了重视学习以达到真正的智慧外,墨子还特别强调通过义利之辨而践行道德。如上所述,墨子特别重视义,“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1](44)。在墨家这里,义不是什么空虚的德目,而是:“义,利也”[1](310),“义:志以天下为芬,而能能利之,不必用”[1](334),“义,利;不义,害”[1](407)。义就是对天下人有利,这正是天的意志所在,所以义就是人们行为的标准和最高的道德。故而人的行为都应当符合义,而不可背离之。另外,墨子所谓“义,利也”的利乃是公利,不是私利,所以墨子认为“思利寻焉,忘名忽焉,可以为士于天下者,未尝有也”[1](11)。可见,墨子也和儒家一样对义利之辨严格对待之。而且墨子同样认识到人在实践仁义之时,情感和肉体等因素会产生不良影响,故而墨子指出,“必去喜,去怒,去乐,去悲,去爱,而用仁义。手足口鼻耳,从事于义,必为圣人”[1](442-443)。人的喜、怒、悲、乐、爱等情感会让人的行为失去方向,从而无法符合义的标准,所以我们在生活实践中必须克制这些不良情感;同时不仅让心灵,更让自己的身体、感官等也都按照义的标准去行动,这样我们的行为才能始终符合义。可见,通过明确正确的义之行为标准而令自己的身、心皆符合义,乃是墨子修身工夫论的另一重要内容。
总之,墨家的修身工夫论虽然没有如儒家那样具有系统性、结构性,但是在日新德行、言行合一、学以成智、明义以成德等方面也有比较精彩的论述。而且虽然修身并不在墨家的“十大主张”之中,但其实如果说“十大主张”是高明智慧、真理认识、行为准则的话,那么上述的修身理论则是达到这种智慧、认知的基本方法。因此墨子说:“世之君子欲其义之成,而助之修其身则愠,是犹欲其墙之成,而人助之筑则愠也,岂不悖哉!”[1](444)“十大主张”如成型的墙壁,修身则是筑墙的行为,故而我们在研究墨家伦理思想时,不可轻忽其与儒家相似的这一修养论面向。
综上所述,墨家的伦理学乃是一种在天人关系视野下展开的具有丰富意涵的伦理学说。其虽然具有重视现实有效性的特质,但仍旧在人禽关系、修身理论等方面分享了与儒家相近的思想理路,这与墨子曾学于儒家有重要关系。而这也提示我们,韩非子之所以批评儒、墨,不仅因为他们是显学,更因为他们都有“俱道尧、舜”“言先王之仁义”[3](457,462)的特质,这种对德行、德政的强调乃与韩非子的法家理论根本相反。因此墨家的伦理学说虽然有重视实效的特征,但它实际上仍是一种重视德行的伦理学,我们不能因为它对功效的肯定就否定了其德行论的底色。因为德行的运用“总是需要承认对于社会和道德生活中的某些特征的某些先在的解说”①参见麦金泰尔:《追寻美德》,宋继杰译,译林出版社2003 年版,第229—257 页。方旭东提出,不只墨家可以被理解为后果论,儒家也可以被理解为后果论,而且两者都“欣赏‘老谋深算的功利主义”’(方旭东:《从后果论看儒墨会通的一个可能》,《孔子研究》2021 年第1 期)。这其实是只在表现上理解儒家与墨家而造成的误解,因为儒家和墨家的所谓“老谋深算”都不是工具理性之计算所能涵摄的,其中有着强烈的德行论基调。因此笔者认为与其将两者定性为后果论,毋宁为德行论。因为这种带有实现更大目标之考虑的德行论述正是当代西方美德伦理学所认可的美德论。,而儒家和墨家的这一前提正是他们的“明据先王,必定尧、舜”[3](457)。根据这样一个前提,墨家和儒家一样坚决反对通过理性计算而牺牲少数人的利益来获取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功利主义的重要主张②金里卡通过分析功利主义中偏好和平等的无法平衡,深刻指出了功利主义包含着一种“允许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牺牲弱小群体”的危险,进而蕴含着一种始终无法整合少数群体与多数群体的根本困难(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刘莘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 年版,第49—66 页)。,并认为“杀一人以存天下,非杀一人以利天下也。杀己以存天下,是杀己以利天下。于事为之中而权轻重之谓求。求为之,非也。害之中取小,求为义,非为义也”[1](404)。墨家认为,杀一人就已经违背了利天下的追求,因此这种行为根本不具有道德性;而且这种在道德与政治生活中权衡利弊的行为本身就是违背了天志、鬼神的意志——义——的,因此需要予以拒斥。可见,墨子的伦理学并不是一种贯彻西方近现代功利主义原则的伦理学,故而当我们运用功利主义这一范畴来描述墨家伦理学时常有一种纠结的感觉③陈汉生在论述墨家伦理学时一方面指出功利主义主要包含“行动功利主义”和“规则功利主义”两种,另一方面既认为墨家不同于这两种功利主义,又最终将之归结为功利主义,于是他创造出“词语功利主义”“体系功利主义”等词汇来描述墨家伦理学(陈汉生:《中国思想的道家之论——一种哲学解释》,周景松、谢尔逊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12—283 页)。事实上,墨家并非西方近现代哲学意义上享乐主义的功利主义、个人主义的功利主义,它其实与儒家一样具有责任伦理、德行伦理的特色。。因此笔者认为,墨家伦理学更应当被理解为一种人在天人关系视野下通过认知来了解“兼相爱、交相利”的天志、通过“力”来践行“义”、通过修身来落实墨家的“十大主张”,进而获得幸福的一种德行论伦理学④一些西方中国哲学研究者也多将墨家归为功利主义,如史华慈指出墨家的学说始终关注“外在世界”,以“行善”为导向而不关注“成善”,其所谓“爱”也缺乏感情性(史华慈:《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程钢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第150—161 页)。不过如本文指出的,墨家虽对人性的讨论不够精细,但也具有改良人性、修养道德人格的诸多理论,同样关注人的“内在世界”;而且其伦理学需要放在天人关系的视野下来进行讨论,它实际上是将“行善”和“成善”融合为一体的。由此,对墨家的功利主义描述是有失公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