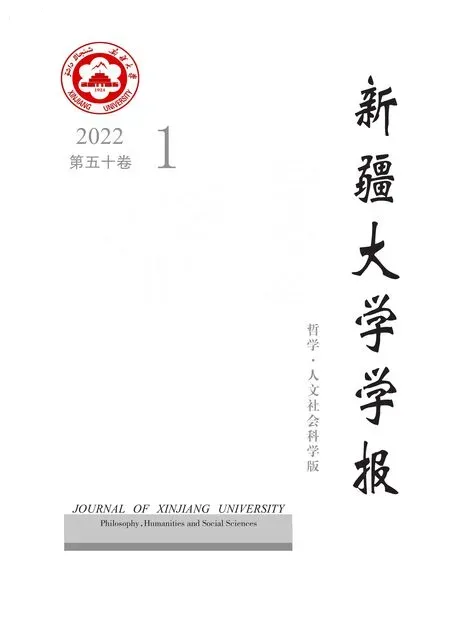基于状态义场景描述的存现句原型特征再探*
蔡 莉
(上海海洋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上海 201306)
一、引言
汉语的存在句属于存现句的一种,存现句的范围包括表事物出现、存在和消失的各类句式。这一观点由吕叔湘先生首倡,他将表“以某种姿态存在”、表“出现”、表“消失”三组句式总称为“存在句”①参见吕叔湘《从主语、宾语的分别谈国语句子的分析》,《汉语语法论文集》(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445-480页。。此后汉语学界一直沿着该思路探索汉语存现句,成为汉语句式研究的热点之一。传统语法研究重视对各类存现句进行细致描写,并探讨各构成部分特征;世纪之交,部分学者运用转换生成语法理论探索汉语存现句的生成,更多学者借鉴认知语言学理论对汉语存现句进行认知解释。
近年来,当代构式语法理论被引入汉语研究,由于该理论较适于解释汉语事实,学者们运用该理论和方法,对汉语中一些常用句式进行重新审视,取得了诸多重要成果。构式语法理论主张一种语言句式形成一个网络“清单”,显示各构式之间横向、纵向的各种承继性“链接”。立足于该观点,可见吕叔湘先生对汉语存现句的概括是合理的,事实表明“存在”预设了“出现”,“消失”又预设了“存在”,本是一条“链”。构式属更高层次的概括,类似Goldberg提出的双及物构式、致使——移动构式、动结构式等。②See Adele E.Goldberg.Constructions: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95,p.42.高层次概括的构式涵盖各类、各级下位构式,因此自下而上的探索方式有助于理清事实真相。比如帅志嵩借鉴词汇——构式理论对汉语存现句的内容和范围重新进行梳理,将存现句的“存”和“现”分开处理,分为静态存在式和动态隐现式两类,前者包括“是”字句、“有”字句和静态位置句(挂、站、贴)三个次类,后者包括出现式和消失式两个次类。此外,还分出了其他一些相关构式③参见帅志嵩《从词汇——构式范式看汉语存现句的分类和范围》,《语言教学与研究》,2017年第3期,第81-91页。。本文赞同该观点并立足静态存在式,着重探索“静态位置”句式,解析该构式的描述功能,暂不涉及其他相关构式。
需说明的是,汉语中单音词是基本单位,语义具有原型性;双音词是两个基本单位的结构体,语义具有整合性,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虚化、泛化。两者在词义、句法、语用等层面存在较大差异,研究语言现象需分而治之,才能保证研究的有效性与准确性。①参见沈家煊《“单双区分”在汉语中的地位和作用》,2013年,日本中国语研究学会第63次年会主题报告(东京,10月)。因此,本文的考察限于单音动词构成的存在句。此外,为表述简明,笔者简化了所用语料,不再一一标注出处,特此说明。
二、功能甄别:陈述与描述
根据帅志嵩对存现句的分类,静态存在式包括“是”字句、“有”字句和静态位置句三个次类。本文首先甄别这三个次类的功能。
(一)“是”字句
吕叔湘先生对“是”的释义是:主要有肯定和联系的作用,且可表多种关系。其中有一种与空间处所有关,所以被认定表存在。②参见吕叔湘主编《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30-134页。下面是《八百词》所举例:
(1)山坡上全是栗子树。
(2)靠墙是一排书架。
(3)他满身是泥。
(4)遍地是鲜花。
笔者认为,对“是”字句表存在的现象我们须重新加以审视。以上《八百词》所举例句有一个显著特征:构式义具有“排他性”,句中往往会出现表全覆盖的范围副词,如例(1)的“全”、例(3)的“满(身)”、例(4)的“遍(地)”。若将“是”字句和“有”字句进行比较,这种差别更明显。例如:
(5)a.箱子里是书。
b.箱子里有书。
上例a句表明箱子里只有书,没别的东西;b句表示箱子里有书,但不排除还有别的事物。可见“是”是关系动词,表前后两个NP空间意义上对应关系,表“判断”功能。如上述a句“箱子”(空间)与“书”(空间占有物)的对应,是一种特定判断,从中我们也能发现“有”字才真正表“存在”。事实上当“是”字与“有”字在同一句中共现,这种差别表现更为充分。如鲁迅《野草秋夜》中的结尾句:
(6)窗外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
例(6)作者先认定窗外有树(存在),再认定它们都是枣树(判断),这说明“是XX”(表判断)预设了“有XX”(表存在)这个前提。孙文访曾指出:“从语言类型的角度看,‘是’动词表示的基本概念,具有如下蕴含共性:判断>处所>存在>领有,汉语和藏缅语系大部分语言中‘是’动词只表‘判断’的基本概念。”[1]
依据上述解析,笔者认为“是”字表存在,是其派生功能,其基本功能仍表判断。“是”字句本身是一个构式群,包括很多下位构式,按照《八百词》的阐释,可表等同、归类、特征、质料、领有或其他关系,表存在是其中一种。因此,与其将“是”字句分解,各归其他构式,不如确立“判断”功能统辖的构式群,使其在汉语构式网络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有”字句
“有”字表存在前辈学者早有定论。黎锦熙在《新著国语文法》里即以“茶棚里有许多的工人”为例,指出“有”表“存在”③参见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46页。。吕叔湘进一步表示“以某种姿态存在”的存在句中,表存在事物的词语是无定的,可用“有”字将其提到动词前,如“榻上坐着一老子”可改为“榻上有一老子坐着”,且强调“有”是最单纯地表存在的动词。④参见吕叔湘《从主语、宾语的分别谈国语句子的分析》,《汉语语法论文集》(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445-480页。笔者认为,这揭示了“有”表存在的语用功能,即确认了“某处存在某物”这一事实,但不涉及“某处”具体场景和“某物”具体状态。例如:
(7)这种鱼好像有毒。
(8)太阳系有九大行星。
(9)空中有一个不明飞行物。
(10)听说无锡有座灵山大佛。
(11)团长胸前有一道刀痕。
(12)他么,思想上有负担,心理上有障碍。
上述例(7)中“有X”是微观的,需化验检测;例(8)中“有X”是宏观的,需天文望远镜才能观察到。例(9)中“有X”说话人能看到,但却是不明飞行物;例(10)中“有X”是事实,但说话人却没看到过。例(11)中“有X”是具体的;例(12)中“有X”是抽象的。可见“有”也是一个关系动词,只要说话人相信或确认“某处”与“某物”的存在事实,就能用“有”字句来表述,因而命题本身也可被否定,否定形式是“没有”。因此,我们认为表存在的“有”字句的语用功能是“陈述”。
(三)“静态位置”句
由于“有”字句的功能是确认(或否定)一个存在事实,而不论这个存在事实的场景和状态,因此“有”字可用描述性动词来替换,使“抽象”的存在概念转化为“具象”的存在状态。例如:
(13)教室里有不少学生。
→教室里站着不少学生。
→教室里躺着不少学生。
→教室里跪着不少学生。
如上替换的句子正是吕叔湘先生确认的表“以某种姿态存在”的句式,这类句式的特点:①V都是不及物动词,表人或动物的身体运动或变化;②表存在事物的词语都具有不定指的特点;③整个存在句句式义表示某人或动物“以某种姿态存在”。下面是其所举实例:
(14)街北蹲着两个大石狮子。
脚底下横不楞子趴着条流浪狗。
斜对门的豆腐店里确乎终日坐着一个杨二嫂。
此类句式正是本文探索的对象,命名为“描述性存在句”。此类描述场景状态的存在句具有“具象性”、“可感性”和“现场性”的特定,下文将详细阐释。
三、语义整合:动作与状态
存在句构式包括三个构件,可码化为:L(方位)+V(着)+(数量)N。从句法层面看:L为处所词,后附方位词凸显场所义,V为不及物动词,后附持续性标记“着”,N为实体名词,前附数量词体现不定指属性。下面先考察由不及物动词构成的原型构式,再考察由及物动词构成的扩展构式。
(一)原型:V为不及物动词
结合例(13)和(14)解析该构式的三个构件,并阐释“具象性”、“可感性”和“现场性”在原型构式中的具体表现。
1.关于构件L。从上述实例看,该构式描述了场景状态,句首处所词为话题成分,有两个特征:其一,语义上,均表具体、可感的场所,从大小看能容纳所描述的人或动物,从远近看所描述的人或动物在说话人视野范围内。其二,形式上,这些词大都后附方位词,以强化场所义。这两个特征为构式描述人或动物的存在状态提供了合适的存在场所。如上文所举例:教室里、街北、脚底下、斜对门的豆腐店里。
2.关于构件N。从上述实例看,句末名词也有两个特征:其一,语义上,均表具体、可感的实体,主要为人或动物,也包括塑像之类的仿制品。其二,形式上,词前均附数量词,以表不定指属性。从构式的整合理据分析,该构式要凸显某物(人或动物)存在的场景和状态,具有描述功能,不在意存在物的“身份”。因此该存在物大多为不定指的,即使是定指的,形式上也会添加不定指标记“一个”,如“一个杨二嫂”。由于存在物不定指,所以只能置于V后,与句首处所词话题相呼应。如“来客人了”中的“客人”是不期而至的(不定指),只能后置(相对于“客人来了”)。这两个特征为构式描述场景状态提供了合适的存在物。如上文所举例:不少学生、两个大石狮子、(一)条流浪狗、一个杨二嫂。
3.关于构件V。构式义及语用功能是核心动词与构式互动的产物,其中核心动词的属性是主导依据。同理,描述性存在句中V是核心构件,指派了前置的“存在场所”、后置的“存在物”,形成了合理的编码序列。从上述实例看,核心构件V也有两个特征:其一,语义上,均表人或动物身体的运动和变化,属于不及物动词,具有[+附着]的语义特征,表明某物以某种状态附着于某处,可概括为“体动”义动词。卢英顺也认为:“存在句中动词所激活的认知图景必须包含‘处所’这一认知要素。”[2]其二,形式上,动词后都带有持续义句法标记“着”字。若动词表行为动作,那么“着”就表动作过程的持续;若动词表示存在状态,那么“着”就表存在状态的持续。因此,描述性存在句中“V着”预设“VP了”这一事实,比如“床上躺着一个人”的状态预设“有个人在床上躺下了”这个过程,即动作完成后转化为某种状态。这两个特征凸显了该构式存在物的具体存在状态。如上文所举例:站着、躺着、跪着、蹲着、趴着、坐着。
(二)扩展:V为及物动词
前文曾提到,“有”字句的功能是确认(或否定)一个存在事实,而不涉及这个存在事实的场景和状态,因此“有”字可用描述性动词替换,使“抽象”的存在概念转化为“具象”的存在状态。事实表明,描述性动词也可以是某些及物动词。例如:
(15)墙上有一幅画。
→墙上挂着一幅画。
→墙上贴着一幅画。
→墙上画着一幅画
上述“有”字句仅表明“墙上有画”这个事实,不涉及这幅画的状态。同类实例如下:
(16)地上铺着一溜红地毯。
窗户上钉着很多木板条。
后台堆着不少用过的道具。
台前摆着很多鲜花。
柜子里放着几个古董花瓶。
头上插着一支铮亮的金钗。
胸前别着一枚新校徽。
(17)旗袍上绣着一朵牡丹花。
包装箱上印着五星红旗。
黑板上写着一个通知。
洞边石壁上刻着“棋盘洞”三个大字。
大殿立柱横梁上都描着古朴的图案。
及物动词构成的存在与不及物动词构成的存在属于同一类构式,只是在原型基础上有所不同。原来的不及物动词被某些及物动词所替换,因此下面集中解析核心构件V,以及V的替换对构件L和N产生的连锁反应。刘街生考察存在句的动词,提到了两类动词,一类是“置放”义动词,另一类是“创作”义动词。①参见刘街生《存在句的动词考察》,《汉语学习》,2013年第1期,第13-19页。笔者赞同这一观点,下面先解析“置放”义动词构成的存在句,再说明“创作”义动词构成的存在句。
1.V为“置放”义动词
构式中V为不及物动词时,动作瞬间完成后表示自身附着于某处的状态。而例(15)和(16)列举的V都是“置放”义及物动词,动作都涉及特定客体,也具有凸显场景状态的语义特征。陆俭明等把这些动词具有的共同语义特征概括为[+使附着],即这类动词通过某种行为方式使某物附着于某处。②参见陆俭明、沈阳《汉语和汉语研究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20页。
但上述[+使附着]的语义特征均表行为动作,而存在句凸显的是某种场所与状态,因此核心构件都是“V着”。在原型构式中,不及物动词V表主体的“状态”,而在扩展构式中V是及物动词,只表动作的“方式”,如“挂、贴、铺、钉、堆、摆、放、插、别”。由于及物动词均带有特定客体,[+使附着]的语义特征表现在这些动词将客体附着于某处,因此不同的“方式”致使客体表现出某种“状态”。构式要凸显的某种状态通过V转移到N,此类存在句的N通常非光杆名词,常带有描述性修饰语,如例(17)。这种被转移的状态附着于存在物,而存在物又被衬托于某场所,因此此类存在句常连用,以描述一个完整的场景。请看如下例句:
(18)屋子里很干净,墙上挂着几幅油画。靠墙摆着一个小衣柜,柜子上放着一台电视机和一台录音机。
此类存在句虽为扩展式,但描述功能却比原型构式更充分、更典型,体现了构式的成型效应。
描述性存在句的V被及物动词所替换,核心动词V及其客体N,甚至构件L都会受到影响。在此类扩展构式中,存在物都是V连带的客体(实物),实物的形状和大小千差万别,导致场所L的空间也可大可小、可远可近,只要是视野所及,范围没有限制。比如“手上带着戒指”中“手上”表述的空间近而小,“山上架着炮”中“山上”表述的空间远而大。笔者从检索出的描述性存在句语料看,扩展构式的使用频率远高于原型构式。
2.V为“创作”义动词
例(17)中“创作”义动词可进入描述性存在句,蕴含了[+使附着]的语义特征。这些动作(如:画、绣、印、写、刻、描)进行的前提是存在“载体”。与“置放”义动词不同,“创作”义动词的连带客体是动作的“产物”,即动作完成后才存在。客体N都是动作完成后留下的痕迹,[+使附着]的语义特征表现为动作在某载体上实施,从而逐渐形成“产物”。因此,“置放”义动词使附着的客体可移动,而“创作”义动词使附着的客体不可移动。除此之外,两类动词进入描述性存在句的其他表现相同,不做赘述。
(三)描述性存在句的构式语义与语用功能
依据上文对原型构式及扩展构式的解析,我们可将汉语描述性存在句的构式语义与语用功能分别概括如下:
构式语义:某人或某物以某种状态存在于某场所。
语用功能:说者对观察到的某场景状态加以描述。
上述概括有三点值得说明:
其一,关于时间背景。笔者认为,描述性存在句凸显的是某人或物存在的场所与状态,因此表“场所”的成分必须出现。时间要素是交际双方“默认”的,在语境中可隐可现,不是描述性存在句的必要构件。
其二,关于语义角色。根据“构式赋义”原理,构式中动词与其相关名词的语义关系不是恒定的,而是根据构式语义整合的需要指派语义角色。比如“某人在床上躺下了”,“某人”的语义角色是“施事”;“有人在墙上挂了一幅画”,“一幅画”的语义角色是“受事”;这是因为它们都是客观事实的陈述性句式,构式以“V了”为核心分别指派了施受语义角色。而“床上躺着一个人”和“墙上挂着一幅画”,“一个人”和“一幅画”的语义角色都是“存在物”,这是因为它们都是场所状态的描述性句式,构式以“V了”为核心指派的语义角色。
其三,关于构式变体。根据实际语料,描述性存在句还出现核心动词形式为“V了”的情况。比如存在一个事实前提:某人在院子里停了一辆车,停好了自然成为一种状态。对于这样一个场景状态,可以有两种情景表述:
(19)院子里停着一辆车,已经好久了,也不知道是谁家的。
(20)老张下班回家,看到院子里停了一辆车,知道儿子来了。
上述例(19)“院子里停着一辆车”,核心动词是“V着”,这是一般形式存在句。例(20)描述了同一事实,核心动词变为“V了”。从语境角度,老张看到院子里停了车,就知道儿子回来了,说明这是儿子的车,平时院子里没有这辆车。此时“了”不是完成体标记,而是实现体标记,预设“原来不是这样”。带实现体标记“V了”同样能实施描述性存在句的功能,只是语义上增添了说话人略感意外的心理色彩,这是实现体标记“了”表明的预设效应。因此,笔者认为此类构式可看作描述性存在句的“变体”。
四、构式偏离:静态与动态
(一)表“动态”的存现句
上文指出汉语描述性存在句具有“静态”的显著特征。由象似性动因推理,有定格摄影,就有连续摄像,这样静态就会变成动态。语料显示部分描述性存在句中场景的存在物确实为“动态”的。如:
(21)地上爬着一条蛇。
花丛中飞着几只蝴蝶。
湖面上漂着一片绿藻。
池塘里游着几条金鱼。
空中飘着几只风筝。
上述实例与前文所举描述性存在句相比,构式义和语用功能均未变,唯一差别是上述实例中核心动词都具有[+自移]的语义特征,因此场景中的存在物显示为“动态”,如上例中的“爬、飞、漂、游、飘”。须强调的是,这些存在物的移动必须限制在说话人的视野之内,未突破场景的界域。因此构式仍维持了描述性存在句的“底线”,不过已经边缘化了。根据构式研究经验,一个构式一旦出现了边缘化的用例,就预示着构式变异的开始。当场所中的存在物是静态时,构式容易控制;一旦存在物在动,构式就容易失控。因为动态存在物一旦突破说话人的视野框架,构式必然变异,这就产生了所谓的“出现”与“消失”。下面分别加以阐释。
(二)描述性“出现”与“消失”
“出现”情景是某物移动进入某一场景,使某一场景中的存在物“从无到有”。如上面所举实例的“出现”:
(21)a.地上爬来一条蛇。
花丛中飞来几只蝴蝶。
湖面上漂来一片绿藻。
池塘里游来几条金鱼。
空中飘来几只风筝。
此类变异很简单,“来”是趋向动词,参照点向说话人移动,因此这些实体(人、动物、实物)就“V来”了,进入了说话人的视野框架,属于描述性“出现”。
“消失”情景是某物从某一场景中移动消失,使某一场景中的存在物“从有到无”。如上面所举实例的“消失”:
(21)b.地上那条蛇爬走了。
花丛中那几只蝴蝶飞走了。
湖面上那片绿藻漂走了。
池塘里那几条金鱼游走了。
空中那几只风筝飘走了。
描述性“消失”则不简单,显著变异有两点:其一是构式编码序列调整了,存在物从动词后移到动词前,并添加了指示代词“那”。其二,“V着”被“V走了”所替换。“走”除表行走义,还表常见义“离开”,与“自移”义动词组合成述补结构“V走”,表消失状态;“了”是实现体标记,预设了原来没消失。蔡莉考察可离合NP句式变换时曾指出:“存在物移到句首充当话题成分,是对客体消失义的主观陈述,表话题成分遭受损失义。”[3]可见,描述性“消失”体现了说话人的主观识解。
(三)陈述性“出现”与“消失”
通过上文解析,可知表出现与消失的句式,也有“陈述性”与“描写性”差别。通常提到表某物出现或消失的句式,总会列举如下例句:
(22)客栈里来了一帮客人。
客栈里走了一帮客人。
可见“来”“走”与“出现”“消失”确有某种内在联系。按照词典释义,此类用法的“来”表“来到”,“走”表“离开”,可见它们表义空灵,非具体动作义。上述实例中“出现”与“消失”属于陈述性表述,不含“具象性”“可感性”和“现场性”描述特征。说话人只要确认或相信某人某物“出现”或“消失”的事实,即可选择此类表述,动词带上实现体标记“了”。陈述性存在构式非本文论述对象,不做扩展讨论。
五、结语
语言研究的事实表明,对于同一语言事实,运用的理论和方法不同,观察的角度和视点不同,分析和解释的结论也不同。这就好比晒渔网,太阳照射的角度不同,地上显示的投影也不同。
施春宏指出:“语言学研究应将构式看作语言系统的基本单位,将构式的描写和解释作为基本任务;方法论上强调整个构式是无法充分还原的,因此还原论和演绎法都不能作为分析构式的基本方法。”[4]因此本文根据构式语法的理念,采取整体论和归纳法的分析方法,以存现句构式作为切入点,基于“状态义场景描述”的定位,对汉语存现句加以重新审视,旨在揭示其原型特征,从而为进一步考察该构式的扩展、偏离及其承继关系提供一个可靠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