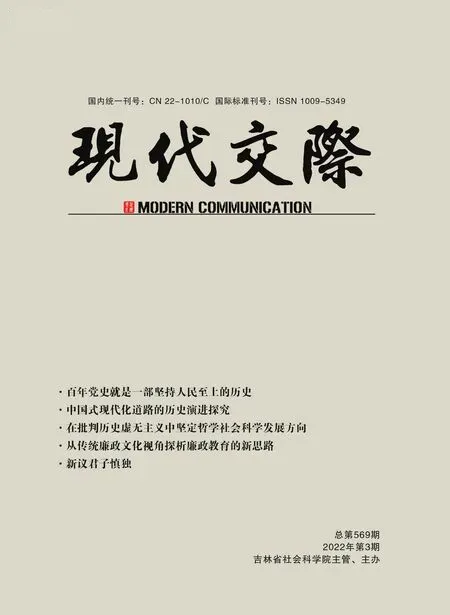新议君子慎独
□罗蜀茸 毕明良
(西藏民族大学 陕西 咸阳 712000)
“慎独”是《中庸》里极为重要的一个概念,“独”既有独居、独处之意,又有人前人后保持如一的含义。郑玄和朱熹都对此有过注解,因两人的影响力较大,导致后世一些理学家及其弟子在解释“慎独”这一词时,被其观念影响而产生相似的理解。郑玄及朱子对“慎独”概念的解释并不完全准确,后世理学家对此概念的研究也很片面。受这些观念的影响,当代学者多从“道德意志”和“诚于中,形于外”这两个角度出发去理解“慎独”。但是仅仅围绕“独处时行为谨慎”和“要多注意外在行为规范”这两方面去理解,未免过于浅显,除了不能做到人前人后行为一致,思想和行为的不一致也是不能慎独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此外,在提到“慎”时,宋儒常用“敬”这一词与其关联,忽略了“诚”与“慎”在内心修养方面表达的含义颇为相似。
一、何为“毋自欺”
“诚其意者,毋自欺”,即不要欺骗自己。正如《大学》里提到的:“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1]8“慎独”的前提是“毋自欺”,“诚其意”的前提是须发自内心的,且是自然的表现,就像面对难闻的气味会不自觉地表现出厌恶,看见美女会不自觉地喜欢,是一种没有经过大脑思考后自然反应的结果。“自谦”,是做到“诚意”后的一种情感满足的表现,换言之,就是做到“毋自欺”之后产生的自我满足。因此,“诚其意”就是面对自己真实的内心,继而在真实的基础上遵循由内心的引导发出的行为。
君子说的“毋自欺”并不是在任何时刻都不欺骗自己,而是指断绝自己“不善”的念头。如若不然,即使在自己不喜欢的人面前,也不加掩饰地表达出对此人的厌恶,这不仅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悖,更与儒家的本意背道而驰。《大学》中虽然没有明确说出当面向人表达自己的厌恶是否正确,但是根据传统儒家表现出来的礼义看,即使是讨厌一个人,也不会在面对这个人的时候有明显的表现。因此,“毋自欺”讨论的部分不包括主观上的喜怒哀乐,只提及有关“诚其意”这一部分的内容。此外,“诚其意”所呈现出的“意”也一定要符合“善”的要求,否则“诚其意”便没有讨论的价值。
明代王守仁提出的“知行合一”是对“毋自欺”的进一步解释。他的“知行合一”含义为:认识事物的道理与其实际执行不可分割。“知”是通过学习对事物产生的了解与认识,“行”是通过已知的道理切实表现出来的行为。做到知行合一,并不是单纯地表现知,认为知等同于行,也并不是单纯地表现为行,认为行能完全体现出知,而是在内要有良知,在外要有良行,“知”与“行”缺一不可。如果没有致良知的过程,就不会展现出实实在在的善行,也体会不出“毋自欺”的重要性。知行合一要有良知正见,坚持正确的道理,无论待人还是接物都没有歪心邪念,哪怕自己会受到打击报复,也要坚定理想信念,毫不动摇。这才是“诚其意”者应达到的“毋自欺”的状态,而并非仅理解为“不欺骗自己”这一浅显含义。
实际上,自欺这种行为源于“知”与“意”关系没界定好。朱熹在《大学章句》中对“自欺”有如下定义:“自欺云者,知为善以去恶,而心之所发有未实也。”[1]8朱子认为会产生自欺行为的人,虽知善知恶,但皆是“心未发”的原因所在。“毋自欺”听似简单,却不易做到,因为欺骗自己是人的本能,两千多年前的“掩耳盗铃”的故事就为这种实在现象提供了佐证——“范氏之亡也,百姓有得钟者,欲负而走,则钟大不可负。以锤毁之,钟况然有音。恐人闻之而夺己也,遽掩其耳”。偷钟者意图掩住自己的耳朵来掩盖自己偷钟的行为,这就是典型的自欺。
二、慎独和闲居的区别
《辞海》对“慎独”的解释是“在独处时能够谨慎不苟”,《词源》的释义为“在独处无人注意时,自己的行为也要谨慎不苟”。因此“慎独”通常情况下会被理解为“人在独处的时候要小心谨慎”,即主体在没有外界条件的约束下,依然能保持自己的德行。从这方面看,“慎独”与“闲居”在表面上是相近的,但实际上两个相似的词表达的方向完全不同。“慎独”指向的是行为修养方面,主要强调的是内心;“闲居”没有涉及修养方面,着重强调处于某种“空间”。两个词无论是表达内容还是使用方式完全不一致。因此,把“慎独”解释为“闲居”实质上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没有弄清其概念。
“慎独”之所以被误解为“闲居”,源于东汉郑玄对“君子慎其独”的注。郑玄注为:“慎独者,慎其闲居之所为。小人于隐者动作言语自以为不见睹、不见闻,则必肆尽其情也。若有占听之者,是为显见,甚于众人之中为之。”[2]意为:当一个人(这里指道德品质相对较差的人)独居独处的时候,因他人不会注意到自己,行为就会很放肆。如果其他人在这时看到他,就会发现他与平时在众人跟前的样子有很大区别。于此,“慎独”即为人“独处”之时依旧能保持良好的道德操守。郑玄对于“闲居”的理解似乎是合乎逻辑的,而且文字上也讲得通。因为“独”确实有独居、独处之意。按照这种说法,只要自己一个人居住,那么他就处于“独”的状态,这种解释显然是不对的。《礼记·孔子闲居篇》里提道:“孔子闲居,子夏侍。”[3]651这句话表达的“闲居”含义自然与“自己一个人居住”的含义不相符,否则,孔子在自己一个人居住的时候,身边怎么还有另一人在身边侍奉呢?这就与“自己一个人居住”相违背了。显然,“闲居”并不完全是独自居住的意思。从这个方面来讲,“慎独”自然也不只是在独处时小心谨慎了。实际上,郑玄所提及的“闲居”不仅不是慎独的核心内容,还误解了慎独的根本。王阳明则认为“独”不仅是自我独知的念头,它同样包含了知此独知之念的知:“所谓‘人虽不知,而己所独知’者,此正是吾心良知处。”[4]
梁涛在其著作《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中提到“《帛书五行篇》与《中庸》的‘诚明’部分在文风上也有相似之处,两篇都是论‘慎独’。据研究,《中庸》的慎独并非如郑玄所云,是指‘慎其闲居之所为’,而是针对‘诚其意’而言,与《五行》‘能为一,然后能为君子,慎其独也’是一致的”[5],同样能证明上述论点。
郑玄及朱子的误解在于把“诚其意”这种内在行为理解为“慎其闲居所为”的外在行为,这才导致把精神上的一致性理解成空间上的独处、独居,从而造成了整体理解发生变化。
三、“慎独”的第二重含义
朱子对“慎独”的理解有所偏差,源于朱子在注解《大学》中“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1]20这句话时,做出了如下解释:“此言小人阴为不善,而阳欲掩之,则是非不知善之当为与恶之当去也,但不能实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掩其恶而卒不可掩,欲诈为善而卒不可诈,则亦何益之有哉! 此君子所以重以为戒,而必谨其独也。”[1]21这种解释显然是有问题的:朱子认为小人闲居本不善,但是当小人见到君子后,选择掩盖了其不善的行为,向人展示出善的行为。换言之,在朱子看来,人会产生自欺之举的原因并不是其不知善恶,相反,正因为此人知善知恶,且明白自己的行为称不上是“善”,才想着隐藏不善的行为。
朱子认为,小人之所以做出“不善”之事,源于其意志力不够强大,因其“意”无法控制其“行”——薄弱的意志无法迫使其行为服从道德约束,才会有自欺之举。既然伪装不能真正掩盖自己不善之行,那么对自己的行为应多加注意,从源头去解决“掩其不善,而著其善”——改其恶行,就不会再出现这种“掩其不善”的行为了。
朱子对慎独的理解之所以有所偏差,是因为小人闲居不善的原因并不是“不能实用其力以至此耳”,而是小人在日常的行为中就经常做些不好的事。这些不好的事与意志力、“实用其力”等毫无关联。小人在见到君子后,将自己的行为与君子对比,发现自己的行为相差甚远,因而才选择隐藏其“不善”的行为。这种隐藏并非发自内心,仅仅是一种来源于君子带给他的强烈对比的道德压力。此时他并没有自觉到他私下的行为有何不妥,只是想着要藏起来而已。而隐藏的动机也并非来自良心发现或产生了羞耻之心,只是在发现别人做了善行后,习惯性地隐藏自己不好的行为。这是小人之所以为小人的原因所在,他没有反思自己的行为有何不妥,反而想隐藏不为人知的一面,这才是小人“掩其不善,而著其善”的前提。小人并没有从本质上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所在。
人的内在和外在表现在很多时候是有一致性的——人的内在意志会在日常行为中逐渐表现出来。因此,在观察一个人的时候,往往是由外及内逐渐看到一个人的本质。当小人产生想做坏事的想法时,他总会在不经意间通过某些行为展现出来。“内”与“外”的不一致是小人“闲居不善”的最本质原因所在,并非如朱子所说在于没有能力监督好自己。
需要强调的是,小人的不一致大概可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人前人后的行为举止不一致,第二种是内心想法与外在行为不一致。这两种不一致都是没有做到“慎独”的表现,而第二种不一致更能体现道德品格。如果一个人内心产生了不好的想法,即便他没有讲出来,别人也没有发现,他此时此刻也没有做到“慎独”。前文已经提到,“慎独”的前提就是“诚其意”,且“诚”的“意”也符合“善”,而此时他的想法与“诚其意”完全相反。因此,“慎独”不应以公私作为区分,因为无论公众场合或私人场合,都应该保持内心的清明。“诚于中,形于外”,慎独作为一种道德力量,要从最根本的地方——内在的精神修养出发,达到人前人后恒常如一。“慎其独”与独处、独居毫无关联,因此《荀子集解》里讲道:“是以辟耳目之欲,而远蚊蝱之声,闲居静思则通。”[6]476
王阳明的弟子王畿在慎独方面也有所感悟,他的慎独与王阳明有所不同。相较王阳明来说,王畿似乎更重视本心,他说:“独知便是本体,慎独便是功夫。”他认为独知本身就是先天的本体。“独知者,非念动而后知也,乃先天灵窍,不因念有,不随念迁,不与万物作对,譬之清净本地,不待洒扫而自然无尘者也。”[7]151王畿在这里把王阳明所说的良知转化为佛教讲的清净本心。在他看来,慎独就是“慎之云者。非是强制之谓,只是兢业保护此灵窍,还他本来清净而已,在明觉所谓明觉自然,慎独即是廓然顺应之学”。这与王阳明所讲的知是知非的良知又有不同。对于王畿来说,独知主要是指清净的本心,而慎独就是保有这个清净心,使内心经常保持为空中鸟迹的状态。
明代儒学大师刘宗周认为“意”在心理结构中有所作用,因此格外重视诚意、慎独的功夫,尤其认为“慎独”是“学”的根本功夫:“而端倪在好恶之地,性光呈露,善必好、恶比恶,彼此两关,乃呈至善,故谓之如好好色、如恶恶臭。此时浑然天体用事,不着人力丝毫,于此寻个下手功夫,唯有慎之一法,乃得还他本位,曰独。”[7]151这个端倪指的就是好善恶恶。“独之外,别无本体,慎独之外,别无功夫”[8]1533,既然意是好善恶恶的意向,那么诚意便是保持此意向不受影响。“大学之道,一言以蔽之,曰慎独而已矣。”[8]1588可以说,“慎独”作为一种功夫是学习的前提。做好“慎独”这一功夫,才能由此及他做好别的事。
从以上论述可知,不管从哪几个方面来讲,慎独都与内心活动相关。保持住本心,做好这一功夫,才会在学业上更为精进。
四、“慎”与“一”的关系
郭店楚简《五行》篇里提到:“‘鸤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能为一,然后能为君子,君子慎其独也”[9]。前四句其实来源于《诗经》,引《诗经》里的话目的是引出后面的“一”。这里的“能为一”又为“专注”之义。因此,思想保持专注在这里与“慎独”同义。根据《五行》篇后续的表达,“一”和专注都是有具体指向的,而这个指向就是内心的德行。再根据《五行》篇文本分析,成为君子的条件便是“能为一”,而君子又被要求能慎其独,可以得知“能为一”在这里指代的就是慎独。
《五行》篇里描述的“仁义礼智圣”这五种“品行”说得上是“德之行”。因此,慎独既然是专注于内的“德之行”,那么“仁义礼智圣”作为“德之行”的代表显然是与独处和独居毫无关系的,从此处更可以证明郑玄及朱熹对于“慎独”的注解及定义是有偏差的。
“仁义礼智圣”这五理既不形于内,那便是具有外在性,“舍夫五而慎其心”便是舍弃这种外在的、表面的仁义礼智圣,重视发自内心的“德之行”。只有从内心出发的这“五理”“德之行”才能为“一”,最终达到“天人相合”的最高境界。梁涛认为:“慎独的真正含义,实际上强调的是内心的真诚。”[10]因为“慎独”的“独”与现代汉语的“独”表示的意义有所不同。它并不是现代汉语中“单独、独自、自己一个人”的含义,更多指向自己内心的修养、意志的方面的含义,换言之就是真实的自己,现代汉语的“独”不包括这一重含义。从这方面看,“慎独”等同于诚意,而诚意在思孟学派作品中的讲法是“慎一”,意为能保持外在行为与内心相互一致。因此,“独”就是“一”之义——是一致的意思。就像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五行篇》里提出的:“能为一然后能为君子,能为者,言能以多为一;以多为一者,言能以夫五为一”[3]101。能做到“一”的才能被称为君子,做到了“一”就相当于拥有了“仁义礼智圣”这五种德之行。帛书《五行篇》与“君子慎其独”都是思孟学派的作品,因此表达的含义也颇为相似。所谓“君子慎其独”的表面含义,自然就是“在一个人的时候要谨慎小心”。而《大学》《中庸》和帛书《五行篇》里关于慎独的表达含义都是“诚其意”。从这个角度上看,“慎独”可以说不只是一个“人”的问题,也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空间”概念,更多指代的是内心的道德与修养。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慎独”不仅是一种专注于内的“德之行”,同时也涵盖了“闲居”之意。
既然是内在的德之行,那么也可以说内在就是指心。这里的“一”除了有数字含义外,还有三个方面的含义,分别是人前人后行为如一、内心之意与外在行为如一、恒常如一。这三个“如一”都包含在“诚其意”的概念里。因此也可以说,这三个“如一”具体指代的是“心”。从这方面来看,“慎独”也可以称作“慎心”,心只有时时刻刻保证在“慎”的状态下,才能人前人后、内心想法与外在行为保持一致。
人是有羞耻心的生物。正因人知善恶,才会掩饰其所不善。如果人不知善恶,或者没有区分善恶的能力,就不会加以掩饰,也就谈不上慎独的问题了。《中庸》注意到这个状况,将“慎独”释为应时时刻刻戒惧的警醒状态:“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1]20
五、“慎”与“诚”的关系
“慎”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在被提及的时候经常会与“诚”联系在一起。
在《中庸》第二十章讲道:“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1]32这意味着“诚”在中国古代的仁人志士心中占据了一定的分量。郭沫若在此处道:“这‘从容中道’的圣人,也就是‘圣人之于天道’的说明,是‘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的做人的极致。”[11]由此可见,“诚”并非外来之物,而是出自于人本身。天道的“诚”是人道的目标与准则,是命之性本身就具有的内容。诚不仅贯穿于显微、动静、体用之中,还无显微、动静、体用之别。因此,君子慎独也可以说是勿将体用、动静、显微相乖离,把这三者当作一个整体。对于天来说,“诚”是天然存在的;对人来说,“诚”意味着诚实不欺瞒的道德品行。所谓“诚意”实际上指代的就是慎独。《荀子·不苟篇》里提到:“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亲,不怒而威,夫此顺命,以慎其独者也。善之为道者,不诚则不独,不独则不形,不形则虽作于心,见于色,出于言,民犹若未从也,虽从必疑。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知矣,不诚则不能化万民。”[6]54由此可见,“化万物”“化万民”的基本前提是保持内心的诚。荀子既然提到“不诚则不独”,就意味着他认为做到慎独的前提是诚,说明慎独是诚的表现之一。这一段话与《帛书五行篇》的主旨内涵也较为接近。
《诗经·尔雅》中也提到了“慎,诚也”。[12]实际上,“慎”与“诚”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相同的意思,都指代的是内心的修养。换言之,既然“毋自欺”的前提就是要人前人后行为如一,那么可以说“诚”不可须臾离,也就是至诚无息,因此保持“恒常如一”才是“诚”。
诚不仅是人追求的最终目标,也是最高的道德准则。周敦颐特别重视诚,认为诚是“纯粹至善者也”,提出“诚者圣人之本”,又说:“圣,诚而已矣。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13]诚作为最高的道德原理,也必然是圣人所以为圣人的境界,更是成圣成贤的重要方式。诚要求“克己复礼”,正所谓“君子乾乾不息于诚,然必惩忿窒欲,迁善改过而后至”。诚作为圣人境界之一,表示纯粹至善;诚作为功夫之一,就是改正一切不善的行为以变成善。
六、结语
自古以来,“慎独”有多种解读,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讲,保持内心想法和外在行为一致都是其主要意义。理性地思考、慎重地决定固然重要,但那些不经过大脑思考的、天生的念头有时似乎不无道理。向善去恶、格物致知是古人带给现代人的勇气和理念。保持自己行为举止与在公共场所一样,是慎独的关键所在,保持内心的清明是慎独的前提,在保证前两点都能做到的情况下更能保证恒常如一,才能证明“慎一”之功夫修养到家。从修养方式来看,“慎独”“慎一”“诚”在成圣成贤上是接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