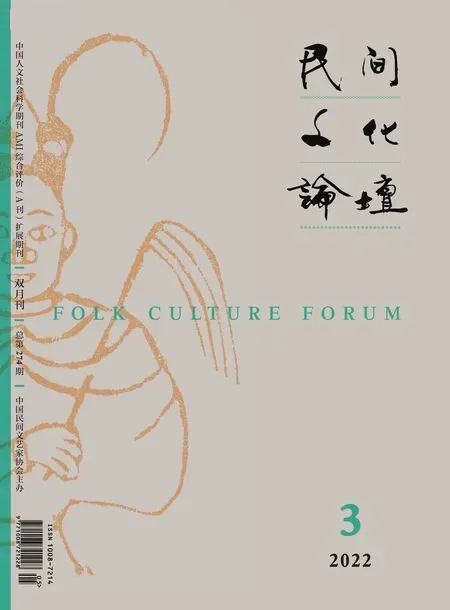民俗学的制度与礼俗研究谫论
王素珍
一、问题的缘起
一位在北京城边村调查的朋友聊天时谈到的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村里的支书非常困惑和发愁的事,就是如何将松散的村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因为他发现,现在的村民,谁也不服谁,谁也不听谁,一个个都似散兵游将,各自为阵,在关乎村庄公共利益的事务上,根本无法达成某种一致性想法,一致的行动就更别奢望了。而纯粹依靠行政命令式的管理,在很多细节上,根本行不通,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将某些个案置于整个社会,我们会发现一个共性的问题:社会如何有效地将个体组织起来?只有将个体组织起来,彼此之间结成各种社会文化网络,社会才能正常运行。村支书在村里生活工作了很多年,他对这个村落的感知无疑是最准确、最强烈的。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各种传统的社会文化网络不断遭到破坏,个体已经无法被村落或社区有效组织起来了。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已经非常明显:人与人的关系淡漠,人对社区的认同感缺失,个体和社区的安全感在下降,有限的历史记忆已经无法让个体产生足够的归属感,传统的公共社会(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正在或已经快速瓦解。现代行政体系显然没能将社区内的个体完全组织起来,许多个体仍然游离于社区组织之外。①“在急剧的变化中,台湾土著社会不论是深山里的或是平地上的,都已全部或局部地抛弃了规律的、保守的、稳定的与特殊的固有文化形式,而呈现出一种非常的失调、复杂与纷乱的现象……现代的社会科学家……需进一步探索一种更细微,更贴切、更活泼、包容更多的方法与观念,来处理这繁复多变的现代的社会,不管是原始的还是文明的。”参见乔健:《漂泊中的永恒——人类学田野调查笔记》,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第154页。学界为了应对由于制度变迁及道德伦理而引出的“制度创新”问题,采用了“制度伦理”概念,对制度进行价值评判与价值引导。
避开纷繁芜杂的社会文化现象,我们真正关心的核心问题是文化与秩序的关系问题。我们试图追问的是:大众日常生活秩序是如何形成的?或者说个体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社会是如何构成的?社会以何种形式将个体组织起来,并维持其正常运转?
二、制度如何思考——来自人类学的启示
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很早以来就是社会学、人类学关注的重要对象。法国社会学家,以涂尔干(Emile Durkheim)为代表的一派,较早关注人与社会的冲突,从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等层面去思考社会何以成为社会、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社会如何将个人组织起来”①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1893)、《自杀论》(1897)、《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围绕秩序和整合的主题,分别回答了“社会团结和整合如何实现”“社会整合与个人是什么关系”“团体意识对社会和个人起什么作用”这三个问题。列维·布留尔(Lvy-Bruhl Lucien)、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埃文思·普里查德(E. E. Evans -Pritchard)等学者从结构和制度层面来研究社会。。1910年,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发表了一篇题为“How is society possible?”的文章,即“社会何以可能?”或者说,“作为一个个体的、小写的‘人’,如何才能集结成一个社会的、大写的‘人’?”此后,“如何将分散开来的个人组织起来”一直成为包括社会学、人类学在内的多学科共同关注的问题。围绕如何将个体组织起来这一问题,学界对其做过各种尝试,比如讨论“社会如何记忆?”②[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法] 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制度如何思考?”③[英]玛丽·道格拉斯:《制度如何思考》,张晨曲译,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3年。学者们发现,社会将个人组织起来的形式多样,但透过诸多的社会现象,也许可以用“制度”“组织”来概括,正是这些制度或组织将个体组织起来,形成特定的社会秩序。
对于现代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来说,围绕制度展开的讨论,层出不穷,各方知识体系和基本问题意识不同,对制度的概念界定,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概括而言,在讨论“制度”的概念时,我们常常会从文化与社会两个不同的维度来加以考虑。
一般来说,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更注重“制度”的“社会”维度,多从制度的产生、构成、类型、功能、变迁的途径及其价值意义进行考察,关注制度在维持社会秩序中的功能。比如,经济学领域,亚当·斯密(Adam Smith)对制度的研究④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1759)、《国富论》(1776)中认为,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是制度。;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经济与社会》中将经济活动的各种要素纳入社会学制度分析的范畴⑤“一种制度应该称之为a)惯例,……b)法律……”参见[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64页。;以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C. North)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更是强调“制度”研究的重要性⑥[美]道格拉斯·诺思:《制度研究的三种方法》,载[美]大卫·柯兰德编著:《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寻租和DUP行动分析》,长春:长春出版社,2005年。道格拉斯·诺思与蓝斯·戴维斯(Lance Davis)于1971年出版了《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他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契约。制度是由非正式约束(道德约束、禁忌、习惯、传统和行为准则)和正式的法规(宪法、法令、产权)组成。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秩序和行为道德、伦理规范,其旨在约束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总体而言,20世纪50年代之前,经济学和社会学都绕不开“制度”这一议题。20世纪末,社会学与经济学学科关于制度分析的范式出现了合流的趋势。⑦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分析框架可以用来解释人类社会制度变迁的规律及其基本趋势,是一种整体的、长期的、历史的、动态的制度变迁观;而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上的新制度经济学对解释各种具体制度的选择及变迁有其特殊之处。在西方社会制度研究中,制度的自然历史形态有习俗(习惯)、道德和法律。制度是一种规则、一种习惯、一种组织、一种模式、一个系统。
在人类学、历史学等人文学科看来,制度更多被视为一种文化形式。早期人类学家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对“亲属制度”的研究①[美]摩尔根:《人类家庭的血亲和姻亲制度》(1871),《古代社会》(1877)。,深刻地影响了其后人类学家的相关讨论。拉德克里夫-布朗(Alfred Reginald Radcliffe-Brown)②拉德克利夫-布朗著有《亲属制度研究》(1941)、《原始社会的结构与功能》(1952)。他把迪尔凯姆的法国社会学引进了英国人类学领域,构建了一个富有活力的社会人类学框架;他把制度看作是保持一个社会秩序的关键要素,并且通过对社会功能的研究,分析了各种风俗习惯和制度是如何帮助一个社会保持稳定的。布朗认为,“制度就是用来指:一个已建立的制度、社会公认的规范体系或关于社会生活某些方面的行为模式。”、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③雷德菲尔德著有《尤卡坦的民间文化》《小社区》《农民社会和文化》等,他提出了大传统、小传统的概念。、雷蒙德·弗思(Raymond William Firthh)④雷蒙德·弗思在《人文类型》中认为,处于某种人类目的实现的需要而连接起来的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就是制度。我们所说的制度,是指一套社会关系,这套社会关系是由一群人为了要达到一个社会目的而共同活动所引起的。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基本制度的划分:性别差异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说,现有的社会习俗更多是在造成两性差别,而不是把差别表现出来),年龄等级制度(长幼有序制度化),乡土制度,家庭制度。制度变迁的主要领域:宗教领域、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参见王胜利、方旭东:《弗思社会人类学制度思想分析》,《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2期。、默多克(George P. Murdock)⑤默多克在《社会结构》中提出了“核心家庭”概念。、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⑥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著有《亲属的基本结构》。、利奇(Edmund Ronald Leach)⑦利奇著有《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对克钦社会结构的一项研究》一书。等纷纷从制度出发来研究社会结构。其中,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将文化划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即已经改造的环境(包括器物、房屋、工具、武器、设备、货品等)和已经变更扩展了的身体(包括知识、宗教、科学、道德、价值体系、风俗习惯、社会组织方式、语言等),并认为文化的真正单位是制度。⑧[英]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费孝通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2—5、92页。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人类学研究发生重大的转向,研究中心从欧洲逐渐转移至美国,这种转向同时还表现在研究对象、写作形式、研究方法、研究问题等诸多方面。传统人类学研究方法和研究单位是进行异文化民族志研究,将日常生活中的直接经验转换成文本或对其加以理论阐释。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个体与社会关系的思考与研究传统在西方人类学发展历程中亦未曾中断,即讨论在个人之上的社会是如何思考和运行的,特别是社会(制度)是如何作用于个人的。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及其著作《制度如何思考》在人类学学科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和意义。它既是对“制度”研究的很好延续,同时也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西方人类学思考问题及研究方式的重大转向。⑨2014年4月23日晚,中国人民大学科研楼人类学所会议室,来自美国加州伯克利分校的刘新应邀在此作系列讲座,这次讲的是玛丽·道格拉斯的《制度如何思考》一书。期间,刘新提到了西方人类学的学术转向问题。本文关于西方人类学学术转向及《制度如何思考》的部分观点及相关思考多源自此次讲座。显然,玛丽·道格拉斯《制度如何思考》一书中的“制度”概念已经融合了人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关于制度社会与文化分析的范式。其背后的问题意识是,传统人类学研究(包括辩论、案例和田野调查)已经很难解决理论问题,理论问题的解决需要寻找新的方向和道路。也就是说,道格拉斯想要回答的是:在当下生活(现代社会),人类学如何进行研究,人类学的发展是否存在另一种可能?因此,她提出将“制度”作为研究对象和研究理论建构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尝试回归涂尔干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来研究现代社会制度。
除此之外,玛丽·道格拉斯及其《制度如何思考》同样也反映了现代人类学研究和写作上的重大转向,充分表达了其所主张的人类学研究的新方向:
第一,写作形式上,从传统民族志转向以学术论文(集)、学术著作为主;写作风格上,从过去的讲故事到以问题为导向的理论思考、哲学思辨。
第二,研究对象上,从关注荒蛮的原始人转向关注当下的现代人;研究兴趣从过去的田野转向书斋(“图书馆里的人类学”),从传统文化转向当下社会问题。
第三,研究方法上,从过去的经验研究转向理论研究,认为田野(尤其是长期的田野)不再是人类学研究的必需,对人类学者能使用其他民族语言的要求也不再那么严格。因为新的人类学者认为,个案无法解释理论,只能在结构或理论层面来解释或获得理论上的突破。
第四,研究问题上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人类学者不再关心异民族、异文化(“野蛮人”“原始人”的文化),转而研究当下社会的问题。从过去讨论“人与人的关系”转而讨论“人与制度的关系”。
与此同时,现代人类学家也发现制度对社会、对个人的意义非常重大。比如事物或研究对象之间的相似性,并非通常我们所认为的事实本身具有相似性,而是因为相关制度安排导致相似的教育思考方法促使我们对事物的相似性认识。同样,关于分类和记忆,以及个人或社区的认同感问题,与社会中特定的制度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比如历史人类学家在关注区域文化多样性的同时,也在思考为什么多样性的文化被主动或被动整合成一个整体?为什么如此多样的东西,被统合到了一个整体中了?其背后的机制是什么?现代人文学者认为,不是个体或者个人的经验构成了整个社会,而恰恰是社会制度将个体组织起来,并形成一定的(大众)生活秩序。在中国,从本土实践出发,有学者提出,礼俗问题(或者说礼俗传统),是多元文化被统一到一个整体之中的关键性问题。①通过礼仪制度的设置,礼与俗就在很大程度上被紧密地结合起来,越来越密不可分……礼仪就扮演了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以“中国”的名义把各种各样的人群结合在了一起……所以我后来就提出一个概念,套用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概念,把中国概括成“礼仪中国”。参见赵世瑜:《“礼仪中国”:礼俗互动问题的历时性建构》,《“礼俗互动与近现代中国社会变迁”三人谈》,《民俗研究》,2016年第6期。也就是说,礼俗为我们民俗学提供了“制度”研究的可能性,关于礼俗与制度的讨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丰富和补充现有制度研究理论。
三、传统礼俗制度与当代民俗学研究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传统社会某些成熟的组织形式、文化体系、乡规民约、礼俗文化,或者说制度,是解决“个体如何有效地被社会组织起来”这一问题的很好路径。
那么,制度究竟是什么呢?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中的制度是否一样?传统礼俗与礼俗制度之间的关系如何呢?
在我国古代,很早便有了“制”“度”“制度”等词的使用。传统社会中的各种制度,既是文化和秩序的重要保障,也是理解个体与社会关系的关键所在。在传统语境中,“制度”通常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法令、法规、礼仪、道德等规范。比如《易·节》:“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孔颖达疏:“王者以制度为节,使用之有道,役之有时,则不伤财,不害民也。”①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70页。《书·周官》“又六年,王乃时巡,考制度于四岳。”②同上,第235页。《左传·襄公二十八年》:“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为之制度,使无迁也。”③同上,第2001页。《商君书·壹言》“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治法不可不慎也,国务不可不谨也,事本不可不抟也。制度时,则国俗可化,而民从制;治法明,则官无邪;国务壹,则民应用;事本抟,则民喜农而乐战。”④石磊注:《商君书·壹言》,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88页。《礼记·礼运》:“故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是谓制度……降于五祀之谓制度。”⑤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418页《汉书·元帝纪》:“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⑥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7页。《汉书·严安传》:“臣愿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贫富不相耀以和其心。”⑦同上,第2809页。史籍中使用“制度”一词,多用以指礼俗、规定、法令、依据等,泛指规范规则或实践模式。在我国古代,人们已将制度视为一种约束人行为的“规”“矩”,把“法令礼俗”作为制度的基本形态。
除史书记载之外,各类笔记散文、个人著述中,也多借用或沿用“制度”一词,泛指超越个体的社会规范或社会结构。比如唐代元结所撰《与何员外书》中记载:“昔年在山野,曾作愚巾凡裘,异于制度。”宋代王安石《取材》:“所谓诸生者,不独取训习句读而已,必也习典礼,明制度。”明代冯梦龙所撰《东周列国志》:“既至夹谷,齐景公先在,设立坛位,为土阶三层,制度简略。”清代吴伟业《遇南厢园叟感赋八十韵》:“改葬施金棺,手诏追褒扬,袈裟寄灵谷,制度由萧梁。”清代李渔《怜香伴·欢聚》:“你们只管掌灯随我老爷走,汉家自有制度。”这些相关记载,似乎都在提醒我们,关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及文化观念,不能忽视“制度”这一重要维度。
一般来说,我国古代对制度的使用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直接使用“制”“度”或“制度”等词汇来指“制度礼法”;一是以“法令”“礼俗”指称制度。在一定意义上,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结构可以概括为“礼俗社会”⑧费孝通《乡土中国》一书中沿用滕尼斯的观点,将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概括为“礼俗社会”。“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积累的经验。”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那是因为在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更大。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第70—72页。中国传统社会是“礼俗社会”,“礼俗互动”不仅存在于中国传统社会,现代地方社会生活中的“礼俗互动”依然保持活力,延续了礼俗传统。赵世瑜将其概括为“礼仪中国”。。礼俗传统不仅是乡村社会日常交往的秩序准则,也是民众应对现实生活的重要话语表达方式;同时,礼俗传统也成为乡村自治的重要机制、乡村社会运行的文化逻辑。“礼象征的是社会的文化规范,俗代表的是人的生物本性,中国古人对礼俗关系的认识和把握,其实是对于如何调解、处置文化规范与生物本性之间的矛盾,在历史的过程中做出的选择。”⑨杨志刚:《礼俗与中国文化》,《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3期。
中国的礼俗概念以及礼俗传统等问题历来被历史学、民俗学等学者所关注和讨论。有学者主张,“礼源于俗”,礼俗不分。他们认为,“礼”的概念及内涵是从“俗”脱胎而来,俗先于礼,礼本于俗,“礼”是对“俗”的某种发展,是对“俗”的规范化、制度化,是“文明”的标志。有学者认为,“礼”虽来自“俗”,但毕竟有别于“俗”,在其获得独立的内涵和意义之后,与“俗”之间更多的是互动。①可以说,礼与俗之间,既有张力,也有互动。参见彭林:《从俗到礼——中国上古文明的演进》,《寻根》,1998年第5期;张士闪:《礼俗互动与中国社会研究》,《民俗研究》,2016年第6期。“礼”“俗”有别,但在实际中,“礼”的实施与“俗”的存在并行不悖,即所谓“君子行礼,不求变俗”②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257页。。
总之,在中国,特别是“礼”这一术语被普及使用后,礼的内涵也被不断拓延,变得丰富而驳杂,“礼为之言理也,治身、治事、治国之道,有制而不可越者,皆得谓之礼。举凡治身之仪文,治事之纲纪,治国之制度,古人皆以礼统之。”③张舜徽:《四库提要叙讲疏·礼类叙》,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7页。其中,“治国之制度”无疑属于礼的范畴。
礼和俗连用,形成了“礼俗”这一新的概念与术语。“礼俗并称,始自《周官》”④柳诒徵:《中国礼俗史发凡》,见《柳诒徵说文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57页。,“六曰礼俗,以驭其民”⑤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646页。。“礼俗”的出现与“礼”“俗”的概念及内涵无疑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它不同于礼⑥关于礼的概念及内涵,学界讨论的焦点集中于“礼的起源”问题,但在中国古代,特别是“礼”这一术语被普及使用后,礼的内涵也被不断拓延、丰富。“礼为之言理也,治身、治事、治国之道,有制而不可越者,皆得谓之礼。举凡治身之仪文,治事之纲纪,治国之制度,古人皆以礼统之。”参见张舜徽:《四库提要叙讲疏·礼类叙》,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2年,第27页。,也有别于俗。“礼俗”这一术语在历史中,不断被丰富和诠释,演绎出颇具特色的礼俗传统。⑦“ 礼俗以驭其民者,其民所履唯礼俗之从也。”(王安石《周官新义》)关于“礼俗”,不仅有话语的传统建构,而且也有意蕴的现代发掘。参见张士闪:《礼俗互动与中国社会研究》,《民俗研究》,2016年第6期。“礼俗互动”不仅存在于中国传统社会,现代地方社会生活中的“礼俗互动”依然保持活力,延续了礼俗传统。⑧张士闪:《礼俗互动与中国社会研究》,《民俗研究》,2016年第6期。乡村社会的礼俗传统渗透到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乡村独具特色的民居样式,各地民居多就地取材,依势而建,既环保又宜居;此外也包括饮食习俗、劳作方式、人生礼仪等等,这些乡土文化、地方性知识的传承,是人们在乡村长期生存和生活过程中经验的总结和沉淀,彰现地方特色,充满情感,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当地民众真正的生活智慧。
在传统中国礼俗社会,制度与惯例、习俗以及儒家思想、道德伦理等均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些惯例、习俗、儒家思想和原则、道德伦理构成了礼俗社会中微观层面的“制度”。“儒家思想和原则化为了一套精细、系统且能够有效自我执行的微观社会制度”,“儒家思想是对农耕社会中已经发生并起作用的社会规范、实践和制度的一种累积的、比较系统的言词表达”。⑨苏力:《纲常、礼仪、称呼与秩序建构——追求对儒家的制度性理解》,《中国法学》,2007年第5期。
用“制度”概念和理论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礼俗社会,可以更清晰地认识和理解礼俗社会是如何将独立的个体有效地组织起来,并维持社会的良性运行。比如彝族的“伙头制”⑩2014年4月30日,文化部民间文艺发展中心李松在山东大学文化遗产学院举办讲座时,就文化与秩序问题,举了彝族“伙头制”的田野个案,本文部分借鉴了此次讲座的内容。另外,关于“伙头制”的具体内容,参考了陈永香的个案调查。参见陈永香:《彝族“伙头制”与宗教信仰——以云南永仁县中和乡直苴村调查为中心》,《宗教学研究》,2008年第3期。,是彝族传统村落基层的民间组织,具有古代民主选举的性质,对彝族村落的正常运行具有较强的规约性,并且与民间信仰关系密切。“伙头”及“伙头田”在公共事务和村落资本的运转上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①伙头的任职更多的是个人对群体的义务,被选上的伙头是不得拒绝任职的,他们主要是为群体服务。一般任期一年,这一年他们要为群体服务,遵守相应的禁忌,对个人的约束很多,对个体的好处并不多。这样的村落组织在彝族中有不同的称呼,但其为群体服务的目的基本一致。这与“制度与礼仪”有一致性,民间社会组织与民间礼俗二者似乎是交融在一起的,也可以说个体与群体的关系通过制度与礼俗进行调和和制约。这一观点是2020年陈永香在阅读此篇论文后与笔者探讨时补充,特此致谢!“伙头制”,普遍存在于彝语支的彝族、哈尼族、基诺族、普米族等民族中,其作为一种礼俗传统,有“自正自制”的制度功能。②一种风俗或礼俗一旦形成之后,逐渐成为大家都要遵守的“自正自制”的社会制度,就会在群体与民众中具有相当强大的规范力与约束力。所谓“自正自制”,就是自我遵守和自我约束。具体参见刘锡诚:《传承与传承人论》,《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在日本,村落社会中存在“契约讲”③从波传谷的社会组织结构来看,村中“契约讲”的存在备受关注。“契约讲”成立于1876年(明治九年),掌管着与村落祭祀、居民生计、村落运营等密切相关的大事。参见[日]政冈伸洋:《地震灾害民俗利用与受灾地的现状——以南三陆町户仓波传谷地区为例》,周丹译,《民间文化论坛》,2019年第5期。。作为一种传统社会组织,“契约讲”与“伙头制”有某些相似之处,比如对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的集体民主协商④“契约讲”的讲长、副讲长、会计合称“三役”,多由选举产生,比如波传谷原本预计在震灾后的第二天进行讲长换届的,但是由于要抗灾,很难选出新讲长。现任负责人,历代顾问为此多次在集会所里开会,反复协商,最终选定了现在的讲长。“契约讲”举行讲会,被称为“总会”的集会,一年召开三次,在集会之际有时会发生激烈的争论,与其称之为群众集会,不如看作是围绕着公共事业、地域资源利用等为核心的各个家庭的利益调节场。参见[日]政冈伸洋:《地震灾害民俗利用与受灾地的现状——以南三陆町户仓波传谷地区为例》,周丹译,《民间文化论坛》,2019年第5期。。礼俗社会诸如“伙头制”所依赖的信仰与伦理标准具有多元性和复合性,在强调人精神层面的追求和声誉的同时,允许多种可能发生,符合了个体的差异。更重要的是,其以礼俗制度形式将不同个体联系到了一起,将个体有效地组织起来,形成相对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换句话说,传统的某些礼俗组织方式或者说制度可以最大限度调动特定区域内个人的能量,包括文化认同与文化归属、文化自觉和行为自觉等。
将制度概念和研究引入中国传统礼俗社会,不仅有利于我们重新审视传统中国社会的风俗、习俗和礼仪,同样有利于我们解释和解决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与矛盾,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制度”创新与“制度”重构。礼俗制度不仅接续了传统社会,而且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基石;礼俗制度不仅是中国社会的重要文化制度,而且也是中国人处理自然与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是他们寻求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存之道。⑤刘晓春:《接续“自然之链”——在人类纪追问民俗学的“现代”》,《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因此,经由礼俗制度这一理论和方法,现代民俗学在研究传统礼俗和现代制度等多个维度和向度上的力度和效度都将会大有作为。
结 语
现代社会如何从传统礼俗中获得制度层面的某种生命力和创造力,从而达成社会对个人的有效组织?或者说,现代制度是否能从传统礼俗社会中的民俗、惯习、仪礼、儒家思想及道德伦理中获取其适应现代社会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实现社会对个人的有效组织?制度研究是一种理论还是一种方法?
西方学术界一般把结构主义视为“一种纯粹的方法学思潮”,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结构主义不是一种哲学理论,而是一种方法”。⑥苏力:《纲常、礼仪、称呼与秩序建构——追求对儒家的制度性理解》,《中国法学》,2007年第5期。民俗学的制度研究应该既是一种方法、一种理论,同时也是一种实践。从中国本土经验而言,民俗学的制度研究最突出的表现为整体研究的提出以及实践民俗学的践行①民俗学的整体研究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提出(刘锡诚:《整体研究要义》,《民间文学论坛》,1988年第1期),钟敬文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建立“民俗文化学”及后来提出的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主张,希望打破学科研究的隔阂,加强学者间的对话与交流,探索如何才能全面和整体地认知中国文化与社会的传统。21世纪,中国民俗学在田野研究、自身实践传统基础上,提出实践民俗学理论(如刘铁梁教授提出“村落劳作模式”“日常交流模式”“在关系中研究关系”等,2019年以来,高丙中、吕微、户晓辉、王杰文等学者均就实践民俗学提出了各自的观点),特别是对生活实践转向的关注(李向振:《重回叙事传统:当代民俗研究的生活实践转向》,《民俗研究》,2019年第1期)。。事实上,民俗学制度研究的朝向可以是多维度的。
首先,传统研究单位多以一定空间(如村落、社区)为主,制度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单位,那就是“制度”。以某种制度作为研究单位,从制度的起源、发展、变迁等视角,考察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对传统的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无疑是一种补充与创新。在积淀了丰富的田野作业经验的基础上,一部分中国民俗学者开始从研究民俗(事象)进而研究人特别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尤其是人们的生存经验、生活策略、忠告与智慧,在交流和实践层面上,尝试回答个人与制度的关系问题。从个体或制度内部出发,来考察和反思某种制度的形成及其发生作用的机制,不仅可以解决个案研究在普适性上的局限,同时也将提升研究效能,赢得整体和结构层面的多维度理解以及多学科的对话空间。②如杨念群的《再造“病人”》一书就从地方个案和普通个体的故事中对我国现代医学知识制度以及医疗制度进行了制度层面的剖析和反思。(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其次,制度如何从传统礼俗中获取价值和意义?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也可以从另一角度来思考,即“如何将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的生存策略、生活智慧转化或引导,使之形成制度”。在制度研究中,我们关注个人、关心个人的情感、关注个体的生存与生活,更重要的是,在背后我们有“制度”层面的关怀与思考。比如说,在华北地区很多村镇都有民间庙会、宗族祭祀、节日演剧、婚丧嫁娶等仪式活动,这些仪式活动影响着广大村民、市民的生活节奏与文化认同。如何认识和研究这些仪式活动以及参与其中的村民、市民个体?如果将其看作是传统礼俗,在地化的礼乐制度,我们就会发现,正是礼乐制度规范下的多样性的仪式活动,构成了具有政治象征的文化场域,以其强大的惯性和感染力,影响着广大村民、市民的生活节奏和文化认同感,有力地维系了由国家统一管辖下的地方社会的生活秩序。③“在当今的中国社会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传统礼乐制度的影响。除了传统的节日、宗族和庙会等祭祀活动还顽强地保留在乡村,我们也会看到传统礼俗的精神以及一些组织形式,也渗入到今天的城市生活当中。”(刘铁梁:《礼俗互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政治文化运作》,《“礼俗互动与近现代中国社会变迁”三人谈》,《民俗研究》,2016年第6期)个体不仅是单个的、独立的,也是家庭、社区、群体、民族、时代中的个体,单个的民俗事象,不仅具有其独立性,也与其他民俗事象有着关系,将单个的、鲜活的个体或民俗事象纳入历史的、结构的“制度”体系中,如此,我们既可以避开经验研究容易出现的“资料的碎片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又可以避免理论研究中将丰富世界结构化。
此外,实践民俗学、新的民俗(族)志④如刘铁梁的《“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文化巨变时代的新式民俗志——〈中国民俗文化志〉总序》(《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个人叙事与交流式民俗志:关于实践民俗学的一些思考》(《民俗研究》,2019年第1期),王晓葵的《灾害民俗志:灾害研究的民俗学视角与方法》(《民间文化论坛》,2019年第5期),孙艳艳的《修行中的‘身体感’:感官民族志的书写实验——以豫东地区S念佛堂的田野考察为中心》(《民间文化论坛》,2020年第4期)。书写将成为制度研究的主要呈现形式。作为经典研究范式的民族志与民俗志,21世纪以来在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对话中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在民俗学界,随着田野调查的普遍开展,民俗志的书写成为核心话题,新的民俗志书写是近年来民俗学研究的重要趋势。从早期的“村落民俗志”到“标志性统领式民俗志”“交流式民俗志”的倡导,以及如灾害民俗志、身体民俗志、网络民俗志、实践民俗学等专题或主题民俗志的兴起,民俗志的书写越来越朝着多样化发展。新的民俗志书写将从单纯的人或事象的描述转而对人与人、人与制度关系的叙述。在关注民俗(制度)主体人的同时,关注民俗作为制度,自身的话语权及其独特性。因为有了对“制度”的关注与思索,新的民俗志不仅有对经验、感性资料的描述,对细节和情感的强调,同时,它将这些资料、细节与情感置于一定社会文化、社会问题、社会制度的体系中加以处理和思考。新的民俗志调查与书写,正是带着这种特殊的学术使命,为当前和未来社会的和谐发展,搭建各种主体文化之间有效对话的平台,在制度层面上关注个人的意愿和诉求,以及群体间的对话与合作。
可以说,制度与礼俗研究,特别是民俗学学科的制度研究,已经引起了现代民俗学者的重视,相关的探讨和研究已经起步,而且这些尝试和探索将有益于我们不断开拓现代民俗学研究的面向。相信不久的将来,对于制度及制度性文化的讨论能够引起学者们越来越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