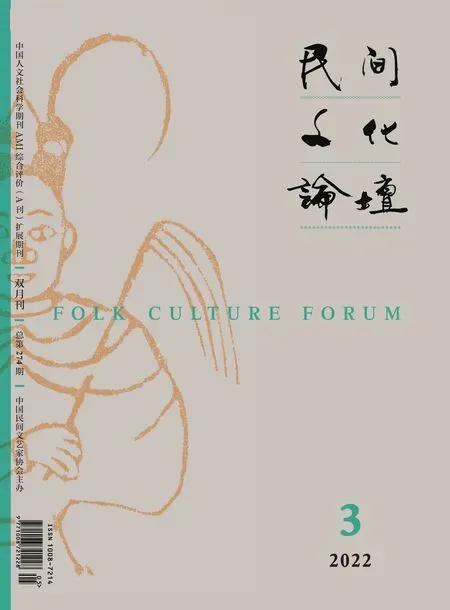文化空间视野下西南少数民族歌场的整体性传承与保护
杨 晖 黄龙光
引 言
中国西南边陲自古就是一块民族文化富集地,西南少数民族指“包括云南、四川、西藏、贵州、广西等省(区),以及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在内的这片广袤土地上,一直生息繁衍着的三十多个少数民族,她们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文化圈”①李子贤:《多元文化与民族文学——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页。。这些民族包括藏、羌、纳西、彝、哈尼、傈僳、拉祜、普米、白、基诺、土家、壮、布依、侗、瑶、傣、佤、水、景颇、仫佬、阿昌、怒、德昂、京、布朗、毛南、仡佬、独龙、门巴、珞巴,以及回、蒙古等。西南各民族不仅创造了各自古老而独特的民族文化,而且通过历史上的民族交往,形成极具凝聚力的活态地域民俗——歌场。因各民族语言存在差异,故歌场称谓不一。彝族称“打歌”“三月会”,壮族叫“歌圩”,侗族叫“坐妹”,苗族称“游方”“踩花山”,瑶族叫“歌堂”,傣族叫“赶摆”“花街”,等等。歌场不仅蕴藏着各民族历史记忆,承载着文化传统,而且通过精彩的文艺展演和活跃的物资交流,实现了族际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社会互动。西南少数民族歌场,在地理空间分布上大多处于交通枢纽位置,具体歌场的文化实践往往都是由区域性多民族交流共享的。一个个歌场犹如一枚枚珍珠镶嵌于西南地域空间的珠链上,其互嵌性节期贯通了地域共同体的经济社会联动,使歌场具有一种区域性文化空间的整体属性,在歌场结构、功能、组织和文化实践等方面呈现出一种普遍规律。
目前有关西南少数民族歌场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安学斌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视角聚焦云南大理巍山彝族打歌,就彝族打歌传承人出现断层、经费保障不力等现存困境,提出一种发展性保护思路。①安学斌:《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以云南巍山彝族打歌为例》,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213—214页。邵媛媛提出以“文化空间”整体保护和开发大理巍山彝族打歌,就地实现打歌“舞台”化,从而在新的文化环境下获得内在可持续发展的观点。②邵媛媛:《“文化空间”视角下彝族“打歌”保护与开发研究》,《民间文化论坛》,2012年第2期。范秀娟以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为调查对象,给予其价值论的正面肯定,认为其蕴含历史记忆,是城市生活的一部分。③范秀娟:《论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文化价值与功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张翠霞以一种整体性阐释视角,呈现了云南大理剑川石宝山歌会的多维表征。④张翠霞:《多维视野中的“歌”与“歌会”及其文化阐释——剑川石龙白族调与石宝山歌会的调查研究》,《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黄桂秋通过调查中越边境壮族歌圩文化濒危现状,提出了建立歌圩协会基地、歌手培训、民歌竞技、学术研究等文化重建路径。⑤黄桂秋:《中越边境壮族歌圩文化的恢复和重建》,《广西民族研究》,2016年第5期。彭正波等以广西歌圩协会发展历程为观察对象,探讨了民间组织参与民族文化传承的模式,提出积极引导民间组织,加强民间组织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的策略。⑥彭正波、马莎莎:《治理视角下民间组织参与民族文化传承的行动路径——以广西歌圩协会为例》,《广西民族研究》,2016年第5期。王云芳等通过调查广西武鸣壮族歌圩现代变迁问题,提出了强化作为公共文化空间的传承场域的民族性、历史性、社会性与民间性功能的观点。⑦王云芳、黎橙橙:《公共文化空间下民族文化传承场域功能变迁的思考——以广西武鸣壮族歌圩为例》,《贵州民族研究》,2017年第21期。平峰以广西田阳敢壮山歌圩为例,呈现了歌圩转型与重构的过程,总结了官方、民间、学界、商界、媒界等多主体介入文化实践模式的规律,提出重建文化主体性,培养传承人,建构新式歌圩文化生态的保护思路。⑧平峰:《壮族歌圩的转型与重构——以广西田阳敢壮山歌圩为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25—326页。陆晓芹认为壮族歌圩的整体性保护,应包括对歌传统、母语环境与民间节日传统。⑨陆晓芹:《论壮族歌圩的整体性保护》,《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这些代表性研究成果,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相关研究基础。
综上,西南少数民族歌场研究成果主要呈现以下三个特点:第一,大多数成果几乎都以社会变迁为调查主线,表达了对少数民族歌场生存现状与传承困境的一种文化忧思。第二,大多数研究基于某一具体歌场进行个案研究,未能摆脱以地方边界、民族属性“画地为牢”孤立研究的影响,缺乏一种基于关系主义的区域性整体研究视角。第三,大多数研究成果针对各自调查所发现的问题,开出了相关保护少数民族歌场的“方子”,这些思考既有出于文化保守主义的“回归乡野”的呼声,也有基于发展主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公共实践倡导。作为一种文化空间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西南少数民族歌场不仅是族际互动和地域认同的文化符号,更是当代西南地区进一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宝贵文化资源,具有重要的传承和保护价值。西南少数民族歌场的现实生存境况,因政府、民间、学界、商界、媒界等多方主体的博弈共谋,通过一系列非物质文化遗产化相关实践,使歌场进入一种由行政主导、多主体协作的传承与保护新模式,这与传统意义上内生驱动型歌场文化传承模式截然不同。当前西南民族地区市场化、商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少数民族歌场的公共实践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诸如空间生产、文化移植、符号化、客体化以及过度商业化等不良倾向,西南少数民族歌场自身出现弱化和异化的趋势,亟需一种文化空间的视野来考察西南少数民族歌场的整体性传承与保护问题。
一、变迁中的西南少数民族歌场社会语境
历史上,西南少数民族社会语境相对静止,各民族社会交流面比较狭窄,民族民间文艺主要在于自娱自乐,歌场均为自发形成,歌场文化亦处于一种自然传承的状态。从广义的角度来看,歌场上各类生产性祭祀歌谣以及仪式展演,表达了各民族对生产祈丰的良好愿望。人们于春播前、秋收后在歌场举行祈丰神祭仪式、庆丰酬神歌舞展演,目的在于表达风调雨顺、人寿年丰的祈愿。春耕前在歌场(市)采买劳动工具、粮种等生产资料,秋收后将收成盈余拿来进行物资交流。歌场不仅是以文艺展演为核心的文化交流场,也是各民族物资交流的重要市场。同时,歌场也是促进青年男女交游、倚歌择偶的社会场。这类歌场歌舞展演的实际功能,在于促进广大青年男女身心成熟和性别气质养成,歌场是他们初成年时情爱启蒙和婚恋教育的重要时空。旧时苗族,“婚姻不用媒妁,彼此寨中男女互相窥阚,农隙去寨一二里吹笙引女业,隔地兀坐,长歌婉转更唱迭和,愈歌愈近,以一人为首,吹笙前导,众男女周旋起舞,谓之跳月。男女不相爱仍离去,如两情相合者,男女告父母以牛羊为聘而娶之。”①云南省编辑组:《云南方志民族民俗资料琐编》,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95页。因此,对每一个青年人来说,在歌场上以能歌善舞和能言会道为评判标准的综合才艺展示,是展现个人魅力和获取异性青睐的主要方式。为此,他们在赶场之前的日常生产生活闲暇,必须进行大量的重复练习和模拟预演,赶场之后伺机进行及时总结;以期来年大展风光,而歌舞文艺就在这个过程中被自然、自发、自愿地获得传承和发展。纵观传统歌场的传承,在物质生产与交换、社会交流与互动两大目的的推动下,不论男女老幼统统都被吸纳到歌场这个重要的社会-文化时空,民族民间相关祭仪、歌舞、口头论辩、服饰、饮食、物资交换等各类相关文化形态,以集中展演和整体呈现的方式获得综合实践,由此推动歌场文化的整体传承。
在传统意义上,西南少数民族传统歌场文化的群体传承,主要由家庭传承与社会传承来实现。在传统社会西南少数民族歌场文化的家庭传承,指上一代对下一代的一种身教和示范传承,这种面对面的传习更多是一种隐性传习,是一种民族文化基因的代际传递和间接流转,因为传统歌场的歌舞展演,除神祭、神娱部分外,大多数是情爱类世俗展演,平时在家宅空间以及血亲社会关系下是严厉禁止的。有时,父母在田间劳作间歇或就山野放牧时会给子女做一些指导。节会期间则是对青年男女歌舞展演和社会交往的一种现场观望式揣摩和体验式学习,这是一种有效的身教示范传习法,属于临场参与式观察和体验式学习。社会传承是一种典型的群体传承,主要基于现场代际间和同伴间的互动与互传。如果再细分,歌场文化群体传承的歌舞学习、训练和预演,主要由青年男女赶场前在平时民间婚丧节庆等各种小型即时性歌场上通过群体交往而实现的。待到固定歌场上进行集中展演时是重要的竞演和展示时间,既是大群体的展演和传承,更是小群体和个体的展示和展现,其中往往还带有一种竞技色彩。赶场后的群体交流、评价和总结,是进一步创新和发展歌舞艺术的有效方式。歌场前、中、后三个阶段所有的训练、展演和总结构成文化整体观视野下歌场的完整传承链。当然,在这个完整的群体传承过程及其主体实践中,还包括祭司、歌师、舞师、艺人核心展演群背后广大忠实的观众群,作为歌场主体一部分的他们是歌场全程关注者、参与者与歌舞技艺的评判者,同时全程参与物资贸易、社会交流等歌场其他相关活动。
当代西南少数民族歌场文化传承的社会语境立体而复杂,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蔓延,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过去那种自然封闭的传统生计和生活方式被打破了,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开放的快节奏生产生活模式。广大少数民族通过跨文化比较遭遇了不同程度的文化震撼,为了快速赶上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种文化自卑从而导致对自我文化传统的抛弃,同时也因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等因素快速将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化和资本化,因此包括歌场在内的很多民族文化传统经历着急剧的社会变迁,面临着相关改编、改造、售卖等异化、退化、消亡等危险。在社会转型的阈限阶段,西南少数民族歌场文化的家庭传承几近断代,群体性社会传承则因现代教育的全面发展面临传承断档的风险,现代应试教育背景下普适性知识的系统学习,与歌场文化在内的地方性知识的社会传习,存在一定程度的隔阂。大多数年轻人也不再需要以歌场时空来养成性别气质与结交异性,随着现代交通、通讯技术的日臻发达,歌场倚歌择偶的婚恋方式渐显滞后。就具体的歌舞展演来说,以各级经认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为核心的展演主体越来越趋于专业化,同时也越来越趋于半职业化、职业化。对于传承人而言,在歌场上的歌舞艺术展演既是一种法定的传承义务,也是一种瞄准社区内外自我发展的文化营销。当前文旅融合等现代性发展趋势,也极大地影响着西南少数民族歌场的空间生产及其保护。歌场原生自然空间格局被打破或被迁移,有的歌场已被转移并圈入公园进行门票制管理;很多歌场上的歌舞展演在一定程度上变为行政化安排或商业化采买。总之,西南少数民族歌场文化自然自发传承的原生状态已然改变,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如何传承与保护西南少数民族歌场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实问题。
二、传而播之:西南少数民族歌场文化整体性传承
当前,西南少数民族传统歌场处于一种立体而复杂的社会语境中,欲将其如文物般原封不动地进行场馆式传承显然不切合实际,这种文化保守主义的做法也不符合歌场持续发展的客观事实。有学者指出,在原真性凝固幻象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馆舍化”实践,往往容易沦为一种小众把持的馆舍产业。①岳永逸:《本真、活态与非遗的馆舍化——以表演艺术类为例》,《民族艺术》,2020年第6期。“不论何时何地,就民族文化传承的实践而言,均是文化主体居于文化主位实施的旨在使文化传统良性延续的一系列操弄和推动。”②黄龙光:《谁的非遗:非遗传承如何创新》,《中原文化研究》,2015年第4期。随着现代交通、通讯技术的日臻发达,民族文化的传承超越了传统意义上面对面传递的现场模式,同时产生了一种跨时空的横向播布。民族文化传播不等同于传承,但是文化传播具有传承的部分性质,空间的横向流动可以复归式促进民族文化价值的自我重估。西南少数民族歌场文化传承,主要指歌场文化在民族内部代际间从上至下地纵向流动和传递,对于民族成员来说大多数时候它是一种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文化心理浸润,这种文化浸润及其口传心授的现场传习,使民族文化基因自然植入民族个体和群体的血脉中代代相传。传播指文化于族际间在地域上的横向扩展和播布,它以一种开放式交流和共享而使歌场文化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之间实现流布,从长时段来看也是一种文化的广义传承,有时因重大的历史突变导致文化反而在起源地消失了,所谓“礼失求诸野”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因此,面对现代复杂而立体的社会语境,西南少数民族歌场文化的传承必须与传播结合起来,纵向横向相交,历时共时结合,二合一地推进歌场的整体性传承。
西南少数民族歌场是一个完整的文化空间,歌场的传承首先要求我们必须秉持文化整体观,才能开展相应的整体性传承实践。鉴于目前西南少数民族歌场很大程度上已被非物质文化遗产化,它们不论是以民间文学还是以民俗(节庆)类别进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都只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工作话语及其划分。虽然为了使传承更具有效性往往会以文学、歌舞或祭仪等为核心和首要内容优先和重点传承,但是少数民族神话史诗吟诵、神圣祭仪、歌舞展演、社会交流以及传统服饰、特色饮食连同自然空间,均作为完整歌场传承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每年农历六月二十一,来自黔西南和贵阳、安顺、黔南、六盘水等市州,以及云南、广西的布依、苗、彝、汉等民族都会不约而同汇集到三省通衢——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顶效镇查白村,对歌“浪哨”①浪哨:也译“囊绍”,布依族青年男女传统社交、娱乐、择偶习俗,也被称为“赶表”“打表”“领表”等。,吃汤锅,吃花糯饭等,共度查白歌节。②谢彬如:《中国节日志·查白歌节》,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年,第14页。事实上,在作为歌场文化主体的少数民族自身眼里,文学吟诵、神祭仪式、歌舞展演、社会交流、服饰饮食等也从来不是泾渭分明地呈演和孤立存在的,它们无一例外地紧紧围绕着歌场这个巨大的时空磁场,结构-功能地形构出一个完整的歌场文化体系并使之良性运转。面对传统家庭传承基本消失的困境,当前西南少数民族歌场文化的传承已更多地主要依靠社会群体传承。从一个更高的角度看,社会群体传承需要不断培养少数民族群体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在文化自觉意识前提下的群体传承,才是真正意义上群体内部文化的自我传承。具体而言,应重视发掘和扶持那些在民间社会享有声誉并极具号召力的民间歌师(仙)、舞师等民族民间文化精英为首的本土民间文艺队,正是这些作为民间文艺自组织的地方文艺社团往往成为歌场上歌舞文艺展演的核心群体,也正是他们在当地日常婚丧嫁娶、起屋建房等仪礼场合传承着歌舞文艺与道德礼仪等民族传统文化。他们肩负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使命,极富文艺展演热情和传承积极性,身怀能歌善舞、能拉会弹等民间技艺。针对目前歌场在某种程度上过于行政化和商业化的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发挥地方民间文艺社团的自组织功能,遵循“民间事民间办”的原则,还俗于民,把歌场重新还给民间,把歌场展演的话语权真正交还给它的文化主体,这样才能激发西南少数民族歌场内在的传承动力和生命活力。
学校是法定传道授业的制度化社会机构,学校教育也应成为西南少数民族歌场文化的重要传承方式之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校教育也跟不上,在某种程度上说甚至还没有社会教育做得好。”③王文章主编:《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第119页。歌场文化的学校教育传承包含对歌场文化内涵及其价值的宣传和教育,也包含文学吟诵、歌舞展演等歌场的核心技艺进入课堂内外得到传习,民间艺人、非遗传承人与学校的教育资源须能互通与共享,通过“非遗进校园”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火花,点燃在广大年轻学子心中而代代相传。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学校都适合开展歌场文化传承实践,对各级各类学校首先要进行分类,民族地区的职(中)中、职业院校、艺术类高校等可能更适合开展相关教育传承实践活动。
西南少数民族歌场文化的传播,包括本地传播、异地传播与新媒体传播等的综合性融媒体传播。对于西南少数民族歌场的文化主体——当地人来说,年度性歌场神祭仪式、歌舞展演以及社会交流等都是其自发的在地化生活传承,但对于游客等外来参与者来说是一种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异域体验与他性传播,神圣肃穆的祭仪、精彩纷呈的歌舞与友善互动的社会交流等一系列歌场的文化表征,均会给这些外来体验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并随着他们的不断移动实现跨时空的文化传播。歌场文化的异地传播,与本地展演式传播不同,主要指由地方政府或民间社团组织的赴外相关文化展演。目前,这种离开歌场原生自然社会环境的文化展演式异地传播有行政任务式、公益演出式与商业演出式三种不同的类型。因为离开了歌场真实的自然人文生境,以歌舞艺术展演为主要特色的此类舞台化、艺术化传播,它无论再怎么精彩精致只是歌场原生语境的构拟,以及对原生歌舞展演的复制和改编,它往往受制于主流消费者对民族文化、传统文化的现代审美需求。当然,此类展演式异地传播虽发生了一定的位移和变形,但它也能回过头来激发歌场主体对其传统文化价值的一种重新评估,从而唤醒和激发他们民族文化传播的主体意识和自觉意识。西南少数民族歌场文化的新媒体传播,基于当代以互联网为核心的全息数字技术,它既可以在本地也可以在异地组织实施。可供参考的各种新媒体平台,诸如旅游文化宣传册(碟)、文化网站、微信公众号、抖音短视频、快手等。其中,随着智能手机终端的普及及其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微信公众号、抖音自媒体文化传播因其带来的即时性、快捷性、互动性与高效性等特点,逐渐成为民族文化传播的新宠,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在虚拟的网络空间里得到一种发酵式传播,同时可以进行即时平台交流与互动,只要一机在手,只要网络覆盖,任何人即可参与、体验、讨论与评价西南少数民族歌场文化,有助于在一种更广阔的公共语境下重塑西南少数民族歌场的文化形象,提升其文化形象与文化价值认知度。
三、由静而动:西南少数民族歌场整体性保护
如果说西南少数民族歌场文化的传承,主要是一种内生性主位文化实践,那么,西南少数民族歌场的保护,更多地是一种外推式客位文化操弄。作为文化空间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西南少数民族歌场,组织实施其保护实践的多方主体包括各级政府、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与个人等。各级地方政府必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及相关地方文化保护条例下,认真履行辖区范围少数民族歌场的整体保护。当前,一方面西南少数民族歌场广大主体的主体意识还未完全被唤醒,另一方面他们的文化主体地位还未完全被赋予,带有较强行政动员力量的各级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自上而下的保护实践中有时可能造成全能式包办,从而导致歌场主体在某种程度上被客体化而悄然不觉,如果在歌场文化的传承保护以及开发利用中的过度行政介入超过其主导角色与限度,往往导致歌场民间自组织长期以来习惯于依赖官方,其原有自组织能力则出现弱化、退化甚至消亡,群体性传承与保护的核心力量逐渐消弭并瓦解,最后导致歌场被彻底异化。因此,各级行政力量应遵循“适度干预”的原则,还俗于民,在法规、政策、人才与经费等相关各方面给予充分保障,积极培育和扶持本地歌场民间核心文艺自组织,让歌场真正成为民族民间公共、公益的文化空间。在西南少数民族歌场的整体性保护上,民间和官方之间应该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官民协作①杨利慧:《官民协作:非遗保护的本土实践之路——以河北涉县女娲信仰的四百年保护历程为个案》,《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可以进一步提高歌场文化空间整体保护的效率和效用。
西南少数民族歌场的静态保护,主要依靠以学界为核心的含学术、文教、宣传系统的相关力量来组织实施。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艺术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专家对歌场文化的静态保护,主要有对作为文化空间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歌场的学术研究和遗产评估两方面。“中国尚缺乏尊重学术独立性的社会氛围和共识,在行政体系尚没有习惯倾听学者主张的当下,学问的自由和独立性常常会被权力裹挟和同化。”②周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与中国民俗学——“公共民俗学”在中国的可能性与危险性》,《思想战线》,2012年第6期。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专业知识的专家,必须在尊重社会良知和学术伦理的前提下,在文化整体观视野下对西南少数民族歌场进行全方位的独立调查和忠实记录,充分挖掘歌场的历史文化记忆,深入描写歌场的当代发展境遇,学理性提出立场鲜明的保护理念、建议和措施,最大程度地避免行政力量及其话语对研究及其结论的干扰和影响。同时,专家学者还要注意警惕自身潜在的学术霸权与话语暴力,避免学术话语对西南少数民族歌场保护的“一言堂”及其危害,要以一种平视的眼光与平权的意识展开对歌场的深入研究,充分尊重并给予文化主体文化阐释权,在话语转换和学术审思上尽可能做到将客观本真与学理逻辑相结合。学界对西南少数民族歌场的系列研究成果,不仅将是长时段内西南少数民族歌场文化的写定保存,而且是对歌场实施全方位保护的学术基础,更是当地通过旅游文化产业对其进行开发性保护的专业依据。
在西南少数民族歌场静态保护实施机构中,教育部门是一个重要的保护主体。目前西南地区很多中小学将当地民族民间歌舞艺术和课间操结合开展本土文化传承与教育,有的区域性高校创建了民族文化传习馆,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地方性知识纳入大学殿堂进行传承与保护③黄龙光:《民族文化传习馆:区域性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新模式》,《文化遗产》,2012年第1期。。但由于现行教育体制应试影响的客观存在,以及作为地方性知识的少数民族歌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边缘属性,总体上“非遗进校园”等一系列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保护实践仍有待完善。总体而言,“教育领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缺乏重视和价值认知,教育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脱节”④乔晓光:《活态文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页。。西南少数民族歌场文化的教育传承与保护,除了包括歌舞进校园等形式外,要进一步及时将学界对歌场研究的最新成果吸收进入相关学校校本教材建设、学科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同时辅以校园歌场文化艺术节、歌唱民俗与歌舞艺术展演组织等形式,培养潜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和保护者,鼓舞和激励广大民间歌场主体的自我文化价值重估,使他们重建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自豪感,从而在少数民族民间社会重建主位式内生保护意识与保护机制。
与学界静态保护有所不同,西南少数民族歌场的动态保护是一种实践型文化操作,它需要将保护的学术理念和专业措施落实到具体的遗产保护行动中来。当代西南少数民族歌场的社会语境与其传统语境截然不同,自然经济时代少数民族传统生计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相对封闭而静止的歌场传承时空早已被打破,在复杂而立体的内外社会语境交织下,如果再退守到自然、自发的状态来谈保护,不是基于一种凭空的保护立场,就是出于一种悬空的传统想象。由唐代讲经庙会发展而来的大理三月街,明代旅行家徐霞客曾写道“俱结棚为市,环错纷纭。基其北为马场,千骑交集,数人骑而驰于中,更队以觇高下焉。时男妇杂沓,交臂不辨,乃遍行场市”①徐弘祖:《徐霞客游记校注》(下),朱惠荣校注,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18—1020页。,至今已发展为文体经贸“同台唱戏”的公共文化空间,作为一个大型地方性节日盛会,也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当前普遍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化,不仅是各地方政府借非遗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逻辑起点,更是商业资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经济化的经营起点。西南少数民族歌场以其超越村落、民族边界的强大社会粘合力,以其绚丽多彩的歌舞艺术展演,正在不断地吸引着各方社会资本的强势介入。对西南少数民族歌场的开发性保护,不同于所谓保护性开发,开发首先是为了保护而不是为了商业获利,作为手段的开发的目的最终应该指向歌场文化空间的真正保护。西南少数民族歌场作为一个文化空间,开发性保护首先也必须基于其整体性原则,其次是相对的原真性原则,同时要充分考虑歌场文化主体的权益,赋予他们享有相对使用歌场文化资源的能力与权力,而不是像现在几乎完全由市场来决定,从而导致其被逐渐边缘化而最终被迫让渡其文化权益。不论是文化主体还是外来其他行政或商界保护主体,均必须无条件遵守遗产保护等相关法律法规,从自然地域到文化内涵各方面,消除一切可能对歌场的原生性与本真性带来损害和破坏的危机,充分保证歌场文化主体能够获得应有的文化惠益。
结 语
作为一种特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西南少数民族歌场不仅蕴藏着各民族古老的历史记忆,以或神圣或世俗的民间信仰及其祭祀仪式,以精彩纷呈的歌舞文艺展演,建构了区域性多民族文化交流与友善和合的社会互动,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与社会价值。“西南少数民族歌场作为一类典型的文化空间,从内部视角看,是西南少数民族有关自身历史记忆、族源叙事、天人关系、文化表征以及社会互动的文化-社会时空集群,从外部(关系)视角看,它是一个族际互动共生的小型超社会体系。”②杨晖、黄龙光:《文化空间视野下西南少数民族歌场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在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复杂而立体的当代社会变迁语境下,西南少数民族歌场文化的传承与保护,要在人类学文化空间的视野下,充分考虑歌场物理属性、文化属性与社会属性三性合一的整体结构特征,充分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化的正面价值,全面激活歌场背后广大主体的文化自觉意识,真正赋予他们享有传承与保护歌场文化资源的权益,还俗于民。各级政府以行政主导做好顶层设计并优化保障机制,鼓励和委托当地核心民间文艺自组织实施民间群体传承,内外结合,传而播之,带动西南少数民族歌场文化的整体性传承。在无条件遵守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前提下,作为西南少数民族歌场保护主体的各级地方政府、学界和商界,均必须在具体的遗产保护实践中明晰各自的角色和承担的分工,到位而不缺位,通力合作,由静而动,避免过度行政化与过度商业化,正视文化干预中的客体化问题并将其影响降到最低,实现西南少数民族歌场的整体性保护,为进一步推进西南地区民族团结进步以及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不断的文化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