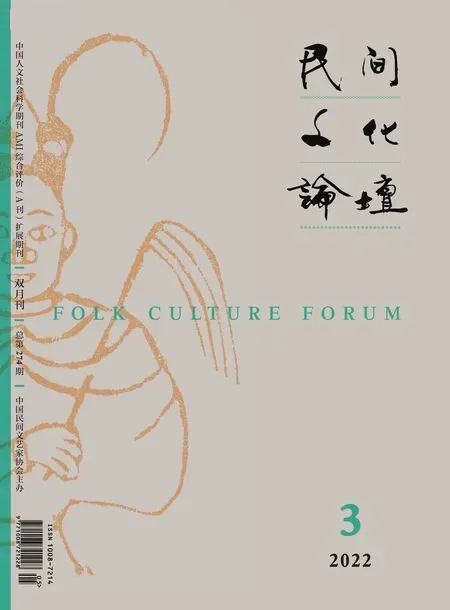共时研究解题指南
—— 评《故事法则》
朱家钰
共时研究由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在探究语言价值系统时,索绪尔发现价值关系只存在于同一时期共存的语言单位之间,不同时期的语言单位之间只有演进关系。由此,他将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对象分为“历时态”与“共时态”两种。共时研究就是对系统内部“共时态”存在的诸要素的功能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民间文学领域的故事形态学①故事形态学的本质就是一种民间文学的共时研究,这两个术语在表述上各有侧重,形态学强调以故事的形态特征做为观察切入点,民间文学的共时研究是对研究方法和思想原则的强调,即剔除时间因素,将研究对象视为静止、封闭的自组织系统。除必要处,本文对这两种表述方式不做严格区分,统称为“共时研究”。就是一种共时研究,其开创者为俄国学者普罗普。
故事形态学理论被推介至中国后,引起了一批学者的关注,在以历时研究为主的民间文学领域,另辟了一条新的研究路径。有学者对比这两种研究方法,指出历时研究只抓住了偶然的、个别的关联,而共时研究才是对更稳定和更本质关系的把握。②施爱东:《民间文学的形态研究与共时研究——以刘魁立〈民间叙事的生命树〉为例》,《民族文学研究》,2006年第1期。另有学者认为共时研究加深了对故事叙事机制的认知,从而能够回归故事学的本位研究。③漆凌云:《立足本体:故事研究向叙事本位的回归》,《民族艺术》,2020年第6期。
《故事法则》④施爱东:《故事法则》,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下文引用本书内容仅随文标注页码。就是施爱东在共时研究躬耕多年的成果。该书对民间文学共时研究的理论来源、前提预设、操作方法、研究目的等理论范式进行了详细梳理,在此基础上进行个案研究,提供了一批可供模仿的研究范例。从这个意义上说,《故事法则》是一本具有双重范式价值的论著。
一、共时研究的充要条件:边界意识
悬置时间因素是共时研究的首要条件,在此基础上,需要将研究对象视为“一个静态的、封闭的、不受外部影响的自组织系统”。(第2页)基于自组织系统内部,各要素按照特定游戏规则,自动形成有序结构的运行机制,共时研究就是对系统的内部结构、各要素功能及其相互关系,以及系统运行规则的考察。形态学研究则是将可观测、可描述、可识别的形式特征做为系统的结构要素,对形态要素的功能展开研究,以解释系统的运作规则、建立秩序为最终旨归。对于故事学的共时研究而言,这个系统就是由不同故事文本组成的研究样本。
不同于历时研究为追溯事物的演进过程,需要竭泽而渔式的网罗资料,共时研究必须严格限定材料的边界。有限材料组成的封闭系统,更易于我们观测系统内部的运作机制,得出规律性认识。因此,在共时研究中,“当更多素材的进入已经不再影响模型结构的时候,我们就认为素材已经基本充足”。(第23页)《故事法则》的每个研究个案均建立在有明确边界的系统之上,当然系统的大小以及内部的要素成分,可以根据研究目的,灵活调整。
明确材料边界之后,我们需要对系统内部的组成要素进行分类,正如施爱东所说:“‘分类’及其标准,在共时研究中,或者说在系统研究中处于一个最基础、最重要的位置”。(第20页)分类的标准决定了我们的分类结果,不同的分类结果会得出不同的规律性认识,从而产生不同的理论。反过来说,每一种理论只是认识世界的一个主观视角,因此也对应了一种不同的分类方式。他反复提及,杂糅多种方法的“综合研究”是不存在的。所以,当我们选择采用共时研究的方法分析民间文学作品时,历时因素和文化因素,甚至同属共时研究的其他理论体系,都必须被排除在外,如此才能确保“分类标准和分析逻辑的一致性”。(第22页)在个案研究中,他严守理论一致的原则,即便选取不同历史时期的文本资料,也会强调“把采自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各种梁祝传说视为均质文化平台上的‘故事集合’来展开讨论”(第108页)。
当我们限定了研究系统,并对系统中诸要素进行类型划分后,或许会发现许多值得深究的问题,此时我们很容易树立起攻克所有难题的雄心,试图呈现一篇全面周到的学术研究,在施爱东看来,这是完全不可取的。所有研究只能围绕中心论题展开,一切与此无关的问题,哪怕十分有趣,也必须抛弃,否则我们不仅难以找出规律性的认识,也会让研究变得极其混乱。所以,排除个例、小概率事件、低频个案是他在研究中常用的策略。
当明晰了取材边界、理论边界以及研究思路边界后,我们的研究才能成为解决特定问题的有效研究。正是基于明确的边界意识,此书作者归纳出诸多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故事法则”。
二、共时研究的旨归:无穷变异的有限规则
流传于民众口耳之间的民间文学具有变异性特质,每一次故事讲述都是独一无二的,都会生产一个新的故事文本,因此民间故事总是处于流变之中。刘魁立将28则“狗耕田”型故事的情节抽象为线段,合并指代相同情节的线段,得到了民间叙事的“生命树”。生命树的借喻象征了民间故事的丰富性、复杂性以及规律性,同时也是对民间叙事生命力和神秘性的赞叹。①刘魁立,[日]稻田浩二:《〈民间叙事的生命树〉及有关学术通信》,《民俗研究》,2001年第2期。事实上,生命树也暗含了民间故事无限变异中的另外两个特征:“自我生长、自我运行”(第7页)与“有序的自然结构”(第107-108页),这也是作者在《故事法则》中探寻故事系统运行规则的两个维度,即故事的生成规则和变化规则。
(一)故事的生成规则
封闭时空内,按照特定规则运行的虚拟语言游戏是施爱东对于故事的定义,同时也是他的立论原点。封闭的时空内包含封闭的角色关系、功能项和道具;同时故事情节也必须逻辑自洽,闭合完满;故事的自适性特征,使其能够汲取外部信息,自我优化与改良。如此,一个封闭的故事世界为故事的生成(语言游戏的运行)提供了基础场域。
既定规则决定了故事情节(语言游戏)的运行方向,也决定了故事的结构特征。作为民众共享的精神文化产物,故事必须建立在民众原有共识的基础之上,如此才能得到普罗大众的理解和认同,这类无需加以强调的默会知识属于故事的“通则”。与之相对的是只在单则故事中限制人物行为和事态发展的“特则”,这类规则由故事中的超自然力量、其他角色或者故事讲述者自行设定。
从故事情节发展来看,民间故事的情节大都由人物状态或事态的转折构成,巧合、误解以及不按常理出牌的搅局者都会促成故事情节的转折。但是,更为精妙的转折往往由故事中的规则推动,作者将这类规则称为“驱动设置”,其中“核心驱动设置”又是促使故事关键性转折得以成立的规则。大多数情况下,故事中的转折就是出现在主人公现有状态和既定目标之间的“障碍”,而“障碍”的设置又必须同时包括“系铃方案”和“解铃方案”两个方面,这就意味着主人公遭遇的所有难题都能得到巧妙化解,故事最终会以实现婚姻、家庭、财富和地位等世俗欲望的大团圆结局收尾。大团圆结局是民间故事既定的、不可更改的元结局,也是故事游戏运行的终极目标。当基础场域、运行规则以及目标指向均已具备,语言游戏便可自动运行,故事的生命树也可以自发生长。
(二)故事的变化规则
在自然界中,树木的生长要符合自然规律;同理,在故事学的生命树上,在由海量异文组成的枝桠与分叉中,也存在一定的规律,这就是故事的变化规则。
为探寻故事变异过程的稳定因素与变异因素,施爱东将搜集所得的“孟姜女同题故事”视为一个系统,将这些故事的母题合并同类项,由此发现了同题故事中稳定存在的“节点”。节点是同题故事或者说同类型故事中母题的最大公约数,无论故事如何变化,节点总是不变的。当然,这也意味着“某个节点被篡改,就会发生连锁反应,可能引起故事逻辑结构的全盘崩溃,或者导致原有故事主题的全面消解”(第76页)。节点是故事变异过程中稳定性的保障,而节点之外,则是供讲述者充分发挥想象力的预留空间,故事变异的自由度也体现于此。
虽然节点与节点之间存在无穷多的可能性,每一处缺失都会被补接上新的母题,使生命树朝向最大限度的无序发展,但是,并不是所有异文都能平等地为大众接受。只有那些具备逻辑合理性、与传统知识和地方知识兼容、主人公能动性强、倾向于共识知识以及符合搭配惯性等竞择标准的故事文本,才能脱颖而出,得到最广泛的接受与传播,成为故事生命树的主流枝干。由此,作者发现,在梁祝故事中,对于搜集到的连接“英台投墓”与最终“大团圆”结局这两个节点的所有母题链而言,它们都是合理的存在,但是最优叙事策略却是有限的,同时也是相对固定、近乎先验的。“最优策略的外在形式就是故事的最优结构”(第132页),这也体现了民间故事趋于模式化的本质属性。
生成规则和变化规则破解了故事游戏的运行秩序之谜,解释了故事生命树的生长机制,同时也回应了共时研究的旨归,揭示了研究系统中各要素的功能,以及它们之间相互连接的普遍法则与规律。
三、共时研究的跨界
一种研究范式对应了一种世界观,同时也对应着一种观测方式和提问方式。掌握一种范式后,可以不断变更研究对象,从特定视角予以观测和提问,并给出既定范式下的解释。熟谙共时研究的施爱东,将自己的研究视野投射其他文学体裁,从民间文学的立场出发,为不同文学体裁提供了一个新的审读视角。
对于史诗的研究,他延续一贯的思路,排除演述情景的干扰,从文本入手,将不同演述人所演述的“同题史诗”视作一个系统,通过比对,析出了史诗的情节基干。情节基干只是演述人的基础文本,任何实际演述都会在情节基干的基础上增添更多的“叠加单元”。鉴于史诗可持续生产的机制,每一次演述中的叠加单元必须“既能满足情节基干所设定的系统内诸关系,又是一个自足的、闭合的子系统”。(第142页)这就意味着,叠加单元如果以“加法”起兴,那么结尾处必定要失去先前所得;若是以“减法”肇始,那么结尾处必定会补齐所有缺失。因此,无论涉及多少元素,无论如何运行,“在该单元结束时,一切必须回到该单元的初始状态。”(第143页)同时,他也在具有史诗叙事特征的古典小说中发现了叠加单元的成分。
叠加单元的本质就是对系统内部运行法则和生长规律的认识,是民间叙事文学可持续生长的结构机制,这一概念的提出也回答了围绕在史诗演述人身上的诸多谜题。如果说共时研究的方法运用于史诗和古典小说,只是发生在民间文学内部的方法论交流,那么,将其用于唐诗和武侠小说的分析,可以说是共时研究范式彻底的“出圈”与跨界。
对于唐诗的研究,施爱东借助大数据检索,提取关键字词,进行类型划分,由此发现唐代涉月诗篇大都离不开由“金”延伸出的五行意象;唐人想象出来月宫中包含的嫦娥、蟾蜍、玉兔、月桂、吴刚等要素,也都无法脱离五行金(西)与水(北)的特性。故而,他验证了“月宫特征是基于特定理论而建构的带有一定‘必然性’的产物”(第236页)这一假说。以关键词为基本单位,检索相关文献,结合历史背景加以分析,由此检验假说的研究路径①金观涛、刘青峰:《中国近现代观念起源研究和数据库方法》,《史学月刊》,2005年第5期。,也是将共时研究拓展至数字人文领域的一次尝试。
此外,施爱东还极具创见性的将金庸武侠小说与英雄史诗中的英雄母题、民间故事中的角色对照模式、古典小说中“杀嫂”情节的功能项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了其中以民间文学为基底的创作模式与套路,以及金庸对于民间文学要素的创造性继承。被继承的母题、结构模式与叙事套路成为新生武侠小说中的“保留剧目”,以确保作品能够契合读者的阅读经验,从而获得最大限度的接受。在此基础上,金庸采取增设节外生枝的趣味情节、以丰富的想象力扩充母题、在稳定模式的基础上改变外部环境变量、变化叙事时空顺序等策略,突破读者的阅读期待,营造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武侠世界。鉴于叙事文本的结构形态与文化深意之间的“互构关联”②康丽:《民间文艺学经典研究范式的当代适用性思考——以形态结构与文本观念研究为例》,《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作者进一步发现,叙事模式的继承映射出金庸潜意识中的传统文化根脉,而模式之外的各种变量则传达了金庸对于传统观念的深刻反思。
施爱东从民间文学的立场出发,跨界运用共时研究法,对不同文学体裁的“故事法则”加以剖析,发现了隐匿于通行文学作品中的民间文学叙事套路。这些共通的叙事模式提示我们,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因“人类”这一共同体得以紧密联系,它们之中蕴含着一致的民众情感倾向与审美期待,这也是民间文学与其他文学体裁对话的基础,以结构精简见长的民间文学便于归纳出具有原型特征的文学形态与文化特质①施爱东:《民间文学的学“术”问题》,《西北民族研究》,2022年第1期。,这或可成为我们解读复杂故事的参照系。
余论:《故事法则》的双重范式意义
托马斯·库恩提到,范式具有两重不同的含义。一方面,它是学术共同体成员共有的信念与价值②[美]托马斯·库恩著:《科学革命的结构》(第四版),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47页。,为共同体成员提供了一种世界观,只有借助范式,共同体成员才能从特定的视角认识世界。《故事法则》厘清了民间文学共时研究的基本概念、操作规范与研究目的,使我们理解不同体裁文学作品的内部结构,以及要素组成、功能和运行机制成为可能,这也是《故事法则》具备的第一重范式意义。
另一方面,范式也是一种作为认知工具的范例。③陈俊:《库恩“范式”的本质及认识论意蕴》,《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年第11期。库恩将建立在既定范式基础上的常规科学比作解谜。对于刚刚踏足专业研究领域的学生而言,学会如何解谜是进入学术共同体的必要条件。学习解题的关键步骤并非掌握解谜的工具(理论),而是如何使用这些工具,库恩将之称为相似性的习得。④[美]托马斯·库恩著:《科学革命的结构》(第四版),金吾伦,胡新和译,第158—159页。这种能力的本质就是在谜题与理论之间建立联系,让具象的谜题与抽象的理论符号、概念一一对应,进而利用理论工具,获得答案。习得相似性的方法之一,就是模仿科学共同体成员已经解答的谜题,即“范例”。在不断的模仿中,学生才能逐渐掌握如何在纷繁复杂的谜题中,确定、观测并提取用于研究的要素,如何在经验要素与抽象理论之间的建立关联,进而掌握与共同体成员相同的学术眼光,学会从特定视角观察和认识世界。
从这个角度来看,《故事法则》为我们提供了一批可供模仿的解题范例。我们可以把谜题替换成《白蛇传》《牛郎织女》等不同的民间故事,甚至还可以替换成其他的通俗文学作品,或是具有幻想故事特质的动画电影,效法范例的解题思路与操作步骤,破解不同故事系统在共时研究范式下的谜题。由此完成一项常规科学研究,扩展共时研究范式的适用范围,对于我们自身而言,也是一次习得相似性的解题过程,这也是《故事法则》的第二重范式意义。对于有志于故事学研究的后辈学人来说,该书无疑是一本具有实践价值的解题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