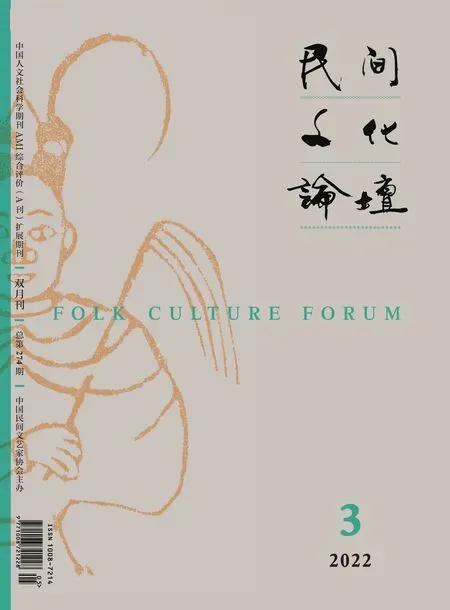作为常态口头交流实践方式的个人叙事
毛晓帅
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的一些语言学者、民俗学者、人类学者先后注意到个人性的口头叙事的重要性,并对其展开了研究。美国社会语言学家威廉·拉波夫(William Labov)较早关注个人经历的叙事。作为一名社会语言学家,拉波夫主张把语言放到社会中去研究,重视语言与社会的关系。他认为个人叙事是一种总结和重述个人经历的技巧,尤其是完成与自己经历事件的时间顺序相匹配的叙事单元的技巧。①Donald Braid,“Personal Narrative and Experiential Meaning,”The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1996(109).拉波夫对个人经历叙事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后美国民俗学界关于个人叙事的研究成果不断增多,许多民俗学者都参与到个人叙事的讨论和探究中。②例如约翰·鲁滨逊(John A.Robinson)、桑德拉·斯塔尔(Sandra K. D. Stahl)、加里·巴特勒(Gary R. Butler)、西德尼·利维(Sidney J. Levy)、唐纳德·布雷德(Donald Braid)、卡米拉·斯蒂弗斯(Camilla Stivers)、萨拉(Sara B. Kajder)、多尼林·罗斯科(Donileen R. Loseke)、艾米·舒曼(Amy Shuman)等学者都对个人叙事进行过理论探讨。真实的故事,与超自然有关的灵验叙事、寓言,当地逸闻、笑话、吹牛,家庭轶事等,日常交流实践中各种类型的以第一人称讲述的个人叙事被大量地发掘和分析。③Mirna VelČić,“Personal Narratives as a Research Method in Folklore,”Nar. UmJet. 1989(26).2014年日本学者门田岳久在《叙述自我——关于民俗学的“自反性”》一文中指出:“有必要将民俗学的研究方向转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在这个学科转向过程中,我们必须认识到访谈对象的自我叙述是最重要的研究素材。”④[日]门田岳久:《叙述自我——关于民俗学的“自反性”》,中村贵、程亮译,《文化遗产》,2017年第5期。受中国民俗学自身发展道路和学术传统的影响,中国民俗学界关于个人叙事的研究在时间上稍晚一些。近年来,刘铁梁⑤刘铁梁:《个人叙事与交流式民俗志——关于实践民俗学的一些思考》,《民俗研究》,2019年第1期。、林晓平、雷天来⑥林晓平、雷天来:《个人叙事与当代风水师身份建构——以赣南地区为例》,《民俗研究》,2014年第6期。、张成福⑦张成福:《个人叙事与传统建构——以即墨“田横祭海节”为例》,《青岛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毛晓帅⑧毛晓帅:《民俗学视野中的个人叙事与公共文化实践》,《民族文学研究》,2019年第3期;毛晓帅:《个人叙事选择与集体记忆建构——基于北京D村花钹会的田野调查》,《民间文化论坛》,2020年第5期。等人都对个人叙事进行了理论或个案探讨。
对于民俗学研究者来说,民众在日常交流实践中讲述的个人叙事是我们在田野作业过程中所获得的最多的一类口头资料。这里所说的个人叙事,大抵是指“以个人亲身经历的生活为内容的口头叙事,它与民间文学研究所长期关注的集体性口头叙事一样,都是人们在日常交流实践中所运用的话语,彼此之间构成一定的互文性关系。”①毛晓帅:《民俗学视野中的个人叙事与公共文化实践》,《民族文学研究》,2019年第3期。这些个人叙事材料虽然难以达到民间文学文类的艺术标准,却关乎当地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建构过程,即作为交流的手段与话题,使得人们不断获得生活的现实感与地方感,也使得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相互沟通。个人叙事也是我们理解所在地方社会民众的生活方式及秩序运转的重要依据。基于笔者近年来的田野调查经验,本文拟对个人叙事概念提出的背景、个人叙事的性质、个人叙事与集体叙事的关系、个人叙事的目的与类型进行探讨。
一、个人叙事概念提出的背景
中国民俗学关于个人叙事的研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直接受美国的影响而借用、照搬过来的一个概念,而是在对民俗志调查的反思和总结中,在“非遗”保护、口述史研究热潮等当下的社会环境影响下提出的。
(一)田野作业经验的总结
田野作业是民俗学研究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通过长期的观察,我们发现在田野作业过程中遇到最多的叙事材料并不是那些民众共享的民间文学,而是大量的与民众个人经历有关的个人故事。这其实也是人们在日常交流中最常态的经验。一个地方社会中,民众彼此之间交流关系的建立,并不是总是依靠那些共有的民间文学文本,也不是其他的艺术性的交流话语,而是通过大量的有着不同交流目的的个人叙事来完成的。在顺义、大兴等先行城市化地区,几乎每个访谈对象都会结合自己的个人经历谈自己近年来劳作模式、交往方式、文化认同的变化。讲述与个人经历相关的个人叙事,是乡民实现个体认同的重要途径。民众讲述的个人经历叙事,对于理解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生活环境的变化,理解他们的角色行动意义至关重要。离开个人叙事,我们就无法理解他们对自身文化传统的认识和感受。
(二)个人叙事与传承人口述史
提出个人叙事概念,也是基于我们对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史的反思。“非遗”传承人,就是某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者。我们对传承人的关注,更多的是从民间文化传承的意义上,关注传承人的担当和作为。本质上,我们关心的是某种文化形式能否得以延续。例如,高密剪纸会不会失传,杨柳青年画能不能得以延续等。因此,我们在记录传承人口述史的时候,往往只关心传承人的技艺,而对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多元的民俗角色和行动实践则缺乏关注。其实,传承人不完全是某种文化事象的文化承担意义上的角色,他们还是日常生活实践中的一个个行动角色。实际上二者有非常明显的差别:传承人,是文化传承意义上的,可被访问的一个对象;而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的行动角色是十分立体和多样的,他们是日常交流实践的行动主体。我们需要对民众在日常交流实践过程中的角色行动意义有更多的关注。民众讲述的个人叙事,对于理解他们的角色行动意义至关重要。我们要关心一个社会,或者日常生活中经常有互动的社区、村落,就必须关注当地民众的日常交流实践,关心民众的个人叙事。因为,在民众的日常交流实践中,民众的个人叙事对于整个社区或者群体的文化建构有一种特殊的参与作用。我们应该把访谈对象作为交流实践的主体,作为一个文化建构的行动者来看待,而不只是信息提供者。
(三)各类媒体、社交平台上个人叙事的大量出现
近年来,网络社交媒体的不断发展,为亿万普通人搭建了书写、展示个人经历的更广阔的空间和平台。于是,各类与个人经历及其感受有关的个人叙事大量涌现出来。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现实状况。
在网络媒体、社交平台还未普及的时候,普通人的个人经历叙事一般只是在自己所在的相对狭窄的社会空间中讲述和交流,听众也大多是区域社会中“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熟人。除了一些道德模范、先进个人等,普通人的个人叙事很难在区域社会之外的更广阔的空间中传播和扩布。而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的出现,为更多普通人提供了展示自我的机会,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在个人社交平台上书写自己的个人经历。许多个人叙事材料还被网友们纷纷转发,刷爆朋友圈的个人经历时常出现。有的个人叙事甚至成了全民讨论的热点话题。2016年11月25日一篇名为《罗一笑,你给我站住》的文章开始刷爆微信朋友圈,作者在这篇文章中书写了自己女儿患病的经历以及他对女儿的眷恋,表达了希望得到大家帮助的愿望。此后的一周时间内,这篇文章的转发和点击量超过一亿,几乎成了全国都在讨论的热点话题。目前,每天都有很多个人叙事在各类媒体、社交平台上出现,这是民俗学研究必须关注的一个社会现实。同时这种现象也说明,随着时代发展,民众已经有了在更广阔的时空中表达和分享个人经历叙事的实际需求。民俗学者应该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牢记以人民为中心的使命,关注民众需求的这种变化。
二、“公”与“私”:个人叙事的双重属性
从民众在日常交流实践中讲述和聆听的关系来看,个人叙事具有私人性,但这种私人性又恰好与其公共性联结在一起,这两种属性是辩证统一的。
首先,个人叙事具有私人性。神话、传说、故事等民间文学文类在地方社会中大多是集体性的,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所共享。每个人都有资格参与这些民间文学文类的讲述、建构与传播。而个人叙事的主要内容或者话题是关于讲述者的个人生活经历的,大多数个人叙事内容不能构成一个地方社会公共享用的叙事文本。个人叙事的讲述具有明显的资格性,只有事件的亲历者或者参与者才有资格讲述,叙事者不主动讲述,他人就难以了解这段个人经历。美国民俗学者艾米·舒曼曾经对个人叙事的“资格”与“移情”问题做过精彩的论述。①[美]艾米·舒曼:《个体叙事中的“资格”与“移情”》,赵洪娟译,《民俗研究》,2016年第1期。例如,2017年7月25日马家堡村的孙德才为笔者讲述了他儿时帮父母做饭的经历:
从七八岁我就开始帮父母做饭了。那时候我们家最常吃的就是贴饼子。家里的锅太大,做贴饼子的时候,我只能够到左边的一半,右边的够不着,我就搬个凳子,站在锅台上,再把右半边的饼子贴完。贴完饼子之后,我还得烧火。②访谈对象:孙德才;访谈人:毛晓帅;访谈时间:2017年7月25日;访谈地点:孙德才家中。
这段个人经历是孙德才独有的,这段个人叙事材料明显是私人性的。如果孙德才不主动讲述,我们就难以了解他的这段个人经历。
当然,在地方社会中,也有个别社会成员的个人经历叙事,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能够成为集体共享的叙事文本。例如,在我国集体化时期,乡村社会中会定期开展忆苦思甜活动,在这样的活动中,人们会主动分享个人的艰苦岁月经历。在忆苦思甜大会这样的公共场合,一些人的个人经历叙事会被地方社会中的其他成员所共享,进而传播,成为集体叙事。另外,在一些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宣讲会或者报告会上,这些人的个人生活经历也会在公共场域中被其他社会成员所分享、传播,成为集体共享的叙事文本。例如,丽江华坪女子高中校长张桂梅曾入选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被授予“七一勋章”。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感动中国十大人物颁奖典礼》节目中,张桂梅就通过电视荧屏讲述了如何帮助山区辍学女学生走出大山、回归校园的个人经历。张桂梅的这些个人经历通过电视荧屏、平面媒体等广泛传播,逐渐成为人所共知的集体叙事。以上这两种类型的个人叙事,在内容上虽然具有私人性,但在特殊的历史和社会环境中,讲述者能够通过公共的平台进行讲述,使之变成大家共享的公共知识和历史记忆。但总体来说,民众日常交流实践中的大多数个人叙事都是私人性的,有些甚至是私密性的。
其次,个人叙事又具有公共性,个人叙事是个人被其所在的社会、群体接纳为正式成员的重要条件。乡村不是每个人都会讲民间故事,但人人都是口头传统的实践者和运用者,日常交流实践的担当者。作为话语交流的实践者、交流实践中的一个角色,人们只有经过不断地交流,才能够被社会接纳为一个正式成员。美国学者约翰·鲁滨逊(John A. Robinson)在《个人叙事的再思考》一文中就曾指出,“讲述关于个人经历的故事是我们每天交谈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一个交流社区中的成员来说,这种叙事能力是必须具备的一项技巧。”①J.Robinson,“Personal Narratives Reconsidered,”The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Vol.94, N0.371(Jan.-Mar,1981).一个社会成员要被大家所认识、了解、认可、接受,是通过他日常生活中的话语交流实践来达成的,而不是仅仅通过成年礼等人生仪礼就能够实现的。在乡村社会中,村民之间的交流内容更多的是个人的见闻和经历,而不是民间故事、民间传说等知识文本。村民通过分享自己的个人经历和见闻来互通有无、增进了解。“我们生活在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如果我们不与他者进行交流,彼此之间就会有隔膜,社会距离难以拉近,最终无法融入社会。民众讲述和分享个人叙事的过程就是一种互通有无、增进了解、拉近距离、融入社会的过程。”②毛晓帅:《桑德拉·多尔比个人叙事研究述评》,《民族文学研究》,2021年第4期。
我们承认个人叙事的私人性,但是这种私人性恰好又是与公共性联系在一起的。一个人不能说具备了公共知识,掌握了集体共享的叙事文本就是一个公共社会中的成员了,他必须同时拥有个人的知识和叙事才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对于民俗学研究来说,我们不仅要关注和掌握那些民众共享的知识和叙事文本,同时也要关注每个人的个人叙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这个社会中的民众对于自己所处社会和历史的个性的感受和体验。我们对这些个人的了解同时也关连着对于其所在社会的了解。要了解一个村落或者社区,就必须了解村落社会或者社区中民众日常互动的话语交流关系和个人叙事。
三、交叉共融:日常交流实践中的“个人”与“集体”
个人叙事这一学术概念是与集体叙事相对而言的,事实上二者既有区别,又有着密切的联系。没有绝对的“个人”或者“集体”,个人叙事与集体叙事交叉、共融在民众的日常交流实践中。
中国民俗学界关于个人叙事与集体叙事关系问题的讨论,最早是由刘铁梁教授提出来的。2014年11月19日,他在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的研究生课堂上指出:“个人叙事与集体叙事这两种叙事类型具有不同的特征,其对于我们理解生活、感受生活也具有不同的意义和作用。”①2014年11月19日,刘铁梁在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研究生课堂上的讲话。2014年11月28日,在山东大学举办的“礼俗互动:历史学与民俗学的对话”学术研讨会上,他做了题为《地方社会发展中的个人叙事与集体叙事》的发言,进一步指出了个人叙事在社会发展中的意义和作用。个人叙事与集体叙事的关系问题是刘铁梁根据自己多年来田野调查的访谈经验提出来的,他敏锐地发现了当前的民间文学研究只注重集体叙事而忽视个人叙事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他是走在学界前列的,这个问题的提出也是比较合理的。但是归根结底,无论是个人叙事还是集体叙事,都离不开民众的日常交流实践。因此,我们还是要在日常交流实践的视角下,来讨论集体叙事与个人叙事的关系问题。
(一)互通有无与知识共享:个人叙事与集体叙事的分异
第一,从交流的目的和预期达成的交流效果来看,民众讲述个人叙事主要是为了彼此交换信息,互通有无,进而使交流双方增进了解、拉近距离;人们讲述集体叙事则大多是为了重温共有的知识和记忆、分享集体的情感,进而达到增强群体凝聚力、维系社会团结的效果。
第二,从交流的时间、场合以及交流内容的性质上讲,个人叙事主要是讲述者对自身生活经历及其感受的演说,具有一定的私人性,其讲述的时间、场合比较灵活,民众随时随地都可以讲述;集体叙事则大多是区域社会中的乡民人所共知的地方知识或者历史记忆,大多是公开的,人们讲述集体叙事的时间和场合相对比较固定,例如创世神话、英雄史诗等一般只在特定的仪式场合讲述。
第三,从交流的方式来看,民众在讲述个人叙事时大多采用第一人称的方式,其叙事内容往往体现着讲述者本人的身份、气质、性格、价值观等信息;集体叙事的讲述则不要求讲述者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叙事,其叙事内容一般隐含着地方社会整体的民俗风貌。
第四,从交流过程中叙事文本的艺术性和稳定性来说,个人叙事的内容在交流过程中相对比较自由多变,讲述者一般不会刻意追求艺术性,也不会形成固定的文本;而集体叙事的内容则逐渐趋于稳定,在地方社会中经过多次的讲述之后会形成一些固定的具有一定艺术性的文本模式。
第五,从交流内容的传播范围上讲,多数个人叙事只在家人、朋友、邻居等熟人之中传播,当然有时也会对一些外来者讲述,总体来说其传播的范围很小;而集体叙事作为一种公共知识、历史记忆会在地方社会甚至更大的区域社会中广泛传播,其传播范围要大得多。
(二)转化与交融:个人叙事与集体叙事的联系
第一,没有完全“个人”的个人叙事,也没有完全“集体”的集体叙事。首先,民众在讲述个人叙事的过程中,除了自身的生活经历之外,往往会结合使用一些集体共享的叙事要素或“表演资源”,例如当地的俗语、谚语、笑话等。其次,每个人的个人生活经历及其身份、个性本身就离不开其所在社会、文化的整体影响和形塑。最后,个人关于其生活经历的看法也会受到地方社会中集体共享的观念、思想等因素的影响。同理,集体叙事的讲述也不可能完全是“集体”的,每个人在讲述地方社会中共享的集体叙事时,其叙事内容、方式、风格都会体现自己的特点,不可避免地融入一些个人性的要素。因此,“个人叙事”与“集体叙事”是相对而言的,没有绝对的“个人”,也没有绝对的“集体”。
第二,一些个人叙事可以转化为集体叙事。例如上文中提到过的忆苦思甜大会上的个人回忆,当代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宣讲等。另外,在地方社会中,一些人为了特定的目的也会主动把个人生活经历的叙事努力变成集体共享的叙事。例如,我们在长期的田野作业过程中发现,一些村干部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就会把自己曾经为群众办的好事等个人经历在村落中对不同的村民反复讲述,久而久之这些个人叙事就会成为村民共享的集体叙事,他的个人威信也会随着个人叙事的不断讲述而逐渐树立起来。这样的例子在村落社会中还有很多。
第三,个人叙事与集体叙事都是民众日常交流实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对地方社会中故事、传说等民间文学意义上的集体叙事的理解,事实上恰好也是需要通过当地人给我们讲述个人叙事来实现的。只有深入了解当地人的个人叙事,我们才能理解他们是怎么样看待这些集体叙事的,进而更好地理解这些集体叙事的意义,理解地方社会。总之,个人叙事与集体叙事是我们根据当前民俗学忽视个人经历叙事重要性的研究现状而提出来的一对学术概念,一种分析工具,二者是相对而言的。事实上,个人叙事与集体叙事都是民众重要的交流方式,二者在民众的日常交流实践中是交叉、共融的。
四、“建构性的交流”:个人叙事的目的与类型
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交流实践首先是为了达成一定的交流目的。在民众日常的交流实践过程中,个人叙事往往也是具有目的性的。因此,我们应当按照交流实践的目的和实际效应对个人叙事进行类型的划分,而不是像那些共享的叙事文本一样按照内容和母题进行分类。笔者就自己在田野访谈与现场观察中所获得的一些经验,尝试从现实交流关系建立的动机与进行交流的直接目的上,对一些个人叙事资料的性质做出几种类型的划分。我们必须承认,民众的日常交流实践比个人叙事所涵盖的范围更广,类型更多,例如仪式、庆典等都是民众的交流实践方式。但是,我们所说的个人叙事在某种程度上又超越了丹—本·阿莫斯、理查德·鲍曼等人所说的交流实践的范围和类型。因为,美国表演学派主要是从民间文学意义上强调“艺术性的交流”,而民众日常交流实践中的大量的个人叙事被他们忽视了。
(一)事关集体记忆的个人叙事
在民众的日常交流实践中,有些个人叙事讲述的是个人的经历,但其交流的目的却是为了呈现、建构集体共享的历史记忆。这类个人叙事文本大多是一个社区或村落中你知我知的,被大家所牢记的信息,具有公共知识的性质。
2014年笔者在北京市顺义区进行民俗文化普查时,官庄村的村民刘先生就给我讲述了这样一段个人叙事:
1951年前后,我们村儿里有个蹦蹦戏剧团。张大姑娘和小珍儿头是村里有名的两个坤角儿,她们唱得棒极了。当时只要是一说我们官庄的蹦蹦戏要演出,方圆几里地的都来看。那时候我才十五六,每次演戏我都去,可热闹了。当时来看戏的人太多了,戏台周围都得用麻绳儿围起来,就跟现在的警戒线似的,怕出事儿。当时富各庄也有剧团,他们那演戏就没什么人看,很松散。①访谈对象:刘先生;访谈人:毛晓帅;访谈时间:2014年7月15日;访谈地点:顺义区官庄村村委会。
在这段个人叙事材料中,刘先生讲述的是1951年前后自己在村里看蹦蹦戏演出的个人经历。但这段个人叙事材料的主要交流目的却是为了再现、建构一代官庄村人关于村里蹦蹦戏剧团历史的集体记忆。这一类型的个人叙事材料中无疑包含着当地人对自身所在社会的认识、理解和评价,体现着当地民众的历史感和地方感,为建构、保存地方社会的集体记忆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这种鲜活的个人经历最温暖,也最动人。在日常的交流实践中,民众正是通过这种个人叙事参与村落、社区的文化建构,书写大家共有的历史记忆。不同于神话、传说等共享文本的艺术性再现,这些个人叙事建构和再现的历史记忆往往是朴素的、真情实感的。
(二)拉近关系的个人叙事
从交流实践的目的上讲,为了拉近彼此关系,或者说为了取得对方的信任、了解、支持的个人叙事是我们在田野作业过程中经常能够碰到的另一种个人叙事类型。
任何故事的讲述都可能拉近大家的距离。在民众的日常交流实践中,特别是在个人熟悉的关系和场域中,个人叙事往往是建构人们之间彼此了解、信任关系的阶梯。从表达个人身份的意义上讲,真正能够将人们的关系更进一步拉近的,肯定是那些带有一定私密性的,区域社会内部的关于具体个人的叙事。这种类型的个人叙事一般是由讲述者在较为熟悉的关系和环境中讲述的,只有由他个人讲述才成为故事。
笔者2013年夏天在北京平谷进行民俗文化普查时,曾多次前往毛官营村,与村里制作豆片的手艺人武老师建立了良好的田野关系。武老师还把笔者的电话写在了他们家的亲戚朋友通讯录上。当笔者第五次来到他家里与他交谈时,他给我讲述了这样一段个人叙事:“其实我之前在村里收过一个徒弟,我手把手地教他做豆片儿。我们两口子待他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可是后来,他还没学成,就想着自己干,想抢我的生意。他自己在家里做了豆片儿,打着我的招牌卖给人家。后来人家说,豆片儿质量不行,要找他。他就赖在我的头上,说是我们家做的。从这以后,我就寒心了。我也不教他了,也不再往来了。这是家丑。我没跟街坊邻居说过,嫌丢人。你就能明白,我们家做豆片儿的屋子,外人谁也不让进了吧。我是看你小伙子不错,上次我眼睛做手术,你还惦记着来看我。所以我才跟你说这个。”②访谈对象:武老师;访谈人:毛晓帅;访谈时间:2013年7月20日;访谈地点:平谷区武老师家中。
从上面这段个人叙事材料中可以看出,武老师讲述的这段个人经历具有较强的私密性。如果他不讲,别人也不会主动要求他讲,他人也难以通过别的途径来了解这些事情。笔者曾先后五次来到武老师家中进行访谈,我们双方之间彼此熟悉。对武老师来说,笔者是外来的研究者,他对我讲述这些私密性的内容既是出于对我的信任,另外也规避了熟人社会中的舆论压力。通过这次讲述,笔者会对他更加信任。从交流实践的现场目的和实际效应来看,他与笔者之间通过这种个人叙事的讲述,建立了互相了解、信任的纽带,拉近了彼此的关系。
在民众的日常交流实践中,这种为了拉近彼此之间关系或者取得对方的信任、了解、支持而讲述的个人叙事是大量存在的。但是,除了少数学者外,大多数民俗学者并没有给予这类个人叙事应有的关注。例如西村真志叶的《日常叙事的体裁研究:以京西燕家台村的拉家为个案》,已经注意到了“拉家”这种日常叙事能够建立民众之间的友好关系,“参与者之间的友好关系,不但是拉家的实践群体赖以成立的组织原则,同时又是拉家的实践群体努力实现的组织目标之一”①[日]西村真志叶:《日常叙事的体裁研究:以京西燕家台村的拉家为个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20页。。
(三)争夺话语权、解释权的个人叙事
这类的个人叙事实际上往往与集体叙事形成了一种互相嵌入的关系。在民众的日常交流实践中,这类个人叙事的交流目的明显地表现出个人介入到了对公共事务的话语权、解释权争夺当中。民众在讲述这种类型的个人叙事时,往往是为了在公共话语的建构过程中,对集体共享的知识、叙事等给予个人的解读、理解。这种话语权、解释权的争夺也正是一个地方社会中共享文本、知识活化的动力,是延续村落、社区历史记忆的重要手段。
2016年5月笔者在家乡进行田野调查时,村民毛某就给我讲述了这样一段个人叙事:
老陶(化名)说以前咱们村的毛理(化名)是个大老粗,没文化。我就跟他抬杠了。他说的不对。毛理跟我是本家啊,没出五服的叔伯哥哥。就是他年龄比我大得多。那时候解放前他可是个名人,“三开”人物②三开人物,就是在三方力量都吃得开、有一定话语权的人物。。共产党、国民党、日本人来了都找他。他都吃得开,谁也不找他的麻烦。你不佩服不行。他有学问,以前上过私塾,相当于秀才。那时候我爱看书,有什么不会的就找他,他什么都懂。那些四书五经他都懂。古文他都懂,他可不是大老粗,是个文化人。这些我都经历过,是真事儿。③访谈对象:毛某;访谈人:毛晓帅;访谈时间:2016年5月13日;访谈地点:毛某家中。
老陶和毛某都是一个村的街坊,且彼此之间非常熟悉。但在村里的名人毛理的问题上,二人出现了分歧。老陶认为,毛理是个大老粗,没文化。而毛某则认为毛理是有知识、有学问的文化人。从上述毛某的个人叙事材料中可以看出,他结合自己跟毛理学习的个人经历对区域社会中集体共享的内部知识进行了历史的陈述。显然,毛某讲述这段个人叙事的目的是为了在公共话语建构过程中争夺关于毛理个人是否有学问这一问题的话语权和解释权。可以说,这种事关话语权争夺的个人叙事在某种程度上是村落传统活化和村落历史延续的重要动力。在话语权、解释权的博弈和争夺过程中,村民之间形成了共识和认同,村落传统重新焕发出了活力。这种口头叙事和交流行为本身就是维护村落历史连续性的重要方式和手段。
(四)造成道德评价舆论的个人叙事
与家风、道德评价相关的个人叙事,是我们在熟人社会的田野调查中遇到的最多的一类个人叙事。这类个人叙事大多是讲述者结合自身的所见所闻,对自己所在的熟人社会中的某个成员、家庭的作风和道德做出的评价。这种个人叙事的交流目的大多是为了通过道德评价形成舆论压力,成为规范社会成员的言行,维护村落、社区秩序的一种力量。一般情况下,讲述者不会在公共的平台、场合进行讲述,讲述环境一般是较为私密的空间,讲述者与听众之间彼此较为熟悉和了解。
2017年3月笔者在家乡进行田野调查时,邻居温升(化名)就对笔者讲述了这样一段故事:“郑龙(化名)这人不行,他偷主家的东西。我爹去世三周年的时候,他在我家管事儿,偷走了俺家一兜猪耳丝。正好被我看到了,气得我不行。我当时就想打他一顿。第二天正好是星期天,来的孩子也多,别的菜都差不多够数,就是猪耳丝不够,差两盘儿。我去问郑龙这是咋回事,他说可能是买少了。他没说实话。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他是个啥样的人了。虽说两盘耳丝也就值几十块钱,但是偷东西不行。东西再不值钱,你作为管事儿的,是来帮忙的,你得给主家办事儿,不能坑主家啊。后来我逢人就说这件事儿,非得让街上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啥样的人不行。”①访谈对象:温升;采访人:毛晓帅;访谈时间:2017年4月15日;访谈地点:大华村。
温升结合自己的个人经历,对村中管事儿的郑龙做出了道德评价。在村落社会中,村民最看重的就是其他村民对自己的道德评价。不被别人说闲话,尤其是作风和道德品行上不被人指责是大多数村民最基本的价值追求。在村落、社区等熟人社会中,事关家风、道德评价的个人叙事几乎每天都在讲述。正是这些话语的不断建构、交流,形成了文化的动力。社会正是依靠文化的动力来运行的。这些个人叙事的不断讲述和交流形成了舆论的监督和制约,规范着村民的言行举止,维护着村落社会的有序运行。如果村落社会中没有了这种个人叙事的评价,村民之间彼此就没有了关系,村落就会失去原有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不仅如此,一个人要想打破村落中已有的对自己的认识或成见,就不仅要规范自己的所作所为,还要通过个人叙事的讲述和交流,拉近大家彼此之间的关系,形成理解和信任。
日常交流实践中的个人叙事就其所交流的现实目的而言,当然不只是这四个类型,在不同的社会与文化中一定还会有不同的表现。但是,这些类型的分析,已经说明了个人叙事的意义难以用母题、故事类型等民间文学意义上的类型分析来进行解释。村落秩序的运转和共享知识文本的解读,实际上是通过民众的日常交流实践中的个人叙事来实现的。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这种日常交流实践活跃了村落社会关系的运转,构成了这个社会的活力。
个人叙事是民众参与社会建构的重要话语行动方式,其作用不可小觑。个人叙事既具有私人性,又有公共性,个人叙事与集体叙事既相互区别又联系紧密,二者交叉、共融在民众的日常交流实践中。我们不能说只要掌握了一个地方社会的故事、歌谣等民众所共享的知识文本就能够了解这个社会,我们还要从当地民众日常交流的话语和行动中来了解他们的生活历程。对于地方社会的民众来说,他们在日常交流中所必须掌握的叙事文本不只是一些民间故事的文本,所要运用的叙事方式也不经常是娱乐性的讲述故事的方式,而更多地是他们通过自己个人各种经历的讲述,来跟别人进行经验、感受的交流和意见的沟通。这样的交流与沟通,是一个地方社会的生活得以正常进行和不断被建构的基本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