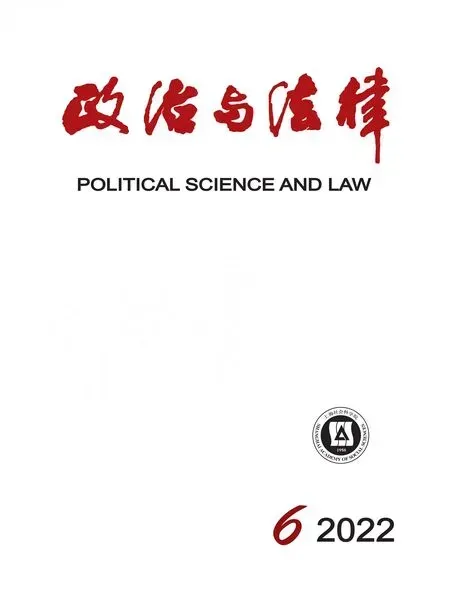身体法益的刑法保护
张明楷
(清华大学法学院,北京 100084)
一、基本观点
与国外故意伤害罪的成立范围相比,〔1〕笔者于本文中区分犯罪的“成立范围”与“处罚范围”这两个概念。因此,认定一个行为成立故意伤害罪,并不当然意味着对该行为科处刑罚,而是完全可能相对不起诉或者免予刑罚处罚。我国故意伤害罪的成立范围比较窄。〔2〕当然,司法实践中也大量存在将正当防卫认定为故意伤害罪的不当现象。参见张明楷:《故意伤害罪司法现状的刑法学分析》,载《清华法学》2013 年第1 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伤害的范围来说,除造成精神病等情形以外,不考虑对精神的伤害,或者说,只将器质性精神障碍认定为伤害,没有将反应性精神障碍认定为伤害;二是从伤害的程度来说,根据法条关系将《刑法》第234 条第1 款规定的伤害理解为轻伤,同时对轻伤的认定标准过高;三是在刑法没有规定暴行罪的立法例下,司法机关也不认定故意伤害罪的未遂犯,导致故意伤害的未遂犯要么无罪,要么被认定为寻衅滋事等侵犯公法益的犯罪。
故意伤害罪的成立范围比较窄只是一个事实判断,问题是应否适当扩大其成立范围?对于后一价值判断,不可能形成绝对统一的共识。本文的基本观点是,应当适当扩大故意伤害罪的成立范围,主要理由有以下四点(其他具体理由将在下文中说明)。
第一,故意伤害罪是针对人的身体的犯罪。“人的身体(及健康)是仅次于生命的、价值高且重要的个人法益。”〔3〕[日]井田良:《講義刑法学•各論》(第2 版),有斐閣2020 年版,第46 页。换言之,“身体的安全是仅次于生命的安全的重大法益。”〔4〕[日]平野龍一:《刑法概說》,東京大学出版会1977 年版,第165 页。与名誉、财产等个人法益相比,身体法益更为重要,对此不必赘述。既然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而身体法益是重要法益,就不能过于限制故意伤害罪的成立范围。
第二,与侵犯财产罪相比,故意伤害罪的成立范围不仅比较窄,而且处罚程度较轻,形成了明显的不均衡现象。例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发布的《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2014 年1 月1 日起施行),头部外伤后伴有神经症状、头皮擦伤面积5.0cm 以上、面部损伤留有瘢痕或者色素改变、眼部挫伤、眼部外伤后影响外观、鼻骨骨折、上颌骨额突骨折、牙槽突骨折、外伤后听力减退、眼球损伤影响视力、腕骨、掌骨或者指骨骨折、外伤致指甲脱落等等,均仅属于轻微伤。故意伤害行为造成上述伤害的,皆不成立故意伤害罪;而盗窃价值1000 元以上财物的行为就可能构成盗窃罪。〔5〕根据2013 年4 月2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8 号)第1 条的规定,盗窃公私财物价值1000 元至3000 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264 条规定的“数额较大”。可是,治愈上述轻微伤的费用也可能不止1000 元,且有些损伤(如听力或视力的减退)难以治愈甚至不能治愈。再如,使用暴力或者胁迫手段抢劫他人几十元或者几百元的财物,即使没有造成任何伤害,也应处3 年以上10 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使用暴力造成被害人轻微伤,被害人花几十元或者几百元治疗费用的,反而不成立犯罪。显然,如果不处罚故意造成轻微伤的行为,就会导致刑法对身体的保护强度弱于对财产的保护强度,这显然不合适。
第三,故意伤害罪的发案率高,因而一般预防的必要性大,不宜限制其成立范围。诚然,故意伤害罪的发案率看起来没有盗窃罪高,“但是,可以说,身体(与财产相并列)是最容易受攻击的法益”。〔6〕[日]井田良:《講義刑法学•各論》(第2 版),有斐閣2020 年版,第46 页。既然如此,就不可能以故意伤害罪的一般预防必要性小为由限制本罪的成立范围。或许有人认为,按照《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由于造成精神伤害或者轻微伤的行为对法益侵害较小、造成的损伤不大,故没有必要预防这种行为。可是,行为人针对被害人一拳一脚可能造成何种程度的伤害,并不是行为人可以完全控制的。例如,暴力行为是只能造成肉体伤害,还是会造成精神伤害,并非行为人可以左右。又如,一拳打死人、一枪未能打死人的现象屡见不鲜。行为人只希望造成轻微伤事实上却造成了轻伤乃至重伤,或者只希望造成伤害实际上却致人死亡的案件,也层出不穷。如果刑法不禁止造成轻微伤的行为,就必然导致相当多的人以为自己的伤害行为不会构成犯罪,进而实施伤害行为,结局却可能导致被害人身受轻伤乃至重伤。〔7〕具有实证依据的“破窗理论”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参见[美]乔治•凯林、凯瑟琳•科尔斯:《破窗效应:失序世界的关键影响力》,陈智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年版,第42 页以下。反过来说,要预防轻伤害与重伤害,首先必须禁止造成轻微伤的行为乃至一切非法暴行,否则,对轻伤害与重伤害的预防效果就极为有限。以下比喻或许不恰当,但似乎能说明问题:倘若监考人员对考生说,“偷看教材二分钟的给予口头批评,超过二分钟的就取消考试成绩”,相信会有许多考生虽然只想偷看二分钟却实际上超过二分钟因而被取消考试成绩;倘若监考人员对考生说,“只要偷看教材就取消考试成绩”,相信绝大多数考生不会起偷看教材之念。对故意伤害罪以及其他犯罪的认定也是如此。
第四,虽然日常生活的不谨慎也可能引起伤害结果,但故意伤害行为引起的伤害结果则明显不同。故意伤害罪一般属于暴力犯罪。“人们对无情的暴力犯罪的恐惧超过了其他任何形式的犯罪行为……暴力犯罪使人恐慌,也因此左右着公共政策。”〔8〕[美]斯蒂芬•E.巴坎:《犯罪学:社会学的理解》,秦晨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第304 页。在暴力伤害他人身体的案件频繁发生的环境中,国民不能安心地从事社会生活,因而也特别期待刑法保护个人的身体法益。〔9〕参见[日]井田良:《講義刑法学•各論》(第2 版),有斐閣2020 年版,第46 页。
总之,在我国当下,虽然刑事立法不必提高故意伤害罪的法定刑,刑事司法也不应提升对故意伤害罪的量刑幅度,但需要适当扩大故意伤害罪的成立范围。首先,由于精神伤害与肉体伤害没有本质区别,应当将故意造成精神伤害的行为认定为故意伤害罪;其次,现行的轻伤害认定标准过高,应当将故意造成轻微伤的行为认定为故意伤害罪;最后,在现行刑法没有规定暴行罪的立法例之下,应当承认故意伤害罪的未遂犯,即对以伤害(包括轻伤)故意实施伤害行为、没有造成伤害结果但存在具体危险、情节严重的情形,应当以故意伤害罪的未遂犯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二、精神伤害
所谓精神伤害(或精神损伤),不是指使他人患上精神病等器质性精神障碍,而是指使他人产生反应性精神障碍,如使他人神经衰弱、抑郁、长期处于不安的状态、长期处于惊恐的状态、产生应激反应障碍、长期失眠等等。〔10〕参见[日]薮中悠:《人の精神の刑法的保護》,成文堂2020 年版,第17 页、第52 页。故意造成精神伤害的行为是否成立故意伤害罪,首先取决于如何理解故意伤害罪的保护法益;而关于故意伤害罪的保护法益,在刑法理论上存在不同观点。例如,针对“伤害罪”包含了对直系尊亲属的暴行罪的立法体例,有学者认为,“伤害罪所要保护的法益乃是个人的身体法益,包括身体的完整性与身体的不可侵害性、生理机能的健全与心理状态的健康等”。〔11〕林山田:《刑法各罪论(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80 页。这一表述可谓相当全面。将“身体的不可侵害性”作为伤害罪的法益,主要是为了说明暴行罪的性质。我国刑法没有规定暴行罪,故不宜将“身体的不可侵害性”视为伤害罪的法益,而需要讨论其他方面的内容。
首先,“身体的完整性”是否属于故意伤害罪的保护法益,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如何理解“身体的完整性”。如果将“身体的完整性”理解为肢体、器官、组织的完整性,〔12〕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第9 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年版,第457 页。那么,身体的完整性无疑属于伤害罪的保护法益;人体的肢体、器官、组织都有一定机能,如果破坏了肢体、器官、组织的完整性,就会损害生理机能,因此,这个意义上的“身体的完整性”属于“生理机能的健全”。但是,如果将“身体的完整性”解释为身体外形的完整性,〔13〕参见[日]団藤重光:《刑法綱要各論》(第3 版),創文社1990 年版,第409 页。结论则异。人的头发与指甲是身体外形的一部分,如果将身体外形的重大变化或者完整性作为故意伤害罪的保护法益,那么,使用暴力或者其他方法除去他人头发或指甲的行为,便成立故意伤害罪。但在我国,将伤害概念扩张到这种异质的内容不一定适当。如果说剪掉头发便损害了身体的完整性,就意味着光头人士(包括普通人与僧人)的身体都不完整,这显然不合适。〔14〕参见[日]平野龍一:《刑法概說》,東京大学出版会1977 年版,第167 页。不仅如此,按照他人意愿剃剪光头的理发行为也是符合故意伤害罪构成要件的行为,只是通过被害人承诺排除违法性,这恐怕也多此一举。在我国,违反他人意志除去他人头发情节严重的,可以侮辱罪论处;去除他人指甲的,不必以犯罪论处(对手指造成伤害的除外)。
其次,可以肯定的是,人的生理机能的健全是故意伤害罪的保护法益。〔15〕参见[日]平野龍一:《刑法概說》,東京大学出版会1977 年版,第167 页;[日]大谷實:《刑法講義各論》(第4 版),成文堂2013 年新版,第25 页;[日]曾根威彦:《刑法各論》(第5 版),弘文堂2012 年版,第16 页,[日]西田典之著、橋爪隆补订:《刑法各論》(第7 版),弘文堂2018 年版,第43 页;[日]林幹人:《刑法各論》(第2 版),東京大学出版会2008 年版,第46 页;[日]山口厚:《刑法各論》(第2 版),有斐閣2010 版,第45 页;等等。问题是,如何理解人的生理机能(生理机能的健全性)与精神状态的健康(精神的健全性)的关系?换言之,行为造成生理机能障碍的肯定属于伤害,那么,行为造成精神伤害的是否属于伤害?
《德国刑法》第225 条规定了虐待被保护人罪,其行为包括给予痛苦或者粗暴虐待。就此而言,德国的判例与通说认为,其中的给予痛苦包括给予精神痛苦。据此,行为引起了他人较长时间的持续或者反复的身体性质的或者精神性质的一定程度的痛苦或者苦恼,就构成《德国刑法》第225 条规定的犯罪。因此,就《德国刑法》第225 条而言,其保护法益包括了精神的健全性。但是,《德国刑法》第223 条规定的普通伤害罪(伤害身体罪)的保护法益是否包括精神的健全性,则存在争议。通说认为,普通伤害罪的保护法益及行为造成的伤害结果,仅限于身体的内容,而不包括精神的内容(身体症状限定说)。如果对他人的精神虐待没有同时造成对身体的虐待,就不成立普通伤害罪。例如,向他人吐口水的行为,虽然使他人很不愉快,但欠缺对身体的作用与侵害,故不属于对身体的虐待。反之,如果不但动摇了精神的平静,而且导致被害人产生神经方面的刺激性病症,因而形成了可以查知的症状,则属于对身体的虐待,能够成立普通伤害罪。通说还列举了其他方面的理由,比如,从伤害概念的历史沿革来看,这一概念一直不包括造成精神障碍;如果包括精神障碍,就导致处罚范围太宽。〔16〕参见[日]薮中悠:《人の精神の刑法的保護》,成文堂2020 年版,第34 页以下。少数说则认为,普通伤害罪包括精神虐待(精神症状包含说)。如Wolfslast 认为,对人的精神的保护很重要,侵害精神的健康与侵害身体的健康并无区别,精神障碍在很多场合是可以跟疾病、病理性的障碍等同的,对精神障碍的程度也是能够判断的。并且,采取精神症状包含说,不会扩大处罚范围,因为在许多场合难以证明因果关系。〔17〕Vgl.GabrieleWolfslast,Psychotherapie in den Grenzen des Rechts,FerdinandEnke 1985,S.19ff.
《意大利刑法》第582 条第1 款规定:“对他人造成人身伤害的,如果因此而产生身体的或者精神的病患,处以3 个月至3 年有期徒刑。”〔18〕黄风译注:《最新意大利刑法典》,法律出版社2007 年版,第196 页。显然,这一规定使得普通伤害罪包括了精神伤害。《西班牙刑法》第147 条也明文规定伤害罪包括对“身体和精神健康”的伤害。《法国刑法典》分则中有“伤害人之身体或精神罪”一章,其中的一节为“精神骚扰罪”。如该节的第222-33-2 条规定:“反复骚扰他人的言语或行为,以损害他人工作条件为目的或效果,能够损害他人的权利及尊严、损害他人的身体健康或精神健康或者危害他人职业前途的,处2 年监禁并科30000 欧元罚金。”〔19〕朱琳译:《最新法国刑法典》,法律出版社2016 年版,第98 页。此外还有两个法条进行了相关规定。可以认为,法国刑法中广义的伤害罪包括了精神伤害。
《奥地利刑法》没有明文规定伤害行为包括虐待行为与精神伤害,但其第83 条规定的伤害由两个概念构成,一是伤害身体(包括侵害身体的完整性,如剪掉他人头发),二是侵害健康。根据判例与通说,其中的侵害健康,是指造成机能的障碍(Funktionsstörung),也就是说,使他人患上疾病或者使疾病恶化,疾病则包含身体的疾病和精神的疾病。也可以说,在奥地利,侵害健康不需要区分身体与精神;造成身体的被害与精神的被害,都属于对健康造成侵害。即使采用纯粹精神的作用方式,也可以成为侵害健康的手段或者方法。例如,职场中的骚扰行为,导致他人精神疲惫、产生重度睡眠障碍或者产生自杀念头的,都属于造成伤害,甚至可能构成重伤害。〔20〕参见[日]薮中悠:《人の精神の刑法的保護》,成文堂2020 年版,第58 页以下。
《瑞士刑法》第122 条规定了重伤害罪,第123 条规定了轻伤害罪(单纯伤害罪),第125 条规定了过失伤害罪,第126 条规定了暴行罪。瑞士的判例与通说认为,伤害罪的保护法益是人的身体的完整性(Integrität)与精神的完整性。基于这样的理解,瑞士刑法中的伤害概念包含两类。一是侵害身体。这是指侵害了作为生命及个人权利的外在表现的身体的完整性。显然,侵害身体的行为大多同时侵害健康。没有侵害健康但侵害身体的典型例子是剪掉他人头发。二是侵害健康。这是指引起了病理学的状态,或者使病理学状态恶化,或者导致健康恢复延迟。在瑞士,健康和疾病是相反的概念,或者说,侵害健康与疾病是同义的。所以,伤害罪的对象并不限于身体健康的人,已经患有疾病的人也是伤害罪的对象,因为使病情恶化的行为也是侵害健康。人的健康则包括身体的健康与精神的健康。〔21〕参见[日]薮中悠:《人の精神の刑法的保護》,成文堂2020 年版,第86 页以下。
《日本刑法》第204 条规定:“伤害他人身体的,处十五年以下惩役或者五十万元以下罚金。”尽管该条没有明文规定造成精神伤害的行为构成伤害罪,但在二战前就有学者认为伤害罪的保护法益包括精神的健全,进而指出,“伤害罪因侵害他人(自己以外的自然人)的肉体或者精神的健全而成立”;“通过胁迫等所谓无形的暴力而损害肉体、精神的健全的,可以认定为伤害行为”。〔22〕[日]泉二新熊:《日本刑法論下卷(各論)》(订正第44 版),有斐閣1939 年版,第519 页、第520 页。现在,“根据判例与通说,作为伤害内容的生理机能的障碍也包含精神机能的障碍”。〔23〕[日]松原芳博:《刑法各論》(第2 版),日本評論社2021 年版,第51 页。如有的学者在说明伤害的含义时,明确将精神病、神经衰弱等精神障碍归入伤害。〔24〕参见[日]内田文昭:《刑法各論》(第3 版),青林書院1996 年版,第19 页。还有学者明确指出:“一直以来,健康状态的不良变更意义上的生理的机能的障碍,不仅包括身体的机能的障碍,而且包括精神的机能的障碍。”〔25〕[日]佐伯仁志:《身体に対する罪》,载《法学教室》第358 号(2010 年),第124 页。
英国《1861 年侵犯人身犯罪法》规定了“身体伤害”的犯罪。“上议院确认,‘身体伤害’包括所有公认的精神伤害。霍博斯(Hobhouse)法官在ChanFook 案〔26〕(1994)99 Cr App R 147,at 152——原书注释。则区别对待‘诸如悲伤或恐慌的纯粹的情绪’和‘有证据证明的属于公认的临床的精神疾况’,前者不足以成为身体伤害,若有精神病医生的证明,后者可能成为身体伤害。”〔27〕[英]杰瑞米•侯德:《阿什沃斯刑法原理》,时延安、史蔚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9 年版,第354-355 页。
综上可知,有的国家刑法明文规定了故意伤害包括精神伤害;在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精神伤害的部分国家,虽然在德国只有少数说认为伤害包括精神伤害,但奥地利、瑞士、日本以及英国的通说与判例均认为伤害包括精神伤害。
在我国,《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只是将“重度智能减退或者器质性精神障碍,生活完全不能自理”〔28〕《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对器质性精神障碍的定义性规定是:“有明确的颅脑损伤伴不同程度的意识障碍病史,并且精神障碍发生和病程与颅脑损伤相关。症状表现为:意识障碍;遗忘综合征;痴呆;器质性人格改变;精神病性症状;神经症样症状;现实检验能力或者社会功能减退。”规定为重伤,没有规定造成器质性精神障碍构成轻伤与轻微伤的情形。《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不仅没有将反应性精神障碍归入伤害,而且明文规定:“本标准所称的损伤是指各种致伤因素所引起的人体组织器官结构破坏或者功能障碍。反应性精神病、癔症等,均为内源性疾病,不宜鉴定损伤程度。”不过,这不是刑法的明文规定,只是司法上的判断。因此,即使不修改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刑事司法也可能将精神伤害包含在伤害概念中。
如上所述,奥地利、瑞士、日本、英国等国刑法关于普通伤害罪的规定与我国刑法并无本质不同,我国完全可以借鉴这些国家的学说与判例,将故意造成精神伤害的行为认定为故意伤害罪。当然,不免会有人认为,这一主张照搬了国外学说。然而,精神伤害能否归入伤害,主要是与人有关,而非与国情有关。诚然,我国刑法对犯罪一般都规定了量(情节)的限制条件,而外国刑法一般没有规定这样的限制条件,这似乎是我国不能将造成精神伤害的行为认定为故意伤害罪的理由。但在笔者看来,这只不过是刑事立法的表面现象,从司法上看,我国对犯罪的“处罚范围”并不窄于国外。例如,《日本刑事诉讼法》规定了由司法警察行使的微罪处分制度,微罪处分率非常高,且具有特效。〔29〕[日]松尾浩也:《日本刑事诉讼法(上卷)》,丁相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90 页。其他移送到检察机关的案件,仍有50%左右未被提起诉讼,监禁率极低,犯罪率也很低。〔30〕参见日本国法務省:《犯罪白書》(令和2 年版),http://hakusyo1.moj.go.jp/jp/67/nfm/mokuji.html,2021 年9 月11 日访问。再如,在德国,只有10%左右的刑事案件起诉到法院,在2013 年审理的案件中,约1%的被告人仅被判处警告,82%的被告人被判处罚金,17%的被告人被判处监禁刑,但其中70%的监禁刑以缓刑方式进行,所以只有5%的被告人进了监狱。这种低处罚率仍然使德国的刑事立案数持续走低。〔31〕参见[德]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事程序法原理》,江溯等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21 年版,第196 页以下。不难看出,虽然国外刑法中犯罪的“成立范围”宽,但司法上对犯罪的“处罚范围”窄。这种使犯罪的成立范围与处罚范围相区别的做法,事实上有利于一般预防。这是因为,刑事立法上告诉一般人“任何侵害法益的行为都成立犯罪”,便有利于刑法规范起到行为规制作用;刑事司法上对构成较轻犯罪的行为不予处罚,让行为人体会到司法机关对其处理宽大,行为人便会感恩戴德。正因为如此,那些受微罪处分或相对不起诉、暂缓起诉的行为人,不再重新犯罪;那些受到实刑处罚的行为人,因为对处罚不满反而容易再犯。在我国,将造成精神伤害的行为认定为故意伤害罪,虽然不一定都给予刑罚处罚,但必然有利于预防故意伤害行为,保护国民精神的健全性。
其实,肉体伤害与精神伤害也未必具有明显的界限。例如,在德国,“长期对被害人进行跟踪和骚扰,导致被害人情绪抑郁,无法入睡和集中注意力”的,被认定为身体伤害罪。如前所述,德国的通说认为:“精神上的损害不是对身体健康的损害,不能成立身体伤害罪。跟踪被害人,导致其产生害怕与恐惧情绪的,不成立身体伤害罪。但是,如果对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进而造成了对其身体健康的消极影响,则应当肯定符合身体伤害罪的构成要件。例如,告知被害人令其感到极为恐惧的信息,持续通过电话恐吓、骚扰被害人或者制造被害人无法回避的、使其身体耗弱的敌对气氛,从而损害被害人身体健康的,均成立身体伤害罪。”〔32〕王钢:《德国判例刑法(分则)》,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72 页、第73 页。不难看出,在什么情况下精神伤害对身体健康产生消极影响的判断,是极为微妙与模糊的。完全可以认为,使被害人无法入睡和不能集中注意力,以及使被害人极为恐惧,是典型的精神伤害。既然如此,不如直接承认精神伤害也成立故意伤害罪。
我国有学者认为,精神伤害作为民事赔偿责任问题提出是可以的,但在刑法上,精神伤害并没有实质上损害身体健康,因而不构成故意伤害罪。〔33〕参见王作富主编:《刑法分则实务研究(中)》(第5 版),中国方正出版社2013 年版,第737 页。然而,这一观点可能受到以下质疑。其一,精神伤害能够成为侵权行为的损害结果,当然也能成为刑法上的危害结果。因为严重的侵权行为都可能构成犯罪。其二,精神伤害对人的危害并不轻于对人的肉体伤害。许多精神伤害的时间持续长,甚至基本上不可能或者难以逆转,因而比肉体上的伤害更为严重。既然造成被害人精神失常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就没有理由否认造成精神伤害的行为也成立故意伤害罪。其三,精神对肉体具有支配作用,对精神的伤害也会直接影响人的肉体行动,乃至会因为精神伤害而进一步形成肉体伤害。国外学者埃弗森•罗斯和路易斯发现,负面情绪状态(包括抑郁、焦虑等)会增加心血管性发病率和死亡率的风险。在全球疾病负担中,约14%源于精神神经疾病。精神疾病增加生病和受伤的风险,而身体健康欠佳也会增加患精神疾病的风险,二者的并发使诊断和治疗更加复杂。〔34〕参见郭慧玲:《由心至身:阶层影响身体的社会心理机制》,载《社会》2016 年第2 期。既然如此,就没有理由将精神伤害排除在伤害之外,否则就明显不协调。
承认精神伤害所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解释论上是否违反罪刑法定原则?日本学者松原芳博指出,将造成精神伤害的情形包含在《日本刑法》第204 条的伤害他人“身体”的文义中,是存在疑问的,〔35〕参见[日]松原芳博:《刑法各論》(第2 版),日本評論社2021 年版,第51 页。即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嫌疑。我国《刑法》第234 条表述的也是伤害他人“身体”,是否只能采取德国的通说,或者像松原芳博教授所说的那样,认为对身体的伤害不包括对精神的伤害?笔者持否定回答。没有理由认为,“身体”与肉体(躯体)是完全等同的概念。可以认为,“身体”一词具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身体是指肉体,广义的身体则包括精神在内。即使认为故意伤害罪的保护法益是人的生理机能的健全性,其中的“生理”也不必然排除精神。并且,“精神机能的障碍,是基于大脑机能的障碍,在人的器官的机能障碍这一点上,可以说与通常的身体机能的障碍没有本质区别”。〔36〕[日]井田良:《講義刑法学•各論》(第2 版),有斐閣2020 年版,第52 页。因此,认为“伤害他人身体”包括伤害他人肉体与精神,没有超过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相信也不会超出国民的预测可能性。
承认精神伤害所遇到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由于是否存在精神机能的障碍,以及行为与该障碍之间的因果关系不明确,因而认定起来是困难的”,〔37〕[日]松原芳博:《刑法各論》(第2 版),日本評論社2021 年版,第51 页。在司法实务上,将精神伤害认定为对身体的伤害是否具有可行性?笔者认为具有可行性。
其一,对精神伤害的鉴定并非不可能。例如,在国外,“医学能够令人满意地证实精神伤害的存在、它的严重程度及其后果”。〔38〕[澳]F.A.特林德:《故意施加的单纯精神上的伤害》,李建华译,载《法学译丛》1988 年第1 期。国内有鉴定人员撰文指出,鉴定人员所属单位从1991 年至1999 年受理的司法精神医学鉴定中涉及受精神伤害程度的评定案例共计36 例,占鉴定总数的9%,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其中急性心因反应5 例、延迟性心因反应7 例、癔症1 例、躁狂症1 例。其中,在鉴定为延迟性心因性反应时,有3 例平时有明显的个性缺陷,精神创伤也不十分强烈,主要表现为焦虑、轻度抑郁、易惊、社会适应能力下降及病程较为迁延等,结论定为间接因果关系较为恰当,施害者则应负大部分责任。〔39〕参见赵毅民、周小东:《对36 例受精神伤害的程度鉴定分析》,载《四川精神卫生》2002 年第1 期。不仅如此,早就有学者提出了精神伤害中的重伤害与轻伤害的鉴定标准。〔40〕参见孙东东、刘克鑫:《论精神伤害的司法精神医学鉴定》,载《中外法学》1994 年第4 期。概言之,司法鉴定既能鉴定器质性精神障碍,也能鉴定反应性精神病、癔症等精神伤害。
其二,不可否认的是,精神伤害的因果关系判断可能是一个难题。如果在具体个案中不能鉴定出精神伤害程度及其因果关系,当然适用事实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不以故意伤害罪论处。在此意义上说,承认故意伤害罪包括故意造成他人精神伤害,也不会导致故意伤害罪成立范围的明显扩大。
其三,将故意造成他人精神伤害的行为认定为故意伤害罪,并不意味着任何与精神伤害具有因果关系的行为均成立故意伤害罪,也不意味着对符合其他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也认定为故意伤害罪。首先,造成非常轻微的精神伤害的行为不成立犯罪,只有达到一定程度的精神伤害(与构成故意伤害罪的肉体伤害程度相当的精神伤害),才能认定为《刑法》第234 条规定的伤害。其次,只有通过虐待、暴行等方法造成他人精神伤害的,才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不具有类型性地造成精神伤害的危险的行为,如恋爱时提出分手、借钱不还等行为,不可能被评价为伤害行为。最后,非法侵入住宅、侮辱、诽谤行为或者寻衅滋事行为造成他人精神伤害的,不会认定为故意伤害罪。〔41〕参见[日]薮中悠:《人の精神の刑法的保護》,成文堂2020 年版,第179 页。
三、轻微伤害
《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将伤害程度分为重伤、轻伤与轻微伤,其中的轻微伤是指达到了一定程度的伤害但不构成轻伤的情形。
《刑法》第234 条第2 款规定了重伤,人们可以据此认为,《刑法》第234 条第1 款规定的是轻伤。可是,《刑法》第234 条第1 款并没有使用轻伤概念,其中的“伤害”,完全可能是单纯伤害或者普通伤害,而非《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所称的“轻伤”。换言之,没有理由认为,《刑法》第234 条第2 款规定的是重伤,第1 款规定的就是轻伤,轻伤就是指《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规定的轻伤。因为这个推理并不符合逻辑。况且,《刑法》第234 条第1 款是故意伤害罪的基本法条,而不能简单地认为该款规定的就是轻伤。例如,在鉴定人对轻伤害与重伤害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完全可以适用《刑法》第234 条第1 款的法定刑,而不可能根据事实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宣告无罪。显然,人们针对《刑法》第234 条第1 款提出的轻伤概念只不过是一个界限要素,旨在区分第1 款与第2 款。事实上,达到什么程度就是《刑法》第234 条第1 款规定的伤害,是由最高司法机关决定的。也就是说,如果要限制故意伤害罪的成立范围,就可以认为《刑法》第234 条第1 款的伤害必须是达到了《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规定的轻伤程度的伤害;反之,如果想扩大故意伤害罪的成立范围,则完全可以认为,《刑法》第234 条第1 款规定的伤害,包括《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规定的轻伤与轻微伤两种程度的伤害,只有尚未达到轻微伤程度的伤害,才不成立故意伤害罪。
如所周知,《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规定的轻微伤,是达到了一定程度的伤害。只不过轻微伤这个概念给一般国民的印象是,伤害很轻微因而可以忽略不计。然而,只要查阅一下《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关于轻微伤的具体规定,就会发现并非如此。换言之,根据《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轻微伤并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伤害,也不是不需要治疗就可以自然痊愈的轻微伤害。此外,轻微伤的鉴定标准并没有完全按年龄作区分,许多轻微伤相对于儿童而言,其实是比较严重的伤害。
如前所述,治疗轻微伤的费用也可能达到了财产犯罪的定罪起点。既然如此,就没有理由对故意造成轻微伤的行为不以故意伤害罪论处。否则,不仅与财产罪的处罚不协调,而且产生不合理的价值取向,使人们认为财产法益重于身体法益,导致一些人恣意侵害他人身体。
即使与其他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相比,也应将故意造成轻微伤的行为认定为犯罪。例如,《刑法》第245 条规定了非法搜查罪,根据2006 年7 月26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高检发释字[2006]2 号),对于非法搜查,造成财物严重损坏的,非法搜查3 人(户)次以上的,司法工作人员对明知是与涉嫌犯罪无关的人身、住宅非法搜查的,均应追诉。但这些情形与故意造成他人轻微伤相比,显然要轻得多。相信多数人宁愿身体被搜查3 次,也不会愿意自己遭受眼部挫伤、鼻骨骨折、上颌骨额突骨折、牙槽突骨折、外伤后听力减退、眼球损伤影响视力等轻微伤。再如,与《刑法》第247 条规定的暴力取证罪相比,故意造成他人轻微伤的行为的不法程度更为严重。
与国外的学说、判例认定的伤害相比,我国《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所规定的轻微伤并不轻微,而是比较严重。
例如,日本刑法理论的通说与判例认为,由于《日本刑法》第204 对故意伤害罪规定的法定最低刑是单处罚金,故没有道理大幅度限定故意伤害罪的成立范围。〔42〕参见[日]中森喜彦:《刑法各論》(第4 版),有斐閣2015 年版,第15 页。易言之,对程度相当轻微的伤害也可以适用其第204 条,只是那种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忽略不计的极为轻微的损伤,才可以排除在伤害之外。〔43〕参见[日]団藤重光:《刑法綱要各論》(第3 版),創文社1990 年版,第407 页。有的判例指出:“一般来说,可以忽略不计的极为轻微的身体损伤,例如,像本人都没有发觉那种程度的发红、表皮剥离或者肿胀,即使不施以任何治疗手段也能在极短时间内自然快愈的疼痛这样的,即使在医学上可能称为创伤或者病变,在刑法上认为不属于伤害是合理的。”〔44〕大阪高等裁判所1960 年6 月7 日判决,载日本《高等裁判所刑事判例集》第13 卷第4 号,第358 页。有的判例提出了较为明确的一般界限:(1)不妨碍日常生活;(2)被害人没有意识到伤害或者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忽略不计;(3)不需要特别的医疗行为。〔45〕参见名古屋高等裁判所金沢支判1965 年10 月14 日判决,载日本《高等裁判所刑事判例集》第18 卷第6 号,第691 页。在日本,作为伤害的具体实例,并不限于创伤、擦伤、跌打伤等外伤,而是包括疲劳倦怠、胸部疼痛、腰部压痛、头晕、呕吐、昏迷、中毒、患病、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等等。〔46〕参见[日]西田典之著、橋爪隆补订:《刑法各論》(第7 版),弘文堂2018 年版,第43 页。例如,行为人给被害人造成外部不能看见、10 天以内可以完全恢复正常的胸部疼痛,日本最高裁判所认定该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47〕参见日本最高裁判所1957 年4 月23 日判决,载日本《最高裁判所刑事判例集》第11 卷第4 号,第1393 页。
在德国,使被害人遭受巨大惊吓,致其“眼前一黑”的,打被害人一耳光,使其感受到疼痛的,将被绑住的被害人头朝下放置较长时间的,胡乱剪掉被害人头发的,以伽马射线或者X 光对被害人进行辐射的,以及向未成年儿童出售酒精饮料的,将可能致人上瘾的毒品交付给被害人的,均被认定为故意伤害罪。〔48〕参见王钢:《德国判例刑法(分则)》,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72 页。
如前所述,在奥地利,故意伤害罪包括伤害身体与侵害健康,对身体的不可侵犯性造成的并不轻微的侵害,就是伤害身体。侵害健康则是健康状态的相反概念或者对立概念。某种症状能否被认定为侵害健康,要根据侵害健康的定义来决定,其基准是,根据行为造成的样态与程度,是否存在可以被认定为疾病的机能障碍。例如,故意造成划伤、砍伤、擦伤、导致皮下出血、骨折、脱臼、挫伤、撞伤等,均构成故意伤害罪;行为导致他人身体的某一个部位发紫发红的,行为人拔他人头发导致头皮有点发红的,行为导致妇女的皮肤上擦伤的面积就像豆子那么大的,行为导致被害人一平方厘米的皮肤内出血的,均被认定为故意伤害罪。至于使他人中毒、感染疾病、感染性病,或者造成某种细菌感染,以及造成孕妇流产的,也属于侵害健康,构成故意伤害罪。〔49〕参见[日]薮中悠:《人の精神の刑法的保護》,成文堂2020 年版,第65 页以下。
在英国,即使是作为袭击罪的加重犯的实际身体伤害,〔50〕英国《1861 年侵犯人身犯罪法》第47 条所规定的“引起实际身体伤害的袭击”属于加重袭击罪,通常被视为轻率地施加伤害或严重身体伤害之下、普通的袭击罪之上的一级犯罪“阶梯”。也包括“暂时失去意识”,“牙齿脱落或损坏、暂时丧失感觉功能、大面积或多处挫伤、鼻子破裂、轻微骨折、需缝合的轻微伤口”。〔51〕[英]杰瑞米•侯德:《阿什沃斯刑法原理》,时延安、史蔚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9 年版,第358 页。
不难看出,上述国家判例所认定的故意伤害罪中的伤害,都包括了我国《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所规定的轻微伤,有的甚至还没有达到轻微伤的程度。
我国司法实践虽然没有将故意造成轻微伤的行为认定为故意伤害罪,但与此同时,司法解释已经将轻微伤作为认定一些犯罪的重要标准。例如,2005 年6 月8 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05]8 号)规定:“行为人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未达到‘数额较大’,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情节较轻、危害不大的,一般不以犯罪论处;但具有下列情节之一的,可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的规定,以抢劫罪定罪处罚:……(三)使用暴力致人轻微伤以上后果的;……。”显然,行为是否造成轻微伤成为上述情形下区分抢劫罪与非罪的标准。又如,2006 年1 月11 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6]1 号)第7 条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使用轻微暴力或者威胁,强行索要其他未成年人随身携带的生活、学习用品或者钱财数量不大,且未造成被害人轻微伤以上或者不敢正常到校学习、生活等危害后果的,不认为是犯罪。”同样,行为是否造成轻微伤,也是区分寻衅滋事罪等罪与非罪的标准。再如,2015 年3 月2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法发[2015]4 号)指出,“虐待造成被害人轻微伤或者患较严重疾病”等情形,“属于刑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规定的虐待‘情节恶劣’,应当依法以虐待罪定罪处罚”。
诚然,在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与司法实践中,并不是仅因行为造成了他人轻微伤就成立犯罪。然而,也正是因为行为给他人造成了轻微伤才成立犯罪(并且是较重的犯罪)。这说明,轻微伤是提升不法程度的重要因素。既然如此,在法定刑最低刑为管制的立法例之下(明显轻于抢劫、寻衅滋事等罪的法定刑),将故意造成他人轻微伤的行为认定为故意伤害罪,也无不妥之处。
此外,《刑法修正案(十一)》修改了《刑法》第236 条与第237 条,将奸淫幼女“造成幼女伤害”、猥亵儿童“造成儿童伤害”的,规定为结果加重犯;其中的伤害显然不要求达到重伤程度。〔52〕日本刑法分则将致人伤害规定为非法拘禁、强制性交、抢劫等罪的结果加重犯的加重结果,但不要求伤害达到严重程度,相当于我国轻微伤甚至更轻的伤害,也可能成为结果加重犯中的伤害结果。例如,日本最高裁判所针对抢劫致人伤害的结果加重犯指出,即使是轻微的伤害,既然对人的健康状态造成了不良变更,就属于日本刑法第240 条(抢劫致人伤害)中的伤害;日本的下级裁判所也遵循最高裁判所的判例。参见[日]川端博、西田典之等编《:裁判例コンメンタ-ル刑法(第3 卷)》,立花書房2009 年版,第226-227 页。既然轻伤害可以成为结果加重犯中的加重结果,就有理由将故意造成他人轻微伤的行为认定为故意伤害罪的基本犯。
在暴力行为致一人轻微伤的场合,如果否认该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反而会导致对这种行为认定为寻衅滋事罪,适用更重的法定刑。例如,2009 年7 月28 日,被告人严某伙同应某、陆某(均已判刑)等人在某区南码头路1453 弄口,拦招已下班的出租车司机沈某,遭拒绝后无故对被害人沈某实施殴打,致使沈某左眼部钝挫伤,经鉴定已构成轻微伤。法院认为,“被告人严某伙同他人,随意殴打他人致1 人轻微伤,情节恶劣,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53〕参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0)浦刑初字第12 号刑事判决书。类似判决呈现出明显不协调的现象:对暴力行为致人轻伤的,认定为故意伤害罪,仅适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的法定刑;对暴力行为致人轻微伤的行为,认定为寻衅滋事罪,反而适用“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的法定刑。〔54〕该案对“无故”的认定也并非没有疑问。况且,故意伤害罪的成立并非存在行为起因的要求。倘若将暴力致一人轻微伤的行为认定为故意伤害罪,则可以避免这种不协调的现象。
在暴力行为致多人轻微伤的场合,如果否认该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会导致对这种行为均认定为寻衅滋事罪,也不利于保护被害人的身体法益。例如,2020 年2 月6 日,被告人唐某酒后未戴口罩至卫生院探视其住院的父亲。进入卫生院大门时,值班医生周某提醒其戴口罩后再进入。后周某查房时发现被告人在正在输氧的病房内抽烟,予以制止,双方发生口角。唐某先是殴打周某,后又殴打上前劝阻的院长王某以及群众姚某和唐某,并拍打卫生院内停放的多辆车辆引擎盖。经鉴定,被害人周某、王某、姚某的损伤程度均构成轻微伤。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唐某的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法院也以寻衅滋事罪定罪量刑。〔55〕参见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2020)苏0925 刑初字第78 号刑事判决书。可是,基于身体法益的个人专属性,对于故意伤害多人的行为应当实行数罪并罚,〔56〕参见张明楷:《故意伤害罪探疑》,载《中国法学》2001 年第3 期。而不能仅以一个寻衅滋事罪论处。否则,也会出现另一方面的不协调。退一步说,即使否认对于故意伤害多人的行为应当实行数罪并罚,对故意造成多人轻微伤且确实构成寻衅滋事罪的行为,也可以按想象竞合处理,实现想象竞合的明示机能,即告诉行为人与一般人,单纯造成他人轻微伤的行为也成立故意伤害罪,从而有利于保护公民的身体法益。
不难看出,只要承认故意造成轻微伤的行为成立故意伤害罪,不管是不并罚的情形还是应当并罚的情形,都可以使案件得到妥当处理。
四、伤害未遂
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基本上没有以故意伤害罪的未遂犯定罪量刑的判例。〔57〕笔者以“故意伤害的未遂”等为关键词在“北大法宝”网站搜索,没有发现一例判决。刑法理论对故意伤害罪是否存在犯罪未遂,存在不同观点。〔58〕其中所谓的是否存在犯罪未遂,是指对故意伤害未遂的行为能否认定为犯罪。
首先,关于《刑法》第234 条第2 款的重伤害是否存在未遂犯的问题。虽然我国司法实践中基本上见不到重伤害未遂的判例,但刑法理论大多对此持承认肯定态度。〔59〕参见马克昌主编:《百罪通论(上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532 页;王作富主编:《刑法分则实务研究(中)》(第5 版),中国方正出版社2013 年版,第743 页;肖中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109 页。在笔者看来,致人重伤包括两种情形。一是轻伤害的结果加重犯,即行为人以轻伤害的故意实施伤害行为,过失造成了重伤害。这种过失的结果加重犯当然没有未遂犯。〔60〕如果轻伤害本身未遂,也不可能成立结果加重犯的未遂犯。二是普通结果犯(或故意的结果加重犯),即行为人以重伤害的意图实施伤害行为,如果造成了重伤,既可以认为是普通的结果犯,也可以认为是故意的结果加重犯。普通的结果犯与故意的结果加重犯均存在未遂犯。〔61〕参见张明楷:《刑法学(上)》(第6 版),法律出版社2021 年版,第449 页。因此,从理论上说,对以重伤害的意图实施伤害行为但未造成伤害结果的,应当认定为故意伤害罪的未遂犯,只是如何适用刑罚的问题。〔62〕一种观点认为,应按照重伤未遂处罚。理由是,按轻伤处罚不能反映行为人的主观恶性,难以达到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的要求。参见赵秉志:《犯罪未遂的理论和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 256-257 页。笔者则主张:“对于意图重伤但没有造成轻伤结果的,认定为故意伤害罪的未遂,适用第234 条第1 款的法定刑,同时适用关于未遂犯的规定。”张明楷:《故意伤害罪探疑》,载《中国法学》2001 年第3 期。“例如,对于出于重伤故意实施伤害行为但仅造成轻伤结果的,均认定为故意伤害(轻伤)罪既遂,适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的法定刑。倘若认为,对于以重伤故意实施伤害行为但没有造成伤害结果的,适用重伤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定刑,再适用刑法总则关于未遂犯的规定,则其处罚反而重于前者,因而明显不合适。”张明楷:《刑法学(下)》(第6 版),法律出版社2021 年版,第1126 页。
其次,存在重大争议的是《刑法》第234 条第1 款的轻伤害是否存在未遂犯。否定说认为:“故意轻伤的,不存在犯罪未遂的问题,即行为人主观上只想造成轻伤结果,而实际上未造成轻伤结果的,不以犯罪论处。这主要是考虑到:故意轻伤的情况下所成立的故意伤害罪属于轻罪,而对于轻罪的未遂行为,按照我国刑法典第13 条但书的基本精神,不宜承认其可罚性。”〔63〕王志祥:《故意伤害罪理论研究六十年》,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09 年第3 期。肯定说则认为,认为轻伤害不存在犯罪未遂没有任何法律根据,“在行为未至伤害的情况下,如果能够确凿地证明行为人具有伤害的故意,而且综合全部案情又不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是可以认定为《刑法》第234 条第1 款伤害罪的未遂而决定免予刑事处罚或者给予适当的处罚的;如果根本否定该款伤害罪有犯罪未遂,就失去了在必要的情况下把这种伤害行为认定为犯罪和处罚的任何可能”。〔64〕肖中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108 页。
笔者以往也采取否定说。〔65〕参见张明楷:《故意伤害罪探疑》,载《中国法学》2001 年第3 期。然而,随着刑事立法与司法现状的变化,以及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笔者主张《刑法》第234 条第1 款存在可能构成犯罪的未遂犯。换言之,对轻伤害未遂但存在具体危险、情节严重的,也应以未遂犯追究刑事责任。〔66〕参见张明楷:《刑法学(下)》(第6 版),法律出版社2021 年版,第1120 页。
关于故意伤害罪的未遂犯的处罚范围,〔67〕根据各国刑法的相关表述,在此不得不使用“处罚范围”一词。但这里的“处罚范围”并非给予刑罚处罚的范围,仍然只是成立范围。易言之,即使各国刑法明文规定处罚故意伤害罪的未遂犯,司法上也完全可能对之不起诉或者免予刑罚处罚。大体上存在以下四种立法例。
第一种立法例是,刑法总则规定未遂犯的处罚范围以刑法分则有明文规定为限,刑法分则没有规定处罚故意伤害罪的未遂犯,但对故意伤害罪的未遂犯大多以暴行罪论处。
例如,《日本刑法》第43 条规定了未遂犯的含义与处罚原则,第44 条规定:“处罚未遂的情形,由各本条规定。”其中的“本条”就是指规定具体犯罪与法定刑的分则性条文。《日本刑法》第235 条规定了盗窃罪的构成要件与法定刑(最高刑为10 年惩役),第243 条规定第235 条犯罪的未遂应当处罚。据此,盗窃未遂也构成盗窃罪。《日本刑法》第204 条规定了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与法定刑(最高刑为15 年惩役),但并没有规定处罚故意伤害罪的未遂。为什么法定刑重于盗窃罪的故意伤害罪反而没有规定处罚未遂犯呢?这是因为《日本刑法》第208 条规定了暴行罪:“实施暴行而没有伤害他人的,处二年以下惩役、三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拘留或者科料。”按照日本学者的观点,“由于实施暴行的结果达到伤害时成立伤害罪(第204 条),所以,暴行罪是没有达到伤害时而成立的犯罪。行为人以伤害的意思实施了暴行,但止于暴行时,虽然是伤害的未遂,但由于伤害罪的未遂不受处罚,故成立暴行罪”。〔68〕[日]山中敬一:《刑法各論》(第3 版),成文堂2015 年版,第38 页。这一说法可能产生的问题是,如果行为人仅有暴行的故意而没有伤害的故意,但造成他人伤害时,应当如何处理?“根据判例与通说,这种情形尽管没有伤害的故意但仍然成立伤害罪(现在已经不存在反对这一观点的见解)。对此可以作如下说明,亦即,伤害罪的规定与暴行罪的规定是基本法规与补充法规的关系。”〔69〕[日]井田良:《講義刑法学•各論》(第2 版),有斐閣2020 年版,第56-57 页。换言之,在行为人具有伤害的故意而实施伤害行为,但没有造成伤害结果时,就适用作为补充法规的暴行罪法条,而处罚暴行罪意味着处罚伤害未遂。〔70〕只有不能评价为暴行且没有造成伤害结果的行为,才不成立对身体的犯罪。参见浅田和茂:《刑法各論》,成文堂2021 年版,第40页以下。
第二种立法例是,未遂犯的处罚范围也必须由刑法总则或者分则明文规定,刑法分则明文规定处罚故意伤害罪的未遂犯。
例如,《德国刑法》第23 条第1 款规定:“重罪的未遂犯,罚之;轻罪的未遂犯的处罚,以有特别规定为限。”根据《德国刑法》第12 条,所谓重罪,是指法定刑最低刑为一年或一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轻罪,是指法定最低刑为未满一年有期徒刑或罚金之罪。《德国刑法》第223 条第1 款规定了普通伤害罪,法定刑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罚金”,据此,普通伤害罪属于轻罪。不过,《德国刑法》第223 条第2 款规定:“未遂犯罚之。”不难看出,德国刑法没有将暴行规定为独立的犯罪,〔71〕其实,《德国刑法》第223 条第1 款规定的伤害身体罪包括对身体的虐待。“根据德国司法判例,所谓对身体的虐待是指恶劣、不恰当、对身体安适和完整性造成并非微不足道之损害的行为。”王钢:《德国判例刑法(分则)》,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71 页。但明文规定处罚普通伤害罪的未遂犯。
《韩国刑法》第29 条也规定:“未遂犯之处罚,以有关条文有特别规定者为限。”第257 条第1 项规定了普通故意伤害罪,第2 项规定了尊亲属伤害罪,第3 项规定:“前二项的未遂犯,亦予处罚。”〔72〕[韩]金永哲译:《韩国刑法典及单行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第5 页、第41 页。
第三种立法例是,处罚所有的未遂,因而也处罚故意伤害罪的未遂犯。
例如,《西班牙刑法》第15 条第1 款规定:“既遂犯(el delitoconsumado)和未遂犯(el delitointentado)都应判处刑罚。”〔73〕潘灯译:《西班牙刑法典》,中国检察出版社2015 年版,第5 页。据此,故意伤害罪的未遂犯应受处罚。
第四种立法例是,虽然刑法总则规定表面上处罚所有的未遂犯,但事实上司法实践中只处罚部分未遂犯。
我国刑法并没有采取主观主义立场,需要肯定未遂犯处罚的例外性。所以,必须实质性考察各种具体故意犯罪的未遂形态的可罚性,换言之,应考察什么样的行为在未得逞的情况下,其行为的不法与责任达到了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进行这样的考察后,会发现以下三种情况:罪质严重的未遂应当以犯罪未遂论处,如故意杀人未遂、抢劫未遂、强奸未遂等;罪质一般的未遂,只有情节严重时,才能以犯罪未遂论处,如盗窃未遂、诈骗未遂等;罪质轻微的未遂不以犯罪论处,如非法侵入住宅未遂、侵犯通信自由未遂等。〔74〕参见张明楷:《刑法的基本立场》(修订版),商务印书馆2019 年版,第303 页。
例如,对于故意杀人、抢劫、强奸等罪质严重的犯罪,不需要司法解释的规定,司法机关均会处罚未遂犯。不仅如此,司法解释还明文规定了处罚组织偷越国(边)境罪、制造毒品罪的未遂犯。〔75〕参见2012 年12 月12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国(边)境管理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2]17 号);2008 年12 月1 日最高人民法院《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2008]324 号);2012 年6 月18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走私、非法买卖麻黄碱类复方制剂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12]12 号)。对于罪质轻微的未遂,司法解释均没有规定处罚未遂犯。对于罪质一般的犯罪,司法解释通常规定处罚情节严重的未遂犯。例如,2011 年3 月1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1]7 号)第5 条规定:“诈骗未遂,以数额巨大的财物为诈骗目标的,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应当定罪处罚。”2013 年4 月2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 条规定:“盗窃未遂,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以数额巨大的财物为盗窃目标的;(二)以珍贵文物为盗窃目标的;(三)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2018 年9 月28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盗窃油气、破坏油气设备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法释[2018]18 号)规定:“着手实施盗窃油气行为,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盗窃罪(未遂)追究刑事责任:(一)以数额巨大的油气为盗窃目标的;(二)已将油气装入包装物或者运输工具,达到‘数额较大’标准3 倍以上的;(三)携带盗油卡子、手摇钻、电钻、电焊枪等切割、打孔、撬砸、拆卸工具的;(四)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2019 年2 月20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生态环境部《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有关问题座谈会纪要》指出:“当前环境执法工作形势比较严峻,一些行为人拒不配合执法检查、接受检查时弄虚作假、故意逃避法律追究的情形时有发生,因此对于行为人已经着手实施非法排放、倾倒、处置有毒有害污染物的行为,由于有关部门查处或者其他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的情形,可以污染环境罪(未遂)追究刑事责任。”
与盗窃罪、诈骗罪、污染环境罪相比,故意伤害罪的罪质更为严重。一方面,从法定刑来看,故意伤害罪与盗窃罪、诈骗罪、污染环境罪的第一档法定刑的最高刑均为3 年有期徒刑,但就最低刑而言,故意伤害罪重于其他三个犯罪;故意伤害罪与盗窃罪、诈骗罪的第二档法定刑均为3 年以上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只是故意伤害罪没有规定附加刑,而污染环境罪的第二档法定刑则为3 年以上7 年以下有期徒刑;故意伤害罪的第三档法定刑则高于盗窃罪、诈骗罪与污染环境罪。这充分说明,从总体上说,故意伤害罪的不法程度并不轻于盗窃罪、诈骗罪与污染环境罪。另一方面,就侵犯个人法益犯罪的不法程度而言,故意伤害罪是仅次于故意杀人罪的犯罪。倘若让一般人在身受重伤与财产损失数额巨大之间选择,恐怕更多的人会选择后者。既然如此,就没有理由仅处罚盗窃罪、诈骗罪的未遂犯,而不处罚故意伤害罪的未遂犯。反过来说,只有处罚故意伤害罪的未遂犯,才能使刑法保持协调一致。
我国刑法虽然没有将暴行规定为独立的犯罪,但不能一概认为我国刑法不处罚暴行,而应认为我国刑法规定了特殊的暴行罪。例如,《刑法》第293 条规定的寻衅滋事罪中“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的情形,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暴行罪。更为重要的是,《刑法修正案(十一)》增加的第293 条之一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催收高利放贷等产生的非法债务,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一)使用暴力、胁迫方法的;……。”其中的“暴力”也是特殊的暴行罪。因此,在与暴行罪的关联性上,承认故意轻伤的未遂犯,是完全协调一致的。易言之,仅处罚特定情形下的暴行罪,会导致处罚的不公平。如果要实现处罚的公平性,就必须将故意轻伤害且存在具体危险、情节严重的未遂犯认定为犯罪。
从近几年来的司法实践来看,对于随意殴打他人没有造成轻伤的,大多会认定为寻衅滋事罪,所适用的法定刑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且按既遂犯处罚,导致处罚过于严厉。反之,如果承认故意轻伤的未遂犯,对行为以故意伤害罪的未遂犯处罚,适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的法定刑,同时适用未遂犯的规定,才更为合适。
或许有人认为,寻衅滋事罪的法定刑比轻伤害高,是因为该行为扰乱了公共秩序,并且,2013 年7月15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18 号)第1 条第1 款规定,“行为人为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横等,无事生非,实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的行为”。然而,这种观点会受到如下质疑。其一,在司法实践中,扰乱公共秩序的判断其实是虚无的,或者说是没有标准的。一个随意殴打他人的行为,也不可能现实地扰乱公共秩序。因此,一个在司法认定上纯属虚无的“公共秩序”不能成为增加暴行的不法程度的根据。更为重要的是,随意殴打他人侵害的是他人的身体,是对个人法益的侵犯。其二,《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 条第3 款规定,“行为人因婚恋、家庭、邻里、债务等纠纷,实施殴打、辱骂、恐吓他人或者毁损、占用他人财物等行为的,一般不认定为‘寻衅滋事’,但经有关部门批评制止或者处理、处罚后,继续实施前列行为,破坏社会秩序的除外”,但在近年来的司法实务中,许多因民间借贷纠纷引发的出借人索取债务行为被认定为“软暴力”,进而以寻衅滋事论处,并将其作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重要内容看待。这便使得上述《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 条第3 款的规定落空。〔76〕参见周光权:《刑事立法进展与司法展望——〈刑法修正案(十一)〉总置评》,载《法学》2021 年第1 期。显然,承认故意轻伤的未遂犯,就可以避免寻衅滋事罪的滥用,且有利于处罚的合理化。
下面笔者以个案为例进行说明。被告人肖某因对被害人方是民(笔名方舟子)和方玄昌进行的“学术打假”不满,为报复此二人,便花10 万元雇佣被告人戴某等人对被害人进行伤害。在戴某的组织下,被告人许某、龙某手持铁管、铁锤、喷射防卫器等先后对方玄昌和方是民进行殴打,并造成二人轻微伤的结果。该案中,被告人的故意内容、行为对象明确,犯罪预备行为充分,故意侵犯他人身体法益的行为性质十分明显。肖某在法庭上也宣称:“我就是故意伤害,不是寻衅滋事,我根本没想通过殴打两人,来让全国的质疑者闭嘴。我明明是要报复他们两个人才实施的故意伤害。”〔77〕《肖传国承认系故意报复对方舟子挨打表示遗憾》,https://news.qq.com/a/20101011/001440.htm,2021 年9 月10 日访问。然而,一审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肖某拘役五个半月,判处其他4 名被告人拘役五个半月到一个半月不等的刑期,二审法院也维持了原判。〔78〕参见高健:《肖传国案终审维持原判》,载《北京日报》2010 年11 月5 日,第7 版。可是,肖某等人的行为明显不符合寻衅滋事罪的本质特征与主观要素。将该行为认定为寻衅滋事罪,可谓对寻衅滋事罪的滥用。“难怪判决一出,舆情哗然,甚至非法律专业的普通人都觉得匪夷所思。蓄意雇凶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怎么‘质变’成了寻衅滋事罪了呢?”〔79〕沈海平:《定罪:依据危害行为还是危害结果——对肖传国案件的思考》,载《人民检察》2010 年第23 期。显然,如果将故意伤害罪的结果要素扩大到轻微伤,或者承认故意伤害罪的未遂犯,就可以妥当地将肖某等人的行为认定为故意伤害罪的既遂犯或者未遂犯;如果仅将结果要素扩大到轻微伤,而不承认故意伤害的未遂犯,若该案未造成轻微伤,则仍然不能妥当处理该案及类似案件。
此外,将故意轻伤未遂的行为认定为寻衅滋事罪,其实是将对个人法益的犯罪认定为对社会法益的犯罪。通过将某种行为认定为侵害公法益的犯罪来保护个人法益,并不是可行的路径。因为这种路径常常导致行为侵害数人的个人法益才成立犯罪,这便不利于保护公民的身体法益与其他个人法益。并且,这种做法必然侵害被害人的诉讼参与权利,也不利于附带民事诉讼。
或许有人认为,如果认为故意轻伤的未遂犯也成立犯罪,就明显扩大了处罚范围。然而,犯罪的成立范围并非越窄越好,而是越合理越好。从前面与盗窃未遂、诈骗未遂的比较可以看出,肯定故意轻伤的未遂犯,并没有明显地扩大处罚范围。并且,如前所述,犯罪的成立范围与处罚范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肯定故意轻伤的未遂犯,并不意味着对这些未遂犯均给予刑罚处罚,完全可能相对不起诉、免予刑罚处罚或者适用缓刑。更为重要的是,肯定故意轻伤的未遂犯有利于实现一般预防目的,并有效地保护一般人的身体法益。因为如所周知,针对被害人身体的暴力行为,所造成的伤害程度具有偶然性。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可能以为自己不会造成他人轻伤而实施暴力,却致人重伤或者轻伤。如果只有造成了伤害结果才成立犯罪,就会导致一些人抱着侥幸心理实施伤害行为,难以预防犯罪。肯定故意致人轻伤的未遂成立犯罪,则能有效地规制一般人的暴力行为,进而保护被害人的身体法益。
当然,主张对故意致人轻伤的未遂成立故意伤害罪,并非没有任何限定。在刑法没有规定独立的暴行罪的立法例之下,《刑法》第234 条第1 款规定的故意伤害罪不可能成为结果加重犯。换言之,成立故意伤害罪要求行为人实施了伤害行为,并且具有伤害的故意。所以,成立故意轻伤的未遂犯,首先要求行为人客观上实施了足以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或者说,行为人所实施的客观行为足以给他人造成伤害结果(具体危险)。其次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造成伤害结果的故意。如果行为人仅具有使他人身体遭受暂时疼痛的故意,则不可能成立故意伤害的未遂犯。
在具备上述要素的前提下,还要求未遂行为本身情节严重。如前所述,较早关于处罚盗窃、诈骗未遂的司法解释,一般仅限于以盗窃、诈骗数额巨大财物为目的而未遂的情形。虽然司法解释中也有“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的规定,但下级司法机关一般不会轻易适用这一规定。依此类比,似乎只有以造成重伤为目的的伤害未遂,才能以故意伤害罪的未遂犯处罚。然而,近年来的司法解释明确扩大了未遂犯的成立范围。例如,《关于办理盗窃油气、破坏油气设备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对携带特殊工具盗窃油气未遂的,也以盗窃罪的未遂犯处罚。〔80〕1998 年11 月27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关于保险诈骗未遂能否按犯罪处理问题的答复》指出:“行为人已经着手实施保险诈骗行为,但由于其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获得保险赔偿的,是诈骗未遂,情节严重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笔者看来,故意伤害他人未遂,除以重伤为目的的情形以外,具备下述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进而以故意伤害罪的未遂犯论处:(1)携带或者使用凶器或者其他危险工具伤害他人的;(2)使用毒药或者其他危险物质伤害他人的:(3)对被害人身体的重要部位(如头部、胸部、腹部)实施伤害行为的;(4)暴力行为强度大或者连续反复使用暴力的;(5)以阴险的袭击方式实施伤害行为的;(6)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伤害行为的;(7)多次对同一人实施伤害行为的;(8)行为具有造成重伤害的危险的。
或许有人认为,笔者于本文中列举的情节严重情形其实就是故意致人重伤而未遂的情形,既然如此,只需要对具有重伤故意而未遂的情形认定为故意伤害罪的未遂犯即可。然而,在笔者看来,这一观点不仅导致对故意伤害未遂可能一概适用重伤害的法定刑,而且难以具有操作性,甚至会诱发刑讯逼供。正如林山田所言:“在理论上……轻伤故意与重伤故意,轻易可以界分清楚,但在刑法实务上,认定行为人究系出于轻伤故意,抑系出于重伤故意,实则困难重重。……况且,避重就轻乃人情之常,在公判庭上的被告,若稍具刑法常识,或稍经法律人指点,亦均会倾向轻伤故意的主观心态的陈述,希冀得以规避重伤罪而获轻伤罪。”〔81〕林山田:《刑法各罪论》(第六版)(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89 页。如果司法工作人员经由客观可见的行为结果,推断行为人的故意内容,那么,在没有发生结果时推断就难以进行;如果司法工作人员经由口供判断行为人的故意内容,则容易导致刑讯逼供。更为重要的是,关于《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不仅普通老百姓不知为何物,就是我们这些所谓刑法学者大概也就知道‘切掉小指头的是轻伤,切掉大指头的是重伤’这一点,能大致搞清楚的大概就只有法医了,就是法医恐怕不认真对照相关规定,也难以分清”,〔82〕杜文俊:《故意伤害罪的二重的结果加重犯性质探究——以故意伤害罪的比较法为视角》,载《政治与法律》2008 年第9 期。行为人就更难知道自己所想要造成的伤害究竟是重伤还是轻伤了。既然如此,单纯以行为人具有何种伤害故意为标准区分故意伤害罪的未遂犯的成立与否,就不具有可行性。反过来说,通过客观行为的情节严重与否判断故意伤害罪的未遂犯的成立范围,才具有合理性与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