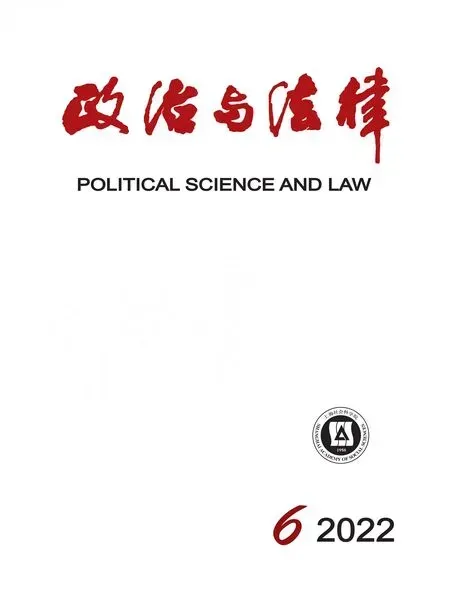轮奸涉及的若干争议问题剖析
刘明祥
(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北京 100872)
近些年来,我国一些学者运用区分正犯与共犯的区分制理论,解释我国刑法关于轮奸的处罚规定,导致刑法学界出现了一些新的相关争议问题。笔者拟从我国刑法采取不区分正犯与共犯的单一正犯体系的立场出发,〔1〕参见阮齐林、耿佳宁:《中国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9 年版,第221 页;刘明祥:《再论我国刑法采取的犯罪参与体系》,载《法学评论》2021 年第4 期。运用单一正犯的解释论,对轮奸涉及的若干争议问题进行剖析,期望能对这些争议予以澄清。
一、有责任能力的人与无责任能力的人轮流奸淫妇女能否成立轮奸
关于有责任能力的人与无责任能力的人共同轮流强行奸淫妇女(含幼女)能否成立轮奸,理论和实务界存在肯定与否定两种不同主张。否定论是传统的通说,其产生的背景是,我国1979 年《刑法》第139 条第4 款规定,“二人以上犯强奸罪而共同轮奸的,从重处罚”,其中的“轮奸”之前有“共同”二字,而“轮奸”又是严重的强奸犯罪,因此,在1979 年《刑法》施行时期,大多认为“所谓轮奸,是共同犯罪的一种形式,一般是指两个以上男子在相隔短暂的时间内,先后轮流强奸同一妇女”。〔2〕高铭暄主编:《中国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第466 页。按通说,共同犯罪以两个以上具有责任能力的人基于共同故意而犯罪为成立条件,据此,一个有责任能力的人与一个无责任能力的人共同强奸妇女,不可能构成共同犯罪,从而也不可能成立轮奸。〔3〕参见王作富主编:《刑法分则实务研究(上册)》,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 年版,第906 页。肯定论则分为两种不同的主张。一种是从传统的共同犯罪论的立场提出的“共同奸淫类型说”,认为轮奸是二人以上共同对同一妇女先后连续、轮流地实施了奸淫行为的强奸犯罪类型。由于轮奸仅是一种共同的事实行为,只要行为人具有强行奸淫的共同认识,并在共同认识的支配下实施了轮流奸淫行为即可,而与是否构成共同犯罪并无必然关系,因而不要求参与者均有刑事责任能力,即便是一个有责任能力的人与一个无责任能力的人共同强行轮流奸淫同一妇女,也成立轮奸。〔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第二庭编:《刑事审判参考》(总第36 集),法律出版社2004 年版,第27 页以下。另一种是从区分正犯与共犯的区分制体系立场提出的“共同犯罪是违法形态说”,认为“由于共同犯罪是违法形态,而责任能力是责任要素,不影响违法性的认定,所以,有责任能力者与无责任能力者,也可能成立共同犯罪。”如“十六周岁的甲与十三周岁的乙共同轮奸妇女丙……即属于轮奸”,甲与乙成立共同犯罪(或共同正犯)。只是因为乙没有责任能力而不对之定罪量刑,对甲则应适用轮奸的法定刑。〔5〕参见张明楷:《共同犯罪是违法形态》,载《人民检察》2010 年第13 期。
在笔者看来,以上分歧的产生,或许是因为立论者对我国刑法采取的犯罪参与体系的认识不一,或者说是采取了不同犯罪参与体系的解释路径。其中,立足于传统的共同犯罪观念者,无论是得出上述肯定还是否定的结论,由于都是严格按文字本义来理解我国《刑法》第25 条对共同犯罪概念或成立要件的规定,实际上不自觉地采取了单一正犯的解释路径。〔6〕参见刘明祥:《论犯罪参与的共同性:以单一正犯体系为中心》,载《中国法学》2021 年第6 期。并且,按单一正犯的解释论,将上述有责任能力人与无责任能力人共同轮流强奸妇女,解释为成立或不成立刑法关于强奸罪规定中的“轮奸”,均存在一定的空间或余地。如上所述,在1979 年《刑法》施行时期,因法条中有“二人以上犯强奸罪而共同轮奸”的表述,将“共同轮奸”解释为共同犯罪,把无责任能力者排除在轮奸的主体范围之外(即不可能与他人一起构成“共同轮奸”),无疑有其合理性。现行刑法采用的是“二人以上轮奸”的表述,既然“轮奸”之前已无“共同”的限定词,那么,将“轮奸”解释为一种共同的事实行为,即共同强行轮流奸淫妇女,无责任能力者虽不能与他人构成共同犯罪,但事实上可能与他人一起共同强行轮流奸淫妇女,构成“轮奸”,只是不承担刑事责任而已,这样的解释似乎也有道理。
肯定论中的“共同犯罪是违法形态说”是以我国刑法采取区分制的犯罪参与体系为基本立足点,同时运用日本流行的共犯或共同正犯是违法形态的观念,来解释我国刑法规定的共同犯罪,认为只要参与者之间有违法行为的共同,共同犯罪即告成立。并且,把对“轮奸”的解释作为实例,认为按我国传统的共同犯罪观念,16 周岁的甲与13 周岁的乙共同轮奸妇女丙,因乙未达到法定负刑事责任年龄,不能与甲构成共同犯罪,不成立轮奸,对16 周岁的甲不适用轮奸的法定刑,明显不具有合理性。然而,只要认识到共同犯罪是一种违法形态,就会得出二人成立共同犯罪或共同正犯即属于轮奸的结论,即使乙没有达到责任年龄,对甲也要以轮奸论处。〔7〕参见张明楷:《共同犯罪的认定方法》,载《法学研究》2014 年第3 期。笔者也不否定,按传统的共同犯罪理论,否定有责任能力的人与无责任能力的人可能成立轮奸,对有责任能力的人也只适用普通强奸罪的法定刑,这确实不具有合理性。因为如果与无责任能力的人共同轮流强奸妇女,同与有责任能力的人共同轮流强奸妇女相比,前者的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性通常大于后者,但按传统的否定论,对前者不能认定为轮奸,处罚会明显轻于后者。这显然不合情理与法理,既不利于打击犯罪分子,也不能有力地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有违立法本意。〔8〕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第二庭编:《刑事审判参考》(总第36 集),法律出版社2004 年版,第27 页以下。
持“共同犯罪是违法形态说”的论者看到了传统否定论的这一缺陷,敏锐地指出:“刑法之所以对轮奸加重刑罚,不仅因为被害人连续遭受了强奸,而且还因为共同轮奸的行为人,既要对自己的奸淫行为与结果承担责任,也要对他人的奸淫行为与结果承担责任。”〔9〕张明楷:《刑法学(下)》(第六版),法律出版社2021 年版,第1140 页。因而,应当采取肯定论。在笔者看来,这固然应予充分肯定,但运用区分制体系的解释论,将我国刑法中的共同犯罪解释为违法形态,不要求共同犯罪人具有责任能力,则不具有合理性。因为并非只有将有责任能力的人与无责任能力的人共同实施的违法行为解释为共同犯罪或共同正犯,才能使有责任能力的人对无责任能力的人实施的行为及其结果也承担责任。事实上,按单一正犯的解释论,每个有责任能力的共同参与犯罪者,不仅要对自己实施的行为及直接造成的结果负责,而且对其他参与犯罪者(包含无责任能力者)与自己共同实施的行为及其结果,也要承担责任,这与双方之间是否成立共同犯罪并无直接关系。如有责任能力的A 与无责任能力的B 共同杀害自己的仇人C,A 将C 推倒按压在地上后,指使B 用木棒猛击C 头部,致C 死亡。此例中的A 与B 虽然是共同参与(实行)杀人犯罪,但B 是无责任能力的人,不具备共同犯罪的主体条件,因而双方不构成共同犯罪,B 依法不负刑事责任,A 不仅构成故意杀人罪,而且还应对B 直接造成的C 死亡的结果负责,要按故意杀人既遂处罚。基于同样的理由,上述16 周岁的甲与13 周岁的乙共同轮奸妇女丙的案例中,甲与乙虽然不构成强奸罪的共同犯罪,但双方无疑属于共同参与(实行)犯罪,有责任能力的甲除了对自己强奸丙的行为应承担责任之外,对自己与乙合作且乙强奸了丙的结果也应负责,即并非是单独强奸而是共同轮奸,因此,对甲应适用轮奸的法定刑处罚,乙因未达到法定负刑事责任年龄而不受刑事处罚。这样处理,既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又能满足司法实践上合理处罚的要求,且与我国《刑法》第25 条的规定相符。
有站在共同犯罪是违法形态或区分制体系立场解释我国刑法中的共同犯罪的论者提出:“如果由于部分轮奸者欠缺责任能力否定了共同犯罪,却又承认所谓的共同事实行为,而且同样可以贯彻‘部分行为全部责任’的法理成立轮奸,则如此区分的实质意义何在难免令人起疑。”〔10〕何庆仁:《共犯论领域阶层思考的现实意义》,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 年第6 期。笔者认为,按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必须区分“共同犯罪”与仅有“共同事实行为”即可成立的“共同参与犯罪”,并且这种区分对参与者的定罪和处罚有重要意义。这是因为我国现行刑法采取单一正犯体系,如上所述,按单一正犯理论,各个共同参与犯罪者不仅要对自己实施的行为与直接引起的结果负责,而且还要对其他参与者共同实施的行为及其结果负责,这一归责原理与区分制体系对共同正犯所采取的“部分行为全部责任”的原则具有相似性。但是数人共同参与犯罪的范围很广,除了共同故意犯罪之外,还包含双方出于不同故意、一方基于故意另一方出于过失、双方均为过失、一方有责任能力另一方无责任能力等多种类型。〔11〕参见刘明祥:《论犯罪参与的共同性:以单一正犯体系为中心》,载《中国法学》2021 年第6 期。我国《刑法》 第25 条的规定表明,我国的“共同犯罪”仅限于数人“共同参与犯罪”之中共同故意犯罪这一特定的类型。按通说对该条规定的解释,共同犯罪的主体必须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12〕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第九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年版,第160 页。因此,否定有责任能力者与无责任能力者共同轮奸妇女构成共同犯罪,但肯定双方为“共同参与犯罪”,责令有责任能力的参与者对无责任能力参与者与自己共同轮奸妇女的结果负责,就是按单一正犯解释论所得出的毋庸置疑的合理结论。
相反,按上述“共同犯罪是违法形态说”,将我国刑法中的共同犯罪解释为违法形态,以无责任能力者共同参与实行的强奸行为也具有违法性,有责任能力者与之共同实行的行为虽然不构成归责含义上(或“完全意义上”)的共同犯罪,但成立违法意义上的共同犯罪或共同正犯,从而适用“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原则,责令有责任能力者对无责任能力者参与强奸妇女的行为与结果也承担责任。应当肯定,在采取区分制体系的德、日等国,这样解释也无可非议。然而,我国刑法采取单一正犯体系,在按上述单一正犯解释论也能得出同样处理结论的条件下,“共同犯罪是违法形态说”的这种解释不仅显得多余,而且与我国《刑法》第25 条的规定明显不符。从我国《刑法》第25 条规定共同犯罪的概念或成立要件、第26 条至第29 条分别规定对共同犯罪人如何处罚不难看出,第25 条“共同犯罪”中的“犯罪”,显然是符合犯罪成立所有要件意义上的“犯罪”,不可能是仅具备犯罪成立的违法性要件而不具备有责性要件的所谓违法形态的“犯罪”,否则,后面几个条文关于对犯罪人如何处罚的规定就会失去存在的基础与前提。也就是说,对不成立犯罪者,不可能对其予以刑事处罚;对构成犯罪者,也不可能不追究刑事责任。刑法规定对无责任能力者不给予刑事处罚,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上述共同轮奸妇女的无责任能力者(13 周岁的乙),不可能与有责任能力者(16 周岁的甲)构成强奸的共同犯罪。如果按“共同犯罪是违法形态说”,肯定共同轮奸妇女的甲与乙成立强奸罪的共同犯罪,那么,按我国刑法的规定,就必须分别确定为主犯或从犯(含胁从犯)并适用相关规定予以处罚。假如认定乙为主犯、甲为从犯,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未达到负刑事责任年龄不应受刑事处罚的人,因“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成为主犯却不被处罚,而对“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的甲,却无法按司法惯例比照主犯乙去“从轻、减轻处罚”;假如认定乙为从犯、甲为主犯,则按司法惯例应对乙比照甲“从轻、减轻处罚”,而乙依法本来不应受刑事处罚,当然毋庸享受这样的“从宽”处罚的待遇。可见,无论是将不负刑事责任的乙认定为共同犯罪中的主犯还是从犯,或者肯定乙与甲构成共同犯罪,却既不认定其为主犯也不认定其为从犯(含胁从犯),均与我国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明显不符。
二、对轮奸能否采用共同正犯的认定和处罚规则
目前,主张我国刑法采取区分正犯与共犯的区分制体系的论者,大多认为轮奸是强奸的共同正犯类型或形态(以下简称:“共同正犯类型说”),因而,应运用共同正犯的原理来认定和处理轮奸案件。〔13〕参见张明楷:《刑法学(下)》(第六版),法律出版社2021 年版,第1140 页。然而,如前所述,我国刑法并非是采取区分制体系,并无对共同正犯如何处罚的规定。〔14〕参见刘明祥:《单一正犯视角下的共同正犯问题》,载《中外法学》2019 年第1 期。尽管采取区分制体系的德、日刑法所规定的“二人以上共同实行犯罪”即共同正犯的现象,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也经常出现,但按我国刑法的规定,这类案件中只有基于共同故意而共同实行犯罪者,才成立共同犯罪,对这类共同犯罪(即德、日刑法中的部分共同正犯)与其他类型的共同犯罪(即德、日刑法中含教唆犯、帮助犯的共犯),采取同样的处罚规则,也就是分为主犯与从犯(含胁从犯),给予轻重有别的处罚。我国《刑法》第236 条第3 款第4 项作为一种加重犯予以规定的“二人以上轮奸”,虽然也是二人以上共同实行强奸,即属于德、日刑法中的强奸的共同正犯的情形,但我国刑法采取不同于区分制体系的单一正犯体系,所以,不能采取区分制体系中的共同正犯的认定和处罚规则,来处理我国的轮奸案件。
第一,按“共同正犯类型说”,轮奸既然是强奸的共同正犯类型,其现在的通说认为,共同正犯除了二人以上均参与实施实行行为的“实行共同正犯”之外,还包含仅参与共谋而未分担实行行为的所谓“共谋共同正犯”,那么,轮奸也不例外,同样存在共谋共同正犯的情形。〔15〕参见张明楷:《性犯罪的争议问题》,载《第六届中日刑事法研讨会暨中日刑法总论及分论中的先端课题研讨会论文集》,第159-160页。转引自林贵文:《“轮奸”成立学说的法教义学批判与证成》,载《法律科学》2019 年第6 期。然而,“如果认为轮奸存在共谋共同正犯,则二人共谋轮奸,一人共谋而未参与实行,仅由另一人实施,若也论以轮奸,显然过于扩大处罚范围”。〔16〕张明楷:《性犯罪的争议问题》,载《第六届中日刑事法研讨会暨中日刑法总论及分论中的先端课题研讨会论文集》,第159-160 页。转引自林贵文:《“轮奸”成立学说的法教义学批判与证成》,载《法律科学》2019 年第6 期。因为刑法规定的“二人以上轮奸”,显然是指二人以上轮流奸淫。二人共谋由其中一人去奸淫,无疑不能称之为“轮奸”,此种二人参与的强奸犯罪,同一人在幕后教唆或帮助另一人实行强奸的共同犯罪案件,并无多大差异,且对被害人性自主权的侵害程度,与普通的单独强奸犯罪也并无不同,因而没有将其纳入加重犯的范围给予比普通犯重得多的处罚的必要性。正因为如此,有论者提出应将其限缩在二人以上轮奸的基础上的共谋共同正犯范围内,即“至少有三人意图轮奸,其中一人共同谋议而未到犯罪现场”。〔17〕张明楷:《性犯罪的争议问题》,载《第六届中日刑事法研讨会暨中日刑法总论及分论中的先端课题研讨会论文集》,第159-160 页。转引自林贵文:《“轮奸”成立学说的法教义学批判与证成》,载《法律科学》2019 年第6 期。这种三人以上意图轮奸,且确实有二人连续轮流奸淫了同一妇女的,由于“二人以上轮奸”的事实已发生,对直接实行了轮奸行为的“轮奸者”,固然要适用轮奸的法定刑处罚,但对仅参与谋议而未实行奸淫行为的“共谋者”,按共谋共同正犯理论,将其认定为共同正犯(即共谋共同正犯),同样适用轮奸的法定刑,则不具有合理性。因为共谋者可能并未到奸淫现场去,即便是出现在奸淫现场,若并未直接实行奸淫行为,就意味着其事实上并未成为“轮奸者”(即连续轮流实行奸淫行为者)。我国刑法规定的“轮奸是强奸罪的加重处罚情节,不是独立罪名”。〔18〕黎宏:《刑法学各论》(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16 年版,第236 页。对共同犯强奸罪的参与者,适用加重犯的法定刑时,同样应以参与者个人是否具备加重情节为前提,而不能以其他参与者具备加重情节作为对同案参与者也适用加重犯法定刑的根据。例如,A 知B 好色,于是教唆其强奸自己仇人的女儿C。案发后查明,B 不仅强奸了C,而且还强奸了D 和E,具有强奸妇女多人的情节。对B 无疑要适用强奸罪加重犯的法定刑处罚,教唆者A 虽与B 构成强奸罪的共同犯罪,但对其只能适用强奸罪普通犯的法定刑。
第二,按“共同正犯类型说”,由于强奸罪被公认为是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相结合而形成的复行为犯,行为人开始实施暴力、胁迫等强制性的手段行为,通说就认为是已着手实行强奸行为,〔19〕付立庆教授最近提出,暴力、胁迫等手段行为是强奸罪的预备行为,只有奸淫行为才是其实行行为。参见付立庆:《论轮奸的限制性认定》,载《法学》2020 年第4 期。笔者不赞成此种主张。在二人以上共同强奸的场合,仅对被害人实施暴力、胁迫行为而不实施奸淫行为者,也可能成为强奸罪的共同正犯。众所周知,妇女虽然不能实行强奸罪的目的行为(即奸淫行为),但却可以实行暴力、胁迫等强奸罪的手段行为。因此,按区分制体系的共同正犯理论,妇女可以成为强奸罪的共同正犯。然而,这种共同正犯人明显不能成为轮奸行为的实行者,即不能成为轮奸者。事实上,“轮奸中行为的共同指的是奸淫行为的共同,并不包含奸淫行为与强制行为或奸淫行为与其他正犯行为的共同。……轮奸的实行与强奸的实行是有重要区别的,共同正犯类型说将二者相混淆”,〔20〕刘国平:《轮奸认定中的三个误区》,载《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9 年第5 期。甚至把强奸的共同正犯与轮奸等同起来,这明显不妥当。如果把区分制体系下的强奸的共同正犯均认定为轮奸,显然会不适当地扩大轮奸的范围,加重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因为“只有二个以上行为人且都实际实施奸淫行为的,才是‘轮奸’。即‘轮奸’是事实,而非构成要件。只有一人实施强奸而其他参与者没有实际实施性交行为,例如实施了暴力(按着手脚)、胁迫行为,虽为共同犯罪,但不能认定为‘轮奸’”。〔21〕林亚刚:《刑法学教义(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年版,第38 页。也就是说,对仅实施暴力、胁迫行为(在德、日应被认定为强奸的共同正犯),按我国刑法的规定,不能认定为轮奸,从而适用强奸罪加重犯的法定刑,而只能认定为普通强奸罪,适用普通犯的法定刑。
第三,日本2004 年修改刑法时增设了集团强奸罪,即“二人以上当场共同犯强奸罪或者准强奸罪的”,作为此类犯罪的加重类型,规定了更重的法定刑。〔22〕参见[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各论》(第三版),刘明祥、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76 页。日本已于2017 年删除了该规定。日本学者一般认为,集团强奸罪“是将现场实施的强奸罪、准强奸罪的共同正犯予以单独规定的犯罪类型,并且,还可成立共谋共同正犯、教唆犯或者帮助犯”。〔23〕[日]山口厚:《刑法各论》,弘文堂2010 年版,第113 页。由于这种犯罪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二人以上共同轮奸,给人的印象是日本的通说认为,强奸案中的共谋共同正犯、教唆犯和帮助犯均可能成立轮奸。可能是受这种观念的影响,我国一些认为轮奸是强奸罪的共同正犯类型的论者,也认为强奸共同犯罪案件中,未实施奸淫行为,仅参与共谋或教唆、帮助他人强行奸淫妇女的,可能成为强奸的共同正犯(即轮奸),对其也应适用轮奸的法定刑予以处罚。如有论者认为:“由于轮奸是共同正犯,故通常均属于主犯,但也存在例外。例如,X、Y 共谋轮奸妇女,Z 知情后将被害人骗到现场但自己不参与轮奸行为的,对Z 仍然适用轮奸的法定刑,但应认定为轮奸的从犯。”〔24〕张明楷:《刑法学(下)》(第五版),法律出版社2016 年版,第874 页。黎宏教授也认为,一个妇女帮助两个男子强奸的,构成轮奸。参见黎宏:《刑法学各论》(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16 年版,第236 页。此例中“自己不参与轮奸行为”的Z,显然只是帮助X、Y 轮奸妇女,属于帮助犯,把这种帮助犯认定为轮奸的共犯,适用轮奸的法定刑,在单独设立集团强奸罪或加重强制性交罪的日本,无疑有其合理性。因为Z 尽管只是帮助X、Y 轮奸,却仍然是与X、Y 共同犯集团强奸罪或加重强制性交罪,要适用这种加重类型犯罪的法定刑,但并不意味着Z 成立这种犯罪的共同正犯,〔25〕有学者明确指出,教唆犯和帮助犯,不在加重强制性交罪的共同正犯之列。参见黄仲夫:《刑法精义》,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6 年版,第574 页。与X、Y 一样以此罪的正犯之刑处罚,而是应认定为帮助犯,按正犯之刑予以减轻处罚。举出上述例子的论者认为Z“应认定为轮奸的从犯”,也印证了不能认定Z 为轮奸的共同正犯,否则,就不能认定Z 为轮奸的从犯。这从一个侧面表明,认为我国刑法中的轮奸是强奸的共同正犯类型的主张,即便按区分制体系的共同正犯观念,也不具有合理性。况且,我国刑法中的轮奸“不是一个独立的罪名”,也不是像日本刑法那样,将其包容在独立的加重类型的强奸犯罪之中,而“是强奸罪加重法定刑的法定情节”,〔26〕马克昌主编:《百罪通论(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548 页。纳入加重犯,适用较重的法定刑。一般来说,没有规定为独立犯罪仍在同一犯罪之中的加重犯,尽管刑法规定了比普通犯更重的法定刑,但适用的条件应该严格限制在加重事实或情节完全具备的情形下,否则,只能适用普通犯的法定刑。就仅参与共谋或教唆、帮助他人轮奸而“自己不参与轮奸行为”的情形而言,由于行为人不是轮奸者,本身不具有轮奸的事实或情节,按我国刑法的规定,只能适用普通强奸罪的法定刑,不能适用轮奸的法定刑;而在轮奸被纳入独立的集团强奸罪或加重强制性交罪的日本,则应适用这种加重类型强奸犯罪的法定刑,只不过对帮助犯,应按正犯之刑予以减轻处罚。如前所述,刑法对同一犯罪中因具备严重情节而规定更重法定刑的,应以行为人本人具备严重情节作为适用的条件,在共同犯罪的场合也不例外,不能以其他共同参与人具备加重情节,作为对自己本人不具备加重情节的参与者,也适用加重犯法定刑的依据或理由。
第四,如果说轮奸是强奸罪的共同正犯类型,即便是将强奸罪的实行行为限定在奸淫行为的范围内,〔27〕参见付立庆:《论轮奸的限制性认定》,载《法学》2020 年第4 期。或者说轮奸是强奸罪中的一种特殊的共同正犯,仅限于二人以上强制性的连续实行奸淫同一被害人的情形,只实施暴力(如按压被害人手脚等)、胁迫行为而不奸淫的,不成立强奸罪的共同正犯。然而,若二人以上意图轮奸,只有一人成功奸入或已完成奸淫行为、其他人未奸入或未完成奸淫行为的,能否认定所有参与者均成立这种所谓特殊类型的共同正犯(即轮奸),仍无法得出合理的结论。例如,被告人许某、刘某、向某于某日深夜发现女青年宋某独自走出一酒吧,便将其挟持到许某独居的房屋内。许某强行与宋某发生性关系后,刘某实施奸淫行为时,因性功能出现障碍未奸入;向某实施奸淫行为时,因被害人极力反抗未得逞。对于此案,有一种观点认为,“刘某、向某与许某之间存在共同正犯关系。根据对共同正犯所采用的‘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原则,刘某、向某不仅要对自己的行为及结果负责,还要对许某的行为及其结果负责”;“许某的奸淫行为已达到既遂状态,因而,虽然刘某、向某的奸淫行为没有完成,但这并不影响轮奸的成立,而且,许某、刘某、项某的行为均属于轮奸既遂”。〔28〕王志祥:《共同实施强奸仅一人得逞,应如何定性》,载《中国检察官》2008 年第9 期。应当肯定,按共同正犯的认定和处理规则,确实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所谓共同正犯,是指二人以上共同实行犯罪的情形。上例中的三个被告人均实行了奸淫行为,只是其中有二人未完成或未奸入,但按共同正犯的认定规则,这不影响共同正犯的成立。如同三人约定一起投石子砸伤被害人,都对其投了石子但仅一人所投石子击中并致伤被害人,这同样不影响故意伤害罪共同正犯的成立。并且,根据“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共同正犯的归责原理,对三人均要按故意伤害(既遂)罪处罚。基于同样的理由,对上述强奸案中的三被告人,也均要以轮奸既遂论处。问题在于,司法实践中,二人以上共同实行犯罪(即区分制体系下的共同正犯)的现象很普遍,刑法规定的绝大多数罪都有可能由二人以上共同实行,故意伤害、抢劫等许多犯罪,都存在这种所谓共同正犯现象。不过,刑法并未将伤害的共同正犯、抢劫的共同正犯等,作为这些犯罪的加重犯规定更重的法定刑。“同样是共同正犯,为何唯独强奸的共同正犯加重处罚,甚至配置无期徒刑和死刑”,〔29〕付立庆:《论轮奸的限制性认定》,载《法学》2020 年第4 期。这显然是主张轮奸为强奸罪的共同正犯类型的论者无法圆满回答的。或许是基于此种考虑,可能意识到应对轮奸的处罚范围予以限制,有论者提出,在有多人意欲轮奸的场合,至少要有二人完成了奸淫行为,才能成立轮奸,其余未奸入或未完成者,由于属于共同正犯,按“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归责原理,也应适用轮奸这种加重犯的法定刑;但如果只有一人完成奸淫行为,其余均未奸入或未完成奸淫行为的,则不构成轮奸,对所有参与者还是只能适用强奸罪普通犯的法定刑。〔30〕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 年版,第782-783 页。张明楷教授在此书第五版中已不再坚持此种主张。这种主张尽管对轮奸的处罚范围略有限制,但不能合理解释在多人已着手实行奸淫行为,强奸的特殊共同正犯已经成立的条件下,为何还必须要有二人完成奸淫行为,才成立轮奸,一人已完成奸淫行为的,却不成立轮奸。按形式逻辑的规则推论,既然轮奸是强奸的特殊共同正犯类型,这种特殊共同正犯的条件一旦具备,也就意味着轮奸成立,若这种特殊共同正犯成立而轮奸不成立,那就表明将轮奸解释为强奸罪的特殊共同正犯类型并不合适。况且,对同案中的未奸入或未完成奸淫行为的参与者而言,其所实施的行为及在案件中所发挥的作用可能并无差异,却在其他同案犯中是一人还是二人完成奸淫行为的场合,要分别适用轻重有重大差异的法定刑,这样处理的合理性也令人怀疑。事实上,在意欲轮奸的二个以上的参与者均实施了奸淫行为但都未奸入或未完成奸淫行为的场合,按上述“共同正犯类型说”,均认定为轮奸,则可避免出现这种处罚不合理现象的发生,也可与共同正犯的认定规则保持一致。这可能也是上述持“二人以上完成奸淫行为”为强奸的共同正犯(即轮奸)成立的论者现在改采此种主张的原因。〔31〕参见张明楷:《刑法学(下)》(第六版),法律出版社2021 年版,第1141 页。然而,如前所述,这种主张与我国刑法对轮奸的处罚规定不符,并且会导致轮奸处罚范围的扩大化,不适当地加重对强奸罪的共犯人的处罚。
第五,我国刑法对轮奸者明显没有采取区分制体系规定共同正犯的处罚规则。德、日等采取区分制体系的刑法均规定,对二人以上共同实行犯罪的“各人皆依正犯处罚”,同案中的所有共同正犯人的处罚轻重原则上相同。如果说我国刑法采取德、日刑法那样的区分制体系,轮奸又是强奸罪的共同正犯类型,那么,对同案中的所有轮奸者就应适用轮奸的法定刑,给予轻重相同的处罚。然而,按我国刑法的规定,对同案中的所有轮奸者并非是都以正犯之刑给予轻重相同的处罚,而是应根据其在共同强奸犯罪中所起作用的大小,分为主犯或从犯给予轻重有别的处罚。如前所述,持“共同正犯类型说”的论者也认为,“由于轮奸是共同正犯,故通常属于主犯,……但应认定为轮奸的从犯”的情形也存在。〔32〕张明楷:《刑法学(下)》(第五版),法律出版社2016 年版,第875 页。对轮奸的从犯,按我国《刑法》第27 条第2 款的规定,“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也就是以所犯之罪的通常之刑(或单独正犯之刑)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而不是依正犯之刑处罚。在区分制的体系下,正犯是犯罪的核心人物,共同正犯是正犯的一种类型,也是犯罪的重要角色,因而与单独正犯同样处罚。只有作为犯罪从属者(或边缘角色)的共犯(即教唆犯和帮助犯)才可能比正犯处罚轻。〔33〕德、日刑法规定对教唆犯按正犯之刑处罚,但司法实务中实际上处罚会轻于正犯,对帮助犯则是按正犯之刑处罚予以减轻。对共同正犯不可能“从轻、减轻处罚”,更不可能“免除处罚”。如果说我国刑法中的轮奸这种共同正犯,还可能成为从犯,享受“从轻、减轻处罚”甚至“免除处罚”的待遇,那就表明这种所谓的“共同正犯”与区分制体系下的“共同正犯”不具有同一性,因此,不能用区分制体系下的共同正犯观念解释我国刑法对轮奸的处罚规定。
三、轮奸是否存在未遂形态
(一)观点分歧
在二人以上意欲共同轮奸妇女,且有人已着手实行奸淫行为,但均未完成或有部分人未完成奸淫行为的,能否认定未完成者为轮奸未遂,〔34〕本文中的轮奸未遂是从文义而言的,即已着手实行轮奸而未既遂的情形,包含德、日刑法学中所指的障碍未遂和中止未遂。前者指已着手实行犯罪,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后者指已着手实行犯罪而自动放弃犯罪或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情形。成为颇有争议的问题。站在区分制体系立场上,不否认轮奸是强奸罪的共同正犯形态,且赞成对共同正犯应坚持“部分实行全部责任”原则的论者,对此主要有如下几种不同主张。
其一是否定说,认为未完成奸淫行为者,不可能成立轮奸未遂。这种观点还可以分为两种不同具体主张。一是“不能视为轮奸者说”,其认为意欲共同轮奸妇女的人,只有自己已完成奸淫行为,才可能与其他已完成奸淫行为的人,成立轮奸。他人已完成而自己未完成的,即便是其他完成者在二人以上属于轮奸,自己作为未完成奸淫行为者仍不成立轮奸,即不能视为或认定为轮奸者,既不能按轮奸既遂也不能按轮奸未遂处罚,而只能以普通强奸罪未遂论处。〔35〕参见钱叶六:《“轮奸”情节认定中的争议问题研讨》,载《江淮论坛》2010 年第5 期。二是“不存在轮奸未遂说”,其认为“无论多少人参与轮奸,若只有一人奸淫成功,全案不能认定为‘轮奸’,……只要有两人以上奸淫成功,全案应认定为‘轮奸’既遂而适用‘轮奸’的法定刑。对于实际奸淫未得逞或者主动放弃奸淫的”,仍要以轮奸既遂论处,也就是不可能存在轮奸未遂。〔36〕陈洪兵:《“二人以上轮奸”的认定》,载《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6 期。
其二是肯定说,认为未完成奸淫行为者,有可能成立轮轩未遂。对这种轮奸未遂者,既要适用轮奸的法定刑,又要适用刑法总则有关未遂犯或中止犯的处罚规定。这种观点又可分为几种不同主张。一种是“轮奸未既遂说”,其认为轮奸成立但未既遂时,所有参与者均成立轮奸未遂;如果轮奸已既遂,则未完成奸淫行为者也为轮奸既遂,而不属于轮奸未遂。〔37〕参见张明楷:《刑法学(下)》(第六版),法律出版社2021 年版,第1141 页;王志祥:《共同实施强奸仅一人得逞,应如何定性》,载《中国检察官》2008 年第9 期。至于轮奸既遂的标准,持此说的论者中,有人认为,参与者中只要有一人将奸淫行为实施完毕(即强奸既遂),则由于轮奸是强奸罪的共同正犯形态,根据“部分实行全部责任”或“一人既遂,全体既遂”的归责原理,所有参与实施奸淫行为者(含未完成奸淫行为者),均应认定为轮奸既遂;〔38〕参见王志祥:《共同实施强奸仅一人得逞,应如何定性》,载《中国检察官》2008 年第9 期。另有人认为,参与者中若有二人完成了奸淫行为,轮奸即为既遂,没有实施或完成奸淫行为者,由于成立共同正犯,对他人轮奸既遂的结果也应承担责任,因而不能以轮奸未遂论。〔39〕参见张明楷:《刑法学(下)》(第六版),法律出版社2021 年版,第1141 页。另一种是“自己未完成奸淫说”,其认为具有轮奸故意的参与者,在有两名以上同案犯已完成奸淫行为(即他人已轮奸既遂)时,自己因意志以外原因而未得逞的,构成轮奸未遂,对其应适用轮奸的法定刑,同时还应适用刑法总则关于未遂犯的处罚规定;但如果有轮奸故意的一名男子已完成奸淫行为,自己已开始实施奸淫行为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时,则因并无轮奸结果发生,从而不成立轮奸未遂。行为人只承担普通强奸罪的未遂责任,同案中已完成奸淫行为者也只属于普通的强奸既遂,均不能适用轮奸的法定刑。〔40〕参见付立庆:《论轮奸的限制性认定》,载《法学》2020 年第4 期。
以上几种主张中,“不能视为轮奸者说”认为基于轮奸故意而实施奸淫行为但未得逞或未完成奸淫行为者,因仍不能视其为轮奸者,从而也就不可能属于轮奸未遂。在笔者看来,按单一正犯的解释论,这种结论具有合理性。然而,按区分制的共同正犯理论,如果说轮奸是强奸的共同正犯形态,在同案中的其他共同参与者已完成奸淫行为、特别是在已成立轮奸既遂的情况下,作为共同正犯的参与者仅因其个人实施的奸淫行为未完成,就将其排除在轮奸的范围之外,显然与共同正犯的成立理论及“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归责原理相悖。“不存在轮奸未遂说”和“自己未完成奸淫说”认为只有在二人以上奸淫成功或完成奸淫的条件下,才能成立轮奸,这与共同正犯的成立理论也不相符。如前所述,二人以上基于共同实行的意思而共同实施实行行为,共同正犯即告成立,并非只有在二人以上完成实行行为时,共同正犯才能成立。若认为轮奸是强奸罪的共同正犯形态,强奸的共同正犯成立,即二人以上基于轮奸的故意而共同实行强奸行为,轮奸就已成立,并不要求二人以上强奸既遂才成立。并且,按“自己未完成奸淫行为说”,轮奸未遂只能在同案犯中有二人以上轮奸既遂的情况下才能成立,也就是在已有人构成轮奸既遂的条件下,自己未完成奸淫行为才成立轮奸未遂。然而,这样解释与区分制体系下的共同正犯原理明显不符。正如林东茂教授所述:“如果轮奸的人有既遂,有未遂,怎么处罚?是既未遂的人,各依加重强制性交罪的既遂或未遂处罚吗?如果是这么处罚,必然与共同正犯的原理冲突。轮奸是共同正犯的一种形态,成立的罪就必须一致,不可能有人既遂,而有人却是未遂。”〔41〕林东茂:《刑法综览》(修订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259 页。“轮奸未既遂说”则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认为二人以上基于轮奸的故意而共同实行奸淫行为,即便均未完成奸淫行为,仍成立轮奸,只不过是属于轮奸未遂,在适用轮奸法定刑的同时,还应适用刑法总则对未遂犯从宽处罚的规定。然而,由于轮奸的法定刑很重,最低为十年有期徒刑,最高为死刑,而按司法惯例,对未遂犯通常只是从轻处罚。如果二人以上均强奸未遂或者仅有一人强奸既遂,那在危害结果即对妇女性权利的侵害上,与单个人犯强奸罪的未遂犯或既遂犯并无多大差异,但处刑却比单个人犯罪重得多,显然不具有合理性。林东茂教授曾明确指出,如果参与者都强奸未遂,“表示没有对被害人的性自主造成严重的侵害,依照普通强制性交(即普通强奸罪——引者注)的未遂处罚,也应该足够了,处罚轮奸的未遂就显得多余”。〔42〕林东茂:《一个知识论上的刑法学思考》(增订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92 页。
(二)轮奸未遂的理论依据评析
上述肯定轮奸存在未遂形态的论者所依据的理论稍有差异,笔者将其概括为两种:一是加重的犯罪构成论;二是以此为基础的亲手犯论。
1.亲手犯论
上述持“自己未完成奸淫说”者认为,意欲共同轮奸的行为人在其他参与者已轮奸既遂的条件下,即使实施了奸淫行为而未得逞,也只能承担未遂的责任。其理论根据在于强奸罪是亲手犯,应“作为‘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例外”,不对其他共同正犯者所造成的轮奸结果承担责任。〔43〕参见付立庆:《论轮奸的限制性认定》,载《法学》2020 年第4 期。在笔者看来,这种理论根据并不可靠。
第一,亲手犯的概念或理论,从上世纪初被德国学者宾丁(Binding)提出,学界就对其从未停止过论争。〔44〕参见[日]大塚仁:《间接正犯的研究》,有斐阁1958 年版,第224 页以下。一般认为,“亲手犯的正犯只能是亲自直接实现构成要件的人。因而,亲手犯既不能以共同正犯,也不能以间接正犯的方式实现,同样,也不能由幕后‘操纵者’实现。”〔45〕[德]乌尔斯•金德霍伊泽尔:《德国刑法总论教科书》(第六版),蔡桂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402 页。这种承认亲手犯概念的观点属于多数说,但否定亲手犯概念的观点也很有影响力。否定的重要理由是,实际上那些被“称为亲手犯的犯罪,仍然有可能通过强制、欺骗等手段,以间接正犯的形式来实施”。〔46〕[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总论》(第2 版),王昭武、刘明祥译,法律出版社2013 年版,第63 页。因此,那种所谓不可能以间接正犯的形式而只能是由自己亲自实施的犯罪(即亲手犯),本来就没有存在的余地。况且,在承认亲手犯概念的论者中,对强奸罪是否属于亲手犯又有不同认识。上述持“自己未完成奸淫说”的论者也不否认,“在德国和日本,多数说虽肯定亲手犯的概念,但却否定强奸罪是亲手犯。……在我国,否定强奸罪是亲手犯的观点也是多数”。〔47〕付立庆:《论轮奸的限制性认定》,载《法学》2020 年第4 期。既然亲手犯的概念即便是在区分制体系下有无存在的价值尚有疑问,况且,肯定亲手犯概念的论者大多也否定强奸罪为亲手犯。加之,我国刑法采取单一正犯体系,在这种犯罪参与体系下,间接正犯和共同正犯的概念本身并无存在的空间或余地,〔48〕参见刘明祥:《间接正犯概念之否定——单一正犯体系的视角》,载《法学研究》2015 年第6 期;刘明祥:《单一正犯视角下的共同正犯问题》,载《中外法学》2019 年第1 期。从而决定了亲手犯的概念也无存在的意义。那么,上述“自己未完成奸淫说”却以强奸罪是亲手犯作为轮奸未遂成立的理论根据,其可靠性当然令人怀疑。
第二,在其他参与者轮奸既遂的条件下,以强奸罪属于亲手犯,应“作为‘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例外”,将实施了奸淫行为而未得逞者认定为轮奸未遂,这与区分制体系下的共同正犯乃至亲手犯的理论也存在冲突。如前所述,二人以上基于轮奸的故意而共同实行强奸行为,在已有人强奸既遂的场合,依据“部分实行全部责任”这一共同正犯的归责原理,所有参与者(包含自己未完成奸淫行为者)均应对强奸既遂的结果负责,如果不否认轮奸是强奸的共同正犯形态,结论无疑是轮奸既遂,而不可能是轮奸未遂。如果说强奸罪是亲手犯,按亲手犯的理论,亲手犯虽只能由自己亲自直接实行,但第三者或他人可以教唆、帮助其实行则毋庸置疑。〔49〕参见[德]乌尔斯•金德霍伊泽尔:《德国刑法总论教科书》(第六版),蔡桂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402 页。因此,自己未完成奸淫行为的强奸者,充其量只是不能成立强奸罪的间接正犯与共同正犯,但同样能成为强奸罪的教唆犯和帮助犯。按区分制体系下共犯既未遂的通说,因共犯具有从属于正犯的特性,作为共犯的教唆犯和帮助犯的未遂,也应以正犯着手实行、终于未遂时为成立的条件,若正犯已既遂,教唆犯和帮助犯无疑也属于既遂,不可能成立未遂。〔50〕参见[日]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第三版),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294 页。另外,按区分制体系下的亲手犯理论,若认为强奸罪是亲手犯,共同参与强奸犯罪的未实行强奸行为者,只能按强奸罪的教唆犯或帮助犯处罚,不能以强奸罪的共同正犯和间接正犯论处。然而,亲手犯的既遂与未遂的认定,与非亲手犯并无差异。在单独犯的场合,自己亲自实行犯罪而未得逞的,成立犯罪未遂;在共同犯罪的场合,作为亲手犯的教唆犯、帮助犯的未遂,也同样应以被教唆、被帮助的实行犯已着手实行犯罪而未得逞为成立的条件,在其实行已完成或犯罪已得逞时,亲手犯的教唆犯和帮助犯即已既遂。这就意味着即使强奸罪为亲手犯,自己未完成奸淫行为者,作为强奸罪的教唆犯或帮助犯,在其他参与者有二人以上强奸既遂的条件下,不可能成为强奸或轮奸的未遂犯,而只能成为既遂犯。只有将自己未完成奸淫行为者视为强奸罪的单独犯,才能认定其为强奸未遂。认定为轮奸未遂,就意味着其并非单独犯,因为仅自己一人单独强奸者,不可能是“轮奸”,若定性为“轮奸”,那无疑是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参与犯罪,无论是亲手犯还是非亲手犯,其既未遂的认定,均不能无视共同参与犯罪的特性,而采取与单个人犯罪既未遂相同的规则,否则就不具有科学合理性。
第三,持“自己未完成奸淫说”的论者,之所以主张在其他参与者已轮奸既遂的条件下,对自己未完成奸淫行为者以轮奸未遂论处,无非是考虑到轮奸的法定刑过重,而对这种未完成奸淫行为者与其他轮奸既遂者同样处罚,不仅处罚过重,而且同没有轮奸故意但对被害妇女实施暴力的帮助者的处罚相比,明显不公平合理,因而对轮奸及轮奸既遂应限缩认定。〔51〕参见付立庆:《论轮奸的限制性认定》,载《法学》2020 年第4 期。在笔者看来,这种考虑也无可非议。然而,对上述未完成奸淫行为者按轮奸未遂处理,不仅与刑法理论相冲突,而且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前所述,我国《刑法》第23 条第2 款虽然规定,对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但按司法惯例,通常只是比照既遂犯从轻,一般不会减轻处罚。轮奸的法定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以轮奸未遂论处,最终的处罚结果仍然过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类案件处罚轻重失衡的问题。
2.加重的犯罪构成论
主张轮奸存在未遂形态的另一更为重要的理论根据是,我国刑法规定的“轮奸不是单纯的量刑规则,而是加重的犯罪构成,因而存在未遂形态”。〔52〕张明楷:《刑法学(下)》(第六版),法律出版社2021 年版,第1141 页。此种主张很有影响力,被绝大多数肯定轮奸存在未遂形态的论者所接受。实际上,上述“自己未完成奸淫说”也是以轮奸属于加重犯罪构成存在未遂形态为前提的,〔53〕参见付立庆:《论轮奸的限制性认定》,载《法学》2020 年第4 期。进一步用强奸是亲手犯的观念来论证轮奸未遂之特殊性。然而,笔者认为,加重犯不存在未遂形态,以轮奸是我国刑法规定的一种加重犯罪构成为根据,肯定轮奸存在未遂形态,不具有合理性。这种加重的犯罪构成论不仅是上述各种轮奸未遂论的理论根据,而且也是一个重要的刑法基础理论问题,因而笔者对此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论述。
第一,刑法规定的有些具体犯罪有基本犯和加重犯、减轻犯之分。一般来说,因具备法定的加重情形而规定处以更重的法定刑的犯罪为加重犯。对加重犯,有的国家刑法在普通犯(或基本犯)之外,另立条文规定为独立的犯罪设置更重的法定刑,如日本刑法在普通强盗罪(第236 条)之外另设强盗致死伤罪(第240 条),规定了比普通强盗罪更重的法定刑;我国刑法则是在与普通犯相同的条文中规定加重犯,同时规定比普通犯更重的法定刑。如我国《刑法》第236 条前段对抢劫罪的普通犯及其法定刑予以规定,后段对抢劫罪的加重犯(包含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等情形)规定了比普通犯更重的法定刑。关于加重犯是否存在未遂形态,国外刑法学界存在激烈争论。〔54〕参见张明楷:《刑法学(上)》(第六版),法律出版社2021 年版,第449 页。对加重犯的未遂是否予以处罚,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刑法规定也各不相同。有的国家(如德国、日本)刑法分则某些罪的条文明确规定处罚结果加重犯的未遂,但我国民国时期的刑法,“对于结果加重犯只有既遂犯的规定,而无结果加重犯未遂犯的规定,因此并没有所谓结果加重犯未遂犯的存在”。〔55〕黄荣坚:《刑法问题与利益思考》,元照出版有限公司1995 年版,第426 页。我国现行刑法分则对包含结果加重犯在内的加重犯虽无是否处罚未遂犯的规定,但刑法总则原则上规定对所有故意犯罪的未遂犯均予以处罚,因而,否定加重犯存在未遂形态,似乎并无明确的法律依据。德国、日本刑法有处罚加重犯的未遂犯的规定,德、日刑法学者大多对加重犯存在未遂形态持肯定态度。受这种外在条件的影响,我国多数学者也认为包含轮奸在内的许多加重犯都存在未遂形态。〔56〕关于加重犯的未遂,存在广义与狭义两种不同情形。狭义的加重犯未遂,是指加重结果或事实(情节)尚未发生但存在发生的现实危险性的情形。至于基本犯则既可能是既遂也可能是未遂。广义的加重犯未遂,则还包括加重结果或事实(情节)已发生,基本犯的结果未发生即基本犯未遂的现象。如意图抢劫财物的行为人致被害人重伤、死亡后未能抢劫到财物的,这通常被认为属于基本犯未遂,结果加重犯既遂。但也可能被视为结果加重犯的未遂。参见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第194 页。本文讨论包含轮奸在内的加重犯是否存在未遂形态,是从狭义而言的,即加重结果或事实(情节)未发生时,能否视为加重犯的未遂。然而,加重犯有多种类型,认为所有加重犯都存在未遂形态明显不合适,为此,多数学者认为有些类型的加重犯不存在未遂形态。持此种主张的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论者认为,应以刑法对加重犯的规定是属于量刑规则还是加重的犯罪构成(或构成要件)为根据,将存在未遂形态的加重犯与不存在未遂形态的加重犯区分开来。“量刑规则是不可能存在所谓未遂的”,如刑法以“情节严重”“数额巨大”作为某罪法定刑升格的条件时,这种加重犯就不存在未遂形态。意图盗窃“数额巨大”财物并已着手实行而未得逞的,不能认为是盗窃“数额巨大”这种加重犯的未遂,而只能认为是盗窃罪基本犯的未遂,适用基本犯的法定刑。如果是加重犯罪构成类型的加重犯,则存在未遂形态,如轮奸、入户抢劫等,“当行为人的行为符合加重的犯罪构成的行为类型,只是没有发生既遂结果时,就成立加重犯的未遂犯,在适用加重犯法定刑的同时适用未遂犯的规定”。然而,持此种主张的论者忽视了我国刑法与德、日刑法对加重犯规定的重大差异。如前所述,德、日刑法将许多加重犯在基本犯之外另立专条规定为独立的犯罪,与基本犯的罪名不同,并对之有处罚未遂犯的明确规定,且处罚独立之罪的未遂犯与刑法理论不冲突。然而,我国刑法中的加重犯与基本犯规定在同一条文之中,罪名完全相同(而非不同罪名),因此,当加重结果或事实(情节)没有发生时,若肯定成立这种加重犯的未遂犯,适用比基本犯重得多的加重犯的法定刑,这明显不具有合理性。因为刑法在同一条文中除对同一罪名的基本犯设处罚规定之外,另对加重犯规定了更重的法定刑,这就表明立法者告诉国民,犯此种罪通常按基本犯的法定刑处罚,只有在具备加重结果或事实(情节)时,才例外地作为加重犯给予更重的处罚。也就是说加重结果或事实(情节)出现,是加重犯成立并适用加重犯法定刑的前提条件。如果加重结果或事实(情节)没有出现,按基本犯处刑即可。这既是立法者这样规定加重犯的精神之所在,也是立法者要让国民知晓的法律规定的含义。如果加重结果或事实(情节)尚未发生,只是因存在发生的可能性,即认定为加重犯的未遂,适用比基本犯重得多的加重犯的法定刑处罚行为人,既与立法精神不符,也违反罪刑法定原则。〔57〕因为按刑法规定,尚未发生加重结果或事实(情节)时,行为本来符合基本犯的成立条件应适用基本犯的法定刑,给予行为人较轻的处罚,但不这样处罚,而要将其行为解释为加重犯的未遂,给予更重的处罚,这明显与罪刑法定原则不符。另外,在刑法规定同一种罪有轻重程度不同的多种加重犯的场合,如我国《刑法》第234 条规定的故意伤害罪,轻伤为基本犯,重伤为较重的加重犯,伤害致死是最重的加重犯,三者的法定刑有较大差距。一般来说,故意伤害致被害人轻伤,即为基本犯既遂,且许多故意伤害致人轻伤的行为,均存在致人重伤或死亡的危险性,如果承认加重犯的未遂,那就会导致许多故意伤害案件都被认定为加重犯的未遂;又由于故意伤害行为含有致人重伤与死亡两种可能性,那么,是认定为致人重伤的未遂还是认定为致人死亡的未遂并适用相应的法定刑处罚,这也是无法合理解决的难题。
第二,以某种加重犯的加重结果或事实(情节)是属于量刑规则还是加重的犯罪构成,来确定其是否存在未遂形态,那就必须将量刑规则与加重的犯罪构成区分开来,但事实上很难找到一个合适而统一的标准将两者恰当区分开来。众所周知,我国刑法理论长期将犯罪构成分为普通的犯罪构成与派生的犯罪构成,所有的加重犯均在派生的犯罪构成之中,〔58〕参见陈兴良:《规范刑法学(上册)》(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109 页。“根据这种观点,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这类抽象的升格条件与数额巨大、入户抢劫等具体的升格条件,都属于加重的犯罪构成(或加重的构成要件)”。〔59〕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第182 页。如果肯定具备这种广义的加重的犯罪构成的加重犯都存在未遂形态,那就等于认可所有的加重犯都存在未遂形态。按上述主张区分量刑规则与加重的犯罪构成的论者的主张,“刑法分则条文因为行为、对象等构成要件的特殊性使行为类型发生变化,进而导致违法性增加,并加重法定刑时,才属于加重的犯罪构成(或构成要件)”;“刑法分则条文单纯以情节(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以及数额或数量(特别)巨大、……作为升格条件时,只能视为量刑规则”。〔60〕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第182 页。这固然对加重的犯罪构成的范围略有限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加重犯的未遂范围,但这种限制是否合理仍令人怀疑。如我国《刑法》第266 条把“数额较大”作为构成诈骗罪的条件,通说认为“数额较大”是诈骗罪的成立要件,“数额巨大”是此罪加重犯成立的要件之一。既然 “数额较大”是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为何诈骗“数额巨大”不是此罪加重的构成要件,而只能视为“量刑规则”?又如轮奸被上述论者视为强奸罪的加重构成要件,但也并非完全不存在否定其为加重构成要件的余地。因为二人以上轮奸,从行为、对象等强奸罪的构成要件来看,与普通强奸罪(或强奸罪的基本犯)似乎并无多大差异,其实也就是数人(含二人)连续数次共同强奸既遂的情形,〔61〕参见黄荣坚:《刑法问题与利益思考》,元照出版有限公司1995 年版,第408-409 页。也有可能被排除在加重的构成要件之外。既然如此,以轮奸是强奸罪的加重构成要件为根据,肯定其存在未遂形态,也就难以令人信服。
第三,同一罪名之下的基本犯与加重犯,既遂的标准也应该相同,即应以基本犯的构成要件为标准,基本犯既遂则加重犯亦既遂。如前所述,加重结果或事实(情节)只存在发生与否的问题,并且加重犯的成立也是以加重结果或事实(情节)发生为条件的,若加重结果或事实(情节)尚未发生,则加重犯不成立,只可能按基本犯处罚,不能认定为加重犯未遂适用加重犯的法定刑。例如,入户抢劫是我国刑法规定的抢劫罪的加重犯类型之一,上述论者认为:“对于入户抢劫未遂的,既要适用入户抢劫的法定刑,又要适用刑法总则关于未遂犯的处罚规定。”〔62〕参见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第182 页。如果是入户之后实行抢劫而未抢到财物的,即作为抢劫罪的基本犯未遂,但因具备了入户抢劫这一加重事实情节,而认定为“入户抢劫未遂”,适用抢劫罪加重犯的法定刑,这似乎也无可非议。然而,如果意图入户抢劫而未能入户的,即“入户抢劫”这一加重事实(情节)没有发生时,还能认定为“入户抢劫未遂”吗?如行为人敲被害人家门,意图入户抢劫,对方不开门,行为人用砍刀砍其家门,威胁其若不给钱进去后就杀死他,被害人拿了一万元钱从门缝塞出去,行为人拿了钱离去。此例中的行为人意图入户抢劫但未能入户,入户抢劫的加重事实(情节)没有发生,能认定为入户抢劫未遂适用抢劫罪加重犯的法定刑吗?回答应当是否定的。我国民国时期的刑法将夜间侵入住宅窃盗作为窃盗罪的加重犯类型之一规定了更重的法定刑,“夜间侵入住宅窃盗”与我国现行刑法中的“入户抢劫”相似。黄荣坚教授就认为:“夜间侵入住宅窃盗……的既遂标准还是在窃盗的本身。……至于加重要件的部分,即夜间侵入住宅……,没有所谓既遂的问题。”〔63〕黄荣坚:《刑法问题与利益思考》,元照出版有限公司1995 年版,第430 页。这当然也没有未遂可言。基于同样的理由,作为抢劫罪处罚加重条件的“入户”,没有所谓既遂与未遂,只有是否存在或具备的问题。此外,在我国,由于加重犯与基本犯大多被规定在同一条文中使用同一罪名,而同一罪名的加重犯往往有多种类型,如果肯定加重犯存在未遂形态,以加重结果或事实(情节)是否发生作为既未遂的标准,那么,同一罪名的犯罪的既遂标准就可能有多种。以强奸罪的加重犯为例,“强奸妇女、奸淫幼女多人的”,就应以被害对象是“多人”为既遂标准;“在公共场所当众强奸妇女、奸淫幼女的”,就应以犯罪地在“公共场所”为既遂标准;“二人以上轮奸的”,就应以二人以上连续实行了奸淫行为为既遂标准;“奸淫不满十周岁的幼女或者造成幼女伤害的”,就应分别以被害对象是不满十周岁幼女或造成幼女伤害的结果为既遂标准;“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或者造成其他后果的”,则应以被害人“重伤”“死亡”或“其他后果”发生为既遂标准。而强奸罪的基本犯,通说认为以犯罪的男子之性器官插入妇女的阴道或与幼女的外阴相接触,作为既遂的标准。这样一来,作为同一罪名的强奸罪的基本犯和加重犯的既遂标准,总共就有十几种。这显然与同一种犯罪既遂的认定标准应尽可能统一或同一的刑法基本理念相悖。
第四,在加重结果或事实(情节)没有发生,但有发生的现实可能性或危险性的场合,否定加重犯成立,从而也不存在这种加重犯的未遂形态,对犯罪行为人也就不能适用加重犯的法定刑处罚,这是否会出现处罚过轻的现象呢?笔者的回答也是否定的。一般来说,只有在可能发生致人重伤、死亡等特别严重的加重结果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按基本犯的法定刑处罚过轻的现象,而在实施基本犯的行为有可能引起这类特别严重结果发生的案件中,由于这类行为会同时触犯其他罪名,进而成立想象竞合犯。〔64〕参见张明楷:《刑法学(上)》(第六版),法律出版社2021 年版,第450 页。只要按从一重罪处断的原则,正确适用法定刑,依法恰当判处刑罚,就不可能出现处刑过轻或轻纵罪犯的问题。例如,甲为了抢劫财物,意图杀死乙后将乙携带的手提箱拿走。甲用木棒猛击乙头部一棒后,乙惨叫一声倒地,被偶然路过的行人发现。甲被迫空手逃离。乙被送往医院救治,很快康复,被认定为轻伤。此例中甲所犯的抢劫罪基本犯未遂,“抢劫致人死亡”的结果尚未发生,如果否定加重犯存在未遂,只适用基本犯的法定刑(即“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同时还要适用未遂犯从宽处罚的规定,这样处罚的结果确实过轻。如果肯定加重犯存在未遂形态,适用抢劫罪加重犯的法定刑(即“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固然可以避免处罚过轻结果的发生,但按想象竞合犯的认定和处理规则,由于此例中的甲为了抢劫乙的财物,有把杀死乙作为抢劫手段实施的故意和行为,同时触犯了故意杀人罪,按从一重罪处断的原则,应适用故意杀人罪的法定刑(即“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同时适用未遂犯从宽处罚的规定,最终的处罚结果与按抢劫罪的加重犯未遂处罚,几乎完全相同。可见,否定结果加重犯存在未遂形态,并不会出现处罚过轻或轻纵罪犯的后果。
(三)轮奸成立与否及其认定标准
如前所述,在有多人参与轮奸的场合,只要有二人以上(含二人)完成奸淫行为,轮奸的结果或事实已经发生,意欲共同轮奸而未完成奸淫行为者,大多数观点认为同已完成奸淫者一样,成立轮奸既遂;只有视强奸为亲手犯的论者认为,属于轮奸未遂(完成了奸淫行为者是轮奸既遂)。然而,笔者认为,轮奸作为强奸罪的加重犯不存在未遂形态,不仅意图轮奸的所有参与者均未完成奸淫行为的场合,不能认定为轮奸未遂,而且,不能在其他参与者中有二人已完成奸淫行为即轮奸成立时,将未完成奸淫行为者认定为轮奸未遂。同时,也不能将这种未完成奸淫行为者,以同案中的其他参与者已有二人完成奸淫行为,按共同正犯的“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归责原理,认定其为轮奸既遂。应当特别说明的是,笔者于本文中虽有多处照常使用了“轮奸既遂”“轮轩未遂”的概念或提法,但那是为了论述问题的方便,并不表明笔者认可轮奸存在既遂与未遂形态。事实上,“轮奸作为强奸罪的一种加重处罚的情形,其本身不是单独罪名,故不存在既、未遂之提法,而是应以其轮奸行为是否实际发生作为该款项成立的依据”。〔65〕许航:《对于强奸罪中轮奸、共犯既未遂问题的思考》,载《中国检察官》2008 年第9 期。
从我国《刑法》第236 条第3 款将“二人以上轮奸的”规定为强奸罪的加重犯类型之一就不难看出,轮奸的成立条件是:主体为二人以上;被害人为同一妇女或幼女;轮奸的结果已发生,即二人以上(至少二人)分别轮流实施了带有强制性的奸淫行为,简称为轮奸或轮流奸淫。由于只有轮流实施奸淫行为才可能成为轮奸,自己不实施奸淫行为,只是教唆或帮助他人轮流实施奸淫行为的,当然不成立轮奸,而只能成为普通强奸罪的共同犯罪人。意欲共同轮奸的行为人,在其他参与者已成立轮奸的条件下,自己未成功奸淫的,同样不成立轮奸,也只能成为普通强奸罪的共同犯罪人。因为轮奸加重处罚的根据在于,行为人不仅与他人共同参与强奸犯罪,而且还与他人轮流奸淫了同一妇女或幼女,使被害人遭受了更严重的性侵害,因而要比共同参与普通强奸罪受更重的处罚。至于同案的其他人成立轮奸,不能成为意图参与轮奸而自己未成功奸淫者也成立轮奸的根据。这是因为按我国刑法的规定和单一正犯的解释论,轮奸只是强奸罪的加重犯类型之一,对共同参与强奸犯罪者的定罪,采取与单独犯强奸罪基本相同的定罪规则,对各个参与者分别认定为强奸罪之后,再根据参与者是否与他人有强奸的共同故意和共同行为,来确定参与者是否成立强奸罪的共同犯罪,对成立强奸罪的共同犯罪人,要以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大小为依据,进一步确认为主犯或从犯(含胁从犯),给予轻重有别的处罚。对共同犯强奸罪的参与者处罚时,要分别根据各个参与者自己具备的犯罪的轻重情节,给予轻重有别的处罚。轮奸只是强奸罪的加重处罚情形(或情节)之一,具备这一情形者,才能以轮奸作为依据适用强奸罪加重犯的法定刑。虽然是强奸的共同犯罪人,其他共同犯罪人都成立轮奸,应适用轮奸的法定刑,但意图参与轮奸而出于意外原因并未得逞的,由于其并未实行或完成轮流奸淫的行为,其参与的行为尽管可能对其他人完成轮奸也起了重要作用,但毕竟他自己没有实行或完成奸淫行为,自己未轮奸,即不是轮奸者,因而不能适用轮奸的法定刑,只能对其适用普通强奸罪的法定刑,但可以作为主犯处罚,同时还应认定为强奸既遂。因为在共同犯罪中,其他共同犯罪人完成了犯罪的,未直接引起结果发生者,也应对其他共同犯罪人实施的共同犯罪行为引起的结果负责,因而也成立犯罪既遂。但对加重结果或事实(情节),应以参与者个人是否完全具备为认定的原则。就轮奸而言,如前所述,之所以不能以同案其他共同参与者已成立轮奸为由,认定意图共同轮奸而未成功奸淫者成立轮奸,就在于他自己未奸淫或未完成奸淫行为,没有成为轮奸者,不能以他帮助过他人轮奸、是与他人共同犯罪,作为责令其承担轮奸责任,适用轮奸的法定刑,从而受更重处罚的根据。另外,由于我国刑法对加重犯大多规定了很重的法定刑,适用应该严格限制。尤其是对共同犯罪案件,不能以同案其他共同犯罪人的共同行为造成了严重结果,就一概责令同案犯对严重结果负责按加重犯处罚。例如,甲教唆乙强奸妇女丙,乙采用超常的强制手段致被害人死亡。对乙无疑应适用强奸致人死亡的法定刑,但如果甲不知乙会采用超常的强制手段作案,就可以对其仅适用普通强奸罪的法定刑处罚,不责令其对乙造成的被害人死亡的加重结果负责。
至于轮奸的结果或事实的发生,采取何种标准来认定,涉及对“奸淫”是从广义还是狭义上理解的问题,且与强奸妇女以“插入”为既遂标准之通说有密切关系。一般来说,关于“奸淫”的含义,“可以认为是‘插入’这一既遂的结果,但是也可以认为‘奸淫’是一种行为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结果是‘插入’,结果发生之前的过程性存在也属‘奸淫’的范畴”。〔66〕张明楷:《性犯罪的争议问题》,载《第六届中日刑事法研讨会暨中日刑法总论及分论中的先端课题研讨会论文集》,第159-160 页。转引自林贵文:《“轮奸”成立学说的法教义学批判与证成》,载《法律科学》2019 年第6 期。在笔者看来,认为“奸淫”是一种行为过程是从广义上的理解,认为“奸淫”是指“插入”这一既遂结果则是从狭义上的解释。两种不同认识对同一案件可能得出两种完全不同的结论。例如,甲与乙夜间喝了较多的酒,回家途中遇见一独行的女青年丙,两人强行将其拉到路边,先后实施奸淫行为,均未能如愿插入。若采取广义的解释,由于甲乙均实施了奸淫行为,就应认定轮奸成立;但采取狭义的解释,由于“插入”的结果没有发生,甲乙都未成功奸淫,即丙被轮流奸淫的结果并未出现,因而轮奸不成立。显然这后一种解释更为合理,且能被行为人和被害人所接受。按前一种理解,将此例中的甲乙认定为轮奸,不仅甲乙会认为自己未成功奸淫而否定成立轮奸,被害人丙也可能会认为,自己只是可能被奸淫而事实上未被奸淫,性贞操没有实际受损,即并没有被轮奸。丙的亲属和社会公众也会这样评价。并且,如前所述,由于我国刑法对轮奸规定的法定刑很重,对其成立条件应该做严格的限制性解释,以缩小其成立范围,避免对犯罪人处罚过重的结果发生;况且,按我国刑法规定的强奸罪基本犯的法定刑,上例中的甲乙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范围内,可将他们均认定为主犯,酌情从重处罚,判处较长刑期的刑罚。这样即可避免处刑过轻或轻纵罪犯的结果发生。相反,若认定为轮奸,适用轮奸的法定刑,就会出现处刑过重或罪刑不均衡的后果。
综上所述,只有在共同参与强奸的参与者中,至少另有一人已强奸既遂的条件下,自己也与之轮流奸淫同一被害人,并已完成奸淫行为(即单独而论自己也属强奸既遂)的,才成立轮奸,适用轮奸的法定刑。无论同案中其他参与者的行为是否属于轮奸,若行为人只是教唆、帮助他人强奸或轮奸、甚至自己意欲轮奸并已着手实行而未完成奸淫行为的,均不成立轮奸,对这种参与者只能按普通强奸罪定罪处罚(即适用强奸罪基本犯的法定刑)。然而,在有共同参与者已完成奸淫行为的案件中,对所有参与者(包含意欲共同轮奸而未完成奸淫行为者),除具备退出参与的犯罪(或脱离共犯)之条件者外,均应认定为强奸既遂。
四、解决轮奸争议问题的最佳途径
众所周知,我国1979 年《刑法》将轮奸作为强奸罪的从重处罚情节予以规定,我国1997 年《刑法》将轮奸改为强奸罪的加重处罚情形。如果考察一下这种立法变迁的轨迹,就不难发现,多数刑法草案均将轮奸规定为从重处罚情节,且常与奸淫幼女同样对待予以并列规定,而将轮奸与强奸致人重伤、死亡明确加以区别,对后者往往配置更重的刑罚。“立法将轮奸从‘从重处罚’调整为‘加重处罚’具有特殊的历史背景”,〔67〕付立庆:《论轮奸的限制性认定》,载《法学》2020 年第4 期。即“受当时正在开展的‘严打’活动的影响,……立法工作机关提高了本罪基本犯的法定刑,同时将‘二人以上轮奸’的列为本罪适用加重刑的加重情形”。〔68〕高铭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诞生和发展完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453 页。“甚至可以说,这是情绪化立法的产物。”〔69〕付立庆:《论轮奸的限制性认定》,载《法学》2020 年第4 期。
然而,将轮奸作为强奸罪的加重犯,规定比基本犯重得多的刑罚,明显不具有合理性。正如黄荣坚教授所述:“既然强奸罪在刑法上也就是一种妨害自由性质的犯罪,那么到底是由同一人连续妨害自由,或是由不同的人连续妨害自由,在刑法上的评价就已经不重要了。所以也不能以不同一人连续实施强奸行为的事实为理由,而认为法律上有做特别处理的必要。”〔70〕黄荣坚:《刑法问题与利益思考》,元照出版有限公司1995 年版,第499 页。至于认为多数行为人在场客观上加大了被害人生命、身体、性等法益被侵害的急迫危险,〔71〕参见黄尔梅主编:《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司法政策:案例指导与理解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4 年版,第129 页。这也不能成为上述立法具有合理性的理由。因为多数人在场帮助强奸也能导致被害人同样的危险性升高,却未被规定为加重处罚的情形。另外,“犯行较易实现”“预防必要性大”等也不足以成为将轮奸作为加重犯予以规定乃至配置无期徒刑甚至死刑的理由。〔72〕参见付立庆:《论轮奸的限制性认定》,载《法学》2020 年第4 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4 年日本虽然在强奸罪之外增设了以轮奸为主要表现形式的集团强奸罪,作为强奸罪的加重类型规定了更重的法定刑,但其法定刑仅比普通强奸罪的最低法定刑多一年惩役(普通强奸罪为3 年以上有期惩役,集团强奸罪为4 年以上有期惩役,最高法定刑相同)。2017 年日本对刑法做部分修正时,就废除了增设仅十多年的集团强奸罪。之所以废除,主要是因为同时将强奸罪原来的最低刑期由3 年惩役提升到了5 年惩役,立法者认为,适用修正之后的强奸罪的法定刑,对轮奸等集团强奸的恶劣性质、严重程度,已经能够作出有效的应对或充分的评价。〔73〕参见[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各论》(第七版),[日]桥爪隆补订,王昭武、刘明祥译,法律出版社2020 年版,第111 页。另外,还可解决增设此罪带来的一些理论和实务上的问题。日本先增设后删除包含轮奸在内的集团强奸罪的立法过程表明,将轮奸作为强奸罪的加重犯规定更重的法定刑并无必要,其最终删除该项规定的经验也值得我国借鉴。
事实上,我国1979 年《刑法》将轮奸规定为强奸罪的从重处罚情节,比现行刑法将其规定为强奸罪的加重处罚情形,更具有科学合理性。林东茂教授也认为:“对于共同强制性交(即轮奸——引者注)的行为必须更严肃的谴责,可以在量刑时从重,没有必要当作加重的要件。”〔74〕林东茂:《一个知识论上的刑法学思考》(增订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93 页。如果轮奸只是强奸罪基本犯的从重处罚情节,那么,上述轮奸涉及的是否存在未遂形态等争议问题,也就不复存在了。因此,再次修改我国刑法时,将轮奸改回原有的强奸罪从重处罚情节,是解决一些相关争议问题的最佳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