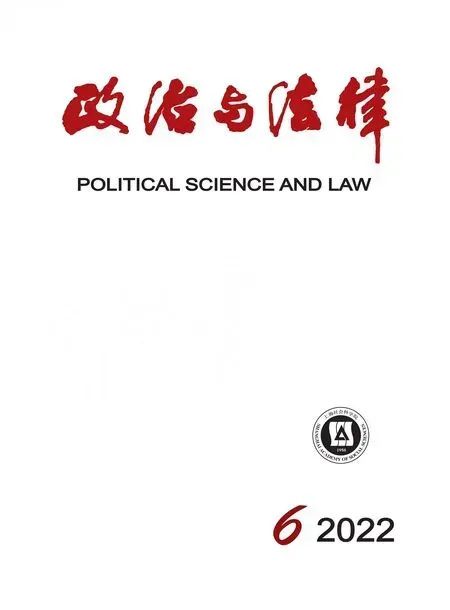跨部门法视角下经济刑法的范围界定研究
涂龙科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上海 200020)
经济刑法基础理论研究领域荆棘丛生,首当其冲的难题是经济刑法的概念与范围的界定。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第一次在我国立法文件中使用“经济犯罪”概念。《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 年第3 期发表的《略论经济犯罪与经济立法》一文,〔1〕参见沈雯辉:《略论经济犯罪与经济立法》,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 年第3 期。第一次在我国学界提出经济犯罪的概念。〔2〕学界一般认为,刘白笔于1986 年9 月26 日发表在《中国法制报》上的《经济刑法学初探》一文,在我国国内首次提出了经济刑法学的概念。此后,国内有关经济刑法的概念与范围一直争论不休,至今未有定论。国外同样如此,虽然经济刑法研究历经近百年,〔3〕据学者林东茂考证,1932 年德国刑法学家Lindemann 的《有独立的经济刑法吗?》,在德国第一次提出“经济刑法”概念。但正如日本神山敏雄教授所言:“关于经济犯罪,不论囯内外在学术上均无统一的概念,因此很难确定其共同的范围。”〔4〕参见[日]神山敏雄:《经济犯罪及其法律对策》,载[日]西原春夫主编:《日本刑事法的重要问题(第2 卷)》,法律出版社2000 年版,第3 页。德国学者汉斯•施耐德教授认为,给经济犯罪明确一个统一、精准的概念是极其困难的。〔5〕参见陈宝树主编:《经济犯罪与防治对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2 页。近几十年来,国内关于经济刑法的概念不下60 种,〔6〕参见涂龙科:《经济刑法规范特性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 年版,第23 页。国外经济刑法的概念同样提法繁多、不胜枚举。实际上,目前使用的经济刑法概念并不严谨,很大程度上是直观、感性地认为部分刑法条文和“经济”相关,或者属于“经济领域”,从而将其标注为“经济刑法”,但对“经济刑法”的具体范围、边界如何,尚缺乏坚实的理论依据和严谨的学理论证。从经济法、行政法、民法等其他部门法的角度来分析、考察、界定经济刑法的范围,实现经济刑法范围的正本清源、明确经济刑法规制重心、澄清对经济刑法法益的不当理解,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一、以经济法为主线的部门法范围之争
从经济法的视角来研究经济刑法,汲取经济法理论素养、通过经济法与刑法的交叉比较可以裨益于经济刑法的概念界定和范围框定。就经济法的滋育土壤和实践需求而言,国内比国外有明显优势。在传统上,国外奉行的是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政府已经不再仅仅是“守夜人”的角色,基于凯恩斯主义的国家经济干预甚至经济管控也属常态,但从整体经济形态上看,自由主义依然是其底色,其他的经济政策只是对自由主义的矫正与纠偏。〔7〕参见[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喧嚣的九十年代》,张明等译,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 年版,第1-2 页。从工业革命至19 世纪中期,经济法只涉足于有限领域的国家经济管理,如农业、手工业、商业和市场、土地资源、森林矿业、赋税制度等等。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经济法的发展开始提速,其历史背景是当时的英国、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产业革命,生产方式的变化极大提高了生产社会化程度。在生产社会化的背景下,作为“无形的手”的市场机制不再能有效地调节社会经济时,需要国家有意识地进行干预,〔8〕参见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第5 版),法律出版社2017 年版,第80 页。现代经济法于是应运而生并得到迅速发展。在立法上,英国等西方许多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并不存在名义上的经济法体系(也不存在作为学科部门法的经济法学),具有经济法实质内容的法律却大量存在。〔9〕参见叶秋华:《西方经济法律制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第101 页。我国脱胎于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国家对经济的管控是原有经济体制的应有之义,市场经济改革的过程是逐步放松经济管控、增加市场活力的过程。因此,与国外相比,我国的经济法实践和理论研究有其得天独厚的因缘和基因。
一部经济法研究史,就是经济法研究范围的界定史。经济法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一直是其核心和根本问题,伴随着我国经济法学科滥觞至今。在学理上,经济法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是个动态演变、整体上外延逐渐缩小的过程。改革开放之初,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引领下诞生的经济法,在基本立场上坚持“大经济法”的指导思想。基于“大经济法”的理念,形成了“纵横统一说”“密切联系说”“管理—协作说”等代表性观点。“纵横统一说”主张经济法调整纵向经济关系和横向经济关系以及经济组织内部经济关系,包括“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内部及其相互之间,以及它们与公民之间,在经济活动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10〕参见陶和谦等主编:《经济法学》,群众出版社1983 年版,第5-8 页;该书1985 年第2 版和1986 年第3 版中的有关表述与第一版相同。198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出台后,立法的实体层面限制了“大经济法”的理论合法性。传统的“纵横统一论”开始出现修正,限制经济法对平等主体之间经济关系的介入,出现了“密切联系说”与“管理—协作说”。前者将“纵横统一说”所主张的调整对象范围中的“横向经济关系”缩小为“只与纵向经济关系密切联系的那部分横向经济关系”〔11〕参见刘国欢:《经济法调整对象理论的回顾、评析与展望》,载《法律科学》1996 年第1 期。。“管理—协作说”则是将“横向经济关系的提法替换为经济协作关系”。还有的学者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政府以管理主体身份与作为管理受体的经济个体之间发生的经济关系。〔12〕参见李中圣:《经济法:政府管理经济的法律》,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 年第1 期。该观点所谓的经济法,其实质是行政法,只不过是发生于经济管理领域的行政法。此后,围绕经济法与民法的关系又陆续出现了“经济协调关系说”“需要干预经济关系说”〔13〕参见李昌麒:《经济法——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形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6 页。“经济管理与市场运行关系说”〔14〕参见刘文华主编:《新编经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年版,第1 章第2 节及其他相关章节。“国家经济调节关系说” 等观点〔15〕参见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109 页。。此类学说的共同点是致力于经济法与民法的区分,并对自身的调整对象加以反思和修正,但是对经济法与行政法之间的关系与学科定位尚缺乏理性思考。
在与民法博弈之余,经济法还面临行政法的有力挑战。双方争论的焦点是市场规制法(或称经济行政管理法)是否应当归属于经济法。经济行政法是早期的经济法学说,该观点以管理关系是否具有经济性来区分经济行政法与行政法,认为具备经济性的经济行政法就是经济法。按照该学说,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应全部或部分属于行政法的调整范围,其方案是要么直接划归行政法调整,要么在行政法中新设一个分支,即“经济行政法”〔16〕参见梁慧星等:《经济行政法论》,载《中国经济法诸论》,法律出版社1987 年版,第129-194 页。。该观点的初衷是寻求将经济领域的管理关系纳入经济法调整范围的正当性根据,但由于缺乏理论支撑且与行政法直接冲突,效果适得其反。此外,各种学说之间在经济法是否包括社会保障法、国有资产管理法、企业内部管理法以及是否需要专门区分出对外经济管理法等方面存在差异。以经济协调说为例,该学说认为“经济法是调整在国家协调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所谓经济协调关系,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即企业组织管理关系、市场管理关系、宏观经济调控关系、社会经济保障关系。〔17〕参见杨紫煊主编:《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年版,第28-32 页。该观点将本属于社会法的社会保障类法律纳入经济法。近年来,在经济法的核心内容上,认为经济法应当包括市场规制法(经济行政管理法)和宏观调控法的观点被广泛接受。换言之,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是在国家以特定的行为影响经济运行的过程中产生的;作用的方式体现为国家以公权力主体身份直接或间接地介入;作用的范围至少包括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两大领域。越来越多的著述认同,这个特定的行为包括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行为和微观经济(即市场运行)的规制行为。〔18〕参见张守文:《经济法理论的重构》,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第212-213 页。还有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主张经济法“是调整在国家调控社会经济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实现国家意志预期目标的法律规范的总称”。〔19〕参见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第五版),法律出版社2017 年版,第84 页。在经济法和行政法的关系上,更为彻底和激进的观点是完全放弃经济行政管理法和部分的经济调节法,质言之,即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只包括国家经济宏观调控关系。经济法的范围在此前的基础上进一步收缩,基本避开了与民法、行政法的正面交锋。
近现代以降,经济刑法的演进是与经济法的发展相伴同行的。〔20〕参见[德]克劳斯•梯德曼:《经济刑法的概念和历史发展》,周遵友译,载《刑法论丛》(2016 年第3 卷),法律出版社2016 年版,第410 页。经济法在筚路蓝缕探求其研究对象和理论定位的同期,经济刑法在刑法学科内部也面临同样的理论课题。经济刑法的概念、范围,经济刑法与行政刑法的关系,经济刑法在刑法学科的地位及两者之间的理论关联等,都在学界引发广泛而持久的争议。极端的经济刑法一元论者将经济刑法完全理解为对经济秩序的维护,经济刑法的前置法只有行政法,经济刑法就是经济管理刑法,完全隶属于行政刑法。但实际上,在行政法之外,经济刑法前置法还包含其他部门法,如经济法、民法等,共同构成经济刑法前置部门法的完整体系。
二、经济刑法的重心是经济管理刑法
(一)经济管理刑法规制行政相对人的经济行为
“经济刑法实际上是行政刑法的一部分,无外乎是行政刑法中发生在经济领域的那一部分而已……”〔21〕参见[日]美浓部达吉:《経済刑法の基礎理論》,有斐阁1944 年版,第1 页。经济管理刑法的前置法是行政法,调整作为管理者的行政主体和作为被管理者的行政相对人之间的行政管理关系。两者在法律上是管理与被管理的不平等关系,表现为管理者地位的强势、行为的法律强制性与被管理者的相对弱势。具体而言,经济管理刑法呈现以下特点。第一,经济管理刑法的前置法为行政法。经济管理刑法是行政管理法的二次法、保障法,通过刑法的强制力保障行政法的顺利实施。第二,经济管理刑法的前置法的调整对象为纵向的不平等主体之间的行政管理关系。曾有纵向经济法论主张,经济法是调整我国纵向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但该观点在后来的学术争论中被率先抛弃。纵向经济关系被认为是行政法的典型调整,属于行政法范畴。第三,经济管理刑法的前置法调整对象是发生于经济领域的行政管理关系。因其发生于经济领域,具有“经济”属性,从而达到限定经济刑法范围的目的。第四,经济管理刑法的规制对象与行政法不尽相同,前者用以规制行政相对人的行为,特别是作为市场主体的行政相对人的经济行为,不包括行政法中的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后者既包括行政相对人,也包括行政主体。曾经有学者把行政主体从事行政管理时实施的犯罪行为也归属于经济犯罪。如有的学者认为:“经济犯罪是指在市场经济运行领域中和在国家对市场经济运行的领域实施组织、领导、管理、监督的职务活动中,违反国家经济管理法规,破坏国家的市场经济运行秩序和国家机关对市场经济的正常管理活动,依照《刑法》规定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22〕参见刘杰主编:《经济刑法概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6 页。然而,现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通说把此类行为认定为贪污贿赂或渎职类职务犯罪,不再视为经济犯罪。
(二)我国经济刑法的实然重心是经济管理刑法
有学者认为,经济刑法是指以整体经济及整体经济中具有重要功能的部门或制度为保护客体的刑法规范。依据该观点,经济刑法是一种“经济管理的刑法”(Bewirtschaftungsstrafrecht),〔23〕Vgl.K.Lindemman: Gibt es ein eigenes Wirtschaftstraftech(1932):S.19ff.保护的是表现为经济秩序的超个人法益。〔24〕“超个人法益说”与“市场秩序说”有共通之处,市场秩序可以理解为超个人法益的一部分。该观点最早由德国学者K.Lindemann 提出,后为艾毕克(H.Ebisch)、施密特(R.Schmitt)等学者赞同。虽然在理论上有不少学者对经济刑法上述定位持有异议,但是,经济刑法的主要内容是经济管理刑法(市场规制刑法)确是不争的事实。
考察我国经济法的调整范围及其与民法、行政法的边界划分可以发现,经济法和经济刑法之间不存在整齐划一、边界明确的“二次法”的对应关系。经济刑法不单是经济法的保障法,还对应了民法、行政法的内容。除了经济法,违反民法、行政法的相关规定都可能具备刑事可罚性而构成犯罪。从我国刑法的规定来看,经济刑法的主要构成部分是经济管理属性的行政刑法,具有经济行政管理属性的刑法条文是其重心。如我国《刑法》分则第三章中诸多罪名的设置,其规范对象大都属于经济领域的行政管理关系,应当认定为经济管理刑法。至于实体法条文设置的内容定位、体系布局是否妥当,另当别论。
(三)经济管理刑法主要保护溯源性超个人法益
虽然超个人法益概念本身的内涵还有待进一步细化明确,其立法批判和解释规制机能常受到质疑,甚至有人认为超个人法益不足以回应理论期待,呈现左支右绌、捉襟见肘的疲态。然而,运用超个人法益来界定经济刑法的概念和范围是近百年来经济刑法研究领域的主流进路。在实践中,超个人法益理论已经成为德国1977 年《选择草案》(Alternativ-Entwurf)的理论基础,得到立法上的确认。
经济管理刑法保护的首先是溯源性超个人法益。溯源性超个人法益源自于个人法益的集聚,所有的溯源性超个人法益都可以追踪到个人法益根据。此时,溯源性超个人法益与个人法益是一种“手段—目的”的关系,即前者作为手段不能反超目的具有独立的保护价值。〔25〕参见涂龙科、郑力凡:《经济刑法法益二元“双环结构”之证成、判断与展开》,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0 年第6 期。在溯源性超个人法益的框架内,抽象的秩序或制度确有维护的必要,但最终目的应是促进作为个体的消费者利益。在消费者利益没有被侵害或具有侵害危险时,即便秩序或制度被侵害或存在侵害的危险,仍不应认定为犯罪。〔26〕参见[日]林幹人:《现代经济犯罪——法的规则研究》,日本弘文堂1989 年版,第55-56 页。在立法上,此类犯罪的构成要件设置为个人利益侵害,而非抽象的制度违反。我国刑法分则的条文表述如“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等。侵害溯源性超个人法益的具体罪名如我国《刑法》第141 条生产、销售假药罪,第142 条生产、销售劣药罪,第219 条侵犯商业秘密罪等。溯源性超个人法益是经济管理刑法的主要保护法益。
经济管理刑法也保护独立性超个人法益。所谓独立性超个人法益,指本身具有独立的保护价值,不直接和个人法益发生关联、无法追踪个人法益根据的法益类型。例如,走私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外汇犯罪、证券、期货犯罪等)等犯罪行为并不针对具体的投资者或消费者的经济权益,该类行为只是侵害了抽象的海关制度、税收制度、金融体制等制度性法益。独立性超个人法益由于缺乏个人利益受损的现实根据而流于抽象。为防止对独立性超个人法益的过度保护导致对市场行为的不当干预,独立性超个人法益入罪的范围要予以严格限定,仅肯定重大性、基础性经济秩序属于刑法规制范围。〔27〕参见涂龙科、郑力凡:《经济刑法法益二元“双环结构”之证成、判断与展开》,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0 年第6 期。从我国刑法修正的历程考察,已有独立性超个人法益出罪的立法例。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将骗取贷款罪第一档法定刑对应的“其他严重情节”删除,修改之后,对于第一档刑罚,只有给银行或者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的才追究刑事责任,该处规定由行为犯与结果犯的结合变成了纯正的结果犯。除此之外,经济管理刑法还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调整,逐步实现部分行为类型的非犯罪化过程:其一,因市场抑制等市场自身缺陷原因而诱发的行为,如部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其二,急剧变动而社会危害性不确定的行为,如利用非法经营罪来规制新兴业态、新兴经济行为;其三,没有实质危害性的行为,如高利转贷行为。〔28〕参见涂龙科:《p2p 网贷与金融刑法危机及其应对》,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 年第1 期。
(四)我国经济管理刑法的实体法构成
作为我国经济刑法大本营的《刑法》分则第三章中的大部分刑法规范的前置法为经济管理法,调整对象是具有经济内容的行政管理关系。〔29〕参见梁慧星、王利明:《经济法的理论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6 年版,第213 页。具体而言,经济管理刑法涉及的罪名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市场准入管理经济刑法。此类罪名用以惩罚未经许可而擅自从事经营的行为,此处的“许可”是指工商营业许可之外的特别许可,意图保护的法益为“特定市场准入秩序”。例如,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就是这一类中的典型罪名。该类罪名也可用来保护某一行业的专属经营权。典型的罪名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目的在于保护银行等持牌机构在吸储业务上的专属经营。又如,我国《刑法》第225条规定的非法经营罪的目的在于保护特定机构的专营专卖权。不少国家和地区对于市场准入秩序的刑法介入持较为谨慎的态度,对于违反市场准入秩序的行为,大都在行政处罚(或者是违反秩序罚)的范畴内予以处理。第二,市场基础管理经济刑法。市场基础管理秩序如税收、知识产权、证券、期货等框架性的市场基本经济制度。市场基础秩序的意义在于建立作为市场基础的“四梁八柱”,为市场的形成与运行提供根基性的制度平台。市场基础管理秩序与市场主体在微观层面的生产、经营活动无直接互动,而是提供宏观层面的制度支撑,其建构的市场环境是市场运行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我国《刑法》分则第三章有大量罪名用以保护市场基础管理秩序,如逃税罪、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伪造货币罪等。经济刑法中的财税刑法和海关刑法两个分支领域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是经济刑法中在教义学意义上特别成熟的分支部门。〔30〕参见[德]克劳斯•梯德曼:《德国经济刑法导论》,周遵友译,载《刑法论丛》(2013 年第2 卷),法律出版社2013 年版,第11 页。第三,市场运行管理经济刑法。市场基础管理秩序是静止的基础性的制度安排,市场运行管理秩序则是动态的市场秩序,包括市场主体在生产、经营等活动中应当遵循的管理秩序。市场运行管理秩序属于管理秩序,容易与市场交易秩序相混淆,但两者性质有本质差异。市场管理秩序的一方主体为行政机关,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实质为行政管理关系,而市场交易秩序发生于平等市场主体之间,两者之间是源于市场交易的合同法律关系。比较典型的侵犯市场运行管理秩序的罪名如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等。第四,市场组织(如公司、企业)管理经济刑法。该类犯罪行为破坏的是市场主体本身的设立、存续、消灭制度。典型的罪名如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罪,妨害清算罪等。应当说明的是,此处的市场主体主要指非国有的公司、企业,也包括部分的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在成立特定的渎职类犯罪时)。
三、经济调节领域刑法有待立法扩张
如前所述,认为经济法的调整范围应当限定为经济调节法是近年来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之一。如有学者认为,经济法是国家调节经济之法,其基本任务和立法宗旨在于经由法律规范的国家调节,影响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运行,实现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并进而促进社会公平的目标。〔31〕参见漆多俊:《“国家调节说”的形成和发展——我的经济法学术之路》,载《河北法学》2008 年第12 期。经济法具体包括三种基本调节措施,即国家直接参与某些民间资本不愿进入的投资经营领域;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以排除市场障碍;国家运用计划和财政税收、金融等经济政策对社会经济实行引导、鼓励或约束等宏观调控。〔32〕参见漆多俊:《中国经济法理论创新及其同实践的反差》,载《江汉论坛》2015 年第7 期。学界一般认为,第一种调节措施领域(国家投资)发生的犯罪为职务犯罪,不认定为经济犯罪,所以本文主要探讨排除市场障碍和宏观调控两个领域中经济刑法的范围。
(一)经济调节刑法主要保护独立性超个人法益
独立性超个人法益是独立于个人法益,但并非与个人法益完全无关的抽象概念。独立性超个人法益与溯源性超个人法益有实质性不同,具有独立于个人利益之外的刑法保护价值。独立性超个人法益虽然从静态上无法直接“溯源”为个人法益,但是在保障个人法益实现的动态过程中,间接与个人法益产生联系。〔33〕参见涂龙科、郑力凡:《经济刑法法益二元“双环结构”之证成、判断与展开》,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0 年第6 期。经济调节刑法保护的是独立性超个人法益,根源于前置的排除市场障碍法的调整对象的特殊属性。排除市场障碍法在适用中,大多并无直接的被害人或被害单位。相应,排除市场障碍刑法的保护法益也不直接表现为具体的个人或单位的利益,在法益形态上呈现出明显的抽象性和独立性。排除市场障碍经济刑法的典型条文如我国《刑法》第222 条虚假广告罪等,此类犯罪行为并不直接侵害具体个人或单位的利益,没有明显、直接的被害人,而仅仅是对抽象秩序的违反。
排除市场障碍刑法主要保护独立性超个人法益,但并非与个人法益毫无瓜葛,绝对抽象的超个人法益并不存在,超个人法益的抽象程度有高有低,在抽象程度低的场合,甚至可以表现为众多的个人法益的有形集合。
(二)经济调节领域不应当是经济刑法立法的重心
国内有观点认为,从管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背景下,经济刑法也应当随之做出调整,实现从管制经济刑法观向自治经济刑法观转变,与此同时,经济刑法保护的法益重心也应当相应调整,树立国民权益与经济秩序并重的新法益观。〔34〕参见张小宁:《经济刑法机能的重塑:从管制主义迈向自治主义》,载《法学评论》2019 年第1 期。该观点主张的经济刑法重心应当转移是近年来国内经济刑法理论界的重要思想倾向。国外也有文献认为,调控法领域许久以来都是经济刑法的核心。〔35〕Vgl.Baumann,in: Festschrift For Oehler,1985,S.91 ff.;Tiedemann,Kartellrechtsverst613e und Strafrecht,1976.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经济刑法重点转移,是否意味着经济调节应当成为经济刑法的立法重心?实际上,上述国外文献中使用的“调控”一词与本文的“宏观调控”在含义上有根本不同。国外文献中的“调控”一词在手段上包括两种方式。一是反限制竞争法规定的对限制竞争、滥用市场垄断地位等行为的规制。二是关于许可企业从事经济活动以及许可其退出市场的规定,如特殊企业的设立和破产刑法。可以看出,国外的“调控”一词的含义实际上既包括概括、宏观、与具体相对人无涉的宏观调控,也包括排除市场障碍和部分经济行政管理。事实上,从德国、日本的经济刑法立法来看,纯粹的排除市场障碍领域的刑事立法并不居于刑事立法的重心。以德国为例,经济调节领域中的价格立法在当今德国已经意义不大;特别是国家实施的定价现在仅限于少数几个特殊领域,如能源、交通、保险行业,以及医药法和医院法等,〔36〕Vgl.Baumann,in: Festschrift For Oehler,1985,S.91 ff.;Tiedemann,Kartellrechtsverst613e und Strafrecht,1976.更遑论刑事立法。在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领域设立的刑事罚则条文,远不能和行政管理领域的刑法条文数量相比。因此,笔者认为主张经济刑法的重心应当加以调整的观点并不足取。
笔者虽然认为经济刑法的现行立法的重心偏向并无不妥,但并不意味着经济刑法条文完美无缺。检视现有经济刑法条文,确实存在如下弊端:经济管理条文过多、经济调节领域刑法立法供给不足;经济管理刑法干预过宽,经济调节刑法保障不足等。在立法完善方向上,总体上应当有进有退,一方面在经济管理刑法领域废除部分刑法条文或部分罪名;另一方面在经济调节领域推动犯罪化,增设罪名。犯罪化主要表现为排除市场障碍领域的入罪化,如滥用市场垄断地位等行为的刑法逐渐介入、扩张趋势,以实现对市场秩序的有效监管。〔37〕参见涂龙科:《p2p 网贷与金融刑法危机及其应对》,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 年第1 期。
(三)宏观调控领域没有经济刑法
宏观调控法的调整对象是宏观调控所引起的直接社会利益关系的变化,如国家和宏观调控部门与市场主体之间、市场主体与市场主体之间、市场主体与公民等社会一般主体之间等利益关系的变化。〔38〕参见徐澜波:《宏观调控的政策调整与法律调整之辨》,载《法学》2010 年第11 期。宏观调控领域的典型立法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法》等。宏观调控的手段包括价格、预算、税收、汇率等。宏观调控和经济行政管理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如无论是经济管理法还是宏观调控法,一方法律关系主体必然是国家,是国家在经济管理或宏观调控中形成的法律关系。同时,两者之间也有本质的区别。宏观调控不直接针对市场主体的具体行为,宏观调控实施者并不通过具体行政行为直接作用于具体的行政相对人。例如,在通过税收或价格手段实施的宏观调控中,政府的调控行为是概括的、宏观的,不针对具体的市场主体,也不专门就特定市场主体赋予特定的权利和义务。经济管理法则与之相反,总是针对具体的行政相对人,规制的对象是行政相对人的具体行为。宏观调控法由于不涉及相对人的具体行为,与刑法基于“行为”的规制体系本质上不同,因此,宏观调控领域不存在经济刑法。
(四)国外排除市场障碍领域刑事立法
如果把经济法的范围限定于经济调节法,那么只有以经济调节法为前置法的刑法规范,才是名实相符的“经济刑法”,除此之外的经济领域的刑法条文,只能是行政刑法或市场交易刑法。从比较研究的视角看,以排除市场障碍法为前置法的刑法(具体表现为经济刑法)古已有之。如为了规制享乐品进出口,1512 年的帝国决议(Reichsabschied)依据帝国的谷物暴利规定,将滥用垄断地位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因而形成了一种卡特尔(刑)法。〔39〕Vgl.K.Vogel JZ 1958,112,m.N.近现代以来,将违反排除市场障碍法的行为作为犯罪处罚的立法例,在国外立法中更为常见。如《德国刑法典》第298 条规定的严重限制竞争行为,以及《德国反限制竞争法》第81 条规定的“违反秩序行为构成要件”(该法没有规定犯罪构成要件,只规定了“违反秩序构成要件”),其目的都在于通过防止市场主体滥用垄断地位,维护良好的市场竞争秩序,从而实现对竞争体制的保障。此外,上述条文的立法意义还包括禁止通过卡特尔协议哄抬物价的行为,保护个人的经济自由;禁止以合同方式以及以其他合谋的方式实施的限制竞争的行为等,这些都属于排除市场障碍的范畴。日本也有反垄断入刑的立法例。例如,日本《反垄断法》第89 条以下规定了应当予以处罚的行为类型,多数的行为类型既是行政法的规制对象,也是刑事制裁的对象。该法制定后,直至20 世纪60 年代一直处于闲置状态。20 世纪70 年代,因石油危机产生了石油卡特尔事件,开始引发司法系统和学界对该法的关注,并陆续出现少量的相关案例。然而,在之后十年,日本《反垄断法》的适用又陷入停滞状态。至1993 年,日本修改《反垄断法》,其中刑事处罚得以强化。这次修改的重点是日本《反垄断法》第89 条(垄断、不正当交易限制以及竞争限制),明确构成相关犯罪的可以适用该法第95 条“双罚规定”。〔40〕参见尹琳:《日本经济刑法的现状与问题——兼论日本法人犯罪的类型、特征》,载《经济刑法》(第1 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年版,第288 页。在日本的立法实践和学术理念中,排除市场障碍领域经济刑法的目的在于实现和保护作为经济交易的基本价值的自由市场经济以及作为市场主体的消费者的利益。
(五)我国排除市场障碍刑法干预范围的应然扩张
在我国现行刑法中,滥用垄断地位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我国《反垄断法》制定时,对于垄断行为是否应当入罪,各方曾经有过争议。有观点认为,市场竞争秩序应当属于市场经济秩序的一部分,因此垄断行为也应当予以犯罪化处理。〔41〕参见胡学相、尹晓闻:《垄断行为刑法规制的法理分析》,载《广东社会科学》2016 年第2 期。但是,立法者最终并没有采纳入罪的建议。在新的经济社会环境下,有学者认为,如果说在我国《反垄断法》出台前,行业集中的程度普遍偏低,垄断的社会危害不大,犯罪化的条件还不成熟,那么,如今对垄断行为予以犯罪化的条件已经完全具备。因此,刑法中有必要增设协议垄断罪、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罪和非法集中罪等三种垄断犯罪。〔42〕参见王良顺:《保护法益视角下经济刑法的规制范围》,载《政治与法律》2017 年第6 期。
虽然我国刑法在反垄断领域没有设立专门的罪名,但是对其他违反自由竞争秩序的行为有相应的罪名,例如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虚假广告罪等。此外,2020 年2 月12 日,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第二部分第四项明确规定,在疫情防控期间,违反国家有关市场经营、价格管理等规定,囤积居奇,哄抬疫情防控急需的口罩、护目镜、防护服、消毒液等防护用品、药品或者其他涉及民生的物品价格,牟取暴利,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依照我国《刑法》第225 条第4 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这一规定可以理解为刑法对价格领域的介入与干预。但从总体上而言,我国在经济调节领域的刑法条文依然较少,涵盖范围不全面,相关立法应当扩张。
四、规制平等主体之间纯粹交易行为的不属于经济刑法
我国《刑法》分则第三章规定的并不全然是破坏经济管理秩序的行为,也包括破坏经济调节秩序、破坏市场交易秩序的行为。市场交易秩序是平等主体之间在交易过程中形成的市场秩序,交易双方是平等市场主体,两者之间的联系纽带是合同交易关系,不存在一方对另一方的优势地位或强制性的法律效果。我国《刑法》分则第三章中破坏市场交易秩序的立法例,如合同诈骗罪、强迫交易罪等。
(一)经济自由不是经济刑法的保护法益
日本学者藤木英雄教授在反思战时统制经济时期经济刑法过于关注对超个人法益的保护的同时,对经济犯罪的概念和本质进行了反思性调整,他在《行政刑法》一书中提出,所谓经济犯罪,是指“在自由经济的体制下,滥用或乱用经济交易的自由,用各种方法引起市场经济的混乱,或者在具体经济交易中,给广大消费者和大众投资者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而使自己获取更大经济利益的经济活动,这种类型的经济活动是滥用自由而危害了自由经济体制的基础”。〔43〕转引自顾肖荣:《战后日本经济刑法和经济犯罪研究的演进》,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1 年第3 期。国内也有学者认为,“经济刑法的法益是市场平等主体的经济自由以及与此联系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国家公共利益。对于没有上述具体法益侵害或危险的行为,只是单纯违反了基于国家命令而形成的经济行政秩序的,应属于经济行政法调整的范围”。〔44〕何荣功:《经济自由与刑法理性: 经济刑法的范围界定》,载《法律科学》2014 年第3 期。此类观点将滥用经济自由导致的利益侵害作为经济犯罪的本质,该观点在批评现行经济刑法立法的基础上,认为经济刑法应当由现在的“秩序法益观”转向对经济自由的保护。上述观点因契合国内对“秩序法益观”的批判潮流,近年来在学界得到较多支持。有学者进而直白地主张,要建构与维护经济自由目标相适应的法律体系,中国经济刑法立法体系改造应当立足于扩大经济自由的目标,以期在实现经济刑法立法观念转型的同时,完成经济刑法立法体系的更新与调整。〔45〕参见魏昌东:《中国经济刑法法益追问与立法选择》,载《政法论坛》2016 年第6 期。
笔者认为,所谓的经济自由无论从其自身属性、学术发端的缘由等,都不能作为经济刑法的保护法益。首先,“自由”本身不具备作为法益的内在属性,如果用“自由说”来代替“秩序说”,经济刑法的法益必然会陷于更加虚无、空洞、抽象和不可把握的境地。类似“自由”等观念上的法益概念助长了把没有现实内容的抽象概念解释为法益的趋势,由此,必然会瓦解法益概念的刑法界定力量,进而影响其机能发挥 。〔46〕参见涂龙科、李萌:《左支右绌、捉襟见肘的经济刑法法益》,载《经济刑法》(第18 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 版,第12-13 页。其次,经济自由说的盛行源于对统制经济时代国家过度干预、管制经济的纠偏,并由此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成为实践与理论关注的焦点。但经济自由说本身不足以成为经济刑法研究的重心所在,规制滥用经济自由行为的刑法条文只是冰山上的一角,虽然易于引发关注,却不是冰山的主要组成部分,市场的基础和重心仍然应该是使其得以正常存在、运转的市场体制机制。
(二)经济刑法不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纯粹市场交易行为
经济调节领域、经济管理领域经济刑法的保护法益是超个人法益不难理解,但市场交易当中,发生于平等交易主体之间的犯罪行为与超个人法益之间是否存有关联?换言之,如果认为经济犯罪的本质是对超个人法益的侵害,那么,发生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市场交易保障刑法(如合同诈骗罪)是否属于经济刑法?笔者持否定观点,理由在于经济刑法不能宽泛地理解为保护经济法益的刑法规范,否则传统的财产犯罪就会被纳入经济犯罪。经济刑法应当是保护经济秩序的刑法规范,包括直接以经济秩序及其重要部门为保护对象的刑法规范和间接以经济秩序为保护对象的刑法规范,其法益是体现为超个人法益的经济秩序。〔47〕参见林东茂:《危险犯与经济刑法》,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 年版,第73 页。发生于纯粹平等主体之间交易的犯罪行为,其侵害的直接法益通常局限于个人法益,不存在超个人法益直接受损的情形,因此,不能认定为经济犯罪,也即民法是经济刑法的前置法,但民法前置的刑法条文只有部分属于经济刑法。
要在理论上证成上述观点,还有以下两个问题需要进一步加以厘清。
其一,如何准确理解纯粹的平等主体之间的市场交易?在我国《刑法》分则第三章规定的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罪中,销售者和买受者之间在形式上也属于平等主体。但是,学界一般认为该罪属于经济犯罪,如何解释?实际上,销售假冒伪劣产品中买卖双方关系与合同诈骗中合同双方关系并不相同。前者的前置法为我国《产品质量法》或《消费者保护法》,属于行政法或经济法,后者的前置法为民法。前者与制度性法益紧密相关,后者不存在此类情形。就具体交易场景来看,前者天然包容一对多的情形,危害众多消费者的利益;后者尽管也存在一人骗多人的可能,但就具体某一合同而言,却有明显的相对性和有限性。因此,本文的“纯粹的平等主体之间的市场交易”指发生于平等主体之间,和制度性法益无直接关联的交易。
其二,秩序的两种不同含义。日本有学者认为,即便在自由经济体制下,经济刑法的法益还是应当理解为“自由经济秩序”“竞业的公正和秩序”。〔48〕参见[日]神山敏雄、齐藤丰治等:《新经济刑法入门》,东京成文堂2008 年版,第5-6 页。此类观点是通过扩大“秩序”的语义范围来实现解释目的。合同诈骗罪等平等主体之间的交易能否理解为实施了某种秩序的侵害,并进而理解为对超个人法益实施了侵害,从而认为具有经济犯罪的属性?笔者持否定观点,虽然两者都表述为“秩序”,但是两个“秩序”的内涵有差别。经济管理秩序以及经济调节秩序中具有相关的制度依据,用以保护制度的有效性,平等主体之间的市场交易形成的“秩序”,更多限于当事人意思自治范畴,不表现为对制度的违反或侵害。
五、经济刑法范围的具体分析
(一)违反经济秩序的行为不属于经济犯罪
关于违反经济秩序的行为是否属于经济刑法的范畴,在理论上有不同的见解。有学者认为,经济刑法不仅包括真正的刑事法上的犯罪构成要件,而且包括其他规范。这些“其他规范”对于有关行为施加的不是狭义上的刑罚,而只是罚款。换言之,经济刑法也包含上述“其他规范”,即经济上的违反秩序行为。〔49〕参见[德]汉斯•阿享巴赫:《德国经济刑法的发展》,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 年第2 期。根据这种观点,前述的《德国反限制竞争法》中的犯罪与违反秩序行为,以及《德国法院组织法》第74c 条中所称大多数(附属刑法上的)其他犯罪构成要件,〔50〕参见[德]克劳斯•梯德曼:《经济刑法的概念和历史发展》,周遵友译,载《刑法论丛》(2016 年第3 卷),法律出版社2016 年版,第403 页。都属于经济犯罪。更多的学者持经济犯罪与违反秩序行为相区别的观点。“区别说”必然产生的理论课题是经济犯罪行为与违反经济秩序行为的区别标准及边界判断,这也是战后德国经济刑法或经济犯罪的理论争议热点。如果加以分类的话,大致有“质区别”理论、“量区别”理论、“折衷区别”理论、“废弃区别”理论等多种主张,且在各自的区别理论中也存在众多见解对立的地方。〔51〕参见[日]神山敏雄、尹琳:《经济刑法的理论框架》,载《经济刑法》(第1 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年版,第21 页。
从德国的立法实践来看,区分经济犯罪与违反秩序行为是20 世纪中期以来刑法改革的方向与潮流。1949 年第一部《德国经济刑法》不仅在其第6 条中通过著名的施密特公式列举了当时有效的经济刑法,而且引入了立法上区分经济犯罪行为和经济违反秩序行为的体系性方针。1952 年3 月25日《违反秩序法》将违反秩序行为的定义发展为当今使用的定义,即违反秩序行为是一种以罚款为其典型法律后果的行为。20 世纪60 年代至70 年代,德国推行经济犯罪改革运动,直接产生了相关的经济刑法,其中最显著的改革成果是轻罪的非犯罪化和违反秩序行为法的体系构建——违反秩序法的制定。从实体法规定看,经济犯罪与违反秩序行为无论是形式上还是实质上区分度都不够。在形式上,不可否认的是,没有一个经济部门不受到大量违反秩序法规则的规制。〔52〕参见[德]马克•恩格尔哈特:《德国经济刑法的发展和现状》,徐剑译,载《刑事法评论》(2016 年第2 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155 页。在实质上,犯罪和违反秩序法行为之间几乎没有实现合理区别;两者常常都保护相同的法益,比如金融市场的运行、消费者或者环境。当违反秩序法规制严重的有害行为时,不法经常被要求和刑法中的不法一样严重。〔53〕参见[德]马克•恩格尔哈特:《德国经济刑法的发展和现状》,徐剑译,载《刑事法评论》(2016 年第2 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155 页。
纵观学界在讨论违反经济秩序行为与经济犯罪行为的界限时,通常包括两个维度:行为危害性的大小、行为侵害的法益是个人法益还是超个人法益。从德国的立法来看,在区分违反经济秩序行为和经济犯罪行为时,最初是从量的维度,采用行为的危害性大小的标准,也即危害性大的归属于犯罪行为,危害性小的纳入违反秩序行为。在超个人法益概念盛行之后,法益属性的差异也被作为区分违反经济秩序行为和经济犯罪行为的标准。如日本学者神山敏雄教授认为:形式上的经济犯罪即制定法中规定的经济犯罪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侵害普通消费者的财产性、经济性利益的犯罪;第二类是侵害作为经济主体的企业、公共机关、商人等的财产性、经济性利益的犯罪;第三类是侵害国家的经济制度或行政作用、经济交易规则的犯罪。实质上的经济犯罪仅仅是指前两类,是指侵害具备预测可能性的法益的行为,第三类犯罪应当被归类为违反经济秩序的行为。对于只是违反经济秩序的行为,虽然制定法上规定为犯罪,但这是不妥的,理应从刑法中排除出去,降格为经济违规行为即可。〔54〕参见[日]神山敏雄、尹琳:《经济刑法的理论框架》,载《经济刑法》(第1 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年版,第19 页。该观点在区分经济犯罪和违反秩序行为时,只考虑了“法益属性”标准,而不论其“危害性大小”。实际上,采用“危害大小”或“法益属性”中任何单一标准都不足以完全、准确区分两者,且不分先后同时使用两个标准会造成标准的不统一和区分结果的混乱。笔者认为,可以建立双层次区分标准,第一层次是“法益属性”标准,即罪名意图保护的必须是经济领域的超个人法益,用以界定经济属性;第二层次是“危害性大小”标准,在第一层次的基础上,危害性大的为经济犯罪,危害性相对较小的属于违反经济秩序行为。
(二)复合法益罪名的刑法归属
在经济刑法中,有的犯罪行为侵犯的法益并不是单一形态,而是两个甚至多个法益的集合。例如,我国《刑法》分则第三章规定的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罪等,其行为不单侵害了海关管理秩序,同时还可能危及公共安全或者国家安全。又如,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许多行为既侵犯了商标、专利等知识产权管理制度,也可能危害了权利人的个人利益。类似此类复合法益的罪名,在刑法中如何确定其归属,如何判断其是否属于经济刑法?
笔者认为,该问题要区分不同情形具体分析,以判断不同罪名的分类归属。一是数个超个人法益并存的场合。在该情形下,应结合刑法条文就立法意图保护的法益加以体系性判断,如前述的走私武器、弹药罪。有学者批评现行刑法,认为刑法规定的走私罪仅关注到行为所侵害的关税管理秩序,而将走私武器、弹药、核材料等危险物品的行为简单地纳入经济刑法,因其法益并非经济系统要素,而具侵害公共安全属性,导致经济刑法的立法失当。〔55〕参见魏昌东:《中国经济刑法法益追问与立法选择》,载《政法论坛》2016 年第6 期。实际上该观点值得商榷,走私武器、弹药罪评价的主要是走私环节的法益侵害行为,由于涉及武器、弹药,此类行为侵犯的法益会扩张至公共安全领域,但公共安全并不是该罪意图评价的。至于公共安全的法益保护,在走私环节之外,还有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非法买卖枪支、弹药罪等其他罪名,共同形成公共安全的刑法保护体系。二是超个人法益和个人法益并存的场合。例如贷款诈骗罪,通说认为本罪的保护法益既包括银行等金融机构对贷款的所有权,也包括国家的金融管理制度。〔56〕参见马克昌:《百罪通论(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296 页。此类罪名直接依据其中超个人法益确定其归属即可。可以追问的是,是否可以认为,即使是传统财产犯罪,如盗窃罪、诈骗罪等,在个人法益的背后也可能关联到所有权制度等超个人法益?此类犯罪行为首先侵犯的是个人法益,同时间接侵害超个人法益?笔者持否定观点,该论断及推理逻辑完全消弭了个人法益与超个人法益之间的界限,会导致两个概念的虚无化。
(三)环境犯罪应当属于经济犯罪
关于环境刑法与经济刑法的关系,国内外学界历来有争议。我国有学者认为,“从我国刑事立法的实际情况看,经济犯罪包括……分则第六章第六节规定的‘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57〕参见陈泽宪主编:《经济刑法新论》,群众出版社2001 年版,第13 页。环境犯罪破坏市场经济系统内的资源分配关系,侵害了基于生产秩序而形成的可期待性的经济利益,当属经济犯罪。〔58〕参见魏昌东:《中国经济刑法法益追问与立法选择》,载《政法论坛》2016 年第6 期。有学者同样从考察实体法的角度得出相反观点,认为破坏环境资源的犯罪,在我国《刑法》分则中列在第六章第六节,属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列为经济犯罪并不妥当。〔59〕参见顾肖荣:《中日经济犯罪概念和范围的演进》,载《东方法学》2008 年第1 期。
笔者对环境刑法归属于经济刑法持肯定态度,理由如下。首先,环境犯罪侵害的是超个人法益——生态法益。反对的观点认为,虽然环境资源包含土地等生产资料,其又是经济活动的基本要素,但是环境资源除了经济价值外,更有重大的生态价值,如果将环境犯罪调整到经济刑法之中,就意味着只从经济利益的角度为环境资源提供刑法保护,而环境资源内含的生态价值就被忽略,会降低刑法对环境资源的保护力度。〔60〕参见王良顺:《保护法益视角下经济刑法的规制范围》,载《政治与法律》2017 年第6 期。但事实上,认为经济刑法只保护经济价值是片面的,将环境刑法作为经济刑法的一部分,恰恰可以加强而不是削弱对作为超个人法益的生态法益的保护。其次,环境犯罪中可能涉及矿产、水资源、森林等经济利益,自然资源是一国最大的经济利益。〔61〕Vgl.Schaffmeister,Diskussionsbericht der Tagung für Rechtsvergleichung über Erscheinungsformen der Wirtschaftskriminalität und Möglichkeiten ihrer strafrechtlichen Bekämpfung,ZStW 1976,S.67ff.转引自林东茂:《危险犯与经济刑法》,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6 年版,第67 页。自然资源的经济属性,昭示了侵害环境资源类犯罪的经济属性,在超个人法益的框架内明确了其经济犯罪的定位。最后,将环境犯罪归属于经济犯罪也是国外许多国家的通行做法。德国1980 年3 月28 日《第十八次刑法修正法》在《德国刑法典》中整体性引入了环境刑法。该修正法将附属刑法中大部分惩治危害环境行为的刑法规范进行整合,将其作为第324 条至第330d 条放入《德国刑法典》分则第28 章,作为经济刑法的一部分。〔62〕参见[德]汉斯•阿享巴赫:《德国经济刑法的发展》,周遵权译,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 年第2 期。此外,在荷兰等其他国家,经济犯罪也包括环境犯罪。综上,环境犯罪在立法和理论上都应当归属于经济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