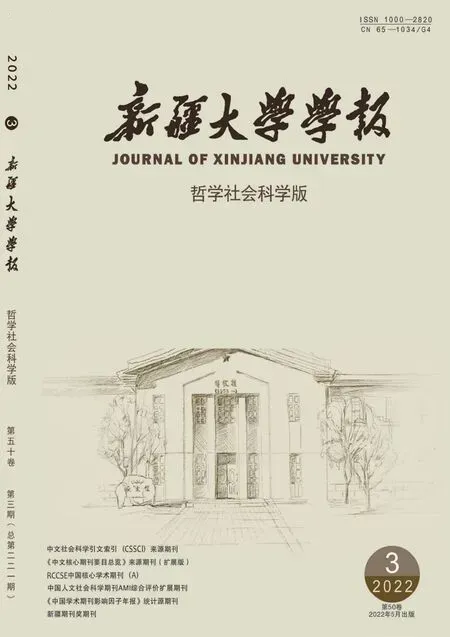扬雄汉赋:中西文明交流与互鉴之桥*
卢 婕
(1.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文学与艺术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72;2.四川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一、引 言
当代著名辞赋研究专家龚克昌认为“汉赋或许没有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那么辉煌……但她真实地表现了大汉帝国的气势,描绘了大汉帝国的精神风貌,她是我国古代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她为我国古代文学的发展繁荣积累了宝贵经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艺术表现手法”[1]36。由于中西文化传统的巨大差异,海外汉学家以“他者”的眼光研究扬雄汉赋时得出的结论与国内学者的研究结论呈现出明显的差异。中外扬雄汉赋的研究呈现出“根干丽土而同性,臭味晞阳而异品”[2]271的局面。从中外学者研究视角和观点的差异性分析中,可见西方文化模子和诗学传统对中国古典文学海外传播的重要影响以及扬雄作为中西文明交流与互鉴之桥的重要性。
二、扬雄之思想:醇儒还是非儒
中外学者就扬雄汉赋的文学性和思想性认识分歧最大的是《反离骚》。对于《反离骚》,中国学者往往给予负面评价。宋代朱熹认为“雄固为屈原之罪人,而此文乃《离骚》之谗贼矣”[3]。清代刘熙载认为“班固以屈原为露才扬己,意本扬雄《反离骚》”[4]。龚克昌认为“《反离骚》体现了扬雄性格的软弱和思想上潜伏的‘清静无为’的劣根子。《反离骚》中扬雄所言‘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更是体现出扬雄的思想境界和斗争精神不可与屈原同日而语”[1]358。中国学者对《反离骚》的批评并不以其文学价值而言,主要以其对屈原的态度为依据。历史上虽另有部分学者,如胡应麟和李贽等意欲为《反离骚》正言,也主要是从证明扬雄对《离骚》之反,乃是“爱原”之心,不是从其文学性来肯定其价值。中国学者在评价《反离骚》时,无不是受到儒家思想影响,以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入世原则作为最高准则。几千年的中国儒家思想深沉而静默地融入到中国文化血脉中,孔子“当为不当为”远比“可为不可为”更重要。这一思想在中国传统文人心中根深蒂固,因此扬雄《反离骚》中对屈原“何必湛身哉?”的诘问自然会被理解为消极避祸和苟且偷生的异端思想而备受批评。
美国的辞赋研究专家康达维对《反离骚》的态度却与众多中国学者迥异。在其1968年的博士学位论文中,他对扬雄的主要作品进行了系统完备的介绍和中肯的评论。康达维的研究并没有受到太多中国学者对《反离骚》的负面评价的影响,而是将它列为扬雄的众赋之首。在介绍《反离骚》时,他援引了《汉书·扬雄传》对扬雄创作《反离骚》的动机的说明,但是对于扬雄“摭离骚文而反之”这一行为,他评价到:“尽管贾谊也曾对屈原未能‘远浊世而自藏’微表异意,但是扬雄才是公开明确地赋诗反对屈原自杀的第一人。”[5]306-307他以刘勰之言为论据说明《反离骚》在中国从来没有被视为杰出的文学作品①刘勰在《文心雕龙·哀吊》中说:“扬雄吊屈,思积功寡,意深文略,故辞韵沈膇。”参见刘勰《文心雕龙》,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6页。。但是,他却认为“扬雄此诗的重要性主要依赖于其清楚发出对屈原自杀的‘儒家式’的反对之声”[5]314。他分析到:“在整个汉代,屈原被奉为儒家美德的典范,他的自杀也被认为是完全正义合理的。但是这与宣扬当时代与环境不利于实施个人理想抱负,或者没能遇到贤明君主时,君子最好不要参与政治生活的传统的儒家教条相悖。尽管在王莽的治狱使者前往天禄阁时他在仓促之间做出了投阁的决定,但是扬雄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倡导上述的儒家原则”[5]315。从他的论证来看,扬雄正是深受了儒家“穷则独善其身”的理念的影响才会反对屈原自沉。
在康达维看来,扬雄这篇在中国学者眼中严重违背儒家信念的作品却成了扬雄乃是坚定的儒家思想倡导者的明证。中美学者对扬雄思想的认识差异主要源于美国汉学家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西方人文传统中的“生命意识”“人本思想”和“个体精神”无时无刻不渗透在其治学的整个过程中。因此,在对中国儒家思想的接受中,康达维选择性地过滤了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思想,而吸收到的是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他对儒家思想的解读是经由美国思维和西方文化模子过滤之后变异了的东方哲学,并非中国儒家思想的全貌和原貌。因此,康达维对《反离骚》的“亲善”态度正是由于扬雄在这篇诗赋中反映出了一种西方学者非常推崇的个体意识和自由意志。
比起康达维而言,巴尼特·迈克尔(Barnet Michael)则以更直接的方式赞美了扬雄的个体精神。他认为:“扬雄珍视社会哲学家的职责——以解释人如何最好地适应有机整体为己任。他的有机主义概念并不严格地把人看作如动物一般被僵化在固定的生存或行为模式中的生命。相反,由于人拥有理性,人可以按照那些超越次人类(subhuman)的单调拘谨的生活理念和原则行事;人可以分析,然后掌握有机整体中的复杂性,通过其对整体的理解而提高其生存和成就的几率。”[6]从他的评价可以看出,西方把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与有机主义(organism)置于二元对立的思想体系中,而扬雄的思想尽管看重社会和国家的有机整体性,但却并不否定个人理性的价值,甚至认为个人理性的能动发挥有利于其个体生命的保存和事业理想的实现。扬雄的认识突破了二元对立的思维范式,将整体与个体融混合一,并行不悖,在迈克尔看来,这是一种伟大的东方智慧。然而,扬雄在《反离骚》中体现的这种高扬个体精神的思想,千百年来却被许多中国学者斥为“明哲保身”的软弱与不作为。中美学者对《反离骚》的评价可谓是南辕北辙。事实上,由于扬雄思想的复杂多元性,中国历代学者在对其儒家思想的评价上曾陷入“醇儒”“变儒”与“非儒”的混乱中。美国学者对扬雄作品的独特解读或许可以作为我们理性地看待其思想矛盾性的“他山之石”。
中国学者受儒家思想影响而贬抑《反离骚》,海外学者却以儒家思想和东方智慧为名赞誉之。《反离骚》在中西文化的不同境遇展示了在西方文化模子的形塑之后,中国古典文化海外传播中的变异现象。正如叶维廉所言,跨文化研究首先要同时从此、从彼驰行,“能‘两行’,则有待我们不死守,不被锁定在一种立场”,“彼是(此)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钧,是为两行”[7]。因此,只有从此从彼,天钧两行,从东西不同的视角欣赏《反离骚》才能理解差异的价值。中美扬雄研究探异的尝试正好印证了叶维廉的观点:“比较诗学的差异性研究是要给文化交流的规则提供依据。”[8]
三、扬雄之创作:模仿还是超越
扬雄“四大赋”在题材的摄取、情节的安排、语言的运用上,几乎无不受到司马相如《子虚赋》和《上林赋》的影响。刘勰还认为《剧秦美新》中“诡言遁辞”和“兼包神怪”的特点也是“影写长卿”[2]200。此外,学界还认为《反离骚》和《太玄赋》是对《离骚》的仿拟;《解嘲》和《解难》在实质上是对东方朔的《答客难》的模仿。因此,在论及扬雄基于模仿而进行的文学创作时,国内学者多持否定态度,认为模仿是妨碍扬雄写作创造性和作品生命力的一大弊病。
然而尼古拉斯·莫罗·威廉(Nicholas Morrow Williams)在其博士论文《文字的锦绣:模仿诗歌与六朝诗学》(The Brocade of Words: Imitation Poetry and Poetics in the Six Dynasties)的摘要中提出:“写作必然涉及对早期样式的创造性模仿,甚至是对于成就最为显著的一些作家而言也是如此。从维吉尔到莎士比亚,从扬雄到李白莫不如是。”[9]abstract可见,他眼中扬雄对前辈赋家的模仿首先是“创造性”的,其次,扬雄的文学地位可与西方的维吉尔和莎士比亚,以及中国的李白相提并论。从其博士论文的摘要来看,威廉在言及扬雄时,毫无半点贬低之语,反而满是崇敬之意。在后文的论述中,他提到扬雄以模仿其前辈蜀人赋家司马相如而开始其诗赋创作生涯,他以班固在关于扬雄的评论为论据,证明扬雄实乃文学模拟之大师,而班固的评价开启了东方学者对扬雄模仿技艺的共识——模仿是扬雄文学创作中开创性的一体两面①班固认为:“(雄)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参见班固《汉书》卷八十七下《扬雄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575页。。他在文中以1993年沈冬青的著作《扬雄:从模拟到创新的典范》、2003 年陈恩维的论文《试论扬雄赋的模拟与转型》以及日本学者谷口洋(Taniguchi Hiroshi)的论文《扬雄“口吃”与模拟前人》(该文收录在《二十一世纪汉魏六朝文学新视角:康达维教授花甲纪念论文集》)为例,证明在中国学者眼中,“扬雄的模仿只是其创作历程中走向原创性之前的一个阶段”[9]43。笔者认为这一结论还有待商榷,因为,以上三位学者的观点均是在20 世纪末至21世纪初期才提出。威廉忽略或者故意遮蔽了一个事实——从汉代以来到20 世纪80 年代,中国学界对扬雄“复古主义”的模仿之举是抑甚于扬的。比如,清代唐晏就认为:“子云为学,最工于拟……计其一生所为,无往非拟。而问子云之所自立者,无有也。”[10]他是中国古代文人中因扬雄好模仿而病之的典型代表。
威廉认为扬雄选择模仿前人作品时,并不仅仅只是将其作为一种文学锻炼或才思的炫耀。相反,他按自己的需求对过去的一些文学样式加以变形。他所有的作品都与其模仿对象有明显的差异,其中差别最为显著的是《反离骚》。尽管它是对《离骚》的模仿,但它同时亦是一首“翻案诗”(palinode),是对《离骚》的主要思想的反驳。另外,他还认为《反离骚》并非只是独一无二的模仿之作,而只是中国汉代模仿传统和哀悼屈原的文学中的一部分。从贾谊的《吊屈原赋》到王逸在《楚辞章句》中增入的《九思》,汉代的文学模仿传统已经根植在中国文化和思想深处,扬雄只不过是其最为形象化的代表而已。汉代是儒家思想的巅峰时期之一,扬雄之类的学者看重对圣人智慧的维持与传扬。这样的文学背景自然有利于文学模仿,扬雄只不过恰好将之发挥到了极致。因此,对扬雄创作中的模仿行为的评价应该回归其所处的历史中给予公正的评价,而不应以当代的文学背景绑架扬雄而对其作品妄加评说。威廉从新历史主义的立场要求还原历史,全面而客观地理解历史人物的行为选择。他的观点对于重论扬雄在中国赋学的地位极有启发意义。
威廉反对王隐以“屋下架屋”来批评扬雄对前人的模仿。他引用《释名》对“文”的定义来批驳“屋下架屋”之说②刘熙在《释名》中指出:“文者,汇集众彩以成锦绣;汇集众字以成辞义,如文绣然也。”。他说:“以锦绣来比喻作文非常贴切,因为它可以延展扩张:你必须以丝线不断编织图案,才能编织出一段没有预设之限制的、越来越大的锦绣。”[9]48可见,在他眼中,扬雄通过模仿前人而创作的汉赋是一张可无限延展的锦绣,而不是屋下架屋的赘余。模仿在他眼中不但不是“毛病”,反而是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扬雄汉赋中的模仿痕迹丝毫不妨碍他与维吉尔、莎士比亚和李白等伟大文学家同列。在其博士论文的开篇,威廉用29 页的篇幅介绍了西方对“模仿”的看法。他首先引用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句子诗意地证明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对“陈”与“新”的辩证认识③威廉引用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74)中的诗句:“推陈出新是我的无上的诀窍,我把开支过的,不断重新开支:因为,正如太阳天天新天天旧,我的爱把说过的事絮絮不休。”。接着他将西方的“模仿”追溯到更久远的古希腊时期。柏拉图认为艺术是对现实的模仿。苏格拉底则认为我们对物质世界的认识是不全面的,是容易引起误解的,就像洞壁上的影子。与这些摇曳的形象相比,真实就像让人目盲的强光。因此,艺术是对模仿的模仿,与理想的形式有着两倍距离。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就是模仿的产物,文艺的共同特征就在于模仿,差别不过在于模仿所用的媒介不同,所取的对象不同,所采用的方式不同而已。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出的关于模仿的观点甚至被总结为“摹仿说”,对西方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后世学者将其概括为:文艺起源于模仿,文艺是模仿的产物,模仿是文艺的特征。因此,在西方学者看来:艺术与模仿具有先天的重要联系,文学作为艺术的表现分支,本身就是对现实的模仿。在西方诗学传统的影响下,威廉不仅不认为扬雄之模仿为弊病,反而觉得这是一种了不起的才华。
威廉以西方的模仿传统力证扬雄文学模仿的合理性,他认为“模仿”对于扬雄的汉赋创作而言是功大于过的。然而,长期以来,中国本土学者却认为扬雄基于模仿的汉赋创作方式是弊大于利的。直到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侯立兵在《汉魏六朝赋多维研究》中指出:西汉后期从扬雄开始至东汉时模拟之风昌盛虽然与文学的经学化不无关系,然而文学演进还有其自身的规律性。首先,“魏晋南北朝社会的变迁不能彻底改变文学观念对传统重视,尤其是对前人经典作品的尊重,所以,赋作的模拟风气时有消长,但是作为创作惯性并不能也没有止步”[11]96。事实上,既然扬雄提倡文学创作的“原道、征圣、宗经”审美原则,他本人对之身体力行也就不足为怪了。其次,“在模拟典范中超越前人,同时也超越自我,从而在创作中获得满足感和价值感,这就是赋作模拟现象频繁发生的不竭心理动因”[11]97。在他看来,崇经尚古的社会环境和炫学逞才的心理动机导致了扬雄的“模仿”之举。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扬雄绝不仅仅只是一位前人眼中的“模拟大师”,他的开创性精神和超越性可以在多篇赋作中找到印证:(一)比起司马相如,扬雄的四大赋在思想内容上讽谏之意更为明白直率,在艺术上也突破了司马相如大赋的体制。(二)与东方朔相比,扬雄对现实的批评更为深刻,情绪更为愤慨。(三)扬雄对赋做出了独有的开拓。扬雄的《逐贫赋》把“贫”拟人化,以诙谐的笔调描写“贫”如影相随,而自己从希望摆脱它到逐渐认识到“贫”为自己带来种种好处。这篇小赋选题别致、构思新奇。因此得到钱钟书先生的高度评价①钱钟书认为:“后世祖构稠叠,强颜自慰,借端骂世,韩愈《送穷》、柳宗元《乞巧》、孙樵《逐痁鬼》出乎其类。”参见钱钟书《管锥篇》(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61-962页。。(四)扬雄的《蜀都赋》还是我国都城赋的先声。从这些赋作来看,扬雄不仅只是简单模仿屈原、司马相如和东方朔等人,他在赋作的传统体式和题材对前人的超越是无需置疑的。
从中外学者对扬雄赋作中出现的模仿行为的解读来看,海外汉学的论证基础是中西文学的模仿传统,对扬雄的模仿大加赞叹;中国学者对扬雄善模仿的评价则经历了先抑后扬的过程。人们普遍认为扬雄模仿前人的原因主要在于崇经尚古的社会环境和炫学逞才的心理动机。两国学者的见解同中有异,各有所长,需互为补充方能形成对扬雄模仿行为公正客观和全面圆通的评价。
四、扬雄之赋论:知人论世还是文本细读
中国学界通常按扬雄对赋的态度的变化而把他的文学创作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扬雄在《法言》中认为赋的功能是“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12]30。《汉书·扬雄传》记载扬雄认为汉赋“劝而不止”,“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于是辍不复为”[13]。中国学者对于扬雄“悔赋”的言论多是从赋学与经学之间的对立来分析。冯良方认为从扬雄一生的著述来看,“他的前半生主要是赋家,后半生主要是经学家”[14]。扬雄“悔赋”这一汉代文学史上的大事件正好印证了西汉后期赋学的式微与经学的昌盛。解丽霞在《扬雄与汉代经学》中总结扬雄辍赋的三个理由:一是赋“劝而不止”的功能丧失;二是“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的角色危机;三是“辞人之赋”“诗人之赋”“孔门经典”的法度不同②参见解丽霞《扬雄与汉代经学》,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5页。。总的来说,中国学者更倾向于将扬雄悔赋的行为放置在西汉末年宏大的社会和文学背景中,得出的结论是扬雄在社会和文学发展潮流中,受到外力的挟裹和揉搓,不得不放弃汉赋而转向《太玄》和《法言》等被刘歆担心“恐后人用覆酱瓿也”的著述。中国学者的研究范式是一种韦勒克(René Wellek)所言的“外部研究”。
西方学者更倾向于采用文本细读的方式,在文本的封闭领域之内体会扬雄思想和态度转变的细微征兆。在《慢读的艺术:将语文学运用于中国古典文学读本研究》(The Art of Reading Slowly:Applying Philology to the Study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ry Texts)中,康达维引用了尼采的一段名言:“语文学是一门让人尊敬的艺术,要求其崇拜者最重要的是:走到一边,闲下来,静下来和慢下来。”[15]康教授的“慢”除了不急功近利的治学心态之外,还包括了一种“慢工出细活”的研究方法。作为成长于20 世纪中期的西方文学研究者,康达维接受了大量“新批评”所提倡的“文本细读”的学术训练。这些早期的训练对他日后的汉赋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对扬雄悔赋行为的分析更多地来源于对扬雄留下的文本资料的考证和钻研,而不是以社会因素和时代背景为基础的由外而内的推测。
康达维认为扬雄晚年的兴趣从文学转向哲学,但是对哲学的兴趣并没有阻碍他继续深入对文学,尤其是对赋的思考。他发现扬雄是一位保守的儒家,他对文学的观点收在《太玄》和《法言》中。因此,他主要在这两部作品中分析扬雄悔赋的原因。首先,在对扬雄《太玄》中关于“文”的四笔符号(tetragram)的阐释中,康达维引用了扬雄的重要观点:“阴敛其质,阳散其文,文质班班,万物粲然。”[16]然后,他逐一对扬雄从“初一”到“上九”等关于文质关系的论证进行翻译和解读,最后总结到:尽管扬雄是以神秘的、非体系的方式表达了自己认为“文”与“质”应该达到完美和谐,但实际上他倾向于认为“质”重于“文”,这就如同祭祀时穿的服装,它们不仅仅只是复杂的工艺品,更重要的是它们在仪式中具有的功能。另外,康达维还分析了《法言》中的类似思想。他引用扬雄与他人的一段关于“文是质非”的对话来证明扬雄的文学观是以“质”为文学核心的。《法言》记载有人问扬雄:“有人焉,自云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门,升其堂,伏其几,袭其裳,可谓仲尼乎?”而扬雄答到:“其文是也,其质非也。”[12]45康达维认为扬雄借这个例子说明了语言在形式上的精美和复杂结果只能导致意义的迷乱,因此它需要有一定的规范并受到某些限制,为了形式而形式的追求是不能容忍的。而对于扬雄在《法言》中关于赋乃“童子雕虫篆刻”的论断,康达维则提出这段话体现了扬雄对诗歌的两种看法①此处康达维所论及的诗歌是包括了赋在内的广义的韵文。。其一,诗歌是教化的工具,主要用于劝说;其二,诗歌是一个审美对象,主要关注对语言富有艺术性的运用。扬雄在劝说性和修辞性的选择中偏向前者,因此他晚年放弃了赋的创作。除了《太玄》和《法言》,康达维还在扬雄的晚期诗赋中寻找他悔赋的蛛丝马迹。比如,在分析《羽猎赋》时。他指出这篇赋是叙事、描写与修辞的混合体,另带有一些魔幻与奇妙色彩……扬雄巧妙地创作了这篇赋,将劝说的意图隐藏于叙述和描写之后,这么一来,赋原来所具有的修辞性效果大大削弱了。正因为如此,扬雄到了晚年否定赋是一种有效的道德劝诫的方法②参见康达维《康达维自选集:汉代宫廷文学与文化之探微》,苏瑞隆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89-97页。。从以上的论述来看,康达维对扬雄悔赋的动机的探索几乎全部是以扬雄流传的文字资料为唯一依据。笔者认为,康达维的研究方法一方面是受到他早期接受的“新批评”教育的影响,另一方面则出于无奈,作为一位海外汉学家,在面对中美客观存在的巨大文化差异时采取的权宜之计。
除康达维之外,1983年美国的华裔汉学家、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亚洲语言文学系的中文教授施友忠(Shih, Vincent Yu-chung)在其专著《文心雕龙:中国文学中的思想与形式研究》(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A Study of Thought and Pattern in Chinese Literature)的序言中也探讨了对扬雄悔赋的认识。他认为早期扬雄对赋的纯粹的美(sheer beauty)与单纯的愉悦(pure delight)的欣赏说明扬雄意识到不可界定的直觉(intuition)或者视界(vision)是所有艺术的来源③See Vincent Yu-chung Shih.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A Study of Thought and Pattern in Chinese Literature.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83,p.xix.。然而后来扬雄对辞赋的态度的改变主要是由于其“好古”的古典主义批评立场。任增强在对施友忠的研究进行再研究后得出结论:施氏主要应用了“文本细读”的方法进行汉赋批评思想研究。他通过扬雄一系列批评话语的细读找到了大量扬雄尊儒复古的证据,然后以比较诗学的视角将扬雄与西方的斯卡利杰(J.J.Scaliger)、约翰逊(Samuel Johnson)与蒲柏(Alexander Pope)进行求同,认为他们都成功地通过吸取经典而使古典意识及与之产生的古典文学趣味在后代人思想中得以强化④参见任增强《美国汉学界的汉赋批评思想研究》,《东吴学术》,2011(4):144-147。。
20 世纪50 年代美国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理查兹(I.A.Richards)提出一个盛极一时的假说。他认为“诗不过是一种透明的媒介,通过它我们就可以观察诗人的种种心理过程:阅读仅仅是我们在自己心中重新创造出作者的精神状态”[17]。事实上,这样的批评方法是把一切文学归结于一种隐蔽的自传,文学是间接地了解作者的途径。从以上分析来看,康达维和施友忠对扬雄悔赋的分析无疑遵循了美国流行的新批评的研究范式,他们将《太玄》《法言》《羽猎赋》以及其它扬雄的留下的文字资料当作了解作家思想变化的最可靠途径,在深度介入这些文本之际,探索扬雄关于文质关系的思考以及关于赋的修辞性与劝说性的对立关系的思考。他们以韦勒克所提倡的“内部研究”的研究范式找出了扬雄悔赋的心理动机。
与美国学者青睐的“纯文本”的“文本细读”研究方式不同的是,中国学者受到孟子“知人论世”的文学研究传统影响,倾向于经由“作者介绍”和“时代背景分析”而演绎出“中心思想”和“主题”。因此中国学者多以西汉的赋学与经学发展走势、扬雄在仕途和治学的跌宕命运为重要依据,结合相关文献资料探寻其悔赋的原因。中国学者通过“考年论人、考时论事”的方法分析扬雄的为人和心态,文史结合,力求从宏大的历史背景与具体的人物命运中剖析扬雄文学观念的转变。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的美国学者由于资料缺乏和新批评的盛行,多从文本内部探寻扬雄悔赋原因。而在进入21 世纪之后,由于中美文化交流活动的密切开展,中国学者研究扬雄的多维方法对美国学者产生了积极影响。2003年普林斯顿大学的柯马丁(Martin Kern)教授在《西汉美学与赋之起源》(Western Han Aesthetics and the Genesis of the Fu)一文中将扬雄悔赋的言行进行了时代语境的还原。柯马丁认为西汉末年中国政治文化领域出现了一场深刻的思想转型。在这一社会思潮大背景中,作为节制与适度的古典主义文化的重要倡导者,汉武帝奢华铺张美学的反拨者,扬雄对汉赋的批评并非是一种疏离和无偏见的行为,而是在利益驱使下所采取的一种话语方式。因此,“现有的关于汉赋的评价即便不是对赋的完全扭曲,也严重损害了赋的声誉”[18]。易言之,扬雄是出于服务当时帝国需要的目的,对赋进行了再阐释,并使后代批评家对汉赋产生负面认识。柯马丁的研究方法从细读扬雄赋论的相关文本入手,然后结合中国学者常用的“还原语境”的研究方法,揭示了扬雄悔赋言辞所体现的真实用意以及西汉末年的时代精神。2007 年,美国犹他州大学吴伏生发表论文《汉代的铺陈大赋:一个皇家支持下的产物与皇家的批评者》(Han Epideictic Rhapsody:A Product and Critique of Imperial Patronage)。他也借鉴了“还原语境”的研究方法,指出汉大赋的铺张扬厉的风格是赋家对君主以倡优蓄之的一种反抗。而扬雄晚年的悔赋言辞主要是由于他没有像枚乘和司马相如一样认识到辞赋的巨大魅力可以令君主恍然若失,使赋家能昂然面对君主的权威①See Wu Fusheng.Han Epideictic Rhapsody: A Product and Critique of Imperial Patronage.Monumentu Serica 55,2007,pp.23-59.。从以上分析可知,中西两种研究扬雄赋论的方法各有长短。
五、结 语
在现实语境之下,以“探异”的模式进行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就显得尤其重要。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以“同质性”为研究基础,以摆脱法国学派影响研究所导致的美国文学在世界比较文学研究中“失语”的窘境为目的。易言之,美国文学与欧洲文学之间的“间性”导致了美国学派以平行比较的研究范式彰显自己的话语权。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之间存在更为明显和巨大的“间性”,因此,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可以借鉴美国学派的平行比较来达成提升本国文化影响力的目的。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并没有满足于在方法论上的“洋为中用”,而是对平行比较的研究范式进行了创新:一改美国学派以“同质性”为平行研究的基础,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创造性地以“异质性”和“变异性”作为平行比较研究范式的基础。曹顺庆教授在《比较文学变异学》(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一书中,从跨语言、跨文化、跨文明三个层面论述了“异质性”和“变异性”对于当今处于“全球化”与“本土化”、“普世性”与“特殊性”的撕扯和焦虑中的比较文学研究的意义:中西文学产生于不同的文明,因此,其文学原则、文论话语和言说方式都具有根本性的差异。但是,通过交流与对话,双方可达到互释互证、互补互通之目的。②See Cao,Shunqing.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Heidelberg:Springer,2013,p.238.正是在这样的一种以“异质性”和“变异性”为基础的比较文学平行研究范式实践中,笔者发现:中外文学研究者成长于不同的文明,其浸染于中的文化模子和诗学传统的差异性导致中外学者对于扬雄之思想是醇儒还是非儒、扬雄之创作动机是源于模仿还是超越前人、扬雄之赋论应该通过知人论世还是文本细读而探索等问题的看法呈现出巨大的差别。中国作为扬雄研究的故国与发源地,一代代学者扪毛辨骨的研究硕果自然值得海外汉学家虔心求教,而海外汉学家独辟蹊径的见解、博学审问和取精用弘的研究方法也有诸多值得中国学者借鉴之处。无论中外学者在扬雄汉赋研究上存在多么巨大的分歧,对于中国的古典文学研究和海外汉学研究而言,中外扬雄汉赋研究的思想交汇和融合贯通都是双方打开新局面、取得新成果的必经之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交流互鉴是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人类始终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相遇相知中向前发展。”[19]扬雄汉赋正是中西文明交流与互鉴之桥,通过比较中外学者在扬雄汉赋研究中呈现的不同研究范式、视角和结论,中外扬雄汉赋研究有望实现“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