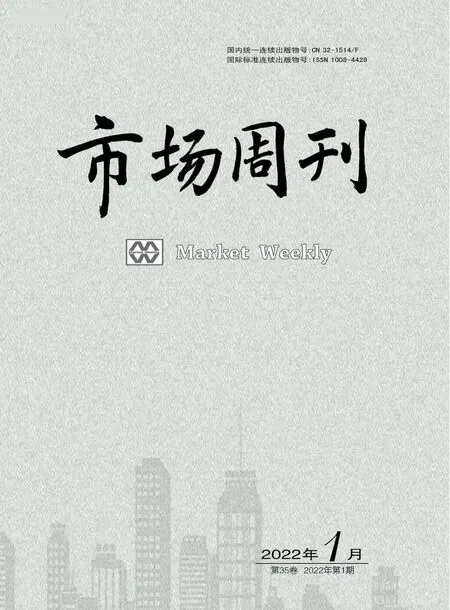论电商平台中知识产权恶意投诉的法律规制
林晓婷,黄秋艳
(广东财经大学,广东 广州 510320)
一、引言
在电子商务领域中适用“通知—删除”规则,有利于权利人以低成本的方式快速维权,但商品链接往往凝聚着大量的商业利益,这种低成本、高效率的维权方式也引发了大量的错误通知及恶意投诉。权利人仅需提交符合形式审查的通知,无须承担达到诉前禁令程度的举证责任,即可达到诉前禁令的效果。而被通知商家即便是成立反通知,链接重新上架,在大促期间已然错失商机,季节限定性商品、时令性商品更是如此。在电商平台“流量为王”的情况下,被投诉商家即使费时费力,前期投入的广告成本、积累的流量基础、商誉、销量排行的损失也难以挽回。
多数学者认为,15日等待期的规定直接导致了恶意投诉行为频发。除此之外,在电商领域的知识产权纠纷中,理论界与实务界对于平台所扮演的角色存在误读。电子商务法起草组认为,平台仅仅作为信息传达的信使。从实际情况来看,立法与司法实践发生了冲突。理论界对于平台所扮演的角色亦未达成一致意见,有的学者主张应对电商平台的权力进行限制,有的学者主张平台应实质性介入引导纠纷解决。
恶意投诉严重破坏了电子商务平台营商环境和治理环境。本文从相关的法律规定和案例入手,对电商领域不同属性的知识产权如何适用“通知—删除”规则进行研究,明晰电商平台在纠纷解决中扮演的角色,以期对规制电子商务知识产权恶意投诉提出建议。
二、恶意投诉的成因分析
(一)“通知—删除”规则的移植与发展
我国于2006年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引入“通知—删除”规则。2009年出台的«侵权责任法»又将“通知—删除”的适用范围扩大到了民事领域,明确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间接侵权责任。与«条例»适用于网络版权不同,«电子商务法»的“通知—反通知”规则扩大到了知识产权领域,规定了“反通知—恢复”规则。
目前,电子商务平台涉及的知识产权案件覆盖多个知识产权领域。由于平台的审查能力有限,对于发明和新型专利,直接根据专利权人的通知,很难对相关商品是否侵权做出初步判断。对此,有学者质疑,电子商务法将“通知—删除”规则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商标权、专利权等互联网侵权领域,赋予了电商平台与其审查能力不相匹配的义务。与物权等财产权相比,知识产权可以用作竞争的工具,滥用“通知—删除”可被用于损害竞争对手和竞争秩序。在电子商务领域,由于商品链接蕴含着巨大的商业价值,加上对商家造成的损害认定困难,对商家适用“通知—删除”规则造成的影响要比网络中被采取措施的作品传播者大得多,有些恶意投诉人便以“通知—删除”作为不正当竞争的工具。因此,不对权利属性加以区分,仅凭符合形式要求的通知就对被投诉商家采取屏蔽、删除、断开商品链接等严厉的必要措施,难谓合理。
(二)“通知—反通知”当事人权利义务失衡
尽管«电子商务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了错误通知责任和恶意投诉责任,但对于无辜的被投诉人,其实际效果无法与提交不侵权声明之后的及时恢复相比肩。在国内首例“反向行为保全案”中,丁某在天猫平台对曳头公司投诉不成立的情况下,再次投诉,平台遂下架了被投诉产品链接。反向行为保全能够有效防止被投诉人损失进一步扩大,弥补“15日”等待期规定的不足。在电商平台大促期间,反向行为保全能够快速解决被投诉人的燃眉之急。虽然反向行为保全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恢复链接,但在电子商务平台大促期间,恶意投诉多发的情况下,会给法院带来不小的压力。
«民法典»第1196条,将«电子商务法»中的“15日”改为“合理期限”,以便于电子商务平台和司法实践中根据具体案情确定采取必要措施的期限。究竟是适用«电子商务法»的“15日”规定,还是«民法典»规定的“合理期限”?对此,薛军认为,“等待期”制度不是强制性的要求,平台承担责任的前提,应是平台内经营者构成侵权。平台能够自主决定是否在15日期限届满之前,采取恢复措施。
(三)“通知—删除”规则——免责条款还是归责条款
«电子商务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平台为平台内经营者的行为基于过错的归责原则而承担连带责任,“过错”来自平台经营者对其承担的合理注意义务的违反。应明确,如果电子商务平台依据通知决定拒绝移除,即使被投诉人构成侵权,平台也并非当然承担侵权责任,其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应根据侵权法的规定和具体事实进行判断。
电子商务平台在这种争议中也十分纠结,在收到权利人通知后,平台扮演的角色究竟是“信使”还是“裁判者”?平台应该采取哪种标准对通知进行审查?若将该条款视为归责条款,平台为了避免承担责任,会倾向降低审查标准,仅对通知进行形式审查。«民法典»第1195条第2款规定“根据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和服务类型采取必要措施”,也就是说,平台收到权利人的通知后,扮演的角色不是“信使”,而是“裁判者”。符合形式审查的通知并不意味着平台内经营者就构成侵权,在平台内经营者不构成侵权的情况下,平台就无法构成帮助侵权。同时,未采取必要措施也并不意味着平台就存在过错。
因此,应当明确“通知—删除”规则是电子商务平台的免责条款而非归责条款。这样一来,平台经营者能够发挥主动性,对通知进行实质审查,具有技术优势、信息优势和治理效率,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维护电子商务平台内的营商环境是极为有效的。
三、认定恶意投诉行为的法律困境
(一)主观恶意的认定
一般认为,«电子商务法»中规定的恶意投诉中的“恶意”,仅包括故意,不包括一般过失。笔者考察相关电子商务知识产权恶意投诉的案件发现,实务中对主观恶意的判断,标准不一,出现了混淆错误通知与恶意投诉的情况,法官对于主观恶意的判断依据是:“通知人主观上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判定‘恶意’的主观要件是通知人主观上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对于错误通知和恶意投诉,法律分别规定了损害赔偿责任和加倍的惩罚性赔偿责任,不能以“应知”的可能性较大为依据而将其定义为恶意投诉。
(二)侵权损失的认定
在电商领域,平台内经营者为了打造爆款带动店铺的销售额,可能会付费进行竞价排名,或以低价销售的方式争取销量。经营者为了恢复店铺的营业,还需要支付额外的推广和技术服务费,无形的商誉损失的价值更是难以估量。平台内经营者的损失通常是抽象的,难以具体估量的。实务中,由于原告未举证证明其因对方行为遭受的损失,也未举证证明对方因此获得的利益,裁判者只能在综合考量各种因素后,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的规定,按照法定赔偿酌定赔偿数额。平台内经营者在经过一番斗争之后,未必能够弥补损失。即便原告能够证明店铺利润的损失数额,也难以证明恶意投诉行为是店铺营业额下降的唯一原因,损失在营业额上的体现只是一小部分,对于前期投入的广告成本、积累的流量基础、商誉、销量排行,以及时令性商品、季节限定性商品链接下架错过的商机、在“11.11”和“618”大促期间造成的店铺利润损失,这些损失更加难以计算具体数值。
三、规制恶意投诉的建议
(一)区分不同权利属性的处理模式
专利领域是否能够直接适用“通知—删除”规则,学界存在不同看法。李明德认为,专利权的保护范围需要专业的工作人员在严格的程序中加以确定、解释,例如审查员、法官或者行政执法人员,而网络交易平台显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王迁认为,“通知—删除”规则适用于网络环境中以信息形式传播作品的行为。网络环境中的专利侵权不是单纯提供信息,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产品技术特征的判断是缺乏能力的。在专利领域应适用“通知、转通知与移除”规则,或增加“反通知与恢复”规则。詹映对此持反对意见,认为应将“通知—移除”规则改为“通知—必要措施”规则。
笔者认为,对于不同的权利属性,应当适用不同的处理模式。对著作权和商标权侵权案件可以适用“通知—反通知”规则,对专利侵权案件应当适用“通知—转通知”规则。对于网络交易平台仅根据通知和初步证据,是难以直接判断侵权是否成立的。权利人发送侵权通知的成本很低,对被投诉人造成的损害成本却很高。正是由于移除性必要措施的规定,平台在明知权利人通知不成立的可能性较大的情况下,出于承担侵权责任的畏惧,只好将被诉侵权链接下架,逼得无辜的被投诉人只能向法院申请反向行为保全。尽管反向行为保全不失为一种及时有效的救助途径,却是一段“弯路”。专利侵权行为发生在线上还是线下并没有什么区别,那么维权途径也不需要有什么不同。平台作为中立的第三方,无须对通知进行实质审查,在接受专利侵权通知后,没有必要直接采取移除性的必要措施,仅需要直接将通知转送给被投诉人,将被投诉人的信息告知权利人,权利人就可以直接寻求司法和行政救济,情况紧急时可以申请诉前禁令。对于无辜的被投诉人,本来不需要承受产品链接被下架造成的损失,也不需要费时费力地申请反向行为保全,法院也不需要在电商平台大促期间紧急受理反向行为保全的申请。
对于专利侵权这种审判难度较大、专业性较强的案件,往往需要由专业的司法机关(如知识产权法院)进行审判。退一步说,即使平台对通知进行实质审查,也未必能够正确判断侵权行为是否成立。因此,专利侵权投诉的处理模式应区别于著作权、商标权,将不同的侵权投诉分开处理。
(二)等待期的灵活处理
«民法典»第1196条规定将«电子商务法»中的15日改为合理期限,以便于司法实践中根据具体案情确定采取必要措施的期限。«电子商务法»中关于15日的规定对于平台内经营者来说太长了,商家很容易因此失去商机。«民法典»的规定赋予了平台更多空间和模式,平台可以根据不同的权利人的特点设置不同的期限,更高效地解决纠纷。
(三)明确电子商务平台的法律地位
1.明确“通知—删除”规则为免责条款
首先,须明确“反通知—选择期间”这一规则应解释为免责条款,而非责任条款。电商平台如果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并不意味着被通知人就能对平台主张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平台的间接侵权责任,应以通知人的直接侵权行为为前提。该条款的本意不是为了打击主动介入纠纷解决的平台的积极性,平台掌握着充分的用户信息,可以更高的科技手段和制度创新对恶意投诉人进行打压,提高平台的竞争力。事实上,已有平台根据权利人投诉的特点采取相应的措施,例如阿里巴巴推出的支持产权投诉的分层机制,能够减少卖家损失,有效保障权利人的权益。
2.平台的损害救济
大量的错误通知和恶意投诉也会扰乱电子商务平台的营商环境和经营秩序,增加平台的审核负担,阻碍其发展。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了平台起诉恶意投诉行为的案件,淘宝公司起诉恶意投诉人,法院认为,恶意投诉人造成了平台正常的经营管理活动受到影响,客观上造成了平台管理费用等经营成本的增加。
«民法典»第1195条相较于«电子商务法»,在平台内经营者的基础上增加对网络用户服务提供者的损害救济。这样一来,平台也可以对错误通知人提起诉讼。平台相较于中小店铺的经营者,拥有更强的实力与恶意投诉人进行抗衡,且对于用户的信息掌握得更加全面,对证据的提取与保存有更多的优势。因此,平台能够有效制约恶意投诉人,降低恶意投诉的发生率。
(四)采取多元化、多层级的必要措施
«民法典»第1195条要求平台采取必要措施,依据侵权的初步证据和服务类型,这一规定意味着必要措施的多层次、多元化。«民法典»网络侵权规则中的必要措施可以根据措施的严厉程度分为三个层次:轻于“删除”的必要措施,如保证金制度;处于中间程度的标准和常规的必要措施,例如删除、屏蔽、断开链接;以及重于“删除”的必要措施,如“终止交易和服务”。例如,在衣念公司多次投诉的情况下,淘宝平台未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客观上放任了侵权行为的重复发生,应为此承担侵权责任。对于重复侵权的用户,平台应对其采取更加严厉的手段,例如关闭店铺,以达到制止侵权行为的目的。“刀豆诉百赞、腾讯案”和“乐动卓越诉阿里云案”,均体现了措施多层次及多元化的必要。平台在处理纠纷中,应采取多层次和多元化的必要措施,而不是机械式地根据通知采取删除措施。
四、结语
在电子商务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如何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促进知识产权的发展是个重要课题。恶意投诉行为不仅破坏了知识产权保护机制,还破坏了电子商务平台的营商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平台在实践中还要探索“合理期限”应如何确定,根据情况采取不同的必要措施。立法应细化平台对于不同权利属性的处理模式,鼓励平台自治。